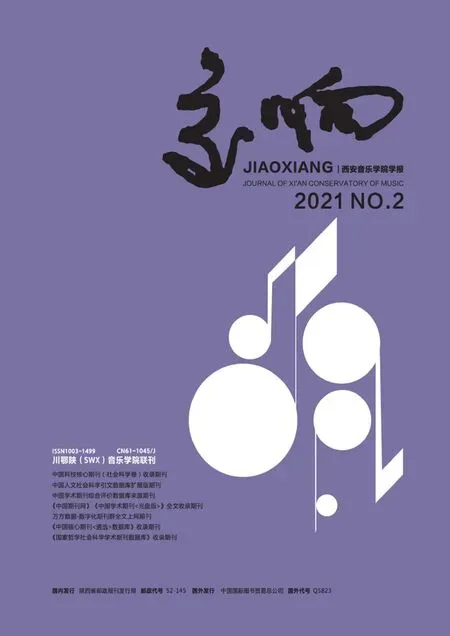徐孟东打击乐三重奏《练习曲I》的速度卡农技术探赜
●胡宝帅
徐孟东打击乐三重奏《练习曲I》的速度卡农技术探赜
●胡宝帅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210031)
《练习曲I》是徐孟东为打击乐三重奏而作的一部小型室内乐作品,该作品以九度六声人工音阶为音高素材,以异化速度为纵向关系,以点状织体为音色布局,以速度卡农技术为组织手段,构建出一部音响新颖、时间扭曲的打击乐重奏图景。现以该作品为研究对象,围绕其简约音高组织、陈述方式及其结构组织与点描技术的多重运用等方面作出细致研究。
《练习曲I》;速度卡农;速度比率;九度六声人工音阶
徐孟东的《练习曲I》()是应2021年上海“世界新音乐节”之委约而创作的一部卡农乐曲,确切而言是一部速度卡农(Tempo canon)作品。自20世纪以来,东西方音乐创作均呈现出复调思维与对位技术复兴之态势,如威伯恩在《目前新音乐道路》(1933)中提到:“我们看到一个脱离主调、回到复调的独立运动”[1](P72)。随着共性音乐写作时期传统调性音乐风格的逐渐瓦解,复调思维及其技术运用在现当代音乐创作中愈发重要。在《练习曲I》中,徐孟东为了突出纵向关系的速度对峙音响特征,采用古老卡农与时间性思维相结合的现代对位技术-速度卡农来构建整部作品,彰显出其高度凝练的复调思维逻辑。
本文标题中的“简约音高”用来表明全曲音高材料的主要特征,作品主要使用九度六声人工音阶作为核心音高素材,通过横向贯穿与纵向移位模仿形成全曲的音高布局。而标题中的“速度失调”(Temporal Dissonance)①一词则用来形容作品中速度设计的关键特征,纵向声部的时间要素呈现出速度对位化关系。文章将围绕《练习曲I》中最具特征的简约音高组织、陈述方式及其结构组织与点描技术的多重运用等方面展开剖析。
一、简约音高组织
徐孟东音乐创作中所使用的音高素材兼具简约性与五声性,如《惊梦》中的核心音高-集合“4-23”;《菩提》中的核心音高-集合“3-7”;《交响幻想曲》中的核心音高-集合“3-7”与“3-6”[2](P146-156)等。在《练习曲I》中,作曲家意欲强调时间性思维的速度与节奏要素,因而他选取更为简约的音高素材,基于此,笔者从核心动机表征与延展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核心动机表征
《练习曲I》以九度六声人工音阶统摄全曲,践行了作曲家简约音高的独特思维方式。从集合性思维而言,这一核心素材整体为集合“6-Z23”,内部由五声性的集合“3-7[011010]”及其倒影形式构成。从传统调性思维角度而言,九度六声人工音阶又暗含d羽和E宫五声调式的特性。
谱例1中所示的动机a、b是全曲音高组织的核心且贯穿全曲,彰显出作品音高素材简约性之特征。动机a为“3-7”的倒影形式(I2),包含一个大二度、一个小三度与一个纯四度;动机b为“3-7”的原型(P11),同样包含一个大二度、一个小三度与一个纯四度。若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统计,则还包含减四度、增四度、纯五度、增五度、大六度、小七度与大七度音程,前述种种音程类型均兼具横向旋律延长与纵向和声衍变的核心“资源库”功效。
谱例1:

(二)核心动机延展
作品整体为三声部速度卡农,三个卡农声部悉数使用核心音高素材-九度六声人工音阶,在纵向上作出频繁换序、音区转换与倒影变型等,在横向上还作出时间属性的衍变。九度六声人工音阶控制着全曲音高素材,其有序中又充斥着无序的变幻方式,使整个作品成为统一的有机体。随着旋律的不断延伸,其横向调性具有泛调性的特点。同时,横向旋律中的持续音调性俯拾地芥,呈现出自由而更为广泛的调性语言。
谱例2:第1-15小节

谱例2是作品主题旋律的开始部分。由第一马林巴奏出,充分展现出因不同调性因素而形成的模糊感,低音声部持续反复的“D”,暗射出以“D”为中心的调性背景。若加以时而出现的动机a(小三度与大二度的组合),此处更确切而言为“d羽”调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动机b在旋律发展过程中时隐时现,包含以“B-E”向上四度的旋律进行,暗含着“E宫”调性调式特征。
《练习曲I》蕴含四个卡农主题,所有旋律材料都源于九度六声人工音阶。第I主题起始将九度六声人工音阶以短小节奏的点状织体形态呈现出来,其后围绕这一核心素材结合换序、变奏、转换音区等手法作出单线展衍。据统计,这一部分共使用九度六声人工音阶达15次。其他三个主题中,第II主题使用九度六声人工音阶23次;第III主题使用九度六声人工音阶34次;而第IV主题使用九度六声人工音阶23次。依据四个卡农主题的长度与核心材料使用的多寡,可见卡农主题的布局呈现出起、承、转、合逻辑关系(见图1)。

图1
二、陈述方式及其结构组织
速度卡农技术是传统卡农与现代时间性思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谈及速度卡农之前必须厘清速度对位技术。从现有文献与乐谱资料中可见最早使用速度对位技术进行创作的是美国作曲家查尔斯·艾夫斯②,最早将“速度对位”理论化提出的是理论家亨利·考威尔③。速度对位(Tempo Counterpoint)④是指两个及以上不同速度的旋律或声部层次以理性的方式做出纵向结合的现代对位技术。而作为速度对位中最为典型的“速度卡农”技术,是指不同速度的相同旋律线条(或声部层次)在不同声部进行连续模仿的现代卡农技术,它主要以速度为音乐发展的基础性要素,第一位对速度卡农技术作出全方位实践的就是美裔墨西哥籍作曲家科隆·南卡罗。速度卡农技术虽肇始于20世纪,但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的“速度卡农”因素古已有之。文艺复兴时期,佛兰德乐派的奥克冈与若斯坎在经文歌创作中,就曾使用建立在节奏比例之上的有量卡农(Mensuration Canon),或称之为比例卡农(Proportion Canon),这可谓是速度卡农的“雏形”。但是,这种有量卡农只是简单的节奏比例关系,与20世纪真正的速度卡农具有本质区别。南卡罗在其创作中,以自动钢琴作为速度卡农技术实验的载体,对速度卡农技术作出全面实践。乔治·利盖蒂曾对南卡罗的作品评价道:“这是自威伯恩和艾夫斯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他对所有的音乐历史都很重要!”[3](P2)南卡罗的速度卡农技术影响了艾里奥特·卡特、乔治·利盖蒂与托马斯·阿代斯等一系列的作曲家,而徐孟东在《练习曲I》创作中,进一步对速度卡农技术的运用作出新的实践与探索。
从整体表象可见,乐曲分为三个排练号,内部含有四个速度卡农组,首尾呼应。乐曲首先是第一马林巴声部(I1)以♩=69的速度奏出卡农主题原型,它是建立在以D与E为中心的泛调性式旋律;其后,颤音琴声部(I2)以♩=92的速度对第一马林巴声部做出加速4/3、高小三度严格卡农模仿,展现出以F与G为中心的泛调性式旋律;紧接着第二马林巴声部(I3)加入其中,它以♩=115的速度对颤音琴声部做出加速5/4、高大二度严格卡农模仿,它展现出以G与A为中心的泛调性式旋律,三个卡农声部依次陈述完成并且贯穿始终(见谱例3)。
谱例3:

就此,从速度布局而言,三个打击乐声部呈现出3:4:5的简单速度比率,纵向速度关系上形成速度失调之状态;从音高布局而言,起讫核心材料动机a(d1-f1-g1)不仅控制着横向旋律线条的发展,还控制着三个卡农声部的纵向音高布局;从调性布局而言,纵向呈现出多调性的音高组织方式;而从力度布局而言,卡农声部之间又呈现出严格的力度模仿方式。综合而言,《练习曲I》展现出涵盖音高、节奏、力度、演奏法等多种元素的整体速度卡农技术特征。
作曲家在速度卡农技术实施过程中,对其时距要素作出多方位实践,继而追求相同主题声部之间的时间变化。所谓速度卡农的时距“是指速度卡农各声部逐次进入时起讫音的时间距离或时间差”[4](P25)。卡农的时距也可以称为回声距离,即模仿声部如同其原型的遥远回声。随着20世纪传统调性和声被逐渐瓦解,瑞士理论家恩斯特·库特(Ernst Kurth)在1917年所著的《线性对位的基础》()中创造性地提出“线性对位”技术,更加突出单个旋律线条自由横向发展的独立意义,各个旋律声部的纵向结合不再受到传统和声的束缚,而是由单个旋律的自由进行方式(上行、平行、下行)及各声部纵向结合中的音响紧张度所决定。速度卡农中“时距”的设置不仅关系到织体密度的高低与音乐张力的变化,还对整体结构的建构起着关键的作用。作曲家在《练习曲I》中对速度卡农的时距作出全方位的设计,使整部作品的的紧张度松弛有序。

图2
由图2可见,第一个卡农组的时距分别为33与19小节;第二个卡农组的时距分别为24与14小节;第三个卡农组的时距分别为14与8小节;第四个卡农组的时距分别为9与5小节。从四个卡农组的时距长短可知,每组卡农声部组的时距都作出递减,这也代表其紧张度逐渐建立;而单独从颤音琴与第一马林巴、第二马林巴与颤音琴的时距而言,也可见其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同样表现出紧张度的递增。伴随着各个声部依次加速模仿,四个卡农组的尾音时距也不断缩减,直至走向聚合。
谱例4:第126-128小节

谱例4为第三卡农组的结尾部分,其中三个声部趋向于聚合点,但又戛然而止、进入休止、悬而未决,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这一位置暗含着全曲高潮点之一,是趋近于第二马林巴声部黄金分割点的部位,也为曲终高潮做出一定的预示。其后,进入卡农时距最短的最后一个卡农组,各个声部不断追逐,时距也不断缩短,力度不断增强,紧张度不断提升,继而到达最终的聚合点(见谱例5),进入全曲的高潮,速度失调得到完满解决。进一步研究聚合点的音高设计,可见它使用的是核心音高动机a的I5与I11形式,且二者相距6个半音。综合而言,这一部位既使用了五声性动机但又蕴含着“三全音”的不协和因素。结尾部分动机a的使用与作品起始部分交相呼应。
谱例5:第162-165小节

三、点描技术的多重运用
“音色旋律”(Klangfarbenmelodie)是勋伯格1909年在《五首管弦乐小品》(Op.16)第三首《色彩》中首次使用的作曲技术,并于1911年在《和声学》中首次将这一概念提出。勋伯格指出,旋律不仅可以表现在不同的音高层面,也可以表现在不同的音色层面,将不同的音色彼此关联起来形成音色旋律。[5](P121-122)被称为“点描音乐之父”的威伯恩受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点描画派的启迪,以“音色旋律”为基础,借以节奏、音色、音区等方面的丰富表现力,将旋律线条刻化成断续点状的、时单时厚的复线条,创造性地精炼出“点描技术”(Pointillism)。在威伯恩之后,布列兹、潘德列斯基与利盖蒂等作曲家将点描技术不断向前演进,逐渐形成音色音乐。一言以蔽之,点描技术以细碎节奏、大量休止与大跳旋律为最基础性特征。徐孟东的《练习曲I》从织体布局上而言,最典型的就是点描形态,作曲家通过碎化节奏材料、变化单一乐器音色、频繁转换音区以及力度序列化进行等方式,创造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音色光谱。
《练习曲I》第一卡农组的第二马林巴声部的起始部分(见谱例6)在横向旋律上做出切割,呈现出细碎的泛节奏材料⑤。
谱例6:第52-54小节

这一旋律的发音点分别为1、2、3、5、2、1、2,展现出微型化的音点,各个音组还中镶嵌着大量休止音符,且横向旋律上频繁出现超过八度的大跳进行,力度也序列化频繁转变(p、mp、p、mp、mf、mf、p、mp……)。颤音琴声部不仅在速度上与第二马林巴声部形成4:5的比率关系,且二者在纵向节奏安排与演奏法设计上也体现出不一致因素,形成动中有静的、复调化的效果。不同于威伯恩所常用的点描技法,徐孟东在《练习曲I》的音高设计方面,并未使用固定的十二音序列,而是将三种不同高度的核心九度六声人工音阶素材置于三个声部,控制中蕴含着自由。整体三个声部的纵向结合,也可谓是 “有控制的偶然对位”。
从“节奏形态”来看,整部作品使用散点式、非律动性的节奏材料,但其泛化点描织体的表现中却暗含着节奏密度的不断衍变。图3中的四个部分代表四个卡农主题初次呈示时所在的部位,第一部分三个声部每小节发音点的总量在2-6个范围之内;第二部分三个声部每小节发音点的总量主要在10-19个之间(其中有5与7个发音点各有1个小节);第三部分三个声部每小节发音点的总量主要在16-27个之间(其中13、14与15个发音点各有1小节);第四部分三个声部每小节发音点的总量在大范围的1-30个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第1-127小节之间的发音点完成从稀疏密度逐渐到达第一阶段最密集处的衍变(第127小节发音点总量为27个,在全曲排在第二位),进入整个作品的次级高潮点,之后音乐突然又回归平静,产生强烈戏剧冲突效果。第129-165小节重新从稀疏的发音点快速到达第164小节的30个发音点,最终于第165小节“解决”至1个发音点,进入全曲高潮,这一位置也为整体速度卡农的聚合点。

图3.节奏密度分析
综前所述,本曲通过碎化节奏材料、纵向音色频繁交接以及节奏密度分阶段序进等方式来实施点描技术,以形成恍恍惚惚的复杂音色音响。整部作品利用速度卡农技术,构建了紧张度逐渐积聚而达到高潮的两个阶段,第二阶段较第一阶段的过程用时更短,音响聚集效果更为动态化。
结 语
徐孟东的《练习曲I》使用简约的“九度六声人工音阶”及其蕴含的两个核心动机素材,并在此基础分别向上四五度移位,构建出另外两个卡农声部的音高材料,就此形成的三个不同高度音阶是三个声部不断衍展的全部音高材料,极大展现出其简约性特征。就此作的“速度失调”特征而言,作曲家通过对打击乐三个声部横向时间的规划,在纵向上形成了3:4:5的速度比率。同时,这三种不同的速度被置于卡农的三个声部之中,使新型时间思维中又融合了古老卡农技术。
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之中,尝试对速度要素进行对位处理的作品一直较为匮乏。由已知乐谱与论著文献可知,为打击乐三重奏而作的《练习曲I》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使用速度卡农技术创作而成的音乐作品。作为一部练习曲,这也对打击乐演奏家的技术训练带来一种新的尝试。至此,若从空间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展现出“简约的音高”;从时间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展现出“失调的速度”;从织体角度而言,作品展现出“点描的音色”;从整体生成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展现出“严谨的卡农”;从乐器编制而言,这部作品又展现出“独奏的重奏”。徐孟东对于《练习曲I》的创作既延续了其简约、五声性的风格特征,又进一步探索了以时间性要素为基础的速度卡农技术,对于作曲家现阶段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如此,此部作品作为中国第一部对速度卡农技术进行全面实践的作品,或将推动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对于速度要素进一步地思考!
①速度失调(Temporal Dissonance),也称作速度不协和或速度不一致,美裔墨西哥籍作曲家科隆·南卡罗(Conlon Nancarrow,1912-1997)曾于1975年在罗杰·雷诺兹对他的访谈中,常采用“Temporal Dissonance”一词来形容其纵向时间观念。参见Roger Reynolds,American Music, Vol.2. No.2(Summer, 1984).
②被誉为“美国现代音乐之父”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于1906年创作小型管弦乐《未被回答的问题》(),就在不同声部使用不同速度的叠置。
③美国作曲理论家亨利·考威尔(Henry Cowell,1897-1965)在《新音乐资源》()纵向速度不一致的对位化概念。
④速度对位一词,可译为Tempo Counterpoint或Polytempo Counterpoint(如同“多调性”Polytonality或 “多节拍”Polymeter),从国外英文文献中可见Polytempo更为多见。童忠良在《现代乐理教程》中将“速度对位”定义为“几种不同速度与不同节拍的旋律用复调手法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参见童忠良《现代乐理教程》第9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⑤贾达群教授曾在《结构诗学》中提到,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作品追求非周期性、非均匀的更为细致、复杂的节奏律动,就如同人的心脏跳动一样,除了正常均匀的脉动外,人的心律会受到各种刺激的影响而频繁地改变这种均匀的状态,这正是人的心律自然属性的客观表现。徐孟东教授在创作此部《练习曲I》中正是追求一种非规范的节奏律动,再而也因应了此部作品“打击乐三重奏练习曲之功效”。参见贾达群《结构诗学》第72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1]Stanley Sadie.Edited by Macmillan Publishers Linited,1980.
[2]杨和平.流体结构及其衍变逻辑——徐孟东《交响幻想曲》音响技术分析[J].音乐艺术,2014(2).
[3]Kyle Gan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胡宝帅.南卡罗自动钢琴音乐中速度卡农技术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
[5]Arnold Schoenberg,Trans. by Roy E. Cart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J614.2
A
1003-1499-(2021)02-0146-06
胡宝帅(1992~),男,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2020级作曲理论(复调)博士。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曲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研究”(编号:18ZD15)阶段性成果。
2020-12-14
责任编辑 春 晓
——为混声四声部合唱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