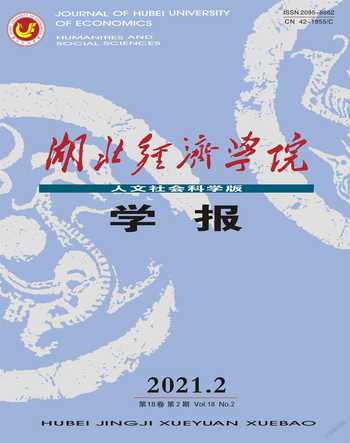敬仰自然,呼唤和谐共生
张巧
摘 要:玛格丽特·富勒是美国19世纪最主要的超验主义女作家、评论家和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她在其作品中密切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本文通过对富勒短文和经典游记作品《夏日湖景》等文本的综合研究发现,在父权制的工业社会背景下,富勒有表达出对亲近自然的渴求,对自然野性的信仰,更有对父权制发展观的批评,而这些思想无疑体现出富勒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并且也为20世纪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玛格丽特·富勒;短文;《夏日湖景》;生态女性主义
一、前言
玛格丽特(萨拉)·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是美国超验主义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她的一生短暂而又传奇(1810—1850),一方面,她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她致力于推动“自我完善”“个人自立”等超验主义核心理念的宣传,对美国文学摆脱欧洲文化的束缚并实现第一次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她借助于超验主义思想的精髓撼动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学说,最先提出“雌雄同体”的概念,被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誉为“女权主义的先驱”[1]129。她用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影响着她身边的很多重要思想家,如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y)等。
西方对富勒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当时有不少批评家发现富勒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阐明了女性改革的理论体系,富勒超前的“双性同体”观念[2]99让西方学术界不禁惊呼自己竟然差点忽略了这样一位美国才女。自从富勒进入批评界的视野后,国外众多学者将视线聚焦于富勒的代表作《十九世纪妇女》(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将其称作“史上关于女性方法和理论的最重要的论述之一”[3]180;也有部分学者研讨富勒文学批评和翻译作品中的文学观念及翻译评论,肯定了富勒在欧美文学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富勒的博学多才和卓尔不群的深刻思想让她赢得了“知识女性超级明星”[4]53的高度赞誉。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富勒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有的论者集中讨论了其女权主义思想(如杨金才2007,孙赟2015),发现富勒“把超验主义的自我完善看作是解决女性问题的重要途径”[5]56,并肯定了富勒“开启美国女性主义话语先河”[6]113的文学地位;有的论者开始关注富勒对美国浪漫主义时期思想名流如爱默生和霍桑的影响(如程心2012,吴汪1996),证实了富勒以超越时代的远见丰富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外延[7]105,并且她对同时代作家霍桑的影响大到霍桑直接以富勒作为原型创作出自己经典名作《福谷传奇》[8]43。
富勒是一位怀有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超验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但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位思想家或者作家的灵感都来源于人文思考和现实关怀。在富勒的作品中,通过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批评,富勒已经预见到了男性霸权是如何将土地,女性和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成为可以剥削的商品的[9]322。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处于“西进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富勒对当时美国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环境退化是极度忧虑的。她在1843年出游美国西部时曾哀叹道,“科学技术的泛滥使大自然被驯服和剥削,人类社会已没有了情感”[10]164。当她亲眼看到被帝国主义“文明”糟蹋的自然环境以及被歧视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时,她开始领悟到“大地,印第安人以及女人的地位是互相聯系的,并且都低于男人”[11]30。国外有学者指出,富勒的身份不应只停留在教师、翻译家、作家、女权主义思想家,诗人和社会改革家这些定位上,她对地球人文的关怀足以让我们给她添加上“早期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角色”[9]322。
近几十年来,富勒作品中的生态主题已引起部分国外学者的重视,如桑杰·D·帕尔维卡(Sanjay D. Palwekar),琳达·C·福布斯(Linda C.Forbes)和约翰·M·杰米尔(John M.Jermier)等都对富勒的生态主题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但主要是围绕富勒作品中对自然风景的审美化描述进行分析和展开,并未系统地对富勒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就国内而言,目前国内学界鲜有学者对相关主题进行初探,所以,对富勒作品中的生态主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深入性研究并且论证其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是亟待开展的。本文基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富勒创作前期的自传体散文《自传传奇》(Autobiographical Romance 1840)和短文《庞恰特雷恩湖畔的木兰花》(The Magnolia of Lake Pontchartrain 1841)进行了深入考察,并且进一步系统探讨了富勒经典游记作品《夏日湖景》中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
何谓生态女性主义?它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蓬勃兴起的第二波妇女运动和当时的环境保护运动应运而生,在理论上吸取了女性主义思想和生态伦理哲学的营养,重新审视了人类社会固有的文化结构中不平等问题[12]3,它批判西方父权制文化长久以来的“男和女”“人类与自然”等传统二元对立制的思维模式,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统治,主张地球所有生命体之间的和谐平等的关系[13]13。从本质上来看,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批评和抵制父权制生态观对女性、自然和少数族裔的奴役,致力于“解放自然,解放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任何群体”[14]57的终极奋斗目标。
二、亲近自然的渴望
生态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政治性的内在关系”[15]62,基于此,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14]58。随着16世纪至18世纪科学革命在西方社会的兴起,自然处于宇宙中心的观点便被逐渐削弱,因此,科学模式和人类理性打破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使得人类得以摆脱对自然能量的依赖,并且逐渐形成人类高于世上万物的理想模式:自然界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包括了人类理性所排斥的所有东西,“包括情感、身体、热情、动物性原始或野蛮、自然界、物体和感觉经验以及无条理性、信仰等范围”[16]57。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里的人类理性是将“妇女、有色人种、奴隶、原始人排除在人的理想模式之外的”[16]57。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是具有男性特征和工具特征的,而妇女则代表着对情感和身体领域,妇女要劣于男性[17]39。因此,同处于人类理性对立面并且被奴役的女性和自然是存在一定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使女性在遭受父权压迫时倾向于向有相似命运的自然寻求慰藉。富勒自童年时期以来便把自然当作汲取慰藉的源泉[10]165,并且以大自然多种植物作为素材进行散文写作,把自己对大自然的亲近和依恋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亲近性正是让富勒得以顽强抵抗父权制压迫的莫大动力。
富勒于181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港,她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①,是家里的长女。富勒的父亲提摩西·富勒(Timothy Fuller)是全家的一家之长,在外是当时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颇为成功的律师、政治家兼商人,他自命不凡,并自豪于自己是哈佛的一位“高级学者”,因此他决定给长女富勒灌输当时只有男孩子才能接受的教育,以便让富勒秉承自己引以为傲的优秀品质。从富勒六岁起,提摩西便教授富勒拉丁语,要求富勒阅读他指定的古典文学和历史,并且执意要求富勒待他下班后在书房地毯上向他汇报当天所学的东西。对于父亲高强度的训练,富勒领教更多的是父亲的严苛而不是慈爱。她在自传体散文《自传传奇》写道,“我常常很晚才被允许上床睡觉,我的神经总是处于不自然的紧绷状态”[18]26。富勒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父亲书房里阅读父亲强制要求她阅读的书目,废寝忘食地去领略古罗马文学中的男性英雄世界。福勒认为自己的童年充满了忧郁和恐怖:“父亲教育的结果是大脑的过早发育,这使我白天成为一个少年神童,晚上成为幻觉、噩梦和梦游症的受害者。”[18]26
在父亲强制性的高压教育模式下,富勒会经常到她母亲精心养育的后花园寻求精神上的抚慰,从而得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在富勒的眼中,母亲的花园生机盎然,开满各种鲜花和果树,是她童年时期用于疗伤的最佳场所,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完全忘记父亲书房里的压抑和痛苦,并获得无限的幸福和快乐。正如华兹华斯所认为的,人们会被自然的“宁静和美”打动,会因自然的“一些力量而心受感染”[19]101,从而“在困难中不至于丧失希望”[19]101。自然可以缓解人“过度的紧张和焦虑”[20]170,可以疏导人内心来源于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焦虑和忧郁。于是,在母亲的花园里,富勒赞叹道,“我是多么欣赏花园的美丽啊,那时我从不舍得摘下任一只花朵,这个花园对于我来说才是家里温情的象征”[18]32。富勒对花园的依恋胜过于家里的一切。与父亲书房的功利性训练相反,在花园里富勒能触碰到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她这样写道,“我亲吻它们,我满怀热情地将它们贴在胸前,这是我从未敢对任何人表达过的情感”[18]32。
富勒对大自然如此依恋以至于她开始尝试在后期的作品中赋予大自然以人的性格特征。奥地利哲学家马丁(Martin Buber)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东西是‘它(it),人与自然建立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人与整个自然是‘我-你(I-Thou)的关系”[21]61。自然与人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人类应该摒弃人类中心思想,学会聆听自然。在富勒关于植物描写的散文中,富勒通过赋予植物以人的思想或特征来实现与自然的精神对话,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回归自然的强烈渴望。在《庞恰特雷恩湖畔的木兰花》一文中,富勒在晚间散步时发现了一株飘香四溢的木兰花,“我终于找到了她,南方的皇后,她正在寂寞的凉亭里对自己唱歌。君主就是这样的,独自一人时最显王者风范。”[22]45显然,富勒用了人称代词“她”代指的木兰花,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平等意识,而且使用了拟人化的表达“唱歌”“寂寞”“君主”“王者”来形容木兰花,赋予了木兰花以人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散文《庞恰特雷恩湖畔的木兰花》里,富勒采用的是男性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来表述自己对环境的体验和感受,当代女权評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将其解释为女性“作家身份的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23]76:父权社会下,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与文学单一性别语境格格不入,从而导致女性作家不得不在作品里采用替身来表达自己的经历或体验。因此,富勒采用男性身份和语言这一行为本身就反映出富勒处于被压制和孤立的现实处境,这也足以解释富勒笔下的叙述者为何能与具有相同处境的木兰花存在精神的依恋和共鸣。短文中的木兰花是人类中心思想肆虐下的牺牲品,它从一颗花满枝头、硕果累累、赐予人类无限恩惠的橘子树沦落到被人类砍伐并且抛弃的悲惨境地。充满孤独和忧伤的木兰花向叙述者倾诉道,“我曾经是那颗美丽的大树,但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听到一些人的声音,说我死了,要砍掉我,再种一株新的花到这昂贵的花瓶里。”[22]48木兰花的命运不仅是同时代所有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界动植物命运的缩影,而且与富勒在当时被父权社会孤立和摧毁的困境相应和。基于同样的处境,富勒通过叙述者“我”表达了自己对木兰花的理解和留恋,“木兰花离开了我,而我没有离开她,我的思绪永远停留在南方湖边关于她的线索之中”[22]49。
正如基尔所说,“不同于男人,妇女对自然界有一种认同感,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因此,妇女更接近于自然。”[16]56富勒通过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并且以第一叙述者的身份与非人类世界探讨生命和死亡,表达了自己与自然界的认同和回归自然的渴望。富勒作品中蕴含着一种意识,即所有生命都密切相关,人类应该承认自然界每样东西都有价值,尊重自然界和所有生命[16]58。
三、对自然的信仰和敬畏
1843年,富勒已成为超验主义学派的一位声名显赫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美国日益蓬勃的工业革命和功利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富勒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工业革命对自然造成的压力和伤害,并且满怀痛楚地看到人性在物欲横流的裹挟中走向异化,她愤懑地感慨道,“物质利益的冲突是如此吵闹”[24]80。随着富勒逐渐长大成人,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让富勒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由一个农业殖民地转变成繁荣的工业生产中心。正如科罗德内(Annette Kolodny)所说,“富勒从前所生活的农场里,男儿们都逃到城市或者边疆谋生,女儿们每天都去不断增多的纺织厂和制鞋厂做14小时的苦力,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同时加剧了农村贫困和城市化进程”[25]115。富勒在给好友爱默生的信件中写道,“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下,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读书或者自愿的努力解决的,最好的办法便是移居。”[26]128于是,富勒在1843年开始美国中西部之旅,途径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边界,试图逃离令她厌恶的工业文明,去亲身领悟大自然的魅力和神韵。因此,她的经典游记《夏日湖景》(Summer on the Lakes 1844)也应运而生。
对于富勒而言,自然山水绝非景观的客观呈现,相反,自然在她眼中蕴含着崇高的神性。富勒对自然的理解超前的预见了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地球为基础的灵性”[27]111文化价值观。近现代生态女权主义者为了纠正以人为中心的狭隘认识,他们试图恢复男性史前期女神崇拜,把自然视为一种供人们敬重且不全为人知的神圣[14]60。不难发现,富勒在中西部之旅中表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近现代生态女权主义者这一生态理念是完全契合的。富勒西部旅行的首个目的地便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富勒用“永恒的壮丽”来表达她对大自然不朽精神的认知。富勒敬畏于大瀑布的神奇和伟力,“它如此吸引我,以至于激起了一种未知的恐惧,就像死亡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的世界一样”[24]72。她坚信自然的魅力能激发人内心超越感觉和理性的无限性灵,她描述道,“在这里所有观察细节的能力和所有零散的意识都完全消失了”[24]73。富勒在努力对大瀑布进行客观再现时,勾勒出了大自然神性的内在气质及其给人的震撼。她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独特视角去观察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具有精神和威严的存在,也许是因为“在富勒所在的时代,领悟大自然的壮丽被认为是通向神灵的通道或者激发人类思想无限潜力的途径。”[11]
富勒在敬拜自然的博大和神性的同时,对那些阻碍人与自然进行精神交流的行为明确表明了反对。当她正沉浸在自然野性所激发的超验反应时,她被一个男人粗鲁地打断了:这个男人“走近瀑布,看了一会,神气活现地想着怎样才能让瀑布为他所用,然后他往瀑布里吐了一口痰”[24]73。吐痰者的行为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下人性的异化:人们时时刻刻涌动着将生灵万物为我所用的欲望。面对人们荼毒自然的行径,富勒表达了强烈的厌恶和愤慨之情,她满腔愤怒地讽刺道,“这种特质完全配得上一个热衷实用主义的时代,以至于帕克勒·穆斯考(Puckler Muskau)认为人们很有可能把他们死去的父母的尸体放到田里施肥。”[24]73与此同时,人类这些亵渎自然神灵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富勒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在富勒所生活的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思潮鼓励观赏者从画美学(the picturesque aesthetic)的角度去欣赏自然风景,这导致人们过分沉浸于美学享受而忽略了道德或伦理上的参与[28]260,从而在意识上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人们只会从实用的角度去凝视自然并从中获取特殊的愉悦感。富勒在接下来的五大湖之旅中,对人们这种疏离自然的欲望躁动进行了批判,富勒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对万物的实用细节进行了如画般的描述,这就像只要在水边或者水上,各行各业都可以变得风景如画;所有的航海工具都变得诗情画意。”[24]79在富勒眼里,人们已经在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庸俗化,寻求财富的强烈欲望已让人们失去了人们原本对自然的纯真信仰。
尽管面临工业化进程和人类功利主义对大自然的双重蚕食,富勒仍然能够超越同时代人把自然当作可利用之物的观念,凭借对自然界的领悟与自然建立非征服型的精神关系。她用浪漫的笔墨勾勒出她强烈的自然意识。一方面,她尊崇大自然神圣光辉的精神力量,于是,在对神性的寻觅中,她驰骋想象,在罗克河之旅中她写下了自己对自然界的痴迷:
这个国家比我见过的任何一片景色都让我着迷,它毫不保留地展现出它的狂放不羁和热情动人。在这里,它的情感如洪流般涌动,到处鲜妍悦目。我在这里从不感到疲倦,虽然我在别的地方领略过更多被精心设计的神秘和魅力,然而这里的魅力更让我心旷神怡[24]100。
另一方面,在痴迷于寻求对大自然感应的同时,她也时常意识到她所拜访之地的政治和物质现实[11]。许多西部拓荒者和移居者在她眼里“除了满足最恶心的物质需求之外,别无他求。”[24]96她甚至预感到城市文明和人类膨胀的欲望会带来自然淳风的尽废,她在自己的游记中发出令人警醒的信号:西部拓荒的进程是野蛮的,而非文明的,并且他们的耕作方式会在未来的二十年甚至十年内让自然的精神完全溃败[24]96。字里行间,富勒对自然精神的崇敬和她对现实物质社会的失望形成了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更加突显了富勒渴望弥合人类与自然的疏离症候,从而得以感悟自然万物的灵性气息,让自己能够达到诗意栖息的胜境。
对于自己的生態梦想,富勒仍抱有乐观的态度,她相信人一定能与自然重回原初的和谐状态。在她的旅途中,她发现有一群移居者已经学会和自然保持友好的关系并建立起如极乐世界般的生活环境,当她拜访这些移居者建立的社区时,她惊喜道,“这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们对定居地点的选址和精心安排都显现出他们对生态灵性和智慧的欣赏。”[24]96这些景象更加坚定了富勒对未来人类会诗意栖息大自然的信念。帝国扩张定固然会对自然景观带来根本性的伤害,甚至让当地土著居民流离失所,[10]172但在富勒看来,“与其抱怨,我们还不如期待一个好的结果”[24]96。
四、对“父权制”发展观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范达娜·希瓦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方针[17]40,它以占领殖民和破坏地方的“自然经济”为前提,加速其资本积累和经济商品化。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被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称为父权制的恶性发展,因为在她们看来,资本原始积累的商品和金钱越多,自然(通过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通过否定基本生活需要)中的生命就越少,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自然合作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妇女必定会首先被利用和剥削。
在富勒出游美国西部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西部扩张高度效仿了欧洲殖民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使得富勒能近距离观察到父权制发展模式下妇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通过拜访这些新建立起的美国中西部社区,富勒发现妇女已变成男性移居者的附属品,她们被迫参与到父权制殖民主义发展中来。富勒描述道:
这些移民生活的最大缺点就是女人们不适合待在这样的新居住环境。住在这里通常都是男人的选择,妇女出于对丈夫的感情而尽力跟随,但她们往往都经历着内心的煎熬和疲惫。并且,她们并不认为留在这里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妇女的角色是最难的,她们也最不适合待在这里[24]106。
显然,镶嵌在自然界中的妇女被视为“他者”,她们被转化成被动的物体,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她们能做的只能是默默忍受边疆艰苦的生活方式并且将其传给下一代。在富勒看来,这是欧洲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对美国的毁灭性影响[24]107,这种父权制发展导致这里的白人妇女和印第安妇女在原本就很恶劣的边疆环境中沦落成“社会的装饰品”[24]106或者是奴隶[24]178。
值得注意的是,富勒不仅意识到妇女在父权制帝国扩张中所充当的被动角色,还强烈谴责父权制发展模式对妇女们获得适应西部新生活技能的权力的掠夺。富勒在旅游途中发现,跟随男人移居到中西部的妇女普遍面临着生存困境:当拥有健硕身躯的男人可以在野外享受涉猎、钓鱼和骑马所带来的娱乐时,既没有力量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妇女们不得不在家里完成更繁重的家务[24]106。更令富勒难以接受的是,城市教育从来不教授妇女这些必要的技能,也不允许她们增强体魄[24]106,这无疑为移居西部的妇女的生活雪上加霜。女性生态批评家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父权制发展体制下妇女的非对称性参与:西方殖民者利用父权制不断削弱妇女的技能以及智力附加值,在技术上和雇佣上不赞成妇女从事与土地有关的殖民事物,进而使她们只能用贫乏的资源来喂养和照顾孩子、老人和体弱者[29]155。富勒似乎也超前地意识到这一点,她认为父权制发展对妇女的控制会使她们身心上变得“无能”[24]106,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有效的办法便是开展教育来弥补妇女所缺失的技能和智力,让妇女也能和男人一样得到对称的充分的发展。所以她强烈地呼吁道,“我真诚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思想的人能在她们周围建立好的学校,来满足她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相应需求”[24]107。
在接下来的芝加哥大草原旅途中,富勒除了细心领略大自然壮丽风景之外,却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早逝的童年伙伴玛丽安娜(Mariana)的故事,进而将笔锋直指父权制发展观对妇女的侵害。玛丽安娜(Mariana)精力旺盛,能言善辩,热情聪慧,充满神秘的力量和幻想[24]119,但这些极强的个性使得她在学校受尽讥讽和指责,在婚姻生活中也不被丈夫待见,导致她最后抑郁而终:她独自度过了漫长的一天,思绪和压力远远超出她的承受范围,她不知道如何处理好它们,高烧不退,病逝了[24]129。富勒为玛丽安娜的早逝感到惋惜,她认为玛丽安娜的悲剧源自妇女缺少充足的资源来得到充足的发展,“对于一个拥有同等能力和同样真诚的男人来说,会有很多资源呈现在他们面前。”[24]131富勒对父权制发展模式下女性欠发展现状的批判引发了她在后续篇章中的人文关怀,因此,她的叙述开启了对边缘化群体的更深入的思考。
除了表达对亵渎自然以及性别歧视的反对,富勒也拒绝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生态批评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为了让同样的产品在任何地方畅销,他们有意识的简化人类群体和文化,[14]60通过推行种族主义来达到世界环境简化的效果。富勒也已经意识到以金钱和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白人男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歧视。在拜访麦基诺岛(Mackinaw Island)的齐佩瓦族和渥太华印第安人(Chippewa and Ottawa Indians)时,富勒尝试从各种文本中引用了一些叙述来介绍印第安人的风俗文化,但她发现这些文本的叙述都蕴含着偏见和歧视。例如,她批评美国西部艺术家和作家乔治· 卡特林(George Catlin)的游记在“事实准确性上不可信”[24]87;英国作家查尔斯·奧古斯塔·穆雷(Charles Augustus Murray)的游记太执着于对印第安人进行负面描述以至缺少“诗意的眼光”[24]88;美国印第安事务局局长托马斯·罗兰·麦肯尼(Thomas Loraine McKenney)的游记中关于建立宗法制政府来管理印第安人的提议不可行,甚至显得“野蛮且自私”[24]212。富勒反对这些形式的种族主义,她在游记中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体现印第安人英雄主义、高贵和自我牺牲的历史文学记录,试图去发现印第安人文化特征的伟大之处。因此,富勒最后呼吁道,“印第安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被看待,而不应该受到人们与生俱來的偏见或者帝国主义文明的排斥。”[11]
《夏日湖景》并非仅仅局限于美国中西部景观描写,它同时带有较强的议论色彩。通过这部游记,富勒抒发了帝国主义扩张下自己对自然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强烈反对。基于自己在美国中西部亲眼所见的自然风景、妇女生活和土著印第安人的风俗民情,富勒得以把自然、妇女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与白人男人相比,都处于劣势地位[11]。由此可见,《夏日湖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富勒通过记游写景来折射那一时代的特征,并且得以全面表现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生态伦理道德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社会意味着人们要反抗自然歧视和性别歧视,并且必须阻止父权制后殖民主义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努力保护“文化多样性”[30]25,让世界万物和谐共生。
五、结语
玛格丽特·富勒的思想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股清流,她的生态关怀和人文思考对美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也被后来的学者誉为“美国最伟大的人文学家之一”[31]178。“自然之爱”是福勒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她回归自然的渴望和对自然的神圣之爱让她难以容忍任何把自然作为剥削对象的功利主义行为,她希望人类不要过度膨胀以至于忽视了对自然的敬仰,正如她在游记中所呼吁的那样,“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眼观天空,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24]132因此,富勒既保持着对大自然的信仰,也坚持着对现实的尊重并对其进行政治性批判。她对美国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父权体系价值观提出挑战,反对将土地、妇女和少数族裔视为可利用商品的意识形态[11],期盼构建世界万物、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富勒这些超前的生态道德伦理为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在世界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 富勒实际上有两个妹妹和六个弟弟。但在富勒三岁时,她十三个月大的长妹茱莉亚夭折;在富勒十九岁的时候,她十六个月大的小弟爱德华夭折。
赫尔曼·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帕克勒·穆斯考(Hermann Ludwig Heinrich Puckler Muskau,1743-1813):德国游记作家,园艺专家。
参考文献:
[1] Showalter,Elaine. Feminist Foremother[J]. Wilson Quarterly,2001,25(1):129-131.
[2] Fuller,Margaret.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New York:Greeley & McElrath,1845.
[3] Welter, Barbara.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6.
[4] Dickenson,Donna. Margaret Fuller: Writing a Womans Life[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3.
[5] 孙赟.论超验主义视阈下富勒的女性主义思想[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52-107.
[6] 杨金才.玛格丽特·富勒及其女权主义思想[J].国外文学,2007,,(1):112-122.
[7] 程心.富勒和艾默生:超验主义的文学关系[J].国外文学,2012,(2):97-107.
[8] 吴汪.被霍桑诅咒的女人[J].世界文学,1996,(4):43-46.
[9] Forbes,Linda C.& Jermier,John M. Experiencing Niagara Fa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arly Ecofeminist[J].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2000,13(3):322-327
[10] Palwekar, Sanjay D. Ecofeminist Study of Margaret Fullers Summer on the Lakes in 1843[D].Nagpur:RTM Nagpur University,2012.
[11] Steele, Jeffrey. The Essential Margaret Fuller[M].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
[12] Mies,Maria & Shiva, Vandana. Ecofeminism[M].New Delhi:Rawat Publication,2010.
[13] 吳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57-64.
[15] 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秦喜清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6):62-65.
[16] 曹南燕,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J].哲学研究,1996,(5):54-60.
[17] 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J].妇女研究论丛,2000,(4):36-41.
[18] Fuller, Margaret. Autobiographical Romance[M]//The Essential Margaret Fuller. Jeffrey Steele.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24-43.
[19]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 孙敏,付美艳.深层生态文化视阈中的《榆树下的欲望》[J].外语学刊,2010,(3):169-172.
[21]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2] Fuller, Margaret. The Magnolia of Lake Pontchartrain[M]//The Essential Margaret Fuller. Jeffrey Steele.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44-49.
[23] Gilbert,Sandra M.& Gubar,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24] Fuller, Margaret. Summer on the Lakes[M]//The Essential Margaret Fuller. Jeffrey Steele.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69-225.
[25] Kolodny, Annette.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26] Hudspeth,Robert N.The Letters of Margaret Fuller[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27] 张妮妮.生态智慧中的灵性因素[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09-113.
[28] Price,Martin.The Picturesque Movement[M]// From Sensibility to Romanticism. Frederick W. Hilles & Harold Bloom.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P, 1965:259-292.
[29] 郑湘萍.从西方“父权式发展”到“生存必需”的另类发展——范达娜·希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观研究[J].学术论坛,2013,(11):154-158.
[30] Gaard, Greta & Murphy, Patrick D.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 of Illinois Press, 1998.
[31] Wade, Mason. Margaret Fuller: Whetstone of Genius[M]. New York: Viking,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