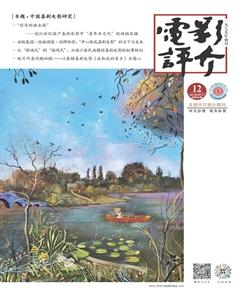《悬崖之上》:张艺谋电影的集体记忆和生命美学
刘刚
《悬崖之上》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伪满洲国时期,彼时的东北地区处在日本关东军的占领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秘密开展了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和细菌战,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是中国人最恐怖最难忘的历史记忆。地下抗日组织进行了英勇反击,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伪满洲国政权,对抗日力量进行了血腥屠戮,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谍战片,影片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以自己的方式加以纪念,其中隐含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生命美学等重要信息,值得认真探究和分析。
一、电影作为记忆的场域
电影不是历史,电影是对历史的记忆。影片在东北的漫天大雪、黑白分明的天地中展开,这种黑白色调让人想起电影《辛德勒名单》中刻意使用的黑白画面,白色象征着死亡和伤病,黑色象征着黑暗和暴力,这个记忆的场域是民族受难的场域。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屈服于异族奴役的斗争场域,也是一个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神圣场域。
记忆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属于心理学或脑科学的范畴。记忆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心理层面上记忆的对象是个人。记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记忆文化属于计划和希冀的范畴,有助于社会意义和时间界域的构建。
记忆有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长大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才形成记忆。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所以‘集体记忆的说法并非一个比喻。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回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1]
社会通过构建出一种记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了自我形象,并在时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谁若还在“今天”时便已企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就要借诸回忆来留住它,过去于是在回忆中被重构。[2]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文化创造。过去是一个社会建构物,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其参照框架决定了“过去”的本质。我们通过创造一个过去的神圣场域,借助对它的记忆来建立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树立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性、权威以及信任。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曾经亲历日本侵华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对于集体记忆而言,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无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伴随而来的便是植根于这些社会环境中的回忆将被遗忘,那些来自于往昔的文本失去了不言自明性,变得需要阐释。电影作为一种回忆,也是一种对于回忆的阐释。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政治和社会需求,要求对往昔的文本进行阐释,有组织的回忆工作便替代了尚未成型的、自然发展的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鲜活回忆以及亲身经历和据他人转述的内容。电影承接了阐释的工作,电影人一而再地回到记忆之所,进行回忆和阐释。张艺谋的电影《悬崖之上》以谍战片的方式对东北的黑暗年代进行回忆和阐释,确立身份认同,寄托理想情怀。
张艺谋目前已有三部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一部是发生在山东高密农村的《红高粱》(1987),一部是发生在南京城中的《金陵十三钗》(2011),一部是发生在伪满洲国的《悬崖之上》(2021),作为记忆场域的三个地方皆具有典型性。山东从近代以来一直被日本視为其势力范围,在1937年全面侵华之前就已经三次入侵山东,犯下累累罪行,山东受祸最深,民众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南京是民族耻辱的集体记忆之地,日本军队通过大规模的强奸屠杀以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侮辱践踏中华民族精神;《悬崖之上》对伪满洲国的记忆,侧重在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反人类罪行以及对抗日力量的血腥镇压和疯狂杀戮。每个民族、每种信仰都会将自己特有的回忆以自己的方式落脚到某个地点并加以纪念,回忆被具体定位在某个蕴含记忆、富含意义的自然场景之中。
二、电影中的集体记忆与历史
抗日战争是真实的历史,电影是集体的记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其著作《在历史和记忆之间》中认为:“记忆、历史,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义词,而是如我们今天意识到的,从任何角度上讲都是反义词。记忆是一个永远发生在当下的现象,是一个在永恒的当下中经历的联系,而历史则是过去的重现。记忆把回忆带入神圣的范畴,历史则把它们从中驱赶出来,历史的使命就是驱魅。”[3]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次序关系,历史始于过去不再被记忆,也就是不再被经验的地方。“一般来说,传统终止,社会记忆消失后,历史才开始”。[4]电影为社会记忆而存在,展现了群体的记忆,而区别于历史。群体记忆强调自身独特的经历及其基于这样的历史而具有的、区别于任何其他群体记忆的特殊性,历史则消除了所有此类区别。《红高粱》是对山东高密乡村农民抵抗日军侵略的记忆,《金陵十三钗》是对南京1937年沦陷后一群女学生和风尘女子悲怆命运的集体记忆,《悬崖之上》是对消逝在伪满洲国的抗日勇士的集体记忆。如果说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而记忆则是小人物的记录,他们是在历史空白处的书写。宏大正统的历史叙事不能替代娱乐性的电影故事,可以说,电影工作者是文化记忆的专业承载者。
德国哲学家布鲁门伯格认为“回忆中无纯粹事实”,指向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5]集体记忆包含两个方向:向前和向后。记忆不仅重构过去,而且组织当下和未来的经验,回忆同时包含着一种希望。谍战片并非“事实”,通过电影对记忆的重构,让细节和画面进入记忆,填充或替换掉此前的群体的过去,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成为所希望成为的“历史”,这正是电影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例如优秀国产谍战片《风声》中,地下工作者神秘莫测的信息传递,让人觉得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离奇感,这些情节正是显示了回忆的“希望原则”。
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试图通过电影刻画出一批为了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隐秘战线的英雄形象,电影是为英雄立传。作为回忆文化的重要内容,悼念亡者是一种典型的“对集体起到促成作用”的记忆。一个集体在回忆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记住某些名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认同,是民族力量的凝聚。成千上万阵亡战士的姓名被镌刻在纪念碑上,无名战士的墓碑上虽无姓名,但匿名的纪念意义仍在,如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这些(无名战士)坟墓如此空虚,其中并无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遗骨,也无不朽的英灵,但他们却充满了幽灵般的关于民族的想象。”[6]这种纪念的最大作用便是促进认同,是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最根本的基础。电影《风声》中,英勇牺牲的地下工作者顾晓梦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在作为记忆场域的电影中,无名的战斗者和牺牲者依然作为集体记忆而活着,而死者之所以继续活着,是出于群体不愿意任其消失的坚定意志,群体还会以回忆的形式保留其成员身份,使其跟随群体前进到每个新的现在。正如古埃及的一句箴言:只要一个人的名字还被提起,他就还继续活着。
三、民族认同与意识形态话语
群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电影的价值导向是一种深刻的民族身份的认同和精神凝聚。群体和个人一样,栖居在自己的过去,并从中汲取塑造其自我形象的成分。抗战一再被回忆指涉,与我们的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系。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等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的需求,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意味着时代和社会面临新的诉求。谍战片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电影类型之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以两部西方著名谍战片为例。一部是美国电影《谍影重重》(2002)。影片改编自作家罗伯特·鲁德鲁姆创作于冷战期间的同名原著。主角杰森·伯恩是一位不断寻找自己真实身份、躲避中情局暗杀的特工,失忆隐喻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安全感源自无处不在的集体权力。影片展现了强大国家机器对个人的碾压以及个体对体制的奋力抗争。另一部是英国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2011),影片根据约翰·勒卡雷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背景设立于冷战时期,讲述了英国间谍机构如何揪出苏联安插在圆场(英国谍报部门)高层“内鬼”的故事。影片着力渲染了冷战时代特有的阴郁、低沉和悲凉的气息,是二战后陷入衰败的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影片背后隐藏着冷战时期英国民众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质疑,以及对意识形态信仰的动摇。这两部电影的共同特点是展示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对冷战意识形态的反思,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从整个西方来看,二战以后谍战片始终是一个主流的商业电影类型,而中国谍战片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虽然有高低起伏的变动曲线,但这种高低起伏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为谍战片始终是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反映。中国谍战片重点安置于抗日战争的文化场域和记忆场域中,因为民族复兴和民族认同是时代的主题话语。
回归到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层面。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艺术活动,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由于文艺创作了自身的生产机制,同时又参与到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因而无法切断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阿尔都塞和马谢雷对文学文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考察。他们认为文学是对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家并不是全能的创造者,文学也并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是一种生产活动。他们强调文学生产是运用文学手段对意识形态原料所进行的加工,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从审美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文学的共性,同时又关注文学的特性。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既有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也有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更有对艺术审美的深度穿透。电影《悬崖之上》艺术性和观赏性兼而有之,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又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主要来自于电影对生命美学的表现和阐释。
四、电影中的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以关于生命自身作为审美对象,审视生命如何被建构为一个美学的对象,生命如何作为美的作品。福柯认为生命美学源自古希腊时期,“之所以我把自己放到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的时代,是因为我想要重新抓住这个时代,当时在希腊文化的古老传统中考虑美的生命、闪光的生命、令人怀念的生命的问题。”[7]福柯认为,生命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最重要之处是它把审美重点从艺术美的鉴赏转向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风格,“对于人来说,其存在方式,他的行为,他的生命在其他人和他自己的眼中所表现出来的外观,他的生命可能留下的印迹,以及死后可能在别人记忆中留下的印迹,这种生存方式、这个外观、这个印迹曾经是美学考虑的对象。”[8]
电影《悬崖之上》片尾处打出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心向黎明、舍生取义的革命先辈们。”地下抗日特工人员的生存状态,如同每时每刻行走在悬崖之上,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同题材的电视剧《悬崖》(2012)中,女谍报员顾秋妍在一次野外发报中遭遇伪满军,在逃跑中坠下悬崖。特工们一再以必死、求死的决心,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悬崖边缘。电影《悬崖之上》中张宪臣和楚良以自己的死换取同伴的生。周乙潜伏在警察厅特务科,每日与魔鬼斗智斗勇,毫无贪生怕死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在生与死的边缘中极端生存正是展示生命美学的最佳场景。纵观张艺谋的三部抗战题材作品,《红高粱》的酒神精神,《金陵十三钗》的女性隐喻,《悬崖之上》的极限生存,无不是对生命美学的展示和书写。影片对主人公展示的不仅仅是他们具备的各种美德,无私无畏、勇敢不屈、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更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平凡、突破极限、把自己作为一个美学作品来完成。
尼采所推崇的酒神精神在电影《红高粱》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呈现,酒神精神是生命美学的重要理论渊源,它象征着人性情绪欲望的尽情放纵,表现了人类本性的彻底还原。余占鳌是酒神精神的代表,他个性刚烈,性格粗野狂暴,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敢于冲破一切障碍而释放自身的内在生命力。他酒后冲酒槽撒尿,为报杀妻之仇而怒杀日本鬼子,彰显了乡野中的民族精神和不屈的斗志,表现了人的感性生命的高涨洋溢和个体身心的彻底自由。正如福柯所认为的,只有以自身的欲望发泄,并使自己陷入癫狂的酒醉状态,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使自身的生活和生命实现生命美学的最高状态。[9]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秦淮河的风尘女子有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精神,以死亡完成了生命的超越和精神的升华。这群被社会鄙视的女子用生命保全了人格的尊严,她们的牺牲精神散发出人性的圣洁光辉。她们由秦淮河的卑贱女子变身为南京城里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完成了自身作为美的作品的创作书写。
生命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把创造和更新,当成自己的生命本身,当成一种快乐和一种美来享受,同时,也把创造性活动,同冒险以及探索生活的极限联系在一起。正如影片中的抗日义士,他们一再尝试以最大的勇气把自己推向“活不了的临界点”边缘。那种“生存和死亡交错”的神秘地带,是为个人经验带来丰富内涵的珍贵时机。美的生活,不应该静如止水,不应该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惯常循环重复的圈子,而是应该如同江河大海那样流动,并时时涌现惊涛骇浪,历经险象环生的旋涡。“人只有学会来回往返于‘生命与‘死亡、‘存在与‘非存在、‘在场与‘缺席、‘有限与‘无限之间,才能享受到生活和创作的乐趣与美感。”[10]无名战士主动选择牺牲献身,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实现了生命美学所主张的生命极限体验。
参考文献:
[1][2][4][5][6][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24,37,33,59.
[3][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5.
[7][8][法]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氣: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36,135.
[9][10]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6.
【作者简介】 刘 刚,男,山东枣庄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