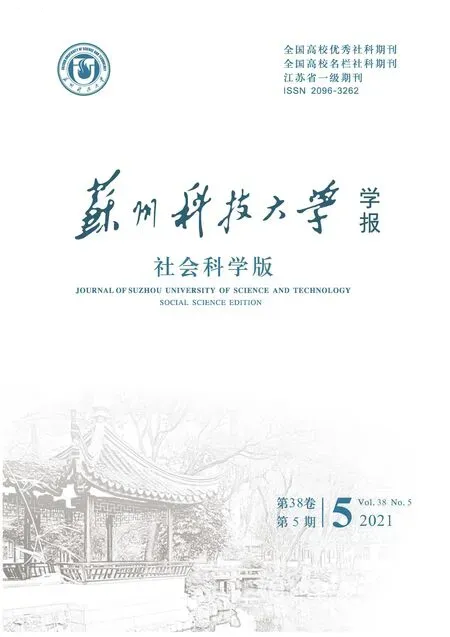1895—1937年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的一体化进程 *
赵 伟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19世纪末,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发轫后不久,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一部分优势企业开始推行扩张经营。这一现象始于20世纪初,盛于二三十年代。扩张经营既是民族企业谋求生存的战略,也顺应了世界企业发展的潮流。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1)相关论文参见杜恂诚《抗战前上海民营企业的资本集中》,《上海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第61~64页;杜恂诚《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兼并与重组》,《改革》1998年第2期第119~126页;杜恂诚《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效果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65~74页;李福英《规模扩张与近代企业集团的兴衰》,《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157~161页。专著主要有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耕《中国近代民营工业企业集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资本、兼并、集团三个角度展开(2)资本(积累、积聚、集中)的理论框架注重揭示企业扩张的实质,兼并(或并购)概念侧重表达企业实现扩张的方式,集团化在于显示企业扩张所带来的组织结构性结果。笔者所论维度是关于企业扩张形式(或类型)的面向,有助于厘清企业扩张的脉络。,对企业扩张阶段的讨论主要参照产业发展的总体进程,并非基于企业扩张特征的总结(3)吴承明、江泰新主编的《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538页)指出,近代民营企业集团的发展分三个时期:草创时期(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黄金时期(“一战”爆发至1921年)、曲折发展时期(1922年至1937年)。。其时,中国企业界已经提出一体化的经营思想,明确了横连、纵合、多角三种维度(4)“横连”即企业“置同类之事业于同一管理之下”,“纵合”即企业“对于一种事业,自产生原料,制成商品,以致销售此商品,皆由一机关为之”,“多角”即“兼营数种事业”。参见赵伟《论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事业集合”思想》,《江海学刊》2016年第6期。,这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企业一体化(5)一体化战略是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根据企业的控制程度和物资流动的方向”,“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种战略”。纵向一体化企业“沿着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链的前后方向进行延伸和扩展”。横向一体化是企业“开展那些与企业当前业务相竞争或相互补充的活动”。多元化,即企业“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甚至经营彼此毫不相关的不同行业”。参见孟卫东、张卫国、龙勇《战略管理:创建持续竞争优势》,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1页;金占明《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薛荣久等《当代国际贸易与金融大辞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理论有一定契合。经济学家方显廷曾指出,“一战”后中国纱厂“企望扩张控制本业之权力,故有集合之趋势”[1]271。由此,笔者将从扩张特征的维度分析近代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的一体化进程。
一、民族棉纺织企业一体化行为统计
鉴于目前学界对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相关企业的扩张行为尚无集中全面的梳理(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附录一”(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1~366页)提供了1890—1937年中国机器纱厂沿革的信息,所有纱厂的简要扩张情况大致可知。不过,该表以单一工厂为对象进行介绍,导致统一企业集团下的多个生产单位分散开来,不能清晰地展现一体化过程,而且部分企业的一体化行为记录并不完全,需要以企业集团为对象集中进行梳理,另外查找史料补充内容。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附录”中的《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1840—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加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页)一书“附录”中的《历年所设本国企业一览表(1928—1937年)》列出了较为完整的纱厂和染织厂名录。不过,二表只提供了基本信息,没有介绍沿革情况。纺织专家蒋乃镛《中国纺织染业概论》(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17~18页)一书中的《民二五年全国漂染整理工厂统计表》和《抗战前全国印花工厂统计表》,列出了具备机器染色或印花的企业名单。由于纵向一体化企业必会整合染色生产,以此为线索可以基本确定纵向扩张的企业。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研究所针对的扩张企业是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生产单位,民族染织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或准近代的生产单位,采用改进的铁轮机织布或土法印染,这些不在考察范围内;第二,部分企业涉及多种经营,此部分仅介绍在纺织染印生产的扩张情况,不包含在其他行业的扩张。,为使本研究具备必要的史实基础,笔者根据既已整理的企业资料,结合报刊、工商史志、文史资料等记载,对相关企业的一体化行为按时间顺序进行简要整理(见表1),并据此分时段及维度统计次数制作了表2。

表1 1895—1937年近代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一体化行为一览表

表2 1895—1937年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发轫、横连及纵合行为次数统计表
(2)字符简称:字母指代:F(Foundation)特指首个生产单位的创办,即发轫;H(Horizontal Integration)指横向一体化;V(Vertical Integration)指纵向一体化。
汉字指代:一指实现方式,即“自”指自建,“购”指收购,“租”指租办,“并”指兼并,“合”指合并;二指行为对象,即“中”指华商,“日”指日商,“英”指英商;三指生产环节,即“纺”指纺纱,“织”指织布,“染”指染色,“印”指印花,“用”指装备修理机器。例如,“购中”意为收购华商生产单位,“中购”意为生产单位被华商收购,“自染”意为自建染色生产单位,“购中纺”意为收购华商纺纱生产单位。
带圈数字①~⑨分别指代1895—1937年8个5年和1个3年的统计时段,用以表2对照表1统计数量。
(3)行为认定:横向一体化主要是纺纱生产单位的增加;纵向一体化主要指纺、织、染、印纵向链条各生产环节的增加。近代民族纱厂附设布机的行为较为普遍,但不视为纵向一体化行为。此行为是附属性质,没有改变企业以棉纱为主要产品的现状,也没有改变总体上以纺纱横向为主的一体化维度;且大部分产品为粗布,非机器印染的主要原料,不具备纵向链条的关联性。另,发轫、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行为时间以正式建厂开工年份为准;合并的原各企业发轫行为均纳入统计。
(4)数量单位:一次横向一体化行为即企业发轫后,1个相同生产或业务单位(工厂或部门)的增加,记为数量1。其中,某一生产序位的单位通过对同一或不同生产单位先租办后收购的方式获得,视为不同实现方式的相继性一体化行为,仅计数量1。一次纵向一体化行为即企业发轫后纵向生产或业务环节上1个单位(工厂或部门)的增加,记为数量1。反之,一次解体行为,即企业一体化关系中,1个生产单位(工厂或部门)的消减,记为数量-1。如工厂被收购、被债权人接管、解除租办关系、委托经营、被战火摧毁等。其中,企业整体被另一华商接收,一体化关系未变,不视为解体;若被外商接收,民族性质发生改变,则视为解体。
另,表2中发轫次数一行括号内是纺纱和染织单位数量相加,横向及纵向次数一行括号内是正向与负向行为次数相减。
1895—1937年,约41家民族棉纺织企业实施了一体化经营行为。发轫、横向、纵向三种行为在九个连续时段内统计数量的变化,为分析一体化维度的总体进程情况提供了依据。
1920年前后是发轫为主的阶段。民族棉纺织业中采取扩张经营的企业,虽于19世纪末即已出现,但“一战”爆发前20年内总共才开办了8家,1915年后明显增加,5年内增添了9家,20年代前半期达到高峰,共开设了13家。此后,呈减少趋势,5年期的发轫次数均再未超过这一时段,抗战全面爆发前3年内只有1次发轫数。
20世纪20年代是横向一体化为主的阶段。民族棉纺织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最早出现于1907年,但时隔12年之后才发生了第二次,20年代前半期则迅速攀升至顶峰,5年内达15次之多,加上2次解体行为,横向一体化行为总数达到17次,整体扩张效果为13次。20年代后半期解体行为次数增加,且接近正向行为次数,仅相差2次,整体横向扩张效果已不明显,然正负向行为次数之和仍有10次,反映了横向维度的行为依然处于活跃状态。其实,此5年是横向一体化向纵向一体化转向的时期,纵向行为虽不在少数,共9次,但仍不及正负横向行为次数之和,也未显著多于正向横向一体化次数。溯前所观,纵向一体化次数略有增长,然并未占据主流地位。
20世纪30年代是纵向一体化为主的阶段。纵向行为开始于20世纪初,1930年前稳定在个位数水平,30年代前半期猛增至最高点的29次,仅有1次纵向解体行为,且是战火毁厂造成,不仅远高于正向横向一体化次数,也大大超过了横向正反行为的总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3年间虽减少至17次,整体纵向一体化效果为15次,亦均明显高于横向行为,而当时反向横向一体化已然超过正向次数。
二、横向为主阶段:抢占粗纱(7)“市场上所谓粗纱细纱,仅系比较之说,并无确定之界说可言。我国通常以二十支以下者为粗纱,过二十支者为细纱。”参见叶量《中国纺织品产销志》,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4页。市场,扩张与发轫并举
1895年以后,华商设厂的障碍被逐步破除,国家在政策、法律、制度上的新政给予民族企业相应的鼓励和保障,社会观念、风气、思潮的转变也为之助推。一方面,现代化启动以来形成的经济技术成果对其发展不断累加推力;另一方面,适应性改良后的传统经济因素也为之扩张提供条件。当然,民族棉纺织企业能够迅速横向一体化的最直接因素是:“一战”爆发后,洋纱的退出使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市场空缺。这一点无需冗述。
1920—1924年,横向一体化与发轫行为次数同时处于高峰。一般情况下,企业创建后需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才具备整合扩张的条件,这也是近代欧美企业普遍经历的过程。美国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直到40年代“在生产中也和在商业中一样,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企业形式”[2]56,即“单一单位的企业”[2]2,制造厂商“采取以合并方式成长的最初的步骤”到70年代才出现[2]366-367。这之间至少相隔五六十年,而中国情况则是不到十年,且建厂高峰期亦是横向一体化风行之时。在尚未获得充分积累的情况下,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的一体化行为具有追赶性,而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状态下形成的企业集团,便具有明显的超前性”[3]。
追赶性横向一体化能够发生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两个原因需特别指出。其一,技术进步成本的消减。钱德勒指出,工厂扩大的限制“主要是技术上的”[2]86,“新的能源以及运输和通讯方面新的速度和规则性,促使业主们一体化他们的经营活动”[2]89。美国花费了五六十年时间完成了技术上的累积进步,而中国通过技术引进消减了绝大部分的时间、试验、改进成本。其二,传统经济因素的适应性。企业扩张首要的是资金支持。清末民初“新式银行开设不多,亦不做商业往来。工商业资金融通完全依靠钱业……对那时方在成长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扶助作用”(8)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0页。从现代金融机构来看,中国银行业在初始阶段(1897—1927)的业务活动“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度极低”,1927年以后才“趋于密切起来”。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55、92页。。传统金融机构对现代企业发展的业务适应为横向一体化提供了资金支持。二者在实质上都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拥有的特殊条件。
追赶性横向一体化的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920年前后,横向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抢占棉纱市场。“一战”爆发后,日、印两国“趋向于细支纱的生产”[4]163,以粗纱为主的中国市场上洋粗纱进口量在逐步减少,而此时日本为“在中国生产已失去竞争力的粗纱”[4]176,开始加快投资设厂,1921—1922年达到“最盛时期”[5]275。这样,民族纱厂与在华日资纱厂必有一战,当然民族纱厂之间亦存在竞争关系。于是,部分优势企业通过实施横向一体化经营战略争夺粗纱市场。多厂联营的大型企业可以获得规模效应,在竞争中胜算更大。其时,由于全国纱厂总数不多,市场尚有较大空间,棉纺织企业主要通过自建纱厂的方式来实现横向扩张,以便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表3显示,1925年前的17次正向横向整合行为中,自建次数是16,超过90%。至1930年左右,民族纱厂已基本占据本国粗纱市场。[4]216,[5]281-282近代中国五大棉纺织企业集团——大生、申新、永安、华新、裕大华都在这一时期形成。

表3 1895—1937年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横向一体化实现方式次数统计表
其中,申新纺织公司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其创办者荣氏兄弟一贯主张横向一体化。兄弟二人早年曾在无锡与人合伙开办振新纱厂,1914年全国纱业横向扩张尚未兴起,荣德生发现纱厂的纱锭规模“内地无过三万者”,提出添建纱厂三所,“二厂在申,三厂在宁,四厂在郑”,然董事会“目光不远”,“闻之大骇”。[6]71翌年,二人退出,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以“多办纺织厂”[7]为战略经营理念,最终鹤立鸡群,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8]172。
20年代后半期到抗战前,正向和反向横向整合行为是中国棉纺织业重组的重要途径。民族纱厂和日资纱厂无序竞相扩张,纱厂数量激增,导致产能过剩,造成“1923年萧条”。由此,中国棉纺织业进入调整时期,并购重组之风盛行,正反向并购行为总共达到12次,以较少资金达到联合经营目的的租办行为也较多出现,正反向共8次。优势民族企业进一步横向一体化,多厂联营以实现有序生产,充分发挥规模经营优势,挤占市场;劣势华商纱厂则通过横向解体减少损失。与此同时,在华日资纱厂也有“集合之趋势”,程度“尤在华商纱厂之上”[1]271,并与之针锋相对。华商纱厂有5次横向解体的被并购案,其中3次与日商有关,却无并购日商纱厂的记录,仅有2次收买英商纱厂的行为。华厂受到来自在华日厂的扩张压力可想而知,进一步的横向一体化带有明显的防御目的,且具有企业和民族双重意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华商纱厂不同,日厂在横向一体化的同时还伴随着实施棉纱“高支化措施”[5]276。这是因为:鉴于中国市场对粗纱的需求“已经没有增长余地”,而1920年以后近代织布业的兴起使得20支以上细纱市场正逐步打开,与其继续在供应过剩的粗纱市场与华厂倾轧,不如转而生产细纱,开拓新的市场,何况细支化本就是当时机纺棉纱的趋势。这样,日资纱厂对华厂的并购,反之即华厂的横向解体,客观上削减了粗纱产能,缓解了危机。然而,民族纱厂“坚持生产面向农村市场的粗纱”[5]308,缓于推动高支化进程。即使通过横向的正反向活动能够获得短暂的喘息,进入30年代,随着粗纱市场缩小和细纱需求的扩大,它仍将直面怎样推进、扩大,甚至转向细纱生产的问题。接下来,扩张维度的转变将从行业格局上对民族纱厂予以促动。
三、纵向为主阶段:推动高支化,实现纺织染联营
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税金融改革改善了民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翻覆,国际银价波动,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突发,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错综复杂、险象环生。
1928年下半年,中国棉纺织业在历经多年的萧条之后终于开始有所好转。可没有几年,又于1931年下半年遭遇困境,直至1936年下半年才得以摆脱,而织业“相当稳定”。这得益于从20年代开始逐步打开的细质布市场,30年代与近代织业相关联的印染业兴起,以及1930年后国家提高各类棉布进口税率的助推。[4]234-235正当一些民族纱厂受困于危机中无奈横向解体、经历行业重组之痛时,许多城市近代布厂或染织厂借助从新兴市场中的获利,积极推动纵向一体化,实现纺织染联营。民族棉纺织业一体化的主流方向遂发生转变。
一些企业一体化维度从横向向纵向转变的实例是整个行业主流方向改变的集中体现。永安纱厂在1930年前以横向一体化为方向,一厂建成投产后,通过并购整合了二厂和三厂,规模仅次于荣氏申新。不过,1930年建成的四厂专纺细纱,3年内将细纱锭扩充至7万多枚。细纱是机器染织生产的主要原料,这样做是为实现纺织染联营的“打算”。永安董事会看到了花色布的“大好利润”,认为“纺织者必须兼办印染厂”,以“适合时趋”。(9)永安在创立时的招股章程中就提出“自设印染厂的打算”。参见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史料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7页。华新纱厂的例子更加典型,20年代拥有四家纱厂,1931年天津总公司撤销后,各厂分别成立公司,横向一体化已名存实亡,而仅仅过了一年,唐山华新厂即完成了纺织染的纵向一体化。1936年,天津华新厂被日商并购,而同年青岛华新厂开办了染厂,转向纵向一体化,更于翌年设立了印花部,成为少有的纺织染印联营的全能厂。除此之外,1932年,裕大华纺织集团的大兴纱厂开设了一座小规模的漂染工厂。[9]申新纺织公司在武汉的第四厂也于抗战前夕添置了日产两千匹的全套漂染整理机器[10]。这两家纱厂纵向一体化染色生产的行为,虽未改变所属企业集团原有的横向一体化主体结构,但不能说没有受到棉纺织业纵向一体化潮流的影响,亦可反映一体化维度的转变。
纺织染纵向一体化的动机有多种,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管理协调成本。(10)“一个交易是在企业内组织(用信中的话说就是是否存在一体化),还是由独立的签约者在市场中进行,取决于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与在企业内进行交易的成本的比较。”参见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起源》,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8页。从市场购买原料,产品的规格、品种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要求,从而在与供应商协调时会增加大量交易成本,如无法协商一致,将会给企业生产带来困难,亦会产生交易成本。大成纺织染公司曾苦于从南通进购坯布“成本既大,规格亦不能统一”,给生产带来麻烦,于是决定创建大成三厂,以增加自给能力。[11]274丽新纺织印染整理公司也抱怨从他厂进购原料时,有些棉纱“不能仿造”,使一些生产活动无法进行,而“自纺纱织布,成本减轻”,“解除困难不少”。[12]111-112市场交易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由此产生的交易风险,企业也会选择纵向一体化。庆丰纺织厂曾与丽新约定漂染坯布的交易,但当产量增加、庆丰要求增加漂染坯布的交易数量时,丽新予以拒绝,尽管庆丰企业主唐星海亦是丽新的股东之一。[13]31市场交易的不稳定促发庆丰创办漂染整理工厂。永安纱厂“向托别人漂染”各种纱布,这让企业主郭乐“不知感受几许烦难”,“受人牵制”[14],难以防御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创办大华印染厂便是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当然,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纵向一体化的动因不仅来自经济范畴,政治因素也起到诱发作用。由于在华日资纱厂垄断中国细纱市场,民族纱厂出品以粗纱为主,且短时期内无法做到替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二三十年代抵制日货运动愈演愈烈,日商频频受限,细纱交易时时陷入困境,导致民族染织厂的原料交易成本居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即转向一体化上游(11)当时已出现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概念,如有论者指出“上下异种部门间之纵断的(垂直的)结合”。参见曾广勋《世界经济与产业合理化》,上海社会书店1932年版第74页。现代战略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商品沿纵向链条‘移动’——从原材料和零部件到生产,再经过运送和零售……处于纵向链条前面步骤的是生产过程的上游,处于后面步骤的则是生产过程的下游。”参见贝赞可等《战略经济学》,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从事纺纱生产,以获得稳定的细纱供应。[15]此外,日本纱厂联营印染生产,也迫使民族纱厂纵向整合的跟进。大成厂主刘国钧认为“日本人……是欺侮中国厂没有染色设备,申新纱厂没有染色设备,就吃了大亏,宝成纱厂也是如此”[16]18。为此,他曾赴日本考察印染,组建印花部时还专门从上海日资纱厂聘请工人,重点发展印染,与日厂争利。可见,纺织染联营的纵向一体化亦带有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
除纺织染联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纵向整合形式,即光裕营业公司的铁棉联营。20年代,大隆机器厂生产的纺织机械“大的中国厂家都不用”,即使通过私人关系售予申新的10部,送予恒丰的2部,也都被束之高阁。销售无路的绝境促使严裕棠涉入机器使用部门,租办进而并购了苏纶纱厂。这一纵向一体化行为切实缓解了大隆产品的出路问题,此后严氏不断扩大联营规模,1936年计划以大隆为基础专门建设一个“铁棉联合的企业”。[17]一些大型棉纺织企业的生产机器并非来源其附设铁厂,而大隆生产的机器基本供应与之联营的苏纶,且是唯一可以制造整体棉纺织机器的企业。因此,只有光裕营业公司的铁棉联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生产与使用单位的纵向一体化。
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形成染织联营、纺织染联营、纺织染印联营、织染印联营、铁棉联营5种纵向一体化类型(12)染织联营企业有华澄、启明、恒丰盛、中国内衣、光华、勤康、华阳、元通、勤丰、仁丰(上海)、鼎新、天一等12家;纺织染联营企业有三友、恒源、鸿章、民生、永安、庆丰、晋华、仁丰(济南)、嘉丰等9家;纺织染印联营企业有丽新、广益、华新二厂、达丰、上海印染等5家;织染印联营企业有光中、阳本2家;铁棉联营企业有苏纶1家(据第一部分史实分类)。。实现方式主要依靠企业自建。这说明布匹,尤其是花色布市场尚处于成长初期,染织行业空间及潜力巨大,竞争强度不大,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其时,染织业存在大量从事土法操作及准近代生产的单位[5]257-259。例如,抗战前上海开工的染织厂达270家,而真正机器染织生产的企业有40~50家,能进行印花生产的只有11家[18-19],整个印染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30年代,纵向一体化行为正在改变整个棉纺织业的产业格局,纺、织、染联营企业逐步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纵向一体化推动了华纱的高支化进程。随着机器染织业的发展,细质纱布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农村手工织业的衰退使粗纱市场逐渐缩小。在前阶段协助民族纱厂占据粗纱市场的抵制日货运动,此阶段却成为一再促发细纱问题的诱发力量。无论是民族染织企业对细纱原料急迫的需求,还是自建纱厂生产细纱的行为,抑或部分原先横向一体化的民族纱厂扩大细纱生产实施纺织染纵向的维度转向,都将促使还依恋于粗纱生产的民族纱厂提高产品支数。另一方面,纵向一体化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印染生产技术的水平。优势民族染织厂对染色、印花连续生产的纵向一体化,既扩大了机器印染生产规模在整个印染业中的比例,也将鞭策准近代生产部门尽快完成近代转变,并逐步淘汰土法印染部门,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发展。因此,优势民族企业的纺织染纵向一体化实际上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联动进步。
四、多元化从低程度趋向中高程度
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相继盛行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民族棉纺织企业虽然有一部分出现了低程度多元化的行为,但仍然以棉纺织生产为主导业务,可以视为多元化的雏形。个别企业则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态势,或是制订了多元化的经营计划,抑或开始了多元化的初步行动。鉴于抗战前横向解体和纵向下行的总体趋势,这些表现可以认为是向中高程度多元化演进的迹象。(13)多元化经营可根据其多元化程度以及各业务间的关联度加以区分。企业的资产、收入等在各行业的比重是考察多元化程度的标志性因素,其中资产投入比例是重要的指标。企业对某项生产或业务的资产投入比重反映了其在经营范围内的地位,总体的资产比重分配则体现了企业多元经营的结构类型。因此,本研究以资产投入比重作为区分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标准。低程度多元化,明确地说即非多元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型,即某单一生产或业务的资产大于等于95%;另一种是主导型,即某单一生产或业务的资产在70%~95%之间。中程度多元化,即主导的生产或业务资产低于70%,且各生产或业务之间只存在有限联系。高程度多元化,即主导的生产或业务资产低于70%,各个生产或业务间不存在联系。参见迈克尔·A.希特等《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概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孟卫东等《战略管理:创建持续竞争优势》,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241页。
出现低程度兼营行为的有3家企业。裕大华纺织集团在20年代是经营单一“事业”的企业。1932年并购利华煤矿后,棉纺织生产资本850万元,占87.6%[20],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杨氏长房(杨瀚西)资本曾创办过多家企业,但大多在1~2年内关闭,多种经营并未成功展开,只有纱厂和面粉厂得以延续。1937年,广勤纱厂资本180万元,占85.7%,广丰面粉厂资本30万元,占14.3%。[21]148、171、175-176,[22-23]较为典型的是无锡唐、蔡系统,其主体是庆丰纺织漂染厂,1937年时资本300万,约占81.1%;其次是九丰面粉厂,以1935年资本50万元计,约占13.5%;其他堆栈及其附设业务(约12万元)、榨油业(约2万元)、砖瓦业(约6万元)等的资本总和只占约5.4%。(14)无锡唐、蔡系统拥有益源、福源两座堆栈,福源可仓储粮食12万石,比益源多二成左右,则益源约可存储10万石,两者规模相差不大,并购福源的资金为6万,则堆栈业估算为12万元;润丰榨油厂开设资本为2万元,此后规模无明显增长;锦丰丝厂创办5年后的1924年即出租,于1928年歇闭,不计入内;利农砖瓦厂,创办资金3万元,有十八门轮窑,1933年又在别处添置一座十八门轮窑,估算资金为6万元。参见钱钟汉《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131页;黄厚基《无锡民族资本家唐保谦父子经营工商业简史》,《无锡文史资料》第四辑,1982年版第67~69页;利农砖瓦机械厂厂史编写组《无锡市利农砖瓦机械厂厂史》,1986年版第1页。尽管该企业涉入行业较多,但总体而言还是低程度的“兼营数种”,纱厂仍旧为主要的生产业务范围。
非典型性多元化企业有2家。大生集团的情况略有特殊,至1923年其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纱厂和盐垦公司,而盐垦公司主要是为纱厂提供原棉,因此两者是棉纺织产业链上原料产出单位和产品生产单位的纵向关系,应同属棉纺织生产部分。1923年,大生集团资本总共1299.3万两,纱厂708.4万两,通海垦牧40万两,棉纺织部类共计748.4万两,占57.6%;其他投入资本较多的五个行业中,海外航业贸易155.4万两,占12.0%,交通运输业100.6万两,占7.7%,食品工业85.9万两,占6.6%,金融业78.7万两,占6.1%,交易所43.2万两,占3.3%;其余各业共87.1万两,占6.7%。[24]相较而言,棉纺织部类在整个集团中的资本比重已明显下降,企业似乎脱离了以经营单一生产业务为主的结构,然所涉其他行业,尽管门类众多,资本比重却远远低于棉纺织部类。大生集团的棉纺织部类呈一头独大之状,其他各业投资偏少,虽已进入多元化,但展开不够充分。
中高程度多元化企业共有3家。荣氏茂福申新集团主要经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1932年,申新资产总值6423万元,占71.1%,销售总值6933万元,占52.7%;茂新、福新资产总值2616万元,占28.9%,销售总值6233万元,占47.3%。[25]尽管申新资产在集团中比重略高于70%,但从销售额来看,申新与茂新、福新却是差不多各占一半,两者都处于重要地位。另外,虽然申新与茂新、福新有面粉袋的供需关系,在原料采购和产品批发上也共享部分渠道,但产品属性、生产技术等都有很大差别。因此,荣氏集团实施的是有一定关联的多元化。
周学熙企业集团主要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华新银行、普育机器厂等构成。滦州矿务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企业单位的创办,虽与周学熙及其资本有关,但并非民族企业性质。(15)周学熙涉办的企业很多,详情可参见李林所制《周学熙与他的资本集团参办、经办实业表》。以往研究以资本为考察线索,凡其涉办及投资的企业均归为该资本集团,但以企业一体化的组织控制为标准来衡量,由周氏资本控股经营的企业并不多。关于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公司,盛斌与姜铎对于二者是否存在资本性质的转化问题见解不同,但对于二者属于民族企业的定性并无异议。华新银行和普育机器厂亦均为周学熙资本创办,后者资本尚不详。滦州矿务公司初为官办,1912年实际上被英资开平兼并,英方在开滦的经营管理上占绝对优势。耀华玻璃公司于1922年创办时即与比利时资本合资,1924年时中资虽占76%,但由于不善经营致业务不振,遂委托开滦代管营业。中国实业银行虽主要由商人资本创办,但无论在股权还是事权上周学熙似乎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否则不会于1921年下半年再筹办华新银行,待正式成立后于1924年辞去实业银行一切职务。参见李林《从周学熙集团看官僚资本的转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3期第53页;姜铎《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第66页;盛斌《关于周学熙资本集团性质的变化问题——与姜铎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第21~22页;程莉《近代实业家周学熙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1、209~214页;施公麟《天津华新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七十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1930年,启新洋灰公司资本有1308万元,占55.7%,华新在30年代的资本大概有1040万元,约占44.3%。华新银行1927年时资本额为100万元,占4.1%;普育机器厂资本额不详,所占比重应不大。(16)历次股本增加的情况参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6~257页。1930年天津华新资本270万,1932年唐山华新资本220万,1924年青岛华新资本270万(以后迄未增资),1923年卫辉华新资本280万。参见《华新纺织有限公司津厂》,《天津棉鉴·天津棉业调查专号》1930年第1卷第6期第3页;华新纺织厂厂史办公室《唐山华新纺织厂的历史变迁》,《河北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第56页;周志俊《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一辑第26页;王天奇《卫辉华新纱厂的变迁》,毛德富《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经济卷(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水泥生产与棉纺织生产基本不存在关联,华新银行的存款主要来自启新、滦矿等企业及周氏亲友,放款以四个华新纱厂为主,有一定资金上的关联。
1922年至1925年,永安集团的各产业资本情况是:永安纺织印染公司600万元,上海永安公司250万元,香港永安公司200万元,永安人寿保险公司200万元,永安水火保险公司75万元。(17)1920年以后港币折合大洋比为1。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上海永安公司经营环球百货、附设银行业部,并附属旅店、酒菜、游乐场等,香港永安公司经营环球百货、附设银业部,附属旅店、酒菜、织造、仓储等。参见《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12页;《永安资本集团各地联号企业(1931年前创办)》,《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19页。棉纺织业占45.3%,上海永安公司和香港永安公司主要涉及的服务业占34.0%,保险业占20.7%,三者之间基本无关联。
可见,中高程度多元化企业正在形成,并且规模均远远超过低程度多元化企业。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有一些民族棉纺织企业开始设想甚至尝试多元化的两种方向。
其一,多种产业体系的综合型多元化。1941年,兄长荣宗敬去世之后,荣德生希望在战后开创荣氏企业的新时代,建立一个宏大的企业集团,称之为“天元实业公司”。他所设想的企业“经营项目可分下列种类:(一)属于‘土’的方面,凡煤、石灰、水泥、砖瓦等类皆是;(二)属于‘金’、‘木’方面,如开采矿苗、冶金、铸锻、铁工、化学、塑胶,以至筒管、棉条筒的制造均是;(三)属于‘食品’方面,则面粉、饼干、点心之属皆是;(四)属于‘水’的方面,如漂粉水之类;(五)属于‘火’的方面,即电气等是;(六)属于‘纺织’方面,包括棉、麻、毛、丝、人造纤维的纺、织、印染、整理、裁制、缝纫等等”[6]152。
其二,多种原料纺织印染生产的专门型多元化。与荣德生相对,1944年3月荣氏长房继承人荣尔仁也提出了战后建设计划,在进一步扩大原有棉粉联营规模的基础上,实施“申新各厂战后整理,及建设计划”,即发展棉、麻、毛、废丝的纺织印染生产。与之类似,同年冬,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也拟订了一个以申新四厂为中心的“申新纺织公司战后复兴计划”,即发展棉、麻、毛、人造丝纺织生产。[26]
事实上,抗战前一些棉纺织染联营的企业已经开始一体化毛纺织染的生产。上海民生纱厂于30年代初添建了毛织、染色、整理各部。[27]1933年,生产棉织内衣的中国内衣织布厂开始致力于秋冬之羊毛内衣。[28]1935年丽新厂的唐骧庭和程敬堂与人合伙筹建协新毛织厂[29],1936年2月正式开工生产,1937年已发展成为自纺自织自染自整的毛织品工厂[30]。同年,大成纺织染厂也增设了毛纺织部。[31]可见,发展多种材料的纺织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
五、结 语
工业现代化的实现是通过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来完成的。1920年前后,民族纱厂的横向一体化实现了加速抢占原本由洋纱开拓出的机纱市场的目的,并在抵制日货运动的配合下不断排挤日纱,最终占领粗纱市场,完成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起步。然而,与传统手工织业结成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却使得民族纱厂在棉纱生产的高支化过程中产生较大的惰性。1930年左右,民族纱厂兼并重组的结果仍是继续坚持留在饱和的粗纱市场,进一步艰难地挤压手工纺业的空间。随着民族染织业开始兴起,近代和准近代生产部门对细纱原料的渴求与日俱增,而抵制日货运动又加剧了细纱的供需矛盾。一部分有实力的民族染织厂纵向一体化细纱生产单位以及部分原先横向一体化的民族纱厂从单纯或主要地增加细纱产量转向纵向整合印染生产单位。实现纺织染纵向一体化的同时,既加快了高支化进程,也增强了印染生产实力,从而推动了民族机器棉纺织生产技术的进步。此时,多元化初见端倪,现代机器生产又将随着民族棉纺织企业多样经营行为,在多种原料的纺织生产和其他行业中扩大范围。可见,优势民族企业的一体化经营行为,增加了民族工业中先进部分的分量,推动了工业化进程。更重要的是,这种一体化行为促进了传统和现代生产部门之间的糅合与嬗进,亦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一元化格局推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美企业不同,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是在没有充分积累的前提下进行的扩张,或者说是扩张和积累并行,以扩张加速积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一体化经营行为又是针对外商,尤其是日本在华企业的竞争逼迫,从而使这种超前行为带有特定目标的追赶性(18)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实施一体化战略具有追赶性特点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可行性、机遇及成绩等问题,参见赵伟《横连与纵合:近代民族企业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34~359页。;在民族矛盾日益急迫的近代中国,一体化行为又赋予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意义,具有民族防御性。无论怎样,产生这种超前的扩张行为,与中国社会经济中传统因素的支持有密切关系。然而,随着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在横向、纵向、多元三个维度拥有更广大的经营范围,在前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传统因素,如企业并购扩张中基于钱庄的资金运作,企业基层管理中基于地缘的工头制,企业上层管理中基于血缘的家族制等,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制度、组织管理、结构设置等都需要进一步革新。那么,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通过横向、纵向、多元的一体化行为,如何推动了企业内外经济环境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糅合与嬗进,又是如何生成和发展了中国特性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制度,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