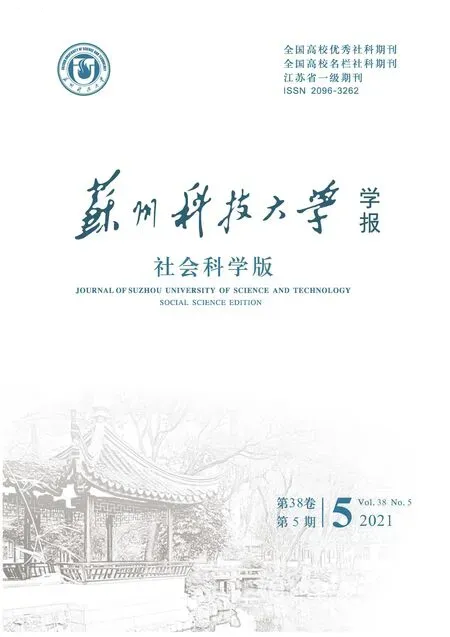试论《骷髅幻戏图》的“真”与“幻” *
张 旎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骷髅幻戏图》相传为南宋著名画师李嵩所绘。“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1)界画,乃一种依靠界笔、直尺的划线来进行绘画的方式,适于建筑绘画中,若配合工笔技法来绘制其他景物时,通称为“工笔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1]李嵩的画贵在“写实”,代表作有《货郎图》《花篮图》《观潮图》等。然而,这样一位崇尚写实的画家却创作出《骷髅幻戏图》这幅风格诡异、充满虚幻色彩和宗教风格的作品,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李嵩另有一幅《骷髅幻戏图》册传世,描写‘五里墩’的村头,妇婴们观赏骷髅戏演出的情景,但其真正的含义现在还不能做出合适的解释。”[2]“李嵩还画过《骷髅幻戏图》,描绘村头妇婴观看骷髅戏演出的情景,对此画的含义很难做出准确的解释,其中或许有庄子的思想在,而从所画可见,画家对人体的骨骼结构有充分了解,这在我国的绘画中是很少见的。”[3]鉴于此,笔者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骷髅幻戏图》的“真”“幻”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此画的“真”与“幻”在绘画构图、艺术媒介及艺术形象中的具体表现与相互关系,阐明其思想内涵、审美意蕴及当代价值。
一、《骷髅幻戏图》的“真”“幻”字释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真”解释为:“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段玉裁注曰:“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然其字古矣。古文作 ,非仓颉以前已有真人乎。引伸为真诚。”[4]691按照段玉裁的解释,“真”字本意为“仙人变形升天”,但在仓颉造字前并没有真人的说法,所以引申为真诚。徐克谦认为:“在中国思想典籍中,特别是在道家和道教的话语系统中,‘真’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出一个‘真’概念,并加以深入讨论,是从庄子和庄子学派开始的。”[5]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
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6]
此外,《说文解字》中“诚”“信”互训:“诚,信也。从言成声。氏征切”,“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因此,先秦典籍中的“真”“信”“诚”三字含义基本相同。那么,这三个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7]也就是说,“真”(实诚)与“伪”(虚妄)相对,指非人为的天然。
除道家外,佛家也讲“真”,但佛教之“真”与道教之“真”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孙昌武的说法,佛经因翻译的需要,借用了“真”字,并将“真实”二字合一,形成融合佛教义理的全新“真实”观,这里的“真实”是与可感的外在现象界相对应的“真谛”“真理”:
根据大乘基本教理,现象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因缘生,无自性,刹那灭,处在生、住、异、灭的流转变化之中。因此“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样,常识的“真”是虚妄的,“诸法实相”即般若空乃是绝对的、本质的“真”。而把握这种“真”,不是靠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而是靠内心神秘的感悟即禅悟。[8]
融合佛教义理的“真”表现为现象与本质的二分,旨在追求超越现象界外的本真。那么,本真是什么呢?佛教认为是“空”,佛教的“真”即指通过体悟达到超越感性现象界的空性。
因此,融合佛、道两家思想的“真”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从现象层面看,“真”强调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描述,反对虚伪,追求天然;第二,从本质层面看,“真”追求超越现象界背后的永恒、静止的世界,并表现为“空”。
再看“幻”字。“幻”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相诈惑也,从反予,《周书》曰:‘无或诪张为幻。’”“诪张”就是“欺诳诈惑”的意思。段玉裁对“幻”字注曰:“倒予字也,使彼予我,是为幻化。”[4]306因此,“幻”即指虚伪、欺骗和迷惑。汤凌云认为“幻”与“变”“化”语义相关:
“幻”也从“丝”,隐含着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或转化。与“变”接近的,还有“更”“改”等词,三者可以互训,都指变化、转变,它们可指某种事物或某种存在状态的终结,也意味着介入另一种事物或存在状态,还可指两种事物或状态之间的彼此关联。[9]2
也就是说,“幻”既意味着变化和转化,又意味着外在的现象界具有变幻不定、富于迷惑的表象。
此外,“幻”还与大乘佛教的色空观有关,指假相和幻象:
严格地说,与中国美学中的“幻”问题关联最为密切和直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佛教认为,“幻”是指“梵语my,指假相。一切事象皆无实体性,唯现出如幻之假相,即幻相;其存在则谓幻有。所显现之如幻现象,犹如魔术师之化作,故称幻化”。[9]3
“幻”作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概念,“它以般若空观为理论基础,强调事物以真空幻有的形态出现”[9]7。
由此可见,“幻”既指依附主体感官存在的、动态无实在的表象,又指真空为显现自身而存在于外在的形象状态,即世间一切实体都是“真空”的幻相显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曰:“色不异幻,幻不异色,色即是幻,幻即是色。世尊!受想行识不异幻,幻不异受想行识,识即是幻,幻即是识。”[10]可见“幻”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现象界中依附主体感官存在的、动态变化着的无实在的假相或表象;二是指虚空本质为显示自身而存在于现象界的外在形态。
对艺术创作活动来说,“真”与“幻”的关系是“实”与“虚”,这不仅需要创作者模仿感性世界中的客观真实,而且要求超越客观实在抵达想象世界的真实。一方面,艺术真实要植根于现实生活,通过对客观现实的精准把握发挥主体的想象力,做到外在真实;另一方面,艺术真实需要创作主体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展开想象,不拘泥于现实,做到内在真实。熊十力先生说:
吾人必须荡除执着,悟得此理,方乃于万象见真实,于形色识天性,于器得道,于物游玄。……真正画家必其深造乎理,而不缚于所谓现实世界,不以物观物,善于物得理,故其下笔,微妙入神,工侔造化也。岂唯画家,诗人不到此境,亦不足言诗。[11]
也就是说,真实和虚构无法分离,艺术虚构的发生需要在把握客观真实的前提下方能展开,没有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可以脱离真实而存在。然而,无法脱离绝不是意味着必须墨守成规地采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如实描绘,而是要求创作者和接受者都能发挥主体想象,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在虚构的空间中看到自身、超越自身,实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
二、《骷髅幻戏图》的“真”“幻”表现
在《骷髅幻戏图》中,“真”与“幻”主要体现在绘画构图、艺术媒介与艺术形象中,表现为虚实结合、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动态循环关系。
《骷髅幻戏图》绢本设色(见图1),绘于纵27.1厘米、横26.3厘米的扇面册页上。左侧署有李嵩的名款,画面钤有“会侯珍藏”“信公珍赏”等几方收藏印。整个画面被分为左、右两个区域,左边区域的中心人物为一个头戴黑纱幞头、身穿透明纱袍的大骷髅。纱袍底下,大骷髅的骨骼清晰可见,他席地而坐,左手按在曲折着地的左腿上,右腿呈三角状支起,右肘抵于右膝上,正悠然自得地挑起木架,提控着一只小骷髅。数缕丝线支配下的小骷髅张口嗤笑,双肘弯曲向下,双掌做招手状,左腿抬起,右腿触地。小骷髅的视线正对着一名向它缓慢爬来的小儿。大骷髅身旁的一担行李中有雨伞、草席、水壶、箱笼、网等生活用具。其身后为一年轻妇人,怀抱婴儿,盘腿而坐,敞开衣襟,作哺乳状,她目光越过大骷髅,正关注着画面中央小骷髅与小儿的嬉戏。妇人背靠一座砖砌方台,台上正中立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有“五里”字样。右边区域有一大一小顺着斜坡往上的两人。小人是受小骷髅召唤、匍匐爬行的小儿,只见他神色好奇,左手与左腿着地,昂首伸出右臂,似要抓小骷髅般。大人为小儿身后的青年妇人,看似富贵人家的亲眷,双手伸出似正在阻拦,表情着急,头上配有简易钗饰,身后亦画有几枝墨竹。

图1 李嵩《骷髅幻戏图》(绢本设色)
就构图而言,画面空间的布局营造出虚实相生的真幻结合感。画面左右区域呈现左重右轻、左密右疏。造成这种密集感的原因在于,左边区域的行李担、土墩、大骷髅和哺乳妇人的摆放给人以厚重、实在、密集的感觉,为画面增添了“实”质;而右边区域只有小儿和青年妇人两人,画面留有大量空白,呈现出“虚”感。左右对比下,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对称和不均衡感。这种构图旨在将观赏者的目光汇集在左下方区域,疏散了对右边空间的注意力。可以说,创作者有意将接受者吸引到画面的核心位置,使观赏者的目光从傀儡戏转移到左边区域的大骷髅。为了将画面的两大区域平衡,创作者在右边区域中画上斜坡,使整个右侧区域的空间形成上升的趋势,从而平衡了由左边区域带来的厚重感,使接受者在欣赏画面时获得感官舒适。“中国古代绘画讲究‘因实生虚’,立足于‘实’而追求‘虚’,充分凸显了‘实’与‘虚’之间的艺术张力,成功地建造起了一座突破有限造型而通向无限彼岸的艺术之桥。”[12]
就艺术媒介而言,作者以线条的浓淡和力度的深浅营造出虚实相生的艺术氛围。李嵩以刚健有力、顿挫分明的线条勾勒出大小骷髅精密的骨骼形态,表现出骨骼的刚硬;以柔和圆润的笔法描绘出小儿和妇女相对虚幻、轻盈的容貌、体态。对行李担中的物品,以疏淡的笔法表现出网的轻盈,以刚健的笔法传达出扁担木料厚实的质感。虚实交替、真幻相生,创作者就在方寸画纸间传达出生与死、真与幻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东方绘画多以线条展现美感,依靠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体会和想象,将线条的流畅美呈现于“虚”的留白世界,以弥补画面的未尽情意,抵达画外之境。
对国画来说,线条乃画家凭以抽取、概括自然形象,融入情思意境,从而创造艺术美的基本手段。国画的线条一方面是媒介,另方面又是艺术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思想感情和线条属性与运用双方契合,凝成了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的艺术风格。[13]
就艺术形象而言,画中人物表达出真幻相生、相合的思想内涵。图2中,笔者将画中人物的视线顺序用箭头标示出来,通过“真”“幻”二分将哺乳妇人、小儿、青年妇人视为“真”(指现实存在的人物和事物,亦可代表活着的生命体),将大、小骷髅视为“幻”(指现象界中依附主体感官存在的、动态变化着的无实在的假相或表象,即现实不存在的表象,亦可代表死亡)。

图2 《骷髅幻戏图》“真”“幻”示意图
那么,哺乳妇人、小儿与青年妇人之“真”有何不同呢?笔者认为,小儿和哺乳妇人怀中的婴儿本质一样,都象征“赤子”“童心”或者“婴儿”,他们的“真”是本真。《老子》第十章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14]道家用“赤子”或“婴儿”比喻赤诚、真诚,因为婴儿是人生最初状态,未经人世玷污。婴儿是本真,是超越一般表象的真,其与天地合一,与道合一,是最理想的状态。
婴儿。婴儿能静、和、柔而不离于自己的性质(德)。这种性质是道表现出来的自然本性。婴儿自然无欲,智慧未开,也没有奸巧诈伪。万物依道而生存。婴儿天真,无所用其心,纯任自然生长。老子的婴儿是“德”,又表现着“道”。道与德(各物的本性,潜力)同是一体,不是二体。……
……婴儿混沌无知,与天地和合为一。婴儿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特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他专自然之气以达到柔和的境地。[15]
与此相应,青年妇人之“真”和哺乳妇人之“真”则代表现实世界的实体真实。但是青年妇人和哺乳妇人又有不同,哺乳妇人乃孕育本真的母体。换句话说,本真要以现实之真为基础,基于自然客观的规律,所以它蕴含在表象之真和现实之真中。
大、小骷髅之“幻”又有何差别呢?笔者认为,大骷髅为本质之幻(至幻),小骷髅为表象之幻(幻象)。表象之幻是现象界中依附主体感官存在的、动态变化着的无实在的假相或表象,它诞生于本质之幻,并受到本质之幻的制约。而本质之幻就是空,是表象之幻的本质,它的显现要通过小骷髅所代表的幻象来实现,这一点恰好与象征着死亡的骷髅形态相对应。“事物各以其独特的形相呈现,这是即形相而称相,因分别而立名。具有名相的事物,就像各种幻喻一般,相待而有,因缘而成。”[9]5
由图2可见,小骷髅(幻象)吸引着小儿(本真),大骷髅(至幻)操纵小骷髅,青年妇人(现实之真)追逐小儿,作为旁观者的哺乳妇人(现实之真)始终关注着小儿与小骷髅的游戏,而小儿和青年妇人似乎看不到骷髅们骇人的形象。笔者认为,作为客观真实的现实生命体会本能地被幻象所吸引,而幻象的本质又是至幻,所以客观真实也在追求着至幻。同时,至幻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努力追寻本真。客观真实一方面追求纯洁天然的本真,另一方面又是本真的基础和母体,二者构成一个循环反复的回路。在审美领域,客观现实(青年妇人、哺乳妇人)蕴含自然真理(小儿),审美意识的发生又需要主体超越客观现实发挥积极想象(大骷髅)。这种想象又以客观现实为基础,蕴含着自然规律,以卓越的艺术形象(小骷髅)表现出来。由此,《骷髅幻戏图》的“真”与“幻”就在艺术形象中表现为虚实结合、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动态循环关系。
三、《骷髅幻戏图》的“真”“幻”超越
《骷髅幻戏图》是南宋写实主义绘画风格盛行的背景下诞生的一幅超写实主义作品。该作品在虚幻诡谲的风格中蕴含着“尚理贵真”的格物精神,同时也超越了南宋绘画的写实局限,展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和追求,以及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甚至体现在当代艺术作品的重塑中,展现出古今时空的超越。
首先,在“尚理贵真”的思想观念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宋代风俗画崇尚对客观实物进行精准描摹。两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宫廷绘画的题材和内容逐渐从北宋初期以寺庙壁画和道释宗教为主的人物画,转变为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也使两宋风俗画的选题须迎合当时宫廷贵族和平民百姓共同的审美喜好。因此,宋初涌现大批风俗画画家,“风俗绘画繁荣发展成为两宋时期除宫廷绘画之外另一独特的绘画风貌。两宋时期的风俗画所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主要以农田耕作、街市贸易、节令百戏、货郎担货、村医灸艾、婴孩戏耍、醉翁踏歌等等百姓世俗生活中常见的趣闻乐事作为创作源泉,涌现了如张择端、李唐、李迪、李嵩、阎次平、苏汉臣、刘松年等等众多名传千古的风俗画家,为两宋风俗绘画艺术留下了大量极为宝贵的精品”[16]。
其次,宋时画派主要分为院体画和文人画,院体画为达到伦理教化功能和普世价值,主张“写实”和“逼真”,讲究真实地再现外在的物象;文人画强调抒发个人情感,主张“写意”,讲究从局部的“形似”中超脱出来。李嵩作为南宋光、宁、理三朝的宫廷老画师必然受到当时院体画“写实”风气的影响。“宋代院画的绘画本质观就是要求绘画在发挥伦理教化功能基础上的写实理念。因为绘画通过‘铸鼎象物’或者描绘暴君贤相以达到教化目的,其理论假设是:绘画是写实的,能让人感受到是所象之物和人物像。”[17]
再次,宋代医学发达,尤其是法医学格外成熟。宋慈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不仅涵盖尸体方面的各种死伤鉴定,而且涉及精准的生理、解剖、病因、药物等医学知识。其“验骨篇”对人体骨骼就有详细、精准的描述:
髑髅骨:男子自顶及耳并脑后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脑后横一缝,当正直下至发际别有一直缝。妇人只六片,脑后横一缝,当正直下无缝。牙有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胸前骨三条。心骨一片,嫩,如钱大。项与脊骨各十二节。自项至腰共二十四椎骨,上有一大椎骨。肩井及左右饭匙骨各一片。左右肋骨:男子各十二条,八条长、四条短;妇人各十四条。男女腰间各有一骨,大如手掌,有八孔,作四行。手、脚骨各二段,男子左、右手腕及左、右臁肕骨边,皆有捭骨。妇人无。两脚膝头各有奄页骨,隐在其间,如大指大。手掌、脚板各五缝。手、脚大拇指并脚第五指各二节,余十四指并三节。尾蛆骨,若猪腰子,仰在骨节下。男子者,其缀脊处凹,两边皆有尖瓣,如棱角,周布九窍。妇人者,其缀脊处平直,周布六窍。大、小便处各一窍。骸骨各用麻草小索,或细蔑串讫,各以纸签标号某骨,检验时不至差误。[18]
由此可见,正是宋代医学体系的完备,才使李嵩的写实能力完全发挥出来,精准、传神地描绘出大小骷髅的形象。
尽管后来黄公望、王重阳曾以这幅画来传全真教之“白骨观”思想,但笔者认为,此画可能融合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所绘并非以传教为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骷髅幻戏图》是李嵩最擅长的《货郎图》的变体,是他借用这常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死观和真幻观。这幅画同样超越了南宋院体画的写实之限,表现出一种文人画的写意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依靠画面模仿镜像的人生,在生与死、真与幻的对照中,以诙谐幽默的场景表现人生幻灭之空。
最后,《骷髅幻戏图》既完成了真与幻的超越,又完成了古今时空的超越。在2017年第57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我国著名苏绣艺术家姚惠芬创作的《骷髅幻戏图》苏绣系列作品,以“一图九变”的方式使这幅古老的宋画焕发出当代生命力,同时也开创了当代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先河。与宋画《骷髅幻戏图》相比,苏绣《骷髅幻戏图》更加立体、精致,光影色彩变化更加多样。姚惠芬采用50多种传统针法,用细密交错的丝线语言表现出原图中的每个事物,可以说在每个事物的背后,都蕴含着极细微地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这种充满矛盾冲突的刺绣语言建构起“和而不同”的审美张力。[19]不仅如此,苏绣《骷髅幻戏图》更是在李嵩本人的绘画主题和思想观念的自我超越基础上,实现的一次跨越时空和技法层面的超越。这种超越传达出不同艺术媒介之间转换的可能性,为日后其他传统作品的当代表达提供了典范。以苏绣《骷髅幻戏图》2号作品为例(见图3)[20],宋画的背景采用留白方式,呈现出空幻之境,而苏绣作品将背景做实,采用云纹样式,创造出云海波澜的意境,给欣赏者一种波澜与诡谲并存之感。

图3 《骷髅幻戏图》(姚惠芬苏绣)
综上所述,阐明《骷髅幻戏图》“真”与“幻”的关系,不仅能深入了解该画的思想内涵及审美意蕴,而且能全面立体地展现出南宋绘画“尚理贵真”背后,创作者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对自我的超越,对形式的超越,以及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超越。同时,该画在古今的艺术碰撞中,在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绘画与刺绣)的融合下,以全新的艺术面貌进入当代,重焕生机。刺绣赋予绘画丰富立体的光影性和多面性,绘画赋予刺绣深邃的立意和思想内涵,两者相得益彰,既传达出不同艺术媒介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又为我国传统艺术作品的当代表达提供借鉴意义,也为我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传统回归提供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