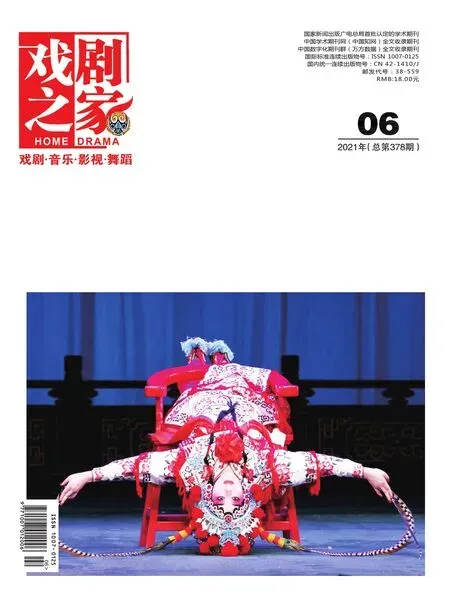再论元杂剧之“杂”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这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致使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文化方面,统治者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存而均为其用的政策,因此文学创作上,传统汉文化得以继续占据主流,但为防止汉人的官宦仕进之路过于宽广,元朝统治者长期停止了科举考试,客观上就迫使一批文人多与艺人组成书会,进行杂剧创作。王国维先生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杂剧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朵奇葩,特点鲜明。综上言之,元杂剧的创作中杂糅了许多文化因子,如汉文化的词牌艺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世俗文化艺术等。这些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元杂剧继承了大量唐宋词牌艺术
“元杂剧中的曲和唐宋词一样也有‘牌’,使用曲牌体音乐。词叫‘词牌’,曲叫‘曲牌’。‘牌’是一种人们熟知的通行的旧有曲调,是一种音乐上的标识。在这种固定的曲调上填写新的歌词,这种曲调就是‘牌’,如【念奴娇】、【采桑子】之类”。元杂剧宫调由许多曲牌组成,曲牌是传统填词制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俗称“牌子”。
元杂剧中的曲牌艺术在创作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大量的词牌艺术。剧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虽对“牌”的内容进行了艺术扩充,但许多曲牌仍按照词牌的句法和格式进行填词创作。例如:
菩萨蛮(词)辛弃疾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这首宋词,词牌名为【菩萨蛮】,它由上、下两阕组成。上阕是由两个七字句及两个五字句组成,下阕由四个五字句组成。这是【菩萨蛮】的定格。
菩萨蛮(曲)侯正卿
镜中两鬓皤然矣,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
这一首【菩萨蛮】,虽然因诸宫调联套在音乐形式的要求,只有四句而已,但它完全继承了宋词的词牌名,并且也是由两个七字句及两个五字句组成。它实际上只有宋词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突破了宋词格式上的限制,只取其一半进行创作演唱。可以说,词牌的双片转化为曲牌的单片,是词牌被继承及被曲化的标志。
元杂剧中的曲牌与宋词中的词牌相比,在句式、音乐上有共同的格式及旋律,相同“牌子”的曲调仍以固有“牌子”为基础,但元杂剧又依据唱词的不同特点,对传统的曲调进行不同的变化处理。因为杂剧曲牌的曲谱允许有变格别体,这种处理,又充分保持着这一“牌子”的某些基本特征。
正因元杂剧曲牌艺术对唐宋词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在杂剧中一支曲牌往往又能演变出许多不同形式的曲调来。这一变革使得曲牌能摆脱它固有形式的限制,可以做出丰富多样的变化,从而具有更大的适应力和表现力。
二、杂糅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因子
元朝的疆域比之汉唐更加广阔,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杂剧作为元代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无论是其创作内容,还是其文学语言,都有多元文化的注入。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一)剧中的蒙古族文化因子
自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其文化也在与中原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被百姓所接受,在元杂剧中便有不少涉及蒙古族文化的剧目。
元杂剧中出现了很多蒙古族语言词汇,如《陈州粜米》中出现的“虎刺孩”,也作“忽刺孩”,蒙语为强盗的意思。再如在《窦娥冤》等一些剧目中经常出现的“歪剌骨”,是蒙语中骂人的话,有贱骨头的意思。元杂剧中有着大量以汉语和蒙语交杂的曲词,如《货郎旦》中哥哥罚孙二在风雪中跪拜,孙二唱:“【叨叨令】则被这吸里忽刺的朔风儿那里好笃簌簌避,又被这失留屑历的雪片儿偏向我密蒙蒙坠,将这领希留合剌的布衫儿扯得来乱纷纷碎。”整段曲词就以汉语杂糅蒙语的形式描绘孙二穿着破衣烂衫长跪在风雪中的可怜场面。这样的曲词正是蒙古族文化对于汉文化渗透的表现。
(二)剧中的女真族文化因子
元杂剧中也出现了一些女真语言词汇,虽不及蒙古族语言出现的频率高,但也着实影响了剧作家们对元杂剧的创作。比如《五侯宴》、《货郎旦》等中出现的“阿妈”,再如《货郎旦》中出现的“兔鹘”。女真词汇虽不如蒙古族词汇多,但也仍然证明了元杂剧对女真文化的借鉴。
女真族民俗文化也构成了元杂剧的一部分内容,如《货郎旦》中:“他系一条兔鹘,海斜皮偏宜衬连珠,都是那无暇的荆山玉。整身躯也么哥,缯髭须也么哥,打着髭胡,走犬飞鹰,驾着鸦鹘……那行朝也么哥,恰浑如也么哥。”此曲词,通过对女真官员形象的描述,也鲜明的刻画出了女真民族的生活习性与外貌特征。这名女真官员身材雄壮高大,骑马驾鹰并留着髭须,“兔鹘”为女真语,指女真族人束衣服的玉带。由此不难看出,女真民族民俗文化已在元代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因此也作为当时一种文化因子,被元杂剧所吸收与融合。
(三)剧中的回族文化因子
在元朝南征北战下,或因战争被俘,或因贸易,大量的回族人居住在中原地区,回族民俗文化也影响到汉地的方方面面。
如回族饮食文化就被剧作家们直接在杂剧中表现出来。《酷寒亭》中出现的秃秃茶食,就是颇受民众欢迎的回族饮食。再如《东堂老》描写的另一种回族美食“大食店里烧羊”,也颇受百姓欢迎。“大食店”是回族人开的饭馆,烧羊也是回族人喜爱的食物。可见,回族文化因子不仅影响到当时民众的生活饮食,而且亦影响到剧作家的创作内容。
三、内容吸收了大量世俗文化
正是因为有民间文化这块沃土,才让元杂剧这朵文学艺术奇葩开放得无比美丽。也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元杂剧接“地气”,颇受民众欢迎。元杂剧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民间元素的注入,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
(一)世俗元素对元杂剧形式的影响
宋元民间故事文化对元杂剧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宋元时期,更加生活化的民间写实故事大量出现,这些故事中“半数为案狱题材的故事类型”,公案题材的元杂剧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其影响,多为“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剧作家在对涉及公案题材的元杂剧创作中,往往在主线大故事中插入小故事、小插曲,来让情节更精彩。如著名的《窦娥冤》中,窦娥受冤的故事是主线,本在窦娥“三愿”应验后,已可作为全剧精彩的结束,但关汉卿又在主线大故事后,嵌入窦娥化为孤魂让窦天章为自己洗冤的小故事,让全剧更加的精彩,更受民众喜爱。元杂剧创作形式的安排,正是由于剧作家受到民间故事悬念性、感染性的影响,这样的结构形式也更受民众喜爱。
(二)元杂剧内容中出现的世俗元素
世俗元素为元杂剧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鬼神显应、民间信仰、算命占卜等,对剧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可忽视。如《盆儿鬼》中,瓦窑神戏弄盆罐赵,是通过鬼神对恶人进行惩罚。这些杂剧通过鬼神显应的朴素民间元素,使得杂剧剧情更加跌宕起伏。民间信仰对一些元杂剧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元杂剧研究方面,《桃花女》并不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但就民俗文化层面而言,它却具有其他剧作无法替代的价值。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利用“桃木”来辟邪驱鬼的传统风俗,剧中“桃花女”就是以“桃木辟邪”为意象,代表下层世俗文化,来对抗剧中代表精英文化的周公,最后“桃花女”的胜利也象征着下层世俗文化的胜利。这些世俗元素在元杂剧中的大量出现,不仅让杂剧受众面更广,而且也丰富了其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元杂剧作为一种融合吸收多种文化元素的文学形式,不仅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时代风貌,而且继承发展了汉文化词牌艺术,杂糅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因子,取材于世俗元素,最终又回馈民众,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在剧作中所表现出的各民族文化元素的碰撞与融合,也是中华民族“和”之精神的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