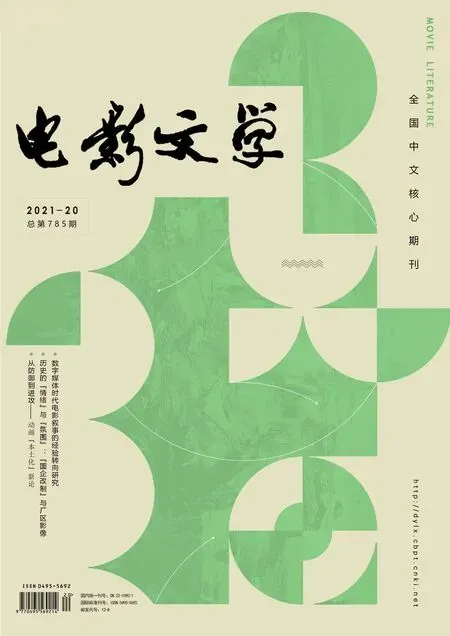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主观化倾向
尹耀东 赵佳瑞
(1.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2.又石大学,韩国 全州 565-701)
英格玛·伯格曼是瑞典的著名导演,其电影创作影响深远。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我们的水平线,作为读者,我们不可能不是“后莎士比亚的”——这样的评论完全可以用来表达伯格曼对观影的影响。在某种层面上,伯格曼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像生活在伯格曼的镜头中一样,透视着面孔特写下的情绪;伯格曼的思考变成了我们的思考,我们采取伯格曼的态度,忧虑在20世纪中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与个体精神生活的动荡。
一、特写镜头与主观叙事中的主体
在伯格曼开始电影创作之前,特写镜头普遍被认为是一种辅助叙事手段,战后的好莱坞电影将其滥用为现成的套路,在这些电影里人物的大特写等于是在预告某种不祥之事即将发生。然而特写镜头在伯格曼的电影里却显得更加安静、深沉,因为在整体意图上,他无意创造悬疑情节来获得观众的注意力,他专注于思与知在生活事件中的感性显现,专注于事件之下的主观化表达,而在这样的总体视角下,特写镜头自然有了别样的用途。
首先,伯格曼将特写镜头发展出二元布局的构图特征。《婚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只有丈夫约翰与妻子玛丽安两个而已,孩子、父母、第三者宝拉和二人后来的配偶都仅仅作为故事背景而模糊存在。伯格曼选择了电影的语言以最少的人物讲述宏观的婚配制度和两性最为常见的关系。在丈夫约翰向妻子玛丽安坦白的场景中,特写镜头根据对话而不断切换,但每一镜头的构图中除主体之外又都包含部分的第二方。这暗示着婚姻关系的本质就是切割自我而达成隐形的契约。但主体又无时无刻不在挣脱契约的束缚,企图恢复完整的人格,于是就这样产生了周而复始的矛盾。如此的二元构图特写并非孤例,《秋日奏鸣曲》中母女弹奏肖邦的一幕以相似的镜头暗示着丰富的画外之音。强势自私的母亲与怯弱愤恨的女儿,在音乐和凝视中合二为一。
对伯格曼乃至20世纪以降的西方艺术语境而言,主体观察视角的变动都与哲学上语言学的转向有直接的关系。巴赫金便以对话论证人总是在,也只能在与他者的交往中观察自身,越是纯洁的个人行为越是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段两人的对话:第二个交谈者的对语被全部略去,整个意思却丝毫没受损失。这里,这两个交谈者是无形的存在,虽然不见他的语言,可他的语言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正是这种痕迹左右着第一个交谈者的所有对语。”
伯格曼的特写镜头也以“第二个交谈者”的角度极大地增强了镜头语言的表现力。《婚姻生活》的坦白场景中,玛丽安表现得唯唯诺诺,但或许并非是她最忠诚的反应,而只是在夫妻互动中的惯性,她在此仅仅是“约翰的妻子”而不是玛丽安。《秋日奏鸣曲》中,母亲夏洛特弹奏肖邦时女儿的凝视也并不仅仅因为牵连起陈年的怨恨,还有远为复杂的层面:崇拜、眷恋甚至痴迷,这些情感不断地将伊娃从一个成年女人变回妈妈的女儿。伯格曼在此体现出了对现代主体性的惊人洞察,他的电影视角怀疑世界上有任何纯粹的自我,怀疑与现代社会互为因果的孤立存在是否真的可能。这一思考在伯格曼的电影中很早便外化为主题,《假面》中爱玛在不断地独白中逐渐变成伊丽莎白影子,成为他人的替身就是这一主题的极端表达。
其次,伯格曼式的特写镜头可以表现情节和语言都难以传达的人物主观世界的分裂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神秘体验。《婚姻生活》的坦白场景中,约翰声称爱上了宝拉,并希望离开这个家庭和宝拉去巴黎同居半年。此时玛丽安的神情从其自身来看无疑是震惊的,然而玛丽安更深层的反应却是一种分裂感。特写镜头在此处成了反讽的手段,以人物和镜头的突兀揭示了作为物理存在的面孔和作为精神存在的情感的不对称关系。此外,伯格曼的特写镜头指引着我们浸入画面,体察到人物的情绪波流的同时,呼吁我们超脱画面,因为盲目的信从会遮蔽掉画面本身微妙的反讽张力。
伯格曼指出我们依赖于感官,但不能够信任它作为精神的表征,正如这一场景中的双重撕裂所造成的表达困境。纵向的撕裂带拉扯着和生活:玛丽安与丈夫的生活看起来美满幸福,电影也事无巨细地如此展现他们的生活片段,从早上的闹钟到夜晚读的书都建构着一个北欧中产家庭的稳定想象,然而这种稳定的生活却最终被揭露为仅仅是生活的表面,丈夫早已开始偷情而朋友全都知情,只有玛丽安一人蒙在鼓里。在横向上,玛丽安又深受自我分裂的困扰:作为离婚律师,她虽然不断看到亲密关系的破裂,但相信自己能够使用一些理性的策略来处理。然而作为一段婚姻的参与者,她的体验却在颠覆着理性的认知。语言在面对这样的深刻的撕裂感和非理性处境时显得格外无力,伯格曼的镜头话语也并非是在提供一个完美的答案,但已是足够好的问题。
二、基督教神命论的艺术与伦理阐发
英格玛·伯格曼的父亲恩里克·伯格曼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教神父,伯格曼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充满自身独特的阐释。伯格曼认为宗教的权威被去魅可能是一个不能被逆转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不会再以传统的形态出现。但读经释经、礼拜祈祷等群体仪式的没落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精神影响力的削减,在伦理的领域内,在私密的个人交往中,神性的影子无处不在。
《处女泉》用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讨论了一个根本性的神学问题:为什么在有一个全能的善的神存在的前提下,还有灾难产生?卡琳的父母都是虔敬的教徒,派女儿卡琳骑马为教堂送蜡烛作贡品,在路上卡琳被三个牧羊人奸杀。牧羊人随后投宿到卡琳父母家中,在识破三人的罪行后卡琳的父亲陶尔亲手为女儿复了仇。电影作为一个叙事整体从镜头语言到文化符号都深刻地质问、控诉着神的道德。陶尔在复仇前拔树的全景镜头是影史经典,其视觉冲击力强烈地表现在画面中空无一物,人力与天命,人与树/自然/上帝的对抗感最大限度地构成了画面的主体。
此外,这种对抗感又表现在对神圣物的亵渎上,电影中的歹徒作为牧羊人登场,然而在《圣经》中羊和牧羊人都是绝对神圣的符号,前者是献给上帝的祭品,而后者正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化身。处女也同样是对圣洁的隐喻,牧羊人对其犯下的奸污、杀害的罪行更是连续触犯摩西十诫中的两条。故而,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看《处女泉》才能感受到它的触目惊心:卡琳这样一个纯然无辜的少女在护送祭品香烛的路上遭到本为神化身的牧羊人的奸杀。陶尔的愤怒正来自神的荒谬。电影中的伦理冲突是作为信徒的陶尔和作为父亲的陶尔所感受到的冲突,本质上讲就是神命论道德与自然法伦理之间的古老冲突。
在神命论道德的体系中,道德起源于上帝,人行事的规则必须依据上帝的意志。《处女泉》所展现的悖论正在于上帝的道德律令却给人以痛苦,全知全能的神默许了罪恶的发生。陶尔在找到了女儿的尸体后悲痛地跪下来质问上帝,导演若以传统的镜头手法来处理这一幕必然选择拍摄人物的近景,强化面部的狰狞活动。然而钟爱特写镜头的伯格曼在此处却从陶尔的背后安置镜头——这一幕中不仅有人,更有神(自然)的参与。随后,陶尔进行忏悔并发誓建一座教堂赎罪,这位虔诚的父亲将女儿的尸体搬开,众人惊诧地发现在她的身下涌出了清澈的泉水。
伯格曼或许从知识的维度上摇撼了基督教,但在信仰的坐标上他仍然还是一个虔诚的导演。他质疑作为一种体制和教条的宗教,但他仍然选择相信在属肉与物的科学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属灵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应当被人的良知与沉思默祷所承认。它也会在很多时候向人显现,《处女泉》中的泉水与《秋日奏鸣曲》中伊娃对埃里克的思念都是如此。基督教伦理在伯格曼电影中更多以家庭为场景,夫妻、母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这些电影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秋日奏鸣曲》中展示了神人关系与人人关系的对照:后者的破裂往往根源于前者的破裂。埃里克夭折,伊娃表示她悲痛但并不绝望,因为“感觉我们相互住得很近……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我们可以相互沟通,没有分界线,没有不可逾越的墙”。在这种宁静的爱中,伊娃原谅了母亲;而在这种爱的缺失下,夏洛特却选择逃避自己的罪愆,再次以虚伪来掩饰虚空。
三、理性与身份:存在的双重“假面”
伯格曼的视听语言曾被视为先锋派的代表,其具有强烈陌生感的形式伴随着对感性、理性的全新开掘,身处在战后存在主义的知识语境中,伯格曼和存在主义之间的确有着天然的适配性。二者同样专注于被以理性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压抑的自由存在,人在被合理化、合逻辑化之前的原始状态,一种“与脐带的原始冲动一起出现”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注定不能再通过套用陈旧的电影形式而完成。
观看伯格曼的电影似乎能触摸到人的梦境,叙事过程插入的跳切镜头寓意着人物内心潜意识的冰川仿佛如同梦境一样忽然闪现,我们也能够得见一瞥那些被合理化的现实法则所压抑的无意识世界。丽芙·乌曼扮演的女演员伊丽莎白忽然失语,所有的检查都证明她身心无碍但是她始终无法恢复语言能力。《假面》从一开始就打破了科学理性无所不能的假象,甚至暗示着当理性成为制度化和本质的要求,它就变成了一副窒息人性的假面。伊丽莎白在理性的解剖下只会闭口不言,条分缕析的研究将沟通的壁垒越砌越高,她在医院里被治疗自然也就不会好转。
理性制度外,我们还要面对亲密关系中的虚伪。人在伯格曼的戏剧中是无比孤独的个体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用家庭关系来定义自己为××的××,试图以此为借口搁置对自身生存的探索,其结局却如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一样,谈话的两个陌生人最后发现对方正是自己的配偶。伯格曼惯于展现那些亲密关系中的荒谬感,爱玛对未婚夫隐瞒偷情和《婚姻生活》里的约翰如出一辙,伊丽莎白所面对的职业与家庭的冲突也让人看到了《秋日奏鸣曲》中夏洛特的影子。在我们努力将自己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同一化的过程中,反而拉扯出更深的鸿沟,身份也成了一副假面。
《假面》的开头就具有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感,几组毫无联系的镜头被拼接在一起:蜘蛛、动物被宰杀、被铁钉钉穿的手掌心,还有老人安详的脸——这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镜头都是死亡的意象,象征着童年时期的伯格曼对死亡的初次接触。《假面》的序幕以一个男孩隔着玻璃触碰一个模糊的女子头像而结束。短短的几分钟序幕营造出了总体的基调与氛围:死亡与生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物而是最大限度地彼此依存着。人与人的界限在剥除外在的身份后也形同虚设,护士爱玛在对伊丽莎白的独白中渐渐与病人的身份相混淆,甚至伊丽莎白的丈夫也将她误认。伯格曼认为不存在绝对的隔离或区分,依赖于主客对立来建构的本质性定义只是一种假象;存在主义以最为人知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打破本质主义的束缚,从哲学的角度将事物回归到本真状态。二者的探索相互补充,假面背后的真实方渐渐揭晓。
结 语
从《处女泉》到《秋日奏鸣曲》,伯格曼以主观化、内倾性的视听语言处理不同的题材,并不提供任何清晰的表意逻辑路线,而是为存在的真实形态敞开大门。其次,经典以其深刻性与普世性建构着自身的力量。伯格曼作品之深奥在于它牵连着整个西方文化世界,上帝之死与宗教的当代意义、理性失格与存在的显现等话题事关重大且难以言传,伯格曼以简洁的镜头为其留白;同时它们又无处不在,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在每一段亲密关系中,都能与之狭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