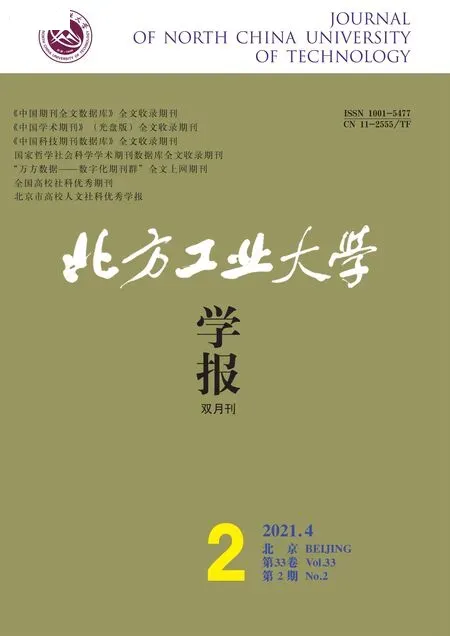戏曲的流传生成和故事内容的变化*
[日]冈崎由美 李莉薇 译
(1.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162-8644,东京,日本; 2.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510631,广州)
“戏曲”①这个词,现在日本是专指作为文艺作品的戏剧脚本,而在中国所谓“戏曲”,则是指与新剧②相对的传统戏剧。就像京剧的新编历史剧,脚本本身是现代的新编作品,但样式形态是传统剧的范畴,所以是“戏曲”。本文③所指“戏曲”,采用中国的用法。
中国的传统戏剧,基本上是用歌唱和宾白演出的“歌剧”。但并不是像歌剧和音乐剧一样,由作曲家创作全新的一个音乐作品,而是采用传统音乐来编排音乐。例如,在中国某个地方产生、流传的民谣俗曲,被当地的戏曲吸收,就成为了构成戏曲的主要声腔(乐曲的系统)。(这个声腔)又被下一个时代戏曲的形式所承继,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域,发展成新的声腔。
同样,故事物语也是被反复传播继承,形成民间共有的东西。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重构,又或者在不同的地域被改写。因此,谈论戏曲的变迁,那可以是样式的变迁,理论的变迁,其他的构成要素的变迁,但作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事象的体系,也可以说是记述了生成、积蓄传统足迹的行为。
1 戏曲变迁史研究的现状
1.1 正统的戏曲史
关于戏曲变迁的问题,就直接是戏曲史视阈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最为正统的戏曲史研究的框架,就是以“南宋的戏文—元杂剧—明清传奇”为主干,在此之前的阶段称为“前戏曲史阶段”。这部分主要集中讨论中国戏曲的祖先为何的问题,也就是戏曲的起源论。“前戏曲史”阶段公认的研究课题大致是“春秋期的巫觋(宗教礼仪的表演)、战国时代的俳优(宫廷的表演艺人)、秦汉百戏、傀儡戏(人偶剧)、唐朝的歌舞戏和参军戏和晚近北宋的杂剧和金院本”。
关于前戏曲史阶段的研究,虽是断代史但基于详细的文献资料考据而写成的力作有任半塘的《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不过,从整体来看,全书倾向于着重探讨构成戏曲的各个要素,特别是形式方面较为接近的事象的起源。中国的传统戏剧,一般由唱(歌)、念(白)、做(科)、打(武打)构成。也即是,百戏指武打和杂技、歌舞指歌唱和舞蹈、参军戏以语言为主、巫觋和俳优是表演者的前身这样的对应关系。正如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所指出的,以部分推导全貌的论述,似乎把具有多样性上演要素的戏曲过于单纯化。
实际上,由于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少,以形式的起源来探讨戏曲的形成的研究方法可谓走到了尽头。
戏曲史关于元杂剧以来的记述,在形式方面,明代有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等同时代的声腔,清代的部分则是各地的地方戏,即是对同时代的不同剧种的记述。如声腔取“昆山”“弋阳”等地名来命名声腔所示,其乐调的产生与流行具有地域的特征。于是,根据声腔形成和流传地域构成了不同的地理分布体系。地方戏的种别、系统,是根据规定唱曲韵律的语言(即方言)和声腔的特征来界定的,因此,对于明代地方声腔的叙述和清代地方戏的叙述,都按照时间轴来描述戏曲的变迁史,再加上声腔、地方戏在地理上的横向扩散,呈现扇状构造。
内容方面,在“戏文—杂剧—传奇”的传承内,同一个剧目虽然会被多次重演,但在文学史上惯常的书写,基本上会按照代表性作品的特征和写作风格的变化来记述,倾向于把戏曲看成是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而非作为可以演出的文本看待。实际上到了明代后期,确实戏曲作品未必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仅仅是为了阅读而创作的倾向较为明显。因此,文学史上主要讨论剧作家的创作状况、文笔、风格,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一直以来的戏曲史是文人的戏曲史、脚本文学的戏曲史、仅仅只是看到戏曲史最明晰的部分。这种意见也是针对正统的戏曲史提出的。
如上所述,所谓正统的戏曲史,从形式上看,是民族文化的的产物;从内容上看,就是关于文艺创作论的论述。
1.2 戏曲史研究的问题点
戏曲史研究具体到戏曲变迁过程的论述,一直以来有两个时期是模糊的混合连接期。一个是关于戏曲的成立,在元杂剧以成熟的形式出现前的阶段是摇篮期;另一个则是突然进入了地方戏勃兴的清代中期。
如前所述,前者正是被反复提及的戏曲起源的问题,“各种相近的技艺成为了戏曲起源的多样性的背景”。
后者的问题在于,清代中期出现的地方戏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和“宋戏文—元杂剧—明清传奇”一贯使用的联曲体所不同的板腔体这一点上。这是据音乐形式的概念而言的。所谓联曲体,就是按照有固定旋律的歌曲(曲牌)来填入长短句的歌词,以旋律为主体的变换歌词方式。一支曲子里所唱的内容、一幕里安排的场次,为曲牌的排列所左右。而板腔体没有固定旋律的限制,七言或十言的歌词可在同一个调子中改变节奏歌唱,以歌词的节奏为主体。因此,与通过曲牌连接的规则来左右歌词的内容和每一幕构成的联曲体比较,板腔体在规定演唱形式的音乐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两者的差异,过去的研究也有提及。但对于这个差异产生的表述,一般都没有提及板腔体盛行的由来,直接就说板腔体出现,然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方戏在全国涌现。板腔体的酝酿期、肯定与联曲体并存的同时代的状况,几乎都没有提及。这大概是因为被文人所接受认同的联曲体戏曲早已理论化,作为案头文学也积累了被人们认可的高水平的作品,而板腔体戏曲大多是来自民间的,连脚本都不完整,往往淹没在与定型化文艺作品无缘的世界里。正是因为是现场演出的戏剧,所以基本上没有文人的记录。关于这点,金文京在《诗赞系文学试论》中已经指出。
补充说明一下,杂剧传奇是基于文献文本的研究领域,而地方戏则属于包含田野调查的艺能研究领域,这种区分在现今的研究者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我们要填补这个研究上模糊点,大概可以不用再墨守沿着线状时间轴设定的戏曲变迁史的界限。苏州文人在自家大宅欣赏着传奇的时候,各地的农村,还有城市里的剧场,也在上演着戏剧。而且,各种近似的娱乐文艺肯定是并存的。对于同时代艺能表演的构造状况,我们应该摸索多角度研究的方向性。因此,跨学科的共同研究也一定是必要的。
1.3 戏曲史记述的分歧点
从198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戏曲史研究专著陆续出版, “宋戏文—元杂剧—明清传奇”的研究范式逐渐解体,从而重构新的戏曲史。
出现这种变化的背后,与把戏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来看待,重新发现民族精神的研究视点有关。大概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长久在各地上演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传统地方戏得以重现活力,又由于提倡爱国主义,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地方戏的复活,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傩戏、目连戏等较为原始的农村演剧、祭祀演剧。作为戏曲研究对象的资料,从文艺价值较高的定型化文本扩展到各式各样的材料,呈现飞跃性的发展。
在这个方面,田仲一成先生的农村祭祀演剧研究⑤是开先河之作。作为把农村社会构造、地域习俗等与演剧结合论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先生的研究在中国戏剧研究史的分歧点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原本声腔研究是早已有之(比如,王芷章的《腔调考源》等),但一方面是由于与主流的文艺创作论式的作品研究的分野关联较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仅凭个人收集的资料难以把分布在全国的地方戏资料收集殆尽,所以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成果。关于这点,在进入1990年代后一直出版发行至今的《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中国地方音乐集成》等全国规模的艺能丛书当中也能明显地反映出来。那就是戏曲研究的范围,可以说已经从文艺作品逐渐扩大为被演出的戏剧。也就是说,我们研究过去戏曲的变迁,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剧种,来考察时间的变迁和地理上传播的足迹。
1.3.1与民俗学、社会史的结合
脱离按时间轴对戏曲的种类和作品作线状论述的体例,重构戏曲史范式的动向之一,就是不再把戏曲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来论述,而是作为在活态社会中演出、传承的戏曲来认识考察。
例如,余从的《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正如书名所示,把戏曲的形成从声腔和剧种两个方面来考述,特别着重追寻声腔继承传播的足迹。如前所述,声腔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特点,因而此书认为中国戏曲的体系就是各地方戏的发展体系,与其说是论述戏曲变迁史倒不如说呈现了戏曲地理志的形态。该书虽然也讨论了从宋戏文到明传奇的变迁,但似乎只是把这段作为地方声腔出现前的阶段,作者对地方戏的声腔形成和流传情况方面花了相当的篇幅。
作者之所以提倡声腔剧种史研究的必要性,是因为今后全国各地的传统戏剧会继续上演,也不断会有新创作的戏出现。中国戏曲在音乐方面,并不是由作者自由创作乐曲的,而是具有在大众文艺的传统中形成、继承的声腔形式上的特征。也就是说,该书排除了由剧作家的个性左右的层面,把戏曲看作是社会集体所共有的民俗文化产出的对象。
该书由于把一种样式特性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所以基本上没有涉及演剧内容的变化。但正如书的前面部分已经强调,戏曲的变化并不仅是遵照时间顺序的,剧目也会和声腔的流传一起流传,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形成尾状型的系统。我们可以从书中的论述获得民俗学现象的启示。
周育德的《中国戏曲文化》的编纂体例(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在“源头篇”(纵向的戏曲史)“剧种史”(横向的戏曲志)的基础上,加上“文学篇”“演出篇”,编成一个全新的戏曲论。在文化史中多方面地考察演剧活动的研究视点很突出。特别是“演出篇”,不仅关注戏曲的上演,更考察了上演的场所、戏班(剧团)。这种研究思路,提示我们对戏曲变迁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到戏剧的形式和戏剧理论,还要关注“演剧的目的”、“什么样的剧团来演出的”这些演剧的目的和手段等要素。
在城市里的剧场以娱乐为目的的演出、农村的寺庙祠堂里进行的演剧,或者特定的人家里举办庆贺祈福延请戏班演出等等各种演剧活动,不仅演出形态各异,社会功能也不同。今天,对于戏曲的分类,比如堂会戏、庙会戏、娱乐戏等以目的功能来区分的体系也逐渐定型。
总之,正统的戏曲史研究虽然一直关注戏曲的表演特质,但已经明显地把研究对象从关注为表演而作的作品(脚本)扩大到构成表演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过去的戏曲史研究,一直把剧团构成、演出条件、演剧的社会功能等要素作为产生戏曲作品的背景来研究,但最近的研究视点是关注包含社会诸要素的戏曲演出活动自身的变迁,这种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戏曲史研究的范式。
关于这一点,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以自古以来剧团变迁的新角度书写了戏曲史。除此之外,近年来学界也关注剧场的变迁史、伶人的社会史,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出土文物资料也被利用起来了。
也就是说,戏曲的变迁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已不仅仅局限在形式和内容这单纯的二元论,作为一种复合的媒介,因而具有的社会性与功能性,正在不断地被重构。
1.3.2演剧美学
以上所提及的研究动向,具有社会史的论述,也波及到戏曲形成的外部环境。也可以说是在地域研究的领域内研究中国戏曲的独特性。与之相对,另一个研究的新动向是从戏曲的内容出发,直接探讨属于戏剧理论范畴的本质论。把中国戏曲定位于世界戏剧的一部分,尝试论述民族精神的普遍性。
也就是说,用世界通用的演剧论来研究中国戏曲。这种研究方法,深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采用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追寻何为悲剧、何为戏剧的观念性问题。例如,郑传寅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谢柏梁的《中国分类戏曲学史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都完全脱离了按时间轴论述的研究路径。前者把戏曲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分析悲剧观、喜剧观、时间观念、空间意识等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识表达等问题。
后者正如“戏曲悲剧学”“戏曲戏剧学”“戏曲创作学”“戏曲流派学”等题目所示,是文艺理论乃至艺术批评的研究路径。研究思路的根本是探究与小说、电影、电视等相近类型的文艺相比,“戏曲之所以称为戏曲的艺术性究竟是什么”,探究“中国传统戏剧的文艺本质”的问题。
以上提及论考,由于要直接论及中国文化的本质问题,因而较为缺乏对个别事物的变化、过程的考察,难以看到直接关涉“戏曲的变迁和内容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论述。
2 演目流传研究的突破口
那么“故事”流向哪里了?戏曲是用歌曲和宾白讲述故事的一个叙述媒介。我们不得不说,前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没有捕捉到戏曲这种媒介体系中“故事”(脚本的内容)功能。
戏曲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涉及构成演出活动的诸多条件,资料集中在稗史杂记等历史记述或者随笔方面。戏剧美学方面的研究,追问民族精神的本质问题。当然,上述研究并非完全排除戏曲在“故事”方面的要素。但是,其论述的主要目的在于总结戏曲作品的风格和主题上显示出的社会因素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戏曲”作品,是定型化了的故事。故事被装在容器里的结果,会成为分类的对象,但不会成为过程的对象。这个情况,前述新的研究的出现,如果是对一直以来的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戏曲史的反思与批判的话,也是不无道理。我们把戏曲史作为社会生活来重新认识的时候,开拓过去一直忽视的未开拓的领域成为当务之急。而那些我们已经听得耳熟能详的故事,即使不说一直置于研究的边缘,也可以说没有给予新的定位。
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流传至今天的戏曲故事(剧目),并不是保留了当时的定本,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读到。阅读杂剧、传奇的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概只是一部分的知识阶层而已。戏曲剧目,通过反复上演而传承下来,保存着生命力。而戏曲故事经历了生成、流布、变化,又或是消失的过程。故事本身,并不完全等值于写定本的作品。正是由于不同脚本之间的关系性,才体现了流传和变迁的意味。
关于这一点,作为戏曲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的地方戏,因可对现场演出情况进行调查,也常常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但总感到与善本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河水不犯井水。这个危机,加藤彻早已提醒过。他在《中国地方戏脚本的流传与展开——以梆子·皮黄剧〈铡美案〉为题材》中曾写道:“不幸的是,由于板腔体地方戏(梆子·皮黄)作为‘戏曲’评价并不高……一直以来的研究有以演出史研究为中心的戏剧研究倾向。如此,‘在研究板腔体地方戏的传播这个问题上,最好的一手材料就是地方戏脚本本身’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却被忽视了。”
如果我们从戏曲变迁的角度把故事设定为研究对象,那就不是作品内容的静态主题研究或结构分析,而是把故事看作是构成脚本的文本群的现象,就必须探讨变化的功能。这样就能在现行的戏曲社会史研究中,找出自身的有机的定位。
基于这样的研究视点,我们以具体的典型例子来分析戏曲史上剧目流传的定位和意义。
2.1 流传的地域性
江巨荣在《南戏〈刘文龙〉的流传及剧情的变迁》(《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把过去一直没有谈及其剧目内容的地方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再现了剧目流传的足迹。该文利用了新出土的脚本、傩戏重新演出等方面的材料,在资料方面是一篇适时之作。
论文的出发点是讨论1975年从广东省一个明代坟墓出土的南戏剧本《刘希必金钗记》(明宣德年间抄本)在“刘文龙”剧目系列中的历史地位。《刘希必金钗记》为《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所影印收录。原来有关“刘文龙”的戏曲,无论是在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编》里的《刘文龙菱花镜》,还是张大复《寒山堂曲谱》里的《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同曲谱注为“一名为《刘文龙传》”),都仅存有题名,具体的故事内容并不确定。只是《九宫正始》⑥等曲谱类上一些不连贯歌曲拼在一起,由此推测大概的故事内容。在广东的《金钗记》出土之前,这个剧目在戏曲史上没有定本。
故事以《史记》本传里的某汉之娄敬(后赐刘姓)为原型。戏曲的梗概可大致推测是讲述汉人刘文龙辞别双亲和新婚妻子上京赴考,其后被派遣到匈奴,不得不长期与亲人离别,最后回乡与妻子重逢的故事。《刘文龙菱花镜》中,夫妇二人把菱花镜一分为二,留作他日重逢相认之信物。该剧名取“破镜重圆”之义。《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则可从剧名推测剧情大概是误以为丈夫已死的妻子祭坟之际,与丈夫再会的内容。是《荆钗记》之类的故事。
正如前面早已指出的,两作品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但故事的全貌却依然不明。
该文以明代出土资料《刘希必金钗记》为中心,收集了福建梨园戏、安徽省贵池傩戏、吹腔《小上坟》,还有清代弹词《刘文龙菱花镜记》等资料,指出该剧属于和蕃型和恋爱型两个母题的复合变形作品。在内容上可以对应《九宫正始》等古南戏残曲中有刘文龙科举考试夺魁旋即被派往匈奴赴任的唱曲,也可以对应刘文龙进京后沉迷出入妓楼,忘记归家返乡的唱词。
吹腔《小上坟》中,刘禄敬(刘文龙)上京赴考后一去不返,叔父设计,欲迫苦苦等候丈夫的刘妻再嫁,谎称刘已在京城病逝。刘妻萧氏走投无路,遂在刘家墓前哭泣悲伤之际,刘文龙归来。弹词《菱花镜记》中,刘文龙进出青楼妓院,叔父假言骗婚,萧氏正欲在丈夫坟前寻死之际,刘文龙归来重聚。这是恋爱型的母题。
另一方面,和蕃型的故事在《金钗记》中存在分歧点。《金钗记》中,讲述刘希必(刘文龙)新婚三日即上京赴考,一举高中状元后被派遣出使匈奴,匈奴王招他为婿,与匈奴公主一起过了二十余年仍念念不忘返乡回家,于是公主助刘文龙逃离匈奴,得以回乡与妻子重聚的故事。作者把《九宫正始》所收的古南戏残曲与该书的字句作对比,判定两个作品为同一系统。更在此基础上,考据出福建的梨园戏《刘文良》剧情与《金钗记》几乎完全一致,乃其嫡系;与传入安徽的弋阳腔相对应,流传的贵池傩戏继承了和蕃型的故事,祭祀性的要素得到加强,其中刘文龙没有和匈奴讲和而是征伐匈奴,是征蕃型故事的第二次变形改编。
这篇论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考据“刘文龙”故事流传的轨迹,评价《金钗记》这部作品的历史定位。论文不仅达到了当初作者写作的目的,在其他方面也给予了我们启发。
例如,作者指出,《金钗记》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关系的设定都受到《琵琶记》的影响,通过和《琵琶记》的字句做比较,歌词、台词方面的表达上沿袭了《琵琶记》。这是扇状类型间显示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说唱、戏曲还是小说,只要出现一个模型作品,就会有细节不同而大体相同的模仿作品或多个作品出现,并相互在表达、内容上有交集从而产生故事群。简单地说,就是流行起来了。
以小说来说,例如《说岳全传》《残唐五代史演义》都有和《三国志演义》在表达上基本一致的近似的场面描写;大的方面来说,大量模仿作品促进了才子佳人故事群的形成与类型分化。后文论述的南戏《拜月亭》,在赖炎元的《四代传奇及东南亚华人地方戏》一文中介绍的马来西亚残存粤剧抄本《双仙拜月亭》,剧情的后半部分也和原作相距甚远。企图自杀却被救的主人公和误以为主人公已死的女主角在道观再会的情节,与《荆钗记》的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正好反过来了。与《拜月亭》的前半部相比,后半部的结构较为松散。现在留存的地方戏也基本上演前半部分。因此,粤剧演出后半部时,可能由于这部分内容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在传播的阶段已经佚失),就借鉴了其他剧作的内容。
此类例子,本来正好证明《琵琶记》《荆钗记》影响力强大,但同时如果考虑到故事的变化,也需考察到这种剧目之间的替换关系引起的分化、流传、消失。
在戏曲史上,从元末明初的《蔡伯喈》《王魁》一类的“负心剧”渐渐演变成“不负心剧”,并流行起来,我们不得不从作品群中考察演出的新旨趣、演出手法的消长和替换的作用。从“负心剧”到“不负心剧”的变化,现在一般仅止于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们还须考察“从哪里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具体状况如何”等问题。从元末到明初,在以北曲的南戏化为主的改编热潮中,以上的这些问题应受到重视。
2.2 脚本分化的指向性
戏曲的流传和变化当属一部反复修改的历史。如今,戏曲也依旧是不断被改编的。本来,俗文学就是常常以现在进行的形式而得以保存命脉。
戏曲的改编并非只对情节、主题等进行改变,更涉及对歌曲的排列进行变更或引用其他歌曲,即使是同一首歌曲也时常重新创作唱词等多个方面。
做出这样的修改,不但可以使演出效果和音乐理论得以统合,在传播到其他地方时,也可与当地戏曲音乐相平衡和基于方言差异而对韵律作出调整。可见,不同地域的观众对戏曲的理解和喜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戏曲的改编。因此,戏曲在各个层面都会被重新编排,在流传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与改编目的一致的指向性。
田仲一成对广为流传的明代戏曲——北曲系《西厢记》及元末以来的古南戏《琵琶记》《荆钗记》等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对各个版本的唱词和宾白进行了详细比较和深入研究,揭示了戏曲流传和分化的指向。该研究成果是立足于对各个版本进行细致的考证,以及对版本系统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
例如,在《明初以来西厢记的流传与分化——以碧筠斋本为起点的考察》中,针对该剧目的各个版本中唱词和宾白的异同、增补和删改进行了对比,分为四类:
其一,万历初期之前的刊本(按文辞分为古本、准古本、校订古本);
其二,万历中期刊本(闽本);
其三,万历后期刊本(京本);
其四,天启崇祯年间刊本(校订京本)。
论者在以上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对《琵琶记》、《荆钗记》的分析结果,提示了以下两种的指向性。
文人型——为追求文辞的艺术性和音乐的相容性,而致力于歌唱部分即唱词的精雕细琢。宾白方面则不甚关心。
演员型——追求情节的简单易懂。
以此为目的,又再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旧作改编型——对旧作的台词进行增补,调整排序。唱词则沿袭旧作。
新编型——对旧作只作部分调整而效果不尽人意,故只沿袭情节,唱词和宾白都重新改写,编成新作。属于对整个脚本的改写。
论者又指出,明代主要的戏曲作品普遍皆存在剧本流传和分化的现象。
概而言之,嘉靖、万历时期对自元末明初以来的古本的改编活动盛行,逐渐分化为追求文辞美化和宾白简化的文人型脚本,与旨在加插场面和宾白饶舌化的演员型脚本。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明末清初出现的昆曲清唱型的上层脚本(京本)和弋阳腔等地方声腔或苏白吴腔(增加吴方言宾白而成)型的下层脚本(地方戏演出本)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
田仲先生进一步指出了戏曲与社会结构的关联: “明代的乡村社会中,乡绅宗族势力对乡村演剧的支配逐渐强化。地方戏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即是分化为乡绅地主宗族的家庭演剧(上层演剧)和由下层农民、商人主导的市场地演剧(下层戏剧)。这恰好与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局势变化相对应。”
脚本的改编,揭示了该演目(故事)采用哪种方式来表演(故事)的变迁过程,所以,与故事的内容互为表里。这一系列研究表明,通过改编,使流传和继承的戏曲具有了反映社会形势状况的指向性。这点,从脚本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自身变迁的历史痕迹也可以得到佐证。
2.3 故事与媒介的亲和性
当一部戏曲演目流传的时候,从唱词和宾白的改编开始,乃至故事情节和主题都会发生变化。该变化不但会在脚本的文本之间、剧种之间发生,而且在小说、说唱俗曲等不同类型的文艺样式之间,也会发生演目的交流互换关系。
在研究戏曲变迁史中出现说唱文艺是否领域混乱?金文京在《诗赞系文学试论》中提到,打破说唱文艺和戏曲两者壁垒的乐曲系和诗赞系,就在于戏曲音乐中的联曲体和板腔体。
实际上,地方戏中主要声腔与当地的说唱文艺有诸多共同之处。简单来说,俗文学的受众群体(观众和听众)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文艺作品,因此,对故事内容的接受,也是有选择性的。事实上,从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拙见认为与其按照小说、戏剧、讲唱文艺等题材来分类,倒不如分为战记、才子佳人、神仙幻怪、侠义等不同系列,反而更能体现出传承媒介的跨界交融和对话的有效性。
此处以由元杂剧改编而成的南戏《拜月亭》(又名《幽闺记》)作为一个典型事例,结合以上的见解,探讨该故事在小说、戏曲、说唱文艺中发生流传和分化的情况。研究方法以脚本字句的比较对照为基础,再通过对脚本的分幕构成、曲牌构成和文辞表达异同的检证,来探讨演出剧目的流传和分化。但较为复杂繁琐的文辞对照引用部分则只能割爱不作讨论。详情可参考拙论《〈拜月亭〉传奇流传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九期,1987年版)。
2.3.1元杂剧的继承
关汉卿原作的《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是以金宣宗时期,受到蒙古军进攻的金国从中都(北京)迁都到南京(汴梁)的史实为背景。故事从逃往汴梁的中都难民中的秀才蒋世隆和王尚书的女儿瑞兰开始。秀才蒋世隆与其妹瑞莲,金朝王尚书之女王瑞兰与其母在逃难途中各自被哨马冲散,两对人交叉相遇。世隆与瑞兰邂逅并在共同逃难中产生感情私定终生。当蒋世隆抱恙在客栈休养之时,从边塞归来的王尚书刚好住入同一家客栈,遂以门户不相称为由催逼瑞兰撇下生病的世隆,跟自己回家。另一方面,巧遇王夫人的蒋世隆的妹妹瑞莲,被王尚书认作义女。病愈后的蒋世隆在汴梁科举高中状元,王尚书欲将女儿许配给状元郎,遂使得恋人、兄妹得以重逢再会。
《拜月亭》正是一部描述了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的作品,剧名的由来源于瑞兰焚香拜月祈祷世隆平安的一幕而来。
以这出元杂剧为原作,元末明初之时已有南戏的改编。元代天历至正时期的南曲曲谱《九宫正始》中收录的残曲也可资佐证。虽仍可窥知该古本大体内容,但古本本体已经散失。
2.3.2文人型和演员型的分化
接下来,如田仲一成所言,万历时期对嘉靖以前的古本进行了改编。此时期相关脚本有四十三折的世德堂本和四十出本六种,以及青阳腔、徽调等弋阳腔系的散出(以幕为单位划分)。从分幕构成来看,已经明显看出世德堂本明显与其他的四十出本的系统有所不同。世德堂本中用“折”来表示幕的单位,而没有采用南戏常用的“出”;从曲牌结构、文辞来看,世德堂本和四十出本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拜月》一幕之后,两者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两者的故事情节也不同。
差异的关键在于有无“误接丝鞭”(错允姻缘)的场面。高中状元的蒋世隆在未知对方是王瑞兰的前提下,便轻率地答应了王尚书安排的婚事,因此在恋人重逢之时有被瑞兰责备其不忠的场面。在世德堂本上仍留有该一幕,但在四十出本中则改为“拒婚的蒋世隆直接告知王尚书与王瑞兰的相好,而瑞兰暗中偷听,二人得以再会。
有“误接丝鞭”一幕的当为旧版系统。元杂剧、《九宫正始》和嘉靖年间曲谱《旧编南九宫谱》的残曲中均有这个情节。可见从元朝到嘉靖时期的旧版系统一直都保留着此情节。另外,比起四十出本的系统,世德堂本的文辞更为通俗,在最终幕的第四十三出(尾声)中有原句:
酝酿就全新戏文书府翻腾燕都旧本
从文辞可见书府(戏剧和说书等剧作者组织)对燕都的旧本(北曲)进行了改编,其当属“演员型”的改编。另一方面,四十出本诸文本中出现了校阅者李卓吾、罗懋登、陈经儒等当时著名文人的名字,他们推进了文辞的优美化。看重音律和谐的戏曲作家沈璟在曲谱《增定南九宫曲谱》中收录的四十出本系统的曲辞,则显然属于“文人型”的改编。
2.3.3进一步向地方戏发展
南戏《拜月亭》世德堂本和四十出本的两系统与明朝万历年间出版的徽调散出集(以幕为单位的诗集)对比可发现,曲牌结构、唱词及台词方面形成了两个系统:几乎都继承了世德堂本;在继承世德堂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文辞进行了修改。
徽调中留有的场面基本都是在蒋世隆与王瑞兰相遇的《旷野奇逢》一幕当中,极易对比。
在改变文辞方面,首先插入了可谓弋阳腔特征的滚调。另外,对于蒋世隆和王瑞兰二人同行的场面,世德堂本以及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世德堂本的徽调散出中,把蒋世隆和王瑞兰各自抒发旅途慨叹的歌唱作了修改。换成了二人合唱,彼此安慰,更有为对方擦汗的动作,强调了二人互动的歌唱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唱词或是演出方面,都着重于突出二人对唱,采取了较为通俗且富有人情味的演出方式。
上述徽调系统可谓在演员型的基础上向地方剧进一步发展。另外,徽调散出集《徽池雅调》中尚留有“误接丝鞭”一幕,虽与《九宫正始》曲牌不同,但有沿袭其唱词的部分。也就是说,南戏《拜月亭》以世德堂本为分水岭,不断发生文人型的昆曲系和演员型的弋阳腔系的反复分化和发展。
在徽调的分化过程中,蒋世隆和王瑞兰的出身也发生了相当迥异的变化。徽调散出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当属《摘锦奇音》所收录的《幽闺记》,其二人被设定成了汴梁人。
【原文】(旦白)敢问,君子家居那里?姓甚名谁? (生唱)家住离城五里台。蒋世隆黌门中一秀才。……(生白)敢问,小娘子家居那里?姓甚名谁?(旦唱)家住汴梁城鼓楼街。我爹爹朝中奉钦差。
《拜月亭》的故事据金国南迁的史实而写,其设定自然是居住于中都的百姓逃往汴梁。但如果本来就是汴梁人的话,那该逃往何处呢?
诚然,通俗文艺的地名、人名、故事人物的籍贯往往出现混乱。但在《拜月亭》里,籍贯的异同,却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律可循,成为考察流传系统的指标。
2.3.4金朝故事系谱和宋朝故事系谱
正值徽调散出集得以陆续刊行的万历年间,有好几种被称为“通俗类书”且具有一定编辑形式的书籍也多有刊行。这些通俗类书中,有两种将《拜月亭》的剧本改编成了长篇文言小说——《国色天香》。收录《国色天香》以及《绣谷春容》的即是《龙会兰池录》。
这部小说与徽调《幽闺记》无异,世隆为汴梁的书生(后为南宋状元),瑞兰则为宋朝尚书之女。
《龙会兰池录》虽为脚本改编小说,但该小说中尤其是在后半部分的故事情节却与戏曲差距甚大。特别是以下两点:
第一,【戏曲】“拜月”为瑞兰和瑞莲祈祷蒋世隆平安无事。
【小说】“拜月”为世隆和瑞兰立下婚约的山盟海誓。
第二,【戏曲】世隆患病,急忙找来江湖郎中。
【小说】瑞兰在海神庙祈求世隆痊愈。
此两处差别迥异。涉及到了标题问题,将戏曲中几乎毫不例外的“请医”的场面改作滑稽的一幕剧。
另外,王瑞兰的名字在小说中成了“黄瑞兰”,瑞兰之母张氏也成了“汤氏”,这或是方言的讹化。即是将听到的人名直接写到小说当中出现的偏差。
然而,出场人物在设定上的差异,绝非因偶然或误解而导致。小说《龙会兰池录》的开头部分作了这样的设定。
时金迫元兵,(百姓)自中都徙汴(汴梁)逃难。宋边城近汴者,又被金兵追赶,遂往杭(杭州)。
就是说,因金国南迁,金兵大举来犯汴梁,汴梁周边附近的南宋百姓遭到金兵袭击,只能逃往杭州。《龙会兰池录》描写的,并非被蒙古蹂躏的金人,而是被金兵蹂躏的宋朝百姓。金人成为了侵略的一方,而汴梁也不是逃亡的目的地,反而成了出发地。世隆在杭州夺魁,而非在金朝。以上均为作品在构思上的转变。这应是故事的受众将背景设定为汉民族的故事,希望使读者从故事人物身上获得共鸣。于是,对这个设定的接受方式,足以成为考察剧目流传的指标。
2.3.5地方剧和讲唱文艺的关联性
在明朝万历年间之前,宋朝故事《拜月亭》是以弋阳腔系统的地方声腔徽调所演。
在明朝嘉靖年间,弋阳腔广泛流行于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南京、北京等地,又与各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后转化为当地的声腔。被称为高腔的系统当属弋阳腔的末代,在当代的川剧、湘剧、婺剧、赣剧等剧种中得以继承。宋朝故事《拜月亭》也是通过这个传播途径得以发展。
江西的东河戏高腔中留有源自《拜月亭》的剧目《抢伞》(《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江西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还有四川的川剧高腔的《踏伞》(重庆市戏曲曲艺改进会《川剧》,重庆人民出版社,1954—1956年),两者均为世隆和瑞兰在旷野中相遇的场面。在世德堂本及弋阳腔系统中尚有保留,但在四十出本及昆曲中则已被遗弃的,较为通俗的对唱演出和文辞在以上二者中被继承,由此可见,在脚本分化方面,不同的演出媒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东河戏高腔中,首先为瑞兰以歌唱表达了对金国的入侵的愤懑:
【原文】君子请听——(唱)都只为那金国作乱、那金国造反、家家逃生、户户逃难。
川剧高腔中也有“兵荒马乱,汴梁遇难”的唱词,体现其采用了宋朝故事的设定。而二人的身世则为住在汴梁城郊的书生蒋世隆,及住在汴梁城内鼓楼街的钦差千金王瑞兰。另外,在马来西亚的粤剧存本《双仙拜月亭》和福建梨园戏均是宋人故事的系谱。
讲唱俗曲方面,清末的子弟书《奇逢》(关德栋《子弟书丛钞》收录)、广东龙舟歌《闺谏瑞兰》(《中国俗曲总目考》收录 以文堂本)、平岔带戏残曲《旷野奇逢》(《霓裳续谱》卷八收录)、马头调《扯伞》(清·华广生《白雪遗音》卷二收录)等等,较广泛范围内,均将故事背景设定为金兵蹂躏以及宋人出身的世隆和瑞兰逃出汴梁。
而令人瞩目的是,瑞兰为卧床生病的世隆而到海神庙祈祷的“瑞兰许愿”这一情节原来仅出现在文言小说《龙会兰池录》中,却在广东龙舟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富桂堂本)中寻得踪迹。可以推定此源于小说,或是促进了小说在民间流传的宋朝故事系统演出载体的母本。
这里面仅有弹词《幽闺记》(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一部沿袭了四十出本南戏的金朝故事系统。其依旧采用了元兵入侵金国,金人迁都汴梁的情节,并且在故事方面也采用了四十出本改编的情节,即高中状元的世隆拒绝了王尚书的亲事。这或许是由于弹词流行的江南地区同时也是昆曲势力的中心地,因此比起文艺题材的类型,优先考虑区域特性的影响。
于是,世德堂本和四十出本分化之后,就发展为泾渭分明的两极分化局面:
金朝故事系统——昆曲系南戏(文辞美化,无恋爱谜题,无“误接丝鞭”情节)、昆曲、弹词。
宋朝故事系统——弋阳腔系地方剧(文辞俗化,有恋爱谜题,有“误接丝鞭”情节)、小说、讲唱俗曲。
在文辞、演出手法、故事情节、设定等多层面上与原作品保持着或亲或疏的关系而流传下来。在《拜月亭》的传播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雅俗的理解程度、兴趣爱好的阶层差异、当地文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等等俗文学的社会功能,这大概已经超越了小说、戏曲、说唱文艺等形式方面的界限。
3 今后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无论是小说领域还是戏剧领域都着力于通过将脚本和小说各版本作对照比较,来追溯流传的轨迹,探讨通俗文学发展和分化的模式。然而难点在于,这必须要立足于作品和剧目层面的个案研究之上才能进行,而对这些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
此外,研究方法虽相当清晰,但研究者也会担心,如果一步弄错,便很容易将错误扩大到全盘的系统构成当中。因此,研究者们相互间公开成果,并加以修正,才是体系化逐渐完善的途径。
正如前述,为了使对剧目的流传和分化的研究在戏曲史乃至通俗文艺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可以跨越传承载体和文艺体裁的界限,对故事群层面作分析。于戏曲史层面谈及故事群时,往往会对其作爱情剧、政治剧、神仙剧等主题分类,并据此论述各类型的特征和代表作。但是,应将这里提到的故事群作为民俗传承的构成要素来理解。原本源于同一个故事而呈现扇形分布故事群,在情节和演出旨趣以及文辞方面发生互动交融。也就是说,虽然不是同一剧目,但在流传上的关联性得以确认,我们有必要以发展的目光对其相互作用作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戏曲:此处日语原文为“戯曲”。
② 新剧:日语里所说的“新剧”,一般理解为中国的“话剧”。
③ 本文原题为《戯曲の変遷と内容の変化》,选自《中国通俗文艺研究的视点》,东京:东方书店,1998。自明治时代以来,狩野直喜、幸田露伴、森槐南、青木正儿、盐谷温、岩城秀夫、吉川幸次郎、田仲一成、金文京等众多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戏曲的研究是日本中国学的一个亮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国内的戏曲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与影响。可以说,长期以来,中日戏曲史研究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了学科的发展。1980年代,田仲一成先生把人类学研究常用的田野调查法运用到中国戏剧史研究当中,再结合戏曲研究史上的传世文献,重新书写了中国戏剧史,给予国内学者很大冲击的同时,日本国内学界受到田仲先生方法论的启发,也陆续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其中,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授通过对同一主题的各类民间文艺题材进行了深度的挖掘、解读,指出戏曲作品的流传,是以多种民间说唱文艺在口头传承中流传,呈现扩散性扇形分布的特点。冈崎由美教授的系列研究,颇受到日本中国学界的好评。今翻译成中文,可为国内研究的他山之鉴。
④ 金文京教授根据在中国各地发现的有关戏曲、曲艺方面的新资料,撰写《诗赞系文学试论》《诗赞系戏曲考》等多篇论文,认为中国戏曲可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股潮流,我们应该根据重新纳入视野的诗赞系资料,改变过去的看法,重新检讨中国戏曲史的架构。参见:金文京.诗赞系文学试论∥中国:社会与文化(第七号),1992。
⑤ 1970年代以来,出版《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中国演剧史》等一系列宗教民俗与戏剧发展的研究专著,在中日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⑥ 《九宫正始》全称为《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据元代天历至正年间的南曲曲谱编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