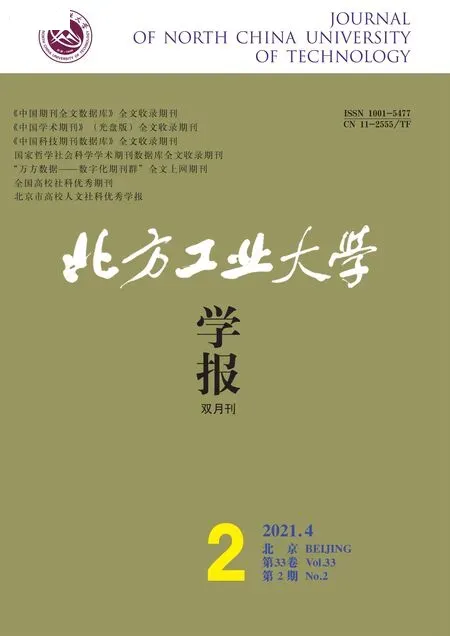论张位《词林典故》修撰的原因及意义*
余劲东 金丽娟
(长江大学历史系,434023,荆州)
明代翰林院作为“备天子顾问”的机构,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明朝中期开始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1]的政治运行一般规则后,一旦官员进入翰林院任职,其政治前途便日见明朗,因此翰林官的言行尤其受到时人瞩目。仅明人专记翰林官群体的生平、言行之书,便有廖道南《殿阁词林记》、黄佐《翰林记》、陈沂《翰林志》、焦竑《玉堂丛语》、董其昌《南京翰林志》、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张元忭《馆阁漫录》等多种,著述不可谓不丰。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对明代翰林院及翰林官的相关问题也多有关注。钱穆高度肯定明代翰林院的典制,认为“明制中尤堪称述者,在其翰林院”。[2]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关文发和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论著主要在宏观层面探讨翰林院发展演变、相关制度及翰林官职掌等内容。此外,吴琦、田冰等人亦对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政治权力等问题进行过探讨,相关著述较多,于兹不赘。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宏观视角考论明代翰林院职能及翰林官群体,而从微观视角对翰林官个体际遇及其著作编纂的研究仍有扩展空间。有鉴于此,本文以《词林典故》这样一本探究翰林官言行规范的著作为中心,分析该书的成书原因、书籍的主要内容与编纂影响,以及该书籍在当时众多官修典籍中的地位和意义。
1 张位与《词林典故》的编纂缘由
张位(1534—1613)于万历十四年(1586)与其僚友于慎行(1545—1607)、陈于陛(1545—1596)“访采见行事宜”[3],共同编成《词林典故》。该书将翰林官的公务活动分为33类,详细列举了明代翰林官的职责和行为规范。该书卷首署名为“张位、于慎行撰”,实则是在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位的领衔下,由当时翰林院的主要官员共同编成的一部翰林院内部典制汇编,编成后由张位主持刊刻并为之作序。
张位自述编刻此书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翰林之设,历代靡不崇重,而我朝为尤盛……士释蹻而进乎是,辄与九卿分庭抗礼,百执事无得以资品雁行者”[4],可见明朝翰林官的体势尊崇,因此值得为之一书。二是“二百年来,衙门所行事体,时移事易,故牒多所变更。通籍者遇有考问,靡得而征焉”[5],可见词林故实早已散落难寻,因此有必要为之一书。三是“万历丙戌,余承乏掌策,教习庶吉士,日坐玉署,多暇”[6],可见张位在处理公务之外尚有余暇,因此有条件为之一书。短短百字,便已详尽说明了编修此书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但除此之外,张位编行此书是否还有其他秘而不宣的现实意图?这就有必要结合其仕宦经历加以考论。
张位,字明成,江西新建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入选庶吉士,其在初入仕途之际便已获“储相”之望。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之父去世后,张居正本应循礼制回乡丁忧,但却突起“夺情”之议;其时众多朝臣指出张居正身为百僚表率,理应严守丁忧之制以垂范天下,但张居正却欲对上奏者加以严处。张位此时正在翰林院任职,其僚友赵用贤(1535—1596)恰因此事而被拟重处,张位不仅奏请予赵用贤等人以轻处,更在赵用贤被黜退离朝之际作诗为其送别。[7]此举触怒了张居正,张位因此被贬为徐州同知[8],并在地方任职多年。直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逝世后,张位才因言官的交相举荐[9],由徐州同知调任尚宝司司丞[10],在贬官五年之后重新担任正六品的官职。而其时,与张位一同在隆庆二年(1568)开始庶吉士修业的同窗当中,贾三近(1534—1592)已经身居“小九卿”之列[11],朱赓(1535—1609)、王家屏(1535—1603)、沈一贯(1531—1615)也早已成为词林先进[12],当然也有不少学友同自己一样因为张居正“夺情”事件而久沉下僚。同窗好友在十四年间竟出现这样判若云泥的差距,很难想象张位对此会无动于衷。张位以不惑之年再回朝堂,在接下来的仕宦生涯中,究竟是明哲保身从而平流进取,还是像之前那样仗义执言而沉沦下僚,对于这样一位已在基层磨炼长达五年之久而重返中央的官员而言,似非太复杂的选择。
张位在重回朝堂后的升迁速度令人侧目。在入京仅四个月后,便升任从五品的司经局洗马[13];旬月之间,又升任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14];八个月后,升任正四品的少詹事[15];十四个月后,升任正三品的詹事[16];半年后,也就是《词林典故》尚未成书的万历十四年六月,张位已经身兼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日讲官、庶吉士教习等多个要职。[17]从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重回正六品的尚宝司丞,张位花了五年时间;而从正六品的尚宝司丞到正三品的詹事,张位仅仅用了不到三年。张位重入京城之后异乎寻常的升迁速度,难免让人猜测其中究竟有何因缘。
明人在论及万历时期庶吉士的政治生态时称:“故事,读书木天者,但持默养重,坐猎高巍;或假归休沐,再入定得馆员。”[18]然而张位并未选择庶吉士常走的任何一条道路,却也能获得快速升迁,实令人侧目。作为文化官僚,能够脱颖而出的路径无过于著书立说,而张位此时主持《词林典故》的修撰,名为整理“典故”,实则意欲以此为名来整肃词林纪纲;而且从“入馆者人给一册”的情况来看,《词林典故》与其说是“掌故”之书,倒毋宁说是“规矩”之书。对礼俗的整肃、对规矩的强调,毫无疑问是新任长官在部门内快速树立权威、获得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这或许才是张位主持该书编行的首要原因。
此外,张位在万历十二年底参与《万历会典》的编纂[19],可以得到众多资料,其自述:“宗伯山阴朱公(赓)示余典故数条,因与同官学土东阿于公、南充陈公访采见行事宜,得三十余款”[20],这当是该书得以编纂的重要条件。万历年间编修的礼仪规范书籍绝不止《词林典故》一种。摘其要者言之,唐伯元(1540—1597)《铨曹仪注》、许弘纲(1554—1638)《台仪辑略》等部门礼仪规范的著作皆在前后编成,很难想象这纯属巧合。唐伯元称:“(铨曹)其失,盖自礼始矣……自嘉靖以来,几于尽弃其籍,官以天名,而体统之亵,至与诸司等。”[21]许弘纲称:“今法宫玄默,警跸希闻。署不必具官,官不必入署。下陵上替,人易其方。……于汉官威仪乎何有?”[22]可见,万历时期的士风渐颓,应当是《词林典故》编修的时代背景,也是编行该书的必要性所在。
在修书肃纪、文献足徵、士风颓靡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词林典故》的编行便不足为奇。四库馆臣评价该书称:“率据案牍原文,不加润饰。往往鄙俚可笑,不足以继《翰林志》《翰苑群书》后也。”[23]认为《词林典故》不过是“鄙俚可笑”的“案牍原文”,实因其未能深究此书的编行背景。《词林典故》的主要编修意图本来就不在于像《翰林志》《翰苑群书》那样考信史、存规范,而在于肃纪纲、立声威,因此呈现出“率据案牍原文”的景象实属情理之中。
2 《词林典故》的主要内容
《词林典故》将翰林官的日常工作划为职掌和仪节两大类。其中,职掌包括经筵、日讲(恩赐、东宫讲读)、纂修(进书仪)、考试(会试、武举、两京乡试、各省乡试)、廷试、廷试举贡、记注编纂、侍直、侍班、扈从、管诰敕、贴黄、修玉牒、捧敕、教内书堂、上陵、分献、册封、斋诏(祭告、使朝鲜),共计19类;仪节包括文移、到任(掌院、宫詹坊局、讲读史官、二司成)、考满(三年、六年、九年、考语、考满呈式)、考察、升迁、朝班(列衔)、公宴、斋宿、杂行(东阁会揖、内阁拜节、内阁作揖、中堂庆贺等仪、中堂迎送、阅卷、行香)、本衙门交际(柬帖、公会、引避、郊饯、馈送、公奠)、别衙门交际、给假、舆从服饰(俸米柴薪、直堂、纸劄、拨官吏办)、庶吉士馆规,共计14类。仅仅只看该书的书名和目录,便不难知悉其为典章制度之书,四库馆臣也将其纳入史部职官类;但如果把视线扩展到三个月后编成的另一部重要典制类书籍《万历会典》,则会让人对张位编修此书的必要性产生疑惑。因为《万历会典》中已经对翰林官的职掌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且由皇帝作序颁行[24],无疑更具法律效力。如果将《词林典故》作为典制之书来编写,其信度和效度毫无疑问难以与《万历会典》比肩。张位、于慎行既是《万历会典》副总裁、又是《词林典故》的主编;朱赓同样以《万历会典》副总裁的身份给《词林典故》的修撰提供了众多素材,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现实情况。两书编成时间接近、主要编修者相同,又都涉及翰林院和翰林官,甚至相关篇幅也大致相同。如果《词林典故》不能在相关内容上胜《万历会典》一筹,那么该书即使通过部门长官的意志强力推行一段时间,也会很快湮没无闻,这显然不是编书者所乐见的情况。因此,《词林典故》必须在内容上与《万历会典》有所差异,才能保证该书籍的存在价值。
经过两书的初步比对,便可发现两书有关条款的详略不同。首先,根据影印情况来看,《词林典故》70页,半页9行,每行20字,估算字数约1.7万字;《万历会典》卷221专记翰林院,篇幅为18页,半页10行,每行20字,估算字数约4千字。因此,《词林典故》比《万历会典·翰林院》的篇幅多出近3倍。第二,《词林典故》当中所记类目为33大类(另附36小类),《万历会典》翰林院部分有50条,较之《会典》而言,《词林典故》的条款也增加了约40%。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词林典故》的内容较《万历会典·翰林院》更为充实。即使仅仅计算《词林典故》的职掌部分,也可发现《词林典故》使用更多篇幅来详述相同的条款,明显较《会典》更为详细。
如果将两书的有关条款进行深入比对,可以看出《会典》与《词林典故》实则各有侧重。试以翰林官的主要职掌“经筵”条为例析之。《万历会典·翰林院》内容为:“凡经筵,钦命内阁大学士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班俱在尚书、都御史上。讲书、展官等及日讲官俱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其经筵讲章、日讲直解,俱送内阁看定。经筵讲章,先三日进呈;日讲直解,先一日进呈。”[25]可见《会典》仅用不到百字简述了翰林官经由阁臣选择参与经筵,以及经筵讲章的进呈时限。而《词林典故》记载经筵的条款多达500余字。在和《会典》内容重复之处的具体表述为:“凡初开经筵,以勋臣一人及首位中堂充知经筵官,其余中堂俱同知经筵。衙门自编修以上年深相应者及掌、詹、祭酒,俱充讲官。修撰以下年浅者充展书官,近年检讨亦题讲官,讲读亦展书。礼部正卿亦有充讲官者。每岁春秋开讲、辍讲,俱诣中堂作揖,朝房投帖,讲官撰完讲章,先送中堂看定,三日前进呈。”[26]较之《会典》,更加明确的突出了翰林院系统内的哪些官员有资格成为讲官、展书官。其后补充的400余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40余字明确了春、秋两讲的起始日期,并提示“须要演习精熟”。剩余的大量篇幅,全部都在介绍讲官、展书官的行为规范。例如何时该磕头、何时当作揖,何时应当站在哪个位置,对讲前、讲中、讲后的具体言行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再以翰林官日常参与的另一重要活动“考试”为例。《万历会典·翰林院》仅用不足130字记载了主持会试和武举的官员从哪些范围内选择,而《词林典故》的相关篇幅几乎达到《会典》的8倍。除会试、武举外,还详细说明了两京乡试、各省乡试的有关情况。此外,完全不提《会典》业已说明的主、同考官选任情况,而是详述从接到考官任命之刻起直到考试结束后,每个相关环节的具体行为规范,对于何时能见何人、何时与何官一同办事、如何做好考试保密工作等细节,都有详尽的说明和解释。
综上,仅对比“经筵”与“考试”两个具体条款就可以发现:《词林典故》详《万历会典》之所略,两者相互补充;同时,《词林典故》尤其强调各级翰林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的行为规范,而不像《万历会典》那样偏重于职责范围的界定。如果只是粗略浏览《词林典故》的书名及卷首目录,往往会直观认为其不过是增广翰林官见闻的典故之书。唯有通读全书方能知晓:《词林典故》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翰林先进的奇闻趣事、也并非明确翰林官的岗位职守,而是打造翰林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让翰林官在处理日常工作、人际关系时有据可依。这或许也是张位在《万历会典》已经发布的前提下,还能够有信心“入馆者人给一册”,而不用担心与《会典》内容重复的原因所在。言行规范无疑应当纳入“礼”的范畴,而“礼”的本意便在于突出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因此,《词林典故》不仅是一部典制之书,更是一部礼书。知晓了《词林典故》作为礼书的性质,便易于理解为何全书内容几乎全是翰林官与皇帝及朝臣的相处仪节。即使在该书的目录当中明言此书的前半部分属于职掌的范畴,也掩盖不了在职掌的条款之下细述仪节的现实。
以翰林官为皇帝的讲学为例。翰林官在接到讲学任务伊始便需开始充分准备,“凡日讲官、经筵讲官及经筵展书官,初题请后,俱约同官偕赴文华殿看视讲案,询演礼仪。日讲官请同官于私宅演讲,备饭;经筵官于射所演讲,备椅、桌、茶。”[27]而在讲学过程中,一举一动也处处透露出对皇上的恭敬。讲学开始前,讲官应向皇帝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讲授过程中,“遇称皇上圣明,则拱手俯躬”[28];讲完后,再行一拜三叩头之礼。甚至于讲授所用之书该如何摆放,书尺何时“两旁直压”、何时“八字斜压”都有明确规范[29],考虑不可谓不周全。
以翰林官与其他官员的交接为例。翰林官参加不同场合的公宴,座次有严格区分,“凡郊祀庆成宴,学士入殿侍,坐在文官四品之上。宫坊坐中左门,讲、读以下充经筵讲官及展书官者,与宫坊同坐。凡籍田等宴,衙门官照朝班序坐。惟廷试礼部晚宴及恩荣宴,宫坊坐光禄卿之上”。[30]与不同品级的官员在不同的场合见面,礼仪亦有不同。如果需要约见其他部门长官,“与各部正卿双侍生帖,亚卿以下俱红单帖。”[31]如果是途中偶遇,“虽冢宰不避,立马让过;与科、道、部属相遇,径站上手,不作环揖;其系曾为提学者,仍执门生礼”。[32]
以上两例,不过是豹之一斑。实际上,《词林典故》对翰林官与皇帝、公卿、百执事交接时的相互称谓、拜帖、座次乃至馈遗礼品都有详尽说明。这些规定看似繁琐,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厌其详的繁琐礼节所营造出的“仪式感”,实则是对尊卑秩序的强调与维护。对翰林官群体而言,遵守礼节还有着其他更为现实的意义。一是突出自身对皇上威严的尊崇。翰林官“一朝获知于皇上,则进身之阶由此畅通”。[33]因此会更加珍惜在君主面前表达自己思想、主张的机会,尤其是在讲学过程中会更加谨言慎行,遵守相关礼制规定,以便给皇帝留下较好印象。二是作为百官的垂范。翰林院作为国家文教中心,翰林官的言行也理应成为朝臣的楷模。倘若翰林官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尚不能够做到动合规矩、言成轨范,则何以飨天下之望?总的来看,翰林官因为承担着教化皇帝、风化天下的职责,如果不能恪守礼仪规范,在给作为“国本”的皇帝讲学、侍读时便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垂范,在和其他部门交接时也无法体现出翰林院体势的崇重。而每一位翰林官的言行,其影响绝不止于其一身,也难免会影响到朝廷上下对翰林院这一部门的评价。这才是张位要在《词林典故》中打造翰林官行为规范的原因所在。
3 《词林典故》的编纂意义
从表面上看,《词林典故》的编纂能够有效与《万历会典·翰林院》互为补充,为全面研究明代翰林官的职掌保存史料、提供窗口。但实际上,该书的编行还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正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34],翰林院与内阁的密切关系可以在明代阁臣的来源中得到印证。根据方志远的统计,自正统后的内阁阁臣基本来自翰林院[35],可见翰林官在明代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因之明政府对翰林官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对较高。而《词林典故》明确规定了翰林官的行为规范、交接礼仪,通过异常周密的条文规定,做到了“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有利于翰林官尽快熟悉自身所处岗位的规章制度与运转流程,客观上为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翰林官队伍提供了保障;而高素质的翰林官员队伍,也有助于维持翰林院的规范运作、打造翰林院的良好部门形象。
第一,表面来看,《词林典故》实有补《万历会典》不足的意味。《万历会典》的翰林院部分,是翰林院现行典章制度的合集;《词林典故》则是翰林院过去典章制度的汇编。无论张位摆在台面上的《词林典故》编纂缘起再怎样冠冕堂皇,之所以要编撰此书,归根结底还在于到张位掌管翰林院时,相当一部分翰林官已经不能严守词林先进的行为规范,现行的礼仪规范较之过去严苛的规制已有退化,所以张位作为部门长官必须对此加以整顿。而部门规制较之《万历会典》更加严格、详细,也凸显出对翰林官自我的身份认同。
第二,就深层次而论,《词林典故》对翰林官的行为作出详尽、严格的规定,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约束翰林官,更在于教化君主。“君德成就在经筵,尤在日讲。”[36]翰林官作为“帝师”,在主讲“经筵”时的行为举止毫无疑问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君主。尤其对于年幼的皇帝来说,日讲官的处事方式和道德品质也会在讲论过程中影响到君主思维模式的形成。由此可见,规范翰林官行为实则也是为培养言成规矩、动合轨范的君主提供保障。
第三,《词林典故》编纂最重要的意义,实则是通过严格标准来培养官员,进而为专制皇权统治提供一个谨守朝廷规制的后备顾问团,影响国家的行政决策、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官员希望获得重用的第一步,无疑是进入君王的视野,翰林官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他们时常亲近君王成为可能。在成为“帝王之师”后,便是让皇帝对自己加以了解、熟悉,并力图通过一言一行来维护自身在皇帝心中的良好形象。一旦得到皇帝的青睐,不次之迁也便成为可能,这从明代翰林讲、读之臣的快速迁转可以得到印证。而在跻身高级官员之列,乃至担任辅政大臣后,便可实现传统读书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共同理想。仅以张位为例,与其一同在翰林院进行庶吉士修业的29人中,便有沈一贯、陈于陛、王家屏、朱赓、于慎行、张位等6人入阁乃至担任首辅,其他身居高位者不知凡几。可见言行符合规范的翰林官,确实大概率能够获得可期的政治前途;尽管万历皇帝在位的中后期几乎不再视朝,但张位及其同窗学友却有效地维持了中央决策机制的运转,在明代政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言以蔽之,《词林典故》的编纂实质,就是通过严格规范翰林官群体行为,最终实现“有位者有为,有为者有位”,是张位整肃翰林院纪纲,打造高素质翰林官队伍的一种尝试。
4 余论:万历修史热潮中的《词林典故》
如果仅就《词林典故》一书而言,或许觉得它不过是张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37]的表现之一。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整个明代中后期,却可以发现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在明代万历时期,各衙门官修并刊行职官类史籍突然成为潮流。
仅举其要者言之。《明会典》是明政府刊行的最为重要的官制书,正德年间李东阳等人编订《正德会典》之后,数十年间未曾改易。至万历初年,明神宗又令张居正等人开始重修会典,并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行。而张位《词林典故》刊行的时间,就在《万历会典》印行的前几个月。如果将视线进一步拓展,我们可以发现唐伯元的《铨曹仪注》关注吏部衙门内的礼仪,编成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许弘纲的《台仪辑略》聚焦都察院内部的礼仪规范,编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俞汝楫的《礼部志稿》关注礼部的仪节和规程,编成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不禁让人疑惑:为何在万历中后期一大批官修礼制书集体涌现?
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和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注意到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后,明政府在陈于陛、焦竑(1540—1620)等人的主导下修撰明朝国史的过程,但他们在研究正史编撰本身的原因及其意义时,限于各自的论述主题,亦未对相关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然而,通过对当时史书的宏观考察,却可以发现此时正史的编修与官修典制实则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一,按照正统的史学修撰体例,“志”是正史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早在陈于陛上奏编修国史时,就把“志”的内容列在首位。而在志书编修中,毫无疑问会涉及到官制的相关问题。因此,一方面官方典制的编修可以为国史当中志书部分的编撰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在编撰国史志书的过程中势必会广泛收集资料,而这些资料也可以用于各衙门典制的修撰。其二,主管国史编修的官员往往在官方典制史书的修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词林典故》为例,上奏请修国史的陈于陛本身也是《词林典故》的参编者,而一度担任国史总裁官的张位更是《词林典故》的署名作者及刊行人。此外,编修国史的官员大多从翰林出身,而翰林官本来大多都是熟稔掌故之人。通过以上两点不难看出,万历中期的国史编修,实则与当时官方典制的编修风潮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国史编修的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当时一系列官修典制的刊行,使编修国史的努力并未白费,相关的资料仍然通过官修典制书的方式流传下来供后人参看,起到了保存国故的重要作用,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明代当朝国史修撰的贡献提供了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