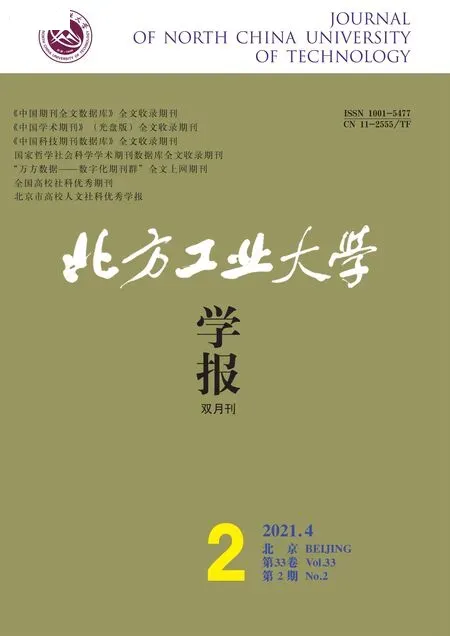当代日本歌舞伎界世袭制的历史文化因素解读*
张 蓓
(1.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100089,北京;2.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300222,天津)
2017年11月,日本松竹公司为歌舞伎世家松本幸四郎家举办了“高丽屋三代袭名庆祝会”,对外公布了二世松本白鹦、十世松本幸四郎和八世市川染五郎祖孙三代将于次年同时袭名的重大消息,这是时隔37年后日本再次出现祖孙三代同时袭名的盛况,也是平成时代歌舞伎界最后一次大型盛会,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和讨论。究其原因,除了艺术世家的社会影响力和演员自身的知名度以外,战后歌舞伎界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愈演愈烈的世袭现象也成为舆论焦点。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后,日本已经成功跨入亚洲民主国家行列。然而,在社会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战前一直崇尚“实力主义”,推行养子、婿养子继承家业的歌舞伎界为何逆势而行,重新建立起世袭制?这一问题仅从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传统艺能的冲击方面难以得到深刻剖析,它还与古代日本社会的家族制度、身份等级制度和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密切相关。
1 战后日本歌舞伎界世袭制的现状
近代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两次洗礼,政治上逐步由幕藩体制走向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跻身亚洲民主国家行列。然而与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相悖,歌舞伎界却一改战前收养养子、接纳婿养子继承家业的传统,转而开始推行以血缘和家族为重要标志的“纵向”世袭制,并通过联姻“横向”发展家族关系网,形成了与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的门阀现象,学者中川右介形容道:“八成的歌舞伎演员都是亲戚”。[1]世袭制虽非歌舞伎界所独有,能乐、狂言界也存在子承父业的现象,但根据“日本艺能实演家团体协议会”①调查显示,一线歌舞伎演员的数量、歌舞伎演出的场次及频率都远超其他门类的传统艺能。[2]显然,相较而言歌舞伎界的世袭制无论从演员体量还是艺术门类本身的社会影响力来说更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2013年4月,拥有130余年历史的歌舞伎圣地——歌舞伎座经过第四次大规模整修后重新开门迎客。首场演出,松竹公司组织了歌舞伎界最具盛名的市川团十郎家、尾上菊五郎家、中村歌右卫门家、片冈仁左卫门家、松本幸四郎家、中村吉右卫门家以及守田勘弥家这七大家族参与其中,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歌舞伎座在日本传统艺能史上的重要性,也体现出这七大家族在业界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通过梳理七大家族的家谱可以明显看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在选定继承人方面战前与战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势,即战前遵循“实力主义”战后推行“门阀主义”。李玲认为:“名题下出身的艺人晋升至名题非常少见,因此歌舞伎的等级制度并非实力优先,而是以家系与血统为重。”[3]诚然,诸如坂东玉三郎、片冈爱之助等享誉世界的歌舞伎演员也并非梨园子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仅是众多歌舞伎演员中的个例,并且探讨他们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他们是先以养子身份进入歌舞伎世家,后又扬名立万的基本事实。
歌舞伎界何以出现这样的“返祖”现象?以往的研究多从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传统艺能的冲击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日本戏剧学家儿玉龙一认为:“二战前,收养才能出众的孩子作养子,将家业传于庶子的现象极为多见。战后,家业仅传给亲生儿子的做法才逐渐多了起来。最大的原因是歌舞伎生存发展的基础缩小了。日本国内曾经遍布大小歌舞伎剧场,还出现了扎根本地的歌舞伎演员。甚至到地方巡演时,还可以临时在当地找到出演儿童角色的小演员,群众基础极其广泛。然而进入昭和时代后,地方举办演出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演员薪酬逐年递减,歌舞伎与整个社会之间产生了距离,进而丧失了人才的流动性。”[4]毋庸置疑,明治维新后日本拉开了学习西方的大幕,全力推动现代化,其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传统艺能界也不例外。突出表现在,“四民平等”制度的实施使日本社会突破了阶层的束缚,赋予了普通民众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同时,纷纷涌入的西方现代文明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也让传统艺能一时间黯然失色,受众基础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受到严重挤压。然而,歌舞伎毕竟诞生于江户时代,除了明治社会的深刻变革等客观原因,分析战后歌舞伎界世袭制的形成还不能忽视古代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及这门戏剧艺术本身的特质。
2 家族制度与歌舞伎
中日两国对“家”的涵义界定不尽相同。“中国的‘家’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的家族经济共同体。”[5]换言之,血缘的代代相续并不是日本家族追求的首要目标,家业的后继有人、绵延不断才是根本。
日本歌舞伎世家的家业即指家艺,其传承正是通过“家”的代代延续来完成的。又因为歌舞伎属于戏剧艺术,“艺”的精湛与否直接关系到“家”的安危所在。因此,自歌舞伎发端的江户时代起,市川团十郎、尾上菊五郎以及松本幸四郎等各大名门世家就已经开始精心锤炼技艺,以求家业昌盛、家族永续。可以说“保家”是歌舞伎世家的首要任务,而“修艺”正是“保家”的不二法门。
“艺”是家业的核心,“人”是传承的主体,“人”的素养直接关乎“艺”的高低,因此歌舞伎世家极为重视继承人的选定问题。日本人家业继承人的选择可以不必受血统和系谱关系的限制,被认定为具有亲子身份关系的养子可以继承家业,这就是日本家族中的“模拟血缘关系”。[6]换言之,日本家族在选定继承人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候选人的血统,而是能力。在歌舞伎界,为了能使家业不至凋敝败落,各大世家在继承人选拔方面并不一味追求血统的绝对纯正,将外形出挑、潜质优良的孩子收为养子,或者以招婿上门的方式把堪当大任的人才以婿养子的身份吸纳到家族内部,这在二战前是业界的通用做法。以市川团十郎家族为例,二世市川团十郎就将养子升五郎选定为家业继承人,九世也因没有男性子嗣而把家中事务托付给女婿市川三升,其后继承家业的十一世也是养子出身。如果将血缘作为能否继承家业的必要条件,那么市川家族恐怕也会早早止步于二世,就不会出现日后稳居歌舞伎界顶端的“市川宗家”了。
“模拟血缘关系”的成立,给歌舞伎世家的传承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选拔继承人这一问题上不“唯血缘”,而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择优选用,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家族败落的悲剧发生,最大限度保证了家业的延续。总而言之,选贤用能、维系家业是各大歌舞伎世家的终极目标,因此“能者居之”一直是选定继承人的重要原则。
有鉴于此,歌舞伎界一直被世人划归到“实力主义”的阵营,但不能否认的是,歌舞伎毕竟脱胎于充斥着世袭制和身份等级制度的江户时代日本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烙印。日本的世袭制由来已久,从平安时代开始已经有公家世袭担任某种特定官职的制度,史称“官司请负制”,这一制度在镰仓及室町时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进入武家社会后,虽然公家大权旁落,但等级细化程度却愈来愈高。从摄关到一般官吏都是按照家族、家格的等级来任命的,由上至下分别是:摄关家、清华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和半家,这些家族也成为明治维新后华族的前身。由于家格始终不变,依据家格高低所能担任的职位自然也不会变。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低家格的人,无论能力如何突出,也不可能担任超出家族等级的官位,世袭制成为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石。更为关键的是,天皇作为日本社会的最高权威和“总本家”,“万世一系”世袭罔替,这深刻影响着日本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是日本世袭制的基本底色和根源所在。
世袭制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不唯血缘、接纳才能出众的养子和婿养子来继承家业一直被视作是歌舞伎界“实力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但不应忽视的是,其前提是建立在“经营共同体”——“家”的延续这一首要目标之上的。换言之,为了“家”的延续,世袭制可以暂时被舍弃,所谓的崇尚“实力主义”也仅仅是“家”的延续大框架下的“权宜之计”而已。一旦首要目标发生变化,世袭制又会卷土重来,重新回到歌舞伎的世界当中。
3 身份等级制度与歌舞伎
“家”的延续这一首要目标为何会发生变化?剖析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歌舞伎世家的延续与否,受到古代日本社会身份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武士身份得以真正确立。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建立幕藩体制的同时,将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身份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在法律上得以固化,自此阶层的身份等级和所从事的职业被紧密捆绑在一起。当然,歌舞伎界也不得不遵从国家法律,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在日本历史上,从事艺术表演的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中世,艺人被划归“非人”。到镰仓时代,初代将军源赖朝发布政令设立机构“弹左卫门”管理“穢多”和“非人”。1603年,德川幕府成立。同年,日本出云地区的巫女阿国始创阿国舞蹈,歌舞伎开始萌芽。虽然歌舞伎诞生于江户时代,但因德川幕府仍然沿用旧制,歌舞伎演员也同其他艺人一道被划归“弹左卫门”管理。1673年,江户歌舞伎创始人初代市川团十郎袭名市川海老藏,歌舞伎进入高速发展期。为了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团十郎组织歌舞伎演员以源赖朝发布政令时歌舞伎还未出现,理应不适用该政令为由起诉到奉行所,最终判定团十郎胜诉,歌舞伎演员才从“非人”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虽然摆脱了“非人”的身份,但歌舞伎演员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世人仍然使用“河原乞丐”等蔑称来称呼歌舞伎演员。
一方面,严苛的身份等级制度带来了职业世袭和阶层固化,阻断了歌舞伎与其他行业间的人员流动,另一方面,低下的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其他阶层人员进入歌舞伎界的意愿。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各大世家时刻面临着因没有适宜男丁继承家业而导致家族消亡的危机。收养养子和接纳婿养子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但又因为身份等级制度的限制,在挑选养子和婿养子时留给歌舞伎世家的选择并不多,更多情况下是将其他世家内继承家名无望的家庭成员吸纳到自己家族中,因此这种流动也仅能看作是行业内部的流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歌舞伎界与其他行业之间隔绝的基本状态。福泽谕吉形容当时的日本社会,“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7]
综上,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会随时引发行业内的人才短缺,而人才短缺是导致家业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稳居江户歌舞伎界顶端的“市川宗家”为例,1704年二世市川团十郎从父亲手中继承艺名,完成了歌舞伎艺术有史以来的首次袭名。1727年二世团十郎又将家名传给了养子升五郎,可惜升五郎在袭名之后不幸染病,22岁就撒手人寰。由于当时市川宗家内部并没有继承家业的合适人选,因此在三世团十郎去世后的第12年,市川宗家才将二世松本幸四郎收为养子,并允许其袭名四世团十郎继承家业。传承到九世时,家族内部又遇到了家业无人继承的难题。无奈之下,只得由九世的女婿市川三升暂管家中事务并积极寻找继承人,终于在1940年将七世松本幸四郎的长子收为养子承袭家业,家族才得以延续。由此可见,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市川宗家”,历史上也几次三番受到后继无人的困扰,其他世家的境况就可以推想一二了。
明治维新后,政府虽然明文规定实行“四民平等”制度,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阶层流通的路径,然而长期根植于日本社会深层的身份等级观念并没有立刻随之消失。有研究指出:“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种新的身份取代了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并在‘四民平等’的招牌下继续演绎着新的身份差别。”[8]从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虽有二世市川左团次在1928年访苏公演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出现,但歌舞伎演员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他们中的大多数经济窘迫、生活困难。三世中村翫右卫门回忆自己在1920年通过名题考试正式袭名时说:“按照事先约定,费用都是由大谷社长出的。”[9]大谷竹次郎正是日本松竹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松竹公司是目前日本最大的综合性民营娱乐集团,经营范围横跨电影、戏剧和音乐领域,在歌舞伎商业演出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是战后歌舞伎界世袭现象加剧的另一个推手。
4 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与歌舞伎
日本的近代剧场与近世剧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经营是否是商业行为。[10]松竹公司较早实现了剧场运营的商业化,而商业化运营直接推动了松竹公司在经营空间、演员吸纳方面绝对优势的确立。
1890年代,松竹公司从经营京都新京极的歌舞伎座、明治座、夷谷座和大黒座、布袋座这5家剧场起步,通过兼并收购其他剧场的方式迅速扩张商业版图,仅仅花费了不足20年时间就将势力从京都、大阪发展到东京。1913年,松竹公司拿下了东京歌舞伎殿堂——歌舞伎座的直营权,标志着其在首都圈歌舞伎商业演出市场中强势地位的确立。时至1920年代,首都圈的演出市场形成了松竹公司、帝国剧场和市川座三足鼎立的态势。1928年和1929年,松竹公司先后实现了旗下东京、大阪地区剧场的股份制改革,完成了艺术经营的近代化。
演出空间的持续扩张加速了松竹公司在歌舞伎商业演出市场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严重挤占了其他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引发了行业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1917年,松竹公司与根岸兴行部剧团围绕歌舞伎演员市川松茑是否出演该剧团演出的问题发生纷争,其结果是,松竹公司逐步改变以往口头邀约演员演出的方式,改为与演员签订专属合同,进一步加强了歌舞伎演员对松竹公司的依附关系。其后虽偶有1920年二世市川猿之助脱离松竹另立春秋座举办演出,及1936年十一世市川团十郎加入东宝剧团等事件发生,但最终都以演员发展不顺不得以重回松竹公司而告终,这些都反映出其坚固的垄断地位并未发生动摇。
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推动了其在歌舞伎演出空间和演员吸纳方面绝对优势的形成,而演出空间和演员吸纳方面的绝对优势又反过来为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加足了马力,前者与后者形成了闭合的逻辑利益链条。这一方面削弱了歌舞伎世家在处理诸如家族继承等事务方面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将家族利益紧密捆绑在松竹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因此,当世袭制符合双方利益时,那么它的确立就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进入经济大萧条,战时剧场内观众爆满的盛况一去不复返,加之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歌舞伎等传统艺能演出市场经营受困。为应对新形势,松竹公司开展多种经营,将上演歌舞伎无法盈利的传统剧场转型成为演出新派戏、喜剧、家庭剧、小品以及电影的新兴剧场。在歌舞伎的低潮期,松竹公司仍旧看好未来市场潜能,以多种形式给予补贴,为歌舞伎界保留了基础力量。二战结束后,松竹公司推动歌舞伎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实现了访美、访苏公演。1950—1960年代,日本电影界出现了一股“忠臣藏”热潮,松竹公司顺势推出了由歌舞伎演员主演的《忠臣藏 花之卷·雪之卷》(1954)《大忠臣藏》(1957)两部电影,把他们推向更广阔的领域。1985年4月,松竹公司为十二世市川团十郎举办了袭名公演,掀起了新一轮歌舞伎热潮。在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下,歌舞伎世家的“家”延续危机中的经济因素影响逐步减弱,演出收益也稳步攀升,因此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后代继承家业成为上佳选项。与此同时,袭名公演已经成为带动歌舞伎演出票房的绝佳卖点,“歌舞伎(松竹)以袭名盈利,宝冢以退团盈利”[11],而祖孙三代或者父子两代同时袭名能够瞬间抓住公众眼球,保证上座率,为松竹公司博取最大经济利益。由此,松竹公司和歌舞伎世家在世袭制上达成了利益共同点。
时至21世纪,日本开始实施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振兴战略,推动了歌舞伎艺术的进一步发展。2001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就是这部法律将1990年代提出的“文化振兴”说法改为“文化艺术振兴”,扩大了对文化概念的解释,显示了对文化振兴认识的深刻。[12]国家对艺术的重视为歌舞伎行业插上了起飞的翅膀,除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之外,随之发生巨变的,还有歌舞伎演员的社会地位。十五世片冈仁左卫门、二世中村吉右卫门、七世尾上菊五郎等人被认定为“人间国宝”,令和元年,五世坂东玉三郎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等人一起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授予的“文化功劳者”称号,这些都彰显了歌舞伎演员今非昔比的社会地位。
挣脱了身份等级制度枷锁的歌舞伎界,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松竹公司的商业运作下,全行业风生水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各大世家不仅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也拥有了与之匹配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家”的延续已经不再是歌舞伎世家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了,加之战后各大世家子嗣绵延,家族的首要目标悄然发生变化,世袭制自然也就“死灰复燃”重新回到歌舞伎的世界当中了。
5 结语
卡尔·科恩说:“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13]在亚洲民主国家日本出现诸如歌舞伎界这样以血缘和家族作为重要标准的世袭制无疑是不平等的,也是违背全社会民主化的大趋势的。然而,通过纵向梳理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不难发现,脱胎于江户时代的歌舞伎自始至终都无法脱离家族制度和身份等级制度的影响,战前展现出来的所谓的“实力主义”不过是“家”的延续这一首要目标下的“权宜之计”而已。加之在歌舞伎领域深耕多年的松竹公司成功的商业运作,为该行业贴上了名利双收的醒目标签,成功将世家子弟留在了行业内部。因此,战后世袭制的回潮不是偶然,而是古代日本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在当代的“重现”。令和开启,新冠疫情下歌舞伎界何去何从,是值得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 “日本艺能实演家团体协议会”成立于1965年,由影视演员、歌手、舞蹈演员、传统艺能演员等组成。目前受日本文化厅委托负责版权的集中管理、从业人员的扶持和行业现状调查研究及政策建言等工作,相当于日本的演出行业协会。
——兼论超级歌舞伎的开创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