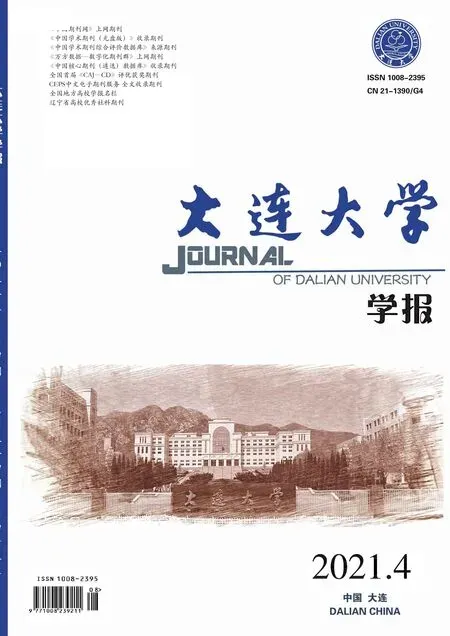论抗战时期“名著改编热”现象
——以巴金《家》的改编为例
刘世浩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围绕巴金《家》的改编研究已经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家》改编为舞台剧、电影的过程以及演出、上映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分析。例如,《忠实原著前提下的名著改编——以巴金〈家〉的改编为个案》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家》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改编及其成败的原因,尽管其中有对时代社会方面等外部语境的分析,但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探讨对比两种改编的优劣成败方面,其关注点不免局促;《曹禺改编巴金〈家〉的心态探析——兼论吴天版〈家〉的得失》则以曹禺改编《家》前后的心态为切入点,指出曹禺版话剧《家》的成功在于抓住了小说《家》的精神气韵,从而超越了拘泥于原著的吴天版话剧《家》;《论巴金“激流三部曲”的话剧改编》将《家》《春》《秋》三部小说的话剧改编作为整体性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为解读巴金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特定的研究视角,但是,这种研究同样未能摆脱“就改编论改编”的思维模式①参见:金宏宇,原小平.忠实原著前提下的名著改编——以巴金《家》的改编为个案[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05):39-42+45;王鸣剑.曹禺改编巴金《家》的心态探析——兼论吴天版《家》的得失[J].四川戏剧,2008(03):38-40;任贵菊.论巴金“激流三部曲”的话剧改编[J].大连大学学报,2020(02):42-48+54。再如:周立刚.《家》的接受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5;王峰峰.家族文化与《家》的改编[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徐江.选择﹑提炼﹑集中——再谈从巴金《家》到曹禺《家》改编的思想及路径[J].戏剧文学,2017(3):44-51;等,均对《家》的改编情况进行了相关论述。。然而,关于《家》的改编与时代思潮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只有2016年海南师范大学许海洋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家〉的认知接受及其所反映之社会思想变迁》从文学认知接受角度涉及了《家》的改编与当时社会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只对《家》这一个案进行了分析,并未从历史长时段中看出《家》的改编究竟处于怎样的社会思潮之中,更没有指出《家》的改编在当时的“名著改编热”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另外,抗战时期的“名著改编热”还引起了当时文艺界乃至社会舆论层面的广泛讨论,这些围绕小说改编的讨论触及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形式技巧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有相当一部分论述是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的角度出发,认真探讨了这种改编的实际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改编效果,其中关于小说改编成电影、话剧、舞台剧的利弊关系讨论在客观上对增进人们对于小说与话剧、电影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着特定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历史长时段中来考察《家》的改编与社会思潮之关系,同时勾勒出抗战时期出现的“名著改编热”现象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审美价值观念流变,就构成了文本论述的重点。
一、《家》的改编及其社会反响
1940年冬,联华公司的编剧吴天率先将《家》改编成五幕话剧搬上了舞台。1941年,中国联合影业公司集合了当时第一流的导演、演员,将《家》搬上了银幕[1]15。随后,1943年4月8日,曹禺版本的话剧《家》在重庆上演,连演百余场,创造了重庆话剧演出的最高纪录。
尽管尚未看到关于话剧《家》演出情况的详细统计数据,但根据当时的报道来看,不难看出其火爆程度。1941年3月10日《小说日报》刊登了《辣斐之〈家〉造成大批病人》一文,文中提到舞台剧《家》连演83场,以至于不少演员纷纷病倒。其中,觉新的扮演者徐立累得几次吐血;扮演觉慧的韩非脚肿得无法走路;高老太爷的扮演者王即絮和替补演员一人一场交替演出[2]。同年《小说日报》4月30日《上海剧艺社改编〈鸳鸯劫〉》一文提到《家》“接连已经演了一百数十场,轰动了上海的整个剧坛”[3]。还有,“巴金的《家》,自从经过吴天改编成舞台剧在辣斐剧场演出后,真可说是轰动一时,造成剧坛空前的卖座纪录”[4]。再如,“《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借以号召观众了。”[5]90-98
话剧《家》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当时上海大多数的电影公司的注意力。1941年《电影日报》11月16日《艺坛风景线》栏目刊登消息称:“巴金之《家》,既由吴天改编舞台剧,因演出后卖座成绩奇佳,吴天决再改编《家》之续集《春》《秋》,而《春》已在吴天积极改编中,不久即可脱稿云。”①参见《电影日报》1941年11月16日“艺坛风景线”栏目。这种成功的同时也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出现了未经作者同意而私自将改编后的《家》搬上舞台的事,以至于巴金的代理人不得不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这种纠纷[6]。
关于《家》何以能够获得读者与观众如此广泛的青睐,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的相关报道中窥知一二。1941年2月11日《小说日报》刊登了题为《周贻白放弃〈家〉的编剧工作》的短文,其中提到:“本来,巴金的作品,完全以一种真情的流露,控制读者的心绪,因为《家》是更富于这种真情者,自然更可以抓住读者的了。就因为《家》轰动一时的缘故,戏剧电影两界,都要将他改编,搬上舞台与银幕的了。”[7]问题在于,除此之外,这种改编的受欢迎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同年《新民报半月刊》第3卷第6期刊登的《关于巴金的小说〈家〉被改编成剧本的几句话》对此进行了探讨:“《家》所以能引起年青人②【年青人】现在写作“年轻人”。的共鸣,不止③【不止】现在写作“不只”。是写出了为多数人所有、为多数所憎恶的大家庭,而是它展开了新旧势力斗争的姿态,并且解决了年青人所苦恼的事,指示了年青人光明的道路,而被青年们所爱戴。”[8]54这些论述无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家》被改编成话剧、电影之后能够迅速获得广大观众喜爱的接受基础,同时也透露出《家》这一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意义与其改编之后取得巨大成功之间的多重关联。
二、“名著改编热”中的《家》
“名著改编热”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是在1941年12月23日《社会日报》上刊登的《名著与舞台剧》一文中,作者指出:“自吴天改编了巴金的《家》为舞台剧,上海剧艺社卖几次好座后引起很多人的眼红,而名著改编舞台剧,也渐次风靡了起来。”[9]这里所说的“名著”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著作,而是特指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名作家创作的畅销小说。
其实,在《家》改编前后,先后有一批畅销小说被改编成话剧、电影,除了巴金的《春》《秋》以及《火》陆续被改编成电影之外,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满江红》《似水流年》《现代青年》《欢喜冤家》,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碧海青天》《恨不相逢未嫁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以个体情感、家庭内部冲突为故事背景同时广泛展现当时时代背景的小说被搬上银幕。
不过,在这些看似毫无秩序可言的改编背后,实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思潮流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刊物所刊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电影界已经开始广泛以小说为故事底本,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电影与小说的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表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出发点大多出于商业方面的因素考虑(如卖座与否),因此,在取材方面,电影公司往往会选择那些情节曲折、能吸引观众的小说作为故事底本。如此一来,那些以恋爱为主要故事情节的小说,便被大量搬上银幕,一时间,摄制恋爱电影蔚然成风。
在严独鹤所主持的《新闻报》《快活林》副刊中所刊载的小说就以情节曲折、吸引读者为特点,并且,在时人眼中,“情节曲折”“受人欢迎”也是这类小说能够改编成电影在银幕上演的基本质素:“本栏所刊之长篇小说……皆以情节之曲折,而受人欢迎。而《啼笑因缘》,尤诡奇可喜,实为近今长篇小说中唯一受人欢迎之作。而全书所述,亦足为摄制影片绝好之材料”[10]。在这种潮流中,偶尔出现的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影片,反而会被视为是一种商业投机,毫无“艺术的成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被搬上银幕之后,就未获得与小说同等的反响,反而是“那么苦涩沉闷,令人见了昏然欲睡”[11]。因此,有人提出,若要借电影传达“左倾”意识,至少要做到“意识与技巧要平行,要和谐,要同时并进”[12]。换句话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便是那些改编自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的影片,也会被视为偏离了艺术本身的轨道。由此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舆论层面对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评论,立足点多基于商业因素与艺术水平,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评价模式。
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电影公司在选取剧本方面越来越注重民族国家方面的内容,以至于连名剧作家的剧本都会因为没有体现出这方面的意识而未被采用。阿英的《群莺乱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担任过明星公司编剧的阿英,于1937年将自己写的舞台剧《群莺乱飞》改编成电影剧本投给当时的联华电影公司,然而这个剧本却在联华召开的编剧会上“未被通过”,“原因是该剧本,除了在恋爱的关系方面写得成功外,就再也看不到别的”,因此,联华公司的编剧认为“阿英先生写这剧本最大的目的,除了暴露大家庭的丑史外,这里面还象征着我们这错乱的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地丑恶,一样地黑暗,然而,阿英先生在《群莺乱飞》多注重恋爱的描写”,由此造成剧本忽略了那些“严重的主题”[13]7。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即便是出自有名的剧作家之手的电影剧本,也会因为没能传达出鲜明的时代意识而被否定。
而《家》的出现恰恰体现出了“名著改编热”中由注重个体情感与家庭关系的表现向注重体现社会现实问题的转变。特别是《家》的演出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因此,如果我们将《家》的改编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进行考察的话,不难发现,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影剧本,《家》的改编者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背后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指向:一方面是青年人受到大家庭的束缚,引起观众对于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另一方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批判已经溢出了家庭伦理批判的范畴,将对封建家庭的批判与对社会秩序的批判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使得《家》的改编既承续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说改编为舞台剧、电影剧本时以个体情感、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模式,又开启了另一种全新的改编潮流——社会批判的潮流。
从《家》舞台剧本的“提要”中可以看到,该剧的“主题”为“暴露大家庭制度的黑暗和罪恶,蕴藏浓厚的反封建意识”[14]22。而从当时社会舆论层面对《家》的改编的讨论来看,舞台剧《家》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保持了小说中所展现的“新旧势力斗争的姿态”:“《家》所以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不止是写出了为多数人所有,为多数所憎恶的大家庭,而是它展开了新旧势力斗争的姿态,并且解决了年青人所苦恼的事,指示了年青人光明的道路,而被青年们所爱戴。《家》的改编在这上面,是好不放松的。不论哪一幕,都强调着新旧斗争的局面。这是小说中的主旨,也是剧本中的主旨。也就是剧本上成功之处”[8]54。
其实,就《家》这部小说本身而言,它所包含的社会现实意义已经为敏锐的批评家所看到:“在这里,家庭的斗争事实上也就是一种社会的斗争。”[15]247-265这一点诚如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读《家》这小说的时候,也应该视做①【视做】现在写作“视作”。它的总称《激流》的一部份②【份】现在写作“分”。,才更能看出整个的时代的意义。不然,它只不过是近似《红楼梦》的大家庭悲欢的历史而已。”“小说是这样,戏剧也是相同。”[16]46-50再如,在桂林举办“西南剧展”期间,曾围绕《家》的演出进行过广泛讨论,其中就有人指出:“对于《家》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无疑地不能估计得太低,因此这个戏也可以说是很富于现实性的。”[17]从上述论述中可以发现,当时围绕《家》的改编的讨论十分注重该剧本的社会时代意义,强调其在表现青年人与封建旧家庭的斗争之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强调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呈现。而在这种改编实践中所投射出的现实关怀也是其来有自的。
三、“名著改编热”的现实关怀
事实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出现的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为特点的“名著改编热”并非一夜之间成为“影戏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925年,就已经出现将小说改编为戏剧的提议,并且此类提议的出发点正是以文艺的方式对“时代”作出的回应:“现代二十世纪是个什么世纪呢?二十世纪是个反抗强权的世纪、自由伸张的世纪,因此革命流血便成了现代文明底③【底】现在写作“的”。一个特色了……我们处在这时代环境中,只有向前而不有退后的道理,我们要向时代前去,只有迎着有现代精神小说改编为剧本到舞台上去宣传”[18]。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可以看到此类观点的延续。在发表于1933年3月11日《影戏生活》上的《小说改编电影剧本的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弹词的说部,落难公子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般的刻版④【版】现在写作“板”。文章,当然是不适于现时代……现在青年男女所要看的,最欢迎的就算是新化小说,它那里面描写畸形的社会、艰险的世路,准对青年的胃口,使你生强有力的刺激,直接发生痛感……制片的何不开摄几部现代的剧本玩玩,吊吊青年的脾胃。”[19]虽然言语中不免掺杂几分轻浮之感,但同样能反映出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期待拍摄能够反映时代社会问题的影片。
在这种时代语境中,茅盾的《子夜》自然也引起了改编者的注意。其实,围绕着《子夜》的改编曾有过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该小说“实无拍电影之可能”[20]13;有人认为“因为环境的关系”,暂不考虑将该小说改编成电影[21];也有消息称“马彦祥最近将《子夜》变成了电影剧本……更将《子夜》搬上了舞台,在最近就可以由中国戏剧协会在南京演出”,理由是该小说“反映出社会的动乱、都市的罪恶,情节复杂,很富有戏剧性”[22]2。这类讨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并且,在改编侧重点方面,越来越突出该小说对时代社会的表现是其值得改编的重要原因:“《子夜》是一部描写大都市内阶层人物的丑恶、虚伪和阴险的杰作,它是一面黑暗社会的照妖镜,这里面,有投机家,有企业家,有工人,也有布尔维乔气息的小姐,把它摄成影片,真是挺配合的”[23]。
此外,就连昔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因为在改编成电影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特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而受到重视。例如,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时,有人认为不能一味地以批评鸳鸯蝴蝶派小说那样的方式来批评由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原因在于这类由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一般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是注意于情节的曲折动人,对于情节发展中所关系到的社会问题的本质,根本忽略……但也不能过分贬低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价值,因为它究是在情节上接触到不少社会问题的现象……所以当鸳鸯蝴蝶的小说被摄制成电影,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因为电影的感化性和表现法是无疑地强大于小说的,它所给以观众的印象和影响当然比较小说的读者的来得更深刻。”[24]255换句话说,此时社会层面针对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的看法出现了某些新的倾向,即越来越注重此类电影在表现社会现实问题方面的功能,而不再一味地对其进行否定。
正是由于当时对小说的改编是以反映时代社会中的问题为价值导向,所以尽管这些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剧本仍不免带有家庭、恋爱等因素,但是,除此之外毕竟还有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使观众可以从中获得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也正因如此,那些“为恋爱而恋爱”的剧本便被指责是“为戏剧而戏剧”:“如果严格一些来批判《恋》,那么剧中的两对主角,他们所走人生的路,好像是仅为‘恋爱’而有。他们没有一些时代意识,也没有一些社会感觉,他们仿佛是关在一只四面都给帘布笼罩着的笼子中的两对画眉儿,他们尽管在笼子里闹恋爱闹得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可是对于笼子以外有些什么,他们都是丝毫无知。”[25]32-34
四、余 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改编热”引起了当时文艺界乃至社会舆论层面的广泛讨论,其中便有针对小说改编成电影、舞台剧的利弊关系的讨论。仔细梳理此类文献便会发现,当时围绕小说改编的讨论触及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形式技巧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
事实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在传情达意方面的优点与不足:“著作可以文字引人入胜,而影片则非有曲折之情节,总难令观众满意也。”[10]同类观点还有:“小说描写布局的技巧,决不全和电影剧本相同,电影剧本虽可取材于小说,然而不在分幕上用一番功夫,和小说一样的描写布局,直摄成一部影片,反而没有像小说一般精彩”。“往往有许多影片的剧情,写成小说,却成为毫无意义,因为虽然是极平凡的剧情,如果能在分幕上运用其技巧,就能使剧力增加,成为不平凡的影片。”[26]2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改编并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小说是以文字来叙述描写各个人物、各种事态,电影是以表情言语来表演各个人物、各种事态;小说可以从作者的笔底,写出许多文字来烘托书中人物事态;电影则不可能(虽有时也可以说明来烘托之,但借助于说明的电影,已非好电影),故以小说为电影剧本者,无异削足就履也。”[11]有人则从电影与小说所表现的范畴方面指出二者不同:“小说里的世界是静的,给予读者的感觉是间接的;电影里的世界是动的,给予观众的感觉是直接的。小说与电影的范畴各不相同,因此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亦不相同。”[27]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讨论并未消歇,反而愈发深入。1941年《新民报半月刊》刊登的《关于巴金的小说〈家〉被改编成剧本的几句话》中,作者认为改编是一种再创作,而“改编和原作不同,是因为各人的创作方法不一样”[8]54。又如,1942年《话剧界》的《从小说改编话剧谈到〈秋海棠〉》中:“戏剧原是独立的艺术,编剧人所受的舞台条件已是如此地苛刻,事实上,他是难以再受小说的曲折情节的牵制了。”因此,作者认为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许比较容易一些,“银幕上活泼的电影镜头真如小说家生动的笔头”,“然而在舞台上,时间和空间一刻也不放松地紧紧的箍着你!”[28]3再如,1943年《国民杂志》第3卷第8期上的《关于〈家〉的再检讨:小说之改编为电影剧》一文中,作者认为小说在心理描写、时空驾驭以及传情达意方面都有着电影无法模仿的优点,正因如此,《家》的改编势必会在某些方面削弱其艺术表现力:“一部两万五千余言的,以整个大家庭为背景的小说,含着热情、果敢、理智的力量的小说,尤其是那故事的庞杂,若改编成为电影剧本底确未能精彩而有力”[29]67。
总体而言,尽管当时的“名著改编热”在演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注意到了小说与电影、戏剧在艺术形式以及思想表达方面的不同,并针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广泛讨论,这种讨论贯穿“名著改编热”的整个过程。客观来讲,这类讨论中不乏泛泛而谈的声音,但是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论述是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的角度出发,认真探讨了这种改编的实际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改编效果,这种讨论无疑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小说与话剧、电影之间关系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名著改编热”现象一方面体现出当时文艺实践活动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人们对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历史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而巴金《家》的改编恰好处于这一“改编热”的中间位置,它既承续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类改编中注重个体情感与家庭生活的因素,同时也体现出新的面貌,由此构成了其在“改编热”中的特殊性。因此,以《家》的改编为切入点来考察抗战时期的“名著改编热”不仅可以突破以往关于《家》的改编研究中拘囿于文本本身的研究模式,还可以勾连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名著改编”现象与社会时代之间的互动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改编所呈现出的审美价值取向的流变过程,可以为我们考察抗战时期小说与话剧、电影之间关系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