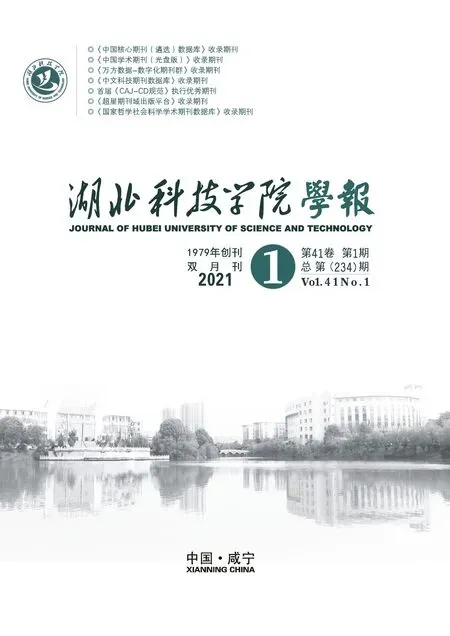农村教育及其发展的主体性问题
吴亚林
(湖北省农村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村教育或乡村教育到底指称什么?是“教育在农村”或者是“农村地方发生的教育”?可能两者都有。但这两者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要追问:农村教育概念蕴含着什么?农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到底怎样发展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这个概念有多重意谓:基于城市与农村历史分明的;基于城市与农村地域分隔的;基于城市与农村产业分工的;基于城市与农村政策分离的;基于城市与农村需求分别的;基于城市与农村发展目标分立的。农村教育这个概念似乎又蕴含着某种“同质性”和“同质化”的因素,虽然从历史发展来说,农村区别于城市,但从教育的旨趣来说,教育意味着同化、趋同性和一致性。远古教育是人类群居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教育与群体、集群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就是把集群的知识和智慧沿袭下来,推广开去,普及化成。
前现代社会,人类聚居,筑城建都,文明都是集中于人口密集的都市。历史和考古学已经证明,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也是教育的中心。西周社会乡遂制度把王城(京畿)以外的地方划分了“乡”和“野”,于是有了以“郊”为界的“乡”与“鄙”的区别。诸侯贵族通过“致邑立宗”的分封把文化带到了采邑和封地,这大约就是文化下乡。前现代社会,准确地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以农立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王城、都鄙、乡野之间的交流虽不平等,但绝对不是异质的。而且,农业和农村作为根基能够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提供养分,因为城乡享有共同的历史条件、自然气候、天文历法及共同的祖先和神灵。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学、太学、国子学与地方乡学和民间社学、私学虽规格不同,体制不通,但目的一致。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生产力的全面落后,导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反动与自我更新,西化与现代化就是表征,也导致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基本否定。现代化所需要的科技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取向。农村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是要改造的对象,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对立之中交杂着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对立。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似乎是现代与传统、工业和农业、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两极的代表,甚至从对立演变为异质性的反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或许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拯救乡村的悲歌与绝唱。在各种思想影响下,尤其的民粹思想的误导,乡村教育给了我们某种道德与理想的幻觉,情感与精神的慰藉。
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的同时,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是国家的贡献者和牺牲者,城乡二元分隔的社会政策建构了新的社会结构矛盾,并影响至今。毛泽东主席认为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国情,在依靠国家发展教育的前提下,还要发动群众来办教育,并明确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毛泽东“两条腿走路”教育发展思想的完整表述,体现在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的一元化设计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农村教育事实上成为弱化和落后的城市教育。简单地说,新中国的教育政策使得农村教育获得了鲜明的主体性和特点:农民、农业、农村的教育,弱化和落后的教育。这也是中国教育体现在农村的特质,这也是我们理解和界定农村教育的一个现实前提。人们把农村教育往往理解为“自觉”和“主动”地脱离农业农村农民的教育,“读不读得出来”和“走不走得出去”成为检验农村教育是否发达的标准。可以说,过去我们都是从改造乡村、支援乡村的角度去看农村教育的,是从国家化、城市化、工业化角度去看农村教育的,而国家化、城市化、工业化恰恰“化约”了乡村这一基本元素,“化约”了农村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情态及传统的人文价值观。而且,现代化、全球化、技术化、标准化消弭教育的异质性,削弱了农村教育的主体性,在一个逐渐同化的序列之中,农村教育是最后的环节,农村教育成为没有特质没有根基的教育。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一系列举措逐步推出,农村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农村教育也经历了一个“迷失期”和“阵痛期”,也在逐渐丧失主体性。但是,这或许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生机,因为城乡融合、农业农村现代化解构了农村教育原有的单一主体性问题,农村教育及其发展需要赋予新的主体性。
农村离不开教育,乡村振兴需要教育的参与,农村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动力之一。农村教育要建构新主体,农村教育应该是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特质的。我们的确需要对农村教育进行“概念重建”,彰显基于农村自然、社会与农村人的农村教育特质。农村教育不应该是落后的和弱化的城市教育,农村教育既包含农村基础教育,又包含促进农村劳动力提升的继续教育,还包含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会教育。农村教育在结构体系上,是包括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广义教育。农村教育应该有其内涵特质和价值取向,但是,农村教育的内涵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教育了。
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今的农村教育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破解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重建农村教育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三农发展的主题,农村教育要坚持农业,农村,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农村教育还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格局以及整个生态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已逾越了城市与农村二元对立的框架,农村教育的主体性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全体国民的教育,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宏观发展体系中的教育。所以农村教育不仅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教育,其主体应该是国家和社会。
农村教育发展是国家教育战略发展的一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农村教育发展关键举措。当前农村教育还很薄弱,农村孩子还不能完全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农村学校和农村教师期盼有更好的发展,需要构建一种动力学模式来推动农村教育发展:政府主导、政策推动;社会参与、产业促动;公共治理、三农互动。政府主导、政策推动是指要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用力;社会参与、产业促动是指发动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力量,支持农村教育发展;公共治理、三农互动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要在国家社会的总体发展中切实发挥主体作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