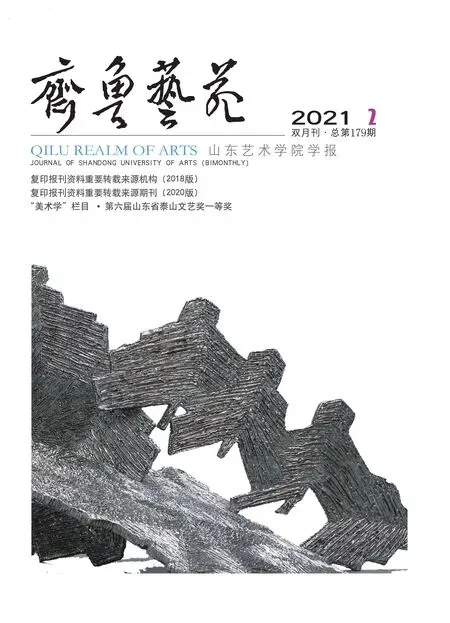由艺术终结到实践理性
——借鉴康德与黑格尔的观点引发的思考
朱尽晖,杜 德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博伊斯用肥肉和毛毡创作艺术品,汉娜·霍克用合成照片的技法来反对传统,某个艺术家可能用一段录像记录了他无所事事的一天,这也可以是艺术品。艺术史似乎已不再受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从一系列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运动——构成主义、至上主义、未来主义、达达、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来看,每一个运动都有自己的宣言,人们无法感受艺术明确的发展方向,能觉察到的只是愈来愈多地与艺术无关的东西——具象的,抽象的,实体存在的,精神内在的等等都被牵扯联系进了艺术中,艺术在近代囊括了足够多地“细枝末节”。如果说我们观看这些“细枝末节”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当前的时代,那么现今,我们面临的历史鸿沟或许从未如此深的横亘在我们的生活中。鸿沟一侧出现的作品是活生生的,直接表现我们生活的艺术作品,另一侧的作品则是过去的,理解这些作品需要特殊的视角,需要特别下功夫。尽管如此我们在阐释的时候也总是面临误读和曲解的风险。在此,我们暂且放下过去的那一侧,就表现我们生活的这一侧而言,它代表了众多的成就,代表了艺术多极化等等,但也同时带来了一些无法被忽视的问题。如今,没有人能为当前存在的艺术带来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价值标准。因为我们是“当局者”。观赏者针对当代艺术的哪一个论断是正确的,这个回答自然要留给下一个时代。
对于那些无法被忽视的问题,其中被聚焦探讨的一个即是我们对某一件艺术品展现出的朝圣般的态度。这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判断还是受到外界强加于我们之上的判断准则影响呢?当面对英国国家美术馆对达芬奇《岩间圣母》所作的长达十四页的条目时,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信息只涉及委托作画人,法律争端,收藏者等关于画作辗转纠纷的旁支信息,这些都力图在证明这副毫无疑问是达芬奇的真迹。约翰·伯格认为国家美术馆的条目正是为了这些因为其是真迹,所以觉得它是美的人而作的。这种感受与艺术家玄奥造作的文化完全吻合。然而这样围绕着艺术原作虚伪的虔诚常常把我们拖入失实的判断标准之中,试图掌控我们自我判断的意识。在此大环境下,逆来顺受并不是合理的办法,我们依然有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以往的方式,从而正确理解所处时代的“艺术”和“观看”。在近代以来,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大概是争论不休的最热门“终结”言说之一了,但是对于此观点的不同角度探讨又往往会给艺术带来新的价值支撑理由,尤其是从当前的时代出发思考时,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发。而与艺术品相伴而行的“观看”这一话题上,康德在其第二批判中也给了我们一些可以引用阐发的观点。在我们以当代为蓝本的视野下,“艺术”与“观看”二者相结合的越发趋向紧密,互为表里依托的共同划分出了当今审美文化生活的行动空间。
一、当代之“代”
在我们谈及“当代艺术”的时候,首先会放眼于这个被命名于“当代艺术”的名词,我们既然用这个名词去解释了这个世界在特定时代所独有的文化语言,那么按照约翰·伯格的观点“我们用语言解释那个世界,可是语言并不能抹杀我们处于该世界包围之中这一事实。”[1]看来先返回到把我们包围的这个时代再去查找一些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线索是势在必行的了。这股文化力量所产生的时代是我们首先要去理解的。尽管我们对于“当代艺术”有着种种非议,“当代艺术”经常一些失于控制野蛮无度的动作也确实让人起疑,有时也不免让人讨厌,甚至于“当代艺术”这个名称也多半值得考究,试问哪个时代没有“当代”的艺术呢?[2]但是每当想起泰特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或是威尼斯双年展某处聚满人的角落时,我们可以觉察到当代艺术都展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对空间及情感的统治力,这是以传统叙事为主线的艺术品所难以达到的。
尤其是通过大部分当代艺术品的话题性特征而论,其给予社会的反馈使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承认一点——这种经常失控野蛮,暴露出血腥无厘头的艺术是我们时代真实反映的产物(除却一些故作姿态的艺术形式和成果),这至少证明了我们没有把艺术和时代割裂开来。我们能从其中得到真实社会的反馈,我们是将自己置身于时代中去进行选择和创造。由此可以得知“当代艺术”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阶级基础上而来的。这是一件看似理所应当,实则很不容易的事情。例如我们无法想象在历史进程的一个时段中,所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艺术品只有唯美的宗教画,从这些画作中可以感到神圣,安静与平和。彷佛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平静且波澜不惊,那个时代的生活就是这样美好。但是实际上,在那时的社会中发生着无数残酷迫害异教徒的事件,这些恐怖的画面并没有被作为艺术题材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些确实发生的悲惨事件似乎都被散发着圣洁气息的艺术品抹去了。因而,不可否认艺术家立足于真实的社会环境之上进行创作之时,其所具备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会进一步加强艺术品和时代的联系。
二、当代的价值
当艺术品与时代处在如此紧密的联系中时,再回顾“当代艺术”这个名词,探究其所具有的价值时,就不免联想到黑格尔的一个观点上,即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离“理念”最远的,将艺术当作“绝对精神”之运动的低级阶段——“艺术不完蛋,精神如何进步?”[3]黑格尔将分为象征性、古典型和浪漫型的艺术美学含义予以定论,他认为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艺术形式已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必须的崇高地位了,被大众广为接受的那种美学特征或许将走向终结。言及此处,这种恰巧被斥责为无度的“当代艺术”或许正好反驳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在“绝对精神”中,以艺术,宗教,哲学为解释其的语言。宗教和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无论如何都高于艺术的直观性,黑格尔认为美的艺术始终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解放本身,真正的解放在思想的要素里。”(在其《美学》中,黑格尔将艺术论及为“从事于真实的事物”)这同时也呼应了另一种“终结”言说,即丹托的艺术“终结”于观念的论点。丹托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实践所提出的“终结论”和黑格尔立足于观念哲学所提出的“终结”一词的含义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此处,我认为与其不断辨别丹托如何以不同的立场与黑格尔的部分观点产生差异,毋宁关注其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尽管立场不一,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强调了观念本身的重要性。
黑格尔恐怕没有想到,在多年后任何的现代艺术,任何的后浪漫派艺术都或多或少属于即兴创作,都有赖于这样一种思想,即感觉,情绪,灵感比艺术理智,批判趣味以及事先做好的艺术更有利于创作,更贴近于生活。[4]我们如今都十分赞同且以此为创作的信仰之一,那就是艺术品最宝贵的元素是突如其来的想法,是意外的收获和神赐的灵感,而我们仅仅需要遵从于此就是我们最明智的一个举动。陆兴华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时说到“观念—理念,为何就不能成为艺术或者艺术的要素呢?”[5]因而在“观念”“理念”成为了艺术的决定性要素后,黑格尔针对艺术所言的观点“认为艺术是属于现实的,而现实脱不开现存的范畴,所有现存的事物最终只会走向灭亡。”或许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了,因为当代艺术往往甚至连形式都完全抛却掉了,又何谈“现实”呢?当这种观念至上的艺术取代了黑格尔艺术三段论中的最后一段浪漫主义艺术后,艺术就凭借此取得了合理的地位,无论在解释主观内在和客观外在上都不弱于任何形式语言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例如肯尼斯·克拉克将在思想上找寻自然的卢梭和在画面上找寻自然的透纳论及为一类人。肯尼斯·克拉克认为他们追寻的是同一种自然,在此处,肯尼斯·克拉克将卢梭的思想与透纳的画面放到了同等的地位。卢梭在阵阵海浪声中说出了“我认识到我们的存在不过是通过感觉而知觉到的时刻的连续。”即——我思故我在。同时,当我们将目光转换到透纳的画面上时,我们能看到的是透纳从真实经验出发而得来的颜色。透纳用他的视知觉来发现真实。“我感觉故我在。”肯尼斯·克拉克认为“透纳的画没有明确的外形而是纯粹的色彩,因而更加生动的传达了对自然整体的真实感觉。”[6]透纳只是其所处时代的一个特例,其创作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自此之后,艺术创作方式和表现方式的变更,在公众心中形成了一个共识便是要使得其更加能传达思想以及划定感性空间。雅克·朗西埃也有着“当代艺术所能调动的感性领域是十分广阔的”这一观点。因此回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在重新考虑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时,得以站在时代的视角上稍窥当代艺术的价值,即宣告了在“观念”与“理念”主导的当代艺术中,其不再是“绝对精神”的最初阶段了,艺术以感性的方式摆脱了低级的运动阶段。当代艺术中看似偶尔不那么合理的方式反而帮助艺术从现实中脱身出来,获得了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三、观看的自由
当观念和理念变为主宰艺术的要素时,相应而存在的主观行为“观看”也自然会发生改变,事实上在当代,“观看”这一过程的变更对主体意志来说更加具有价值但是也更容易遭受蒙蔽。当回到历史中寻找这一主观观念变更的历史,会发现18世纪正是这一过程产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由于理性的膜拜将启蒙的思想逐渐蔓延到了大陆的各个角落,所以在谈论观看审美的话题上,前所未有的出现了多种争议以及不同角度的解读,但是不论是皮勒的观点赋予门外汉审美的权利,或是休谟的观点强调品味判断的主观性。似乎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在决定品味标准的时候力求让观者摆脱影响自我判断力的成见。这也是康德所追求的。针对于此,艾柯认为“在18世纪美学中,大众的品味更注重于主观层面,而康德所著的《判断力批判》正是统领此趋势的高峰之作。”[7]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审美经验的基础在于从美的静观中获得的不涉利害的快感。在不建立在观看主体的任何爱好上,我们对其的判断是完全自由的,观者不能以任何属于其本身的爱好来解释获得的快感。[8]其中,康德所言的“完全自由的判断”除了要求不涉利害以及不建立在主体爱好上之外,是否真的就完全自由呢?还是说另有隐含的限制?
从自由的判断出发,在艺术的自由意识发展到更高峰的时候,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作为最“自由”的艺术反叛精神,其曾风靡了整个欧洲,这是前所未有的“艺术独立宣言”了。但是这里面充满了尖锐的对立性。艺术是自身的目标和目的还是说我们只是以此作为达成某一个目的的手段呢?阿诺尔德·豪泽尔给出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把艺术品比作一扇窗户,人们可以从这扇窗户观察生活而不必考察窗户玻璃的结构、透明性,颜色。按照这一类比,艺术品就像是单纯的观察工具和认识工具,就是说,像一扇玻璃或者一副眼镜,它本身无关紧要,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过,人们也可以把目光对准玻璃的结构而无需注意为自身的缘故而存在的形式产物,将其理解为一个意义关联。”[9]阿诺尔德·豪泽尔这段话看似将自由的决定权给予了我们。但是实际上,朗西埃揭示了阿诺尔德·豪泽尔的言下之意“艺术品最难克服的悖论,就在于它既像是独立存在又不像是独立存在,在于它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受历史和社会因素制约的公众群体,但同时又让人觉得它根本不理会公众的存在。”[10]因此,这种唯美主义观点忽略了艺术本身就必须处在社会劳动分工之中才能得以存在,也侧面说明了康德的“完全自由”也处在相对之中,自由的主体和静观的对象依然是社会分工的一份子。
在康德的第一批判中,其“先验统一”论似乎也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即“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属于一个意识”。在汤姆森·加勒特阐述康德这一观点时他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当你眺望车窗外时,你看见的所有景象都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都是你的经验。这种形式统一就是使自我意识成为可能的东西。”[11]而既然先验的意识属于所有的自由存在,那么个人自然是无法从先验统一中脱离出来的,汤姆森·加勒特的解释也进一步证实了康德所言的“完全的自由”并不是真的“完全”。
四、自由之内的正确观看
正因为“观看”本身存在着自由的界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其在合理的范围内更好的回归到本身的含义上。康德在第三批判中认为“当我们对一个对象的知觉使得我们觉得有理由把自然看作是可理解的,那么这个对象就是美的。而美使我们把自然看成本体以现象方式的展示。”[12]康德正是通过这句话使得现象具有了美的内容,也使得观看回归到本身的含义上。由此而论,当我们有了判断美的结论时,势必是建立在“我们觉得有理由”这一基础之上的。通过康德的这段观点来看,如果某人做出了与大部分公众所不同的判断,这个判断如果是出自自身理解的,那么是可以被承认的。也是因为这样,观看的艺术品才是我们自主意识做出的选择,是处在先验统一中的客观存在。这一建立在“自我理解”上的判断意识,在康德的第二批判中被称呼为自由选择的实践理性。于此,具备自我理解的判断力,才能在自由划定的感性空间内,合理的做出理性的自由意志选择。
现代社会的观看方式,审美逻辑的运作过程,都让每个人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观看”才是正确的。“当代艺术”要聚集的核心在每一个有权威的人眼里都不尽相同,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当代艺术品的意义也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一极是内在的,与生活与作品之外的现实绝缘的存在,(然而这股内在也来源于生活)。一极是由生活、社会、时间决定的功能。从直接的观看审美体验来看,自我和自我满足是艺术品的本质,由此艺术家往往追求将我们带入一个易受感染的地带展现其力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家说什么就更有说服力了,但是最伟大的艺术品往往在此过程之后会指向一个其艺术品之外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多重的,多样的,无法由“当局者”给出确切答案的。例如在阿诺尔德·豪泽尔看来是“如何让人类的存在获得意义”,在雅克·朗西埃看来又是“如何重新构成我们的政治形势和机构。”
因而,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自身的合理判断之上。在现代,通过具备这股实践理性的“观看”之法,可以得以让我们踏足符合自身判断标准的感性领域,以规避掉迷惑判断的陷阱。这个陷阱在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中是这样阐述的:“今天,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同一目的又在得逞,它使用的手段是把判断事物吸引人与否的虚假标准强加于人。”[13]这一点长久的存在于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上,不过在近代就如约翰·伯格所言,其又在得逞了,并且越发严重。它成为了误导我们独立性的最大敌人。这股误导我们的力量在格奥尔格·奇美尔针对时尚的研究中被谈及,他发现上层阶级抛却的时尚正是被底层社会所采用的,这样的行为表现了上层阶级和底层社会地位不同。上层阶级热衷于通过创造来表达自我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很快会被中产阶级模仿,被模仿后上层阶级又会找寻新的符号来代表自我优势从而区分阶级。[14]“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光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这句话恰到好处的概括了这一趋势。正因为此,在如今的流行趋势中,某些判断标准的真实性值得考究,其真正的目的或许别有用心。我们现今依然容易陷落在由经济制导的判断陷阱中。雅克·朗西埃认为:“总有一批人企图制造一个固定的空间,这是我们需要避开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去制造一种异质以对抗,以宣扬,我们要证明:你们代表的不是我们。”[15]很显然,这些妄图制导我们的客观力量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本来试图通过自我的行为去模糊阶级的存在,却又恰好落在了设置好的陷阱中。因而,要时刻提醒自己去根本地了解艺术的形式是如何通过某种意识将我们置于某个艺术品的感性领域中,又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引起共鸣的感性领域去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分割了时间和空间,这种分割定义了我们今后该如何走,往前或往后,怎样在中间,在里间又如何到外面,艺术成为了自由的排练场。这一点显然是某种资本操纵的“共识”领域所抵触的。合理的判断标准是建立在正确认知所处时代的“艺术”与“观看”之上的,在偏离了正确轨道之时,也不应忘了拿好自己的“武器”在当代艺术划定的感性空间内尝试着学会自由的“造反”。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