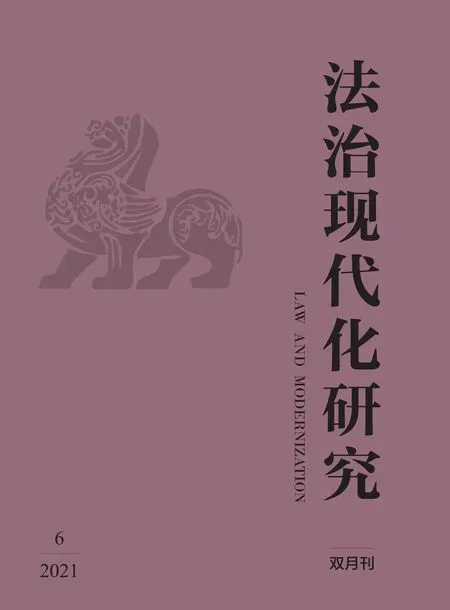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股份制改革
刘云生 孙 林
2018年,自然资源部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下称2018“一号文件”)精神,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专题调研。随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专题调研组分赴上海(松江)、安徽(蚌埠)、湖北(宜城)、四川(泸县、广安)、陕西(高陵)、宁夏(平罗)等地进行深入调研、访谈。就决策层面而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仅被纳入议事日程,且大有推广、普及之势。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之名实关系如何界定;“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下文简称“三变”)措施如何落实;法权困境如何突破?唯有厘清上述核心理论问题,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对象范围、路径选择等问题。
一、 文本解读与对象限定
农村宅基地是否适合“三权分置”,能否进行股份制改革,如何进行改革?学界论者寥寥,偶或论及,亦多持审慎态度,甚或有过激反对者。如针对农地股份制改革政策导向,有学者指出,集体经营性资产指向不明,“对集体资产的股改,就是当下‘子孙’对‘祖产’实施私分,就是散伙,就是刨农村的根基!”(1)参见李昌平:《对集体经营性资产实施股份制改造应该暂停》, 载“甘肃白银会宁县河畔镇中滩村网”,http://134089.cnlhzb.com/article885409,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1日。因为此类股份制改革最终可能导致私有化,会败掉集体几十年的资产积累。同时,现有的成员权足以抵充股份制改革之制度效能,无须蹈险履危,再翻新曲。
或避而不谈,或审慎保守,或过激反对,是目前学界对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三种常态反应。探本求源,无非是基于农村宅基地之制度功能、价值定位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特色,不能也不可能充分推行市场化改革。但在国家决策层面,随着2018“一号文件”的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变”措施渐次被导入农村宅基地改革各大场域。
(一) “三权”之名实界定
对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2018“一号文件”的具体表述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征诸文本语境,农村宅基地所涉三权分别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之名实问题自无疑义,但后续两种权利则需进一步厘定。
所谓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系指农户以户籍为标准,以集体成员身份为依据获取农村宅基地的主体资格和土地利用权力。因未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也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在界定名实关系时需特别留意两个问题:一是宅基地法权以“农户”为主体,但“农户”之“农”,很多已有名无实。众多乡村“空心化”,部分村民已然定居城市(镇),甚或城郊乡村已然进行了“村改居”,但仍然以农户身份持续占有宅基地,闲置颓败;二是“农户”之“户”多有泛滥之虞。诸多地区,通过分户、收养、吸收荣誉村民等形式规避法律,肆意扩张宅基地,圈占后或闲置囤放,或坐等拆迁,或违规超面积建造。如石家庄鹿泉市某村按“荣誉村民”身份获批宅基地者即达36人之多,每人为一户,共获批11亩,而实际占地20.4亩。(2)参见李增勇:《“荣誉村民”身份获批宅基地》,载“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08-01-16/01591475140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1日。针对上述乱象,有学者曾主张在宅基地的申请取得上,不能再抽象秉持“一户一宅”原则,而应以分户条件、宅基地面积和可建筑容积率为标准。(3)参见韩松:《论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至于宅基地使用权,看似没有问题,但仍然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风险。就法权逻辑设定与权利体系构造而论,宅基地使用权系民法典物权编明确界定之用益物权,但在进行权能界分和体系归纳时,宅基地使用权既非传统意义上之地上权,亦难与用益物权相契合,且无法涵盖现有农村宅基地权所涉一切权利。易言之,“宅基地使用权”并不能涵摄用益物权之所有权能,亦不能包蕴现实宅基地权利之实存权利。究其实,因为与成员身份和不动产建筑血脉相连,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使用权”,至少但不限于包含如下三大系列权利:一是现有法律保护的农户实际占有宅基地之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二是农户修造于宅基地之上的不动产建筑物、附属物之所有权,三是虽未实际占有但基于集体成员权而产生的集体宅基地收益分配权等权利。
(二) 农村宅基地改革之文本语境
细加寻绎,2018年“一号文件”的文本语境应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解读。
1. 行为动因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真正目的是激活并实现庞大的农村宅基地的资产效益,优化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体而微,进行“三权分置”的目的有三。第一,完善农村建设用地政策,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文件特别指出,目前宅基地法律和政策已然无力调控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必须改弦更张,推动农村宅基地效益增长。据澎湃新闻报道:从2015年试点开始,到2018年初,浙江省义乌市可盘活的宅基地资产即可达到1000亿元,足以为当地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新动能。(4)参见葛熔金:《一千亿元:义乌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盘活农民沉睡的资产》,载“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5445,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1日。第二,落实宅基地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土地市场效益。2018“一号文件”之所以被民间普遍解读为集体土地“上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该文件以宅基地为突破口,放权赋能,集体成为真正的有限市场的土地供给者,可以实现宅基地市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居住条件。第三,探索改革新渠道,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落实集体宅基地所有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还是推进“三变”改革模式,股份制改革都不失为一种最优化选择。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不仅可以实现体制变革,还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振兴乡村提供可靠而强大的动力和推力。
由是论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积弊痼疾,实现土地效益增长,增进农民福利,推动乡村现代化步伐。就历史经验而论,此种选择可谓切中肯綮,找准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按照斯波义信的理论,土地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核心。斯波义信借鉴新经济史学理论,从纵向、横向时空比较了宋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与走势,特别指出,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利用制度。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虽有影响,但并非决定性作用。一定程度而论,上述各大要素都是为土地利用制度所吸引,最终趋于良性集聚。(5)参见[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9页。
2. 措施与路径
文件对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设计的用语是“探索”,此点足以表明决策高层对农村宅基地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审慎态度,同时也为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多元化试点空间和改革路径选择。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使用权改革措施的用语则是“放活”。该用语无疑从逻辑上承认了一个事实:此前法律与政策囿于身份性、内部性、保障性等目标定位,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使用权管得过死。
通过“探索”与“放活”,除了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不得转让外,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可以实体化,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使用权均可以转换为商品,实现其市场价值,最终凸显土地的资源属性。土地权利的外部化促进了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住宅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流转,城市工商资本亦可持续流入乡村宅基地市场。此种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不仅深度契合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需求,也满足了农民土地价值实现的多元需求。囿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此前的农户建房只能用于自我居住,而不能用于工商经营。但根据有关学者的调研,过半的农民都希望宅基地除了满足住房所需外,还应当允准农民进行适度的非农化、经营性使用。(6)陈小君教授等人通过对全国十个省的调研数据分析,证明在四川(51.7%)、黑龙江(54.14%)、湖北(55.25%)和湖南(54.64%)四省的农户,一半以上希望宅基地能够满足住房之外的其他需求,主要满足小商店、小饭馆或小规模养殖、小作坊、修理店等土地需求。参见“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10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
3. 前提与底线
与保守的学者不同,较为激进的学者认为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土地“最落后的制度安排”,主张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7)参见席志刚:《刘守英:深化土改意在全面激活乡村》,载“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oj/2018/02-02/843974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1日。实际上,物权法制定之初,学界主张农村宅基地市场化的学者亦复不少。如梁慧星教授认为,宅基地使用可以转让,但因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无偿划拨的基地使用权,故有偿转让时土地使用权人应当交纳出让金。(8)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1页。陈小君教授认为,应当依法确立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肯定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认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抵押、出租、入股等流转方式的合法性,赋予其法律效力。(9)参见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高富平教授主张应当向农民开放其宅基地商业化利用途径和规则,禁止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出资以及其他商业化利用将严重限制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10)参见高富平:《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我国不动产物权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页。
但揆诸历史与国情,农村宅基地不可能全盘市场化,只能走有限市场化道路。高圣平教授审慎地提出建议:在农村宅基地的保障性与市场化之间,必须首先满足保障功能,才能论及宅基地的财产效益充分实现问题。(11)参见高圣平:《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法律逻辑》,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此种立场正是2018“一号文件”的立场,也决定了农村宅基地改革的大前提和底线:保障功能优先,适度推进有限公开市场化。所谓农村宅基地“有限公开市场”,系指宅基地市场化改革必须受到如下约束或限制:不得背离公有制应有之公平正义立场,不得损害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不得危及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不得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立法原则,不得违法违规超规模、大面积占用宅基地。
(三) 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对象限定
基于上述文本语境,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对象与范围在逻辑上和价值上必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户保障型宅基地。此类宅基地具有身份性,保障性,不宜亦不可能全盘市场化,仅能就宅基地使用权及不动产进行有限商品化,股份制改革空间较小。另一类是资产型宅基地。这是未来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重点区域,也是本文的重心所在,细加区分,该类宅基地又包括实体型与资产收益型两类。
第一类是实体型宅基地。按其来源,可归结为如下几类:一是集体所有且预留的未利用、未开发的宅基地。二是农户退还的宅基地。农户由于户口迁徙、置换、闲置等原因将原宅基地无偿或有偿退还集体。2016年,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国土资发〔2016〕123号),明确要求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结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要求,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而按照2018“一号文件”精神,即便进城落户的农民,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并不必然消灭且须积极保护。集体可引导此类农户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三是集体收回的宅基地。主要是对严重违规违法占用宅基地的不动产建筑进行拆除后回收的宅基地。
第二类是资产收益型。具体包括:① 留居村民以权利入股。经过优化布局、整体改造后,留居农村的农户以自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的不动产使用权入股,交由集体或其他经营主体进行市场化经营。此类属于农民安居乐业后最大限度实现土地、住宅市场价值的举措,能够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互动共荣,适用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领域。② 离乡农户投资入股。离乡农户以宅基地使用权或宅基地补偿款、分配收益等投资入股。此类仅限于虽然离乡但仍保留农村户口且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如义乌市即采取如下模式:鼓励离乡农户将腾退的宅基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整治后以“集地券”的方式在市域范围内统筹使用。“集地券”有两大优势:一是突破了聚居的地域限制,农户可进入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城乡新社区集聚;二是农户可将“集地券”作为股权于特定区域进行投资和交易,立体化实现农村宅基地市场价值。③ 宅基地使用费。即对轻微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按照一定标准收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费。义乌市针对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农户,土地违法面积在36平方米以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参照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按20年一次性收取有偿使用费。经统计,此举共计清理128个村,累计34 592户农户交纳有偿使用费9.5亿元,占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④ 因连片开发、集体安置、留地安置而产生的宅基地增值部分,农户既可以实际占有、居住,亦可选择入股、出租等方式进行处分。⑤ 因土地征收由集体享有的宅基地补偿款,于村民大会议决后,既可以领取现金,亦可以配股投资。
第二种类型中,无论是实体型的,抑或是资产型的;无论是集体所有的,还是农户享有的;无论是资本型,还是权利型的,均可作为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借此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居住品质,最终实现城乡互动,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速率。
二、 宅基地股份制改革:困境与突破
宪法第10条第2款表述宅基地所有权时,立法用语用的是“也属于”。一个“也”字显露了宅基地的敏感度和立法者的谦抑性。因为宅基地关涉农民的生存权、住房保障权,如果不做如此柔性的表述,可能会诱发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甚至政治风险。也正因为如此,原物权法第十三章虽然冠名为“宅基地使用权”,但屈指数来,整整一章只有四条。因为无法细化,也不能细化。宪法的柔性表达和原物权法的极简设计都说明了国家对宅基地保有极为审慎的态度和博弈心态,但由此必然引致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困境。此类困境于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层面问题较容易解决,但在使用权层面则较为复杂。
(一) 法权困境
宅基地是公有制主导下城乡二元结构中维护农户住宅保障权的特别土地制度设计,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革必然遭遇多重法权困境。
1. 功能具有社会保障性,难以作为资产进行投资或入股
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如果农户实体占有宅基地,住宅亦仅用于居住,其所能设定抵押融资的仅为不动产建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内部性、保障性,且基础权利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一般难以作为资产投资、入股。此点无疑从价值和逻辑两方面阻断了股份制改革的通道。根据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5款的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换言之,法律并不禁止出让宅基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却可能引致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消灭,此举无异釜底抽薪。探究其立法本意,无非是防范农民凭借宅基地的无偿性、福利性牟利并借此保护土地资源、强化土地管理,但因噎废食,从立法上阻断了农民移转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
但法律有禁条,农民有对策。征诸民间实践,并不乏借转移房产之名出让宅基地之实的事例,且均可通过生存抗争、权力寻租、关系网络重新获批宅基地。(12)据陈小君教授等人对中国十个省的调研,有接近30%的农民认为出让宅基地后可以重新申请宅基地。参见前引⑥,陈小君等文。此种显性违法也间接说明:只要存在农村宅基地的市场需求,就会有突破法禁的理由和路径。唯有“变法”,才能适应现实需求,减少、避免违法现象的发生。
2. 主体为“户”,谈判成本高,法律风险大
目前法权认定的宅基地权是“一户一宅”,此点导致股份制改革谈判成本和风险双向增大。宅基地以户为单位,农户内部属于共同共有关系,非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可能构成无权处分。即便农户阖家同意参加股改,股份配置是按人头配股,还是按户配股;如果按户配股,农户内部股份又如何配置;股权如何行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3)参见吕翾:《宅基地使用权的双重属性矛盾亟须化解》,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1月13日。
3. 行政审批严格,转让受限
依照现行立法,宅基地权需农户申请,村社同意,还得经行政部门审批。此点决定了宅基地权入市、入股的法权障碍:集体作为所有权人是否同意?行政部门是否批准?征诸各地立法,对宅基地权都施行严格的身份性、内部性控制。如《浙江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农村村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个人只有使用权,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转让、出租。”
4. 合法(规)与违法(规)
以上障碍属于制度性障碍,可通过尊重民间智慧、认可民间习惯、矫正制度缺失等方式克服。毕竟,什么鞋合脚,只有穿鞋者(农民)自己最清楚。但即便克服上述障碍,目前农村宅基地权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合法、合规的宅基地权进行股份制改革自无疑义,但有相当数量的宅基地及其上的不动产建筑有违法、违规之嫌。此类权利是否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如果一体对待,无疑会刺激、滋长“法不责众”“违法趁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等消极法律认知,既削弱成文法权威,又背离土地资源公平分配的正义法则,还可能危及乡村土地生态均衡。
5. 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
对宅基地权进行股份制改革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我国奉行“房地一体”原则,但在实践中,该一原则又有两种模式:一类称之为“房随地走”,凡是土地被征收,其上的不动产建筑物也一同消灭,此点适用于农村土地征收,推行多年,除了征收补偿可能出现争议,并无其他障碍。另一类是“地随房走”,针对农村宅基地却难以实施。如果农户将房屋出卖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买受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殆无疑义,但能否遵循“地随房走”规则取得宅基地权?不行。因为宅基地权的身份性、保障性、内部性决定了宅基地权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转让。
(二) 功能替代与转换困境
如何在农村宅基地领域推动“三变”?本文认为,除了突破上述法权困境,还必须实现宅基地保障性、身份性两大功能的替代和转换。根据民间实践,一般有以下三种类型可资参酌。
1. 有偿退出再入股
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以宅基地使用权补偿金作为货币资本入股,或者将补偿金折股。此点可以化解诸多难题,但仅限于户籍尚在农村且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者,详见前述。
2. 集体收回后入股
对于长期闲置的宅基地,集体有权进行补偿后收回,纳入集体经营型用地,集体进行股权配置后农户或农民作为权利人入股。农户如果愿意以补偿金或补偿费用折股,则参酌第一项。
3. 置换后折价入股
在农村居民区进行片区化改造后,农户原宅基地面积与现有面积有差距,则可将置换后多出的面积差部分折价入股。
上述任何一种方式,既可替代宅基地权的社会保障功能,还能有效实现其经济功能,且可有效回避各类法权风险。
(三) 无偿性与无期性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无偿性与无期性,如进行股份制改革,必然涉及两个问题。
1. 如何作价
宅基地使用权的对价缺席引致了该项权利入股计价上的困难。在缺乏统一、公开的市场定价机制情形下,如何作价?此点可以采取两个解决方案:一是适度参酌当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或补偿标准;二是由当事人多方协议,议定价格。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无偿性问题相对而言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涉及法权风险。
2. 期限如何界定
目前的法律、法规及各地的宅基地管理办法均未对宅基地使用权期限作出明确规定。此点也是民间、学界推定宅基地使用权“无期性”结论的主要依据。但严格意义上讲,无期性仅仅是一种产权永续性的理论假设。无论是宅基地灭失,还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死亡,抑或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放弃权利,集体调整、收回宅基地都可能导致宅基地权消灭。究其实,在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模式下,无期性带来的最大问题不是有期无期的理论纠结,而是在特定时段内股权如何定价的问题。此类问题亦不难解决。于股份合作社组织形式下,股东享有随时退社并回复宅基地、农房的自由,其定价可参酌入股协议约定;如未有约定,则参酌股权营运期间的标准价格定价。在土地股份公司模式下,股东的股权可以继承、转让,自可遵循公司章程及市值定价。
(四) 宅基地调整
宅基地承载着公益性、保障性功能,自然也就面临调整的问题。如《浙江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实施村镇规划进行旧村、旧城改造需要调整宅基地的,原宅基地使用人应当服从。”此点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必须服从宅基地调整所面临的后果,可能影响到股权的稳定。但如果参酌上述置换方案,加上适时进行股权、股额变动,此困境亦不难破解。
三、 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效能预判、前置条件与基本原则
(一) 宅基地股份制改革的组织张力和资产整合力
土地的资产属性与资源属性息息相关,在在相连。按照通说,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整体性、选择性特征,稀缺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与可流通性,整体性决定了土地的生态利用战略,选择性则决定了为实现土地最大效益而选择的土地制度设计与构造。就农村宅基地而言,最值得留意的是土地资源的可选择性。选择宅基地股份制改革,不仅可以强化乡村经济实体的组织张力,还可最大限度实现宅基地的资产整合力。易言之,宅基地股份制改革可实现如下积极效能。
1. 按照经营模式标准进行“规模+整合”选择
股份制作为一种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其手段就是通过权利的结合,实现有限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增进土地的效用。这种选择模式可以有效规整农用地,相较之下,此种选择更适合宅基地。由南而北,自东徂西,目前大量集体通过新建成片区住宅区,整合众多的宅基地资源作为建设用地,激活、盘活宅基地资产,发展当地经济。
2. 按照权利功能实现标准进行“可替代性”选择
依照国家目前的法律和政策,海量的小产权房难以“转正”,获得合法性认可和权利确证。基于单纯的资产属性,这些显属违法、非法资产,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甚至政策对其进行行政罚款、限期拆除或者强制拆除,极个别地方甚至以“没收”方式将“小产权房”收归公有。
但从资源属性而论,为了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可以采用另外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私权方式,补偿这些违法建筑的工料成本(含土地整治费用)和资本使用费,外加未来市场价值的一定份额,就可以将此类房屋转化成为农村居民区,置换出数量可观的宅基地资源。二是通过公权方式,政府通过赎买方式将该类建筑转化为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适房或廉租房。这样既解决了城市土地、住房的稀缺性困境,又有效承担了社会责任,还省去了大量的建设、管理成本,消弭潜在社会隐患。
第一类适用于偏远地区生态环境较好的度假房,第二类适用于城郊接合部土地资源紧张、房价居高不下的集体小产权房。
此外,还有一种替代方案,就是政府—集体—农户联动,对众多小产权房进行混合产权改造,由政府—集体—农户各占一定比例的股份,交由特定的经济实体进行合规性建造整改后进行市场化经营。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农户通过房屋置换、现金补偿或以房屋、货币入股进行资本化、证券化营运,集体则通过租金收益获取土地利益,然后在集体成员间按股分配、提取公用基金。该方案不仅可以整合闲散宅基地资源,还可巧妙矫正违法违章建筑所诱发的社会风险,更可实现宅基地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的完美对接和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利益衡平。此种替代方案可适用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14)参见刘云生、吴昭军:《偏倚性理论与“城中村”股份制改造》,载《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 按照供求互适关系标准进行“优先发展”选择
农村宅基地股份制改革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可以为当地优先发展何种特色产业提供产能支持和土地供给。特色产业不仅会集聚有利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还能够创造、拓展不可替代的市场资源,使当地经济保有竞争优势和引导力、影响力,最终立体化、优质化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带动各类要素市场的升级转型。
4. 按照生态、文化需求进行“绿色发展”选择
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集约化、现代化、组织化要求,在组织形式上更注重市场化的主体设定,以获取更高的产出。这类土地的股份制改革一般多采用商事法意义上的股份公司或农业发展公司等组织形式,不仅加快了土地的流转频率,扩大了土地利用规模,还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发掘、活化、传承具有历史价值的乡村文化资源。
(二) 集体宅基地所有权股份制改革的前提
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此前囿于原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63条,担负了解决农民居住权的政治、社会使命,理论上和逻辑上都不能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无论是法律规范层面,抑或是政策引导层面,集体宅基地所有权股份制改革均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政策层面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后的各类文件中,论者多多,兹不具论。法律层面的显性依据为民法典第268条,集体可依法以其所有的不动产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换言之,只要能找到解决农民居住权的替代方案,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同样可以步入市场,前述几类资产型宅基地及其收益权均可进行股份制改革。
鉴于宅基地的特殊功能定性和定位,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入股至少应当满足如下前提。一是必须确保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剥夺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不得限缩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因为公司亏损、破产危及农民的住房保障权和不动产所有权(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也不能以集体宅基地所有权抵押融资,当集体无力偿还债务导致集体之债权人强制实现抵押权而妨害农民的上述两项权利。二是土地功能必须转换。基于公有制的特别属性和宪法、民法典的特别保护,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只能转化为集体资产形态后才可以进行市场化流转,亦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入股,且不得危及或妨碍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三是必须保障农民对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享有的收益分配权。对于集体宅基地所有权入股之收益,集体组织成员依法享有成员权与分配权。根据上述三大前提,理论上宅基地所有权股份制改造似无异议。但在事实上,必须强调另一个前提:能够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宅基地所有权不能是农户实体占有、使用、收益的宅基地,只能为闲置、腾退、置换后羡余的宅基地;也只有该类宅基地才能实现功能转换,成为集体经营性资产。此点已详前述,不复具论。
此外,集体宅基地所有权股份制改革必须保留集体股。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继2015年试点后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转化为集体经营性资产并进行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强劲动力。按照该《意见》精神,集体宅基地所有权以集体经营性资产形式入股,必须将该类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此点看似没问题,但仔细考察,不难见出,该类改革具有很强的内部性:一是组织形式采取股份合作社或社区股份合作形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公司化股份制改革;二是股权设置以现有成员股为主,可以不设集体股;三是股权一旦配置、设定,不因人口增减而变动、调整。此种内部性最大限度保护了现有集体成员的成员权。以广州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天河区进行股份制探索,先规定了集体占股60%以上,不到两年,即明确取消“集体股”,全部量化为个人股,“生不增,死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有效地将身份性的成员权转换成为一种经济性的权利。(15)参见傅晨、杨钢、郭晓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广州市天河区社区股份合作制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 年第1期;陈暹秋、郑划:《广州社区集体经济引入股份制改造合作制做法及意义》,载《农村经营管理》2004 年第4期。但如果集体股缺位或淡出,集体资产公益性目的如何实现?窃以为,在宅基地股份制改革进程中,只要还没有进化到完全的城市化、城镇化水平,必须也应当保有集体股。
毋庸讳言,集体土地所有权不仅承载了发展农村经济的时代使命,在乡村振兴社会语境中还承载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功能或组织功能。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乡村管理人身份的集体所起到的进步作用自不待言。但不容否认,时至今日,集体社会角色及其功能发生扭曲:保护农民权利与剥夺农民权利交替有之,为国家服务与增加国家负担骈列而行。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正式权利被非正式运用,基层权力偏离公共利益轨迹,最终诱发乡村权力腐败,积弊丛生,势在难绾。其中,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包括同乡、血亲、姻亲、朋友、同学以及因某种特殊经历和生活情节而建立的各类联系,背离了集体设立之宗旨以及国家、政党所倡导之理想。(16)参见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随着国家威信日益下降,乡村精英渐次退避,村级恶棍恣意横行,更深层次加剧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紧张关系。(17)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会陷入杜赞奇所担心的历史恶性循环:国家因自身功能的弱化,国势衰败,财政短缺,制度松弛,最终难以控制来自乡村社会的抵制甚至反叛。(18)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弗里曼教授等更严峻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彻底消除传统社会的家长制、性别歧视等负面因素。传统的文化观念、亲戚与个人关系网、宗族等地方因素仍然构成农村权力的基础。如果缺乏集体自有、农民享有的公共财富,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力必然被削弱。(19)参见[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乡村治理如何脱困并走上法治化道路?确保必需的公共管理费用后进行有效的村民自治和市场化流通是其最佳通道。但该项费用既不能全盘希冀政府公共投入,亦不可能从农民手中征取或者如此前向农户摊派,只能依靠集体资产经营所得予以保障。此外,对于乡村各类公用事业所需资金,除政府有限的项目扶持和资金支持外,更多的只能由集体自身筹措。最后,集体宅基地股份收益保障“在场”(有宅基地)成员收益,殆无疑义;但更应该保障“缺席者”(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不享有宅基地)的权利。(20)参见刘云生:《统筹城乡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与模式设计》,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三)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股份制改造的方向
如前所述,对于农户实体占有、使用、收益的宅基地,首先应保障其居住功能,不宜强力推行一刀切式的股份制改革。但对闲置、腾退、置换的宅基地,其宅基地使用权与住宅、附属设施均可作价、折价入股。
(1) 闲置宅基地利用与开发。对于此类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有偿退出、集体收回、集体回购或者农户入股进行整理、改造、开发方式推行。
(2) 宅基地规模化经营。社区化、片区化、规模化的农村宅基地改造必然产生置换、新建、改建、拆建等环节,如果出现面积差额,就差额部分可进行股份制改革。
(3) 集体收回进行股改。集体将原宅基地核查面积后进行统一回收,进行股份制改革,要么按股分配,要么按股计价,对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收益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