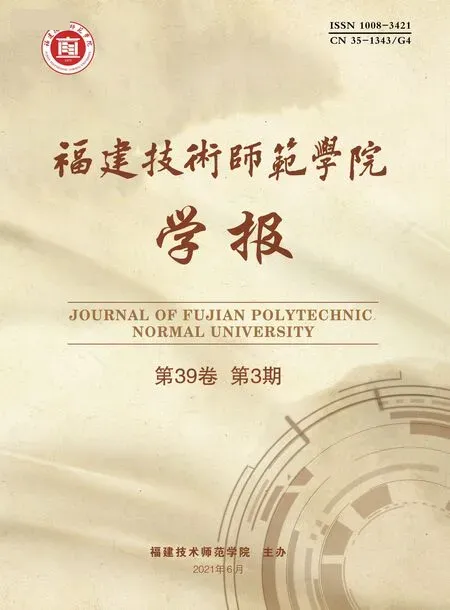疫情中的话语博弈
——新闻编译之再叙事
喻欢欢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在高度信息化和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体对一项政治议题的报道、传播深刻影响着国际国内公众对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进而影响议题本身的走势”[1]。新冠疫情在对世界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政要、智库、媒体的舆论战。面对复杂的国际态势,在报道中如何化解争端、争取国际支持和公众认可成为亟待考虑的问题。
一、翻译叙事学与新闻编译
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思维不同,英国翻译学家蒙娜·贝克(Mona Baker)的翻译叙事学跳出了翻译等值的视角,以社会学理论中的框架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学与交际学探讨如何从叙事角度建构语言,从而引导冲突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一理论对新闻翻译具有较高的阐释力。贝克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一种通过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人物事件再定位等策略实现的再叙事行为;通过再叙事,原叙事将会被增强或弱化或改变。新闻编译“既是信息传输,又是语言转换,同时也是文化沟通,发挥着整合、加工、传递乃至阐释的复合功能”[2]。在新闻编译中,译者既应遵循基本的翻译伦理、忠实于原文,又要理性取舍变通、适应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心理预期。文章以2020年3月至7月我国媒体对西方疫情相关新闻文本的编译来探讨在国际新闻翻译中如何进行话语博弈,通过再叙事策略实现叙事目的,为我国立场发声。
二、新闻编译再叙事之策略
(一)时间表达与视角转换:时空建构
时空建构是将文本植入另一时空语境,以使叙事文本更为凸显,并促使读者将其与当前影响他们生活的叙事建立关联[3]。在此次疫情相关国际新闻的编译中,时间建构主要体现为时间的明确化及日期表达方式的转化。《参考消息》5月8日“美媒文章:‘指责中国’成特朗普竞选战略”一文对比了2016年及2020年特朗普竞选策略,发现二者可谓如出一辙。在叙事过程中,由于原语读者对此事件熟悉度高,原文本在时间轴上略显模糊。转译后,读者群体发生改变,与之对应的叙事脉络亦随之变化。原文第三段第一句说“Candidate Trump declared that Mexico was ‘sending people that have lots of problems’ to the United States”,并未指明时间。由于译入语读者可能不熟悉美国总统竞选细节,译文“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称,墨西哥正向美国‘输出存在诸多问题的人员’”增译了时间“2016年”。在后一段谈及2020年竞选时,亦在原文“Trump and his Republican enablers are now offering the country what amounts to a remix of 2016”前加上了时间状语,译为“4年后,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提供了相当于2016年战略的调整版”。编译作为一种二次编码,其目的正是“通过语言的转化和文化的跨越将讯息编码为可被本国受众理解的新闻文本”[4]。此处时间的明确化填补了受众可能存在的知识盲区,保证了读者的理解度。另外,在日期表达上,英美读者惯用星期而中国读者对日期更为熟悉。因此在编译中,译者还常常转换日期表达方式,以迎合目的语受众阅读习惯。《参考消息》5月6日“特朗普不能将美抗疫失误归咎中国”中,将原文本“White House economic adviser Larry Kudlow said on Friday”译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1日说”,将星期表达“Friday”转译为日期表达“1日”,让中国读者能置身于他们熟悉的时空中,将叙事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减少阅读与理解障碍。
由于译者编译的一些国际新闻是从原语国家视角出发的,在译入我国后,通过转换视角来进行空间建构亦十分必要。例如,6月29日《环球时报》文章“疫情后中国的情况会好于美国”编译自美国雅虎财经网,原文从美国角度探讨疫情后世界局势,使用了第一人称表达如“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等。为适应目标语受众空间,译者对视角进行了转换,由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转译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解构了原叙事,使中国受众能将文本与自身所处空间语境进行联系,从而实现叙事的有效传递。
(二)选材、省略及添加: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
《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是中国大陆能直接刊载外电的报纸,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外媒体对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疫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等问题各执己见,其中既有在内容及措辞上支持我国的正面报道,亦有掺杂正负态度的中立文章,还有居心叵测地反对我国的负面新闻。在有大量海外新闻供择取的情况下,选择哪些新闻进行编译报道是译者需考虑的首要问题。除选取与中国相关的客观报道外,译者在选材时还应以“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改善中国形象”为宗旨[5]。纵观《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对此次疫情相关国际报道的选材,可发现明显的倾向性,即更偏向于选择在观点、语气上对我国持中立或正面友好态度的报道,而摒弃对我国有所误解的文章。例如《参考消息》7月14日刊载的“澳前总理陆克文称:美糟糕表现令中国地位增强”乐观预估疫情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7月10日头版的“美媒认为:中国没有制造病毒攻击他国”回击国际社会一些不怀好意之人对我国的无端猜测和无理指责,《环球时报》5月19日的“英媒:争取中国,而不是对其妖魔化”呼吁西方国家与中国理性相处、加强合作。这些选文均借外媒之口表达了鲜明的中国立场。
对外媒报道的选择性转载亦常体现为翻译过程中对原报道的叙事重构。上文所及之选材乃译前叙事选择,而蒙娜·贝克所言之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则更强调译中叙事建构,即“发生在译文内部的选择性采用”、文本内部的省略和添加[6]。新闻编译中的选择性采用和排斥能反映译者对某一叙事的赞同或反对。省略是时政新闻编译中的常用策略,有时译者会删除某些政治敏感内容,以弱化原文叙事话语。例如,《参考消息》5月29日的“外媒评述:美国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但这掩盖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并非来自中国,它来自欧洲。”此段话的原文很长,在“China is an easy target”和“But all of these truths obscure the one crucial point: America’s coronavirus epidemic didn’t come from China. It came from Europe.”中夹杂大段内容解释西方部分人指责中国的原因,如说中国“was the origin of the outbreak”(病毒溯源问题尚有争议,已有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亚洲出现前就已在别处存在,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仍不遗余力地炮制中国制造病毒的虚假言论)及中国“suppres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Wuhan pneumonia”(主要影射李文亮事件。然就未知病原体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在对病毒了解不足情形下为防止民众恐慌而发生早期误判实难避免,此观点亦被许多国际媒体认同。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爆发式传播后其他国家的应对中也出现了诸多纰漏)。对于这些不利于国家形象与人民利益、涉及政治敏感或未有定论问题的省略,弱化了原文的隐含叙事,压制了原文叙事者的声音,体现了译者的价值取向和判断。
除刻意略去一些不利于我国官方叙事的信息外,译者有时还会添加少量原文没有的信息,以强化或更改原文叙事。如在6月3日中国日报网上“美国如何借新冠疫情抹黑中国?美媒:利用‘机器人’账号炒作阴谋论”一文中,第三段末尾“事实上,此类谣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事实核查小组揭穿。美国卫生官员同样否认了这种病毒是人造的或转基因的说法。”和第五段开头“截至3月下旬,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在‘匿名者Q’等群组中,带有‘新冠病毒为中国生物武器’话题标签的阴谋论帖子被分享了近900次。”中间增译了一句话“但是在推特上,这些散布‘新冠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的群组仍十分活跃。”此增译一则承上启下,提高了叙事的连贯性,二则强化了原文对造谣者的批评叙事,既能帮助读者把握脉络,又可引导他们更好地理解、接受我国官方公共叙事,可谓一举两得。
(三)命名标示及标题重构:标示式建构
依照蒙娜·贝克的观点,标示式建构是“用词汇、用语或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6]。命名是标示式建构的常用方法。对叙事元素的命名不仅是称呼问题,还代表立场及观点。例如,4月9日《参考消息》“专家认为:中美可借抗疫开辟共处新路”一文中,将“its leaders recognize that global hegemony … would be unsustainable and more of a burden than a boon”译为“中国认识到……与其说全球霸权是一种福利,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原文的“its leaders”被“中国”替换,由强调个体变为着眼整体,将个人意识化为国家意志,有利于塑造团结共进的国民心态。
标题是对内容的提炼总结,新闻标题的合理建构能帮助编译成功实现其叙事目的。在新闻编译中,改换标题的现象俯拾即是。标题重构能帮助译者迅速构建全新的诠释框架,其目的之一是为赢得民众对叙事的支持,树立国家形象。如7月4日《环球时报》文章“疫情加快中国经济自立步伐”原标题为“COVID-19 Accelerate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译者将“polit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改为“经济自立步伐”,突出积极意味,符合我国叙事立场,有利于增强国民信心。标题重构目的之二是为质疑、揭露某些外媒的公共叙事。如5月14日《参考消息》“澳媒文章:澳不应充当美攻击中国爪牙”一文,原标题“Geopolitics Makes an Unwelcome Return to the Coronavirus Era”指向性不够明确,而译文点名“澳”“美”并直言中国立场,通过标题重构直接引导解读,使读者抵制不利于我方的叙事。
(四)他者叙事与改变措辞:人物事件再定位
从翻译叙事学角度看,人物事件再定位即调整语言参数,以重新定位文本叙事内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3]。新闻编译中,再定位的方式之一是他者叙事,即在叙事定位过程中将自身置于第三方位置,以淡化主观色彩、增加可信度。例如,译者在编译中常明示媒体或信息来源,向读者声明文章内容非我方观点,乃他者言论。概览《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可发现,许多文章加上了“美媒文章”“英媒社论”“外媒评述”“澳媒”等字眼以注明媒体来源,拉远自己与报道内容的距离,增强客观性。此外,为表明信息权威性,有时译者还会注明信息提供者的身份或机构,如“美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等。
改换措辞亦可帮助实现人物事件再定位,进而影响读者对事件和话语的解读。翻译过程中,译者常通过种种策略加强或弱化原文叙事的某些内容,以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例如,参考消息网3月26日“英媒:新冠疫情或成美国的‘苏伊士时刻’”一文将“China is using its outreach on the pandemic to try to establish the parameters for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译为“中国对此次疫情的对外援助努力或为未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制定参数”。对比可知,译文将主语进行了移位,原主语为“China”,叙事重心为中国“利用”(“is using”)对外援助扩大国际影响,暗指中国援助他国乃另有企图,是外媒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译文弱化了动作的主动性,改变了文本内参与者间的政治联系,修正了原叙事对中方意图的误读,通过改变措辞将中国对外援助影响世界格局定位为一种无意识行为、而非处心积虑或汲汲营营的政治谋略,实现了在我国立场叙事框架下的合理变译。
三、结语
当今翻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翻译已不再被看作一种简单的双语转换行为,而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7]。翻译叙事学认为,翻译是政治的一部分且参与创造政治[6];译者受国家意识形态、媒体编辑方针等因素影响,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新闻翻译,尤其是时政新闻编译实质是一种话语再叙事,是公共叙事主体争取传播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此次新冠疫情的相关编译报道体现了我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的话语博弈。在现今由西方媒体主导的传播领域中,为避免“陷入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旋涡,在国际舆论中失语”,译者不能一味固执地追求忠实原文、坚持译者的“隐身”[8]。合理运用叙事建构策略能引导和制约受众对报道的反应、操控读者对叙事的解读、提高我国对外编译传播效果。为更好地树立国家形象,新闻编译者不能盲目屈从西方媒体的强势话语,而应灵活理性地进行叙事重构,在帮助国人了解外媒眼中中国的同时实现预期的叙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