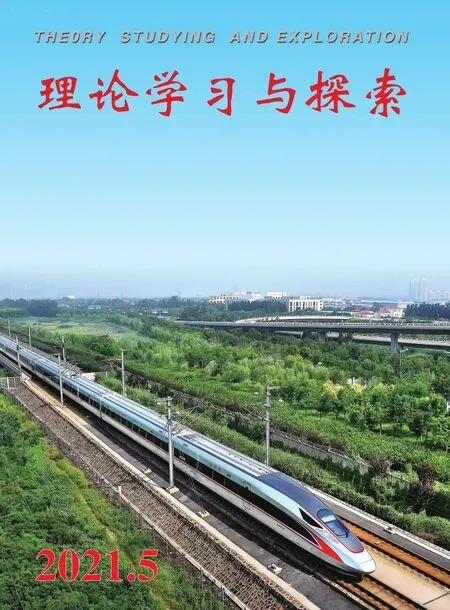中国铁路进入新时代的逻辑勘定
苏志加
(铁道党校,北京 10008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概念,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铁路百年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视域。问题旋即而生,如何认识中国铁路进入了新时代?
回首来路:“中华铁路,师夷之技,源唐胥始,于龙号起,几多艰难,历经风雨。”唐山机务段火车头纪念碑上这段铭文,时刻提醒旧中国的铁路之“无”。
面向未来:辉煌伴随苦难的发展历程,使中国铁路不甘于作为世界铁路发展史的一个简单结果,而是将自身作为服务于人类交通文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背书,并将在世界铁路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中获取自身更为精准的前进坐标。
一、旧中国:世界铁路的“中国化”
(一)陆路国家之殇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几次较量,无疑让清朝子民验视了枪炮与刀枪、铁路与驿路的天壤之别;无疑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反思那个时代,反思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巨大差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路国家之一,而没有作为工业文明代表的高效运输工具——铁路,这无疑成为陆路国家之殇。
借路攘利还是因路割地的抉择超越了铁路本身的取舍,其背后更反映着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近代中国该往何处去?从空间意义着眼近代工业一体化进程,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网、快速的运输工具和高效的运输组织,不仅仅广袤的区域、内陆与沿海,甚至国际间都无法互联互通;从时间意义上看,这更事关国家的发展速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事关中国能否作为“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因此,当“世界历史”[2]进入到普遍交往阶段,已不再接纳做孤岛式存在的民族国家。
(二)逐“路”中国与“瓜分中国”
近代以降,通过战争强占领土逐步转换为通过“条约”攫取“筑路权”、进而实现领土占有的事实化策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建筑铁路……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3]围绕铁路和通过铁路“瓜分中国”[4]逐步事实化。从投资筑路到攫取路权,列强的势力沿着铁路向中国内陆扩张并不断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筑路权问题,其表是围绕铁路逐“路”中国,其里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以殖民化的暴力性剥削“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5]。
1.并吞领土战略转向攫取路权策略
沙俄率先攫取到垂涎已久的战略利益,而铁路则成为这场瓜分狂潮的焦点。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奏章中直言:“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6]西伯利亚铁道路基已于1895年修到赤塔,1896年的中俄谈判使俄国在远东的影响进一步事实化。该密约的签署实现了“东清铁路”途径黑、吉两省直达海参崴。在强占旅顺和大连的基础上,俄国又“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7]
德国紧随沙俄之后“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99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8]。法国取得滇越铁路,英国取得沪宁铁路和广九铁路,比利时取得卢汉铁路和汴洛铁路,美国取得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
2.支离破碎的民国铁路
南京临时政府实现了运输发展的制度化,在设立交通部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虽然也制订了铁路发展规划,设立铁道部统管全国铁路事业,虽然经过长达20余年的经营,但成效十分有限。自1928年至七七事变,仅在关内修建了3600公里铁路;抗日战争时期,以拆旧轨充新线等办法,勉强修建了1900公里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只顾发动内战,铁路建设几近空白。
(三)受制于人的“中国化”
混乱中曲折延长的近代铁路史也折射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近代铁路始终“扭曲”地延伸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始终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始终未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始终未能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的铁路
旧中国铁路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日伪统治等不同历史时期,但路权却始终操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始终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英美两国最初合谋的“寻常马路”,逐步演变为“吴淞道路公司”,最后既成事实为“吴淞铁路公司”,其所有者怡和洋行实为英国在华的代理人。甲午战败之后,英、俄、法、日、德、比、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攫取中国的铁路权益。自1876年至1911年修建的近万里铁路,国有和商办铁路等仅占20%左右,帝国主义直接修建经营的约占41%,通过贷款控制的约占39%。北洋政府时期通过“统一路政”的方式,将各省铁路悉数收归国有以抵外债,进一步出卖中国路权。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官僚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相勾结,成为铁路建设及运营的主要资本力量。一方面为列强进一步染指铁路权益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官僚资本的贪欲和腐化,无疑使中国铁路的发展雪上加霜。
2.“万国化”的铁路技术标准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可统计的机车有4069台,出自9个国家的30多个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万国机车博物馆”之名由此而来。迥异的技术标准和铁路设备被竞相“安装”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中国铁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也外在的具象化为纷乱的技术标准、混乱的运营管理和杂乱的机车车辆设备等。
仅以轨距为例,德国一手操办的胶济铁路“轨距为1.435米”[9],沙俄修筑的东清铁路是1524毫米的宽轨标准……囿于时代风气未开,晚清政府更是“开创”了荒唐的“马拉火车”之先河。
3.“势力范围”化的铁路规划
旧中国的铁路发展“规划”实质上是各列强国的“势力范围”化,即以“条约”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事实化的“独立王国”。标准不一的铁路,走行于列强的“租借地”或“占领区”内。严重破坏了中国铁路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甚至个别军阀如阎锡山之所以采用窄轨标准,重要的出发点之一竟也是要在山西建立一个“独立王国”。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万多公里的铁路大都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等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各列强少有染指的西北、西南等地区,铁路里程仅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6%左右。
二、新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中国铁路
新中国铁路发展之所以能够获得后发优势、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来自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铁路新方向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10]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新中国人民铁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主席在接见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发表了事关中国铁路发展方向的重要讲话,“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11]这是毛主席对新中国铁路所做的第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专题讲话,为新中国指明了建设人民铁路的方向。
在建设人民铁路的号召下,广大铁路职工与铁道兵团日夜奋战。1949年总计修复铁路8278公里,修复桥梁2717座,“全国通车的铁路已达21810公里。”[12]预计要用10年时间才能修复的铁路,不到一年就基本修复通车。“国民党政府从1936年提出修成渝铁路,14年未铺一根枕木、一根钢轨。新中国从1950年6月15日到1952年7月1日,仅用两年多时间,成渝铁路就建成并正式通车。”[13]同期还有天兰、湘桂铁路来镇段相继通车。“一五”期间,全国新建铁路4890公里,铁路里程较解放前增长了22.5%,达到26707公里,改变了旧中国“势力范围”化的分割布局,初步构建起相对平衡的内地铁路网骨架。
(二)牵引动力自主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电力机车登上世界运输历史的舞台,已经错失蒸汽机时代的中国铁路,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铁路的牵引动力革命势在必行。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电气化铁路逐步修建和投入运营,铁道部同期制定了《铁路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技术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牵引动力的改造,要安全迅速地、有步骤地由蒸汽机车转到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上去。一机部湘潭电机厂和铁道部株洲机车厂联合研制的第一台大功率6Y1型电力机车问世,以毛泽东主席的诞生地“韶山”命名。至20世纪70年代,电力机车的研制呈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以韶山1型电力机车为基础,韶山8型、9型客运机车和韶山4C、韶山7B重载货运机车,相继成为电气化铁路客货运输的主力车型。以韶山1型为代表的系列电力机车填补了中国独立自主研制电力牵引动力机车的技术空白,使错失蒸汽机车时代的中国铁路,追赶并步入电气化铁路时代。
(三)中国铁路第一次“走出去”
随着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新中国铁路经过艰苦创业和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铁路工业在短期内逐步形成一个适应铁路发展需要的、多品种和多类型的独立生产体系。各种类型机车和车辆设备的生产实现了由修补到制造、由仿制到创造、由对外依赖到独立自主的转变。这三大转变使新中国铁路工业一方面具备了服务新中国铁路自身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为中国铁路走出去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性条件。
应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总统的请求,中央做出了援建坦赞铁路的重大决定。由于技术标准不一致,援建的机车车辆和各类装备均需重新设计、试制、试用和生产,一切几乎均需从零开始,对新中国的铁路工业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同期在此修建的公路与坦赞铁路有交叉点,美国工程同行一度质疑中国的技术能力,直言该项工程半个世纪也难以完工。中国铁路工程建设队伍不但率先通过交叉点,而且仅用5年时间便实现了坦赞铁路的全线贯通。
坦赞铁路工程不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更使大批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建队伍得到了锻炼,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铁路对外合作、技术交流、劳务输出及派遣等诸多新的合作领域,初步为中国铁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三、新时代:中国铁路走向世界
百年铁路,跨越三个世纪的中国铁路历经迥然相异的两个70年。作为铁路技术的非原生国,旧中国被动地历经70年世界铁路的“中国化”;新中国成立的70年来,中国铁路以独立自主的开创精神,推进自主创新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开启中国铁路“世界化”的新征程,开创了中国铁路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由2万公里左右增长到13.1万公里以上,增长了655%;铁路旅客年发送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2亿人[14]增长到33.17亿人,增长了3252%;电气化铁路从无到有,增长到70.3%,居世界第一位;高速铁路从无到有,达到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15]。70年中国铁路人励精图治、砥砺奋进,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
(一)“走出去”的中国高铁标准
中国高速铁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由追赶到超越的发展路径,取得了铁路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具备普速、高速和重载铁路三大技术标准体系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铁路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修订工作,截至2018年年底,共主持参与ISO、UIC重要国际标准55项,中国铁路已成为国际铁路标准制修订的重要力量。
“走出去”的中国高铁标准已经在印尼雅万、中泰铁路等项目中得以积极应用,走出了中国铁路“世界化”的第一步。中国高铁标准将进一步规章化系统化,并逐步实现中国铁路标准的国际化和世界化,进一步提升中国铁路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走出去”的中国铁路建设
中国铁路建设“走出去”,是中国铁路拓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经环节,更是中国铁路引领世界铁路发展的重要一步。中国铁路建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能推动铁路技术装备及劳务等出口,更为自己创造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战略机遇。
2014年中国在海外承建的首条高速铁路即伊安高铁顺利通车并正式投入运营;2016年雅万高铁正式开工;第一条完全采用中国技术标准的中老铁路稳步推进;2017年由中国承建的蒙内铁路正式通车;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开工建设,莫斯科-喀山高铁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走出去”的中国铁路建设,不仅涉及施工建造、设备出口乃至国际标准认定等多个领域,而且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交通运输的范畴,事关未来中国铁路在国际铁路事务中的参与力、影响力和领导力。“走出去”的中国铁路建设,进一步开启了中国铁路建设“建设”世界、中国铁路创造“创造”世界、中国铁路力量“助力”世界的新时代。
(三)“走出去”的中国铁路方案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铁路开创性地打造出中欧班列物流品牌。中欧班列的开通,在交通的意义上为世界交通一体化进程加注了中国铁路力量,并为世界的互联互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战略交通平台;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为世界交通运输发展的可持续进行积极探索并持续贡献着中国铁路智慧和中国交通方案。
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启的蒸汽交往体系,通过“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西米亚森林的道路,使多瑙河失去作用。”[16]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7200列,开行线路60余条,横跨亚欧大陆,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穿越不同的文明,途径多国铁路,需经多次换轨……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欧班列,超越了传统区域间的交往和沟通方式,为世界的普遍交往贡献了中国铁路交通方案,也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70年前,中国被动接受了世界铁路的“中国化”;70年来,中国铁路从中华文明最为厚重而倔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出发,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反身“走出去”,实现了中国铁路的“世界化”,走出了属于中国铁路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