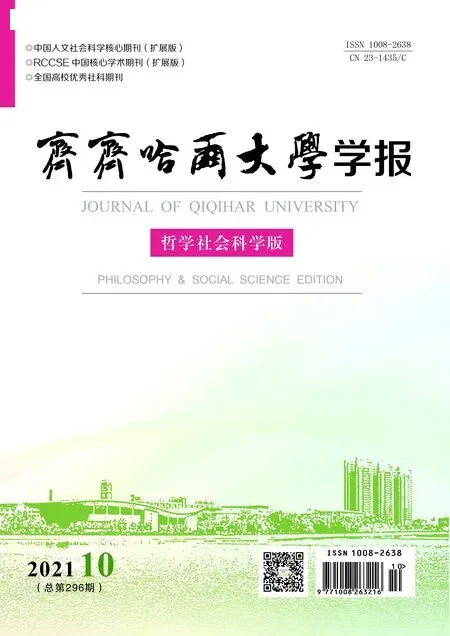《资本论》中科技创新思想的自然生态之维
姜 惠,刘宝杰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纵观《资本论》,马克思虽然并未直接使用“科技创新”一词,但他常以“劳动资料的革命”、“机器的急剧改良”等具体表述来意指“科技创新”,并从多领域多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考察与论述。其中,自然生态维度是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重要一维。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挖掘自然生态维度下的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探寻科技创新生态化发展的推进路径,是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科技创新的自然孕育:自然生产力
自然界先在于人,自然生产力因不同属性并以不同方式对科技创新产生影响。自然力、自然物质和自然地理位置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自然生产力,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的二重性意义。
(一)自然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自然力划分为“单纯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三部分。从自然生态维度考察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影响科技创新的自然力为“单纯的自然力”,即自然界中用以代替人力的动力,如水力、风力等。
实现自然力的生产性应用,是推进科技创新的基本动力。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力,需要“人的手的创造物”,并提及:“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1]444将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需要创制与一定自然力相适应的技术人工物,并将其作为发挥自然力作用的手段,以实现自然力的消费。举例言之,在对水力的占有中便是如此。[2]727由于自然瀑布的数量有限,人们在工业中往往设法谋求对水力的充分利用。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水力,在水流条件优良的情况下,人们直接改良水车。而在水流条件欠佳的情况下,人们则进一步发明了涡轮机。由此可见,基于对自然力利用的现实需要,一系列新工具、新方法等应运而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自然力的天然特性,是影响科技创新的直接原由。这直接体现于《资本论》中发动机演进历程中关于自然力选择的论述。具体而言,发动机作为机器中的动力供给部分,它或者自身直接产生动力,或者接受外部自然力推动。“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1]432迫切需要发动机克服自身阻力,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实际上,动力的选择面临着诸多困难。风力稳定性差且不易于控制,水力受地势和降雨等因素影响较大,时常出现径流量不足甚至完全枯竭的情况,因而风力和水力也不适宜作动力。后来,瓦特发现利用煤和水产生的蒸汽力,摆脱了地点条件、气候因素等客观限制,由人随意控制,可作为发动机的动力。在这一自然力的动力支持下,瓦特发明了双向蒸汽机。由此可见,自然力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二重影响。当自然力能够突破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时,往往引起颠覆性技术创新。反之,科技创新则停滞不前。
总而言之,各种自然力以其作用特性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一方面,自然力的现实应用要求一定的中介物将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这催生出机器的研发、方法的改进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自然力作为一种客观作用力,不同自然力所具有的自身特性使得它对科技创新具有推进或阻碍的不同意义。
(二)自然物质
“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3]72充满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物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自然物质对科技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意义。
多样富足的自然物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质前提。其一,自然物质的多样性为科技创新的多样性创造可能。在这里,自然物质的多样性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即不同自然物质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同一自然物质的属性具有多样性。一方面,多种多样的自然物质以实践为中介,参与到技术进程中并构成科技创新的现实对象,使科技创新的形式、类型等也因此呈现多样化。“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1]212例如矿石与采矿业、鱼与捕鱼业等。如此,自然物质既是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也是采掘技术的作用对象,多样自然物质的存在促进了各种具体采掘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1]213当某一自然物质被应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中,它将发挥其多种属性,继而产生多种科技新效应。就水而言,利用其动力属性,人们发明了水车;利用其渗透属性,人们开展了农业灌溉。其二,自然物质的富集程度,为确定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奠定自然基础。丰富的自然物质,是进行研发、试验以获取新发现、创造新发明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自然物质在不同地区的种类和数量具有极大的差异,设置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就需要将自然物质贮藏分布情况考量在内。例如,发展冶金、化学等工业,就需要考虑煤、铁等自然富源的制约。煤、铁等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是设立工厂的最佳选址,也是最利于进行科技创新的区域。
自然物质的运动规律,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原理基础。自然物质运动的规律即为自然规律,它产生、存在并表现于自然事物的运动过程和相互作用。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渐深入,人类越发能够在自然规律的指导下获取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成就。以电的运动规律为例,“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1]444就为资本家所利用,推进了电报等的发明和使用。同时,“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机器”,[1]444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连锁反应。
总而言之,自然物质是影响科技创新的重要自然条件。由于自然物质种类和属性的多样性,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也呈现多样性。同时,自然物质在不同地区的贮藏情况对科技创新的战略谋划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自然物质自身的运动规律,也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提供原理性启迪。
(三)自然地理位置
自然地理位置,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地球上所处的方位和特点。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的科技创新,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自然地理位置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生成。在论及埃及的治水工程时,[2]588马克思援引居维叶的《论地球的灾变》,阐释自然地理位置对埃及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在古代埃及,人们依据所处地理位置和尼罗河汛期来制定历法。人们发现,每当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看见太阳和天狼星同时在地平线升起时,尼罗河汛期即将到来。这一天即为一年的开始,并规定一年有12个月。通过观察太阳和天狼星的升起,埃及的天文学也逐渐发展。此外,在尼罗河地区,每当尼罗河泛滥后,都需要重新计算和划分土地,土地丈量技术和几何学也由此发源。由此可见,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创新的起源。
自然地理位置影响一个国家开放式创新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居于沿海地区的国家,其开放程度较高,这往往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且,生活于开放的自然环境中,人们的思维更具发散性、活跃性,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创新主体的思维基础。磨的发展历程就将此充分体现。早在十或十一世纪,德意志发明了风磨。至十六世纪,荷兰引进并广泛应用德意志风磨。然而,这种德意志风磨容易受到强大风暴的破坏。在对德意志风磨进行分析和应用的基础上,荷兰人对风磨进行了改良性创新,通过调整风磨的顶盖和支架来调节风磨的制动装置,这种风磨也因此得名为荷兰风磨。所以马克思说:“它们从德意志的风磨变成荷兰的风磨。”[4]335因而,处于开放地理位置的国家更易引进并创新科学技术。
总而言之,自然地理位置是影响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的起源和类型往往同当地的地理性特征相适应,通常而言,沿海沿河等开放性地区更容易吸收和开发出新技术。从自然生态维度阐释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关键在于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剖析科技创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既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过程,也是人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物并返还自然的过程。在前一境况中,科技创新作为实践中人与自然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推进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开展。在后一境况中,受到工具理性和生态理性影响的科技创新,引发并修复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
二、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中介属性的科技创新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当人利用科技创新对外界自然打上人类烙印的同时,外界自然也赋予人以“自然界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借助中介在人与自然间进行自然物质、主体意志等因素的双向传递,才能使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顺利进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阐释了人类在实践中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传导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指明科技创新是推进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特殊中介。
(一)自然的人化中的科技创新
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在实践中运用特定工具,按照自身目的改造自然,使外界自然被赋予人类活动印记的过程。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科技创新寓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之中,使人身外的自然不断蕴含人类主体意识。
其一,人与自然对象化关系中的科技创新。自然的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利用工具将自身意志作用于外界自然,造就人化自然的过程。作为人类实践的作品,人化自然是人类自身的再现,是人类本质的凝聚。人类面对人化自然,实质上就是在直观自身。因而,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与自然是对象性的关系。在人类实践中,科技创新作为手段,加强了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在考察英格兰的农业生产时,马克思指出,农场主以获取富足农产品为目的,“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1]780增加对土地的投资。结果是,租地农场中的耕种面积日益扩大,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实际上,这就是人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将意志赋予自然,以实现自身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是联结人自身目的与外界自然的中介。
其二,人与自然主客体关系中的科技创新。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逐渐由消极适应自然转变为积极改造自然,自然也随之积淀了人性特征。这意味着人之于自然具有能动性,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与之相对应,受到人类主体的改造,自然之于人具有受动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因而,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与自然是主客体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科技创新以中介形式,传导了主体力量在自然界中的外向显现。在考察土壤肥力时,马克思指出,自然肥力的利用程度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水平,包括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程度。因而,采用新的化学或机械方法排除不利于土壤收益的障碍,便能提高土壤肥力。反之,若要降低土壤肥力,马克思称“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都会产生这种效果。”[2]734总之,在发展的农业科技的作用下,被改变肥力的土壤显露出人的实践痕迹。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表现为人改造自然的方法。
(二)人的自然化中的科技创新
人的自然化是指人在实践中受到外部自然的影响,在自然规律的制约与实践活动的作用下,“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5]306转化为主体能力的过程。科技创新在人的自然化过程中,使人不仅超越了肢体器官方面的限制,而且提升了思想认识方面的能力,人自身的自然不断体现“自然界的本质”。
其一,人的劳动器官延长论。马克思主张,“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3]109而由人的天然躯体动作所完成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同动物的无意识本能性活动类似。自由且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把人和动物根本区别开来,劳动的发展催生了劳动资料的创造,劳动资料是“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6]288在生产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就在自然界中发现了劳动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外在天然物品。石块、木头和贝壳等经过人类加工,曾起到劳动资料的作用。受制于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机能和数量,人们就利用这些经过加工的自然物作用于其他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209就石头而言,起初人们从自然中挑选较为锋利的石块用以投、磨、压、切等。基于现实的使用经验,人们将石块改造为更为锋利的石制工具和武器,借其延伸肢体本能以进行更为复杂的活动。由此可见,科技创新通过改造自然物,延长了人的肢体、器官,放大了人的肢体、器官的功能,使人的自然化加快。
其二,人的思想认识发展论。人属于并存在于自然界,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人创造了技术系统并逐渐融入其中。在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的同时,科技创新推进自然意蕴内化于人的思想认识之中。在马克思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中,自然界对人类思想认识的感染和同化,集中体现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将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自然规律、自然现象等映射于人的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科学认识。当人们形成并掌握对自然的认识之时,实际上已是“将自然规律和自然的力量纳入自身,变为自身的部分”。[7]102在对工艺学历史的考察中,马克思援引波佩对工艺学的相关梳理,强调技术发明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仪器设备支持。例如,18世纪流量计的发明为人们确定水的运动速度提供了专门仪器,水准器是水准测量的专门仪器,这两种仪器共同推进了水流压力或阻力学说的形成。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为了加速水流,人们将水平槽改为抛物线形式的水槽,构成了水槽理论形成进程中的专门设备。[4]336借力于技术创新,人类逐步揭开了自然界的层层奥秘,自然规律和现象等更多内容转化为人的思想认识。
总之,当人通过自身自然力的“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208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领域的新产品、新方法等在人与自然间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推进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实现。
三、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工具理性扩张下的科技创新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了丰厚充实的物质财富。基于“对技术模式效率优势的意识与自觉追逐”,[8]301工具理性盛行于世。在此情形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587贪婪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试图利用科技创新,对自然界进行无限掠夺,这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裂缝”,即人对自然界的索取与返还出现了偏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生态系统与生产系统紧密联结。因而,探究工具理性扩张下运行的科技创新,也应将视野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工农业生产。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是人们依靠劳动直接从自然界获取所需之物的生产部门,“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9]399因而,农业是最能直接体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产部门。在农业部门,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渗透基质,农业科技不断革新并服务于从自然界攫取利润的目标。
在研究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时,马克思认识到了以机器劳动方式代替手工劳动方式的农业技术工业化。由于工业革命蓬勃开展,农业技术不断变革并日趋工业化,这鲜明表现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蒸汽化和机械化。人们以蒸汽力代替人力、畜力,发明和应用了以蒸汽力为驱动的农业机械,并以其逐渐代替了传统手工工具。农业技术的改良推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意味着人类能更快更多地获取自然物。鉴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有产者愈发利用新兴农业机械,不断拓宽对自然的利用界限,甚至过度利用自然。因而马克思强调:“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580总之,在无休止追逐财富的价值观念侵蚀下,农业科技的创新,加深了对自然界的掠夺,导致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被破坏。
此外,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就灌溉而言,开凿人工渠道。逐利者通过大力“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10]212对土壤进行灌溉,获得了丰厚的农业利润。这一方法的过度使用,在提高土壤含水量的同时,却容易导致土壤中营养物质的流失。就肥力而言,研发人造肥料。在骨粉肥料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发现化学物质与土壤颗粒的反应机理,进一步研发了化学肥料。有限度地使用化学肥料是改良土壤肥力的合宜之举,基于对利润的追逐而无限度地使用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地的再生能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579-580可见,大规模的农业科技革新,促使利益追逐者从土地拿走更多的东西,又未将其归还于土地,威胁着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工业科技创新
除农业部门外,马克思直言,工业和商业也“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2]919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用以谋求无限利润的科技创新的开展及应用,导致城市及工业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其一,在原料利用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1]519原料是指同土地脱离后又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归根到底来源于自然界。增殖性生产的发展使机器的更新换代成为必要,这就导致愈来愈多的自然物质从自然界中析出。对自然物质攫取的扩大化,且未成比例地将物质返还于自然界,使得人与自然间出现物质变换的断裂。
其二,在废物排放方面。科技创新在推进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生产排泄物,这些排泄物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之中,造成了经济浪费和环境破坏。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的应用和大工业的发展,吸引大量人口迁往城市。人们不顾自然界的消化能力而直接将日常生活的消费排泄物排入自然界,给城市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例如,在伦敦,人们的粪便排入泰晤士河,给泰晤士河造成了直接的污染。[2]115
其三,在空间特征方面。在讨论“物质变换裂缝”问题时,马克思并非将视野囿于一国之内。他强调,人与土地物质变换间的断代,会导致对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2]919由此可见,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工具理性的膨胀,科技创新引发的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征。
总之,资本家始终以肆意索取自然物质,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就是自然物质消费过程。在科技创新的资本主义应用下,自然资源消费的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在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生产中,这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富饶性降低,甚至是枯竭。[11]135基于如上论述,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除破坏人类自身的自然力外,“二者会携手并进”,“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2]919这意味着,受工具理性影响的科技创新,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裂缝。当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1]107与引发人与自然物质变化断裂的工具理性主义科技创新相对应,参与这一断裂修复的则是生态理性主导的科技创新。
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修复:生态理性支配下的科技创新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科技创新的审视,具有前瞻性、辩证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既认识到工具理性盛行下生态问题的科技创新诱因,也在生态理性视域下提出生态问题解决的科技创新路径。生态理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指明的“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928-929如此,生态理性科技创新就构成人与自然物质变换顺利进行的技术支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科技创新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填补。
(一)变革农业技术,发展生态农业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土地的无节制掠夺,马克思强调,要在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下变革农业技术,推行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在农业生产模式的改革措施中,内含着农业技术的创新意蕴。其一,实行轮作制。轮换种植不同作物,合理均衡利用土地,将用地和养地相统一。其二,改革农作安排。“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种植甜菜”,[4]368把沙地和荒地改为种植麦子。这样,在获得丰富农产品的同时,也为畜牧业提供了优质饲料。其三,施用有机肥料。在消费排泄物的农业利用上,可将人类的粪便和消费残留物等施于土地。在英国,人们用海鸟粪向田地施肥。[1]277可见,马克思在改革农业生产时,以变革农业技术为手段,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性、系统性和永续性。其中,这一过程的农业技术变革实为受生态理性支配的技术创新。
(二)发明和应用高性能机器,节约原料消耗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发生断裂的关键一点,就在于人类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界无限支配。对此,马克思主张通过发明和应用高性能新机器,降低资源损耗量,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
机器是科学技术物化的产物,是人类根据自然规律发明创造出来的,也是人类利用自然的物质载体。因而,发明和应用高性能的机器,是减少自然资源损耗量和控制自然资源开采量的可行性路径。关于谷物脱粒加工工作,马克思指出,在等量原料的前提下,机器生产比手工劳动生产的产品量要多。比较脱粒机脱粒和手工脱粒,机器脱粒的谷物损耗量要少约2.5%。[4]368此外,马克思引用詹姆斯·内史密斯信中关于蒸汽机体系节约燃料的例证。在兰开夏郡,人们对蒸汽机进行彻底改革,当蒸汽从锅炉进入到其中一个气缸后,人们一改以往通过活塞冲程排掉蒸汽的流程,将蒸汽转入另外一个低压气缸,在其中完成膨胀后继而导入冷凝器。这种伍尔夫蒸汽机,既提高了机器的生产效率,也将每小时耗煤量由12磅到14磅降到3.5或4磅。[2]112-114新式蒸汽机对煤的利用率大为提高,相对减少了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
(三)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资料,减少废料产生
马克思指出废料的减少即为“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2]117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两种方法。
其一,改进生产工艺。生产工艺代表着工业生产中加工原料的程序、方法和规则等,优良的工艺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工艺的进步往往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废料产生。例如,在亚麻加工业中,人们用极粗糙的方法加工亚麻时往往会产生许多废料。而当人们发明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等精细方法来加工亚麻时,废料就会减少很多。马克思甚至指出,若用较好的机器来梳理亚麻,这种损失就可以直接避免。[2]116
其二,改进生产资料。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从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转移次数来看,生产资料包含原料燃料和机器设备两种形式。马克思指出,废料的产生主要受生产过程中机器、工具的质量以及原料的质量的影响。一方面,原料成为废料的转化率与生产中所使用的机器、工具的质量呈负相关。机器工具越发达,原料中转化为废料的部分就越少,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原料转化为废料的多少也与原料的质量相关。原料本身的质量越高,转化的废料可能性及数量就越小。由于原料的质量又主要受到“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2]117以及“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2]118因而,与原料相关的产业技术越发达,原料的质量就越高,废料就越少。总之,最大程度地利用原料,减少废料生成,就需要改进生产资料。
(四)推进科学进步和机器改良,实现“排泄物”再利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中,排泄物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认为,这些排泄物仍具有一定的生产价值,它们可以再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对此,马克思指出,通过改进方法、改良机器等途径发现排泄物的有用性质,对排泄物进行资源化再利用。
其一,科学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能够发现新的有用物质和已知物质的新用途,并提供新的方法来实现废料的再利用。在这里,再利用的废料不仅指本工业的废料,通常也包括其他工业的废料。比如在化学工业中,人们通过运用新的方法,不仅将煤焦油制成了新的苯胺染料,甚至后来将茜素制成了药品。[2]117其二,机器的改良。通过改良机器,将以前的无用物质加工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对其进行新的利用。以英国的丝织业为例,由于丝织业机器的改良,废丝被制成了具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2]117如此,依靠科学的新发现和机器的新改进,便能实现变废为宝。
总而言之,马克思将受生态理性影响的科技创新视为缩小人对自然资源索取量与归还量之间差距的手段。利用科技创新填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是马克思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体现了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生态学价值取向。
五、自然生态维度下《资本论》中科技创新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技创新持审度态度,既探讨了自然生产力对科技创新的基础影响,也阐释了科技创新对自然生态的改造意义,其自然生态之维,对当下我国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立足自然禀赋,加快科技原创性突破
在马克思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论述中,自然力、自然物质和自然地理位置等自然生产力由于其属性、功能等差异,对科技创新具有推进或阻碍的二重性意义。立足华夏大地,丰饶的自然富源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充实的自然根基。基于此,我们应充分考量并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以切实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认知自然生态,夯实基础研究。从自然生态维度解析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时,可以发现,各种自然生产力在技术上的新应用,往往是基于对这些自然生产力的新认识。马克思曾直接指出,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2]96因而,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构成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我国自主创新的深入发展,需要拓展对自然界的系统认知,即加强自然科学领域的前沿探索。主要包括:科学认知自然系统中各要素的性质、结构以及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反应表现、运行机理,完善自然生态知识体系;拓展自然资源基础理论认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分布及预测分析;深化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探索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机理等。
整合自然要素,优化研发布局。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地理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例如,马克思曾阐述丰富的自然力、自然物质催生出多样的科技创新以及自然地理位置影响着技术创新和科研布局。可见,谋划和推进科技创新,需要统筹考量并合理运用各种自然要素。其一,在资源富集区,自然资源为科技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开发的现实需要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基本动力。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推进资源保护区选划、探索安全精细探测技术、采用多方式组合的提取技术、开发环境检测组网等,进行资源规模化高效开发。其二,在资源贫瘠区,尽管科技创新受制于当地的自然资源,但可以通过区域间资源流动与分享,以他地资源助力本地创新。其三,依据自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分布等因素,构建适宜的科技创新空间规划,特别是凭借自然优势,发展区域特色创新。
(二)弥合人与自然,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
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科技创新及其成果作为中介参与其中,不断改造人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加速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演进,各类学科交叉渗透,科学技术以新的范式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从当前科技发展现状来看,各类新兴技术具有显著的颠覆性特征。基于此,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应大力开展并应用颠覆性技术创新。
其一,突破应用会聚技术。当前,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在广泛交叉和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12]85在科学技术的融合互动中,会聚技术这一新兴技术形态派生而出。会聚技术以“打破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界限”为路径,[13]1634以“提升人的能力、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为目标,[13]1632包含对人类生理心智能力的提高以及对自然界的目的性改造。可见,谋求人类体内与体外环境的协调互动,会聚技术或许是一种可行性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创新的现实应用中,增进各类技术的协同攻关,探索人与自然联合互动的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会聚技术的发展逐渐催生了人类增强技术。
其二,合理利用人类增强技术。人类增强技术是一项利用技术人工物改造人的自身能力的典型技术。在人类增强技术中,传统范式的人类增强技术以间接的外在方式作用于人类,例如创制和改进工具以延长人类肢体器官的“外部性技术”,这同马克思关于科技创新推进人的自然肢体延长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以直接的内在方式作用于人类,例如提升人类认知、思维的“内部性技术”,这类似于马克思所阐述的科技创新推进人的思想认识发展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某种人类增强技术手段往往只是着眼于提高人类身体的局部能力,这容易造成身体状态的失衡。因而,只有在适度范围内合理应用人类增强技术,才会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增强”。[14]74
(三)遵循生态理念,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化
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着重分析了不同理性形态下科技创新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揭示了科技创新是生态问题的重要诱因和解决手段。特别是关于生态理性支配下的科技创新论述,为我国利用绿色科技创新处理生态问题提供了启迪。
以生态高效为导向,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化工业化。我国是农业大国,推进农业绿色科技创新,是建成农业强国的现实路径。首先,系统开发高端农业装备,在合理规划作物种植方式的基础上,规模化应用农业机械。其次,着力培育全新的优良品种,实现种业自主。再次,深入开展生物肥料等技术研发,积造有机肥,提高对畜禽粪的综合利用率。最后,将信息技术与绿色资源融合,以大数据、5G等信息技术为依托,构建覆盖产供销等各环节的绿色供应链,使优质生态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总之,加强农业绿色科技自主创新,打造绿色农业。
以清洁低碳为转向,大力开展能源技术革命。化石能源的传统开发和应用在带来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能源短缺的危机。基于此,开展能源技术革命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保障。其一,通过创制和改进化石能源利用的新型发电机组,以及继续深化创新“洗煤”和“捕碳”等技术,提高对化石能源的清洁转化再利用,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其二,在“基础技术、重大设备、示范工程和创新平台,四位一体同步推进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15]94之中,开展新能源革命,进一步深层开发和有效利用新兴能源。总之,新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紧能源技术革命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希望。
以绿色循环为指向,深入探索废弃物再利用。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能源资源被使用后是可以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进行回收处理,再进一步得到利用的。在新兴资源化技术的作用下,废弃物转化为可用资源的效率和效益日趋提高。在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生产循环可持续,首先应分析考量废弃物的属性和价值,对废弃物进行细致分类。继而针对废弃物构建分门类的闭路循环体系,并完善废弃物处理的配套设备,以满足高效处理和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的迫切要求。总之,科技创新为废弃物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流程,助力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虽未完全显现,但马克思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这一严峻问题,并指出两种理性形态下科技创新的不同生态意蕴。从中可见,生态理念指导下的科技创新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行方案。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生态理念下运行的科技创新,是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现实路径。“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6]4要求我国强化科技创新生态转向,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