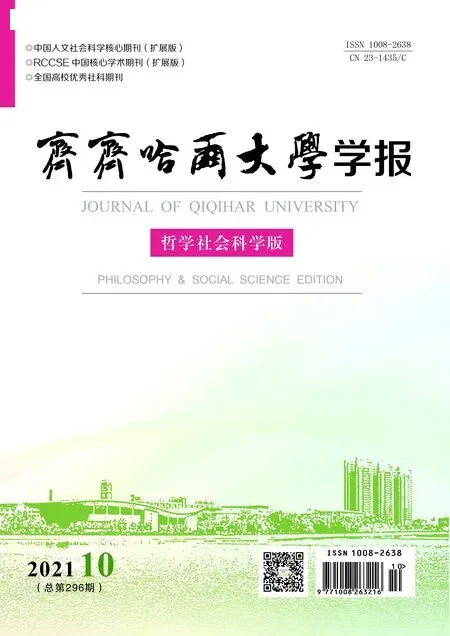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历程
姚 涛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自19世纪60年代始,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导下,进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然而,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洋务派30年“励精图治”却一朝惨败于东洋“蕞尔小国”,向来鄙视日本的国内士大夫阶层无不深受震撼。恰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作为近代中国较早一批接触到西方社会的人之一,身处天津的严复既震惊于清政府的惨败,又痛心于昔日同窗及学生的牺牲,“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2]愤而在天津《直报》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反思甲午败局、批判洋务运动、探求自强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救亡图存之道。在严复看来,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国家间竞争的实质是人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只有着手于教育,逐步发展民力、民智、民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富强。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战后的严复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奋力译介西学以开启民智,辗转南北各地以图教育振兴。
一、译书与办报
甲午战败,举国哗然。严复虽对北洋一系的腐朽堕落了然于胸,却未想到会输的如此彻底。震惊之余,严复深感救亡图存不能只依赖于朝廷和海军事业,必须另辟蹊径。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躬耕不辍的西学上,于是“得有時日多看西書,覺世間惟有此種是真實事業,必通之而後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國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3]对西学长达20年的深入研究使得他深刻意识到,“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4]欲讲西学,就必须将西学经典著作加以翻译,引入国内供国民学习,他说:“複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閔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5]随后,严复开始了自己的翻译事业。从1898年《天演论》出版开始,严复相继翻译出版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美术通诠》《名学浅说》等一系列西学名著。这些名著的翻译出版,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知识视野,为国人学习西学提供权威文献,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无过于《天演论》。1895年,深受甲午战败刺激的严复先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未数月而脱稿”,[6]在书中借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向国人生动地阐述了国家间“优胜劣汰”的残酷性,敲响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警钟。
为了进一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推动变革,1897年夏,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7]这两个报刊以通上下之情、中外之故为宗旨,刊发了大量中外要闻,对列强的侵略与国内顽固派经常通过社论加以批判,尤其关注维新变法运动,与南方的《时务报》一起,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活动、宣传变法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作为创办者,严复也时常在《国闻报》发表社论,阐述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根据王栻先生的研究,《国闻报》从1897年夏创刊到1898年10月14日,总计发表了42篇社论,其中有27篇可以确定是严复所作。[8]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后,《国闻报》由于鼓吹变法、言辞激烈而遭到清政府查封,严复的办报事业就此结束。
二、初涉教育
从1880年被李鸿章调至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一职开始,严复供职于北洋水师学堂长达20年之久。20年间严复虽然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对于海军教育始终尽心尽力。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期间,严控生源质量,重视教学管理,完善奖惩制度,全程参与了建校、师资、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实习等工作,为中国海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驾驶班学生六届共120名,管轮班学生六届共85名;[9]昆明湖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24名于1893年在此毕业;[10]自美回国学生王凤喈等9人亦在此修习肄业。[9]396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留在水师学堂任教,有的入海军现役担任军官,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骨干;有的还步入政界,如民国总统黎元洪、海军总长刘冠雄等。可见,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担任总办的严复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元勋。对此,严复曾自信的说道:“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即吾生徒。”[11]可惜,1900年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尽毁天津水师学堂,师生四处逃散,严复也由天津逃往上海避难,从此脱离了天津水师学堂,结束了海军教育生涯。
甲午战争失败后,眼见俄国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奏效,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极力主张采用“联俄制日”战略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为培养对俄外交人才,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严复奉朝廷之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7]81他本人出任总办并亲自拟定课程,聘请教员,完善学校机构设置,主持考试。作为中国最早的俄语专门学校,天津俄文馆附设于天津水师学堂内,主要是利用水师学堂的闲置校舍进行教学活动。
同年,朝廷议覆御史陈其璋有关推广学堂的奏折,准许官绅集资办学。受此政策鼓励,在总理衙门任章京的张元济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堂。身为张元济至交的严复早就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多有不满,于是大力协助学堂的创办工作并亲自为其取名为“通艺”。1897年2月12日,通艺学堂开馆,[7]84有学生四五十人,主要学习英语、数学、天文、地理、农、商、矿、化学、制造等学科。严复虽因事务繁忙没有亲自到通艺学堂任职,但他推荐了自己的侄子严君潜担任学堂的常驻教习,并在后来为学堂聘请外籍教习一名。此外,严复曾利用1898年四五月间赴北京办事的机会两次往通艺学堂“考订功课,讲明学术”。[7]114同年9月18日,因光绪帝召见而寓居通艺学堂的严复在此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比较中西不同的学术传统、介绍斯宾塞构建的学科体系和具体学科的功用与划分、将求学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在京师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然而,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爆发,张元济被罢免所有职务,通艺学堂遭到解散,学生纷纷退学,严复在通艺学堂耗费的心血也付之东流。
三、系统实践
(一)主持复旦公学
1905年5月,严复从欧洲返回国内抵达上海,受震旦学院创始人马相伯邀请,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等28位社会名流共同担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董。[7]198随后,严复开始具体投入学校的创建工作,与马相伯一同筹建新校舍、制定“本学教授管理法”。鉴于严复在国内的显著声望,校董们曾建议由他担任总教习一职,但严复深感“主意之人太多,恐辦不下”,[3]438于是加以拒绝。面对复旦公学在办学经费上的困难,严复亲自撰写《復旦公學募捐公啟》,强调“興學”对于“自強保種”和“民生髮舒”的重要性,阐明复旦公学面临的经费困难,号召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为兴学救国贡献力量。[12]1905年8月24日,严复与马相伯亲自主持了复旦公学的首次招生考试,从500多名报考者中录取了50名优秀者,严复治学之严,可见一斑。9月14日,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严复在校承担英文翻译教学任务。但1906年上半年,复旦公学出现严重内乱,马相伯于春夏之交辞去监督之职。11月29日,严复应学生们的恳求,出任复旦公学校长。由于再次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严复只得电请两江总督端方拨款相助。同时,为了节约办学经费,1907年春,严复精简了复旦公学的人事安排。只留干事三人,分别负责监学、会计、文案,由教员兼任。另外,为了贯彻体育教育思想,特聘请一位美国武官负责教授学生体操,严复本人则隔日到校巡视监督。在严复的严格管理下,复旦公学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学生总数突破200人。眼见人满为患、校舍不足,4月18日,55岁的严复只得再次亲往南京拜访端方商讨扩建校舍事宜。或许是过于操劳,或许是年事已高,严复返沪后“忽患肺炎,幾成危候”,[13]“至四月中旬,乃稍平復”。[14]1908年初复旦公学开学后,校舍问题更加尖锐,庶务员叶景莱趁机煽动学生闹事。对此严复说到“私念衰老之人乃與頃領小兒計論短長,真為可笑”,[15]再加上自己常年奔波于上海、南京、安庆各地,体弱多病、不堪重负,于是在1908年4月至5月间正式致函端方,[7]262坚辞复旦公学监督并推荐夏敬观等三人为继任者。离开复旦后,严复又受继任校长夏敬观之托替复旦寻觅教习,颇费一番周折。
主持复旦公学期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抱负,从学校的创建到日常管理、经费筹集、课堂教学,严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他与马相伯共同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为学校确定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内容细致周详”,[16]1906年11月继任校长一职后更是对学校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使得复旦的发展重回正轨。然而,他对复旦的办学效果却并不满意,1908年4月曾有诗云:“桃李端須著意栽,飽聞強國視人才。而今學校多蛙蛤,憑仗何人與灑灰?”[17]严复不辞辛苦地主持复旦校务是为了培养救国救民的“桃李”,怎奈学校之中充斥“蛙蛤”之辈,阴为绊阻,不免使人心灰意冷。或许这也说明:教育救国,道阻且长。
(二)监督安庆高等学堂
安庆高等学堂,初名“求是学堂”,创办于1897年。开办数年来,管理不善,成效甚微,急需一位德高望重而又有能力的学界前辈加以整顿。1905年秋,安庆高等学堂代理监督姚永概获悉严复正于上海办学,便函请严复前往安庆主持学务。10月25日,姚永概不待严复回应即携安徽巡抚诚勋亲笔信亲自登门邀请。严复起初犹豫不决,亲友也多反对,“皖中亦已有反對之人,數數寄以匿名信相恫嚇”,但见安徽官绅言辞恳切,而自己又素有教育救国之志,“乃許其勉效綿薄”[14]249。1906年4月5日,严复自上海乘船赴安庆就职。[7]2224月8日,严复抵达安庆,受到安徽各界盛情欢迎,巡抚恩铭尤其殷勤。见此,严复暗下决心:“誓必令此校有成”[14]249。
经过初步了解,严复发现安庆高等学堂办学规模很大,讲堂、校舍、食堂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常年办学经费多达6万元,不足之时还可申请追加;学校规章制度较为严谨。缺陷在于缺乏优秀教员、课程设置不可理、学生对西学掌握尚浅。有鉴于此,1906年上半年,严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第一,学制上,以五年为限。头三年用于学习普通知识,后两年分政法、实业两科进行深入学习。毕业后保送至京师大学堂,表现优异者则派往欧美留学。第二,调整课程设置。基于以西学为主、兼顾中学的教育理念,西学作为五年内的主要学习内容,全部以外语教授。伦理道德、经学、国史、掌故等中学内容一律用国文教授,头两年后仅留月课,由学生自学。第三,调整师资构成。头两年教学先用本国人,而后三年由聘请的外国教员授课。第四,因材施教、分斋修业。鉴于学堂内待毕业学生较多,故分师范、预备两斋,分别为一年、五年为期毕业,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意愿选择修习。1906年下半年,严复继续进行校务改革。第一,由教员兼任斋、庶两长,缓和师生矛盾。第二,聘用若干英文教员、中学助教。第三,细化课程设置,以英文、数学等西学基础课为主,兼顾中学。第四,设立监膳官一名,另由学生推举两位董事参与食堂管理,以促进学校饮食卫生。此外,为了存优汰劣、端正学风,1906年底,严复对预备各班学生进行甄别考试,总共不到300人参加考试竟然有37人被淘汰,一时间,严复“手辣”之名传遍全城。对于教员严复也严加考校。他与教员一一面试,考察其授课能力和教学方法,将几名滥竽充数的东归教习辞退。经过这次淘汰,严复满意的说到:“本學堂經我秋間整頓之後,至今日有起色,學生亦肯用功,毫無風潮,皖人同聲傾服,至今唯恐吾之舍彼而去也。”[18]不过他也深知,这些被淘汰的教员和学生必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但为了学堂的长远发展,严复已经无暇顾及,恰如他所说的:“食人之祿,不能不任怨也。”[19]
1907年4月,安庆高等学堂开学,不仅增添了新校舍,学生人数也扩大到300名。正当严复擘画学堂新学期的发展蓝图时,5月24日,一场蓄谋已久的学潮爆发了,矛头直指以监督严复、斋务长周献琛为代表的所有闽籍教员。此时的严复正因过度操劳而肺炎复发、卧病上海。眼见学潮愈演愈烈,舆论又不辨真伪、煽风点火,安徽官绅不思平息事端、但求分肥。心灰意冷的严复坚决辞职,于6月7日乘船离开安庆。关于此次学潮的起因、经过,严复在《與沈曾植》、[20]《與安慶高等學堂》[14]249-253、《與甥女何紉蘭》[19]458等信件中已有说明,后世学者如皮厚锋在《严复的教育生涯》、[16]54-62沈寂在《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21]等文章中也进行了较为细致严谨地探讨,此处不再展开分析。
综上所述,监督安庆高等学堂期间,严复以自身的教育救国思想为蓝本,从学制、课程、师资、外语、考试、升学、留学以至于膳食等方面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堂的建设发展。然而,一场学潮终结了严复在安庆高等学堂的教育实践,这既是安徽教育界的损失,亦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之路步履艰难的生动写照。恰如严复后来满怀失望地感慨:“不佞所深恐無窮者,在今日通國之學務,安徽一隅,尤其小小耳!唉!”[14]253
(三)执掌北京大学
1898年、1902年,时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张百熙曾先后举荐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洋总教习,均因守旧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师大学堂原总监督劳乃宣反对共和,甘当清政府的殉葬品,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虽是临危受命,但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严复深感欣慰。3月8日,严复自天津抵京,正式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然而,刚一就职,经费不足的问题即迎面而来。民国政府初立,学部、度支部经费紧张不愿拨款相助;学堂存款又即将告罄。万般无奈之下,严复只得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重信任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白银7万两,暂时解决了开学经费问题,全校师生倍感振奋。随后,严复开始对学堂进行改革:第一,为了节省办学经费,除此前已签合同的洋教员继续执行合同,其他职员一律依照严格标准或续聘,或淘汰,共裁员20余人。第二,将全校所有科目进行调整合并,分为文、法、商、农、工等科,每科设学长一人,选取出洋毕业优等生担任,严复自兼文科学长。第三,调整课程设置。开设介绍近代西方文化学术的课程,推动西学教育;提倡外语教育,规定除中学课程以外全部用外语授课。“5月3日,袁世凯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为校长,仍以先生署理校长”。[7]318正当北京大学校教学工作正常开展时,6月初,财政部“以庫款支絀,通行京內外各衙門,凡薪水在六十元以下者,照舊支給;其在六十元以上者,一律暫支六十元”。为了稳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北京大学校全体教职工的情绪,严复亲自撰写《上大總統和教育部》一文,阐明限薪对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巨大影响,主张“學校性質與官署迥殊”,[22]教职工不应当被限薪。同时,为了表现对政令的服从,严复表示只要其他教职工薪水不变,情愿自己降薪至60元。在严复的据理力争之下,最终北京大学校全体职工薪水仍旧全额发放,避免了混乱。
然而,一波初平,一波又起。7月7日,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办学效果不佳、社会各界多有不满为由,突然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闻讯后异常气愤,甚至一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但为了保护北大,最终还是语重心长地向教育部条陈《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貼》,[23]从北京大学校的历史、西方各国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性等方面陈述北大不可停办的理由。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学效果,平息各方不满,严复又上呈《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貼》,[24]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如何整顿师生队伍以节省办学经费;如何培养本国师资力量;如何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文科、法科、理工科、农科、商科等学科的发展等。在包括严复在内的全体师生的坚决反对下,教育部权衡利弊,最终取消了停办北大的决定,北大再次逃过一劫。此后,北大回归正常教学秩序,逐步展现出生机。“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大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即其学历成绩被英国上述单位承认。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提高了。”[25]尽管办学效果逐步显现,严复却终因与教育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不得不于10月7日主动辞职,结束了他在北大短暂而又波澜迭起的办学经历,也结束了他的教育生涯。对于严复离开北大的原因、经过,严复在《與甥女何紉蘭》[19]468-469书信中有所说明,后世学者如皮厚锋在《严复的教育生涯》、[16]54-62张寄谦在《严复与北京大学》、[25]141-165尚小明在《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26]陈平原在《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27]等文章中已经做了较为深入而严谨的分析,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由上可知,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严复始终在为北大的继续存在和长远发展而四处奔走,他依据自己教育救国的具体主张对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使其走出旧式大学堂的阴霾而逐步转变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府,他“提出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思想,被后来的蔡元培校长发展为‘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28]为北大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学术、制度和精神基础。这既是对北大的保护,亦是严复在教育救国之路上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三个主要办学经历之间,严复还进行了其他一些践行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活动。譬如,1902年3月4日,严复接受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聘请,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任职期间,严复时刻以译书救国、启迪民智自勉,其所制定的《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29]极为重视教科书的翻译,对所翻译教科书的实用性、涉及科目、门类划分做了细致的规定。据统计,严复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两年间,译书局共翻译新式教科书达45种112册之多,[30]为各地新式学堂提供了急需的教学文本,促进了学堂教育的发展。同时,随着西学的逐步翻译引入,其中包含的大量术语在中国传统学术用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为避免民间私定标准引起混乱,1909年5月,学部尚书荣庆聘请严复担任审定名词馆总纂,“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6]1550。在严复的主持及亲力亲为之下,学部审定名词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据统计,名词馆审定的名词术语“约有30000条”之多,“涵盖22门学科”。“这些全新的、统一的名词术语,经中小学教科书而广为流传,不仅成为国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而且促使中国社会全新的文化符号环境形成,文化新陈代谢意义功不可没。”[30]30此外,严复还积极参与留学工作,1906-1908年间多次应邀主持各地留学生考试工作,几乎成了一名职业考官;献身社会教育,屡屡在各地演说,阐述自己的教育救国思想,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上海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商部高等实业学校等处都留下了严复的足迹;注重发展女学,不仅大力支持女弟子吕碧城创办女子教育会的举措,为《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还对甥女何纫兰创办女学的设想加以细化,在书信中为女校建设提出七条建议。[19]455-456
综上,从1879年9月回国到1912年10月离开北大,严复职业生涯基本都在教育界度过。任职于天津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除去日常教务还勤奋学习西学,钻研西方富强之本,终于在甲午战争后发出了自己的怒吼,提出了旨在自强保种的教育救国思想。此后,从发奋译书到参与创办《国闻报》、从总办天津俄文馆到协助创办通艺学堂、从主持复旦公学、监督安庆高等学堂到执掌北京大学,包括其他一些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严复始终在为促进中国的教育发展而大声疾呼、四处奔走。然而,起而执事不同于坐而论道,看似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常常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反复碰壁。严复在复旦公学、安庆高等学堂和北京大学等处的教育实践时间都不长,往往都是来去匆匆,坎坷不断。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包括: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重视西学学习;推行外语教学;精简学校机构、将主要经费投入教学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所在学校的发展,但与他所期望的通过教育实现民族自强的长远目标之间仍相距甚远。不过,“比照严复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强行’者。”[16]62他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和具体措施虽不是尽善尽美,其中却始终闪耀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教育救国的理论光芒。他的教育实践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启蒙。而他在教育领域所经受的一系列挫折,既源于社会局势的诡谲多变,亦与其清高自负的性格有关,更反映了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教育救国之路的曲折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