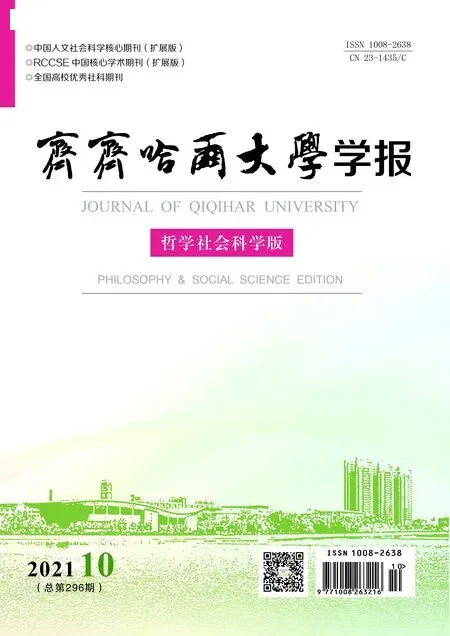“他者”目光与本土旨归
许 莹,崔 铮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晚清以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时代构筑起来的“上帝已死”的个体自由价值体系,无疑可以看作是一个体量巨大的“他者”,泛摄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审视侵袭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较早介绍诺贝尔奖的是《东方杂志》,先是1919年第16卷“内外时报”栏目刊载了袁同礼的《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一文,对诺贝尔奖进行了整体性介绍,其中文学奖的标准被翻译为“世界所公认之文学著作。足以表示理想之取向者。”[1]次年,该杂志又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本年度得奖者》介绍了当年获奖的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主编胡愈之也先后以“愈之”、“化鲁”之名,发表文章介绍近时期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由此看出诺贝尔奖评奖的国际性,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萧伯纳曾经造访中国,也使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诺贝尔文学奖威信最高,……其权威地位也是不容怀疑的。”[2](P41-43)如果我们以此奖项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世界性参照系是具备合理性的,并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中国从置换传统文学要素,希图获得“他者”认同,到当下所追求的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双向建构的发展途径就愈加清晰可见。
一、鲁迅的世界文学观念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段公案, 至今仍多次被学者提及,直至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对此事进行了相应的说明:首先,“他在中国1920和1930年代的文坛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鲁迅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第一,他的著作是他死后才译成外文,第二,没有人推荐他。”[3](P8-9)其次,“按照台静农先生的说法,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遇见鲁迅,就乘这个机会跟鲁迅单独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也许刘半农把鲁迅的回答传达给了赫文定先生。”[3](P8-9)这个说法我们在鲁迅给台静农的回信中,大致可以得到印证:
静农兄:
九月十七曰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4](P73-74)
鲁迅在这封信中谢辞了刘半农建议他参评诺贝尔文学奖的善意。在他看来,这是“为我,为中国”的决定;再则,鲁迅内心并不认为彼时的中国文学已达到获取世界性文学赏金的水平,包括梁启超在内。虽说鲁迅和梁启超都将文学当作“新民”的有效载体,但梁启超在译介作品时更加注重的是具有较强戏剧性的作品,而鲁迅对此是颇有微词的,“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换……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5](P472)鲁迅将翻译一些市民阶层阅读趣味,情节新奇,富有悬念的小说作品的翻译,看作是是一种不合时宜,隔靴挠痒的文化传播,因为这并非引发人们思考人生和民族未来的严肃作品,他更看重是那些包含反抗精神,科学态度的异质的外国作品。“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6](P105)与周作人在日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鲁迅吸收外国文学的重要实践和选择。但《域外小说集》实际上并不能代表鲁迅对外国文学作品接受的全体面貌,因为当时确实仍有他“想译,没有这力”[7](P282)的外国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就是荷兰作家望·蔼覃于1887年发表的作品《小约翰》。在1936年的时候,他仍然提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8](P33)“这是从他从事文学工作开始,三十年来一直爱好不释的一本书。”[9](P232)由此看来,鲁迅把《小约翰》放在了当时世界文学潮流的顶端,但同时他又放低了中国文学的位置,这并不是一种妄自菲薄的压抑,而是对刚刚形成的白话文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世纪情况一种自觉审慎的态度。鲁迅所追求的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的等量齐观。从鲁迅对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理性自省态度上来看,也正是由于鲁迅在吸取异域文学时,对于文学“他者”有意识地吸收和传播。“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中,从历史文化的深层透视文言文的惰性——对民族思维方式发展和民族智力水平的巨大阻滞作用的,鲁迅是第一人。”[10](P214)
对鲁迅来说,《小约翰》的价值不仅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象征写实底童话诗”;还在于它“实际和幻想的混合”,充满“人性的矛盾,而祸福纠缠的悲欢。”[7]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领略到由“璇儿”、“荣儿”牵领下的充满奇幻色彩的大自然,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平等交流,万物奏鸣的大自然要远比被人类物化的社会自然要丰富许多,然而,小约翰的内心仍然充满着对未来、对未知的种种疑惑和焦虑,被混沌、生死、城市、虚空这些关涉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问题困扰。这种既充满童真的梦幻感和难以掌控命运的无助感相互杂糅的悲剧性审美蕴藉是鲁迅所称道的。当然,鲁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取舍是有其特殊的标准的,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作品,都会获得鲁迅赞许,譬如,同样是描写个人心路历程与宗教忏悔精神的作品,他对但丁《神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王瑶先生对此曾做过出过精炼的评述:“因为‘<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而陀氏则‘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使他们什么都做不出来’,就是说,这类作品无论其艺术成就如何,那种对现实宗教的忍从和对不幸者的冷酷的态度,对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是没有帮助的。”[9](P207)可见,鲁迅对于以西方宗教关怀看待和克服人间苦难的隐忍忏悔的思想模式是拒斥的,鲁迅所推崇的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摩罗”精神,他认为中国人需要有在铁屋中呐喊的人,让人们从昏睡中醒来。不仅如此,鲁迅同样难以接受外国作家在创作中将宗教精神与中国现实的怪异结合,他对赛珍珠(即布克夫人)创作的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大地》里所体现的对土地与生俱来的热爱的情感颇有不满,他在给姚克的信中写道:“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既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12](P)在战乱不堪、革命呼啸的艰难岁月,追思形而上学意义,蕴含忏悔意识的史诗性作品在这一时期显然就缺乏生成的原动力,然则从民族心理学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上对“问题与主义”的关切又暗合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士情节和现世关怀。鲁迅通过译介外国作品以求获得异质文明的精髓,是循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偏至”态度而去的,他所寻求的是肯定个人价值,为被侮辱与被损害阶层振臂疾呼,敢于对社会不公平进行抗议披露的文学作品,对于拒绝受推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名利双至这种对外有选择地对文化“他者”的吸收和采纳,对本民族文化内涵自觉的反思和批判,在鲁迅的思维当中形成了一道有效的价值屏障,抵御了西方宗教思想的渗透,而着力于民族解放,人的觉醒的创造性书写,是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置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2](P57)的深致渴求。创作出充满科学精神和启蒙意义的《小约翰》的望·蔼覃在鲁迅心中是世界文学的巅峰,鲁迅自觉自己文学造诣无法与之比肩,同时也不愿因了自己是黄种人而获得有待,并时刻对用“软刀子”的方法来哄骗国人时刻保持的一种清醒和警惕,在上世纪的开端这位文化巨人留下的精神姿态仍然给予后人启迪与警醒。
二、新时期的自主对接
1984年,《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内部形式发行,该文集将有关国外现代小说创作技巧的讨论进行了全面收集和整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技法的争论,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对当下中国文学叙事技巧滞后的不安。由此引发了1985年文艺创作方法的讨论,文学史将之称作为新时期的方法年,紧接着的1986年则命名为观念年。“文学本体论”作为一种对马克思文艺理论核心观念“反映论”的反方代表,经孙绍振、鲁枢元及刘再复等学者的阐述,逐步实现了一种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体化文学的抵制,回归“人学”的有益尝试。[13](P55-58)作家对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手法的有意背弃,折射出作家寻求一条新型创作途径的心路历程。中国理论界和创作界通过具体的文本实践,力图拓展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元素。在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提到了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将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学翻译环节缺失影响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14]引起了文学界,翻译界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传播方式上的重视。马悦然访华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关键环节,通过马悦然的介绍,文学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价值有极高的赞誉,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作家在创作中对西方、拉美作家的借鉴问题,他认为中国作家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1987年,马悦然在接受采访中对文学的民族性持的是另一种看法:“民族形式的问题可以忘掉,可以不提了。我想,世界上各国的文学将来可以走一条路”[15]
先锋派作家余华的短篇小说《现实一种》对巴特“零度叙事”的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贯彻,在限制性的叙述视角营造出的自体抽离的悬空状态,小说的整体结构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余华在故事中设置了层层升级的血亲复仇链,身为父亲的兄弟二人山峰和山岗,因山岗儿子皮皮不慎导致山峰儿子的死亡,而开始进入一种冤怨相酬的毁灭模式。小说语义修辞当中“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蓄意断裂,是作家企图打造的一艘文本的“迷舟”,以种种似是而非的象征和隐喻游荡在文本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催生读者阅读过程中的阐释暧昧与意义晦涩。余华早期的短篇创作中除《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之外,《一九八六年》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作品,在篇幅不长的短篇当中,余华采以最冷漠的叙述刻画最疯癫的感官幻觉,塑造了一个因文革批斗导致家庭破裂,最后在疯狂中走向自我毁灭的男教师形象,余华采取一种幻觉与真实交替进行的叙事手法,更直观地展现出精神分裂患者感知世界的主观感受模式,更让人触目惊心的还有这个被非正常的社会运动迫害至心智失常后,男教师在幻觉中出现的一种自我镜像,历代各种酷刑在幻境中得以实现,而这些酷刑夹杂着某种历史的真实,读者可以凭借想象勾勒出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可能经历过的肉体和情深上的戕害。在创作的承袭中,中国作家无疑是将最新接受到的西方文学创作潮流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余华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16](P174)这种执着于叙事圈套的设置也正是对程式化的情节冲突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种全方位的解构,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从时代与文学之间互动的关系来看,这些西方技法的吸收和借鉴正是对左倾文学的一种全面批判。
贾平凹试图回避外国文学对于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他古韵备至的文字下,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作家在一些人类的基本生存本能刻画上对西方精神元素的借鉴,这种借鉴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寻找,“读二十世纪以来的作品……汲取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新的思维”。[17](P301)与牛月清、婉儿、阿灿等不同女性之间淋漓尽致的欢爱场景描写,是作家迎合市场的文学形而下运动的实质呈现。尽管在物质与权力人性的腐蚀和异化的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批判态度。但是从审美的接受经验上来看,读者接收到的仅仅是一种叙事空间的离奇铺陈,以及各式人物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行动,以及这些行动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但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象却在行动的渲染下,被遮蔽被解构。故事的结尾通过报纸上新闻报道的方式,读者和庄之蝶一起发现了阿灿自慰死于性高潮的轰动性报道,医院诞生了一个有头无四肢,透明如蝉蛹的婴儿,这与小说开头出现的西京四日的场面相互交映,让读者犹如置身于一个没有已经失去未来可能性的废都之中。学者王彬彬曾经指出新时期以来的作家擅长一种恶的写作,让人仿佛置身于垃圾场和屠宰场。[18](P34-43)新时期作家可以集体发出恶声,一方面是由于建国以来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片面性和遮盖性,忽略了人性当中事实上存在的一种原初的兽性之恶,另一方面也与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有密切的联系,萨特,加缪、卡夫卡等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流行,给中国作家带了很大启示。
三、现代性与传统回归
诺贝尔文学奖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并不能显示中国文学当下的成功,而是作为“他者”的西方对中国文学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自主性建构的认同与接纳。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已然脱离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限制。1988年山东举办了一次关于莫言创作的研讨会,莫言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房赋闲所写的综述上看,当时评论主要聚焦于莫言小说创作形式和内容上探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莫言创作中大量形式与内容上所体现出的“丑”,对于莫言作品中大量以“丑”入文的表现形式,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种“丑”恰恰就是直面生存苦难,不回避痛苦,张扬现代精神,“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导性美学流向”。[19](P101)莫言在研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把丑写褂那样淋演尽致?就是为了强化个性意识。……文学为民请命当然好,但文学不是为了拯救万民,而是为了拯救自己。正是在思想痛苦的挣扎中,才有了我。如果我个人的痛苦矛盾和时代的痛苦一致,我就有前途,发泄得越厉害,便越有前途。我不想解脱自己的矛后和痛苦,而只想把它们深化下去。”[19](P102)这段发言表露出了莫言在早期创作当中彰显个体意识反叛传统伦理的创作意图,他尝试将意识流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引入中国的文学创作,试图将这种“他者”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社会现实进行融合,形成本体与他者之间具有张力的关系,但是早期创作当中,福克纳和加西亚这“两座灼热的熔炉”仍然是莫言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里提道:“我当然不否认上列的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皇皇巨作里那样一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20](P4-5)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形成井喷的现象,显示出精英作家们渴望用长篇小说来反映中华民族心灵秘史的雄心和抱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阿来等作品以不同视角勾勒出中国人民近百年的精神图景,形成了一种对民族历史的想象式回溯,但是在这些作家当中,莫言无疑是最具备“想象视野。①他对现代汉语言的应用已经到达了一种畸形而又庄严的边际,正所谓“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作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绝对不仁不义的造物主,他必须克制自身情感对文本的介入,以使艺术本质从遮蔽之中解放出,达到人物与情节最真实的浮现。例如,莫言的作品《檀香刑》中,主人公孙丙因妻子被德国兵侮辱,家乡受到德军侵犯而奋起反抗,然而真正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以及那个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底层的乡间民众,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就被以“谋逆”之名,处以最残酷的刑罚!荒唐时代造就的灾难却要无辜的人去承受,甚至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样一个本已沾血带泪的民间故事往往会让创作者充满感性情感而失去理性节制,而莫言仍然以极强的全局把控力,控制着小说的整体节奏。在谈“极刑”时,叙述者借用刽子手赵甲之口,将其描绘的绘声绘色云淡风轻——被腰斩之人像蜻蜓一样对着自己被切割走的另一半身躯扑腾;受檀香刑的人,檀香木由身体谷门穿透身体,因失血少可以熬得久一点才死亡,居然还打算给受刑者喝参汤补一补,能活的更久些,痛感能更钝重些;这些手段极其残忍的刑罚,在赵甲的叙述中充满强烈的感觉冲击力,不仅如此赵甲还为自己是刽子手职业技能最强的人而接受了大清朝老佛爷和皇上接见而感到骄傲。整个描写过程中,作家并没有对于极刑和是非进行任何道德判断,反而配合与地方戏曲茂腔的戏文对唱,营造出一种戏中戏,剧中剧的“看热闹”似的效果。
在完成《檀香刑》创作后,莫言认为这是自己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莫言又说道:“我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21](P418)以反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热”文学作品《蛙》为例,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执行者,对当地女性自然生育采取的铁腕干预的政策,导致无辜妇女命丧产床,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开始反省中国计划生育二十年的惨痛历程,特别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落后认识与铁的政策的双重负担下,女性在当代社会再一次成为陋俗与制度的牺牲品,莫言以一幕幕血淋淋的描写祭奠那些无辜逝去的灵魂,他以梦幻现实的手法真切切反映出了中国的现实伤痛,将制度之恶,平庸之罪进行示众。
回归传统的莫言,将80年代在空旷的荒原与广场游荡的个体,拉回到了中国乡间的公堂庙宇。他如沙场秋点兵的将帅,指挥着脑海中的人物,他直面人性中丑恶卑鄙,自私自利的罪的一面,让他们伴随着夸张变形的民间戏曲出场,接受化身为命运的小说家的审判和裁决。最后,作家借蝌蚪之口宣判“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技术借鉴的同时进一步回归传统,使依赖本土精神资源的小说创作具备世界文学的属性,让异域文化的读者可以读懂莫言所讲述的故事,莫言用独特的乡土方言模式勾勒出中国世纪变迁下,形形色色人物的爱欲纠缠,生死离合。对于莫言创作最核心的特质,瑞典文学院给出了词组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应该说这个词的重点在于“幻觉”,并且这种幻觉更多的是由创作者主体经验对于客观事实的蓄意夸张而产生的,瑞典文学院认可的是莫言对中国历史现实的个性化叙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在叙事技法上提升所作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认可。
莫言获奖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绝不仅仅在文学范围内,“对中国文学界乃至知识界和民意社会来说,令人惊诧的是,环绕着莫言的获奖,居然发生了如此歧义、分裂、对立的立场和舆论现象———甚至说是社会的撕裂也不过分!”[22](P22)经过百年积淀,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已不容质疑,虽然政治视阈从不曾离去,但是它必然带着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审视世界文学,多元的民族性和人类的共存性应该如何找到结合点,这仍然是各民族文学创作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间最微妙的博弈。目前,中国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后莫言时代”,也许我们都清楚文学可以实现心灵的自由,却难以实现真实社会中的自由,精神可以拯救自省的灵魂,却唤不醒装睡的大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整个社会身份认同的巨大隐喻,在接受西方的文明的同时,民族记忆深处最深的潜意识仍然在暗中发挥着它强大的规约性,无论是鲁迅的否定传统,高行健的身份回归,还是莫言的双向建构,都无法摆脱几千年中华文明在其身上潜藏的印记。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历史言说不充分之处展开其无限可能,并获得了阐释这个民族社会历史的能量,并为后人的前进提供者“切实的指示”。
注释:
李欧梵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人文六讲》中说:"中国当代小说,在幻想的层面似乎比不上南美和印度作家,也许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宗教成分较为薄弱,魅力不足,志怪和《聊斋志异》的传统,始终不能转化到当代写实小说之中,我认为是一件憾事。";刘再复在《莫言的腰撼与启迪刘再复-从李欧梵的<人文六讲>谈起》一文中将其归纳为"想象视野"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