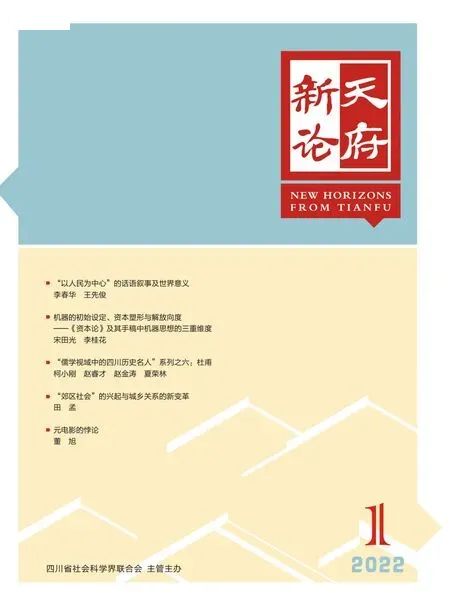说真话与“不安伦理学”
——重新思考晚期福柯的主体观念
王苍龙
“说真话”是福柯生命最后几年学术研究的主题,在其整个思想生涯中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就福柯一生思想的三个关键词——知识、权力和主体而言,对主体问题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体现在福柯晚年对“说真话的主体”这个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我们从福柯中后期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中可以发现,福柯在讨论“说真话”之前,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集中讨论了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问题。因此,他对说真话主体的探讨,其实非常明确地针对着被生命政治权力技术化了的现代主体。可以说,说真话的主体寄托着福柯对一种自我风格化的主体的期待。
“主体”是贯穿福柯学术研究的总主题。如果说福柯早中期的学术生涯旨在揭示区分、干预和控制主体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机制的话,那么晚期福柯则转而关注主体如何作用于自身以形塑自我。对此,福柯说道: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这整个20年期间,我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它既不是对权力现象进行分析,也不是精心描绘出这种分析的各种基础。相反,我的目的是创建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被塑造成各种主体。(1)福柯:《主体和权力》,汪民安编:《自我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
福柯概括了三种把人变成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第一种是质询模式,主体借此把科学地位赋予自己;第二种是区分实践,既包括主体与自我的区分,也包括主体与他人的区分;第三种是“人使自己变为一个主体的方式”。(2)福柯:《主体和权力》,汪民安编:《自我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7-108页。福柯对“说真话”的探讨应该放在第三种主体塑造模式中,其核心在于主体如何通过说关于自身的真话而把自己建构为真理的主体。“我试图以另一种形式来加以审视,”福柯说:“(……)主体可能且能够说出的关于自身真相的话语,可以采取一些文化上得到承认且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如‘承认’、‘忏悔’、‘自省’等。”(3)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第24-26页,第31-39页。他强调,真正需要分析的并不是作为真话的话语本身,“而是在说真话的行为中,个人通过何种形式建构了自己,且被他人建构为说真话的主体”(4)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第24-26页,第31-39页。。
鉴于此,本文意在切入对福柯“说真话”问题的探讨。国内学界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出现一些探讨福柯晚期思想的文章。(5)参见朱雯琤:《“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王辉:《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4期。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6)本文所参考的外文文献主要是英语文献。虽然这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翻译问题,但基于以下四个理由,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影响是可控的,且引用英语文献亦有必要性。第一,尽管福柯原著多以法语面世,但大都很快被译成英语,进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第二,很多法语的福柯研究专著也被及时译成英语,促使英语世界对福柯思想的研究是及时跟进的;第三,由于前述两点,英语世界已经涌现出大量高质量的福柯研究,而这些研究的价值仍有待中文学界关注和探讨;第四,本文关注福柯后期思想,而福柯本人在后期也尝试直接用英语演讲或接受采访。,旨在通过回应以下三个问题以推进当前对该主题的研究:第一,福柯是怎么讨论“说真话”的?第二,如何在福柯总体思想框架里理解“说真话”问题?第三,“说真话”问题反映了福柯怎样的主体伦理学?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探讨。
一、说真话:作为伦理实践的直言与“真的生活”
关于真理及其言说,福柯在其学术生涯中经历了几次焦点转移:先是从对真理的关注转移到对真理言说者的关注,之后再转移到对说真话活动的关注。对说真话活动的关注,代表作品是福柯1983年的伯克利课程和1983—1984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在这些作品中,福柯阐明了一种探讨真理政治的新方式——直言(parrhesia)实践。他通过对古希腊文本的分析,讨论了直言在政治自由中的作用,特别是说真话活动如何介入主体形成。何谓“直言”?从词源来看,“直言”指的是某种说出一切的活动,“直言者”(parresiaste)指说出一切的人。福柯所论“直言”,意思是“说真话,不加掩饰、毫无保留、不打官腔、不加修辞”(7)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第24-26页,第31-39页。。福柯指出,直言是古希腊伦理学中四种说真话模式中的一种,另外三种分别为预言者模式、智者模式和教师模式。在古希腊文明中,这四种说真话模式常常混在一起;但在现代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模式已经消失,被嫁接于其他三种模式之上。(8)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第24-26页,第31-39页。
福柯认为,“直言”实践在公元前4世纪发生过一次根本转变——从根据城邦民主体制确定的一项公民身份权利转化为根据个人的内心、品行和道德素养确定的伦理实践。这一转变根源于一场直言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古希腊城邦民主体制存在一种结构性缺陷,即缺乏一种在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好人和坏人、最优秀的人和最差的人之间作出恰当的伦理区分(ethical differentiation)的机制,因而无法为说真话留足空间,甚至无法分辨真话和假话。(9)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第24-26页,第31-39页。换言之,民主体制阻碍了说真话的实践,导致民主走向反面。另一方面,君主制由于制度性地接纳了伦理区分原则而使直言成为可能。专制体系之所以为直言留有一席之地,是因为谋臣有机会劝说或教育君主的内心,通过说真话对其进行伦理教化,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从而使他们内心能够倾听真话,并以真话为准绳调整自身的行为”(10)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0页,第183-187页。。而且,由于君主制下对城邦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自身的品行和伦理,因此君主本人也倾向于接受来自谋臣们的真话。
由此可见,福柯对直言问题的阐述突出了道德伦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甚至把伦理向度视为区分不同政治体系的结构性要素。是否存在伦理区分,是民主制和君主制在说真话模式上的关键区别。自危机之后,说真话不再只是一项针对城邦政治的公民权利(民主制度领域),而变成一项指向个人内心和品行的伦理实践(个人道德领域)。由此,直言者自主地实践一种伦理的自我治理模式(model of ethical self-governance),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为伦理主体。(11)Luxon, N.,“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而且,面对潜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直言者的自我治理艺术有助于其养成一种“稳健的性情” (disposition to steadiness),使他们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处事方式,始终如一地对自己和对他人保持真实。(12)Luxon, N.,“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
作为伦理实践的直言,最典型的例子是苏格拉底。通过分析苏格拉底之死,福柯指出伦理直言的核心是自我关怀,即操心自己的理性和真相,关怀自己的灵魂和内心。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他没有从政是因为从政者往往能言善辩,而这会导致他们忘记自己是谁;苏格拉底拒绝从政,从而得以始终以简洁、直接、毫无修饰的方式说真话。苏格拉底敢于直面说真话带来的死亡危险,因为他声称是神灵赋予他说真话的义务;面临神灵的话语,他通过责问、批判和讨论的方式考察人们的内心,考验他们的灵魂,促使人们自己关怀自己。在《裴多篇》里,福柯分析苏格拉底在临终遗言里提醒门徒必须给神灵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公鸡,指出这里的隐喻是提醒门徒不要疏忽对自己的关怀和对内心的照管。总之,苏格拉底之死确立了一种伦理的、哲学的说真话模式,这是一种充满勇气、考验灵魂的直言,最终目标是帮助人们关怀自己的内心。在这一主体与真理的自我治理模式中,直言者实践并获得一种存在的自由和自主的意志,他们勇敢地讲出自己笃信的真理,坦然面对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关怀自我中实现自由的本质。(13)Luxon, N.,“Truthfulness, Risk, and Trust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 Inquiry, No.5, 2004, pp.464-489.
福柯认为,伦理直言指向一种自我风格化的生命美学,其隐含的自我关怀的主题将生命与真理的关系引向一种“真的生活”实践。所谓“真的生活”,是一种没有任何隐藏和混杂、正直的、保持自我一致性的生活。(14)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0页,第183-187页。对此,福柯探讨了犬儒者如何实践“真的生活”伦理。他指出犬儒生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犬儒生活的真实性在于,他们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掩饰因而不会为任何事感到脸红的生活,并把自己的生活坦然地置于他人的目光和自己内在的目光之下。第二,犬儒者们过着一种与自身完全统一、与所有事物保持距离、自我依赖、自我满足、自给自足的生存风格;这一生活原则表现出来的形象是贫穷,而犬儒者们的贫穷是现实的、主动的和无限的。第三,犬儒生活是一种善于分辨善恶、真假和敌我的正直生活,符合自然法原则。第四,犬儒生活是一种自主生活。一方面,主体全部占有自我,整个生命都属于自己,快乐要在自己身上寻找;另一方面,出于责任感和义务感,主体要与他人乃至全人类建立关系并增进他们的福祉。总之,犬儒者所实践的并不是学说传统而是生活传统;其历史价值在于作为一种显现真实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通过犬儒主义,福柯呈现出一种实践自我真理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一种生活形式、存在模式和生命风格的历史。
二、说真话与福柯的思想总体
在阐明了福柯对“说真话”问题的基本观点后,这个部分将转入第二个问题: “说真话”主题在福柯的总体思想框架里处于什么位置?笔者认为,福柯对“说真话”的探讨并不是其思想总体的断裂,而是深植于他的思想总体。一方面,知识、权力和主体构成了福柯思想体系的三角形,与之对应的分别是对说真话方式、治理术形式和自我实践技术的批判分析。这三个基本面相互建构、不可化约,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单一而平行的研究,提问任何一面都必然关联另外两面。正是在这个总体框架中,福柯以直言为切入点开展了真理与主体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福柯对直言的讨论并不限于话语领域,亦涉及生活领域;伦理区分原则是苏格拉底式直言和犬儒主义直言的根本立足点。对此,我们仍然要从福柯的总体理论框架出发来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福柯逐渐把康德之后的思想发展区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先验向度,意在确定真理的形式条件,对应的问题是“我可以知道什么”;另一个是批判向度,意在确定对人的治理的条件,对应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被治理的”。(15)格罗:《授课情况简介》,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6页。对直言的讨论让福柯发现了伦理向度,意在确定真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丰富了他的理论体系,而且提出了一个关乎福柯晚期思想脉络的关键问题——有哪些主体化模式可以与对人的治理形式相联结,以抵抗或进入权力关系?事实上,福柯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努力在“哲学作为理性学问”和“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之间寻求平衡,并且倾向于把知识视为一种达致“真的生活”的风格学。
因此, “说真话”主题是福柯思想脉络在其生命晚期的一个延续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晚期福柯转向直言主题并非无章可循。在早期探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时,福柯就已经暗含了伦理取向,这些探索让他关注治理艺术,分析和批判现代主体的历史性构成。根据凯文·乔布(Kevin Jobe)的归纳,从1977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开始直到1984年去世,福柯的思想经历了三个关键转型:一是从牧领权力转向精神导引;二是从精神导引转向直言;三是从直言转向“政治学”游戏。(16)Jobe, K.,“Foucault and the Telos of Power”,Critical Horizons, No.3, 2017, pp.191-213.
第一个转型发生于1978—1982年,福柯在这个阶段区分了牧领权力/控制与意志形成/导引这两组主题。(17)Patton, P.,“Foucault and the Strategic Model of Power”,Critical Horizons, No.1, 2014, pp.14-27.早在1977—1978年的课程《安全、领土、人口》(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中,福柯就专门论述了精神导引实践,包括基督教洗礼、忏悔和教学法等,但并不把它们视为行动者的自愿行为,而是义务和服从,因此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牧领权力的治理术,通过引领个体的精神世界而使个体完全顺从于牧领者的命令和他者的意志。(18)Foucault, M.,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78,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175-179.在1979—1980年的课程《对活人的治理》(OnTheGovernmentoftheLiving)中,福柯进一步把权力理解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治理,亦即“一些机制和程序,目的是引导人们,指引他们的行为,导引他们的行动方式”(19)Foucault, M.,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9—8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2, p.255..。在该课程中,福柯区分了精神指引实践的内在目标与牧领权力强加的外在目标,前者是一个自愿的主体化过程,后者指个体对他者意志的屈服。这是一个重要区分,它给福柯后期思想带来了一个根本变化,即福柯不再认为个体内在的精神导引实践必然伴随外在权力的干涉、强制和限制;恰恰相反,个体可以自主地导引、学习和观察自己的行为。(20)Foucault, M.,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9—8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2, p.255..
基于此,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福柯为何转向直言主题(上述第二个转型)。事实上,福柯早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就强调,分析个体与集体的意志之形成对于研究牧领权力的谱系学意义重大。(21)Foucault, M., “What Is Critique?” In S. Lotringer and L. Hochroth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New York: Semiotext(e), 1997, p.76.之后,福柯在1979—1980年的课程中进一步凸显了主体自决意志的重要性,把精神导引实践视为一种坦率或讲真话的艺术,这为后来的直言主题埋下伏笔。在1982—1983年《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TheGovernmentofSelfandOthers)的课程中,福柯提出,直言在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模式,主体之所以直言并不是为了某些外在的策略性目标,而是其内在意志、伦理承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使然。(22)Foucault, M.,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2—83,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56, p.159.因此,直言并不是权力本身的运作,而是主体作用于自己和他人的自主的道德行动。(23)Jobe, K.,“Foucault and the Telos of Power,” Critical Horizons,No.3, 2017,p.201, pp.191-213.这一点在1984年《说真话的勇气》课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福柯看来,不论是苏格拉底式直言还是犬儒者的说真话模式,皆非主体的被迫行为,而是其自发、自主、自觉的行动;直言者并不受制于外在权力关系,而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和神灵的旨意。这样的直言模式是个体的伦理实践,一种“自由中的实践”(practices in liberty)(24)Luxon, N.,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 pp.377-402.,pp.377-402, pp.341-343.,主体通过说真话以捍卫自己的意志自由。由此可见,福柯在后期摆脱了认知主体的框架,不只关注知识和话语;而且发展出一种以伦理主体为核心的治理艺术,它指向实践和生活,注重主体与自身、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于是,主体形成一种稳健的性情,采取一系列具体策略去实践这一伦理的自我治理,并且最终取代规训治理术。(25)Luxon, N.,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 pp.377-402.,pp.377-402, pp.341-343.
更进一步,福柯对直言转换的阐述意味着其后期思想演变的第三次转型——从直言转向“政治学”游戏。(26)Jobe, K.,“Foucault and the Telos of Power,” Critical Horizons,No.3, 2017,p.201, pp.191-213.在福柯看来,直言最初是一种“政治的”(political)观念,即植根于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实践,是一种法律的、制度的公民权利;但后来变成政治学(politics)领域中的一种伦理实践,一种自由的、勇敢的个体行为,个体通过说出真话而劝说和导引他人。(27)Foucault, M.,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2—8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58. 在这里,福柯区分了所谓“政治的”与“政治学”这两个概念——前者与宪政合法性、司法主权、公民权利挂钩;后者不必与此挂钩,而主要涉及主体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伦理联结。因此,直言从作为公民权利转向作为个体伦理,意味着直言从作为“政治的”观念转向作为“政治学”场域里的游戏,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寓含伦理区分。所以,要真正理解直言概念,需要把它置于“作为游戏和体验的政治学的系谱学”(28)Foucault, M.,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2—83,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56, p.159.加以分析。虽然伦理的自我教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行动和公共参与,但前者可以为后者做准备,因为如果个体具备高度的伦理道德反思能力,那么他/她就更有潜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主和自控。(29)Luxon, N.,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 pp.377-402.,pp.377-402, pp.341-343.另外,直言的政治学为我们理解福柯的其他概念打开了视野。例如,福柯指出,围绕直言概念,治理术问题得以出现和构型,“权力在真理话语中运作”(30)Luxon, N.,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 pp.377-402, pp.377-402.,pp.377-402, pp.341-343.。再如,以直言为视角,权力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学”游戏、一种植根于社会联结中的行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行动者引导他人行为而无需诉诸法律或暴力;而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注定只是一个抽象概念。(31)Foucault, M.,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No.4,1982,pp.341-343.
三、“不安伦理学”与说真话的主体
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 “说真话”是一种主体作用于自身的伦理行为,其核心在于主体与自己以及他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 “说真话”的主题指向了一种福柯式的伦理学。对此,笔者将转向对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说真话”反映了福柯怎样的主体伦理学?笔者认为, “说真话”是福柯“不安伦理学”(ethics of discomfort)的一部分,而该伦理学之产生与发展贯穿福柯思想的学术生涯。所谓“不安伦理学”,根据鲍尔(Stephen Ball)的概括,指的是一种我们与自身及其存在模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我们需要理解自己在知识/权力中的构成,学习我们自身的限度,懂得我们的生存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和撤销;总之,这是一种主体自身的历史本体论。(32)Ball, S.,Foucault as Educator,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35, p.36, p.38.我们可以把“不安伦理学”视为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谓的“伦理暴力”(ethical violence)(33)Butler, J.,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的一种形式。对此,艾伦(A. Allen)解释道:
我们必须探索与现状有关的反常性、黑白颠倒和愤世嫉俗。我们应该矫正自己良善但浅薄的承诺。要想反抗,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不安。反抗是一种严厉的责难体验,反抗者自始至终都感到心神不宁。(34)Allen, A., Benign Violence: Education in and beyond the Age of Reason,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50.
“不安伦理学”意味着一种内心不安的失稳体验,其核心是挑战和反抗所有外加于主体的权力关系。由于我们正是权力关系所造就的,所以反抗权力关系意味着创造我们之存在模式的新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有限度的,承认有一个外部空间(35)Falzon, C., Foucault and Social Dialogue: Beyond Frag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4.;在那里,我们可以实践“自愿不服从”(voluntary insubordination)的艺术,学习如何才能摆脱某种被治理的方式,从而获致新的自由形式和自由体验。(36)Ball, S.,Foucault as Educator,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35, p.36, p.38.“不安伦理学”指向一种主体对自身正确性的怀疑,它要求我们抛弃掉本质主义的、固定不变的存在模式,恢复我们自身的流动性和可更改性。(37)Foucault, M.,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Lectures at Dartmouth College, 198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129.
“不安伦理学”要求主体对自身采用一系列自我技术,尤其是批判技术。在福柯看来,批判是一种伦理态度,既面向内部也面向外部;它要求主体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存在模式和行动路径,质疑看上去中立的制度结构及其对主体的限制,揭示并反抗以隐蔽的方式作用于主体的政治暴力。(38)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4, p.171.批判的主体是一个倔强的、不服从的、难以管治的主体,它对权力关系抱有永恒的怀疑倾向,对治理技艺如何发挥作用充满长久的好奇心,对自身的限度怀有深刻的反省。(39)Rabinow, P., The Foucault Reader,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39, p.46.福柯对批判态度的观点与他对启蒙的理解有关。福柯对启蒙持有一种矛盾立场。(40)Ball, S.,Foucault as Educator,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35, p.36, p.38.一方面,福柯把启蒙时代理解为一个被人文科学主导的时代,充斥着对人的规训和规范化、对身体和灵魂的监控、对不正常群体的边缘化和排斥的知识;另一方面,面对专横暴虐的启蒙理性,福柯主张用永久的偶然性取代康德的普遍主义,承认所有真理的本质是一种历史偶然。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作为一种伦理实践关乎我们如何历史地构成我们自身——它使我们从我们所是的存在模式中解脱出来,为有限度的生命打开新的可能空间;它要求我们对塑造我们的情境、结构和关系进行历史调查,把我们识别为此时此地所思、所做、所言的主体。(41)Rabinow, P., The Foucault Reader,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39, p.46.
具有批判态度的主体必然是不安的:一方面,批判实践使主体意识到自己比想象的更加自由,进而为创造新的生命态度和审美政治敞开大门;另一方面,批判实践导致真正的生存模式不再是绝对的、本质的,而是呈现为一种动态的、流变的状态。当批判的主体试图说出关于自身的真话时,它不得不在下面两者之间反复挣扎:一是与自己所在的真理政体保持批判关系,二是必须讲述自身的真实性。(42)Ball, S., Foucault as Educator,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52, pp.53-54.因此,说真话的主体必须适应不安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既不可避免也十分必要。主体说真话,亦在实践不安的伦理学。这意味着,说真话的主体不会对自己的主观假设感到心安理得,也不会因为一个新出现的事实就推翻这些假设,更不会允许自己随意更改这些假设;恰恰相反,它会对司空见惯的东西保持警觉,对每一个确定性后面所隐藏的未知进行拷问。(43)Zembylas, M.,“‘Pedagogy of Discomfort’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s: The Tensions of Ethical Violence in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Ethics and Education, No.2, 2015, p.166.福柯的目的是把不安的表征进行问题化而不是把它描绘为不诚实或怯懦的行为,从而打开行动的空间而不至于滑入预言性的情境。这样的主体既非单一主体也非本质主体,而是作为权力效果的个体。(44)Foucault, M.,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98.说真话的主体敢于违犯既定的规则,通过采取一系列策略性的微小行动和短暂侵犯,使主体的限度变得清晰可见,从而动摇传统习俗,开创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说真话的主体还是“不安伦理学”,福柯讨论它们时都有一个现实的比照,即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西方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治理的场所同时也是拒绝和批判发生的场所,进而也是主体性生成的场所,也就是反抗我们之所是、拒绝我们之所非的场所。(45)Ball, S., Foucault as Educator,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52, pp.53-54.在这种现代治理形式的政治中,拒绝成为主体重要的自我技术——通过拒绝迎合现代启蒙的政治感受,伦理主体被一种不安感围绕,力图超越常识,超越想象力的边界,超越所能言说的范畴的极限。(46)Falzon, C., Foucault and Social Dialogue: Beyond Frag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1, p.39, p.56.这不是自我否决,而是“我们自己与他人的遭遇”(47)Falzon, C., Foucault and Social Dialogue: Beyond Frag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1, p.39, p.56.,是建立在创造性活动和违犯行为基础上的对话,进而在我们存在的边缘地带产生出新的、未预期的东西。(48)Falzon, C., Foucault and Social Dialogue: Beyond Frag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1, p.39, p.56.更进一步,主体通过拒绝、反抗、批评和违犯等技术发展出一种自我政治学,指向对自我的关怀和持久的拷问。正如福柯所言:“批评是主体赋予自己权利以质疑权力效果的真理性、质疑真理话语的权力的运动。批评是一种自愿不服从的艺术,是一种反思不顺从的技术。”(49)Foucault, M.,“What Is Critique?” In S. Lotringer and L. Hochroth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New York: Semiotext(e), 1997, p.388.主体性存在于权力策略和反抗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它创造了关于真实自我的新表述,阐明了自我构成的局限性,并使我们的自我构成变得可疑。总之,一个人只是他与真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塑造并给予了主体生命。(50)Blacker, D., “Intellectuals at Work and in Power: Towards a Foucauldian Research Ethic,” In T. Popkewitz and M. Brennan (ed.), Foucault’s Challenge: Discours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Education,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p.71.
四、结 语
本文针对福柯“说真话”的主题尝试回应了三个问题。
首先,福柯对直言的讨论侧重伦理维度。他阐明了古希腊民主直言向伦理直言(包括苏格拉底式直言和犬儒主义直言)的转变,突出了对伦理区分原则的关注。由此,福柯指出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由于缺乏伦理区分的制度空间,所以民主政治无法在卓越的政治领袖与平庸的社会公众之间划出伦理边界,也无法界定两者的道德差异,最终只能导致坏的治理。
其次,“说真话”问题是福柯思想脉络在晚期的一个延续性发展,是其思想焦点的一次调整而非断裂。从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中探讨各种把人变成知识和分类体系客体的现代性场所,到在《性史》(HistoryofSexuality)中探讨人可以面对权力说出真理进而把自己塑造成为政治主体,再到作为伦理实践的说真话行为,福柯的思想焦点一直在转变,但每个焦点之间都有内在关联。正如福柯自己所解释的,他的思想变化始终指向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在早期思想中,他从强制实践和科学话语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关系;而在后期思想中,他转而从自我构成的审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审美”指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训练,个体由此发展和转化自己,达到某种存在模式”(51)Foucault, Michel,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ondon: Penguin, 1997, p.282.。
最后,“说真话”问题是福柯一以贯之发展的“不安伦理学”的一个体现,反映了他批判的、拒绝的、反抗的、违犯的主体观念。 “不安伦理学”是一种主体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它要求主体适应因反抗外来权力、实践自愿不服从艺术而产生的内心不安体验,通过批判、拒绝等反行为打破本质主义的存在模式,恢复动态变化的生命状态。说真话的主体必然是不安的主体,主体通过说真话而实践“不安伦理学”。
总之,直言是主体的真理实践,是伦理的自我治理模式。通过勇敢地说出真话,个体把自己发展为“敢于行动”(dare to act)的伦理主体(52)Luxon, N., “Ethics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s of Self-Governance in the Late Lectures of Michel Foucault,” Political Theory, No.3, 2008,pp.377-402.,学习如何关怀自己的心灵,并过一种言行一致的“真的生活”。然而, “真的生活”不是现成的,它作为另一种生活必然是非同寻常乃至异类的,因此要求对现存生活进行改造和革新。结果,真理的主体会教化自我以培养一种“异”和“非凡”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美学。言及此,不妨以福柯在最后一次课的书稿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福柯如是说道:“如果没有对异的本质态度,就不会建立起真理;真理从来就不是同一(meme);只有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形式中才能有真理。”(53)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