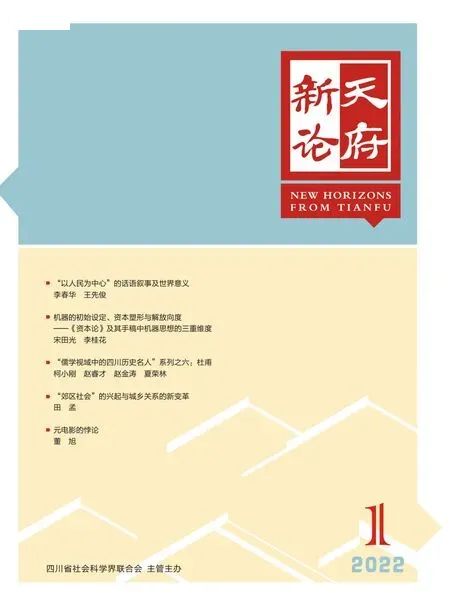杜甫人格论
——以“五伦”关系为中心
赵睿才 赵金涛 夏荣林
人格是“源于个体身上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1)杰瑞·伯格:《人格心理学》(第七版),陈会昌等译,中国轻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杜甫人格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样子?其内部过程是怎样运行的?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洪业先生说,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实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2)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第1页。。不论是从“天伦”关系看,还是从“人伦”关系看,杜甫都堪称典范,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昭示着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
“五伦”是人与人之间五种基本的道德关系及其相应道德规范的统称。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滕文公章句上》,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705页。“五伦”就是五爱:亲子之间为慈爱,夫妻之间为挚爱,兄弟之间为友爱,朋友之间为信爱,君臣之间为忠爱。当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4)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第1页。,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哲学家将其置于最高殿堂的原因所在。唐君毅先生说:“吾人道德生活中最大之问题,盖在吾人如何知一至当不易的表现仁义礼智之特殊方式。”(5)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杜甫以他的诗歌找到了这一“特殊方式”。洪业先生认为:“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6)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人格力量无疑是重要的。“人格评价是人格研究的核心。”(7)杰瑞·伯格:《人格心理学》(第七版),陈会昌等译,中国轻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人格研究的方式有多种,本文集中以“五伦”关系来研究杜甫的人格。
一、君仁臣忠关系中的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理想人格,不仅停留在先哲们的言论中,更体现在具体的为人风格上。在古代中国,有一些人一生都在践行君子人格,自己最终也成为一名真正的君子,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位。君子人格思想最早出现在《周易》中,指的是一种道德人格,如《周易·乾卦·文言》释卦辞“元亨利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8)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5页。此四德是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孟子概括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9)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691页。汉儒董仲舒又加上了“信”,是谓“五常”。“五常”的介入极大丰富了人伦关系的道德内涵,一定程度上缓和乃至消弭了人际关系中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紧张。杜诗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某种象征,其第一要义即“仁者心”。杜甫的《过津口》直契孟子,其中有云:“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10)本文所引杜诗均出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以下不另出注。常存恻隐之心的伟大诗人并不孤独,他的每一根生命之丝,都绵绵延伸出去,与其他生命之丝发生关联,织成生命之茧,生命之茧便是孕育人性、人格的人伦世界。
杜甫其人是“诗圣”,其诗为典范之作、为集大成之作。圣,是圣人,是圣贤;是神圣不可亵渎、不可侵犯,是心存敬畏。杜甫是“五伦”关系的忠实践行者,堪称典范。杜甫“诗圣”的地位主要建立在对苍生黎民广大而深挚的同情上,这种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历来解杜者多以“忠君”说冠之,且有夫子自道为证:“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壮游》)其忠悃之情,实属可嘉!宋人对此早有认识。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素以严苛著称,可是他认为北宋及以前堪为世人楷模的人物只有五位,即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朱熹将其誉为“五君子”。 “五君子”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超强的人格力量,在道德和人格层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具备“绝对坚强之意志与伟大之才气”(1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朱熹接着说:“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12)朱熹:《王梅溪文集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所举五人的君子品格是十分闪亮的。
这种君子人格体现在君臣关系上,或者说君臣之爱上,就是臣下报答君上的忠义与君上同情臣下之忠义的结合体。最初语涉杜甫“忠君”思想的是《新唐书·杜甫传》:“(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8页。很明显,“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是宋人对杜甫忠于君上、心忧家国形象的初步概括,这才有了苏轼的评价:“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4)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18页。苏轼取重的是臣子对君王的眷恋与忠诚。当理学家们把杜甫的“忠君”思想固化为臣必须忠于君的时候,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思就被无形弱化了。好在有一部分宋人看重其忧国忧民之心,认为杜诗中表现的“志士仁人之大节”,出于“闲踬流离而不忘君”(15)李纲:《梁谿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即“不忘君”乃“志士仁人”的价值依归;“不忘君”就是“爱君”,而且是出于“天性”,杜甫的人格与诗作必与之环环相扣、处处相合,成为不可或缺的必然元素。这是对杜甫“忠君”思想较为全面的理解。
有关杜甫忠君忧民思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下文重点辨析“一饭未尝忘君”的问题。关于君臣关系,杜甫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诗文中再三致意。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在杜甫这里成了一种本性,其根源则在于其“奉儒守官”的家传和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即使在漂泊流离之际,也是“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越是身处离乱,他对国家统一、安定太平的渴望就越是强烈,并成为支撑其生命延续的强大内在动力。 “闻道长安似弈棋” “故国平居有所思” (《秋兴八首》其四)云云,都是诗人“漂泊西南天地间” (《咏怀古迹五首》其一)时的心思。正因为如此,当事关国家治乱时,他不仅能苛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叮嘱朋友严武说: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这一看似不大吉利的临别赠言,却凝聚着儒家“君子爱人以德”的精神。杜甫的爱君忧国之心何其浓烈,与严武的友爱之情又是多么醇厚(详下文)!可知,杜甫一心想着天下太平,宿夜匪懈:“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杜甫在诗中感慨自己对时艰有心无力,故只能寄希望于“二三豪杰”能“整顿乾坤济时了”(《洗兵马》)。即便是垂垂暮年,杜甫仍在慨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须知,此时的杜甫已以舟为屋,漂泊在潇湘一带。朗朗乾坤之大,竟容不下一个子美!然而,子美心中仍放心不下君与国。
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另一个表现,即陷贼长安后,他拼力逃脱,竟以“麻靴见天子”,其忠已近乎痴。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无饭亦不忘君”,更见其忠。后来诗人离蜀赴夔州,本想从江陵绕道赴京为国效力,预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终未能成行。诗人哭诸葛亮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没想到竟成了他自己的谶语!在滞留江陵时,他甚至面临断炊的窘境:“童稚频书札,盘飱讵糁藜。”(《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即使是这样,他仍在等待朝廷的消息,关注着君国。此两句,历来注家多有解读。一谓老杜此时右臂已偏枯,书札多由其子代书(王嗣奭);一谓留舟中的儿子给偶经异县的老杜写信(李因笃);一谓粮绝致书亲友(张远);一谓故乡少辈来书促归(张溍)。笔者以为,老杜初至江陵后就把家安置在了当阳,现在家中断炊,儿子频频来信求救——因有老杜大热天冒雨到异县求援的突发事件为证。然而,“异县惊虚往”,没有借到,于是只好求助于江陵友人:“同人惜解携”,已近乎乞求了。自孔子以后,中国士人的自尊自觉之心已甚强,诗人的乞求得鼓足多大的勇气!杨伦解此两句云:“公在江陵时,妻子或留当阳,故家人以困乏来告。”(16)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22页。杨说近于诗意,透露出“妻子或留当阳”的信息。有人说“杜甫功名心很强,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17)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64页。,未免过于尖刻。
另一方面,杜甫的忠君是以“道高于君”为原则的,是以君有道为现实目标的,绝不是愚忠。这里既有对肃、代两朝君主政治失道的严肃批评,也有微妙的暗讽。如关于玄、肃父子矛盾的问题,黄庭坚就评价说:“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书摩崖碑后》)这里,黄庭坚将元结的《舂陵行》《大唐中兴颂》与杜甫的《杜鹃行》并举,对其中的寓意加以揭示,可谓眼力独到。元结《大唐中兴颂》有云:“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二圣重欢”的微言是“二圣失欢”,是揭露肃宗事亲不孝的罪状。杜诗“谁言养雏不自哺”,更是对明皇处境的担忧:上元元年(760)九月三日,大太监李辅国带兵执剑胁迫上皇从南宫搬到西宫,态度极其嚣张傲慢。如果没有肃宗的授意,家奴哪敢如此猖狂!元结《大唐中兴颂》说“事有至难”,乃用荀悦“为善、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之典,暗讽人主肃宗不能向善,不能“为善”,不能善待上皇。杜诗与元《颂》可谓异曲同工!
二、父慈子孝关系中的仁者人格
骨肉之爱与“五常”中的“仁”对应,故称之曰“仁者人格”。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说:“儒教底二大目的在忠君与孝亲二方面。忠君即所以爱国,孝亲即所以忠君。由来忠孝是一致,是殊途同归的。故眷眷君国心在魏阙的,一方面尝恋恋于父母妻子,云山万里,一日也不忘家乡。”(18)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下),孙俍工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儒家讲“仁”,而“为仁”形之于日常生活中,就是“孝弟忠信”。杜甫为人子则孝,为人父则慈。
(一)骨肉之爱之一:对长辈的孝
王绍玺先生说,在注重父子关系的中国社会,“十分强调父子相继,也就必然派生出子孙要‘肖’乃父乃祖的观念,‘肖’其父祖,恪守祖宗成法、家业,不改父祖之道,就是好儿孙,不然的话,就是‘不肖子孙’,就是家门的最大不幸。”(19)王绍玺:《东方两性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3页。杜甫对“肖”与“不肖”的认识当然很清楚。如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就是家族传统。“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的创作成就和自信,对“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的杜甫势必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当杜甫认定“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人诗家流”(《同元使君舂陵行》)、“例及吾家诗”(《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创作意义时,儒家理想与诗歌创作便成了杜氏一族的荣耀徽章和维系家族光辉的精神血脉。在老释风靡之世,杜甫承祖先之素业,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进雕赋表》),这就是杜甫“未坠素业”的事迹和自信。
如果说先祖杜预、祖父杜审言主要从事业上影响了杜甫,那么二姑(裴荣期夫人)则主要从人格、气节上影响了他。二姑是杜审言第一任夫人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她“可能是对杜甫影响最大的女性”(20)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页,第21页。,杜甫崇敬地称其为“有唐义姑”:
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尝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21)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1页。
这一细节向世人昭示,二姑的行为足以担得起“义”字。我们知道,杜甫生母崔氏早亡,由二姑养大。二姑的决定性影响之大,我们从杜甫一生的许多抉择中能清晰看到。诸如“麻靴见天子”、疏救房琯等,在那些事关出处大节的决定中, “杜甫都有意选择了自我牺牲”(22)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页,第21页。。有其姑,必有其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子罕》,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489页。杜甫确实学到了孔子刚健、坚劲的精神。须知,有唐一代的士风是浮华的,社会风气是浊靡的,为后世诟病。如“安史之乱”中,宰相李希烈、驸马张垍(张说子)等相继投降,忠义之缺乏,到了何等地步!像颜真卿、颜杲卿、张巡、杜甫这样的仁人志士是很少见的。当然,就对时局的“无力”感而言,杜甫只能慨叹“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孔子当年念念不忘体天德之仁,最恶同流合污;杜甫之“进取”“有所不为”,是唐代典型的“狂狷者”,直契孔子人格中淳厚的本性而遥承孔子。
有“义姑”又有“义叔”。杜甫叔父杜并十六岁(24)《新唐书》卷二○一《杜审言传》说“并年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5页),《旧唐书·杜审言传》亦云。苏颋《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言,杜并“春秋一十有六”。后者较为可靠。,在吉州厅馆袖刃刺父仇敌周季重,自己亦见害,“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25)刘昫:《旧唐书》卷一九○《杜审言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4999页。。某天,“则天召见审言,甚嘉叹异”(26)刘肃:《大唐新语》卷五《忠烈第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9页。。他的先祖杜叔毗也有类似的壮举。这种侠义精神或“顶天立地之汉子精神”(2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对杜甫的影响很大,时刻感召着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氏满门忠烈。正因有此家风,杜甫才有冒死疏救房琯之“大丈夫”之举。须知,此时的杜甫已自身难保,旋即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特别是在惊魂未定之时,其悲情何以承受!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勇”的表现。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宪问》,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510页。孔子是将“勇”视为君子“三达德”之一的(其余二德是“仁” “智”)。荀子进一步拓展了孔子“勇”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标举“士君子之勇”(29)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56页。。杜甫一次次践行的“勇”当然是“士君子之勇”,可以说是从思想、精神、人格等多方面继承了儒家文化之精华。
(二)骨肉之爱之二:对儿女的慈
清人俞犀月说:“杜公至性人,每于忧国思家,各见衷语。若徒为一饭不忘君,而不动心骨肉者,必伪人也。”(30)杨伦:《杜诗镜铨》卷三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29页。“动心骨肉”乃是天性或人的本性使然。
杜甫爱儿子,亲昵地称其为“娇儿”,如《羌村三首》其二“娇儿不离膝”、《北征》“平生所娇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娇儿恶卧踏里裂”等。在相伴的日子里,父子间的互动甚为丰富,如“呼儿”即为一例: “呼儿正葛巾”“呼儿日在掩柴门”“呼儿具纸笔”“呼儿觅纸一题诗”“呼儿问煮鱼”“呼儿问朔风”。此外还有“呼童”“遣儿”“令儿”“问儿”等,这些互动方式既能见出父亲的权威,又能反映父子间亲昵的生活常态。杜甫还喜用一“从”字,如“失学从儿懒”“书从稚子擎”“失学从愚子”“从儿具绿樽”等,含有顺任、放纵、娇惯之意。
对子女人格的培养是父爱关注的重点。如“人生贵是男,丈夫重天机”(《咏怀二首》其二),以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培养子女的人格。又如“男儿性命绝可怜”(《逼仄行赠毕曜》)、“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莫相疑行》)、“丈夫多英雄”(《牵牛织女》)等,告诫儿子要珍惜男儿的尊严。杜甫还在诗中多方面地挖掘“大丈夫”的内涵,如对优异特出的男儿(包括自己的儿子)以“千里骏”“天马”“骅骝”“骐骥儿”“骥之子”“麒麟儿”“騄骥”“汗血种”等予以赞美,又以“九霄鹏”“皂雕”“雕鸮”“凤之子”等加以赞誉。“天才”与“地才”兼备,是杜甫的教子目标。
可是,生逢乱世,人生无常,父子缘分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几人全性命”(《述怀》)的危境中,在“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糠籺对童孺”(《雨》)、“妻孥未相保”(《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等困境中,与妻儿的团聚相守就显得尤为珍贵。更有甚者,如果说“痴儿不识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的哭闹、“痴女饥咬我”的惨状还可以忍受的话,那“幼子饿已卒”就已“所愧为人父”了。当然,父子间的互动也有儿子对老父的关爱,如“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儿扶犹杖策”(《别常征君》)等,可见亲子双向互动的自然亲切和孩子早熟的性格。
我们从杜甫这类诗中看到的是父亲之于儿女、儿女之于父亲的互爱。老杜这类诗将亲情置于动乱岁月里人人苟活的处境中,不仅透出自己生命幸存的不易、家人相聚的可贵,而且更强烈地透出在极端的背景中人性的高贵和生命相依相赖的美。这类诗不是靠想象力与美感交流的对话,而是直抵人性的深处,充分展现出杜甫的“仁者心”。
三、夫义妻顺关系中的智者人格
夫妻之爱与“五常”中的“智”相对应,故称之曰“智者人格”。杜甫一方面要致君主于尧舜之上,一方面为室家安危而担心,为妻儿饥寒而流涕。继李白之后,杜甫大量作“妻子诗”,其笔下称“妻”“老妻”“瘦妻”“山妻”的诗有三十多首。杜甫笔下的妻子,大多是以老瘦贤慈、沉默牺牲的大地之母的形象出现,承载着贫困流离的生活重担,在忍辱负重中实现妻子、母亲的道德价值。
诗人有意突出妻子枯瘦憔悴的形象。杜甫之妻杨氏乃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从《客夜》“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看,杨氏受过教育。“老”与“瘦”看似毫无审美情趣,却洋溢着真情实感。当时,杨氏30岁左右,何以称“老”?老者,瘦者,并非耄耋垂垂之貌,而是饱受生活沧桑之苦的写照。杜甫在诗中屡称“老妻”,如“老妻寄异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画纸为棋局”(《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进艇》)、“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老妻书数纸”(《客夜》)、“偶携老妻去”(《寄题江外草堂》)、“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还有“瘦妻面复光”(《北征》),都是“糟糠之妻”的真情书写,这才有了王安石《杜甫画像》中“瘦妻僵前子仆后”的慨叹。诗中多有对妻儿生活无着之苦况的担忧,如“妻子衣百结”(《北征》)、“长贫任妇归”(《屏迹三首》其三)、“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妻儿待米且归去”(《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都是写衣食不足的困窘。而“囊虚把钗钏,米尽坼花钿”(《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把钗钏”“坼花钿”的细节,即当卖钗钿购买柴米的举动,是何其动人!又如“晒药能无妇”(《秦州杂诗二十首》二十),“藉糟分汁滓,瓮酱落提携。饭粝添香味,朋来有醉泥”(《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既有自给或补贴家用的晒药,也有操持家务的繁杂,又是多么勤劳!同时还可以看到满满的母爱:“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北征》)“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发阆中》)诸诗中的母亲既是娇憨女儿模仿的对象,也是为儿女罹病忧心不已、对儿女温柔呵护的慈母,在在可见母亲角色的伦理定位。
杜甫型的夫妻关系,“从妻子的角度而言,虽然一生勤勉操劳不已,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因为她也许认为世间的生活大都如此,况且她是伴随在视自己为一生中唯一的女性的丈夫身旁”(31)笕久美子:《以“女性学”观点试论李白杜甫寄内忆内诗》,《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9-260页。。下面再看诗人与妻儿的隔绝之苦:“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彭衙行》)“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述怀》)“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雨过苏端》)诗人只身在外奔波,不仅有对妻儿的牵挂,更多的还是自责与内疚:“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飞仙阁》)“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随汝曹”“愧老妻”云云,特别是在幼子死于饥寒、老妻不饱于糟糠的日子里,消息杳然,半夜怀家对月,时时彰显着诗人温柔敦厚的人性美、人格美。毋庸回避,杜甫经常写哭、写泪,纵观诗人的一生,一语“穷途那免哭”(《暮秋将归秦》)道出了多少血和泪:或“吞声哭”,或“双泪垂”,或“两行泪”,或“双泪痕”,或“涕涟涟”,或“泪数行”,或“涕泪零”……试问,在那个以男子为中心的“家长制”的社会里,有谁这样善于解剖自己?
当然,杜诗中也有与“老妻”“瘦妻”相对的“女神”书写,如《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对月》:“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进艇》:“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可是在“老瘦”“瘦妻”的巨大冲击下,“女神”书写始终处于隐而不显的一面。两种书写的结合,方可见血肉饱满的杜甫、人格健全的杜甫!
四、兄友弟恭关系中的礼者人格
兄弟之爱与“五常”中的“礼”相对应,因之称“礼者人格”。礼者敬人,乃天地之序。如果说孝者是无违,以礼事之,持谦卑心,那么悌者则是友爱,以礼亲之,持仁爱心。如《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字字忆弟,句句有情。又如《忆弟二首》《遣兴三首》等,关爱、惦念之情溢于言表。陶开虞《说杜》曰:“乱离中骨肉之思更切,老妻幼子,弟妹诸侄,依依婉恋,正见其笃于末伦也。”(32)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引,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8页。
粗略检索,杜甫思念弟、妹的诗有30余首。从天宝四载(745)的《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至大历三年的《远怀舍弟颖观等》《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等,历时十余年。儒家伦理强调“兄友弟恭”或“兄良弟悌”,杜氏兄弟对此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兄弟、兄妹的手足之情、友爱思念,不时跃于纸上。多数学者以为,杜甫有四个弟弟(颖、观、占、丰)和一个妹妹常被深情地写到,虽是同父异母,但看不出一点隔阂。作为老大的杜甫,其礼者人格的示范作用做得更好(同时代人称其为“杜二”,可能是家族中的排行)。杜甫的这类诗很有特点,或以问候的方式切入,或遥想弟妹所在的空间,或揣测弟妹行踪的时间,或开篇即叙牵挂之情。这类诗都是将主题置于战乱的大背景下,在一片亲情流注于空间与时间之际,将人伦之情丝编织成生命共同体的情茧。杨伦有这样的评论:“公忆弟寄弟诸诗无不佳,以其从真性情流出也。”(33)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542页。如《元日寄韦氏妹》云:“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秦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平使,啼痕满面垂。”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元日,是乱中思妹之作。诗中钟离县、“郢树”,为妹之所在;“秦城”,为杜甫所居。斗回枝发,点出元日春景;朝使路梗,哀音信不通。特别是“郢树”化用《楚辞·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诗意,尤其加重了不得相聚的悲意,而且揭示出战乱这一不得相聚的根源。又如《同谷七歌》“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云云,让读者悲泣。如果说上一诗抒发的主要是不得相聚之苦,那么此诗表达的还多一层千丝万缕的牵挂在里面,因为“十年不见”且其“良人早没诸孤痴”。可是终因豺狼肆虐,不得相见,也不知妹妹拖带着诸孤挣扎到了什么地步。两句“四歌兮歌四奏,林猨为我啼清昼”,千载以后仍催人泪下!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不能同弟妹一起去插茱萸的重阳,诗人“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感慨万千,愁情万种,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弟妹。然而,有酒不得同饮,有菊不能同赏,遥想弟妹在处,应是“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真此处彼处两茫茫!再加上“干戈既侵,衰谢又迫,恐两相催逼,终无聚首时也”(3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中华书局,1979年,第1764页。,诗人才十分惨切地道出:“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九日五首》其一)在清明佳节里诗人道出了同样的情怀:“古时丧乱皆可知,人世悲欢暂相遣。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清明》)——纵情恣游的人们晚归而去了,自己同弟侄一样在飘零中,兼之干戈阻绝,音信全无,好生悲凉!然而现实毕竟是“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 (《至后》), “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元日示宗武》),是“第五弟漂泊江左,近无消息”逼出的数行泪,亦是血泪倾诉“不见”之悲苦。这同《同谷七歌》 (其三)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一样表达“生别展转不相见”的凄凉。而“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九日登梓州城》)所展示的家国两样愁更为浓烈。
五、友爱之中的信者人格
朋友之德与“五常”中的“信”相对应,因之曰“信者人格”。中国人伦思想中自古以来就极重视友情,并列入“五伦”之中,是儒家讲究言之忠信、行之笃敬的体现。朋友之伦的建立不同于其他“四伦”,乃是立足于人的自由选择与人情的真实关切。作为一个十分珍视友情的“圣者”,杜甫在诗中表现的友情深厚而真诚、圆润而广大,所谓“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同心不减骨肉亲”(《戏赠阌乡秦少翁短歌》)、“来因孝友偏”(《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可见,“意气合”“性情真”和“孝友偏”是诗人的交友之道。因此交下了“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的李白,“思君令人瘦”(《九日寄岑参》)的岑参,“欢娱两冥漠”(《九日五首》其三)的苏司业、郑广文,“喜结仁里欢”(《晦日寻崔戢李封》)的崔戢、李封,还有艰难困苦中有一饭之德的孙宰(《彭衙行》)、与之“泥饮”的“田父”“田翁”(《寒食》《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还有那些“失业徒”“远戍卒”“天下寒士”,更有平等视之的家仆伯夷、辛秀、信行、阿稽、阿段。诗中处处体现着诗人的仁者、信者人格。
考察杜甫一生,尤其是困难时期,给予其经济援助的主要有高适、严武、李之芳等人。杜甫与他们的友情是矢志不渝的,下文将重点谈及。回想杜甫与高适友谊的建立,从开元末年的“汶上相逢”(《奉寄高常侍》),到宋州重逢时的“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昔游》),再到天宝十一载(752)秋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交情越来越深。直到高适为官彭州、蜀州,特别是上元元年(760)九月两人在成都相会后,交往渐趋频繁,高适的经济援助才多起来,杜甫多依之。如杜甫寄诗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乃以兄弟情求助,可见两人交情非同一般。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杜甫先后作有《奉简高三十五使君》《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等诗。合观以上诸诗,知杜甫与高适晚年情好甚洽。永泰元年(765),高适在长安去世。远在西南的杜甫闻听噩耗,睹物思人,肝肠寸断:“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虚历金华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闻高常侍亡》)还有一首诗将杜高之友谊推向了高峰——《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高适去世五六年后的大历五年(770)正月,杜甫偶开书帙,得高适任蜀州刺史时的“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遂追酬一诗悼友兼自悼: “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乃已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杜甫写自己漂流潇湘一带的苦况;“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叹己虽“百年多病”、白首扁舟,却还活着,而昔年的老友已埋骨九原。老杜所云“叹我凄凄求友篇”,正道出他与高适交情之真醇,对“忘形故人”感念至深。
梁启超曾说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情圣杜甫》)。就是这样一位“不肯趋承人”的杜甫,曾为老友严武的安危而担忧:“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九日奉寄严大夫》)杜甫写严武的诗大致有35首,是杜甫赠友诗中最多的。杜严两家是世交,两人早就是朋友。可是,两人生死之交的缔结还是在杜甫定居浣花溪、严武任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节度使期间。这段时间严武给予杜甫不少的接济,并表奏其为尚书工部员外郎,杜甫先后写下《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奉济驿重送严公》《九日奉寄严大夫》《奉待严大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可见其友情之深。严武病逝,身在忠州的杜甫写下《哭严仆射归榇》诗,深致悲悼。在《诸将五首》 (其五)中,诗人深情回忆了严武在成都“共迎中使望乡台”的情景,对严武镇蜀的卓越功绩和超人才略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回顾了严武的一生,对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的卓越建树,倍加推崇;对严武“小心事友生”的深情厚谊感激涕零。在杜甫广泛的交游中,关系最密切而相处时间又最久的,当推严武,所以浦起龙说“公所至落落难合,独于严有亲戚骨肉之爱,是亦宿世缘分”(35)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七律》,中华书局,1961年,第635页。,从而断言“严系知己中第一人,自尔情至”(36)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五《五古》,中华书局,1961年,第149页。。至于酒后两人对骂,严欲杀之之事,盖小说家言,不足信。
关于杜甫与李之芳的交谊,最早可以追溯到天宝初年李为齐州司马、杜甫壮游齐鲁时。如天宝四载(745),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原注:“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宝应二年(763)三月,李之芳使吐蕃,至其境,被扣留。杜甫《王命》诗“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即写此事。诗中有云: “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忧国忧友之深,以致“恸哭”。大历二年(767),杜甫在夔州,有《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时之芳在峡州,诗云:“音徽一柱数,道里下牢千。”三年春,杜甫来到江陵,与郑、李盘桓多日,屡有唱酬。更重要的是,在杜甫断炊的情况下,正是郑、李等友人的援助,才使杜家挺过一段极其艰辛的日子。该年秋,李卒于江陵,杜诗《登舟将适汉阳》《哭李尚书之芳》记下两人最后的友谊,可见“二人一生的友谊使得生者一定要在死者的棺椁前为永远的离别至哀”(37)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六、余论:杜甫性格缺陷辨
性格和人格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概念,这里无暇进行分辨。我们以为,性格偏重本能,人格侧重伦理、道德。两《唐书》的《杜甫传》对杜甫的微词主要在其性格方面(3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杜甫传》云“(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傲诞”(中华书局,2013年,第5054页、第5055页);《新唐书》卷二○一《杜甫传》云“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8页)。。总体而言,宋人的微词不外傲诞、不羁、傲岸、矜诞、不自检诸说,实皆古今诗人之常习,不足为怪,更何况人无完人。宋人所讥的“高而不切”主要是就杜甫“窃比稷与契”而发的。究竟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这是杜甫在书写个人怀抱,如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样,是“盛唐气象”孕育出来的颇具盛唐时代特色或时代精神的思想性格与精神境界。盛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以出将入相自期,倾慕稷、契、范蠡、张良、谢安之类往圣先贤或帝王师式的人格风范,此乃盛唐人积极的进取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彼时的士子们普遍表现出的一种强烈的社会群体意识,也是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尺度。杜甫饱受熏染,才有了“窃比稷与契”的志向。另一方面,我们又可将其视为杜甫生命的最高境界,乃其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既将苍生社稷系挂于胸中,而且是“老大意转拙”;又是对孟子“饥溺”观的体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39)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2731页。这一最寻常、最具有真实意义的体悟,几乎贯穿了诗人的一生。诗人一生坎坷,经纶之志不遂,奔走衣食,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始终郁郁不得志,又尝自比“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一浮萍”,真是命运捉弄人!
“窃比稷与契”还可以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勾勒的上古圣君贤臣谱系中来解读。在这里,诗人把稷与契、尧与舜、巢与由并置在一起,耐人寻味。即将宽厚仁德、万民拥戴的明君尧舜,勤勉有为、施惠于民的贤臣稷契,同抗志守节、高蹈不仕的隐士巢由并列,来诠释君臣大义,因而注杜者或坐实“尧舜君”为唐玄宗,或赞美杜甫志向远大,或嘲笑杜甫自比“稷契”,均属皮相之见,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构建的一个完整的理想政治模式。巢与由是大隐士,孔子原本尊重隐士,隐士所坚守的节操亦是儒家精神的一个方面。隐士的存在有时也并不因为政治苛酷,而恰恰是缘于政治开明,尧曾让天下于许由便是明证。那么,巢与由应预设于理想政治模式中。这种理想政治模式从天人关系看,又成为人道的和谐与进取的一个象征,是杜甫的政治蓝图。因此,一切风云际会中的贤臣(如诸葛亮)都可拟之以稷契,杜甫也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总之,从哲学的高度说,杜甫的人格可能担不起“尽善尽美”,这要尽心、尽性、尽伦、尽理都做到了才称得起;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他能尽才、尽情、尽气、尽伦理的挥洒、尽生命的挥洒,是可以尽美又尽善的。何以言之?杜甫是情感丰沛的人,是多泪的诗人,或痛哭,或悲愤,仰为忠君之情,俯为怀乡之念,其诗苦心经营,不忘君国,堪称“诗史”。唐君毅先生说:“因为杜甫是一个性情醇朴的人,他对于人类万物,有真诚的爱好,所以他的作品中,充满着热烈的情感,流露出生命真实的意义,显示着人生真正的价值,这是合得称做诗人的。……杜甫所注意的,却是注意人类向上的善的方面。”(40)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杜诗中“人类向上的善的方面”,是通过“五伦”关系体现出来的五种人格来践行的。唐君毅先生又说:“中国儒家之圣贤者,天人之际之人格,持载人文世界与人格世界之人格。儒家精神,乃似现实而极超越,既超越而又归于现实。然儒家之精神,在开始点,乃纯为一理想主义之超越精神。”(4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深植于儒家“理想主义之超越精神”的杜甫人格,迈过1300多年,至今仍闪耀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