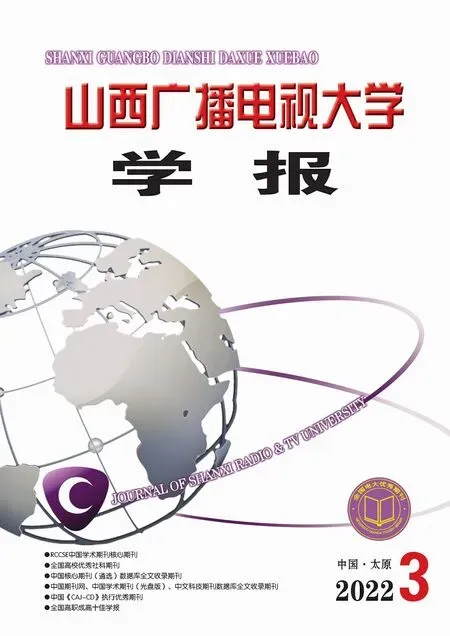浅析法显对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作用
□李志芳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长治 046000)
法显(约337—约422)本姓龚,平阳武阳①人,3岁出家,20岁受大戒。慨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和同学从长安出发,度流沙、越葱岭,远赴天竺求法。前后凡15年,游历30余国,携回经书数十种,译经10多卷。此外,法显还亲自撰写了历游天竺经过的《佛国记》(亦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等)。《佛国记》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许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
一、西行开拓和中印海陆交通的凿空
在我国佛教史上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并称,正如唐朝高僧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述:“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法显不仅是西行求法的开拓者,同时也是打通中印海陆交通的第一人。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他第一次返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各国国情,……确立了打通河西道路经营西域并进而开拓通往‘西极’的国际通道以扬汉王朝威德于四海的决心。”[1]而实际上,中印之间的丝绸通道“很可能在战国时期已初步开通”[1],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交通,但这是转口贸易带来的,而非直接贯通。基于此,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即是公元2世纪伴随印度、中亚一带的商人、使者和移民,先传到今新疆地区,后传入中国内地的。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而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向大月氏派遣使者求法,抄写《四十二章经》而归,则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但是其间经籍的传译多由中亚及印度的僧侣来完成,受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传来的经籍往往篇章不完备或传译失真。此后,汉地开始有西行求法者。三国时魏人朱士行被认为是内地往西域最早的求法者。朱士行,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般若》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魏甘露五年(260)从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出发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取得梵本《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六十万余言。
朱士行之后,西行求法运动兴起。士行之后法显之前,西行求法的僧侣见于史载的主要有:竺法护,西晋人,祖籍月氏,随师外国沙门竺高座游西域,带回经卷百多部;康法朗,东晋初僧人,远足流沙,游历诸国;于法兰,东晋初僧人,远适西域,终达交趾(今越南河内境),中道而逝;竺佛念,前后秦僧人,祖居凉州,“少好游方,备贯风俗”;慧常、进行、慧辩,均为东晋人,太元四年(379)如天竺,过凉州(今甘肃武威)而史不传其返;慧睿,东晋、南北朝僧人,《高僧传》称其“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毕晓”;支法领、法净,东晋僧人,其游方至于阗得经以归。但上述西游僧侣真正达到天竺的,只有慧睿。慧睿(355—439),冀州(今河北高邑)人,少年出家,游方学经,至南天竺界,但求法未果,归庐山不久,又北上师从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的天竺僧人鸠摩罗什受学,最后到南朝刘宋的京师,住乌衣寺讲经[2]。所以在5世纪初之前真正到达天竺并有所成就的仅法显一人。
法显在其回国后所著的《佛国记》一书中声明了他西行的真实原因,并对这一经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3]法显一行经甘肃张掖,西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穿过新疆的漫漫戈壁,翻越葱岭(今喀喇昆仑山)进入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境内),然后南下跨越小雪山(今塞费德科山脉),约在公元402年进入北天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经过了3年的艰苦行程。由于佛教自古重记诵口传,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因此,法显继续远涉中天竺,希望能在佛教中心的恒河流域有所收获。约在公元404年至摩竭提(摩揭陀)国之巴连弗邑(今印度之巴特那)。此邑原为阿育王之都城,为法显西行所经之最富盛之城邑。此城有信奉大乘佛教的“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其国王以师视之。此邑建有摩诃衍僧伽蓝(大乘寺),而居于此寺的高僧文殊师利为摩竭提国内大德沙门及各大乘比丘所宗仰,时各地之高僧及学问人皆诣此寺,寻求义理。但是不久,法显又由此向西前往佛释得道之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之伽雅城),而此城所呈现出的荒芜景象显然非法显这次行程之目的地。综合所经之途的实际情形,大概在公元405年法显再次返回巴连弗邑。从法显这次去而复返的情况来看,他此行之目的自然是要寻求源自释教发源地的佛僧戒律写本,但所经之途,终不得遂愿,不但北天竺无本可写,中天竺“亦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于文字。”“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3]巴连弗邑遂成为他这次行程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在此间,他写录的戒律有:《摩诃僧祇众律》和《萨婆多众律》;另外写录的佛典有:《杂阿毗昙心》《綖经》《方等般泥洹经》及《摩诃僧祇阿毗昙》。
大约在公元408年,法显南下瞻波大国(今印度之巴格尔普尔),在此写经画像居留2年,后乘商船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师子国居留的两年(约410—411)时间内,经过实地考察研究,法显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杂何含》《杂藏》。公元411年搭商船泛海东归(有关海归路线目前学界争议较大),于义熙八年(412年)归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旋南造京师,次年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
法显打通中印海陆交通特别是西行求法的成功,其示范、榜样和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张骞之后法显之前,虽然存在通过西域、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及通过中国南海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和红海到达欧洲、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史籍不载有海陆并行者。就求法僧人而言,从公元260年朱士行开创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始,到公元399年法显西行的139年间,远足异邦的中土僧人虽世代不息,非但史籍记录无一海陆并行者,即使陆路求法成功者也乏善可陈。从法显西行求法成功并打通中印海陆通道,至8世纪佛教民族化过程基本完成,西行僧侣比肩接踵,代有西行求法成功之僧人。其中有陆去海还者,如(南朝)宋永初元年(420)法勇(昙无竭)尝闻法显躬身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招集同志僧猛等25人往天竺,勇至中天竺,由海道归于广州;有陆去陆回者,如北魏神龟元年(518)惠生偕敦煌人宋云经葱岭入印土广礼佛迹,携大乘经百七十部由陆路以归;还有海去海归者,如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从广州乘船经南亚、东南亚赴天竺,25年后由海路归广州。义净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谓“西去者盈半百”且仅限于太、高、天后三朝。所以史籍不载而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求法之盛由是可知。
法显西行成功的示范作用及其此后西行取经成功率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速度和佛教在中国的规范发展。应当说打通中印海陆交通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法显这次西行寻求戒律本身的意义。
二、戒律传译和佛教规范发展
法显西行之前,传入内地并翻译的戒律主要有:三国时,天竺僧人昙摩(柯)迦罗在嘉平二年(250)到洛阳,译《僧祗戒祇心》一卷,为《摩诃僧祇众律》四十卷之节要,昙摩迦罗据此在中国首创授戒度僧制度;西晋时,随着比丘尼僧团的出现,竺法护译《比丘尼戒》一卷;前秦时,昙摩持、竺佛念译《十诵比丘尼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同时,中国僧人也开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入传的戒律制定佛法宪章。较早对这一问题感到忧虑并付诸行动的是道安。道安(约314—385),为佛图澄弟子,后赵时入邺(今河北临漳),后为避战乱到襄阳传法,东晋太元四年(379),前秦克襄阳,被带入长安。在邺时道安曾随佛图澄对流行戒律进行修订,到襄阳后深切感受到戒律缺失对佛教传播带来的严重影响,在此间所著的《渐备经序》中书曰:“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乃最急。”于是,他千方百计寻找戒律原本,并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三项。《高僧传》本传载:“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道安制定的戒律影响很大,《高僧传》称,“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同时,江南佛教领袖人物支道林也著就《众僧集议节度》。不久,道安的弟子慧远也在庐山写成了《社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但与迅速发展的佛教相比,这些戒律显然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佛教戒典残缺不全,给教徒的管理和佛教理论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戒律尚处于草创阶段,戒律的传译和创制远远不能适应佛教的发展。佛教传播过程中自然造成的真空,必然在佛教的实践中反映出来。豪强地主和寺院地主虽在理论上尊崇佛法,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守清规戒律,且为非作歹,有的蓄财近利,有的酒色是耽,更有甚者干预国政。以上种种,一方面说明当时寺院经济还不足以维持佛教自身的发展,广大僧侣不得不妄作与佛教无关的甚至是与佛法相抵触的事务来维持其生计;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无序传播和因此造成佛徒的不规范行为,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进行规范。因此,传译戒律在当时就显得尤为迫切。
法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游并取得成功的。法显赴天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戒律的,因此,他自天竺寻求戒律的成就巨大。
释迦逝世百年左右,佛教内部对于教戒和教义产生不同认识而分裂为两大部派——“上座部”和“大众部”,此后两大部派又不断进行“枝末分裂”,衍生出众多部派。而各部派则根据本部派对教义的理解,制定部派戒律。传世的上座部主要戒律有5部,即昙无德部之《四分律》、萨婆多部之《十诵律》、弥沙塞部之《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迦叶遗部之《解脱戒经》和婆蹉富罗部之《婆蹉富罗部律》;传世大众部的主要戒律有1部,即《摩诃僧祇众律》。在佛教传世的6部主要戒律中,除《解脱戒经》和《婆蹉富罗部律》未传入中国内地外,另外4部均在4世纪末5世纪初传入中国内地。
昙无德部之《四分律》,后秦弘始(399—415)中由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出;萨婆多部之《十诵律》,即法显在巴连弗邑写得的《萨婆多众律》,《十诵律》始译于公元404年,初由后秦罽宾僧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弗若多死后由龟兹僧昙摩流支续译,东晋罽宾僧卑摩罗叉整理补充,在法显回国时,此律已有完整的译本,故《出三藏记集》卷二法显名下著录云:“萨婆多律抄,梵文,未译。”;弥沙塞部之《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因由五部分组成亦称《五分律》,即法显于师子国求得之《弥沙塞律》藏本,南朝宋景平二年(424)罽宾佛陀什应竺道生之请,与于阗沙门智胜等共译;大众部之《摩诃僧祇众律》,由法显从中天竺之巴连弗邑写得,法显归国后不久,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共译。
传入中国内地的4部主要佛教戒律中,由法显携归的有3 部:即法显取自巴连弗邑的《摩诃僧祇众律》和《萨婆多众律》(《十诵律》),得自师子国的《弥沙塞律》。由此可见法显对戒律流传的贡献之大。南北朝以后佛教管理的逐步规范应该说法显是居功至伟。
三、“六卷泥洹”和佛教兴盛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虽然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其局限性依然十分明显,即佛教基本上为上层社会那些崇尚玄理的所谓“社会名流”所器重,普通的民众进入佛门的社会环境没有形成,且佛典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许多人想遁入空门,但又担心自己出身卑微或作恶太多而不能成佛。而法显从中天竺之巴连弗邑所抄之经卷《方等般泥洹经》正好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
《方等般泥洹经》为《大般涅槃经》部分异译,因译出其中较为重要的六卷内容,亦称为“六卷泥洹”。据《出三藏记集》卷八所收《六卷泥洹出经后记》载,该写本由法显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及其弟子宝云,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在建康道场译讫。 在法显等译“六卷泥洹”的同时,《大般涅槃经》也由北凉昙无讖开始翻译。昙无讖(385—433),一作昙摩讖,据《高僧传》卷二载,为中天竺人,初学小乘,见《泥槃经》,自感惭愧而改习大乘。年20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后到西域,因此地流行小乘,便入北凉,在北凉玄始十年(421)译完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经》,因其后有南本《大般涅槃经》译出,故凉译本亦名《北本涅槃经》。
在《北本涅槃经》还没有传到江南以前,《方等般泥洹经》先行流布。《方等般泥洹经》认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所谓“一阐提”系指那些善根灭绝的人。此论一出,则引起轩然大波,称之为魔书者有之,疑为伪作者有之,宗之者亦不乏其人。其中,竺道生对此加以发挥,大胆推论,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只是经本传来未尽而已。竺道生(335—434)原是佛图澄的(竺法汰)再传弟子,后北上师事鸠摩罗什,东晋末年回到南方,宋初与慧严、慧观为朝野所重。道生较早地接触法显译的六卷本的《方等般泥洹经》。他将《方等般泥洹经》基本思想加以发挥,认为世上最坏的人“一阐提”既然属于众生,那么他们也同样具有佛性,也有可能成佛。他的这一理论在初期遭到反对,为旧学僧徒所摈斥,甚至他本人一度被逐出僧团,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的这一学说终得到多数僧侣的认可并广为流布。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凉译《涅槃》传到南朝建康时,宋慧观与谢灵运等以其本为主,对照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
涅槃之学渐盛,教徒之盛由兹。东晋以后我国佛教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促成这一情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毫不夸张地说,法显带回并译出的《方等般泥洹经》起到了理论上的奠基作用和发展中的推波助澜作用。
注释:
①平阳武阳,一说今山西省临汾市,一说今山西省襄垣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