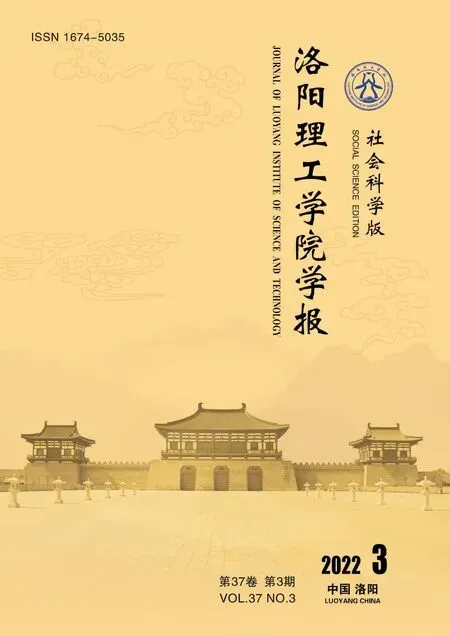长做洛阳花下客
——北宋西京洛阳花会述略
陈朝阳, 王晏然
(1.洛阳理工学院 古都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471023; 2.泰山学院 历史学院, 山东 泰山 271000)
奇容异色之花是自然对人类的馈赠,自古以来,上自王公贵族、下自平民百姓无不被花的美好、雅致所打动。洛阳作为赵宋的西京,文人荟萃,文化生活异彩纷呈,爱花风气盛行,加之宋代文人“尚雅”,花——特别是国色天香的牡丹在人们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牡丹更是社会繁荣稳定的象征。唐代时,洛阳牡丹就已经名动天下。李白诗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1]590刘禹锡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2]789白居易诗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3]218洛阳是大唐的东都,加之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可以想象花开东都时的盛况。
北宋立国后,作为陪都,洛阳的地位仅次于汴京,西京洛阳士民赓续有唐以来爱花、赏花、惜花的风尚,在洛阳任过职的官员大多有对这种风尚的吟诵。司马光作诗:“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4]477欧阳修发出感慨:“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5]1900梅尧臣写道:“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今年夸好方绝伦,明年更好还相比。”[6]377
欧阳修初入仕即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欧阳修在洛阳前后有4年时间。洛阳的山水花木人情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欧阳修写下了我国现存关于牡丹最早的花谱《洛阳牡丹记》,在文中给予洛阳牡丹极高的评价:“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5]1891欧阳修后来离开洛阳到他处为官,西京洛阳和牡丹都会勾起欧阳修深深的回忆:“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5]317“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5]54
《洛阳花木记》的作者周师厚在少年时就久仰洛阳花卉之盛名,对其赞不绝口,“予少时闻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7]卷26。但是周师厚年少时一直没有机会到洛阳一睹繁花似锦的牡丹,这也成了周师厚的遗憾,“尝恨皆未能尽观其繁盛妍丽”[7]卷26。周师厚的这个遗憾后来因为其兄长在洛阳工作的原因而得到弥补。周师厚前来洛阳省亲,时间又恰好是农历三月,因此遍游各个名圃,发出“向之所闻为不虚”[7]卷26的感慨。
正是洛阳爱花、赏花的风土人情催开了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这两朵花谱中的奇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洛阳人把牡丹直呼为花,既为喜欢又露爱重。罗大经曾记载:“洛阳人谓牡丹为花,成都人谓海棠为花,尊贵也。”[8]244宋人不用刻意说牡丹二字,只要说花就是专指牡丹,“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5]1891。名贵品种姚黄开花之时,“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7]卷104。甚至有官员抛开公务外出赏花。熙宁元年(1068)张唐英途经洛阳,发现“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9]171。这足以说明,当牡丹盛开之时,大家都不愿错过一年一度的花开时节。
一、官方举办的花会
洛阳花会在北宋时期,已经成为洛阳民众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洛阳花会始于何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经过唐末五代的混乱,北宋立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到宋仁宗时,“西京牡丹,闻于天下”[10]239。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官方洛阳花会应该是在钱惟演担任西京留守之时。钱惟演在洛阳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士也在此任职,因此他们经常进行诗会文游,花会也就应运而生。“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插花钉挂,举目皆花也”[10]239。太守即钱惟演。钱惟演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正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河南府的长官。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第七子,“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11]10342,随其父归宋后,长期在东西二京居住。这是怎样一种花会盛况?用各色花作为屏障,房屋的各种架构上都用花朵装饰,整个人完全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从文字记载中可以感受到“万花会”带给参会人员的美好感官体验。
“宴集之所”又指的是哪些场所?
北宋西京洛阳城市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园林景观众多。苏辙曾说过:“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居室,园圃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2]412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的记载,仅收录的园林名字就有150个,详细叙述了19个著名园林,其中天王院“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因而有“花园子”之称。
由此可知,西京的私家园林是花会首选的宴集之所。“岁正月梅已开,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9]186。同时,也可以看出有些园子是对市民开放的。但是,有些园子则是需要付费才可以一睹花容,特别是魏紫在宋代时比较名贵,所以花的主人可以趁花会期间获得可观的门票收入。“(魏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州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5]317。“魏花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9]186。
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规模不大,但是也别有一番韵致。司马光家的园丁吕直,对进入独乐园赏花的游人收取门票。“夏月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13]卷上。吕直并没有独吞这些花会收入,而是用这些钱自建一井亭,司马光问吕直建此井亭共花费多少,吕直回答说需要十千。也就是说单司马光一个私家花园的收入在短短一个花会期间就可以有这样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可见,整个西京种花之所在花会期间的收入也是不可小觑的。还有一些园子,则是承包给个人,待花会结束时,双方五五分成所得收益,“洛中例,看园子所得茶汤钱,闭园日与主人平分之”[14]卷中。
二、西京洛阳的花市
西京花会除赏花外,还有花市。花市承载赏花、娱乐休闲和鲜花及其他商品交易的功能。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的花市同花会一样已成为城市之盛事。洛阳“至花开时,张幕屋,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15]61。也就是说,因花会而起的花市是在临时性的地点搭建,花开起市,花落罢市,“士庶竟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5]1900。
白天赏花逛花市,晚上的夜花市也同样吸引人们前去游玩,买花卖花,头簪鲜花,“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9]186。好一派繁荣安康的盛世景象。有花有酒,乃人生之快意之事,有道是“有花无酒头慵举,有酒无花眼懒开。正向西园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16]卷4。
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宰臣文彦博用诗歌描述了洛阳夜花市的曼妙场景:“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都鲜妍。交驰翠幰新罗绮,迎献芳樽细管弦。人道洛阳为乐国,醉归恍若梦钧天。”[17]394灯光和鲜花、音乐和佳人把花会时期的洛阳装扮成了人间天堂,令人流连忘返。
三、花会的影响
钱惟演举办的万花会,提高了洛阳牡丹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了影响力,洛阳花会的影响已经辐射到周边,吸引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赏花。范公偁记载河东的刘跛子连续10年来洛阳看花:“洛阳十年为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终。”[18]322“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19]46河北大名人王荀龙因赏花前来洛阳,并到洛阳拜见邵雍。邵雍有应和诗曰:“君从赏花来北京,耿君先期已驰情。”[10]202有的人在赏花同时还把花带回自己家乡。陆游曾记载:“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20]卷42宋人郭应祥记载了河阳县一次朋友聚会簪带洛阳牡丹的情景,“谁把洛阳花,翦送河阳县。魏紫姚黄此地无,随分红深浅”[21]2229。这在无形之中普及了牡丹的种植。
洛阳花会不仅吸引外地人士前来参观,而且其他有特色花卉的城市也受到洛阳赏花风气的影响,既而引起效仿。
洛阳对蜀地的影响。据相关记载:“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20]卷42“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22]卷1“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帟幙车马,歌吹相属。”[20]卷42天彭和西京多么相似的场景,上至官员,下至百姓,赏花饮酒,满城花香袭人、丝竹悦耳。无奈,北宋时西京的盛世美景只存在文人的笔端供人唏嘘长叹。
洛阳的风俗影响到扬州。王观记载:“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23]卷1蔡京在扬州任职时,也效法洛阳,举办万花会。“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10]239。
洛阳牡丹以其独特的姿容成为贡花。上贡鲜花和宋人簪花习俗密切相关。洛阳的民众不仅赏花,而且喜欢簪花。据欧阳修记载,洛阳人无论身份贵贱,在春天到来、百花盛开之际,皆爱插花。邵雍说:“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24]187头簪娇艳欲滴的牡丹,口饮醇厚绵长的美酒,是宋人享受生活、体味生活的一种表现。宋熙宁五年(1071)五月二十三日,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跟随知州沈立去吉祥寺僧人守璘的花园集会赏牡丹。第二天,沈立向众人展出10卷《牡丹亭》。苏轼看到赏花画面的壮观以及与市民一同游玩的乐趣,有感而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不知是朝廷影响了民间,还是民间浸染了朝廷,总之,簪花这一时尚潮流也引导和推动着各个阶层对花的需求和喜爱之情。
皇帝赐给臣子牡丹花,被视为一种殊荣。“晁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为真宗所优异……后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25]2。晁迴和钱惟演都是真宗朝名士,且均在西京洛阳任过职,宋真宗对二人高看一眼,视其为亲王、宰臣,特别是晁迴,不令自戴反而命中使为其戴花,可见皇帝对他的认可。牡丹花作为皇帝的赏赐,对大臣来讲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故事:西京每岁贡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库酒赐馆职”[11]186。曾得到过赏赐的韩子仓就对赐花的殊荣念念不忘:“忆将南库官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11]186
宋神宗对西京所贡牡丹也非常喜爱,曾簪姚黄一朵以表喜爱之情:“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26]117-118关于姚黄的进贡,据苏轼记载始于钱惟演:“洛阳相君忠孝家,近时亦进姚黄花。”[27]222苏轼写这首诗的目的却是讽刺钱惟演出身忠孝之家、名门望族,也为邀宠而进贡牡丹。
进贡朝廷的牡丹自然是珍稀品种。“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此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赏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11]186。当时姚黄已然是珍稀品种,而新培育出来的欧家碧则冠于姚黄之上,花会期间自然要进贡皇家。
除向朝廷进贡花外,当皇帝、宰相来西京洛阳的时候,给他们献花也已成为洛阳官员相沿成习的行为。姚黄的扬名就和牛氏献花相关。“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5]1895。文人士大夫之间赠送牡丹,以牡丹为主题的唱和更是数不胜数。“陈尧佐字希元,修《真宗实录》,特除知制诰……尧佐退居郑圃,尤好诗赋,张士逊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遗之”[28]2260。
四、结 语
西京洛阳之所以能够形成花会,与其社会风尚是密切相关的。当自然之物被赋予文化和审美的意蕴时,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尚和持久风行的可能。北宋西京洛阳花会的形成就与西京洛阳本土文化和北宋文人尚雅之习俗密切相关。陈寅恪曾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数千载演进中,西京洛阳绽放着独特的光辉,精致、内敛、天人合一的西京文化使洛阳人对赏花有独到的心得和理论。邵雍久居洛阳,曾言:“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24]212以花喻人、以花喻理、以理赏花之妙、以花之妙喻人之道,花人合一,所以,世人才会爱花、惜花、重花。
北宋西京洛阳虽然与开封并为两京,但是西京没有朝中斗争、博弈的凶险局面,这里聚集了经历过宦海沉浮、见识过浮生荣辱的官员,陪都洛阳给他们的感觉是轻松、闲适,这里成为他们放松疲累之躯、浣濯蒙尘之心、纵情花木山水的理想之地。正如程民生所说的那样:“开封是滚滚红尘,争权夺利,是政治家的战场;洛阳是花气蒙蒙,修身养性,是学问家的天堂。”[29]81官员文人又是引导地方风尚的关键人物。“钱文僖公惟演生贵家,而文雅乐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守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盛,无不到者”[30]21-22。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催开了北宋西京的洛阳花会。即便到了今日,花会仍然是洛阳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