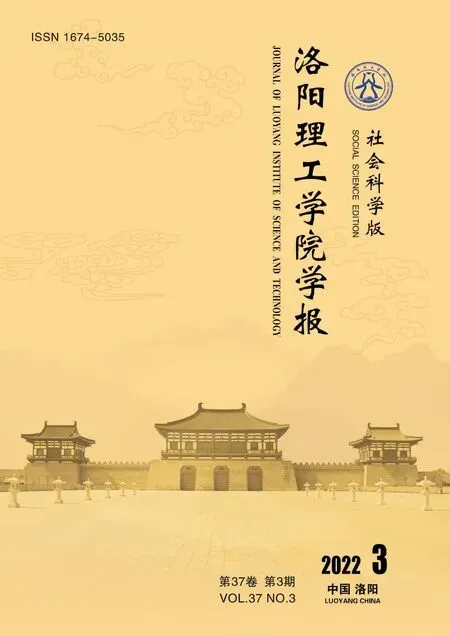宋金以来墓志铭文体嬗变研究
陈 蕾, 王婷婷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遵义市第十中学, 贵州 遵义 563000)
墓志铭,是置于逝者墓室并记有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卒葬年月等信息的石刻,一般由志和铭组成。志文多以散文形式记叙死者基本信息和生平事迹,而铭文多以韵文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赞颂。历代文人学者多次对墓志铭进行定义。唐代封演云:“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1]56明代吴讷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2]53马衡云:“冢墓之文,有墓志,有墓莂,墓志纪年月、姓名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谓之墓志铭。”[3]89因此,墓志铭是一种既具备文物属性,又包涵历史、文学价值的实用文体。书写墓志铭既有“防止陵谷变迁”的志墓功能,还有镌刻逝者人生轨迹的志人功能,更是寄托生者对逝者无限哀思的载体。
墓志铭书写在我国由来已久,可上溯先秦时期。“铭旌”在《周礼》《仪礼》《礼记》中有所记载。《周礼注疏》载:“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4]1415此时的墓志铭书写注重实用性,文体尚未定型。两汉时期,出现了埋刻石于圹中的做法。魏晋时期,墓志铭吸收骈文创作手法走向骈俪化,体制趋向成熟稳定。唐代,墓志铭书写趋向散文化和史笔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文风的嬗变,宋金以来的墓志铭文体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潮、文学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变化,总体上处于继承与创新并存的状态。
一、宋代墓志铭“史笔书写”和“散文体式”的沿袭与定型
宋代以前,墓志铭创作经过唐代文人的努力,剔除了魏晋墓志铭浮华无实、千篇一律的弊端。在文体形式上,唐代墓志铭在前代以骈文为主导、崇尚华丽辞藻的基础上,开始用散文进行创作,但还是难逃骈文窠臼;在叙述方法上,唐代墓志铭开始以纪传体书写为主,发挥“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5]214的写实叙事功能。如张说、韩愈等将史传的笔法引入墓志铭创作中,用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方法叙述死者生平事迹、品德功绩,奠定唐代碑文创作的写实风格,为宋代墓志铭创作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在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墓志铭创作基础上,对文体文风进行变革,吸取同时代其他文体的长处,使“史笔为碑志”“散叙结合”成为墓志铭的主要创作倾向。
(一)尚实从简的纪传体风格
墓志铭文体发展到宋初,时人已经意识到魏晋南北朝“藻饰郡望、铺排声律”的文体弊病。宋代墓志铭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延续了唐代韩愈等人开创的尚实从简的文风,创作上以“史笔作墓志铭”为主导,将墓志铭的纪传体风格推向成熟。同时,为兼顾墓志铭书写“隐恶扬善”的原则,在叙事时注重简而精,纪大略小,做到求真务实。如《北宋授朝散郎守殿中丞致仕骑都尉赐绯银鱼袋孟良墓志》载:
大宋赵郡赞皇县熙宁七年新改为镇,划属高邑县。龙门乡马村授朝散郎、守殿中丞、致仕骑都尉、赐绯银鱼袋孟良墓志。年八十一岁,于熙宁八年乙卯状月廿八日,谢世于本宅。县君韩氏,年七十三岁……有三男:长男锡。次男士雍,前任河东路保德军司理参军。次三男演……托于铭曰:□落,光景难留。埋金荒野,万载千秋。[6]115
这则墓志铭,作者用三百余字,将墓主姓名、为官经历、子嗣情况、卒葬年月等写得清清楚楚,语句简洁明了。又如《南宋故吴郡黄府君(俣)墓志铭》为逝者的侄子黄淇撰写。黄淇在志文中,先叙述自己与逝者关系,然后选取最能表现逝者性格特征的事件进行叙述,“少颖悟,从故参政郑公闻及乡先生潘承议孜受《尚书》,后喜习辞赋。甫冠,有声于郡庠,屡以进士试于有司,数奇不偶,未老即谢场屋。虽杜门却扫,然未亦尝废卷。性恬淡节俭,不为居养所移,而又处事谨愿,遇下慈祥”[7]8。黄淇用伯父勤于读书,却屡仕不中,但仍未放弃读书的经历,来表现伯父的淡泊名利。宋代的女性墓志铭也遵循史传实录的记叙原则,多从日常生活入手,少有虚美之词。如《北宋故孙府君(傅)夫人刘氏墓志铭》云:“夫人事上抚下,恩义周恰。各得其欢心,而莫不庆孙氏有妇焉。府君早世,儿女尚童幼,未堪克家事,夫人养育训饬,使为成人。而门户生产,维持完守,不减于府君在时。”[7]7该墓志铭作者从治家、抚幼、门户生产等日常小事入手,展现刘氏贤淑、勤勉的品德。
(二)叙论结合的散文体式
宋代墓志铭文体延续唐代墓志铭的散文体式。在句式上,宋代墓志铭抛弃魏晋时期文字艰涩、行文对仗、华丽尚典的风格,打破呆滞的四六格式,长句开始出现;在语言上,摒弃浮华虚饰的溢美之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叙墓主事迹,发挥散文流畅自如的优点。如《宋故夫人茹氏(柴炳妻)墓记》载:
夫人本卢州舒城人也,姓茹氏。父□议郎东启……后同母兄随□朝请郎东济寄居阙下,以崇德元年,适华州蒲城县将仕郎柴炳,实朝请大夫知房州鼎臣之第二子也。夫人既归柴氏,□□奉下,咸得其宜。勤于治家,躬以□□。好施与,喜宾客。自将仕公丧,于今十三□,□但日课佛□,月持十戒,终始如一,未尝少怠,以此人皆重之……葬于本县□龙乡孝仁里夫人之茔焉,谨记。[8]158
该墓志铭通过对茹氏出生背景、人生轨迹、性格言行的简单介绍,突出其治家有道、乐善好施的特征。此篇志文不事用典,文笔顺畅自由;句式不受骈文约束,句子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宋代墓志铭在散文体式的基础上,还加入作者议论,使文章情彩兼备。如《宋故安丰王评事(熙)墓志》不仅记叙了墓主一生的经历,而且在文中多有议论:“公游者,来无虚日。或谓时不乏人,于今士林中,唯王光甫之名字得之何多!盖此公以道利物,润色英豪,果于有为也。故如是,其如细谨小行有负于尘世者,盖亦鲜矣。”[8]159作者感叹墓主不虚度光阴,一生果敢有为,为世间少有!宋代墓志铭中“议论”“感慨”的增多,与宋人好议论和表现才学的行文习惯有关。宋代墓志铭书写除铺排墓主的为官政绩外,还对人物事迹的细节进行侧面描写,以避免内容的呆板。如《刘夫人墓志铭》写道:“夫人享年七十九岁,以景祐四年孟冬月十有三日坐于正寝,倏谓诸眷爱曰:‘吾与汝朝欢聚会,暮恐别离,各善保绥,更不多嘱。’于是眷爱涕泗滂沱,不忍是言,弥增惶恋。靡移顷刻,魄散魂消,遗玉体于高堂,显灵踪于霄汉,是谓神性历历,言语昭昭,何故若兹,莫非阴德!”[9]20作者描写了刘夫人去世前与家人告别时的感人场景。宋代墓志铭的写作以散文为主,并在其中加入议论与细节描写,实现了墓志铭的文学性表达。
二、金代墓志铭的复古和旷达之风
金代文学崇尚淳古文风。《还山遗稿》言:“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育,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10]250受文学风气的影响,金代墓志铭创作在学习唐宋文人朴实自然的书写特点上,进一步发挥墓志铭的实录作用,体现出尚古务实的风格,但又有其民族的旷达之风。
(一)尚古务实
金代在墓志铭创作上,秉承“尊重事实,不徇私情”的原则。元好问推崇实录精神,他的《奉直赵君墓碣铭》云:“晋来速铭,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11]658如《金故宣威将军知镇戎军州事兼沿边安抚使刘公(孝忠)墓志铭》载:
三代居燕然之地,生公英雄,少有立志,年十八,当辽之时,父荫供奉班。二十,外插试中御射,为左承制,历年不得擢用。天会初,圣朝兵起伐辽,公南奔归宋,为安州团练使……公庙算神武之兵不可与战,起义招降诸军将、郡官等六十余员……于是,朝廷赏功,充易州军州事。明年,随帅军功河北真定,河南汴京、雄、莫等州。[6]118
这则墓志铭记录了墓主家族谱系和为官经历,文风平实,无渲染之笔。该墓志铭借鉴唐宋史传笔法,以时间为记叙顺序,记述安抚使刘公的生平。墓志铭用流畅自如的散体古文形式,无矫揉造作的语言,也不回避刘公改节归金的事实。墓志铭最后铭曰:“忠节捐躯,人臣所尚。时衰不达,未为良将。辽宋天亡,如何辅相。”[6]118体现了金代墓志铭尊重史实的写作特点。
(二)旷达之风
金代文风具有“华实相扶,骨力遒上”的特点。在墓志铭创作上,受这种刚健质朴的文学风格影响,墓志铭行文洒脱自由、不拘一格,具有旷达之风。如《金故河南封公(志安)墓志铭》载:
公讳志安,字道宁,世为华州蒲城人……族属有贫者,俱蒙赒济,阖门数十口,仰给于公,生计日增,用度不匮,皆公之力。公生于治平之乙巳,卒于元祐之辛未。感疾捐馆,一邑之人悼公早亡,无不挥涕。惜乎不获寿考,悲夫!公娶冯氏。公既卒,有遗息,方五月。冯氏曰:使我生男,虽死不移。后既生,果弄璋焉,遂发共姜之誓……其后父母终不能易其节……享年六十一岁。[8]160
这则墓志铭行文平实流畅,写封公为人忠诚善良,生前致力于接济族中的贫困人家;又述封公之妻冯氏一生“不改其节,养子促学”:“使我生男,虽死不移。后既生,果弄璋焉,遂发共姜之誓。”[8]160冯氏质朴的语言彰显其从一而终、坚忍抚幼的志气。又如《金大兴府易州涞水县故敦武校尉张公(守仁)墓志铭》载:“呜呼!其有德业材能,不见昂立于人上,而复夭阏于丁年,不知上天报施其何如哉!”[6]117-118与宋代文人“止乎礼义”的情感流露不同,作者在文中尽显哀痛之情,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激越洒脱的情感表达。
三、元代墓志铭的简化与虚幻笔法
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狩猎和游牧文化的影响下,元代文学的类型和主题日益丰富,墓志铭有着虚幻奇异的特色。元代墓志铭创作师法唐宋散文笔法,文体形式简化,用语平淡简明,少有粉饰。
(一)墓志铭文体形式简化
相较于其他朝代,元代墓志铭写作程序简化,墓志铭大部分只有志文而没有铭文,“有志无铭”的现象增多。如《元故中顺大夫浙东宣尉副使任公(仁发)墓志》《元故敕授集庆路溧阳州儒学教授任公(良佑)墓志》《元故提举任公(贤德)墓志》《元故承务郎宁国路泾县尹兼劝农事知渠堰事任公(贤能)之墓》等,均有志无铭。这类墓志铭多在志文末尾写:“葬日薄,为能请铭当世立言君子,姑叙其岁月梗概纳诸幽,而藏其副于家。”这与前代重视身后立言的习惯截然不同。唐宋时期的逝者家属往往请名家润笔并题铭,希望扬名后世。并且,在元代墓志铭书写简化趋势的影响下,墓志铭撰写、篆刻多由直系亲属完成,寻求名人撰写、刊刻墓志铭的行为呈下降趋势。
(二)墓志铭创作的虚幻奇异笔法
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12]279元代之前,诗、词、散文、赋是作家主要的创作类型。元代及以后,戏曲、小说逐渐形成与诗、赋齐头并进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也为墓志铭创作带来了虚幻奇异的笔法。受当时文学作品的影响,墓志铭中开始加入神话、梦境等情景。如《参议官熊震龙墓志铭》载:
公异人也,在孕逾月,有道人踵门,出丹一粒,霞光映掌,授母氏王宜人曰:“服此生贵子,可间我于羊角峰。”是夕公生,丰骨昂声,不类常儿……梦天门开,神人于玉色中揭君此心如皦日六字,来自麻姑山者……道其师寄意公,玉源君候已久。至元戊于九月十日,黄龙复屋,云气郁纷。公曰:“吾其去矣。”越四日清晨起浴整衣冠,谓玉源君来访……毕,端坐而化。惟公异人出世,故生死去来不凡。[9]253-255
这则墓志铭既是对墓主熊震龙人生的记录,同时也近似一篇小说。为突出墓主的传奇,志文描写了墓主出生和逝世时发生的神异情景:出生时“有道人踵门,出丹一粒,霞光映掌”,去世时“黄龙复屋,云气郁纷”。又如《宋丞相文天祥墓志铭》写道:“至拘北营,驱逐北去,犹冒万死南走,蒙疑涉险,寄命顷刻,仅而得达。当是时,其飞潜若□,其变见若神,南北□不想见其风采。故军日败,国日蹙,而自远归附者日众。”[9]249墓志铭用“其飞潜若□,其变见若神”突出文天祥的骁勇善战、机巧如神,暗示其成功不仅包含个人智慧,更有天赋之资。
四、明代墓志铭的教化作用及传记风格
明代儒学地位不断提升,文学创作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颇深。墓志铭写作也充满教化意味,铭文中频繁使用议论进行说理叙事,使用虚词发表感叹。明代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等的繁荣,使类似小品文的人物传记兴盛。明代墓志铭吸收人物传记笔法,描写墓主事迹更为细致,语言上更贴近生活,体现出与人物传记合流的倾向。
(一)志文重视教化作用
明代统治者通过八股取士和学校教育,提升儒家纲常礼教的地位,利用儒学教化消除异端思想。墓志铭创作者受“德治”和“礼治”思想影响,重视铭文的教化作用。为加强墓志铭的教化意味,作者在志文中频繁加入个人议论。个人议论在墓志铭中出现较早,但较前代而言,个人议论在明代墓志铭中处处可见,呈泛化趋势。如《大明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阎工(本)墓志铭》曰:“天下有可必之理,亦有不可必之数。可必之理,义在人也;不可必之,命在天也。君子行义以听命,但能全人以循当然之理,而不能违天以脱偶然之数。至于斋志以没焉,是则可哀也已。”[8]171该墓志铭开篇议论:君子应遵循道义,重视自我修养,面对不可控的生死和变数,当顺应天命。这改变了前代墓志铭篇首程式化地介绍墓主族系、姓氏、履历等的固定模式。又如《明故处士宣君汝旸(升)合葬墓志铭》载:“且《檀弓》有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仪礼》曰:夫妇生时同室,死同葬之。又曰:合葬,所以固夫妇之道也。故《诗》曰:死则同穴。古礼然也。”[7]47这则墓志铭在篇末引经据典议论生时同室、死则同穴的夫妇伦理之道,起到升华墓志铭主旨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宣氏夫妇的情深义重。
为增强教化作用,明代墓志铭中常用“哉”“呜呼”“耶”“乎”“矣”等语气词。如《明故松江府儒学生墓志铭》写道:“璚仲兄廷瓒率孤子辅哀拜乞铭。呜呼!余忍铭璚也耶……其可恸也。欲不可铭乎?”[7]29又如《明故处士陈汝敬(钦)墓志铭》写道:“呜呼!处士生逢盛世,死终令命,本蕃枝茂,子孙相仍,求之如公者,鲜矣。”[7]32再如《明故(徐博)妻张氏(贞)墓志铭》写道:“呜乎痛哉!君德如此,宜其安享禄寿,以衍庆泽于无穷,岂谓遽丧我贤妻哉。”[7]38志文通过句首、句尾的语气词,渲染情感的表达,使之更加感人。
(二)志文传记风格的出现
明代墓志铭的创作受当时人物传记影响,撰文者在撰写志文时对墓主的事迹精心选择、细致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以突显墓主的个性特征。如《赠镇国将军袁忠既妻邹氏墓志铭》记:
公天资磊落,自幼读书明理,达于世故,遭家中衰,旧业为他人所有。公甫长,奋自树立,倍其直复之,曰:“此先人所遗,可轻弃乎!”人有以业售公者,亦力辞之,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吾不为也。”[9]297
这则墓志铭选取袁忠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家道中落,旧业为他人所有,成年后苦心经营重振家业,拒绝乘人之危而得利。通过对袁忠家境的前后对比,展现其读书明理、达于世故、不乘人之危的品格。又如《明处士解公(士郁)墓志铭》记:“宣德庚戌,入山樵采,脱其新制锦衣,归而忘之,因失去,不以为意。继而往樵,亦得一遗衣以归,家人喜曰:可以尝所亡矣。公斥曰:他人戚所丧,亦若吾戚所丧,容可利之?翌日,潜携往候,卒以畀失者。”[6]125这则墓志铭记述解士郁上山打柴,丢了新衣服,后又去山上打柴捡到一件衣服,他没有听从家人将衣服据为己有的建议,而是回到原处等待失主并将衣服归还。志文通过对解士郁和家人对话的描写,突出其高尚的品德。解士郁作为明代普通人的代表,没有精彩的仕途经历,却能恪守本分做人的道理。明代墓志铭与明代人物传记一样,着力对墓志主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以追求人物形象的真实美。
五、清代墓志铭的骈散并行与非程式化创作
清代师古之风盛行,或师法唐宋,继承韩愈、欧阳修的散文体式和史笔书写;或承继魏晋,学习对仗工整、华丽典雅的骈体文创作。清代文学复古的两种倾向,使墓志铭文体呈现骈散并行的现象。而清代高压的文化政策,使墓志铭减少对宏大历史的书写,通过描写生活琐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墓主的社会经历、家庭生活、求学场景等。清代墓志铭充满浓郁的情感色彩,呈现非程式化的特征。
(一)骈散并行的文体
清代文人被束缚于程朱理学之内,文字狱较明代而言更甚,这使清代文人多埋首于故纸之中,从事考据学。文人在梳理经典的过程中,积累了广博的才学,为骈文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尤侗、陈维崧、毛奇龄、蒋涟等人在创作中承袭六朝以骈体为文的方法。陈维崧《词选序》载:“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13]54但以朱彝尊、方苞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反对骈文倾向。方苞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14]483文体上的骈散之争,无形中影响了清代墓志铭写作,使清代墓志铭文体呈骈散并行的趋势。如《皇清例赠修职郎瑞菴杨公(文瑛)既岳孺人合葬墓志铭》曰:
时奉古格律铭座右以自箴,生平遵信,愿体集一书烂胸中,应世接物胥准此,非道相撄,不情相干,依体集行,不爽尺寸。然柔不茹,刚亦不吐,临大事从容镇静,处之有方,心力加一等。常居自谓无益于闾里,其实被福者伙矣;自怨有忝于孝友,其实敦伦者至矣。[8]359
这段墓志铭既有押韵对仗、文辞优美的骈句,又有灵活自由、长短不一的散句,使墓志铭的书写兼具骈文的整齐精美和散文的从容疏宕。又如《张母周孺人墓志铭》曰:“淑慎自持,温恭有度。姜家堂上,喜孝妇之湘鱼;石氏床前,代光勋而涤器。显章之嫁,惟奉于欢容;赵母之终,自投于妇手。”[15]232此段以整齐四言、六言的骈俪体书写,不仅典雅工整、辞彩绚丽,而且吸收散文自由挥洒情感的长处,使墓志铭颇具情彩。
(二)着重细节描写和情感渲染的非程式化创作
清代墓志铭减少了对时事、政治的书写,吸收小说创作的范式,通过描摹生活细节,来展现墓主真实的人物形象。在行文上,清代墓志铭突破程式化书写特征,一改呆板之风,使志文富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如《清敕封孺人梁(允嘉)母王氏墓志铭》曰:“悽然增伉俪之重旨哉!此言足抵安仁一赋矣……至于百折摧心,千忧疾首,潮汐涕泣,荼蓼肝脾,以聚首之唏嘘,重分辕之寤叹,则友又以悽多愉少,而增永怀。”[6]374撰文者用“悽然增伉俪之重旨哉”诗句开篇,以渲染夫妻情深,却难以相守的悲感情绪,引起读者共鸣。墓志铭在赞美王氏持家有方、事夫勤恳时,主要通过对具体事例的描写使王氏的美好德行跃然纸上,如:
先生少病失血症,夫人长斋茹素,炳香吁天,祈以身代,先生乃霍然起也。先生轩轩,霞举高亮,而略于家人产,乃门以内,金刀蔬茹,秩秩有经,则夫人持筹明敏力也。[6]374
此段吸收小说创作的描写手法,展开对逝者的追忆。回忆了王氏在先生身患失血症时,坚持吃斋念佛、焚香祈祷,甚至甘愿代替丈夫遭受病痛折磨的感人之举。还写了先生忙于外事、略于治家时,王氏独自维持门户生产,把家中大小之事打理得井然有序。并且,在墓志铭中加入王氏丈夫的悼念之词:“予悼予妻,复追忆先妣,不禁涕泪之沾衣,盖念结慈帷,故茹通益深也。”这则墓志铭以相对自由的形式融入语言、动作描写,抒发情感,使志文成为一篇感人至深的哀悼文。
综上所述,宋、金、元、明、清等5个阶段的墓志铭随着社会历史、时代文风的发展而变化。在体式上,墓志铭文体继续朝着唐代墓志铭散文体式、史笔书写的趋势发展。在叙述方法上,突破墓志铭程式化写作,吸收戏曲、小说等文体的元素,增强墓志铭的文学性。在写作功用上,墓志铭借鉴哀悼文、祭文等文体的长处,从颂美逐渐向抒情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