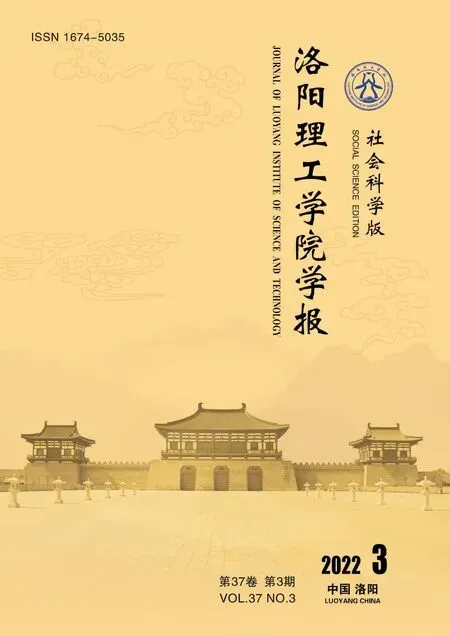永嘉:文化地理符号与清代谢灵运诗歌的经典化
王 玉 林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谢灵运一生“好与名山游”,在出守永嘉期间,大量创作山水诗,对其诗歌风格定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期间,“永嘉”一词也潜在地发生从自然地理名词到文化指称意义的符号学转变①,“谢永嘉”的称谓应运而生。李白漫游东南之地时也曾作诗云:“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1]1128可知,至唐代永嘉与谢灵运之间便已形成了符码规约性。除“谢永嘉”外,“谢灵运体”以及仿谢体等具有约定俗成指称意义的符号化现象,参与了谢灵运诗歌经典化历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总结道:“(谢灵运诗)其影响所及,效法者极多,以至有‘谢灵运体’‘谢康乐体’的专名。”[2]60在清代,具有符号意义的“谢体”、仿谢诗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永嘉”文学地理符号等,共同构成了谢灵运诗歌经典化过程,同时也是建构“永嘉”地域文化的重要环节。笔者立足于清人仿谢诗的具体诗歌作品,分析永嘉景观对谢灵运诗歌创作影响以及清人对谢灵运诗歌与永嘉山水文化的接受,进一步探讨文学地理学超时间的空间风格与超地域的时间风格论题。
一、永嘉作为文化地理符号的意义
“永嘉”最早作为历史纪年的时间概念出现在西晋时期,指晋怀帝司马炽统治时期的永嘉元年至七年(307~312)。自东晋太宁元年(323)建立永嘉郡(今属浙江温州),南朝刘宋人郑缉之撰写《永嘉郡记》后,“永嘉”便在自然地理概念与行政地理概念的基础上,作为文化地理概念逐渐出现在历史典籍中。清光绪《永嘉县志》云:“温在浙东号为名郡,而永嘉倚郭为县,广轮二三百里。东南际大海,西北阻群山,襟江带湖,绮壤绣错,水陆之美无不饶,衍盖东南一郡会矣。然而南通闽越,北接台栝,使车络绎,商旅辐辏,公私亦少困焉。”[3]21永嘉位于楚越大地,东临大海,西接群山,紧邻瓯江,中有重湖,山水绮丽秀美,风光如画,具有天然的诗性美。半环形的地理环境客观上构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诗性地理空间。永嘉自然山水不仅为谢灵运诗歌创作提供丰富的审美观照对象,同时,其自然地理特点亦客观、直接地影响了谢灵运的艺术审美知觉。钟嵘《诗品》称:“《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窹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4]372这句诗出自谢灵运出守永嘉期间所作《登池上楼》一诗,正是永嘉天然地理环境的滋养,谢灵运才能创作出被评为千古佳句之祖的“池塘生春草”。同时,通过谢灵运的重塑,永嘉山水独特地域文化风貌也逐渐成型。钟嵘《诗品》借用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4]351芙蓉出水之“清新自然”不仅是谢灵运山水诗风的特点,也是永嘉山水的主要地域文化特征。
温州古称瓯越、东瓯。郑缉之《永嘉郡记》“瓯水”条云:“水出永宁山,行三十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5]25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中云:“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瓯水盖即今楠溪。”[5]25可知,东瓯古城在瓯江北岸的楠溪下游一代,属永嘉郡范围。自晋室南迁,设置永嘉郡,原有的瓯越文化开始转型,趋向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6]23。王羲之、郭璞、孙绰、谢灵运、颜延之、檀道栾、邱迟等曾先后游览永嘉。自从晋室南迁偏安江左,逐渐形成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左文化圈”。其以玄、佛思想为学术根底,以玄言诗、山水诗创作为主体,构造出“清绮”的文学地域总体风格,共同参与江左地域文化的建构。
谢灵运游览永嘉诸地,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作用下,在神与物游的艺术境界中,永嘉山水的清音、清气、清辉以不同的方式,渗进谢灵运的审美心理结构,使谢灵运笔下的景观呈现“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的阔大空间感与清莹之气。同时,永嘉江山也内化为谢灵运的心灵审美空间,塑造出独特的永嘉意象,形成一种文化记忆。
二、清人仿谢诗对永嘉情境的内化
仿谢诗歌中对谢诗语句的化用及意象的借鉴,是谢灵运诗歌在清代经典化的内在表现,对永嘉景物的内化是清人仿谢之作的突出特点。从谢灵运诗歌与清人仿谢之作的比较,可直观感知“化用”艺术手法的运用。如李元度《又拟谢康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一诗中“东扉已在瞩,南径相与趋”[7]655一句,与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的“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选用相同的意象“东扉”“南径”,且动词同为“趋”。吴乃伊《拟谢灵运游南亭》一诗中“新篁媚幽姿”[8]424,合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潜虬媚幽姿”与《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初篁苞绿箨”两句诗为一句,极为工巧。沈铎《拟谢康乐游山》中“半规远峰藏,幽光密林现”[9]261一句化用谢灵运《游南亭》中“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同时,清人对谢灵运诗歌句法及意象结构的设置,既有承续又有超越。以杨锐《读谢康乐游览诗拟作八首》组诗中其中一首为例。
云敛霁初夕,夕瞑山气寒。缭垣辏野阴,飞阁撼风湍。烧痕原野红,返照川林丹。岚变景多新,谷深趣易阑。征鸟逝愈疾,孤兽走复还。(《晚出西射堂》)[10]45
谢灵运的诗歌《晚出西射堂》前10句形成5组对偶句,可以分为3类,即“动词+地点+景物”“时间名词+景物+色彩词”“动物名词+情感词+景物”。首句“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步出”“遥望”相对,“步”“望”均为表示动作的词,“西城”“城西”表示方位,“门”“岑”是具体的景物;“晓”对“夕”,时间相对,“枫叶”对“岚气”均指具体的景物,“丹”对“阴”色彩明暗相对;“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一句,整体的情感色彩相似。
此外,清人多仿写谢灵运在永嘉时所作诗歌,但对其诗中传统的永嘉景观注入新的审美情趣,形成超时间的地域风格。如陈祖法《晚出西射堂》一诗“勅康乐体,并用原韵”。
散步解烦郁,悠然对西峰。青葱树如接,窅冥天欲沉。轻风吹夕阳,淡兹芳草阴。抚序增感慨,一叹情忽深。别馆来秋月,长风散空林。羁禽无定柯,能无感故心。短褐走中野,意气绝华衿。短啸忽未竟,已来松上琴[11]672。
西射堂是谢灵运出守永嘉时的居所,陈祖法仿谢诗依然运用与谢灵运诗歌相似的意象,延续了其诗对山峦重叠、草木葱茏、羁鸟旧林之景的重点刻画,保留了谢灵运诗歌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但受北方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谢灵运诗歌中形成的文学地域传统又有所不同。如“西岑”“西峰”,同样是运用“山”的原型,但“岑”与“峰”的运用,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地域风格特点。“岑”,《说文解字》是指:“山小而高”[12]439,多指南方峻峭小山。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有:“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13]35“峰”,《说文解字》云:“峯,山耑也。从山、夆声。”多指北方广阔大地连绵山脉之高而尖的山头。“青翠”与“青葱”,“岚气阴”与“芳草阴”,“揽带缓促衿”与“短褐走中野”等,虽同样运用草木意象,南方云蒸霞蔚、氤氲朦胧之气与北方水草秀美、干燥爽朗之气有显著不同。在人文景观方面,易于进行土地劳作的平民粗布短衣与贵族长衫紧衣也有鲜明对比。与谢灵运诗歌一致,陈祖法仍然承续其“清”的艺术风格,如“青葱树如接,窅冥天欲沉。轻风吹夕阳,淡兹芳草阴”。由近处清风到高空夕阳,由青葱树林到淡淡芳草,从景物的高低、远近的变化,通过白描的手法整体构造出“清空”的艺术氛围。陈祖法将北方审美情趣注入摹写谢灵运南方山水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南北方区域文化的不同特点,深刻实践了“江山之助”的创作原理。总体来看,清人仿谢诗突出了谢灵运诗歌在意象选用、意象结构安排、时空情境构造等方面的特点,塑造出专属谢灵运的独特景观文化。
清人仿谢诗的出现说明谢灵运诗歌在清人眼中是具有典范意义、可学习的诗体。通过模仿谢灵运的诗歌,清人将主体精神带入谢灵运所创造的永嘉山水世界。同时,清人通过句式的化用、意象的选择与设置、整体艺术风格的呈现等感性体会、理性分析方式,又重塑了永嘉景观,形成南北方文艺风貌交织的新的文学地域风格。这一由内而外的艺术构造过程,既客观反映出一种谢灵运诗歌在清代经典化的方式——内化永嘉景观,又实践着文学地理学所谓“超时间的空间风格”理论②。
三、清人通过永嘉景观产生情感共振
清光绪《永嘉县志》云:“谢康乐为郡,好游名山,由是此邦山水闻于天下。天下之士行过是邦者,亦莫不俯仰留连吟咏不辍,以诧其胜今,故略为采掇附之。”[3]21蔡克娇也说:“今温州各地存有纪念谢灵运的遗迹有二十多处,这是历代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吏都不曾享有的。主要有:康乐坊、竹马坊、谢池、谢池巷、池上楼、西堂、谢公村、飞霞洞、谢客岩、西射堂、谢公岭、鲜澄阁等等。”[6]28自谢灵运遍览永嘉诸地,永嘉山水变成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向往的精神栖居之所。以清代为例,如龚鼎孳的《富春渚用康乐韵》《七里濑和康乐韵》《留别黄石公用谢康乐南楼望所迟客韵》,沈季友的《七里濑和谢康乐韵》、王廷灿的《七里濑吹谢康乐韵》、叶矫然的《富春渚用康乐韵》、施闰章的《泊富阳》《谢公岭》等,以用永嘉地名、和康乐韵的方式,来彰显对永嘉山水的神往、对谢灵运诗歌的推崇。“谢康乐体”“康乐韵”“七里濑”“富春渚”“谢公亭”等已成为指代谢灵运诗歌及永嘉山水的符号。
康熙元年(1662)十月,为避通海案,朱彝尊与王世显同行共赴永嘉。康熙二年(1663)春,朱彝尊游历永嘉松台山等地,其间创作了《永嘉杂诗二十首》。其中《春草池》《西射堂》《谢客岩》等诗[14]83,以地名为题,所到一处,便怀谢公。
谢公去已久,空余池上楼。春风园柳色,朝夕使人愁。《春草池》
已见官梅落,远闻谷鸟啼。愁人芳草色,绿遍射堂西。《西射堂》
朝看白云飞,暮看白云宿。闻有山阿人,曾歌白云曲。《谢客岩》
朱彝尊居永嘉期间游历赋诗,“忧愁”“孤独”“思乡”是其诗歌的主题。朱彝尊于康熙二年七月初七曾作《七夕》诗抒故乡之思,面对秋景对月怀人,其《永嘉杂诗二十首》对永嘉景观的描写,均以“愁”为情感基调。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因卷入上层权力斗争,以“构煽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被迫离京外任永嘉太守。永嘉山水虽清新明丽,但落寞孤哀、忧愤愁思的情绪始终萦绕在谢灵运心头,其诗歌中一个疾病缠身、困顿忧苦的诗人形象,始终若隐若现。如《富春渚》称:“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15]45《七里濑》云:“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15]51朱彝尊为避祸远赴永嘉,面对家无斗储、福祸难料的现实,忧愁苦闷的心情始终无法排遣,面对永嘉山水,也发出“春风园柳色,朝夕使人愁”“愁人芳草色,绿遍射堂西”的慨叹。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满园春景,更增添了朱彝尊无穷的忧苦。“如逢秋水生,我亦西归客”想到自己与谢灵运一样都是永嘉过客,羁旅伤怀、何以为家之感更溢心间。此时,朱彝尊真正体会到谢灵运内心无限的哀愁,欲用永嘉美景充溢眼眸、填充无所依傍的内心,但是一时享乐之后便又陷入更深的愁思之中。
因谢灵运,永嘉客体自然被注入观赏者的主体精神,永嘉山水也逐渐成为一个情感符号,从此有了“孤”“愁”等悲美情感所指内涵。观览清人仿谢诗可知,谢灵运诗歌中哀禽、羁雌、迷鸟、衰林、故林、空林、荒林、春草、秋月、孤客等带有感伤色彩的意象进入清人的诗歌,谢灵运诗歌中所刻画的独特永嘉地域风格也进入清人的仿谢之作。钱陈群曾作《岁暮,舟经武原旧居,慨乡里习尚不敦古处,感而有作,用谢灵运登池上楼韵兼效其体》一诗,虽是写其故乡武原之景,但其仿谢灵运在永嘉所作《登池上楼》,也带有永嘉山水的影子。其诗云:
朔风振逸响,倦羽遗孤音。云烟相蔽遮,水天互浮沉。喧散贸初退,农安力既任。远帘招隔岸,近帆失前林。即景一领略,观理默鉴临。俗薄积倾轧,我静忘巇嵚。晏岁婴众感,寒霄结曾阴。巨川接密罟,野田来饥禽。客怀悲故土,衰绪余微吟。自怜遂初服,终叹寡同心。执德亮犹昔,委情匪自今。[16]389
“云烟相蔽遮,水天互浮沉”与谢诗“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异曲同工,均写远、近、上、下景物的相互映衬、相互对仗,构造出水天相接、云烟交织的空间景观。“远帘招隔岸,近帆失前林”一句突出河岸之曲折回环,舟行远处可观隔岸之景,行至近处则山岭遮挡处无法领略前林美景。汪学金《集王雁湖斋分拟谢康乐登池上楼》一诗也有:“广川罄窈曲,层峰辨崎嵚。”[17]431山峦稠叠、曲岸州渚是谢灵运山水诗着重刻画的永嘉自然地理特点。谢灵运有“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15]41诗句。萧驰认为,谢灵运对“江南山水之间由山峦和陆滩延至水中的汀渚沚湄之曲线美颇有领略”[18]94。水之湄柔和的曲线模拟着诗人心中(眷恋故土)依依之情[18]95。谢灵运送从弟惠连诗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隐汀望绝舟,骛棹遂惊流。”[15]166诗通过迂回蜿蜒的山水、时而隐现的孤舟,表达谢灵运对亲人的不舍和留恋。“客怀悲故土,衰绪余微吟。自怜遂初服,终叹寡同心。执德亮犹昔,委情匪自今”“惠风荣故卉,暄阳悦时禽。超化契任钓,伤羁感舄吟”[17]431,由景入情,在自然景观的新旧变化中,诗人慨叹惠风故卉、年华易逝,羁旅伤怀。
由此可知,清人无论是在永嘉当地创作诗歌,还是超地域写作,均借永嘉景观表达其与谢灵运相似的生命之感、时光之叹。诗人通过永嘉景观产生的情感共振,体现出超地域的情感风格的一致性,而这种情感风格也是超时间性的。
四、结 语
通过分析清人对谢灵运诗歌的仿作,发现谢灵运山水诗所建构的永嘉景观,已经成为清人对永嘉山水的文化记忆。永嘉景观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地理符号与谢灵运及其山水诗之间构成了紧密的意义联系。清人所作仿谢诗,虽以谢灵运诗歌为参照对象,但不是完全没有主体精神的参与,清人在接受谢灵运所塑造的永嘉景观的同时,从主体内在审美倾向、诗学理想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构,呈现的主体内在意识空间对永嘉景观进行的转化—生成,可谓一种内时间意识③的经典化方式。此外,从文学地理批评的角度看,永嘉山水既是谢灵运进行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境,又是其山水诗的表现对象,构成了一个相对具体的“地理场”④。谢灵运被贬永嘉,满怀忧思游览永嘉创作山水诗,满足了场合这一条件;永嘉自然地理及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具备场地及场景要求,符合陶礼天所云由场所、场景、场合所构成的微地理空间。同时,永嘉这一微地理空间,不仅参与了历代文人的文艺创作,且由此产生了相似的文学艺术风格,形成了永嘉文学艺术传统。谢灵运之后,南宋永嘉四灵诗派显赫一时,其诗歌所具有的清新风格及平淡简远的意境,从某种程度上说离不开永嘉自然及人文景观对其产生的内在影响。
注 释:
① 赵毅衡云:“符号,即发送者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对方(这对方可以是人、其他生物、甚至是有分辨认知能力的机器)能约定性地了解关于某种不在场或未出现的某事物的一些情况.”此时“永嘉”便不仅仅是一个表示行政区域划分的及地理位置的称谓,更与谢灵运在永嘉创作的山水诗及诗歌呈现的清绮之风、佛学顿悟之辩等文化意义内涵有着直接联系.参见赵毅衡于199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符号学》第5页.
② 关于“超时间的空间风格”,笔者认为清人对谢灵运诗歌仿作,既继承谢灵运诗歌中所写永嘉山水的原有基本地域性特征,但又注入清人所受北方地域文化风貌的影响,而构造出融合南北方文学地域特征的新的永嘉景观,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谓是对“超时间的空间风格”理论的实践.
③ 指排除经验客观外在时间的“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参见埃德蒙德·胡塞尔于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由倪梁康翻译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第35页.
④ 参见陶礼天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十周年·江西高端论坛”所作题为《微地理与文学空间若干问题新思考》的学术报告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