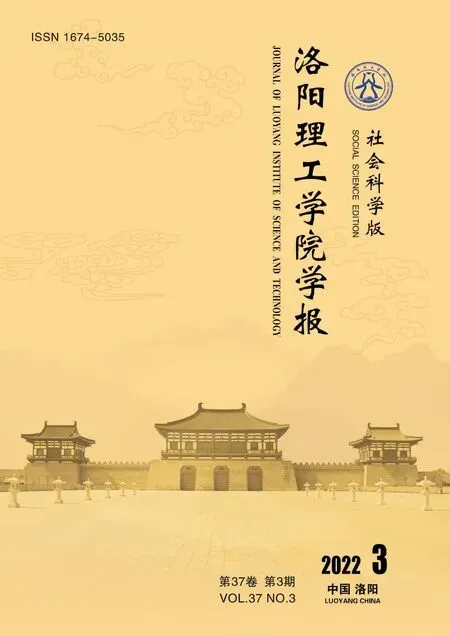论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历史书写与艺术表达
邹 菁
(人民网国重运管中心 科研管理部, 北京 100733)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全景式地描摹了1915~1921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等重大事件和人物群像,成功地运用艺术形式呈现历史价值,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自开播以来,该剧好评如潮,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片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佳作。
一、打破常规思维限制,历史书写时代人物风骨
《觉醒年代》能够脱颖而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打破常规思维限制,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塑造一批具有争议但贡献巨大的历史人物、在近现代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时代印记的知识分子以及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人物等,真实还原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人格魅力。
《觉醒年代》创作者搜集大量史料,并对历史知识进行深入钻研,考证最新研究成果,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大胆选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陈独秀作为主角之一,首次正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探索过程。《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主席说过,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党。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主席的话距今已经76年,但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陈独秀的这个功劳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1]《觉醒年代》编剧敏锐地抓住历史的这个闪光点,实事求是地还原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弥补影视剧对这段历史的创作空白。
《觉醒年代》对于蔡元培、胡适等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给予真实的历史还原,肯定他们在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文化、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等方面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觉醒年代》用素描线条简单勾勒陈延年、陈乔年等早期共产党员,展现他们舍生取义的高尚人格和高尚道德。这些民族精英20多岁就慷慨就义了,随着他们的生命消逝在岁月长河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革命事迹,直到《觉醒年代》的火暴出圈和影像传播,让观众重新了解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牺牲。这种对历史人物塑造的创新性突破,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新鲜感,而且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正如编剧龙平平所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体现编剧的历史观,反映编剧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如果编剧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诠释教科书的概念,人云亦云,不可能写出生动故事,不可能打动观众。”[2]
《觉醒年代》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创作经验:要想突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难题,就要冲破固定题材和固化模式的拘囿,深入钻研和解读历史,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用影像艺术担负起“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使命任务。
二、叙事架构独辟蹊径,思想溯源诠释历史逻辑
以往的建党题材影视剧多是聚焦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是能够深刻揭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等历史大事之间因果关联的作品少之又少。《觉醒年代》从思想启蒙的角度追根溯源,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关重要的6年所发生的重大史事进行串联,用理性思维方式诠释中国共产党建立是必然的历史逻辑。这是《觉醒年代》又一个重大特色和新视点。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三件大事,构成整个电视剧的主体。三件大事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现,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由来”[3]。《觉醒年代》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作为电视剧的叙事中心,以《新青年》杂志的发展变化贯穿整个思想觉醒过程,全景式描摹中国1915~1921年这6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百态人生,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展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时间叙事脉络上来说,电视剧按照“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个历史逻辑进行思想溯源。从空间叙事架构上而言,电视剧从“红楼”延伸到“红船”。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人们熟悉了解上海的石库门和嘉兴的红船,却很少知道北大红楼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孕育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引领的思想启蒙,推动以救国为主题的五四运动,二者的交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引导社会各阶层共同思考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最适合中国的。经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仁人志士的反复探索,实践证明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是拯救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最合适的道路。觉醒是前提,建党是结果。从思想启蒙的文化视角切入,进而探讨政治历史问题,呈现启蒙与救亡、思想与政治的双重性,这样的叙事线索脉络清晰、逻辑缜密、主题鲜明,同时又巧妙地规避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编年体式的流水记录。
“人的觉醒”是思想启蒙的核心,也是《觉醒年代》的思想主题。编剧龙平平曾这样说:“新文化运动用电视剧的手段很难表现。因为它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平台是一本杂志,有矛盾冲突,但没有核心故事情节,争论的载体是文章,特别是当初新旧两派争论的许多问题,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不宜展开。所以,我思考再三,决定抓一个看点,就是新旧两派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3]电视剧运用历史辩证发展观,展现革新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思想交锋,纠正人们长期以来对新文化运动思想的误解,呈现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扬弃与创新的内在关系。革新派钱玄同提议全盘废除汉字遭到两派阵营的竭力反对,复古派辜鸿铭提出“中国精神”获得两派阵营的一致认同,这说明新旧派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碰撞的包容。电视剧将这种历史辩证发展观具体体现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段经典台词中。面对北大内部掀起的新旧文化之争,蔡元培告诫北大师生:“北大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地方,各种学术观点争论是个正常现象,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更应该兼容并包,不管是维新还是守旧,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年代之觉醒,实则是思想之觉醒。”从这个角度讲,《觉醒年代》不仅是一部历史剧,而且是一部思想剧。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切入阐释历史,赋予电视剧更深邃的思想和历史高度,通过对时代风云人物矛盾冲突的描摹,揭示风云背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样的架构让叙事更鲜活、人物更丰富、历史内涵更丰厚、创作更具新意。
三、合理想象解读人物,戏剧冲突突显细腻感情
与以往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人物进行扁平化、概念化、程式化的解读不同,《觉醒年代》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下,将真实的历史人物放入典型的历史环境合理地进行想象创作,发掘历史过程和人物性格的每一个细节,用合乎情理的人物性格冲突去展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确保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觉醒年代》用大量的细节刻画人物,让观众觉得真实、鲜活。陈独秀在日本流浪时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回国创办《新青年》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睿智的北大教授,日常生活中和常人一样喜欢嗑瓜子、涮羊肉。为开启民智,即使冒着被抓的风险,陈独秀依然坚持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即便身处监狱,陈独秀依然高唱苏轼的《定风波》,以示无惧。电视剧对于复古派人物并未简单地进行脸谱化表现,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对人物进行客观描写,寥寥数笔却极为传神地勾勒出层次分明的人物群像。辜鸿铭、林纾、黄侃、刘师培虽然复古守旧,但是他们的身上也有难能可贵的文人风骨和气节,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历史厚度。
人性化解读历史人物,选用精巧的故事进行戏剧性架构,为典型人物的刻画营造典型环境。为更好地突出人物冲突,《觉醒年代》即使虚构一些艺术化场景,仍然比较真实地呈现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当陈独秀看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后思想发生裂变,从坚持“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改造国民思想,提高国民素质,再到坚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和李大钊与胡适渐行渐远。电视剧最后一集虚构一段他们三人在山林饮酒对话的场景,从相识相知再到相离,这段 “信仰虽异,友情笃深”的故事令人唏嘘。蔡元培欣赏陈独秀,三顾茅庐邀请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同革新北大教育,二人雪中相邀以及日后相别的场景催人泪下。虽然陈独秀有敢于打破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魄力和胆量,但是他却无法克服粗暴、专制的家长制作风,也无力化解自己与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和误会。电视剧虚构陈独秀亲手为陈延年、陈乔年炒花生和南瓜子以及赶往火车站送别的场景,这段父子关系的描画突显人物间细腻的感情,具有很强的人情味。粗犷豪放的北方汉子李大钊与目不识丁的妻子赵纫兰在北大的亭子里依依不舍地话别,李大钊承诺有朝一日将在教室里一笔一画教妻子写字,让她学会后给自己写信。亭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亭内二人情不自禁地留下泪水,这样的场景似乎预言着他们的即将分离,浪漫又伤感的画面具有打动人心的震撼力。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觉醒年代》众多人物形象中,既有作为电视剧主体的真实历史人物,也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虚构出的一些人物,不管是正面的、中立的还是反面的,他们既真实又鲜活,非常具有感染力。“真正最有艺术魅力的戏剧性往往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的话,那么电视剧也是人的电视剧,以人为本、满剧皆活。这也是许多观众评论这部剧的焦点之一,教科书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这部电视剧中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可以说,艺术用自己的魅力完成历史的启蒙教育”[4]。《觉醒年代》的成功之处在于秉持以人为本的情怀,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相统一,自然而非刻意地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戏剧化的人物冲突,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塑造一个个充满艺术张力、艺术活力的历史人物。
四、艺术创作匠心独运,诗意审美表达历史深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要想更好地担负起表现革命历史内容的任务,还需要在艺术创作手段上苦心经营,以“更精准、更生动、更丰满、更立体”的创作手法,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和事件转化到荧幕。《觉醒年代》在艺术创造上进行有效的尝试和探索,成功使用隐喻、意象、蒙太奇的拍摄手法及穿插版画等艺术手段,营造东方式写意的审美效果,从而更好地表达蕴含深意的主旨内容。
《觉醒年代》使用骆驼、蚂蚁、青蛙、车辙等意象,通过隐喻的手法表达主旨,委婉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时代背景。剧中开头交代当时国内政局混乱的历史背景时,出现挂着铃铛的骆驼商队穿梭在集市,隐喻当时闭塞的生存环境。剧中也多次出现蚂蚁意象,寓意深刻。比如,陈延年放生的蚂蚁,隐喻他将踏上拯救苍生的救亡之路;陈独秀演讲时话筒上的蚂蚁,隐喻他以一己之力引领后人前行。剧中反复出现石板路上深深车辙的意象。正如导演张永新所说,“两千五百年不变的车辙如何去面对船坚炮利,只有一条路——觉醒”。剧中反复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在泥泞中行走的场景,隐喻他们寻找信仰之路所经历的艰难跋涉。
《觉醒年代》运用电影中常用的蒙太奇拍摄手法,用符号象征增加艺术深度,而富有诗意的细节刻画能充分调动观众的解读热情。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段落令人拍案叫绝。镜头里首先出现的是手里紧紧抱着油纸包(里面装的是《新青年》杂志)的背影踏着水坑疾驰,艺术化呈现路边随之溅起的水花,微妙地预示重要人物的出场。同时,镜头还将插着草签等待买家的孩子和坐在汽车里吃东西的富家孩子放在一起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当那个背影转头看向孩子和地上捡食的乞丐那刻,毛泽东的正面镜头才正式出现。这是一组非常具有节奏感的动态镜头,呈现当时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环境,“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画面浮现眼前,言有尽而意无穷。网友评论说:“人民的苦难,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觉醒年代》采用蒙太奇“闪前”方式预叙陈乔年、陈延年的人生结局,也是颇为经典的一幕,不断被社交媒体、网友所热议。陈独秀送陈延年、陈乔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父子仨人化解矛盾、依依惜别。在告别时镜头突然切入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前满身的血迹、沉重的脚镣的画面。电视剧还单独给出他们踏过血路上的桃花镜头,暗合龙华监狱墙壁上的革命诗,“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牺牲前回头的灿烂一笑与陈独秀的悲伤交织在一起,渗透出亲情的眷恋和理想的高尚,表达出耐人寻味的意涵。这种手法在电视剧中多处使用,精巧的艺术力和饱满的感染力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
黑白的影调、粗粝的线条等这些木刻版画艺术形式,配上大提琴低沉粗重的音色,穿插在电视剧的片头和片尾、重要情节的过渡、背景的介绍等关键时刻,传达叙事信息,渲染情绪气氛,引领观众反思历史。这样的艺术形式充盈着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画龙点睛地深化了主题。
“《觉醒年代》的艺术实践证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既是历史观照的富矿,也是艺术创造的富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担负着表现重大革命历史、展现革命历史规律的使命任务,但这一使命任务是经由电视剧的艺术创造来实现的。没有成功的艺术创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便不能从历史抵达艺术”[5]。电视剧《觉醒年代》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进行诗意化的艺术表达之间并不冲突,它在这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在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前提下,自觉地对历史进行诗意化的表达,用充满艺术活力的历史质感反映历史剧的厚重生命力。
五、结 语
一部优秀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必须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必须做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6]。《觉醒年代》将严谨求实的历史书写和充满诗意的艺术表达进行完美结合,忠实地复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充分挖掘艺术审美特性,用鲜活生动的影像呈现人性的觉醒、思想的觉醒、年代的觉醒,用强大的艺术创作力赋予电视剧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觉醒年代》的创新成果给观众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让许多观众边追剧、边学党史,打造出一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优质教科书。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而这正是从“觉醒年代”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传承和延续下来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对这类电视剧进行创新与再造,用艺术手段更好地体现历史价值,肩负起表现重大革命历史、展现革命历史规律的使命任务,这也是以后艺术作品要积极探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