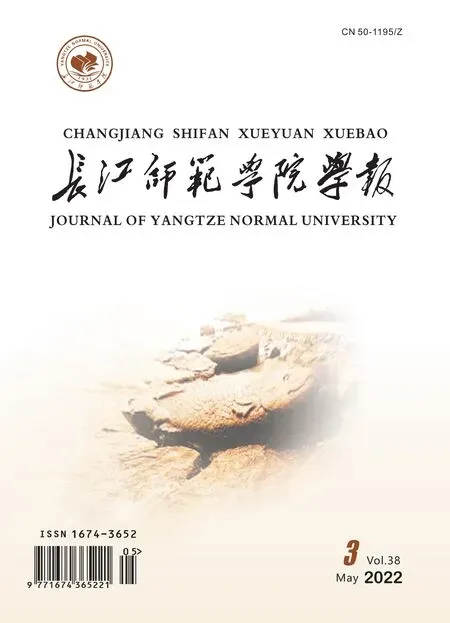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角下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的再认识
黄潇逸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命题。那么,古建筑与人的生存状态有何关联?如何在建筑领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由此出发,探讨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人类实现诗意栖居的重要意义。
一、20世纪50年代不被认识的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兼论建筑的现代性困境
(一)北京城墙的存废之争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城的规划开始有序进行。然而,面对这样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都,一个棘手的问题呈现在人们眼前:传统的遗留与现代化的发展该如何选择?
当时,人们设想未来的北京该是一座“从天安门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的工业化城市,对妨碍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古建筑应当拆除。但是,城市的建设一定要以古建筑的消失作为代价吗?身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的林徽因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她认为,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并多次发表“保存古建筑”的观点,更于1950年在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的设想,试图保留北京城墙。热爱古建筑的林徽因,甚至在一次聚会上就北京城墙的保护问题,情绪激动地与人争论道:“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1]
那么,让林徽因如此情绪失控的北京城墙,为何在当时非拆不可呢?原来,在北京城规划初期,人们采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仿照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场,以天安门为中心,把旧城作为行政中心。然而这样一来,城内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交通逐渐开始堵塞,牌楼、城楼和城墙一下子阻碍了交通,妨碍了城市的发展,于是有人主张将城墙拆除。同时,正值国家建设的热情高涨时期,有人认为城墙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必须拆除才能迎来思想上的解放,更何况城墙阻碍了交通的发展,已无存在的意义。再者,从城墙上拆下来的砖块,还可以用来造房屋或铺马路,产生经济效益。
林徽因认为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但忽略了城墙的重要价值,更何况,城墙并不是非拆不可的,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北京的城墙和巍峨的城门楼是构成北京的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不是没有生命的砖石堆,而是浑厚伟大的艺术杰作”[2]49。我们保护北京城,不应只保护个别建筑,而应将整个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保护。正如李允鉢所说:“中国的观念是十分深远和极为复杂的。因为在一个构图中有数以万计的建筑物,而宫殿本身只不过是整个城市,连同它的城墙、街道等更大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而已……这种建筑,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3]
其次,城墙并不会阻碍北京的发展。北京历经四次大规模的改建,但均没有被城墙所限制,“全城各部分是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而有所兴废。北京过去在体形的发展上,没有被它的城墙限制过它必要的展拓和所展拓的方向,就是一个明证”[2]176。至于交通问题,只要在城楼两边开豁口、在牌楼两边拓宽马路让车辆绕行便可以解决。
最后,城墙并非“封建的余孽”,它记载着北京城悠久的历史,总会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虽然它过去被帝王所占有,但“当这种建筑环境不被统治者所独占时,它便是市中最可爱的建筑型类之一,有益于人民的精神生活”[2]192-193。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城墙,封建帝制被摧毁后,这些美好的建筑成果全属于人民,它们不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而是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同时,城墙在北京市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将城墙改造成公园,市民们可以在其中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护古建筑,还可以增添市民的生活情趣。
然而,林徽因的理念却被忽视。北京城墙轰然倒塌,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独特风貌,正如郑天翔在《回忆北京十七年》中所叹:“古城风姿,为之减色。”[4]1972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重访北京,却发现城墙已被拆除,且拆下的城砖竟被用在新建筑物上,顿感痛心的他说:“我们对40年前的北京最为熟悉,并且以怀旧的心情找寻昔日的遗迹,而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却要我们去看新建的地铁。”[5]
如今,北京地铁线路越建越多,人们已不再对地铁感到惊奇,却时不时会回忆起那些巍峨、雄伟、沧桑的城墙。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当时一味对古建筑进行拆除是不妥的行为,面对残缺的城墙追悔莫及,开始复建古建筑。遗憾的是,作为北京城仅存的两处明城墙遗址之一的内城西城墙南端,在1988年却被修成了假古董。“就其形制来说,修建者显然想将其设计成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交会处的碉楼形制,但原来的碉楼是与内城城墙的敌台相接的,并非筑于敌台之上”[6],真应了林徽因当时的那句话——“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1]。侯仁之在为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中译本作序时感慨道:“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真正到来,可是旧的城墙和城门除个别者外,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令人惋惜不置的了。但愿这类情况今后不再发生。”[7]
事实证明,林徽因的建筑思想超越了功利的维度,从诗意的方向诠释了建筑对于人类生存、人与自然共生的意义。在对建筑的标准日益工具化的今天,重新认识林徽因的诗意建筑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20世纪50年代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不被认识的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10]230人类在对自然进行改造时,虽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只有建立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关系上才得以成立。马克思对此曾这样阐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现实、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0]102可知,在马克思的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绝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也绝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来讨论。
然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并未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对待自然。在马克思所预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的发展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苏联却片面地放大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崇拜科技的飞速发展、无限扩大人类的能力,提出了“像征服者那样征服世界”的口号,认为人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试图征服自然、控制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对自然的滥用和控制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苏联在“赶超”战略背景下,采用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追求有用、功效的城市建设背景下,对北京城的规划也是理性至上的,追求有用性、追求物的功效最大化,理性成了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人们更关心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林徽因提出的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城墙花园”构想,自然就会受到冷落和忽视。
然而,正如马克思本人曾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绝不能在实际运用中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建设活动,他们只是在理论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进行预测,因此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对于我国而言,不能完全套用他国模式,必须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开辟属于自己的生态发展路径。
(三)工具理性视野下人与建筑丧失了诗意的联结
在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和古建筑的保护产生了矛盾,而现代性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古建筑被视为妨碍发展的无用之物,因而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古建筑基本被全面清除。中国受苏联城市建设的影响,认为拆除城墙、修建道路、拓宽街道就意味着走向了现代化。当时主张“废”城墙者认为拆除城墙可以使北京城内外的建筑风格整体规划、协调统一,同时拆除城墙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也就是说,当时对城市的规划是建立在经济、理性、实用的原则上,首要任务是改变城市的落后,实现城市建设的优化,因此城墙的处理需要首先服从这个原则。由此可以看到,现代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是诗意地栖居,而是人和自然的分离。当工业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人们已顾不上保护历史,同时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社会新的需求也让建筑的形式不得不发生改变。
现代的建筑师要用最经济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效益,设计出具有严格功利性的建筑。现代主义大师勒·考柏西耶就曾有“房屋是居住的机器”之说,将建筑标准化的同时,更是将人也标准化。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考柏西耶便假定建筑的功能,即人的需求是“标准化的”。他认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功能。人人都有同样的需要。”[11]那么,人也像建筑一般成了可以量化的机器,这是现代人的悲哀。
技术的发展带给我们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却将我们变成僵化的标准。这些由现代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最终能依靠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吗?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到底应该诉诸何物?这些问题真的只是因为技术而产生的吗?技术本身具有这样的价值判断吗?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0]50建筑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劳动产品,但现代建筑崇拜技术、追求效率,走向标准化、程式化、机械化,最终将人排除在建筑之外。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认为“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因,经济利益是其发展的现实动因。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追求最高的效用,逐渐在社会中形成一套标准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人进行思考的。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发达的工业社会通过高度的自动化、标准化“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12]。人们从属于某一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人的自由意志被剥削,人本身就异化成了具有机械化标准的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由头并不在技术,实质是资本的逐利行为让人们无法诗意地栖居。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大力发展现代建筑,造成极大的环境破坏,人们骄傲地改造和利用自然,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随之出现的是水土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口爆炸性增长、农耕土地退化、城市交通堵塞这些问题,同样令人反思。经典的现代建筑充分彰显了工业文明的价值追求:高效、经济、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们已经认识到仅有理性并不可取,文化、性格、传统才是好的建筑的内核,同时建筑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至关重要。人与自然应该是平等互存的关系,“人及其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同一生命体系中的构成部分,破坏其中的某一个部分就意味着对整体的伤害”[13]。
二、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的本质探究:诗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在北京城墙争论战中,为什么林徽因对古建筑葆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林徽因的城墙公园构想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林徽因在建筑生涯中始终坚持的信念是什么?其实,如果回溯林徽因的建筑生涯,甚至延伸至林徽因的整个人生,我们就不难发现,“诗意”是她身上最大的特点,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均蕴含于“诗意”一词中。对林徽因而言,诗意不仅是她进行建筑事业的具体准则,更内化成她的生活方式。令人惊奇的是,林徽因的诗意建筑理念与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都不谋而合地指向同一个地方——人应该诗意地存在于大地之上。
(一)林徽因诗意建筑理论:“建筑意”即“诗意建筑”
“诗意”是一种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诗意”即无遮蔽的人的本真,“诗意建筑”便是体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的建筑。林徽因曾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提出“建筑意”这一概念,她认为,建筑中“美的所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2]223。这里林徽因提到的“诗意”是文学范畴中的“诗”。如果扩大范畴,将诗的概念延伸到“人的存在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林徽因所说的“建筑意”便是在建筑领域中“人的诗意存在”,是一种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吻合的以人类的现实关怀为基础的诗意建筑理念。
“建筑意”首先在空间上便体现出与“诗意”相同结构的深刻一致性。在林徽因看来,建筑需要经过“人的聪明建造”,并且这种建造需要体现有作用的、有机的、适当的结构之美,这种建筑美是不脱离实际的、不矫揉造作的,坦诚地体现内部材料本质的自然之美,具有天然的诗性。建筑中的这种“诗意美”是通过结构呈现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与人的互动中才得以呈现,人在建筑空间中运用心灵感知,引起自己与建筑之间“特殊的性灵的融会”,才赋予了建筑在空间上的意境和诗性。这种心灵的融合相通,在哲学意义上便是人的自由解放的“诗意”状态的展现。
“建筑意”与“诗意”的相应关系,不仅体现在审美的空间维度上,还在时间维度上有着更为厚重、沉甸的表现。林徽因提出的“建筑意”概念强调建筑的生命力需要“受时间的洗礼”,要经过“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才得以旺盛生发,这是建筑的文脉所在,也与“诗意”的时间性相吻合。真正具有诗意美的建筑是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洗,在社会的变迁中生成、发展、积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这种美与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保持着和谐的一致性。时间维度上生成的“建筑意”是对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进行的具体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见证,同时在见证中丰富自己、传达自己,并且在与后人达到灵魂相融时让后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确证了自己的存在,达到了自由舒展的“诗意”状态。
林徽因提出的“建筑意”概念,从人的存在性问题出发,与“诗意”的概念具有内在的深刻一致性,因此可以将“建筑意”看作诗意建筑。
(二)人与历史的和解:“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为什么现代人的漂泊感越来越强?如何让广大人民能安居在新中国?林徽因在建筑生涯中不断地追问自己,并且在实践中一次次完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海德格尔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8]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此处所指的诗,并不是纯粹的文学范畴,而是从栖居的本质或者说是生存的方式解释诗的含义。因此,此处的诗人也并非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作诗之人,而是指从事建筑活动的人,进一步放大范畴来讲,是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
认真审视海德格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的“还乡”,实质上为漂泊无依的现代人寻找心之安处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返乡即是回到生命本源的地方,得到生命状态最大程度舒展的可能性。马克思将人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考察,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也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人创造了历史,人在历史中生成自己,因而人必然也从历史中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
因此,我们也就能明白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明白古建筑、历史遗迹等为什么对当代人实现心灵的安居如此重要了。人类的文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成了历史和文明忠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成了历史和文明的一部分。林徽因曾这样讨论建筑和社会文明的关系:“建筑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与习俗风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13我们保护古建筑,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记忆,保护我们的元初,保护我们的本真。从哲学层面讲,古建筑的存在,能让我们更加接近“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能让我们更加明晰未来“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拥有历史,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发于此,源始于此,我们那些关于“存在意义”的苦苦求索都在历史的烛照中渐渐得到回答。
至此,我们对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北京市民而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墙根下,北京城墙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心中有着重要地位;对全中国人民而言,北京城墙是记载着朝代更迭、新生活开始的重要建筑,也是北京独特都市风貌的表现之一。林徽因认为,归根结底,北京城墙承载着我们的历史,它的存废不能仅从理性的角度思考,还要从历史、情感的角度思考,“新中国的建筑师‘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2]51。拆除北京城墙,无异于将过去抹灭,会造成我们记忆的残缺。一座又一座的古建筑拆除之后,我们与这座城市的联结也渐渐消失。我们面对崭新的城市,它十分现代,充满着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仿佛这就是“新世界”该有的模样,却只觉得僵硬、冷漠和陌生。所以,面对已经失去效用的古建筑,我们不应该一杆子推掉,而应设法将它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正如林徽因当初所提出的“城墙公园”设想,实现人与历史的和解,只让我们心有所依,才有可能安顿漂泊的心灵。
马克思认为,文明如果只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的发展,则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荒漠[9],在这里,“自发”和“自觉”是两个关键。如果文明始终“自发”地朝着未来发展,也就是盲目地开展现代化进程,那么我们会失去很多“习俗、习惯和信念”,成为没有身份识别的流浪者。
那么,文明应该如何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转向马克思所言的“自觉的发展”。既然建筑也是文明一部分,那么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建筑文明也应“自觉”地发展。怎样才算是“自觉”的建筑呢?我们先看林徽因是如何批判工业时代“不自觉”的建筑的。她曾说:“以‘革命’姿态出现于欧洲的这个反动的艺术理论猖狂地攻击欧洲古典建筑传统,在美国繁殖起来,迷惑了许许多多欧美建筑师,以‘符合现代要求’为名,到处建造光秃秃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筑。中国的建筑界也曾堕入这个漩涡中。”[2]43在工业化、机器化的背景下,建筑也“自发”地走向更具效率、更具实用功利的一端,然而这种建筑缺少生气和灵魂,它们只做到了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却没能和人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所以,“自觉”的建筑应该体现人的精神性。林徽因认为诗意的建筑应该涵盖更多的可能性,要在满足人类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赋予人们更加丰盈的情感体验和生命觉知,“作为能满足物质和精神双重要求的建筑物来衡量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筑,它们是没有艺术上价值的,而且应受到批判”[2]43。如今全球化带来的建筑趋同势头愈发猛烈,建筑的多样性和地域文化逐渐丧失,没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建筑犹如丧魂之人,建筑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从林徽因对北京城墙的珍视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林徽因眼中的诗意的建筑,不仅要满足人们物质上的安居需要,更要与人们在精神上达到契合。如果我们从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不难领悟到建筑与人的存在问题紧密相连,林徽因的诗意建筑理念,能帮助现代人摆脱工业背景下僵硬的理性建筑的桎梏,在大地上舒展生命本真的状态,进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还乡亦是人的自然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绝不存在主客体之分,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0]52。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再深入地讨论“还乡”这个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还乡”还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复归。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包括“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就“人的自然化”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人的自然化,即人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的自然化。人与自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融合、共生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内在人的自然化,也就是说,人的情感、知觉和感想与自然发生碰撞,产生不可言说的心意相通。林徽因的诗意建筑理念正是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人类应该用何种方式寄寓于自然之中?人在居所中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林徽因在考察中国古建筑时,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现的是对于自然的敬畏,而非征服和控制,建筑的结构也处处体现出和谐之道,她对山西民居与自然之间的巧妙融合曾发出这样的惊叹:“外墙石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筑造,楼居其上。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2]281山西民居的墙壁与山崖相互缠绕、相互盘旋,建筑与自然仿佛融为一体。这样与自然和谐相生的中国传统建筑,除了山西民居,还有很多。福建的土楼、傣族的竹楼等民居均体现了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亲和的思想。此外,不只是民居,中国的传统园林更是将山水、建筑、人三者的融合发挥到了极致。这些便是诗意建筑理念中蕴含的外在人的自然化的思想。
至于内在人的自然化,林徽因更是有独到灵动的见解,她创新性提出的“建筑意”的概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十分诗意的诠释:“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2]223可以看到,好的建筑能在自然中引起人的共鸣,这是在理性层面无法解释的,但它却又真实地存在,它是一种更高价值的思考,包括人类应该如何存在,以及如何与自身所寄居的世界相处。这种感觉就像林徽因看到大同善化寺的雕像时所描述的一般:“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瞪目咂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2]73
在林徽因看来,要让建筑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居住状态,就必须尊重非理性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别的,正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人的良知良能是超越功利性的心灵感悟,这种心灵感悟则正是诗的本质体现。返乡,就是回到历史、回到诗、回到良知。
三、林徽因诗意建筑理论对现代性的超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重新审视林徽因的诗意建筑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生态问题的认识上放大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05年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我们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提供了指引。
马克思强调人依赖自然界而存在,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只有与人发生对象性关系,打上了人的主体意识的烙印,才是真正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界。在马克思所建立的人化自然观中,能从自在的存在物转化为自为的存在物,能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出发认识自然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支配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按照人类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改造自然界的目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不计后果地盲目对自然进行改造,要改变“人为自然立法”的错误价值取向,明确价值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提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0]104,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因此建筑也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对于统治阶级这个对象物而言,是王权的象征,但是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则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对象会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条件已经改变,对于人民群众而言,王权已经解体,城墙已不再是封建王朝的象征。当时林徽因从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封建王朝灭亡之后,建筑便是劳动人民共享的果实。
新时代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美学观的辩证统一。由于社会历史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美学从一开始便以艺术的社会效应为主题,要求艺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必须反映批判精神。但是,这种美学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李泽厚认为:“所以,从理论传统和实践传统看,马克思主义美学这种特征是有其时代历史的原因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在艺术——美学领域中的体现。这就是我们所习惯了的马克思主义学。”[14]37这样的艺术和政治紧密相连,功利性遮蔽了艺术的无功利性,即诗性。
北京城墙的拆除实际上也是与革命分不开的行为。城墙的“废”“存”不仅关系着现实语境中的城市建设问题,而且意味着封建和解放的选择。北京城墙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墙,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墙。主张拆除的人认为城墙会给人们留下皇权至上的印象,拆除北京城墙有利于人们思想的彻底解放。
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随现时代的需要和特质来发展自己,否则就难以生根发展。“坚持不是发展,发展才是坚持。”[14]41我们不能仅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角度看待美和艺术,更应该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生存困境的消解来研究美和艺术。在建筑审美方面,现代性建筑强调规律性服从目的性的美,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因此,需要通过个体感性与大自然的交往来进行补充和纠正,这正是林徽因诗意建筑中所倡导的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的人化”美学观的体现。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0]53人类的社会生产对大自然的改造使自然界日益成为人的对象,人不仅在生产劳动中使自然对象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且在思想和情感上使自然界从精神上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产对象和生活资料产品,也是人情感的表达工具。人们建造的建筑也成为人类自身延展的一部分,代表人类想要呈现的自我形象,即建筑如何面对自然环境体现了建造者自身如何面对自然环境。建筑对自然界是部分之于整体的关系。“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0]53建筑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同样也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这种美源于自然并且展现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
(二)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再认识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的现实意义
虽然林徽因对北京城墙的“城墙公园”设想没有实现,但为后世保护与利用城墙提供了新思路。国内许多城市,如西安、南京、苏州等,均围绕古城墙修建了公园,既保护了古城墙,又展示了城市的历史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城墙公园结合了古城墙、绿化带及历史景观,充分彰显了城市的人文风光和生态图景。最初,南京围绕城墙结合周边的自然景观、地形地貌,形成环绕城墙的公共绿化风光带。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系统逐渐建立,护城河的水治理逐渐完善,以城墙为背景的绿化带演变成可供行人慢走、游览的公园。南京城墙公园并非独立的存在,还结合了周边的历史文化景观,如雨花台、太白亭和范蠡筑越城雕像,在不同的城墙段营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氛围。南京的城墙公园可谓是林徽因“城墙公园”构想的现实成果,体现出人工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在展现城市历史的同时,保护了古建筑,也带动了南京的旅游发展。
建设美丽家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古城墙之类的古建筑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产物,也是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在今后的发展中,建筑更应注重与自然的融合,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林徽因从建筑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古建筑之于现代建筑发展的借鉴作用、古建筑对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作用、建筑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些都是美丽家园建设的重要议题。
进一步说,美丽家园的建设更涉及精神文明的建设,包含对后代的心灵塑造和人格培养的问题。美丽家园突出的重点是“美丽”,那么何为“美丽”呢?新时代背景下,对“美丽”的定义绝不只停留在经济理性上,而是从人类本体论的哲学角度出发,讨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林徽因诗意建筑理念中包含了对这种“美丽”的追求,超越了形式和功能,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灵自由,应为新时代建筑美学带来更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