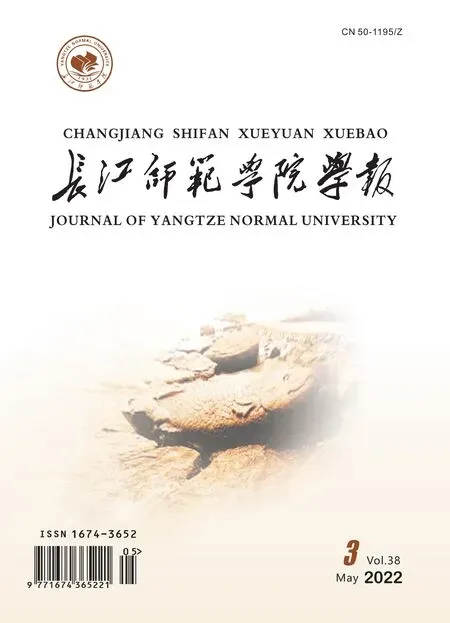唐诗中的丝缕意象
周凤莉,尹英杰
(1.哈尔滨学院 文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2.哈尔滨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唐诗多寓情于景,与画相通,画面中浮动的线条,无论长短、粗细、曲直,皆为“有意味的形式”①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说:“线条、色彩在特殊方式下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每一根线条都对应着诗人特定的情感。唐诗中的线意象丰富多元,其中,丝缕意象尤为动人,是重要的审美对象。丝缕意象空灵飘逸、纤柔曲婉,弦外之意含蓄蕴藉,读来韵味悠长。
一、“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女红”题材中的丝缕意象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1](卷372,4193),孟郊的这首经典之作,旨在吟诵母爱的深沉和伟大,它呈现主题的场景和动作堪称经典:慈母穿针引线,将对即将远游的儿子的深情缝进密密麻麻的针脚中,那穿梭回绕的细线被赋予了别样的深意,具有动人的美感力量。文学作品中那些缝补织绣的画面在丝缕的流转、绵密中定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红”与女性的密切关联。“女红”是女性重要的活动,是女性力量得以被确证的要点,与女性的命运紧密相连。嫁为人妇之前,女性需要完成个体仪式化的成长,其中就包括“女红”技能的获取,女性甚至需要拼尽青春之力来获取这项技能,以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的刘兰芝即为典型代表。围绕丝缕意象关注唐代诗歌中的女性,能提供研究女性的多元视角,使对唐代女性的认识更立体。
李益的《莲塘驿》:“江村远鸡应,竹里闻缫丝。”[1](卷282,3205)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的缫丝之声和鸡鸣声,暗示了缫丝劳作的辛苦,鸡鸣声暗示缫丝人晨起需赶早。白居易《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中的“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1](卷427,4714)。这一句道出了缫丝、捡丝、练线、染色这一整套工艺流程,也暗示了女性劳作的艰辛,她们需长期劳作在丝缕萦绕的环境中。杜甫的《白丝行》“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1](卷216,2256)中,明确要求丝要长,不能断,断则短,短的价值就会降低,就难以织成上品的越罗、蜀锦,反映了缫丝工作难度与强度并存。
缫丝之后的工序是织丝成匹。鲍溶在《织妇词》中说道:“百日织彩丝,一朝停杼机。”[1](卷487,5575)“百日”这一时间修饰语道出了织丝成匹的辛苦,它需要女性专注于织布机前,耐得住寂寞和枯燥,日复一日地重复相似的动作,是对体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诗歌的描述虽简洁易懂,但韵味无穷。不难想象,织妇在停机杼的那一瞬间,可能会因大功告成而获得片刻的轻松、愉悦,但一想到自己辛苦织就的锦缎只能在自己眼前、手中作短暂停留,最终成为富贵人家女性身上的华服时,女性眼角、眉梢笼罩的忧思愁绪使得诗歌的意蕴又多了一层。
和前两道工序相比,绣的“锦上添花”之意淡化了这项工序的艰辛感、沉重感,尤其是个体性的绣的动作,能激发女性身上的美感特质。因为绣的动作纤巧、精细,所以在绣的过程中,女性往往呈现出曼妙优雅、专注娴静的姿态,女性的柔与静、巧与慧的气质得以淋漓尽现。女性绣的图景本就已经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如果诗歌再借此画面来抒发女性内心细腻、敏感的情思,诗歌中叠合的味道就更耐人寻味。朱绛的《春女怨》:“独坐纱窗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1](卷769,8820)该诗中女子伤春意无限,却不知道诉与何人听,一人独坐,意态慵懒,行针走线的动作异常缓慢,最后索性停针不语,不是黄鹂的叫声扰人,而是心绪不宁又如何能专心刺绣呢。诗歌以“绣”这一动作来暗示女性的心理,赋予抽象情感以具象呈现,构思精妙。白居易的《杂曲歌辞·急乐世》:“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秋思冬愁春恨望,大都不得意时多。”[1](卷27,389)该诗中的女子正在聚精会神地抽线、绣花,忽然的一声黄莺叫,惹得女子蛾眉微蹙,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将女子的满怀愁绪巧妙地传达出来。白居易的《绣妇叹》:“连枝花样绣罗襦,本拟新年饷小姑……针头不解愁眉结,线缕难穿泪脸珠。”[1](卷448,5075)此诗中的女子,起初是赶着时间,于针头线缕间,忙碌不停,但当绣花图案中的连枝花样引发了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后,她陷入了莫名的悲伤中难以自拔,泪流满面、愁眉难解,再无心绣花。
唐诗中经常提到“针”这一意象,“针”与“线”作为意象组合是互不相离的,如果不是极其特殊的情况,“针”的出现也意味着“线”在场。唐诗中屡次提到刺绣用金针,以金针刺绣同样具有深意,针是女性施展自己才艺技能的重要工具,女儿家对针格外重视。金针强调的未必是针的金属属性,而是针的社会属性,强调针对女性的重要性,另外,女性往往将自己复杂细腻的情感融入一针一线的动作中,所以金针也是反映女性的重要艺术意象。韦庄的《清平乐》:“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1](卷892,10147)晁采在《子夜歌十八首》写道:“感郎金针赠,欲报物俱轻。”[1](卷800,9096)刘言史在《看山木瓜花二首》说:“深藏数片将归去,红缕金针绣取看。”[1](卷468,5356)这些诗句均在用金针巧妙地暗示女性的处境与心意的作用。
围绕丝缕意象展开的劳作对女性的要求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劳动强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技巧性的要求,它要求女性心明、眼慧、手巧。女性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双巧手,七夕的乞巧习俗,代表了女性这一强烈的诉求。七夕之夜,女性会虔诚地祭拜织女,积极参与到穿针引线的竞赛中。在比赛中,能够穿过七枚针孔者“得巧”,穿不过的则“输巧”,唐诗中对此多有“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1](卷130,1327),林杰在《乞巧》中的“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1](卷472,5392),王建在《宫词一百首》中的“每年宫里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1](卷302,3443),权德舆在《七夕》中的“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1](卷329,3682),施肩吾在《乞巧词》中的“不嫌针眼小,只道月明多”[1](卷494,5631)。这些诗句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七夕乞巧的盛况:热闹的场景、虔诚的祭拜礼、专注的模样、不服输的神情都一一展现出来。这是一场高度仪式化的文化活动,更多地满足的是女性的心理诉求。但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展现的却是女性现实生活中最常用的生存技能——“穿针引线”。因为是借着月色穿针,针孔小、丝线细,加上风力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能够迅捷、顺利穿过七孔针的女子一定不多,唐代诗篇中也描述了这一动作的难度,正如沈佺期在《七夕》中的“月皎宜穿线,风轻得曝衣”[1](卷096,1028),祖咏在《七夕》中的“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1](卷131,1335)。所以,最终拔得头筹者,皆为眼力不凡、技法高超、具有神闲气定之功力者,她们努力做到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所有人为设定的障碍都旨在使女性在仪式中完成心理的蜕变,使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对自我的内在需求。
丝缕轻盈、精妙的美感遮蔽不了其背后的沉重感与苦痛感,锦衣华服、绫罗绣缎的背后流淌着底层民众的血泪,诗人对此进行了冷峻地审视。白居易的《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中那软、暖、厚的红线毯背后是“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1](卷427,4714)。在《缭绫——念女工之劳也》的“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1](卷427,4715)中,“缭绫”的织成意味着织女要忍受“丝细缲多女手疼”,要承受“扎扎千声不盈尺”[1](卷427,4715),无休无止的劳作。白居易通过这两首诗歌揭露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表达了对劳苦女性的深刻同情。在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1](卷636,7347)中,诗歌以简练、晓畅的语言道出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二月”“五月”,表明这是以提前预支的方式来维持当下的生活,明知卖青意味着损失惨重,将来的生活会更窘迫,但也只能如此,“眼前疮”若不治,将后患无穷,只能以“剜却心头肉”的方式来医治眼前疮。在此,生活的逻辑被逼迫成悖论,诗歌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二、“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渔钓”题材中的钓丝意象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渔钓”意象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是隐逸文化的表征,唐代诗人充分借用这一隐逸符号,在诗歌中表达自己淡泊明志、退隐江湖的情怀指向。“渔钓”意象包含一整套艺术符号,从主体到客体、从整体意象到局部意象,皆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意蕴。鱼钓意象中的钓具包括钓竿、钓钩、钓线(也称钓丝)钓饵等,它们频繁出现在诗篇中,多为鱼钓意象的指代符号,往往以个体代整体,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时往往缺少对其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关注。钓丝作为钓具的一部分,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其鲜明的表征中蕴含着独特的韵味:钓丝的两端,一边是钓竿,一边是钓钩,钓竿与钓钩的物质属性偏硬、偏刚,钓丝的轻飘灵动,促成了以柔连刚,使整个钓具意象流畅、圆满,为渔钓图景的寂寥与旷远之境添加了动感,使得鱼钓者在动与静的结合中感悟人生、洞察宇宙。
韩愈在《赠侯喜》中写道:“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1](卷338,3794)诗人惊喜于预感到的“忽有得”,于是举竿引线,线之下是诗人满怀的期待,但是等线与钩脱离水面之后,诗人的惊喜瞬间落空,因为钓到的是只有一寸、才分鳞与鬐的小鱼。诗人内心的落寞可想而知,伴随着钓线沉、起的时间落差,诗人情感的落差也一并而生。这暗示了诗人仕途的坎坷:长时间的无鱼可钓,比喻官场上长期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半生已蹉跎,好不容易偶遇机运,但这微官、卑职却再难激发中年人的壮志雄心,理想和抱负终究没有得以施展的舞台。船子和尚在《拨棹歌》中的“千尺丝绦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2]20,流淌的是禅意和玄理。“千尺丝绦直下垂”极尽夸张之能事来形容钓线之长,钓线的出场,意不在鱼,钓线钓的是心灵的获释与圆满:钓线是一道界线,隔开了水面上下,也是一条连线,悬垂于天地之间,将天象、水纹、人情勾连在一起,达成化境,实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如果没有了这条线,“渔钓”意象就不再完满。一根千尺钓丝意象将虚实结合在一起,使诗歌开篇立意极高,为诗歌营造了高远、玄妙之境,也为下文的波动、船空、载月辉而归作了铺垫,使得诗歌中充盈着禅意,诗歌最后的悟禅在开篇就已经通过钓丝的悬垂埋下了伏笔。李群玉在《钓鱼》中写道:“七尺青竿一丈丝,菰浦叶里逐风吹”[1](卷570,6667),形象地勾画了钓竿与钓线的长度比,钓具的讲究与其说是在意钓的结果,不如说在意钓的过程和情致,一丈长丝,悬垂于水面之上,动与不动,都是天地之间、湖泽之畔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李贺在《钓鱼诗》中写道:“菱丝萦独茧,蒲米蛰双鱼……长纶贯碧虚。”[1](卷392,4429)“菱丝萦独茧”“长纶贯碧虚”两句强调钓丝用线讲究,需要用高等蚕丝制成,诗人对钓丝、钓竿再到钓饵的严格筛选、匹配,明面强调对钓鱼本身的重视,暗中喻示的是作者给予“钓”的情感期待。张籍祭韩愈的诗歌《祭退之》中写道:“钓车掷长线,有获齐欢惊。”[1](卷383,4315)张籍追忆昔日与好友韩愈垂钓的场景,往日场景虽历历在目,但眼下却物是人非,使人无限伤感。“钓车掷长线,有获齐欢惊”一句是以乐景写哀情,抒情效果是其哀倍增,往昔惊呼欢庆的场景越能够清晰地再现,就越会引发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进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惋惜。空中钓丝抛出的曲线,是昔日与友人情深意浓的见证,但随着友人的离逝,那根线终被虚化直到虚无掉,这何尝不是一根象征存在、见证生命轨迹的线条,它所呈现的美感是缥缈含蓄的。陈陶在《避世翁》中写道:“海上一蓑笠,终年垂钓丝……直钩不营鱼……自古隐沦客,无非王者师。”[1](卷745,8557)“终年垂钓丝”的避世老翁,意不在鱼,他心心念念的是有朝一日自己能够遇到有识之士,之后便罢鱼竿,入庙堂,辅佐君王。渔钓虽为隐逸符号,但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的“隐”并不绝对,很多人终生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庙堂还是江湖,一些人早就做好了双重的心理准备,由此不难看出唐代历史发展轨迹的复杂以及诗人身上多元文化交融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出古人通达、随性的一面,他们深谙坚守的意义,不执拗,懂进退。杜牧在《赠渔父》中写道:“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独醒人。”[1](卷524,6047)该诗塑造了一位在芦花深泽之畔垂钓的渔夫形象,因为未曾遇到志同道合之士,所以即便是舟孤、水寒,依然坚守几十春。袅袅纶丝,是他理想人格、高尚情操及坚定信仰的见证者。皮日休在《鲁望以轮钩相示缅怀高致因作三篇》中写道:“一线飘然下碧塘,溪翁无语远相望……三寻丝带桐江烂,一寸钩含笠泽腥。”[1](卷614,7130)“三寻丝带桐江烂”一句暗示了诗人对历代渔隐先贤的缅怀,先贤之高致激发了诗人的偶像崇拜情结,三探、三寻,追随着偶像的足迹,感受着偶像的气息,深情地表达了个人的志向。
钓丝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指向士人的隐逸情结,但这不意味着钓丝只具有象征意义,钓丝也为农家田园平添了情致和趣味。杜甫《春水》篇即为此类诗歌的代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1](卷226,2441)诗歌画面简洁明快,充满了浓郁的田园气息和情趣,“接”“垂”“连”“灌”四个代表性动作将农家日常劳动的场景鲜活地呈现出来。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穷愁困顿,但总能从困苦中超拔出来,实现小我向大我的转化与升华,这源于他对国家、对百姓深沉的爱。杜甫诗歌中表达的爱,深沉、伟大、具象、生动,即便是烟火人生中极为普通的场景和瞬间,都能引发他的诗情,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笔下的这类诗歌,同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钓丝作为表意之“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高度契合的产物,它在线性的表征下饱含哲理性意蕴:钓丝一部分浮于水面上,一部分潜于水面下,昭告了一份明朗,也隐藏了一份神秘;钓丝于空中、水中皆能顺势而变,悠游而动,暗示了一份旷达、随性;钓丝融“渔钓”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于一体。“渔钓”意象之所以能营造出诗歌的旷达、邈远、超逸、空灵之境,是因为离不开钓丝意象的审美融入。作为丝缕意象,钓丝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需要深入探究,飘荡于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中的钓丝,是象征诗人的缕缕情丝。
三、“燕草碧如丝,秦桑低绿枝”——如丝如缕的“纤草”意象
唐诗中的丝缕意象,还包括那些如丝如缕的意象,这些意象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纤草”意象。广义而言,草意象内涵丰富,泛指除了树木、庄稼、蔬菜的所有茎干柔软的植物。狭义审视,草的内涵和外延则相对固定,多指生活中常见的如丝如缕的“纤草”,如草坪、草地、野草等指称草类的名词中所指涉的草的含义,本文涉及的草为狭义之草。
唐之前,咏草诗就已大量存在,到了唐代,“草”这一意象更加成熟,频繁出现在羁旅、边塞、山水、田园、宫怨、闺怨、悼亡、奉制、宴饮、咏史、怀古、禅意等各类题材的诗篇中,成为唐代诗人抒发情感的主要艺术符号。草非名花贵木,为何被诗人如此青睐?这源于草的自然属性与诗人复杂、细腻的深情所形成的“同构”关系:草绵密纤柔,草色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渐变,容易与诗人内心的情感产生共鸣,引发诗人之思;草具有春荣秋枯的特性,往往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启发身处困境之中的人重新燃起生命的斗志;草,易生、易长,随处可见,可大面积种植和近距离地亲近,人草交互的点很多;草与其他意象组合会拓展出多重意蕴空间,契合了人情感思绪的丰富性。草蒙茸、绵密、纤柔,呈现出鲜明的丝缕特点,虽非丝缕,但如丝如缕,是分析丝缕意象不可忽视的审美客体。
(一)诗人赞美草的生机与活力
春意醉人离不开春草的渲染与感召。春草旖旎可人,以流光之色与纤柔绵软之态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撩拨人的思绪,给人以特殊的美感,无论是远观、近望,还是细察、粗看,都韵味独特。春草蒙茸柔婉、绵延滋生、生机勃勃,往往预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容易激发人积极、活跃的生命状态,引发人的诗情。唐代诗人纷纷表达了对春草的喜爱、赞美之情,借咏春草表达对春天的热爱之情,抒发个人婉转细腻、积极向上的情感。
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1](卷443,4977)浅草与乱花,早莺与新燕一并构成一幅春光烂漫的早春图,浅草与马蹄相映成趣,一静一动,以静带动,渲染了气氛,激活了画面,语淡、情浓,西湖春景的清新明丽、生机无限在一片浅草中鲜活生动开来。白居易的另一首《杭州春望》中说:“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1](卷443,4979)匠心独运,将春草与细路融为一体,将草夹道而生的景象想象为女性的“裙腰”,想象奇妙,意象俏丽玲珑、浑然圆满。“腰裙”旖旎妩媚,随风摆动,摇曳生姿,诗人借其形容春草、幽径这一组合意象的线性之美,想象奇特、技法高妙。“裙腰”意象语义双关,表象是以女性的裙和腰的组合意象来形容草路呈现出的线性之美,同时又暗含着对女性青春活力及春天的蓬勃生机的赞美,诗歌对大自然的生机与人的蓬勃的生命进行了双重的礼赞。上官仪在《早春桂林殿应诏》中写道:“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1](卷40,509)诗人借对清新自然的优美景致的描绘来抒发个人的欢欣、愉悦之情,是诗人“春风得意”的写照。芳草、翠堤、诗人踏春的节律,共同营造出早春之景与诗人之情巧妙融合的意境。
(二)诗人借草抒发感伤之情
唐诗中有大量以草意象来抒发感伤之情的诗篇,草以绵软、纤细的特性暗示诗人的哀伤、愁绪,将情感形容得凄婉动人。
王昌龄在《长信秋词五首》中的“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白露堂中细草迹,红罗帐里不胜情”[1](卷143,1446),“细草”意蕴丰富:一方面,细草与白露意象的组合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反映出失宠嫔妃居所的荒凉寂寥,这是诗歌的表层;另一方面,细草意象暗示了宫人的悲剧命运,流光易逝,红颜易老。女性如堂中的细草,细草要经受秋之凉、冬之寒,女性则要忍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常处于孤独、凄楚、幽怨之境中。宫中女性的命运甚至不如草,草枯可以再荣,人死却不能复生,更何况苦短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被动地等待、无望地守候、孤独地面对中度过的,怎能不令人伤感?李白在《春思》中写道:“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1](卷165,1712)该诗视角独特,立意新颖,诗中女子独守于秦地,她日思夜想的男子远在燕地,眼前这株绿枝低垂的桑树引发了女子对男子的相思之情,即便是单方面勾画女子相思之守的画面,画面中流动的相思之苦就已经够浓、够深,但诗歌的镜头同时又捕捉了另一幅画面,即女子想象中的图景,女子想象着男子也一定如自己一样,被如碧丝的燕草所触动,在深情地张望远方,怀念家乡的自己。碧丝样的细草、绿枝低垂的桑条,摇荡着女子和男子的性情,表达了男女双方对彼此深深的思念,具象地呈现了相思之苦的沉痛体验,读来韵味悠长。
唐代诗也人常借草发思古之幽情,通过人与草的比对来喟叹历史。诗人感叹草的生命可以生死循环,人和王朝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再荣耀一世、盛极一时,最终都只能成为过客,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只留下旧迹残垣。断壁残垣处野草的永恒存在,愈发反衬出人生的苦短、历史的无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刘长卿在《春草宫怀古》中写道:“君王不可见,芳草旧宫春。犹带罗裙色,青青向楚人。”[1](卷147,1482)楚宫台榭,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荒芜,只有春草青青,绵延不息,跨越了时空的界线,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景越荒凉、草越青翠,就越易引发诗人的思古之幽情,正如诗评家俞陛云评曰:“楚宫台榭,久付消沉,废殿遗墟,剩有年年芳草,似依恋楚人,……谁复踏青荒圃,凭吊故宫耶?”[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