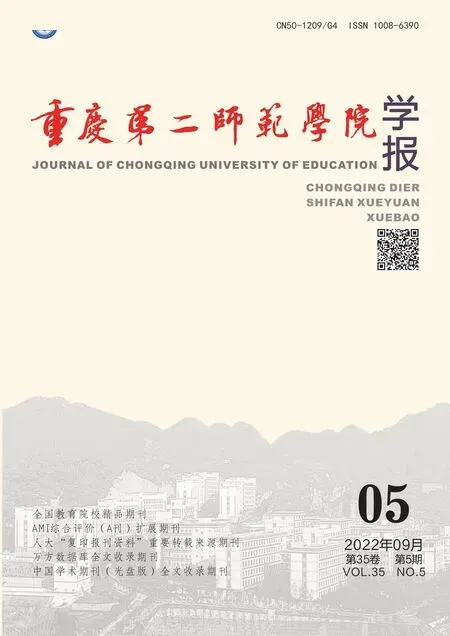三峡地区庙宇民俗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张飞庙为例
卢 锐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重庆 400067)
民俗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作民间信仰,包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自发形成的神灵崇拜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对应的制度仪式[1]145。三峡地区的古巴人以“尚巫”著称,包括神鬼、祖先等崇拜的民俗信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作为承载民俗信仰文化的庙宇也在民间不断得以兴建,如纪念大禹开江治水的宜昌黄陵庙、纪念诗人白居易的忠县白公祠等。正如杨庆堃所说“庙宇是中国民间弥散性宗教的核心结构元素”[2]287,以庙宇为代表的神圣空间在民俗信仰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庙宇逐渐从百姓祈福祭神的神圣空间,演化为兼具神圣和世俗双重功能的公共文化场所。位于三峡地区的重庆市云阳县,拥有全国知名的张飞庙(或称张桓侯庙)。新编《云阳县志》记载:“张桓侯庙始建于蜀汉末年,初为纪念张飞而设的祭祀祠。”[3]1003原张飞庙坐落于长江南岸飞凤山(俗称凤凰山),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将之原貌搬迁至云阳新城对岸。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产生重大影响的高级别地面文物搬迁。张飞庙在云阳民俗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围绕张飞庙进行了多元文化旅游建设布局。具体而言,以张飞庙为基础不断深化地域文旅融合,推进云阳 “三国文化旅游城市”建设。因此,探索张飞庙民俗信仰的特点及其成因,研究张飞庙所承载的民俗文化内涵及功能,可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民俗信仰寻求正向引导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新思路。
一、三教糅合:云阳张飞庙民俗信仰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对中国民俗信仰的包容性作了明确阐释:“凡为民所用者,都被加以供奉,形成巫、道、佛互相包容的宗教信仰,至于寺院供道教神仙,道观供佛教神灵,也比比皆是。这是中国民俗信仰的突出特点,也是各民族文化信仰密切往来的自然结果。”[1]158云阳张飞庙集中体现了民俗信仰的包容性。云阳县地处三峡,古时属巴国,巴人尚巫,秦灭巴国后,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在三峡地区相对复杂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中,交织着多元民俗文化因素,孕育了众多民俗信仰,同时也接纳了不同宗教形式。云阳张飞庙是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寺庙,民国编《云阳县志》记载:“氓俗所趣无异曩昔,但今县境庙祀三教杂出,或掍糅无辨,非道士之宫独多。”[4]可见当时云阳县域三教糅合情况已普遍存在,仅一个张飞庙就融合了儒释道三种信俗模式。
(一)儒教:官方支持下逐渐兴盛
儒教又称孔教,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核。学界认为,最早的“儒”就是宗教神职人员,故儒教虽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张飞庙虽源于民间“淫祀”,但随着社会的“礼崩乐坏”,封建王朝为维护纲常伦理、加强专制统治,便大力宣扬张飞的忠义骁勇,历朝历代不断加封,中央和地方也将张飞庙的祭祀活动纳入官方“正祀”体系中。张飞从蜀汉“桓侯”至宋朝“忠显王”,直到清朝春秋祭祀、享受帝王礼遇。张飞在封建王朝儒教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有关他的祭祀也不断儒家化。此外,包括诗圣杜甫在内的历代文人雅客在云阳张飞庙留下大量传世诗篇,这从宋朝至近代修缮庙宇时所立碑刻以及历代云阳县志所载张飞庙诗赋可窥一斑。清光绪学部专门司候补主事彭聚星捐出家藏金石,由雕刻名家何今雨篆刻了岳飞所书诸葛亮《出师表》等儒家经典。在地方乡贤共同努力下,张飞庙被誉为蜀东“文藻胜地”,成为儒学交流传播的重要枢纽。
(二)佛教:外来宗教元素的融入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便一直维持着广泛影响力。三峡地区佛教传播始于东汉永平年间(58—75)的忠县龙兴寺,而后佛教在三峡地区快速发展,信徒修建了众多寺庙,佛教文化逐渐融入当地社会风俗中。有史可考的云阳地区第一座佛教寺庙是刘道于唐末在县城以西的长江之滨修建的下岩寺[3]1061-1062,自此县内建寺塑像之风盛行。随着佛教不断传播,张飞庙的祭祀或祈福活动也愈发表现出佛教文化特征。云阳民间普遍尊称张飞为“张王菩萨”,张飞庙被誉为“千年古刹”。民国初年,张飞庙的实际管理者便是地方知名佛教僧侣瘦梅上人。瘦梅上人又称宪然和尚,他在做住持期间,曾为重修被洪水冲毁的张飞庙奔波化缘,历经多年新庙落成。张飞庙由此香火兴盛,祈福求名者纷至沓来。总之,张飞庙的日常祈福祭拜仪式、庙宇建筑风格无不体现出佛家文化色彩,这些佛教文化元素与民众对张飞的信仰崇拜已然形成了高度融合。
(三)道教:本土宗教元素的遗存
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道教最早一派),其“师君”张鲁的部曲多在巴蜀,他通过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巴蜀、汉中等地[5],自此道教风行三峡地区,并在唐宋之时达到兴盛的顶峰。新编《云阳县志》记载,道教最晚于南北朝时期已传入云阳,至明初即有全真派的支派活动。民国时期,云阳县民政科对县内道教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本县道教今尚无合法组织者,其信道者,全县约500人,以县城之经善堂于云安镇之张王庙为集聚研道之所。”[3]1062此外,在对张飞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两尊高约30厘米的砂质岩石像。这些石雕虽然粗糙,且有残缺,但依稀可见其中一尊是道教人物像,一尊是佛教罗汉像[6]。人物石像的发现佐证了道教在三峡地区的存在及其对张飞庙的影响,而这或可说明道教曾将张飞庙当作自己的“道场”。概言之,两尊拥有不同宗教元素的石像,足以说明三峡地区的宗教合流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历史上,云阳张飞庙作为儒释道三教信仰的共同活动场所,既体现了张飞庙民俗信仰的包容性,又表现出民俗信仰不同于五大宗教的非制度化特征。张飞庙民俗信仰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可以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在普通民众中具有相对旺盛的生命力。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民俗信仰能够对底层社会关系予以整合,并在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同时,有效推动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
二、多维互动:云阳张飞庙民俗信仰的灵力来源
张飞庙历经千年而香火不绝,背后原因不仅是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乡土民俗文化因素的相互交融,更重要的是张飞庙民俗信仰的灵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建构。作为人们所托借的一种虚拟力量,神明的灵力是民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力来源也是多重的。官方和民间不同层面的祭祀活动是张飞“由人成神”的两股主要力量[7]139,神明显灵和祈福灵验两种方式能显著增强庙宇及所祀之神的“灵力”。此外,庙宇的建筑风格、“灵体”遗存和寺庙所处的自然环境对“灵力”生产同样功不可没。
(一)灵体遗存:庙宇灵力的基础
张飞本是河北涿州人,遇害于阆中。云阳与阆中相隔千里,缘何建庙祭祀张飞?这或许可在各类史料中找到答案。《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8]700-701明嘉靖《云阳县志》亦载:“侯既被害,两贼函首东下。蜀师问罪,吴人归元媾和,旅瘗于此。”[9]此外,新编《云阳县志》有更传奇的记载:
据说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司隶校尉张飞正驻守在巴西郡(今四川阆中),东吴孙权那里有两个刺客潜入到了张飞帐下。那时正值午夜,张飞正在营帐中呼呼大睡,两个刺客见此情形,便立刻想刺杀张飞。但张飞身经百战,不知道有什么神通,脖子竟是如钢铁一般,两个刺客怎么都割不下张飞的头颅。正在此时,张飞感觉脖子痒痒的,以为是蚊子在叮咬,便一巴掌拍在脖子上,结果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两位东吴刺客大喜,立刻装起张飞的头颅投入到江水之中。张飞的头颅随着奔腾的嘉陵江水一路向东流,再汇入长江,从阆中一直流到了川东云阳地界。话说云阳长江边上的铜锣渡口有个老渔翁,张飞托梦给他,欲求渔翁打捞起他的头颅。果不其然,老渔翁在第二天打捞上了张飞头颅,老渔翁在埋葬张飞头颅时还挖到了一坛金元宝,他认定是张飞显灵,便花掉所有金银财宝为张飞建造了一座大庙,这才有了今天的云阳张飞庙。[3]1251
正史杂以传说,使得张飞“身在阆中,头在云阳”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张飞“灵首”的遗存为云阳张飞庙的建立提供了合理性,也为云阳张飞庙的“灵力”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源泉。与仅存“灵躯”的阆中张飞庙和仅有张飞出生地之名的涿州张飞庙相比,云阳张飞庙更拥有祭祀张飞的“正统性”和“灵力”底蕴。
(二)山“灵”水秀:周遭环境的衬托
在三峡工程启建之前,云阳张飞庙坐落于长江南岸的凤凰山麓,与长江北岸的云阳老城隔江相望。陡峭高耸的山崖如屏风,加之浓荫蔽日的古树,张飞庙就如翠屏上的一幅山水画,与云阳老县城相得益彰。宋代诗人陈似所提《云安桓侯祠碑记》如此描绘云阳张飞庙所处环境:“北直军垒,瀑布旁注,翠蔓蒙络。”英国探险家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亦如是说:“庙的一侧有一道美丽的石桥,从石桥往上看,只见一条瀑布从一个陡峭的窄谷中飞奔而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完整的一幅东方美景。”[10]82
因凤凰山地势陡峭,云阳张飞庙的设计需要依山取势。当时的能工巧匠们通过开采的石条来垒砌台基,以抬高和加宽庙基。此外,还从江边到庙门处修建了一条梯道,人们从长江渡口拾级而上即可来到庙前。云阳张飞庙濒临长江,雄踞于江岸巨崖之上,庙前极为狭窄的江道和奇峰峭壁形成特殊的角度,民众只有仰视才能感受其“紧邻长江、背负陡山和古木森森的环境”[11]以及雄伟气势。可以说,云阳张飞庙所处独特的地理环境营造出了“灵气十足”的氛围,唤起了民众极其庄严肃穆的情感,并因此增添了庙宇自身的“灵力”。
(三)官方认可:由人成神的“张王菩萨”
无论是正史书写还是民间传说,张飞一直都是疾恶如仇、忠义两全的形象。张飞在民间“淫祀”中不断被加以崇拜的同时,逐渐成为官方宣传忠义骁勇的标榜人物。《夷坚志》记载,宋高宗绍兴初年,金人大举进攻陕西,宋魏国公张浚坐镇秦蜀,将指挥部移至四川阆中。这年秋天,有个士兵竟然死而复活,专为传递千百年前的蜀汉大将张飞将助宋抗金的消息。果然,之后金军来犯均被宋军击退,四川与陕西得以保全。战后,张浚上奏朝廷请求封赏张飞,张飞也由此被封为“忠显王”[12]。可见,在宋元之际,连年战乱,张飞保境安民、维护汉统的形象更加得以凸显。从蜀汉时期被谥为“桓侯”配祀刘备“惠陵”开始,张飞得到历代朝廷不断加封,清嘉庆年间更是被敕封“桓侯大帝”配享太牢。在官方叙事中,张飞从“暴而无恩”的武将已然转变为“文武兼备”的人神;在民间叙事中,百姓也尊称张飞为“张王菩萨”。对张飞的祭祀崇拜在封建王朝达到最高点,实现了正祀化和国家化[7]139。云阳张飞庙因此有了官方背景加持,其“灵力”生产也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动和肯定。
(四)神秘传说和灵验故事:灵力建构的核心
神秘传说和灵验故事作为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赋予了所信奉神灵一定的可信度和传奇色彩。相传,张飞的神灵为回报云阳百姓为其建庙立祠的恩情,常常助过境云阳的船只几缕清风以助其航行顺利,故张飞庙中有“助风阁”。从前在长江航行的船长,首航前必到云阳张飞庙前烧香祈福;每逢张飞诞辰(农历八月二十八),过境云阳的船只也要燃香放鞭炮。张飞庙在川渝地区分布广泛,除阆中张飞庙和云阳张飞庙外,涪陵、长寿皆有有一定知名度的张飞庙,各地民间传说和灵验故事共同对云阳张飞庙的灵力生产起到正向作用。
1.神秘传说
清康熙年间,当朝大官张鹏翮经长江水路回乡祭祖。张鹏翮所乘航船将要经过云阳张飞庙时,有部下请求张鹏翮暂停航程入庙祭拜张飞,否则,恐怕会引起“张王菩萨”不悦。以清廉享誉京城的张鹏翮认为无须祈求,并以“相不拜将”的理由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于是张鹏翮一行人向上游航行15公里后夜宿于三坝溪。第二天醒来,张鹏翮一行发现回到了15公里外的云阳张飞庙脚下的渡口处。张鹏翮不以为然,坚信是昨晚船工未将船绳拴牢所致,于是一行人又航行15公里,并在同一个渡口又歇息一晚。不料,他们一觉醒来发现船只再次停到了云阳张飞庙前,仿佛进入了循环一般。同行人再次请求祭拜张飞,可张鹏翮仍然一意孤行,直到第三次一夜之间回到庙前渡口。张鹏翮不得不听从了部下的建议,他赶紧登岸参拜张飞。参拜完毕后,长江之上突然刮起一道清风,一口气将张鹏翮的船只送到15公里之外,张鹏翮为感谢张飞助风送行之恩,请人在助风阁立一石碑并题诗:“铜锣渡口蜀江东,多谢先生赐顺风。愧我轻舟无一物,扬帆载石镇崆峒。”[3]1258-1259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将张鹏翮回乡省亲的故事与张飞显灵的传奇进行了融合,生动表现了张飞坐镇长江之滨神圣威严的形象,虚实交织间无形提升了张飞的神性。在张飞神性被不断加强的同时,张飞神职所涉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屠夫祖师爷到护航水神到“天降甘霖”的雨神,多种神职集于一身[7]139。可见,经过民间传说的修饰,张飞已经变成具有“保境安民、忠肝义胆、文武兼备”等“正能量”特质的人神,其神性的不断增强和神职的不断扩展,形成了张飞崇拜所需要的灵力。
2.灵验故事
受访人黄某居住在云阳县磐石镇对面(即张飞庙对岸),平时赋闲在家,独子毕业后在区县当公务员。据讲述人自述,她每年都要去张飞庙祈福,给张王菩萨(当地百姓对张飞的敬称)上香,捐香火钱,对张王菩萨毕恭毕敬,十分虔诚。她家孩子考大学时她就去张飞庙进行了祭拜,带了很多香烛,专门为孩子求了一个签。结果,她抽到一个上上签,孩子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读了不错的专业。孩子毕业准备入职考试时,她又去张飞庙为他祈福。讲述人认为,张王菩萨见她心诚,又怜子如命,就给她家带来了好运,她儿子果然在毕业后考上了心仪的岗位。当笔者问她为什么对所谓“张王菩萨”十分崇拜时,她解释说:“张王菩萨文武兼备嘛,既能上马打仗,又能写一手好字,听说还写过书呢。他以前不是当的将军吗,后来还当上了王侯,死了以后还成了菩萨,所以说,娃儿升学求职找张王菩萨绝对没得错吧。”①这一事例既说明云阳当地百姓对张飞崇拜之深,又体现了民俗信仰的功利性特点。
综上,民间传说故事和封建王朝官方的“背书”不断加深了百姓对张飞的崇拜,百姓因祈福而发生的“有求必应”的灵验传说与故事同样印证了张飞庙的灵力,二者的互动为张飞庙的灵力生产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正如王景文《夷坚志别序》所说:“云安梦张翼德其信,然则王之威神,经千载之后,犹昭揭如此,人那得不加敬乎!”[12]
三、世俗变迁:民俗信仰场所功能转变
庙宇作为以民俗信仰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除五大传统宗教活动场所外更具有原生性、多样性、地域性特点的信仰场所。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如今云阳张飞庙不仅发挥着民俗信仰所固有的神圣功能,而且其所承载的功能不断往世俗化、多样化趋势演进。
(一)泽惠流离:信仰场所的社会功能增强
抗日战争时期,在云阳张飞庙产生了一段“在远不遗、泽惠流离”[13]的佳话。抗战初期,我国沿海一带即已沦陷,江浙等地大批难民溯江而上到达今云阳县域内,云阳县接纳难民达数千人。为妥善安置难民,云阳县政府及张飞庙实际管理者秉持人道主义精神,腾空了张飞庙所有房间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安排栖身之所。时任云阳慈善会会长刘斐成还依靠内部会员乐捐和向外部富商募捐等方式,为难民提供生活支持,直至抗战胜利。寺庙作为开展民俗信仰活动的场所,一般也是出家人修行弘法的清净之地。一般来讲,民众只能在参与上香、祈福等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与寺庙产生联系,不能随意破坏寺庙的神圣庄严。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民众思想观念逐渐转变,民俗信仰的俗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寺庙作为宗教信仰活动场所的神圣功能不断向世俗功能变迁。云阳张飞庙在经历此次救困扶危事件后,其社会关怀的社会功能属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
(二)灵钟千古:信仰场所的日常功能增强
据考证,云阳张飞庙的庙扁上所书为原云阳县令李载庵于清光绪三年所题“灵钟千古”四字,而非现今的“江上风清”。庙内障川阁处俗称“钟楼”,曾放置数口大钟,每日有专任庙工准时敲钟报时。在传统佛教文化中,钟具有断烦恼、增福寿、脱轮回、长智慧、成正觉等功效,佛门的《鸣钟偈》可为印证。比如寺院早上的《鸣钟偈》写道:“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晚上的《鸣钟偈》则言:“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并且,佛教认为世上有108种不同的烦恼,需要敲击108次钟才能消除。此外,钟还有庄严道场的作用。在佛寺每月例行的各种法事及法会中,钟都作为法会的重要乐器配合僧众梵呗响叩,供养圣贤和摄受与会大众,显现出佛门法会的隆重与庄严,“暮鼓晨钟”也成了佛寺中持续至今的常见现象。
据说,云阳张飞庙庙匾原为“灵钟千古”四字的原因,是传说庙内青铜铸钟附有灵性,每当云阳张飞庙对岸的云阳县城不幸遭遇火灾、洪灾以及匪患时,青铜灵钟便会提前自动鸣响警醒县民,避免生灵涂炭。传说固不可信,青铜灵钟应是在紧急情况下,被目睹灾情的张飞庙僧人所敲击。但由此可见,钟从庄严法场的佛门重器到造福一方的日常工具,体现了云阳张飞庙所具备的日常报时、减灾防患的日常功能属性,这恰好也是寺庙功能世俗化趋势的体现。
(三)文藻胜地:信仰场所的文化功能增强
随着骚人墨客的到访,金石书画、诗赋名篇集聚云阳张飞庙,使其成为“巴蜀胜境、文藻胜地”。杜甫滞留云阳期间,曾在张飞庙养病,留诗《杜鹃》,张飞庙内杜鹃亭即因此诗而得名,并以此来纪念杜甫,这也使得张飞庙成为同时祭祀文武的庙宇。除了外乡文人墨客的留迹,本地乡贤对张飞庙的苦心经营也不可忽视。住持瘦梅上人每有客来便以茶相待,以求客人挥毫赠诗题词。瘦梅与篆刻名家何今雨交好,便邀其篆刻名篇佳句,一时之间张飞庙书画金石“甲于蜀东”。乡贤彭聚星早年倾其家藏金石书画交与篆刻名家何今雨与张飞庙住持瘦梅上人,离乡赴京时嘱托他们参照善本完成碑文精刻。他晚年返乡继续经营张飞庙金石碑刻并留下大量书画于庙中收藏,张飞庙前“江上风情”即其所书。可见,本地乡贤和到访的历史名人是云阳张飞庙成为“文藻胜地”的两股重要力量,他们使云阳张飞庙除具有祈福功用外,还可以供人在此谈经论道、评鉴书画以及欣赏江上风光,文化属性得到显著增强。
(四)文旅结合:信仰场所的经济功能增强
如今云阳县正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依托张飞庙资源,以“三国文化”为背景和“张飞文化”为主线,辅以多元地域文化,致力构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兼具故事性和品质性的文化旅游体系。云阳张飞庙景区一方面对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一方面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云阳当地做了不少工作。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八(张飞诞辰),有时恰逢国庆黄金周,全国各地朝拜张飞的香客纷至沓来。云阳张飞庙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立足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通过举办具有民俗风味的庙会,并融入弥漫现代元素的音乐节、美食汇等活动,弘扬地域民俗文化,展示云阳发展成果,增强游客体验。自2005年以“游胜境览三国故事,祭张飞作忠义完人,承传统扬民俗文化”为主题举办首届官方庙会以来,云阳张飞庙庙会至今已举办十届。此举不仅提升了张飞庙在川渝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影响力,而且有力带动了云阳地方旅游经济发展。
以上几个方面,呈现了本应清净的民俗信仰场所被世俗的烟火气息所打扰的情景,但同时与佛道等宗教济世度人的理念相符,也与民间信仰世俗化的趋势并行不悖。云阳张飞庙的神圣功能之外,众多世俗功能也集聚一庙,反映了世俗生活对信仰场所的合理化改造,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庙宇在历史长河中自我重构以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四、结语
本文从信仰场所的宗教融合状况、民俗信仰的灵力构成、信仰场所功能世俗化趋势三个方面厘清云阳张飞庙民俗信仰形成的脉络,分析云阳张飞庙的民俗信仰历史及现状,以此研究三峡地区庙宇民俗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笔者发现云阳张飞庙的民俗信仰具有如下三个特性:一是民俗信仰内容的多元性。民俗信仰内容的多元性也意味着民俗文化及民俗信仰的包容性,民俗信仰不仅植根于百姓大众,而且对其他宗教教义、制度乃至神灵都可以兼收并蓄,云阳张飞庙三教糅合的现象便是一个例证,这是中国民俗信仰的重要特点,也是民俗信仰等民俗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民俗信仰灵力构成的多维性。民俗信仰起源于民间大众,从统治者大力打击“淫祀”到封建王朝为维护统治而渐渐认可“正祀”,一个庙宇祭祀的对象从人到神,是民间和官方两种力量角力的结果。民间传说、灵验故事增强了以“功利性”为主的普通信众的信心,官方的层层加封提高信仰对象的地位,再加上民间文学的粉饰、地理环境的渲染,民俗信仰神灵和信仰场所的灵力构建才趋于完成。三是民俗信仰场所神圣功能与世俗功能兼备。从民俗信仰场所原始的祈福、祭拜功能扩展到收容难民、监测灾害、文化交流及旅游开发等功能,皆体现了民俗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民俗信仰场所功能的多样性及民俗信仰强烈的入世色彩及俗信化趋势。
从社会功能来看,民俗信仰能够从古传承至今,是因为民俗信仰对社会系统的运作有着独特的作用。民俗信仰既能起到精神安慰、道德感化及民族认同等作用,又能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根植于乡土的民俗信仰也具有一部分负功能。王存奎等[14]认为民俗信仰的功利性使得崇拜者不满足于消极等待,便通过迷信和巫术加速达到自己的目的。民俗信仰植根乡土社会时间之久,对乡土社会影响之深,决定了民俗信仰深层的顽固性和渗透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警惕不法分子利用封建迷信行危害社会之事,积极推动民俗信仰与社会建设相适应。总体来看,民俗信仰的正功能大于负功能,民俗信仰基本上都是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当民俗信仰内化为大众的惯习时,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也应当承认民俗信仰在社会特定发展阶段对人们心理安全的积极慰藉作用。作为一种从古代延续至今且仍具有生命力的古老信仰,民俗信仰目前所具有的影响力涉及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而且已经深深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要认识到民俗信仰的积极作用,重视民俗信仰场所集聚的功能,保护好民俗信仰所包含的优良文化,发挥好民俗信仰传递积极文化要素的作用,助力社会文化建设。同时也要认识到民俗信仰保守和消极的一面。尽管民俗信仰作为一种习俗流传至今,其中已鲜有虔诚和迷信的因素夹杂其中,但仍要加强对民俗信仰类型民俗文化的引导和管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将民俗信仰更好地嵌入经济、文化建设之中也是一个重要议题。要把握民俗信仰的正功能,发掘民俗信仰的潜功能,推动民俗信仰的文化重建和价值再生,积极推动民俗文化与我国社会相适应,助力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重庆工商大学白俊奎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受访人:黄某(1976 — ),女,重庆云阳人,初中学历,无业;访谈人:卢锐(1997 — ),男,重庆工商大学2021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访谈时间:2022年2月3日;访谈地点:重庆市云阳县滨江公园。
——重庆市云阳县中医药学会抗疫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