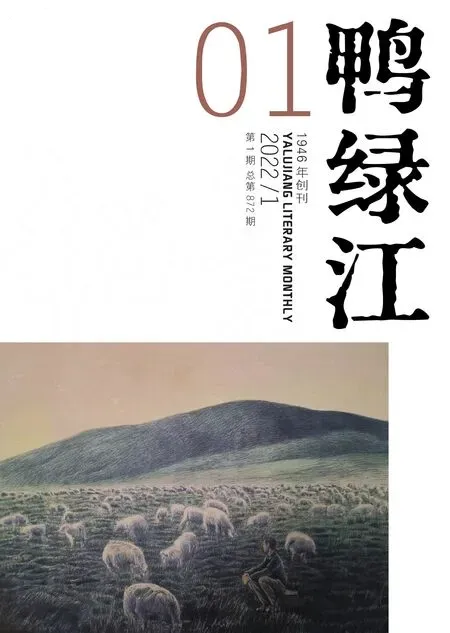浮桥(短篇)
一声惊雷过后,大雨倾盆而至。孟东野坐在阁楼书房的电脑桌前,看到窗外的露台瞬间成了汪洋,而泛白宽大的电脑屏幕上,几个汉字也似乎在“水面”上摇曳,像露台上那些在风雨中摇摆的花草。他已经坐了一个下午,一个小说的开头写了删,删了写,最后只剩下一个标题。过了今年7 月7 日,他就四十岁了。四十岁写小说,酝酿的时间长,憋得慌,迟迟落不下笔,落笔了也不痛快,像挤牙膏,一个字一个字爬上去,又抹了去。说不上来为什么,有些胆怯,有些紧张,只觉得两肋局促,呼吸费劲,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回想起二十多岁,写小说时灵感像自来水,只要拧开了水龙头,便任它淌下去。
当然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刚恋爱,和女朋友在租来的二居室里缠绵,饭都没时间吃。每个周末两天时间约会,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如今,他和妻子分床睡了十年,终于在今年春天,她搬了出去。一块儿带走的还有儿子孟思齐,十二岁,对他常常出言不逊。
天是漏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露台上的水已经齐膝深,一丛蜀葵已淹没了一半,一丛蔷薇还有几个花尖在水面闪着。他忽然站起身,下楼,旋转木质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楼下客厅那巨大的鱼缸里,四条发财鱼无精打采,看上去奄奄一息。不知为什么,他养的鱼每年都会死掉,有时候半年就死光了——每到春节前夕他会重新投放一批,第二年再重新投放。之前张娜在的时候,鱼的死亡速度还慢一些;如今,春节新购的发财鱼、锦鲤和虎鱼,二十多条只剩下了四条。鱼的肚皮很白,鱼也会眨眼睛,鱼还会求救——这是这些年他观察到的,不知道对不对。
他把四条濒死的鱼捞出来,双手捧着上了楼。“鱼就应该在大水里活着”,他一松手,把它们送进了露台的“汪洋大海”。“去吧,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别在这个鱼缸里等死了。”他突然感到很轻松,仿佛自己也扑了进去,就像当年他从坝头上跳进那条大河——小伙伴都那样做,一手捏着鼻子,赤身裸体叉开腿往下跳,“扑通”就跳下去了。那时候,他们不觉得那条河多大,也不觉得多危险。在枯水季节,它甚至不如村前那条水渠宽阔。只是它的水很浑,因为它叫黄河。黄河有宽的地方,也有窄的地方;有水流急的地方,也有水流缓的地方。他们村是名副其实的黄河滩,大堤里面,二堤以外,除了村就是一片茂盛的芦苇丛,芦苇尽头就是那条河。那条河在他生命的前十八年,一点儿也没显出特殊的价值来。直到他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坐在遥远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地理,他才慢慢感到它不一样。班上有同学听说他就是在黄河边长大的,羡慕得不得了,咋呼着要跟他回老家看黄河。他那时候还有些蒙。
“黄河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山区才好看吧?!”
“山有啥好看的?爬起来累死人。”
他还没见过大山,但黄河再熟悉不过了。黄河给他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格外黄,甚至眼珠子都是微黄的——这是第一次和张娜接吻,张娜告诉他的,他哈哈地笑起来。不说不知道,他回乡后仔细观察了父母和族人,果然,他们的黑眼珠并不黑,真的有些发黄哩!他想起来每次下河洗澡,回家后,母亲都会用指甲在他胳膊上划一道,黑黄的皮肤上马上会出现一道白色的印痕。母亲不让他下河,那河几乎每年都会淹死人。那道白色的指甲印痕就是他下河洗澡的证据,只要出现,自然少不了一顿笤帚。但孩子哪有什么记性,第二天照常去河里疯玩。
大雨还在下,把他浇了个劈头盖脸。四条发财鱼突然焕发了青春,活了过来,它们在露台上像闪电一般倏忽来去,再也不把白色肚皮翻到上面来。然后,很快,它们就顺着下水道游了下去,在如瀑布的哗哗的水声中不见了。
鱼会摔死吗?孟东野伸头往楼下看,天色已经暗下来,下水管道里发出雷鸣般的奔泻声,下面什么也看不见。随它们去吧,他重新回到阁楼,把湿衣服脱下来,随手扔在地板上,书房的地板上马上就洇了一摊水。他把窗帘拉上,打开灯,就那样赤身裸体地站着。这让他想起魏晋时期的嗜酒狂士刘伶,在家里不穿衣服,以房子为衣服的典故。孟东野不禁笑了一下。他在家里也没必要穿衣服了,一个人的住所,穿衣服遮给谁看呢?
电脑屏幕上那几个字也湿漉漉的,像几条鱼,几条他当年在黄河里洗澡时捉到的鲫鱼。红红的眼睛,微黄的鱼鳞,两条胡须不停地摆动,像两根弹簧。
他决定明天回家。他突然很想那条河,很想那条河里的水和鱼,还有那片河滩上的人。当年离开故乡奔向远方的时候,他是多么討厌那些有着一嘴黄牙的故乡人啊,他们狡诈、阴险,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迈进四十岁后,他突然不可遏制地又想他们。那条河也越来越重要,几乎成了他所有思念的源头。年轻的时候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年里,不少同事、朋友都跟他回故乡旅游过,他带他们看的第一站就是黄河。每次必不可少的,就是他自己回乡,时间再紧张,他也要到黄河边站一站,抽支烟,待一会儿。
这些年里,河上多了一处风景——浮桥,是他的两个堂兄和几个有点钱的人投资搭建的。他们村后是黄河最窄的地方,他数了数,十六条船,十六条大铁船连排在一起,从这岸到对岸,就“天堑变通途”了。上大学之前,河上没有浮桥,他也从来没见过浮桥。那时候到对岸去,要坐船。小时候是木船,撑船的是本家没出五服的二爷爷。有人去河对岸走亲戚、赶集、赶庙会,都要坐他的渡船过去。船不大,木板都开裂了,人和牲口一上去,那船就沉下去一大截,船舷吃水很深,摇摇荡荡的河水几乎和船舷持平。他从来没登过那艘船,河对岸什么样,他也不知道。后来,二爷爷死了,要想过河,得绕几十里路去另一个乡镇的潘家渡口。考大学出来前,村上一个姓路的有钱人买了一艘摆渡轮。机动船比木船自然大了好几倍,关键是再也不用划桨了。路姓人家站在船尾,用手摇舵,柴油机嘟嘟嘟地在船后翻起一片黄色的浪花。自行车、摩托车,甚至三轮车也可以上船了。那时候河对岸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他们村是有名的蔬菜村、西瓜村,每天都会有人去河北岸卖菜卖瓜。孟东野还是没去过对岸,没坐过柴油船。那时候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坐上船到对岸去看看,听说上岸走 不久就是县城,街上的姑娘都穿短裙子。到了晚上,大街上依然亮如白昼,散步的、跳舞的、唱卡拉OK 的到处都是。红林常跟他爹去卖瓜,回来讲给他听,孟东野心都飞去了。红林说,那个县城有个很大的新华书店,里面什么书都有。书店旁边有个录像厅,白天晚上放录像,还有黄色录像。啥是黄色录像?孟东野想象不出来,难道也和黄河有关?后来他知道,和黄河风马牛不相及,他忍不住笑了,觉得那时候真幼稚啊。
他不敢说过河,他每次一说,母亲就会疯了一样发作,又哭又闹。其实,母亲娘家就是河北岸的,但母亲从来没回去过。他们都没去过。也就是说,在孟东野印象里,他从来没有走过姥娘家。这让他很委屈,别人都有外公外婆,他没有。一提起来,他母亲就黑着脸说“都死了”。小时候他相信,后来,他听奶奶隐约说起,似乎不是那么回事。“那得多大的仇恨呀!”奶奶自言自语,“自己的闺女和爹娘一辈子不相往来。”爷爷也会插一句:“那还算爹娘?那就是畜生,不回去就对了!”直到孟东野三十三岁那一年夏天,他有个机会到河北岸去出差,终于瞒着母亲,根据多年来搜集到又埋在心底的线索去寻了一回亲,但无功而返。那一双应该叫姥娘、姥爷的人都已经离世了。一个舅舅早已不在村上,据说在湖南安家落户好多年,十几年没有回来了。
这些年,河上多了浮桥。第一次回家见到浮桥,他很吃惊。远远看去,是一艘一艘的铁船排在一起,踏上去,就是一条路——通衢大道。汽车、拖拉机、农用车畅通无阻,桥两岸有收费站,行人不要钱,车辆按照规格大小收费,据说日进斗金。“摇钱树,”孟东野的堂弟孟东强向他描述,“哥,你要有钱,你也入个股。这就是印钱机器啊,每天过多少车啊!”
“大车竟然也可以开到河对岸去?摇晃得厉害吗?”孟东野很惊诧。
“稳当得很,别说大车了,挖掘机也可以!”孟东强说。
“过个河就这么简单了?可以直接开车去对岸县城?要是涨了大水……”
“水涨船高嘛!哥,有了这浮桥,过河就简单得很,不仅可以开车到县城,就是开到姑娘心里去都简单得很!”
这几年,河北岸嫁过来的姑娘很多,家乡依托黄河资源成了省级示范点,都富起来了。小伙子们买了豪车,一溜烟开过去勾搭姑娘。
但孟东野知道,“心”可不是那么好过的,哪怕是浮桥,他也不想投资。孟东野没钱,他只是个自由作家。张娜还在的时候,他家收入算是不低。张娜是个有能力又很要强的人,在上市公司已经拿年薪了。张娜的父亲是这个城市某个部门的实权领导,张娜公司的老总很多事情要靠他周旋。但家里的钱不是他的,是张娜和儿子的。孟东野毕业后也有过一份工作,在一家企业上班,后来企业倒闭,他成了“坐家”。那几年他势头不错,每年能发不少小说,加上获几次奖,收入也和正常上班差不多。他有个作家梦,人又不活泛,干其他的也干不好。张娜那时候也不在乎他挣不挣钱,反正也不指望他。他就这样把爱好发展成了“事业”。“事业”这个词,说出来他自己都心虚,但这么说好像也勉强。在圈内,他名气还是有一点的,但名气换不来真金白银。幸亏他消费很低,除了抽烟,没其他欲望。前几年,他应邀写过一个电视剧,虽然后来电视剧没播出来,但稿费没有欠他。有这几十万在手,他也不着急,就这么混成了自由人。
自由人,孤家寡人。张娜对他还是不错的,抚养费给他免了。这让他很有些况味杂陈,他不觉得自己很可怜,但在张娜眼里,他真的这么一无是处?为了一口气,有时候他来了稿费或者获了奖金,就会给张娜转账,指明给儿子零花。他心底还有些不安,他怕一分钱出不到位,最后儿子不认他了。其实,也没考虑那么长远,他觉得自己是有责任感的男人。差不多是这样。
大雨过后,他决定回一次老家。这些年,那条河让他很牵挂。很多跟他来看黄河的朋友来了之后会失望:“原来这就是黄河呀!太小了吧!”“还不如我尿的一泡尿。”开始的时候,他很生气,后来也习惯了,不与他们争辩。因为他好像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条河不仅仅是因为大才出名和重要的,更因为它是一条有历史的河、有性格的河,是一条有变化的河。枯水季节,河水窄得恨不得一脚能迈过去;发大水的时候,它又能宽得一眼望不到边。
前几年,他参加了一家杂志社的走黄河采风活动。那一次,十几个作家溯流而上,真过瘾啊!走下来他才发现,原来每一段黄河都不一样。山西的和山东的不一样,宁夏的和甘肃的不一样,他们村后的和壶口的不一样,上游的和入海口的不一样。它那么长,曲里拐弯,每一段都不一样。一路走,一路百度黄河的历史,那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啊?简直是一部人类史!
他有好几次掉了泪,在银川古渡的羊皮筏子上,在兰州的黄河大桥上,在入海口的黄蓝分界线上。对这条河的理解,在快四十岁的时候,和他小时候真的不一样了。
终于,在去年,他有机会去了青海的高原,从西宁到玉树,从玉树过杂多,他一直追寻到了黄河源。那高原雪甸的汪汪水坑,那清澈凉爽的源头之水,高海拔让他有些缺氧,喘不过气来,但他在源头待了很久。他的眼里蓄滿了泪水,好多次站起来朝远方张望,幻想着自己变成一叶小舟从这里出发,顺流而下,一直流到他故乡所在的那个拐弯处,那座浮桥边。
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窗外的雨似乎停了。月亮升起来,弦月。他关上灯,拉开窗帘,一道月光照进书房,月光洒在他的裸体上,他像沐浴在黄河里。
他想起张娜第一次跟他来看黄河,在码头上,他站在她身后,她伸出双臂,让他也伸出双臂。这个镜头是《泰坦尼克号》上露丝和杰克的经典镜头,那一刻他隐约有一丝不好的预感,觉得不吉利,但他没敢说;后来,他知道,也许那一刻的开始就为结局埋下了伏笔。
那一年的水真大,是他记忆中黄河最大的一次,庄稼全淹了。他们村成了孤岛。黄河水把他们村包围了,靠外的宅基不停地坍塌。家里没有饭吃,眼看就要断粮,爷爷决定带着父亲去河北岸要饭。那条船真小啊,二爷爷的小木船像个玩具。河北大集,村上各家都去了人,到集上去讨饭。黑压压的人挤在船上,把船压得吃水很深,船舷与河面在一条线上摇曳,混浊的水一漾一漾,涌进船舱,船舱里的水有脚面深。二爷爷大声喊“人太多,再下去几个”,可是哪有人听啊,淹死也比饿死强啊,淹死一人,饿死可是全家。
那是一次不祥之旅。孟东野十岁,眼巴巴看着芦苇般的小船飘飘摇摇朝远处划去。后来的几十年,孟东野老是想起那个镜头。一叶小船载着一群视死如归的乡亲朝洪水滚滚的黄河对岸驶去。天色阴沉,乌云像翻滚的河水。他和妹妹跟着奶奶和母亲在家里等他们回来,家里的面缸只剩下最后一把面粉。奶奶把面粉抓到大碗里,浇上水,磕上了最后一枚鸡蛋,搅拌了一下。母亲已经在厨房里烧红了鏊子,柴火都湿了,她烧的是一块箱子板——她的嫁妆。奶奶在鏊子上摊煎饼,小小的一坨用竹篾子一刮,就是薄薄的一大张。那煎饼真香啊!他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煎饼。后来他读到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里面有专门一章写“黑煎饼”,他又忍不住贪婪地流下涎水。“这可是救人命的煎饼啊!”奶奶和母亲舍不得吃,把煎饼留给他和妹妹。她们烙完了煎饼就去宅子前的大柳树下坐着,眼神痴呆呆地望着远处洪水滔天的黄河,“老天爷呀!别把人饿死了呀!”
天色暗下来,街上忽然像着了火似的涌动起来。
“不好了,船翻了,淹死人了!”有人哭着喊着往河边跑。母亲一腚坐在了地上,奶奶扶着柳树好不容易站起来,迈着小脚蹚水朝大河边跑,孟东野也跑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起了大风,眼看到岸了,翻了船。二十多个人都翻进了黄河里,游上来十六个,死了七个。村上人把木桶、柜子都扔进河里,骑上去捞人。乡政府也来了人,开进来两艘快艇,把红色的救生衣扔给在水里扑腾的人。三天后,七个人捞上来四个,都死了,白白胖胖,衣衫不整,肚子大得像鼓。爷爷是其中的一个,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块窝头。一溜儿尸体摆在大堤的坝头上,马家渡口的家属去认亲,哭声一直响了十几里路。幸好父亲没事,他没在这条船上。他是第二天回来的。那一天没要到多少干粮,要饭的太多了,一群接着一群。父亲狠了狠心去了孟东野姥娘家,他让爷爷背着干粮先回来。后来知道,在姥娘家,他被姥爷的一根棍子赶了出来。“滚,我没你这门亲!我也没那个吃里爬外的闺女!”父亲落荒而逃,在黄河边上哭了一场。天快黑的时候,他沿着河堤去了河北岸的县城,那里有他一个战友,在粮站工作。父亲走投无路,只好找他去赊些粮食。粮食赊到了,三十斤高粱,二十斤瓜干。第二天父亲背着往回来,到了渡口才听说昨天翻船的事。他急得像一头牛,眼珠都红了,背着粮食拔腿就朝二十里路外的潘家渡口跑,他知道那里还有一条船可以过河。
那几日,整个村庄被死亡的气息笼罩,淹死的、失踪的人家哭声彻夜不断。撑渡的老船工二爷爷会凫水,从黄河死里逃生爬上来,进屋就从里面插上了门,三天没有下床。村上没有人去找他兴师问罪,但他自己终究没有过去那个坎,等村上人埋了死者回头找他的时候,才发现他把自己锁在屋里好多天了。大家预感到不好,几个本家用膀子撞开屋门,就见老船工直直地吊挂在屋梁上,身上已经有了活蛆。
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虽然之前他也不爱说话,但这次之后,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了。父亲水性不错,也有一条小木船,他干着捕鱼贩鱼的活儿,在黄河里撒网、下钩,每天天蒙蒙亮出河收网,中午把船开回来,用摩托车驮着鱼到镇上鱼行里去卖。清水镇谁没吃过孟黑子的黄河鲤鱼?
他身上鱼腥味很浓,这是他留给孟东野最大的味道。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把家搬出黄河故道,搬到堤外平原上去,搬到镇上去。这条河留给他的家族太多噩梦般的记忆了。孟东野那时候小,感受并不深刻,但已经隐隐知道一些事。那条河在他们村头有道二叉河,是黄河的分叉,水不流动,所以很清,可以看到底下的细沙,鱼虾也多。孟东野爱和红林、喜鹊一起去这条河里洗澡。岸边的大柳树上一蓬一蓬的柳枝垂到水里,他们站着从树上往下跳,像电视上奥运会跳水的运动员。他也常逮了黄河鲤鱼或鲫鱼,用柳枝串了拿回家去。母亲是最反对他下水的,见一次打一次。孟东野逮了鱼常避开母亲,悄悄去找奶奶。奶奶有些痴呆了,并不管这些,她接过鱼来撒上盐,用泥巴裹上,再用荷叶包了塞进灶膛里去,给孟东野烧鱼吃。鱼烧熟了真香啊,奶奶还会把爷爷死时没喝完的酒拿出来让他喝。他抿一口,“咳咳咳”,酒辣得他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孟东野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回老家时捉几条黄河鲫鱼带回来,放到鱼缸里,再拉一大桶黄河水,原水养原鱼。去他妈的发财鱼吧!去他妈的锦鲤!去他妈的雪龙、鳗鱼以及各种观赏鱼!这次回乡,他准备先去五金商店买一个大的塑料桶,把黄河拉回来!
后来每一次际遇,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开会、采风、领奖,只要出差的地方有黄河经过,他都要到河边去看一看。就那么站在河边,他可以冥想许久。离开时他总要用矿泉水瓶带一瓶黄河水回去——很黄很浑的黄河水。水带回去放在书房书架上,现在已经有十几瓶了,经过沉淀,现在每一瓶都澄得清澈见底,瓶底有一层厚厚的沙土。他把瓶子拿起来,晃一晃,那水马上又混浊起来。啊,又是一条黄河在流淌!
水晃动起来,黄河就翻腾起来,不混浊还叫黄河水吗?这个时候,他坐在电脑前写字,灵感就会频频光顾,那些文字似乎也湿漉漉的,有文气。
四十岁的生日,他回到了家。这么多年了,房子还在滩区,一直没搬到镇上去,但听说这次是真的要搬了。黄河滩区整体搬迁,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社区建在镇上,楼房主体已经起来,正在配套装修。老房子置换,花不了多少钱。这也是他想尽快回去的原因之一。他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再不回来看看就找不到“老家”了。年底前一户不留,全体搬迁住新房、过新年。四十年前,他出生在老房子里,那一年黄河水不大,庄稼丰收。在当地,黄河滩区的孩子不用褯子,用沙土当褯子。那沙又软又细,闪闪发光,能吸水,不起痱子,还不硌人。孩子尿了、拉了,就直接垫上沙土,要多干净有多干净。尿完了拉完了,铲子铲出去,再铺一层新沙,热乎乎,软和和。黄河滩的孩子皮实,都是沙土上滚大的。
他是早产,生下来像个猴子,松皮拉草,皮肤又红又黑,长满细毛。娘缺营养,接生婆上门来家里接生的,差点大出血。这事是奶奶告诉他的。长孙长子,孟东野从小备受呵护、疼爱,在蜜罐里慢慢长大。“就是黄河的孩子,吃黄河水长大的。”爷爷这样说。那时候,他生命中几乎只有这一条河,他甚至没见过其他地方的河,脑子里也就沒有河水不黄的概念。
“黄河了不起吗?”
“黄河长啊。”
“有多长?”
“长到天边,黄河万里长嘛!”
“天边在哪里?”
“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果然,三十九岁这一年夏天,他追踪黄河来到了源头。五千米的高原,让他头晕,高反得厉害。一路上越走人越少,树也没有了,只剩下草地,草地远处是雪山,草也不见了。还有牦牛,草地上是一群一群的牦牛,藏族人养的,据说一头牛一万多元。肉他也吃了,可是咬不动,因为煮不烂。只是一路上他没看见一个放牛人!牦牛随意地在草地上吃草,有时候也到大路上来,行车得很注意安全。他们怎么分辨出是谁家的牦牛呢?就不怕别人偷牛吗?他心里有疑问,问司机。“外人很少进来,高反气都喘不动,哪有力气去拽一头牦牛?本地人都在帐篷里喝酒、睡觉,多一头少一头也根本不清楚,不在乎。”
这就是黄河源头了。草甸子有一汪一汪的水,那么清澈。黄河的确很长,到这里来得坐飞机、坐汽车,地图上从西到东,几乎贯穿了整个国域。回来后他又去了入海口,正好赶上黄河口诗会,诗人们站在入海口处诗兴大发,朗诵诗歌,拍照。他一个人跑到海边,看黄与蓝交汇画出的绝美的线。
浮桥要拆了。
这是母亲在电话里告诉他的第二个消息。在他的记忆中,黄河浮桥已存在了十多年。这种巨大的铁船组合成的联合体,像航空母舰。第一次见到时,他很震撼。他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船可以排在一起牢牢地固定在洪水滚滚的黄河上。比曹操的战船还结实吗?比夫妻的结婚证还牢固吗?那一年大学毕业,他跟着张娜来到南方这个省会城市,这里有一座断桥,据说是情人不得相见的地方——这又是一个不好的隐喻!张娜领着他来看断桥,给他讲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爱恨缠绵的故事,他又想起在黄河边码头上学泰坦尼克号上那对情人比画的姿势了。
那时候,他有些灰心。生活了半年之后,他发现这里并不适合他。为什么呢?环境?天气?张娜尖锐而占有欲又极强的爱?都是,也许又不全是。后来,他站在那条大河边,突然醒悟,他之所以想要逃离,很可能是因为一条河。这两条河太不一样了,一条婀娜多姿,静水流深,碧绿清澈;一条波浪滚滚,泥沙俱下,焦黄混浊。这里可没有浮桥,几公里长的跨江大桥气派、高贵,一点儿也不像那条河上的浮桥,忐忑、漂浮、摇摆。
如今,浮桥真要拆了吗?
浮桥的投资者,有当年古渡摆渡的二爷爷过继的侄子孟驰。他的第一桶金就是二爷爷半辈子积攒的渡河钱,后来他承包了维护黄河堤坝码头的工程,他带领着车队从泰山东山套里一趟一趟地拉来石头,堆放在坝头上,以备不时之需。几年的工夫,他发了财,和几个兄弟爷们儿出资去南方船舶厂订购了十六艘铁船,在黄河上架起了浮桥。浮桥开通那一天,他摆了祭品在黄河边做了祭奠,有心的人看到他眼角上挂了泪滴。有人说他是为二爷爷赎罪;有人说他是子承父业,为了将二爷爷的遗愿发扬光大。但不管怎么说,浮桥通车的那一天,可算是清水镇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可以载入史册。
多少年来,孟东野很想去河北岸看一看,但都没有成行。唯一一次寻亲无功而返,也不是从黄河浮桥过去的。那偌大的铁船,像战舰。他禁不住想起赤壁之战中曹操大军连接在一起的战船,但诸葛亮借助东风火烧连营,这又是不吉利呀!他又想起来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他爷爷背着褡裢踏上二爷爷那艘木船时的情景,逃荒要饭的人啊,一条黄河淹没了庄稼,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他终于理解了他们。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他和张娜宛如河的两岸。他有时候会这样想,之前为什么在一起呢?他黄河般的皮肤和黄河般的汹涌吸引了她?还是她静水般的婉转和长江般的执拗征服了他?那他们是如何渡河的呢?是一艘木船?机动船?浮桥?
如今,浮桥要拆除了。据说距离此处不远的地方,黄河铁路、公路桥即将竣工。届时,去河北岸再也不用花钱上浮桥了,宽阔的黄河大桥四车道,限速一百二十公里,可以尽情驰骋。铁路桥更雄伟,新高铁会呼啸着穿行而过,从此岸到彼岸只是瞬间的事了。当年他托红林从对岸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平凡的世界》,后来,那本书被他翻烂了,滚瓜烂熟,了然于胸。那也许又是一个暗示,否则,认那么多汉字干吗呢?许多年以后,为什么他真的就干上了码字的工作?天下的字那么多,每天排列组合,真的有价值吗?
他又突然很牵挂那几条鱼,它们从楼顶瀑布奔泻下来,摔死了没有?如果没有,它们又去了哪里?是不是顺着下水道流进了汶溪,又顺着汶溪流进了那条大江?
老房子破旧得不像样子了。整个村庄都差不多。村人们都做好了搬迁的准备,就在河堤外面,有一片大社区,灯火通明,高楼大厦,医院、学校、篮球场……新社区叫渡口新村。他没想到村上的人都愿意搬。为什么不搬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不比住在河道里整天提心吊胆强?
“那地呢?咋种?”
“该咋种咋种,少不了你的地;不仅不少,平了村,地还会多起来。到时候开着轿车来种地呗。”
“农民开着轿车种地?”
“咋?看不起咱农民?孟东野你别忘本,咱们村现在就至少一多半比你有钱!”
“可是那浮桥……那铁船……”
“浮桥是历史了,这么些年我也赚得盆满钵满了,黄河大桥多方便。船是铁的,还可以卖废铁。”
“那以后你干啥工作?”
“我呀,哈哈,这你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开发房地产啊。这个社区就是我承建的。”
孟东野回来后和几个堂兄一块儿喝酒,酒喝的是国窖,烟抽的是软中华。孟东野酒量不行,几杯酒下肚就面红耳热,有些醉意。
“我走了,你们慢慢喝。”
“干啥去?这才喝了多少?”
“我想去看看浮桥,看看黄河。”孟东野说话有些动情,眼圈有点红。他不知道以后回到老家来,他还能去哪里看黄河呢?浮桥拆了,那个看了多少年黄河的地方还有吗?
他揣着剩下的半瓶酒,还有一包刚拆封的香烟,朝浮桥原址走去。
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去浮桥那里站站,到那个渡口边抽一支烟。仿佛那里有一个人在等他,二十多年了,一直等着他。他记得很清晰,那一年,他十三岁,就在浮桥搭起的那一个渡口上,翻了一条打鱼船。
船是后来被吊车吊出来的,父亲人没有找到。
他趴在岸边哭,母亲挣扎着要跳下去,被人死死拉住。后来,母亲不跳了,一把搂住他,娘儿俩趴在地上哭。
河里涨水了,浪头很大,旋涡也很深,人跳进去,比一只蚂蚁还要渺小。
有一年,他顺着黄河朝下游走,遇到了一对捞尸人。那里是一处开阔的浅滩,岸边红柳林里有一片没有墓碑的坟堆。捞尸人是五十开外的两个汉子,据说已经捞了三十多年了。遇到上游来找的,找到了,赏几个钱拉走,或者就地火化。更多的是无主的,政府有补贴,捞一个给二百块钱。
“1993 年有没有捞到一个黑胖子?”
“1993 年?多少年了,记不得了。哦,那一年发大水,捞了好几个呢。”
“人呢?都认走了吗?”
“认走了两个,其他的要么顺着河漂到海里去了,要么在那里躺着,呶!”
柳树林里阴森森,没有墓碑,只有一抔黄土。黄土堆上有洞,有老鼠或者黄鼠狼钻進钻出;有虫子在唧唧鸣唱,和老家的虫子唱法似乎并不一样;树上是蝉,叫得让人烦躁。
“这一片树林子出知了龟,晚上来摸知了龟的比鬼还多!”
两个人说着笑起来,露出黑黄色的牙齿。
那一年在入海口,孟东野流下了泪,但转瞬又笑了。那海水真蓝啊,黄河的水真黄啊。偌大的湿地,有仙鹤飞来飞去,茂密的芦花似雪,白得耀眼。
几辆吊车正在拆浮桥,从河中心往两岸拆。每拆开一艘船,孟东野心就咯噔跳一下。但拆掉浮桥后的河道显得宽阔多了,那滚滚而来的黄河水也更急了,简直一日千里。
【责任编辑】安勇
作者简介:
乔洪涛,1980年生,山东梁山人,现居沂蒙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炜工作室学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首届齐鲁文化之星。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其作品被转载和收录于多种选本。曾获万松浦新人奖、奔流文学奖、齐鲁散文奖、刘勰散文奖、银雀文学奖、沂蒙文艺奖等。出版小说集《赛火车》《一家之主》,长篇小说《蝴蝶谷》。著有长篇散文《大地笔记》《湖边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