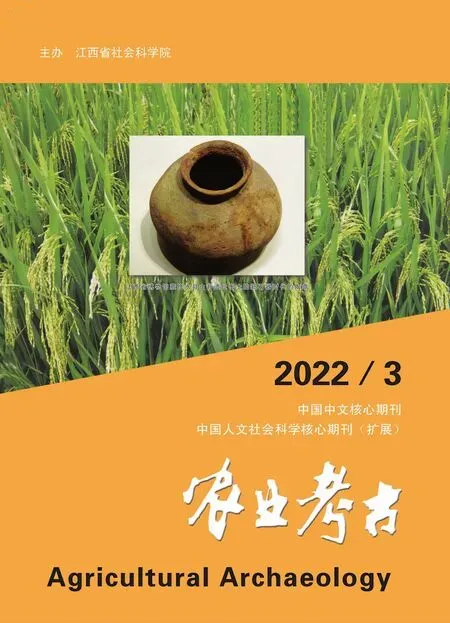再论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
——基于农业技术交流的视角
钱露露 叶 磊
纵观日本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水稻生产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上古到近世,日本的稻作农耕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从日本两千余年稻作农耕的历史实践来看,其传统稻作技术与农耕方式是颇有特色和成效的,对当世和后世社会影响深远。正如日本当代农史学家堀尾尚志所说:“日本稻作农业经过千年的发展,在建立起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推动了以米谷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相关技术理念和措施对当代农业生产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佐佐木高明(1989)、王勇(1996)、李国栋(2019)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做出了大量论述,但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稻作起源与传播、稻作遗址考古发现、稻作民俗文化等方面。基于农业技术交流视角所展开的对稻作农耕方式的历史研究则十分鲜见。鉴于此,笔者立足于日本古农书史料和相关研究著述,通过梳理和考察中日两国稻作农耕技术的交流发展史,力求从“稻作”和“农耕”两个方面探明日本上古到近世时期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源流、引进和创新、效果和影响等,以期为日语学界提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一、上古稻作农耕:水稻技术的传入与农耕具的运用
论及日本早期的稻作农耕,必先从中日文化交流的开端说起。学界一般认为,中日两国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有了初步的往来接触。此时,中原华夏文明已经崛起,其文化成就正源源不断地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地区传播和辐射。作为华夏文明成就之一的稻作技术亦在中日交流的历史大潮中传入日本,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在改变日本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使日本社会快速地由采集经济实现向生产经济的转变。
根据现今考古调查研究成果,绳纹Ⅲ期后半期的日本列岛可能已经存在原始的谷物类植物栽培。其中,从东北地区至九州地区,东西日本都有绳纹时代稻谷(陆稻)的发现,其时限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由于日本列岛的自生植物中不存在栽培型稻谷,因此可以肯定稻作技术是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列岛的。关于水稻东传的路径和方式,目前学界主要有安特生(1921)提出的“中国华北、东北—朝鲜—日本九州传入说”,安藤广太郎(1951)提出的“中国江南—朝鲜—日本九州传入说”,柳田国男(1961)提出的“中国华南—日本冲绳—日本九州传入说”,樋口隆康(1971)提出的“中国山东—日本九州传入说”,安志敏(1984)提出的“中国江南—日本九州传入说”,严文明(1988)提出的“中国江南—中国山东—中国辽东—朝鲜—日本九州传入说”等观点。以上观点尽管各有主张,但有两点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其一是认为日本的稻作技术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其二是认为水稻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一条路线才实现的,而是多次的、通过多种渠道完成的。
根据日本记纪神话,将稻作技术直接传入日本的人群可能是那些“海人部”,也可能是吴越地区的先民。不管传入者是谁,稻作技术的东传拉开了弥生时代的帷幕,也开启了日本列岛组织集团化稻作农耕的历史,为后来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不过总的来说,弥生时代的稻作还属于个别区域的零星种植,尚未得到广泛推广,所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中国长江流域传来的短粒型粳稻。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农业生产力相差悬殊,因此,东传的稻作技术在日本本土未能保持其原有的姿态,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先进的犁耕技术、插秧技术、堆肥技术等并未得到有效运用,栽培管理相对原始和粗放,水稻从播种到收获均在一块田地中完成,基本不区分秧田和本田。也就是说,日本当时的水稻栽培主要采用直播技术,即简单整地后撒上稻种直至收获,这一原始的栽培方式显然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根据考古发掘,冈山县百间川遗迹的小区划水田中发现了部分有规则性的稻茬痕迹,反映出弥生晚期个别农业生产力发达地区可能也存在着插秧和育秧的技术。事实上,无论是直播还是插秧,弥生时代的稻作产量水平并不算高,约相当于现代产量的一半左右,主要是因为弥生水田本身的生产力不高。现代考古发现,不少水田的遗迹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杂草种子,其中不仅有水田杂草,还有旱田杂草,说明当时的水田很有可能是采取休耕法,每年只是在一部分水田实施耕作,其他水田则处于休耕状态。由于水田耕作生产力的限制,稻作收获量无法完全满足整个社会的粮食需求。因此,在弥生时代人们的生活中,杂谷、坚果等依然占有一定的比重。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水田稻作遗迹有福冈县板付遗迹、静冈县登吕遗迹、佐贺县菜畑遗迹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遗迹中还出土了不少与水田耕作密不可分的农耕具,反映出弥生时代稻田耕作的基本格局。从农具的来源来看,这一时期以输入型农具居多;从农具的种类来看,以水稻生产农具居多,此时尚未出现畜力农具,因此稻田农耕主要还是依靠人力;从农具的材质来看,主要有木质和铁质两类。木质农具镐和锄是弥生水田农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耕具,笔者认为是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在借鉴秦汉农具特别是中国传来的榫接技术后所形成的一种改良型设计。镐脱胎于汉代的多齿锄,从功能上可分为用于硬土翻耕的长型镐和用于整地匀田的胖型镐、叉型镐;锄类似于古代中国的耒耜,从形制上可分为单柄锄和组合锄两类,主要用于开垦土地和耕作低洼湿润的黏质土壤。从日本大阪龟井遗址中出土的一把单柄锄的形态来看,弥生时代的锄与我们今天农作中所使用的铲似乎差异不大。除镐和锄外,木质农具还有田履(木制大脚)、田舟、单柄耙、竖杵、捣棍等。这些农具推测在公元2世纪前后由中原地区传入日本,农具名称基本沿用中国传来时的称呼,材质上多使用硬木制造,因此比较坚固耐用。到了弥生中后期,中国大陆铁器的传入使弥生农具朝着铁器化的方向发展,并由西向东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准确地说,弥生中期传入的铁器多为铁质武器,铁质农具的传入、使用和普及应是在弥生后半期。稻作农耕的发展最需要的是生产工具的供应,只有使用坚硬的铁器工具才有可能达到量产化,铁镐、铁锄和铁镰等铁质农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普及开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农具的铁器化虽然在弥生时代已经完成,但当时的日本并没有直接生产铁器的能力,中国成品铁器的输入应是弥生时代铁质农具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的铁质农耕具与中国汉代农具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总之,纵观日本上古弥生时代的稻作和农耕具,中日农业技术交流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稻作生产工具明显带有中国大陆文化的特征。从日本对相关技术的利用,尤其是镐、锄、单柄耙、大足、田履等农具的使用情况来看,弥生时代的水田稻作是颇为体系化的,至少已经形成了平整稻田、土壤培肥、田间管理等工序,标志着古代日本的精耕细作农业已经开始萌芽。
二、中古稻作农耕:水稻技术的本土化发展与牛马耕
从广义上讲,中古时代是指从6世纪末飞鸟时代的开启到12世纪末平安时代完结的600年间。由于铁质农耕具的不断普及,水稻种植在中古时代的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广,但这一时期的种植制度依然是弥生时代以来的作物单熟制。尽管此时日本的农作物品种已十分丰富,理论上可以实施轮作复种,亦即在水稻收获后种植二麦、大豆等其他作物,但或许是由于排水干田技术较为落后,以稻作为中心的多熟制并未真正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已大规模开展了对中国大陆水稻技术的本土化改良,其典型事例是奈良时代水稻品种的本土化选育。《续日本纪》养老六年七月戊子诏曰:“宜令天下国司劝课百姓,种树、晚禾,藏置储积,以备荒年。”(笔者译,下同)“晚禾”即意味着当时的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分。根据日本学者平川南(2008)考证,奈良时期的水稻不仅有稻期之分,更有熟期长短之别,稻种名称有 “和佐”(早稻)、“白和世”(早稻)、“长非子”(中稻)、“古僧子”(晚稻)、“地藏子”(晚稻)等,说明时人已不再完全依赖中国大陆传入的稻种进行种植,而是能够因时、因地、因种进行针对性的品种选育和本土驯化。再者是平安时代育秧移栽技术的本土化。日本史书对水稻育秧移栽的首次明确记载见于《今昔物语》。笔者推测育秧移栽的出现很可能是受9世纪东传农书《齐民要术》的影响,认为此法可以减轻草害并有利于提高水稻的产量。及至平安后期,育秧移栽逐渐成为日本稻作的主流,弥生以来的直播技术仅存在于湿地新垦田的种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育秧移栽相比以往的直播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女性逐渐成为日本稻作的主要劳动力。总之,随着育秧移栽技术的实施,日本水稻的种植程序进一步完善,涵盖了翻耕、碎土、分畦、施肥、下种、育秧、移栽、除虫、培土、除草、收获、脱粒等多个环节,精耕细作的稻作栽培体系初步确立。
除水稻栽培技术的本土化外,其他配套管理技术也开始了其本土化的发展和实践。例如,日本天长六年(829)因“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在旱损,传闻唐国之风,堰渠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在时任大纳言的良峰安世推动下,日本在中国唐时传入的“龙骨车”的基础上积极改良和推广新式灌溉工具,命令民间自造新型水车“以为农业之资”。此类水车借用人力或畜力,能够将水从低处提升至高处,灌溉耕地面高于水面的田地。又如,日本承和八年(841),朝廷命令诸国推广大和国宇陀人所发明的晒谷技术,即在田中设置稻架(干稻器)“悬曝种谷,从而改变了自古以来席地晒谷的传统,解决了因此而带来的种谷遇水霉变等诸多问题。
关于稻田耕作,从史料的记载情况来看,中古时代稻田的农耕动力已由人力转变为畜力,其标志性事件是犁的引进和使用。根据日本农史学者河野通明(2009)研究,犁和牛均是在公元6世纪时由朝鲜移民带入日本的,最早引进的犁是无底板犁(日称“子日手辛锄”),由于在水田中的操控性差,如有不慎就会导致稻田底墒漏水,故自其传入后便立刻转用于旱田耕作。依据《和名类聚抄》《杨氏汉语抄》等古籍文献,真正用于稻田耕作的犁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前后从中国华北传入日本的。这种犁由于犁底较长,因此也称为长底板犁(日称“长床犁”),其优点是具有较好的摆动性、速耕性以及较强的平衡性,缺点是因长床的存在而限制了深耕。事实上,长底板犁在古代中国仅用于旱地作业,旨在通过浅耕来保持土壤水分。但因长底板犁稳定性强,故而这一旱地耕具在引进日本后被创造性地改用于水田。纵观整个中古时代,日本除了在稻作农业区大力推广长底板犁外,还逐步对犁型实施了本土化改良:一是将犁底由原先的5尺增长到6尺(相比同期中国的长底板犁要长出1尺余),进一步增强了犁的稳定性和可操控性;二是使犁底与犁壁成为一体型结构,即由一块木板制成,这一点已从公元927年的《延喜式》和14世纪的卷式图画中得到了印证。总之,犁的引进和改良在日本农业历史上的意义重大,它使日本从原始的“锄的时代”一跃进入到了畜力牵引的“犁的时代”,牛马耕取代了人力被投入到水田农业生产当中。据令制规定,每二町官田配置牛一头。在《续日本纪》中也有“马牛代人,勤劳养人”的记载,表明牛马已逐渐代替了人的繁重劳动。尽管各类史料中并没有指出日本古人为何会选择“马”作为农耕动力,但笔者猜测可能是因为“马耕”的效率要优于“牛耕”,比较适合硬土翻耕作业。而相比之下,马在中国仅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在各类农史典籍中很少见到有将马投入稻田耕作的记载。
三、中世稻作农耕:水稻技术的精细化发展与耕耙结合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世稻作农耕的水平又有显著进步。日本在引进宋代中国“太唐米”等新品种的同时,也致力于驯化和选育本地品种。至室町时期日本的水稻品种已达到数百个之多,早生和中生品种的栽培开始逐渐增多。随着中国明沟排水技术的传入和推广,种植制度也实现重要突破,多熟种植渐成常态。综合笔者所掌握的史料,相比中古时代,这一时期的稻作农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
一是水稻栽培技术的精细化。受唐宋东传农书的影响,日本中世农人开始重视水稻栽培与后茬作物的轮作,致力于通过轮作方式提高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自镰仓中期“稻—麦”种植(一年两熟制)取得成功后,“稻—豆”“稻—粟”“稻—菜”等以水稻为中心的多样化、精细化的轮作复种形式在日本列岛逐步推广开来,成为日本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事件。水稻栽培技术的精细化还体现在水稻播种前人们对稻谷的创造性处置,即水稻的浸种催芽。也就是说,自中世起,人们在下种前又增加了浸种催芽这一新的工序,其目的在于刺激种子内部的发芽势头。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一技术很可能是通过《齐民要术》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推测是在9世纪前后。发展至中世时,无论是浸种的方式还是浸种的天数都已与中国的原生技术差别较大,体现出日本民族既重吸收也重创造的性格特质。
二是配套管理技术的精细化。随着唐宋以来中国水利灌溉技术的不断更新升级,日本民间在中国先进经验基础之上成功自制了“水力车”,实现了稻田灌溉由人力畜力向自然力的转变。据考证,日本水力车的原型为宋代的水转翻车。日本应永十年(1403)到访日本的朝鲜使臣在回国的报告文书中曾对其所见到的运用水力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由于灌溉技术的进步,日本多数地区都实行了轮作复种和多熟种植,在畿内平原等光热条件较好的地区甚至创造出了水稻的一年三熟制,即三季稻。
三是稻作管理理念的精细化。在宋代“地力常新壮”思想的影响下,中世日本开始重视广辟肥源,要求“精于用粪,勤于用肥”。稻田肥料除使用草木灰外,还广泛利用人粪尿、牛马厩肥、酒糟、油渣等农家肥。在强调“多肥栽培”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施肥、精准施肥的重要性,追肥因此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除施肥外,人们还十分重视稻田的中耕除草,要求“细锄、勤锄、锄早、锄小”,认为即使没有草害也要耘田,这一观点与宋代《陈敷农书》“薅耘之宜篇”中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为了防止杂草与稻苗争肥,改善土壤透气性,中世日本在《陈敷农书》的经验基础上发展出蓄水耘田法、近根中耕法、轮作除草法等多种行之有效的中耕除草方法,同时还创造出“三本锹”“耘镰”“耨锄”等高效耘田工具。据日本《农具便利论》载,“三本锹”亦名“雁爪”,具有“省工省时轻翻入土使草成肥”等妙处,其精细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稻田耕作依然使用的是中古时代的长底板犁,尽管耕深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但是在同时期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视耕作的质量,强调“耕”与“耙”相结合,即要求“耕得精”“耙得细”。据载,自室町时代起,以近畿农业区为中心的稻田作业中,犁耕之后新增使用了各种“耙”类工具来平整土地。此类工具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当属“马锹”。马锹即马拉的水田耙,是一种用于水田翻耕后的碎土平整农具,在古代日本有多种称呼,如《弁色立成》(奈良时代)称“马杷”,《新撰字镜》(892)称“马齿”,《延喜式》(927)称“马锹”,《伊吕波字类抄》(12世纪末)称“马把”,《朝仓始末记》(1573)称“马地”,近世后期统一定名为“马锹”。这一农具早在古坟时代就已由中国传入日本(最初仅用于旱地作业),其原型是中国三国时代的畜力拉耙。中世时期出于精耕细耙的需要,马锹开始由旱地转用于水田,并逐步分化为“车马锹”“药研马锹”和“谷马锹”三种类型。其中,“车马锹”在关西的播州平原使用广泛,适合在土壤黏重的水田耕作;“药研马锹”的形制与“车马锹”相似,主要用于平整田泥;“谷马锹”形制最小,比较适合小面积土地的耕作。总之,马锹的推广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壤耕作的质量和效率,加之这一时期稻作栽培管理技术的精进,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相比前代有了显著提升。
四、近世稻作农耕:水稻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与精耕细作
近世时期亦即17世纪以来,随着中日两国汉籍交流的兴盛,中国农书开始大量东传。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日本引进和翻刻中国农书的数量多达140余部,其中明清农书就有114部。在东传农书的启发和影响下,日本掀起了自编农书的浪潮。日本元禄十年(1697)的《农业全书》就是一部以明末《农政全书》为范本,结合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与日本各地农事经验的代表性农书。该书的出版拉开了日本地方农书的编写序幕,进而使明清以来中国先进的稻作农耕技术得以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日本稻作也因此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高度成熟发展阶段,构建起包括育秧移栽、肥料积制、虫害防治等技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水稻栽培管理体系。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稻作农耕是对中国传统农学的亦步亦趋,那么近世时期的稻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个性发展和自主创新。这一时期日本稻作技术领域最大的创造就是“稀播疏植”特色水稻栽培方法的运用。人们通过长期生产实践成功摸索出以“稀播,长育,疏植,少本栽插”为核心的稻作栽培法,这一技术的创立不仅纠正了以往稻作“密播密植”的通行做法,同时也实现了包括水稻在内的多种分蘖性粮食作物的高产稳产和瘦田增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耕稼春秋》《农业自得》等近世日本农书十分强调“稀播疏植”的本土自创性,但是考虑到近世日本普遍实施这一技术是在18世纪以后(时值清代中前期),而中国方面据明末清初《沈氏农书》记载早在17世纪前期就已十分重视“稀播壮秧、疏植透光”的技术经验,由此推测,这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了明清中国的启发和影响。毕竟这一时期日本引进和翻刻中国农书的数量十分庞大,而《沈氏农书》很可能就是近世日本“稀播疏植”稻作技术的直接来源。
除水稻栽培法的创新外,日本稻作管理的其他环节亦有不少新的创造。譬如,人们在传统农家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出具有更高肥效的商品肥料,亦即各类农书中所记载的“金肥”,如干鰯(沙丁鱼肥)、鲱粕等深海鱼肥以及拍成砖或饼的油菜籽、棉籽等籽肥。“金肥”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日本肥料单一的局面,有效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因之得到了显著提升。在虫害防治方面,人们创造性地发明了“鲸鱼油治虫法”来防治稻田虫害(浮尘子),这一措施极具日本岛国特色。据日本《除蝗录》记载,单位面积稻田注入鲸鱼油少许即可收治虫奇效。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所发明的“暗渠排水技术”,为日本近世农学家大坪二市所首创,后由大藏永常所改良,中国农书似不多见,其技术要领在于稻田底部堆砌规则石块以布置沟渠,并在沟渠交汇处置以可活动的松木角材来进行水分管理。对于该法,日本当代农史学家冈光夫评价说:“近世的暗渠排水法是在古代中国明沟排水法基础上的一种重要创造,在改良稻田土壤、保障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出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代表了这一时期农田给排水工程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稻田农耕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农业的精耕细作需要深耕,然而中古时代沿袭下来的长底板犁又无法实现深耕,因此,近世稻田翻耕又由“犁耕”回归到了“锄耕”,所使用的耕具是人力铁锹,而人力铁锹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备中锹”。这种高度专门化的裂刃锹由中世的平刃锹改良而来,其耕深和耕作效率要远超长底板犁。日本《农具便利论》中说,“备中锹可替耕犁,可省劳力,其乐无穷也”利论》,P1。正如堀尾尚志(1977)所说,日本的农耕具发展史是一个锹(锄)与犁交替演进的历程,即“木锹(上古)→长床犁(中古中世)→铁锹(近世)→短床犁(近代)”。需要说明的是,近世农人在将人力铁锹作为稻田主要耕具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长底板犁的使用和改良。在东传《农具记》等农器图谱以及中国曲辕犁技术的影响和启发下,人们创造性地将长底板犁的直辕改为了曲辕,犁壁由木片改为了铸造铁片,为长底板犁向近代短底板犁的过渡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前述耕具发挥出最大的耕作效率,日本各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了许多颇具特色、更加精细的地方耕作法,如日本《会津农书附录》中所记载的“真果敢耕作法”“左转真果敢耕作法”“右转真果敢耕作法”和“钩果敢耕作法”就是四种不同的精耕细作式的稻田耕作法从某种程度来说,前述耕作法既是对明清中国地方耕作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种结合日本地方实际的自主创新设计,相比起传统的耕作法具有细密高效、劳动强度低和耕地质量高的特点。
除耕具和耕作法的改良创新外,近世其他稻作农具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其种类相比中世增多了数百种,其效率相比前世也提高了数倍。例如,中耕除草新农具“油扬万能”由中世普通平锄改良而来,因除草效率高而受到近世农人的普遍欢迎;汲水灌溉新农具“踏车”和“小车”均为近世发明的简易立式水轮,因造价成本低、提水效率高而在这一时期广泛普及;粮食加工新农具“千齿打谷器”相比前代竹制的“脱粒筷子”,其效率提高了近10倍。总之,这一时期适用于稻田耕作各个生产环节的农耕具已配套成龙,为稻作农业精耕细作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五、古代日本稻作农耕的成效和影响
(一)古代日本稻作农耕的成效
反映稻作农耕成效的主要指标即稻作单位面积产量,具体可通过观察全国单产和地方单产两个指标进行判断。根据安藤广太郎(1959)、楫西光速(1980)等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古时期日本全国稻田单位面积产谷每反(约合现今1.5市亩)约1石上下,中世时期为1.3石上下,近世初期增加到1.5石上下,近世末期达到2.5石上下,折合现今每市亩400市斤。地方单位面积产量可见于日本古农书典籍,如日本《会津农书》记载,17世纪会津地区的稻田单产为3.8石(折合现今每市亩590市斤)。由于会津地处日本东北寒地,在不利的气候条件下依然能够有如此之高的产量,足见其稻作技术的水平和成效。另据日本《农业自得》记载,19世纪中叶下野国河内郡田村家长期实施“稀播疏植”稻作技术,其上田产量高达4石有余(折合现今每市亩640市斤),这也是笔者所见古代日本地方稻作的最高单产记录。
再看古代中国的稻作产量情况,根据我国农史学家吴慧(1986)研究,唐代水稻亩产1石上下;宋元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平均亩产大致在1-1.5石之间;明清以来基本维持在亩产谷2石以上的水平(折合每市亩292市斤)。南方要略高于北方,单季稻产量要高于复种稻产量。当然,各类史料中也不乏对地方稻作的亩产记录。如清代《齐民四术》说“苏州亩常收米三石”(约产谷4石,折合每市亩584市斤);又如《黄梅县志》载“本县泉甘土沃,计亩可获五六石”(折合每市亩730-876市斤)。通过对比发现,古代日本的全国水稻单产虽然一直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国,但是其整体产量水平却在不断提升。日本的地方水稻单产虽不比四川、黄梅等地,却与中国核心稻作区苏州不相上下,这一点也恰恰说明了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技术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之所以能够取得不俗的成效,笔者认为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因即日本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从中古到近世,无论是公家朝廷还是武家政权,出于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的需要,均面向广大农民实施了积极的农业政策,如中古的班田收授法、中世的新田开发法、近世的检地与小农自立政策等。一系列激励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成为农业进步的有力杠杆,进而有力促进了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因即中日两国长期友好的文化交流。在两国数千年的农业交流史上,农书的传播交流在推动日本传统稻作农业发展方面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据考证,《齐民要术》《兆人本业》两部农书早在唐代就已传日。明清时期,中国农书的对日传播交流达到顶峰,日本立足中国农书自编了大量本土农书,从而使得中国先进的稻作农耕技术得以在日本列岛广泛推广,对日本传统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古代日本稻作农耕的影响
我们认为,古代日本稻作农耕技术的出现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日本文明的形成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和发展。正如蔡凤林(2015)所说:“古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大陆各种文化多时期、多方向、多次数、多途径传入日本列岛,和日本文化碰撞、交融、发展的结晶。”而早期中国大陆各种文化中最具主导和决定意义的无疑是先进的稻作技术和稻作文化。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生活急速转向为以农耕为主的集落定居生活并进而发展为氏族部落。此后,为了解决长期稳定的稻作农耕定居生活所带来的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等问题,氏族部落集团通过战争相互统合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国家(大和国)。随着水稻农耕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进一步发展,大和国开始兼并周边小国并逐步实现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进而实现了日本文明的质的飞跃。从古代日本“原始散居→村落定居→氏族部落→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稻作农耕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无疑是日本文明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
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方式还影响并决定了日本国民性格的生成。水稻这一单一性质的生产形态作为变革力量在激发社会制度变迁的同时也空前丰富了精神领域的内容,即在稻作农耕的特定生产方式和特殊自然环境下孕育发展出了强烈显著的国民性格。笔者曾在《稻作农耕与日本民族的稻作文化性格》一文中指出,这种日本国民性格具体包括“高度依赖”的集团意识、“精细勤勉”的精农主义以及“以和为贵”的协调精神。集团意识是日本稻作农耕社会中形成最早、最为突出的民族意识。日本人高度依赖于集团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古代稻民对村落集体这一水稻生产管理组织的高度依赖以及日本民族在历史上对水稻种植这一单一生产形态的高度依赖。精农主义是劳动者勤恳专心、精耕细作,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态度。由于水稻生产是日本古代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主要途径,因此,精农主义也就表现为日本民族对稻作农耕活动的忘我投入。“以和为贵”的协调精神同样来源于稻作农耕这一生产方式。古代不同村落间水资源的协调与管理造就了“和”这一精神形态的诞生与存续,这种精神在后来东传并日本化了的儒学伦理观念的作用下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可以说,日本民族的“和”更为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进而形成了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回报自然的和谐自然观。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技术理念和措施在当代的农业生产中依然焕发出光彩和活力。前文所述及的近世“稀播疏植”稻作技术即现今日本自然农法所推崇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长期实践表明,“稀播疏植”传统稻作方式相比现代机械化肥稻作虽然无法做到省时省工,但却能够在不施化肥、不撒农药的同时保证水稻的每穗颖花数和千粒重得以显著提升,其单位面积产量也因此更胜一筹。由此不难看出,传统稻作的实施尽管较费人力,但却避免了因施用化肥、农药所造成的土壤板结和食品污染等问题,维持了稻田生态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正常循环。笔者看来,在环境及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传统稻作农耕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尤显重要。现代农业所追求的应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即以传统技术保障水稻生产的质量和安全,以现代科技提升水稻生产的效率和产量。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才是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之道。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稻作技术与农耕具技术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吸收与改造并重、引进与创新并举的特点。日本上古时代的稻作农耕受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影响最为深刻,无论是稻作技术还是农耕具技术都带有明显的中国大陆文化的特征;中古时代,日本的稻作农耕进入到本土化发展阶段,稻作技术及其配套管理技术多有改良创新,犁的东传和引进使农耕动力由人力转变为畜力,牛马耕得以推广,精耕细作的稻作栽培体系初步确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世时期的稻作农耕更趋精细化,稻作栽培管理的理念、技术与方法不断成熟和精进,稻田耕作开始强调耕耙结合,在耕后新增了使用耙类工具平整土地的环节;近世时期在中国东传农书的启发和影响下,日本掀起了自编农书的浪潮,在稻作技术等领域实现了个性发展和自主创新。出于深耕的需要,稻田翻耕又由“犁耕”回归到了“锄耕”,耕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了许多颇具特色、更加精细的耕作方法。适用于稻田耕作各个生产环节的农具也已配套成龙,精耕细作的稻作栽培体系正式确立。
可以说,古代日本稻作农耕的发展离不开中日农业技术的交流,而日本稻作农耕在依靠东传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根据本土实际自主创新,从而形成了同源性与自主性并存的双重内在特质,构建出与中国方面“类而不同”的、具有典型岛国特色的稻作农耕技术体系。通过产量指标的对比研究表明,古代日本的稻作农耕技术是卓有成效的;其稻作农耕形式不仅对日本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对当代生态农业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