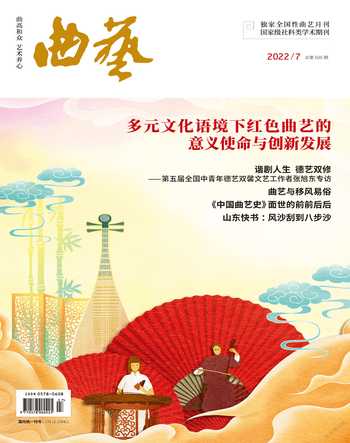《中国曲艺史》面世的前前后后
倪斯霆 耿柳
作为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父亲倪钟之的代表作《中国曲艺史》经评审专家组审议,日前已获立项,将被译成英文在德国出版机构Springer Nature出版发行。对此,诚如媒体报道所言,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世界对中国曲艺的了解,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从概念化走向精微与幽深。其实,让源远流长的中国说唱艺术走出国门,既是父亲生前的心愿,也是他这一生不倦的追求。如今这一切都将变成现实,确实让人感到由衷的欣慰,然而,高兴之余不免生出一种深深地怀念,不仅是对父亲,也是对此书的出版策划者耿瑛老师。
时光易逝,转眼间《中国曲艺史》首版面世已31年,父亲故去已6年有余,耿瑛老师故去也已4年多,如今回想起这本书当年的写作出版历程,一幕幕往事不由得又浮现眼前。
1984年,隶属文化部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在津筹建。经上级部门点将,父亲成为当时的三个筹建人之一。在负责学校所有专业课老师遴选、考察和调入的同时,还主持了各专业设立及课程设置工作,并被校方任命为首任教务主任兼曲艺文学系主任。
那些日子,他整天忙于考察、谈话、磋商。经过认真考量和与相关领导及机构反复磋商,最终经父亲之手为学校引进了骆玉笙、田连元、孙书筠、王世臣、刘学智、徐桂荣、韩德荣、朱学颖、张剑平、刘文亨、阚泽良、曹元珠、田立禾、王文玉、田蕴章、魏文华等一批专职与兼职教师。此举既确保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增强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北方说唱艺术的传承,自古便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以团带学员的方式培养新人。因此,曲校筹建之初,别说是教学大纲,就是一本学员手册也没有出现过。面对此等现实,作为学校学科负责人和教务主任,父亲只能白手起家独自承担起了“曲艺教学大纲”的制定和编写工作。在经过数月调研学习和策划撰写后,父亲完成了一部百余页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教学大纲》。这部教学大纲最终通过了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双重审核,可以说,它是首部被国家认可的正规曲艺教学规范模板,不但成为当年曲校专业教学和课程设置的依据,而且还被其他艺术院校所照搬。
那时父亲已有将教材进一步丰富完善交出版社付梓的想法,没想到很快在耿瑛老师的帮助下,父亲的这部书稿被春风文艺出版社列入了重点选题。记不清有几次了,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和写作进度,耿瑛老师不辞辛苦从沈阳赶到天津,住在父亲所分的曲校宿舍那间简陋的书房中,一边审阅完成的稿件,一边与父亲一起研究修改方案。我曾多次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早上我将买好的早餐送到他们住处,连夜工作后的他们走出烟雾弥漫的书房,到曲校后面的水上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他们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刻。1991年3月,经过父亲的辛苦撰写和耿瑛老师的严格把关,《中国曲艺史》终于完稿,并完成出版,次年该书被评为“中国图书奖”,被称为“填补空白之作”。随后,在由中国曲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曲艺史》学术研讨会”上,关德栋、程毅中、张锡厚、白化文、刘锡诚、汪景寿、耿瑛、张鸿勋、车锡伦等业内专家学者,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文汇报》等各大媒体,做了翔实报道。该书在经过30余年的检验后,2021年,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插图本。
父亲之所以能够写出《中国曲艺史》并取得如此佳绩,与他长年构想和多方准备密切相关。父亲是遗腹子,1936年11月16日生于津城一个平民家庭,自幼随祖母与寡母长大。民国时期的天津,戏曲、曲艺演出流派纷呈,名角荟萃,被誉为“戏曲大本营”和“曲艺之乡”。父亲少年时期因随母亲经常出入各戏院、杂耍场,由此喜爱上了这些传统艺术。1957年,父亲从天津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今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建工局工作。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对中外演艺文本及表演艺术的钻研,在研读了大量戏曲、曲艺史料的基础上,他结合当时流行的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对当年尚未形成任何理论的曲艺创作与表演进行了学术思考。
1958年,他在《海河说唱》发表了曲艺研究处女作《谈相声的欣赏》。对在新时代人们如何欣赏相声及相声如何适应新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等问题,作出了理论阐述。此文一出,便引起国内专家学者及业内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新中国首场关于全国曲艺界尤其是相声界的大讨论。此举不但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对已经公演的部分相声作品进行重审,而且也对当年马季等名家的新相声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场大讨论,实际上就是当今人们从接受美学与观众心理学角度对相声艺术进行研究的肇始。

1962年,因在曲艺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业绩突出,父亲被调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其实当时文化局是准备将他作为新文艺工作者,调入天津市曲艺团的。但父亲那时已有写作中国曲艺史、杂技魔术史及演艺民俗史的想法,他认为,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涵盖了“撂地”时期杂耍儿技艺的各个类别,不但具有市曲艺团所包含的各类曲种,而且还有评书、魔术、杂技等“市团”不具备的演出项目。此外,在这个“区团”中,保留“原生态”演出遗风的艺人众多,他们不仅阅历丰富,而且演艺民俗色彩更为浓郁。父亲觉得这些人对他将来写史帮助更大,于是他便主动要求去这个“区团”。在此后的时光,父亲便充分利用“区团”的这些优势,在外出巡演及市内各种演出间隙,采访记录了众多老艺人的表演经验与从艺经历。这期间,举凡发生在天津文艺界尤其是曲艺界的大小事件,他都曾亲身经历,并且在诸如防洪水、战海啸、农村下放、四清、慰问知青及内地建设者等运动及活动中,创作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曲艺作品。
父亲勤于笔耕,继《中国曲艺史》之后,又相继推出了《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倪钟之曲艺文选》《刘文亨和他的相声艺术》《张剑平和他的曲艺创作》《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倪钟之曲艺二论》《中国当代曲艺史》等专著。其中的《中国当代曲艺史》长达120万字,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卷出版。此外,父亲还与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共同主编了《中国曲艺通史》。
2016年2月18日,父亲因积劳成疾,在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多后,不幸辞世。当时年长父亲三岁的耿瑛老师闻讯异常悲痛,含泪写下“身在辽沈望天津,我与老倪友情深。如今人去书还在,学他研究曲艺真。”,并让其女耿柳赶往天津悼念。耿瑛老师心情略微平复后撰写了悼念我父亲的长文,岂料两年之后,耿瑛老师也不幸故去。如今,《中国曲艺史》即将走出国门,我想这应该是对他们二老的最好告慰。
英译版的《中国曲艺史》社科基金立项准备出版了,恩师倪钟之的公子斯霆兄想起此书的出版经过,心潮起伏,说要写点什么,纪念一下,我听完颇有感觸,也把思绪拉回到30多年前。
1988年,我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曲艺文学班,学习曲艺理论与创作。倪钟之先生是曲艺史、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授课老师,那年倪老师50岁出头儿,中等身材,很结实,不修边幅,爱穿浅灰色的上衣,两个兜盖儿总是不对称,一边儿鼓鼓囊囊,可能揣的“大前门”,另一边儿起着四四方方的棱子,估摸是揣了盒火柴。他长方脸,浓眉毛,眼睛不大很有神,头发一簇一簇的很粗壮,一如他的耿直。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谈时,有几绺白发微微颤动,像极了飞舞的半截粉笔头儿,好像随时要被抛出来打向不认真听课的我。倪老师写板书很快,语速也快,个别语句有独具特色的天津口音,每节课的信息量都很大。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和我们偶尔拉个家常,他是不苟言笑的,所以即便我知道他和我父亲是多年的好友,我对倪老师还是充满了敬畏。
1989年,我们文学班的评书、相声、鼓曲创作课都结课了,时为教务主任的倪老师向我父亲发出邀请,请他来校教授二人转的写作技巧。我父亲虽然是曲艺编辑,但是他对曲艺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编辑层面上,他热爱曲艺,平常喜欢与老艺人打成一片,悉心学习钻研曲艺艺术,20多岁就创作了《二人转写作知识》一书,后来还有专著《正说东北二人转》出版。即便如此,二人转毕竟属于地方曲种,据我了解大多数的学生不那么有兴趣,而且我的母亲脑出血后还在康复阶段,也需要照料。我就给我爸写信:“……来津校授课要半个月,上课后还要批改作业。除了东北的学生外,其他地区的学生并不想学二人转创作。另外您来的话得住在男生宿舍的另一头儿,条件很简陋,我妈妈身边没人我也不放心,您斟酌一下推荐个其他人来为好。”我父亲却说有教无类,“哪怕有一个人想学,我也去!”我母亲一直也十分支持我父亲的工作,并没阻拦。

想不到的是,父亲到津之后的课很受欢迎,他课余时间把我的教材拿去看,倪老师的曲艺史油印本深深吸引了他。我本想父亲来了能带我出去下几回馆子,结果我每天喊他去吃饭,他总是说:“等我看完这章就去。”常常是食堂过了饭点儿,学校所属偏僻,晚上也买不到吃的,他就只能饿着肚子接着看稿,跟他说话他也不搭茬儿,我只好讪讪地溜回自己宿舍。到他快走时,他已经把厚厚的教材看完了,还密密麻麻做了很多笔记。父亲对倪老师说:“此稿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我回去以后马上给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写报告申请出版。”
倪老师听到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机会出版,可以让更多读者学习了解曲艺,感到十分欣慰。我父亲也为能出版《中国曲艺史》这样的鸿篇巨制而兴奋。然而,一盆冷水悄然泼下,因当时并没有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项目和扶持政策,需要出版社自负盈亏,《中国曲艺史》并不能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所以我父亲的报告石沉大海了。
转眼到了1990年寒假前,收到父亲来信,对我只有寥寥数语:“爸爸起早贪黑编写书稿,没工夫给你写信,你要努力学习。”却有一封长信让我转交倪老师,信中有申报选题中遇到的困难和其他情况说明,也有对《中国曲艺史》的充分肯定和修改建议。倪老师回信:“耿兄,看后详情尽知,体会到老兄为此书努力之情。从现在进度看,春节后可完。如有问题,可在耿柳返校时带信给我……因为这是第一本正规的曲艺史,很多资料需要反复核实,在接待外宾时,总有人问及我国有无此类著作,出版此书也许能对国内外学者有些影响,这只是一点奢望,也不敢想得更多。”
我父亲耿瑛是1933年1月生人,高中毕业就到了出版社当编辑,编过大量的文艺书籍,196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变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后,他陆续编辑出版了王亚平的《百鸟朝凤集》、马季的作品集《登山英雄赞》、刘宝瑞的《单口相声集》、《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等书籍,这些名家首次出版的作品集印数都达数万册。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任春风社艺术编辑室主任,和辽宁省曲协联合调查了辽宁说书艺人的情况,编辑出版了刘兰芳的《岳飞传》、田连元的《刘秀传》、单田芳的《明英烈》、陈青远的《响马传》、郝艳芳的《小将呼延庆》等70多部书籍,印数都在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新华社在报道中说“春风社刮起了评书春风”。
1990年夏天,距离父亲退休的日子只剩下二年半的时间。他心急如焚,再次给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写报告申请出版《中国曲艺史》,这次他附上了一封信:“我给春风社编辑出版过600多种图书,绝大多数是赚钱书,我在退休前能够完成《中国曲艺史》的编辑出版工作,死而无憾!”
这封信引起了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春风文艺出版社领导的重视,能让一个有几十年编纂经验的老编辑如此铮铮一语、掷地有声的书,一定是有价值的好书。就这样,经过夜以继日地编校,终于在1991年3月,倪钟之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曲艺史》与读者见面了,红色封面上印着的“击鼓说书俑”笑语盈盈,似乎在对二老说:“我是中国曲艺史的一部分,你们亦是。”
正所谓:
一部《中国曲艺史》,同声同气两情痴。
墨梓遗香今在手,薪火传与后人知。
(责任编辑/邵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