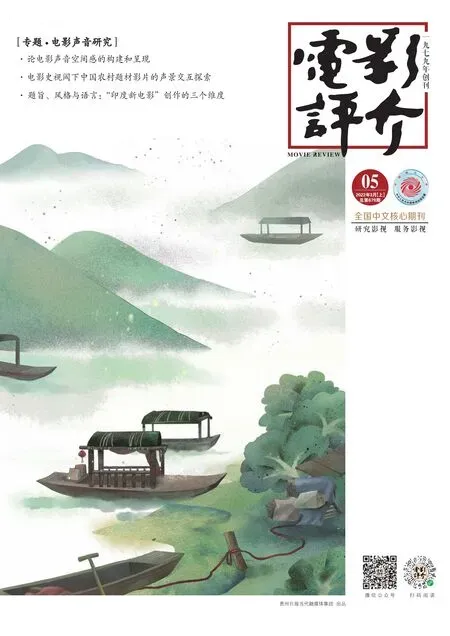民俗展演·家庭叙事·文化表达:当代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婚丧景观
邓天一
人从一种人生状态过渡到另一种人生状态,往往需要进行缓冲,由此便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仪式。“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是仪式的根本目标。法国民俗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虽然在概念辨析上不能与婚礼、葬礼等人生礼仪画等号,却是分析与理解人生礼仪的重要指导理论:既关注礼仪的过程与形式,又关注其背后的意义。婚丧嫁娶作为人生状态过渡的重要节点,具有纷繁复杂的礼仪形式,不同类型和题材的电影中都曾展示过婚礼、葬礼。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1993)以一场荒诞闹剧般的“假葬礼”讽刺“大操大办”的封建迷信思想;《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英国,1994)以轻喜剧的方式,在四次婚礼和一次葬礼的仪式中引发了对婚姻与爱情意义的思考;《摘金奇缘》(美国,2018)通过一场极尽喧闹奢华的婚礼完成了一次对亚洲富豪刻板想象的书写。
纵观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婚丧景观,在浪漫与荒诞之外,显露出更为丰富的意涵。一方面,是对民俗的还原与展演,无论是真实记录还是艺术化排演,婚礼和葬礼的诸多细节都在电影中得以细致呈现。另一方面,婚丧景观是家庭叙事的起点,婚礼和葬礼并非只代表着新人的结合和对逝者的告别,同时也会牵连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及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一切隐秘的回忆和情感冲突都在婚丧景观中铺陈开来。民俗展演和家庭叙事交织的背后,婚丧景观也传达出不同的生死观与人生观,这种文化的表达与碰撞使家庭题材电影超越家庭叙事走向社会叙事。
一、民俗展演:一种民族志式的婚丧景观呈现
婚丧嫁娶作为民俗,不同地域的礼仪各不相同,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者通常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某一地区与当地人长期生活,从而观察、记录与研究其风俗文化,同时也是研究者经过调研所形成的一种文本形式,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影像。近年来,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婚丧景观虽然大多是按照剧情设定的排演,却使不同地域的婚礼与葬礼中或复杂繁琐或奇异怪诞的仪式过程得以细致的影视化呈现,这是一种具有民族志风范的民俗展演。
《喜宴》(1993)中高伟同与葳葳在美国假结婚的喜宴;《别告诉她》(2019)中浩浩与日本女友在中国东北的婚礼,两部电影中举行婚礼的时间与地域大相径庭,但不约而同地充分展示了中国式婚礼的仪式环节。《喜宴》从寓意着早生贵子的“小朋友压床”,到婚礼上整蛊新郎新娘的游戏和敬酒,再到众人声势浩大地提红灯笼、摆麻将桌、为难新郎新娘的闹洞房环节,传统中式婚礼通过一场在异国他乡且实际是假结婚的婚礼得以呈现。《别告诉她》中的婚礼从始至终都洋溢着亢奋的情绪:从酒店迎宾激昂的口号、震耳的锣鼓,到喧闹的节目表演、宾客们的真情流露,再到人已经逐渐恍惚的游戏环节,到达顶峰的亢奋情绪在360度高速旋转镜头、消音和声画对立中被形象展现出来。中国式婚礼热闹、亢奋、百无禁忌,平日里难以启齿的真心话、隐而不发的情感和压抑着的天性仿佛都在婚礼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在我国,葬礼以汉族为代表,都是从古代周礼演变而来。我国古代有‘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原则。把处理死者看做重大的庄严事情。”因此,相较于婚礼,葬礼是具有更多细小而琐碎习俗的礼仪。葬礼不单指追悼会或告别仪式,同时还包含逝者从去世到下葬期间的诸多礼仪形式。穿孝服、烧纸钱这些基本礼仪形式在电影中已成为背景式的标准配置,可发挥的空间不多。而“哭丧”这一礼仪在葬礼中极其讲究:什么时间哭?怎么哭?都有了模板化的规定,民间也有职业的哭丧人,这使得“哭丧”这一礼仪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悲伤情绪,成为一种景观化表演。不同电影通过对“哭丧”进行多元化的艺术呈现直指其在葬礼中已成为景观的本质:《父后七日》(2010)中逝者儿女被师公(主持葬礼的道士)随时随地叫去哭丧,无论是在刷牙还是在吃饭,甚至出现口含牙膏泡沫和塞着满嘴米饭也要立刻哭丧的荒诞情节;《别告诉她》中将哭丧者声嘶力竭地哭喊以致狰狞的面部近景剪辑到墓园雕像木讷面部近景之后,两相对比令创作者的态度不言自明;《我的姐姐》(2021)中,姑妈前一秒还在痛哭弟弟的早逝,下一秒就能笑盈盈地招呼客人;《吉祥如意》(2020)中,出殡日的丧盆一摔,送葬者的哭声便齐刷刷地响起,老人刚去世时,亲人们却互相提醒着“现在不能哭”,因为根据民间习俗,为避免逝者灵魂留恋人间,人刚离世的时刻不允许哭泣。
除了“哭丧”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礼仪,诸多电影也展示出平时可能不为人所熟知的葬礼细节。《孤味》(2020)中被过继给他人的女儿阿眉来参加父亲葬礼,当母亲得知她已怀有身孕,立刻找来一根红丝线系在其腰间以防喜丧相冲。《吉祥如意》用影像真实记录了一场摄制组“意外遭遇”的葬礼,诸多民俗细节在电影中得以展现。导演父亲用电话通知亲友参加葬礼时,推算出殡时间可能是明天或后天,但随即确定是后天即农历二十九,此处看似随意的对话实则暗含着“七不埋、八不葬”的民俗,即每逢农历遇到带“七”和“八”的日子,不宜出殡、下葬。同时影片也完整且真实地记录了出殡时葬礼主事人引导逝者去往另一世界的说辞、指导提示送葬者送别逝者的各种仪式规范。这是以往电影中很少出现的珍贵影像,使这部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穿梭的独特电影拥有了更接近于民族志似的诉说。
除却具有通约性的婚丧礼仪形式外,电影也通过婚丧景观展示了民俗的地域独特性。《父后七日》中,葬礼上的罐头塔是中国台湾地区独有的丧葬风俗,究竟是受地理与交通因素影响,还是因为其在方言发音中的吉祥寓意?这种风俗形成的确切原因已无从考证,但在电影中其成为被资本裹挟的具有多重意义的景观——不单是对民俗的展示,也是议员为赢得选举而树立的“形象宣传牌”。《我的姐姐》中灵堂与麻将桌并置,用打麻将招待前来的吊唁者是川渝地区葬礼的独特景观,该地区将对麻将的热衷自然融入葬礼景观中。《别告诉她》中说着地道东北方言的司仪在一唱一和的主持词中尽显东北人豪迈、热情、好客的性格,也奠定了整场婚礼高昂的“东北基调”。除此之外,《喜丧》(2015)中充斥着低俗趣味的表演,不仅是偏远地区葬礼的标志,而且反映出民俗的变味、人性的麻木与参差。
不论是热闹的喧天锣鼓还是恶俗的游戏和闹洞房,不论是繁复夸张的法事还是有地域差异的葬礼细节,家庭题材电影借助影像和语言还原与呈现婚丧嫁娶中的礼仪。但这种复刻和艺术化加工,并未使婚丧礼仪成为被束缚在影像中的观赏性景观,反而使不同的婚丧嫁娶民俗通过电影实现记载与传播。
二、家庭叙事:拥有多重“聚合”功能的婚丧景观
婚丧景观在家庭题材电影中不仅对民俗进行了民族志式的复刻与展演,也与家庭叙事有机交织在一起,实现了其多重“聚合”的功能。葬礼最主要的目的是与逝者告别,而婚礼则预示着新家庭的组建或新人即将融入新家庭,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分隔礼仪在丧葬仪式中占主要成分;聚合礼仪在结婚仪式中占主要部分。”然而,在繁复的礼仪过程中,诸多仪式间的互动已难以将它们定性为某一种单一性质的礼仪。“亲身在场并共享相同的情感”使参与者成为临时的共同体,婚礼上欢声笑语的宴席是聚合礼仪,葬礼告别仪式上送葬者共享的悲伤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强调分隔的仪式一定的聚合意义。同时,在家庭题材电影中,婚礼和葬礼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其作为叙事原点连接起家庭的过去、现在、未来,人物间复杂的关系及情感羁绊在婚丧景观中逐渐显露。因此,在家庭题材电影中,无论婚礼还是葬礼,“聚合”不仅关涉外在的礼仪形式,也牵涉内在的情感体验,更是展开叙事的核心点。
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家庭通常不是“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这些家庭或人数众多、或具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或经历过不平凡的故事。婚礼与葬礼成为聚合人物、展开叙事的契机,那些平日里分隔各地甚至素未谋面的亲人皆因一场婚礼或葬礼共聚一处。《海街日记》(日本,2015)中父亲的葬礼促成了三姐妹与同父异母妹妹的相见乃至后来的共同生活;《花椒之味》(2019)中同父异母的三姐妹在父亲的葬礼上首次见面,并在随后磕绊碰撞的相处中建立起姐妹情谊;《别告诉她》中浩浩的婚礼将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聚集在一起,婚礼也成为他们回来见被诊断患有癌症的奶奶最后一面的借口;《孤味》中过继给他人的女儿、从未与母亲谋面的“情敌”均在父亲的葬礼上出现。婚礼和葬礼是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前台”,不仅展播着代表不同民俗的仪式,电影的主要人物也在此悉数登场。
相比于葬礼仪式,葬礼过后,家庭在方方面面需要处理和面对的变化更显繁杂。由于家庭成员变动,以往潜藏着的、新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伴随着葬礼被推至台前,迫使剩下的家庭成员必须勇于直面。《花椒之味》中父亲去世后火锅店是去是留?《吉祥如意》中“姥姥”去世后生活无法自理的“三舅”由谁赡养?《我的姐姐》中父母意外身亡,年幼的弟弟归谁抚养?“生者怎么做”成为由葬礼作为起点的家庭叙事的核心冲突。但大多数电影并未执着于尘埃落定式的对问题的完美解决,而是将葬礼作为切口,在人物磕磕绊绊的相处中梳理人物关系,在葬礼进行过程和缓慢流淌的家庭叙事中,着眼当下、回首往昔,力图弥合人物之间的情感裂隙。

电影《别告诉她》海报
电影通过婚丧景观表现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花椒之味》中大女儿如树按照传统风俗操办父亲葬礼,纸扎、金元宝样样不少,法事喧闹夸张,中途却在前来吊唁的友人口中得知父亲信佛,问及父亲店里的员工,原来只有作为女儿的她对此一无所知,父女之间疏离的关系通过葬礼的具体形式得以显现。《孤味》中在离家多年的父亲的葬礼上,陪伴他走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爱人按照父亲遗愿请来同修的友人为其诵经助念,母亲立刻叫来道士与鼓乐队同时进行法事。灵堂中低沉肃穆的助念声与喧闹的法事吹弹声此起彼伏,仿若同台竞技。两种不同形式礼仪的较量实则是母亲对这位“情敌”发起的挑战,自身的不甘和对小女儿偏向父亲的不满也同时裹挟在两种礼仪的较量之中。
婚丧景观中的种种细节是通向回忆的入口,在当下葬礼与以往回忆间的辗转中,逝者的形象逐渐立体,过往的故事被逐渐补全,一个家庭的前世今生乃至生活的细枝末节被渐渐激活。《父后七日》中父亲的“遗像风波”引发了女儿阿梅一连串与父亲有关的回忆。父亲仅存的照片是他在自己的夜市碟片摊位前唱卡拉OK时拍摄的,这张珍贵的照片令阿梅想起在夜市与父亲一起唱歌的快乐回忆。然而,遗像一般要求简洁、庄重,这样的照片显然不符合葬礼要求,因此照片需要重新处理订做。阿梅取回重新制作的遗像时,骑车载着父亲大幅遗像的动作又令她想起父亲骑车载着她的时光:父亲的玩笑和与父亲赌气的场景历历在目,以往没有好好珍惜与父亲的相处时刻,如今都变成绝版回忆。葬礼期间被哭丧所麻木的情感在一个个与父亲相关的微小礼仪细节中被重新点燃,阿梅开始认真思考“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孤味》通过诸多与父亲相关的遗物——明星咖啡馆的软糖、年轻时写给母亲的情书等慢慢勾勒出父亲的形象,这场葬礼本身就是一次关于家庭历史的回溯,在葬礼与不同人口述回忆的切换中,一位以“孤味”闻名的餐厅老板的百味人生由此铺展开来。从执意不在家中举办葬礼,到最后签下多年前的离婚协议书,与自己和解。
婚礼和葬礼在时间和地域的维度上,将众多人物聚集起来,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电影中,这种聚合都使参与者共享着相似的情感体验。在家庭题材电影中,婚丧景观的“聚合”功能超越了礼仪本身,其作为叙事的原点联结着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家庭历史,在礼仪的呈现中完成家庭叙事的书写。
三、文化表达:婚丧景观作为生死观与人生观的映射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民族志的目的不止于对民俗的复述与展示,家庭叙事也不囿于家长里短之事。在民俗展演与家庭叙事的接合处,婚丧景观映射出不同的生死观与人生观,其中包含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有不同个体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化表达。
“落叶归根”这一观念在众多地区都具有普适性。因此,在诸多家庭题材电影中,“回家”成为大部分逝者的心愿,对这一观念的重视也在影片的婚丧礼仪中得以充分体现。《吉祥如意》中姥姥在病危后被接回家中度过最后的日子;《父后七日》中医院的工作人员用呼吸机维持逝者最后一点生命体征直到将其送回家中,并将到家后撤掉呼吸机的时间记为逝世时间;《孤味》中已在台北市生活十几年的父亲回到故乡台南市的医院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的遗愿是在家中举办葬礼。“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对“回家”的眷恋与执念是人们“故土难离”观念的直观反映。
对亡者世界的想象是不同文化中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寻梦环游记》(美国,2017)、韩国“与神同行”系列电影均以奇幻、温情的风格完成对亡者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基于一种相信逝者灵魂不灭的观念,其本质是生者对逝者浓重的思念与缅怀。家庭题材电影中的婚丧景观也在诸多细节中透露出对亡者世界的想象,传达对逝者的思念与祝愿。《父后七日》中师公让儿女拿来父亲生前喜欢的物品放在遗体旁边;《花椒之味》中为父亲烧的纸扎中有“尊贵洋酒礼盒”“行驶证”“保险卡”;《孤味》中母亲在“头七”(人去世后的第七日)这天为去世的父亲准备了饭菜,晚归的大女儿看到桌上的餐食,轻轻说了声“晚安”。“丧礼期间,守丧之人与亡者形成特别群体,处于生者世界与亡者世界之间。”葬礼为生者与亡者打造了特殊的缓冲地带,生者在这个地带为亡者“送去”世俗意义上的“好东西”,这是以现实世界为原型对亡者世界进行的想象。《别告诉她》中奶奶带着一家人在爷爷墓前祭拜,“上供人吃”的民俗是生者清醒知道逝者已逝的事实;但在叔叔给爷爷点烟的举动后,奶奶与叔叔争论爷爷是否戒烟成功的问题令人不禁产生爷爷这么多年似乎从未离开过家人的幻觉;最后奶奶祈求爷爷庇佑家人的愿望又将观者从这一幻觉中拉回。因此,丧礼中对亡者世界的想象,一方面蕴含对逝者的思念与祝愿;另一方面引申出对“生者如何活”这一问题的思考。
“生者如何活”的问题含义广博且对其回答具有较强的情境限定性和个体差异性。《孤味》中被家人公认为性格最像父亲的大姐陈宛青,在父亲葬礼期间遭遇了“如何活”问题的考验。她似乎总是有着与众人背道而驰的人生观与生死观:经历过一次抗癌之旅,当家人、朋友甚至追求者都劝她坚守一段稳定的婚姻,而她将自己活成了“自由的风筝”;当病魔再次向她发出诘难,家人、朋友劝她抓住生的希望,她发出“为了延续5年生命,还要吃那么多苦值得吗”的疑问。海边那句“你怕死吗?”不是在问同行的阿关,而是在问她自己,这句话也并非她惧怕死亡,而是一种对生之艰辛的恐惧。她向小妹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境并设想了自己临终时的场景,父亲的葬礼和复发的病情令她陷入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不断拷问。《花椒之味》中葬礼后,如树与曾经差点步入婚姻的男友之间的争论令她陷入回忆:刚刚购置了结婚用品的二人本来高高兴兴,但男友对“吃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令如树重新审视了二人之间的关系。男友对任何事情都表示“可以啊”的态度令她怀疑对方不是“自己想要结婚”,只是“可以陪她结婚”。“想要”与“可以”之间的差别,反映出二人人生观的巨大差异:面对人生是选择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参与?
个体选择的背后往往是不同文化与逻辑的碰撞。“谎言”是《喜宴》与《别告诉她》两部电影中婚礼的共同《喜宴》中高伟同不敢将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告诉父母,选择与想要取得美国“绿卡”的画家葳葳假结婚来应付他们;《别告诉她》中家人不愿将奶奶身患绝症的事实告诉她,却假借浩浩婚礼的名义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家人们回家见她最后一面。虽然两部电影所聚焦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反映了同一种东方式的人生观:生命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这种人生观认为人自出生起便无法与家庭和社会分隔开。因此,伟同面对年事已高的父母的期待与追问,无法向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家人为了照顾奶奶的情绪,不愿告知她真实的病情。“善意的谎言”背后蕴含的是主观化的“为他好”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损害了个体生命的独立与尊严,也损害了个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喜宴》通过影片结尾处对“父亲听得懂英文”这一细节的刻画强调了这种逻辑,父子双方都秉持并坚守着为对方着想的原则而不肯吐露真实心声。《别告诉她》中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碧莉始终不解家人向奶奶隐瞒病情的行为,最终却也妥协并协助他们修改了奶奶的病例;新郎浩浩则因为这场婚礼的双重意义,终于在婚礼尾声顶不住压力失声痛哭。热闹的婚礼景观与其承载的“生命是集体的”人生观和“为他好”的逻辑的并置,传达出东方文化的静默与隐忍,并伴随着淡淡的酸楚与窝心。
婚丧景观在与家庭叙事的交织中映射出不同的生死观和人生观,虽然无法穷尽每一种婚丧景观在不同背景下的社会文化意义,但可以确定的是,婚丧礼仪在家庭题材电影中经由影像化的呈现已经从景观走向文化,从家庭叙事延伸至社会叙事。
结语
婚礼与葬礼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题材电影中最具视觉吸引力的景观。不同于单纯唤起视觉刺激的影像奇观,婚丧景观在家庭题材电影中实现的是近似于民族志式的艺术化呈现,同时又与家庭叙事有机相连,不仅人物间的关系与情感纠葛通过婚丧景观渐次显现,不同的人生观与生死观也藉由婚丧景观得以映射。对礼仪过程与形式的记录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探讨在电影中交汇,这是对民俗学侧重记载过程和哲学聚焦意义探寻的双重超越,婚丧景观在家庭题材电影中实现了自身的多义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