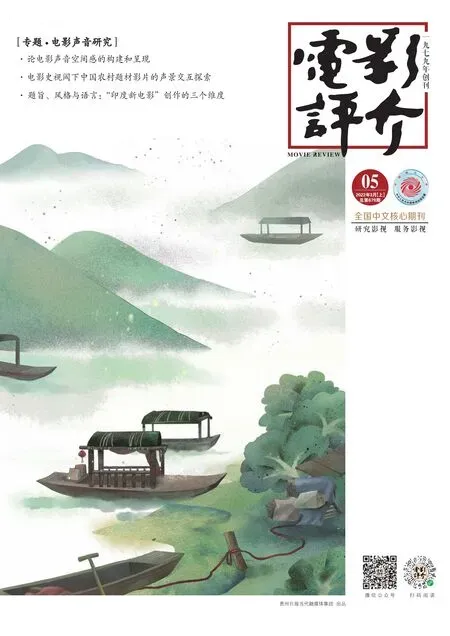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生态意识的影像表达
——2000年以来生态灾难电影叙事策略探析
高歌
生态灾难电影是指以极端自然生态现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灾难电影。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屡屡出现,如何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成为人类首要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领域就已经开始反思生态问题,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在其撰写的《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一书中就已经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应思考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随后在文学领域内掀起生态学批评的浪潮。
在电影领域内,艺术电影与纪录片最早开始关注人类现代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1964年由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片《红色沙漠》,导演重新赋予生态环境以扭曲的颜色,表达现代人精神与内心世界的不安和对现代工业发展的质疑。之后许多商业灾难电影也将故事建立在自然生态灾害之上,在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力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这一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1975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大白鲨》,不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人类与生态关系的思考,但此时电影领域内尚未形成系统的生态电影批评体系与创作意识。直到21世纪后,由美国学者斯科特·麦克唐纳于2004年首次提出的“生态电影”这一概念,为大众提供了电影的全新视角。2004年由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生态灾难片《后天》,以全球变暖为故事背景向观众展现了温室效应带来的巨大灾难。影片拍摄于美国毁约京都协定书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生态危机这一议题再次推向公众面前,引发强烈的社会思考与讨论。
本文意在以2000年以来美、日、韩等国家的生态灾难电影为研究对象,结合电影创作的时代语境与社会文化氛围,梳理影片中对于生态意识的影像表达,并分析影片的叙事策略。
一、情感诉求与生态认知
在媒介化社会中,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以视听结合的手法最直接地传递信息,影像表达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受众文化背景的差异,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因此,电影成为传递思想、承载教化功能的重要工具。然而,如何有效进行生态意识传播,使受众接受生态理念并付诸行动,则需要影像在传播过程中辅以观众情感的加持。
借助现代科技技术,影像可以较为容易地引发观众对自然灾害的恐惧情感。银幕上呼啸而来的龙卷风、势不可挡的巨浪给观众造成强烈视觉冲击力。此外,由于影片中所展现的各种气候变迁,其背后涉及许多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普通观众难以通过表象了解每一种气候变化背后隐含的生态科学原理。因而,电影媒介在气候传播过程中扮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气候变化知识的解释者。影片中大多借助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角色,运用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串联各种生态现象,从而洞悉其背后生态环境变迁现象,使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能够深入人心,使普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不再仅限于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生态灾难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观众看到他们过去没有见过的对象或时间,使之变得十分生动,成为群众经验的一部分”,借此起到生态科普的作用。
情感诉求还需要与文化环境相结合,才能唤起作为独立精神个体的观众心中对环境、自然与生态的情感,促使他们自愿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环境保护和参与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创作者赋予影片的社会价值。因此,在由远古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对天灾的恐惧而形成的原初公众心理下所产生的神话寓言,为末世的形成与降临提供了合理语境。
荣格认为“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原始意象(原型)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结。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积淀,并因而是他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在诸多灾难片中会出现公众较为熟知的寓言情节,如诺亚方舟、潘多拉的魔盒等,这些情节与典故为灾难的降临提供了理由和解决方式。同时,有效地将想象中的世界末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经久流传的神话寓言已成为公众既有认知中的一部分,因此以神话语言作为背景铺垫,使原初公众心理产生作用,可以唤起观众对于现实生态问题的情感共鸣。在众多神话寓言中,被频繁使用的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和洪水。如在摩西出埃及记中,就有摩西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途经红海的情节,这里的“水”指代的就是劫后重生。在神话寓言中,洪水是来自上天的惩戒,而在灾难片的现实语境中,洪水则来自生态环境的变迁。如《2012》(2009)、《未来水世界》(1995)、《后天》(2004)等影片中的洪水来自于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温室效应。此时,神话寓言中引发神明怒火的人类之罪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向,就是超出自然调节负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侵占,使得公众对自身行为所带来的生态负面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情感上能够引发公众自省。
然而,无论是视觉的震撼、宗教信仰的加持,还是生态科知识的科普,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短暂的,但生态环境的变迁却是持续的。如何有效延长电影引发的生态意识,则需要把控影片对于观众情绪的影响力度,为观众提供自省与思考的空间。用影像的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观者的习惯认知中,引发观众对影像所指向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生态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从而在生态保护的“持久战”中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英雄身份的转变与阶层的跨越
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灾难片的身影。该时期的灾难片多以纪实题材为主,如《火灾》(1902)、《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1903)、《火烧旧金山》(1936)等。随着电影制作技术与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灾难片具有了更加丰富的面貌,以物种变异、核能源危机、温室效应等为题材的灾难片层出不穷,同时也形成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如在影片《世界末日》(1998)中,一颗巨大的陨石要与地球相撞,而此时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要钻洞贯穿至陨石的核心,放入核弹炸毁陨石。因此,钻油井工人哈里被委以重任,一夕之间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影片《我是传奇》(2007)更是将英雄主义叙事做到极致,影片讲述了在一场毁灭性的病毒暴发后,绝大多数人类被感染后变成怪物,由于主人公罗伯特的血液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生的免疫力,因此成为纽约市唯一的幸存者。他用自己的血液研制抗体血清,试图以一己之力寻找逆转病毒的方法。尽管这些影片具有不同的故事背景,但都有相同的英雄叙事内核。对于这些影片,与其说是体现生态意识,不如说是以飓风、地震、海啸等极具冲击力的自然奇观追求商业票房,生态危机也成为抒发个人英雄主义的背景板。因此,即使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生态变迁为故事背景的灾难电影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但仍未使生态环境这一议题引起更多社会反响。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电影”这一概念进入电影创作后,电影的社会属性发生转变,英雄叙事也产生了新模式。
首先是任务模式的转变。从孤胆英雄逐渐变成团队作战,拯救世界的重担被分散到每一个小队成员的肩上。在影片《后天》中,以气候学家杰克一家人的三条叙事线索推动了故事发展。影片中,父亲杰克穿越冰天雪地前往纽约营救儿子山姆;母亲露西作为医生坚持守在无法移动的病人身边,等待救援;儿子山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守护了一起滞留在图书馆的同伴们,最终成功获救。影片以一个家庭为主体,当灾难来临时家庭成员虽身处各地,但亲情却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小小的家庭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缩影。
其次是叙事目的的转变。英雄主义是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价值观,是将某一时期社会所追寻的目标与精神凝聚在一个典型人物身上,从而号召公众模仿这一人物。在以生态命题为叙事背景的英雄主义叙事中,主人公的主要目的就是征服自然,这背后是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态意识的不断提升,英雄主义逐渐由征服自然转向敬畏自然。影片《全球风暴》(2017)讲述未来人类为了能够有效管控灾难天气,研发了名为“荷兰男孩”的卫星系统,然而卫星的故障却使更为严重的气象灾害席卷全球。同样,影片《雪国列车》(2013)的故事背景是人类为解决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研发了人工冷却剂,却遭到反噬导致全球性的极寒气候。两部影片都是以人类试图凭借自身力量改变自然、征服自然却遭到反噬为背景而展开,使观者再一次意识到人类力量的局限性,只有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并与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未来继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种叙事目的的转变是对长期以来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
最后是英雄结局的转变。从古希腊时期起,英雄就是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伟人,始终是独特、伟大并让人仰视的存在。影片《完美风暴》(2000)没有给主人公打造传统英雄色彩的结局,捕鱼船的船长比利近期时运不济总是收获甚微,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带着同样被生活所困的船员前往更加遥远的海域冒险,不想却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船长比利带领着船员竭尽全力与风暴搏斗,但无济于事,在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过于渺小,最终全员葬身大海。船员鲍比没能回到岸上与女友开启盼望已久的新生活,同伴戴尔也没有再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影片最后没有过度渲染船员们离去的悲伤氛围,他们成为小镇纪念馆墙壁上的一个个名字,亲朋好友也逐渐从悲痛中走出,再一次出海继续生活。影片中的主人公不是传统意义上灾难片中的英雄角色,他们会被经济收入所困扰,也会在遮天蔽日的巨浪面前感到恐惧。然而,正是这种角色的转变,使观众更加为之动容,也使得影片更加具有人文色彩。
21世纪以来,部分生态灾难片中充满主角光环的英雄身份逐渐转变为平凡的普通人角色,可能是医生、警察或者科学家,带领着一群人战胜重重困难,最终使人类得以幸存。在凭借人类力量难以对抗的自然灾难面前,被神化的个人英雄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忙于逃命、寻求幸存机会的普通人。在影片中,一小部分人类在英雄的带领下得以幸存,但没有人是这场“英雄斗争”中的胜利者。灾难过后,幸存下来的人类重新回到与自然平等相处的模式。英雄角色的转变背后是社会目标的变化,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公众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逐渐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难以与自然相抗衡的局限。
如果说英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缩影,是人类与外界事物权益的区别划分,那么阶层则是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另一种中心主义。诸多影片在对未来的幻想中,总是将阶层作为重要的表现命题。早在1927年的科幻片《大都会》中,就有对阶层的展现。影片中导演用垂直的画面构图形象直接地展现阶层划分,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资本家们高居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内,而靠体力劳动换取生存机会的劳动工人们群居于黑暗狭小的地下城内。这种对于阶层结构的垂直化展现影响了后世的科幻作品,如影片《雪国列车》(2013)、《极乐空间》(2013)、《逆世界》(2012)等。而在生态灾难片中,经常以打破阶层划分来推动叙事。阶层这个元素在生态灾难片中的展现,以灾难发生为节点,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灾难发生过程中,阶层特权不复存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存在。以影片《2012》为例,影片中具有经济优势的富豪阶层购买了诺亚方舟的船票,获得了生存的特权,但在最后关头仍未成功登船,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双胞胎儿子和女友的宠物犬;统治阶层具有政治特权的美国总统,自愿放弃登船的机会选择与多数普通民众共同面对末日的降临。二是在灾难发生过后,人类重新组织文明社会,此时的阶层也被重组。在影片《雪国列车》中,登上列车的幸存者们被划分到不同的车厢,由此被分成不同阶层,前列车厢的人们醉生梦死,尾端车厢的人们艰难度日。同样在影片《极乐空间》中,由于地球的人口过剩,环境难以被修复,资源也即将耗尽。少数特权阶层抛弃地球,入住了漂浮在宇宙中的“极乐空间”继续享受生活,徒留地球上的人们苟且偷生。这两部影片都是以主人公试图打破阶层划分为叙事动机,但是往往到最后才发现即使打破现存的阶层划分,也无法到达想象中的乌托邦。此时,回到人类社会起源,重新找寻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唯一的出路。在生态危机面前,英雄与阶层,个人与集体都被重新定义。长久以来,人类想象中的命运共同体不过是狭义的由一群利益共同受益者所组成的临时联盟,而在其中的人们却因眼前的利益而毫无察觉,直到巨大的灾难降临,人们才意识到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就像影片《后天》的结尾,劫后余生的美国新任总统对国民发言中所讲的“这为我们证明了世界的改变,不光是美国人,地球上所有的人现在都成为了被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客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接纳和收容了我们。”生态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命运的共通性,只有善待共同的家园,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人类才能拥抱美好未来。
三、人文景观的危机与自然的反击
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对改造自然和攻克疾病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类愈发坚信自己是生物圈中心,是优于其他生物的存在。人们坚定地认为自然资源需要为人类发展而服务,是人类力量的点缀和附庸。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为人类利用其他生物的行为构建了合理语境,使人类更加心安理得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然而,这样的行为却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后果,人类社会开始遭到自然生态的反噬。在生态灾难片中,创作者在影像中以对人文景观的破坏与具象化自然的反击来引发观众对于人与生态关系的思考。

电影《全球风暴》海报
视觉特效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提升,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冲击力,成为灾难片最为卖座的元素。在电影中,总是以破坏象征着人类文明的标志性人文景观来展现自然与人类力量的悬殊。如在影片《后天》中地表骤降的温度,冻住了飘扬的美国星条旗,滔天的洪水涌入纽约港瞬间冲毁了曼哈顿的街道,冰封的自由女神像周围尽是被巨浪拦腰折断的观光游轮。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主人公山姆一行人被困在纽约公立图书馆,该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共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馆藏几乎包括美国建国以来全部的珍贵历史资料。影片中为了应对寒冷的天气,被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人们开始“烧书取暖”,在寻找烧火原料的过程中,图书管理员与山姆的同学却对“能否烧尼采的书”进行争论,这一情节对人类现代文明颇具讽刺意味。
与《后天》中被冰封的世界不同,影片《极乐空间》的故事背景是在21世纪末期由于人口膨胀,病毒肆意,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地球上的富人们纷纷逃离了这个星球搬到了名为“极乐空间”的空间站。被人类文明抛弃的地球,由于过度的开发和攫取,变成百孔千疮的废墟,充满贫困、饥荒和疾病。从太空中俯瞰地球表面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生态系统被完全破坏,枯萎的农田被垃圾堆满,简易的房屋簇拥在一起,整个地球就像巨大的废弃垃圾场,生机全无。与地球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空间站中开阔的草坪、成荫的绿植,空间站中的人们依仗着发达的科技,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超尖端的医疗技术使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生老病死。在影片中,巨大的环形空间站、高度智能的机器人与能改造人类基因的医疗床等,展现出一幅遥远且梦幻的人类文明图景。然而在这迷人的景观背后,却只剩下废墟的地球,科技带来的硕果使人们只专注于仰望星空,却忘记了脚下的满目疮痍。
尽管两部影片中所呈现的极端自然景观、超前的人文景观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甚远,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逐渐融化,海啸、飓风、干旱、暴雨、台风、洪水等生态灾难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部分岛屿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像在影片《未来水世界》中所呈现的那样,被大海淹没。气候灾难的加剧将造成更多物种灭绝、淡水资源减少、农作物减产、病毒肆意、海洋生物系统失衡等现象。因此影片《后天》《极乐空间》与《未来水世界》中的虚构性镜头并非危言耸听,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21世纪以来,生态灾难电影的叙事中,除了在故事背景的建立与角色的设立方面发生转变外,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创作者开始赋予自然具象的反击行为,同时也加入来自第三者的审判。在影片《灭顶之灾》(2008)中,由于人类长期滥用自然资源,激起自然对人类的反击。在美国境内突然刮起一阵奇特的风,被风吹到的人类会不受控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风由地球上的植物产生,意在以这种方式调节地球负荷,重新恢复生态秩序的平衡。影片以这种带有恐怖色彩的叙事方式,具象了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击。
此外,影片《地球停转之日》(2008)虽然是讲述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但在该片中的外星人来地球的原因不单单是为了侵占地球,而是作为审判者依据人类是否能解决地球上已有的许多如温室效应的生态环境问题,来判定是否要毁灭人类。最终外星人被人类的亲情所感动,终止了对人类的清除计划,遭遇浩劫的地球迎来新的日出,在久违的鸟鸣声中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与生态的关系。
结语
生态灾难电影用炫目的视听技术与宏大的叙事规模,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个具有警示意味的生态寓言。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重新整理分析这些影片可以发现,其在情感烘托、角色设立与视觉因素等叙事策略上的改变。以这样不同以往的叙事策略更好地发挥了影片的社会教化功能,使观者在享受视听娱乐的同时,意识到现今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将生态思想融入电影作品中,唤醒观众的生态意识,是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所要具备的社会影响功能。生态灾难电影需要思考在将生态意识融入电影创作的同时,如何转变叙事策略以更好地发挥电影的文化宣教功能,使生态意识的能量传输给更多观者,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探索着构建人类与生态之间更和谐的联系,这是目前生态灾难片正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