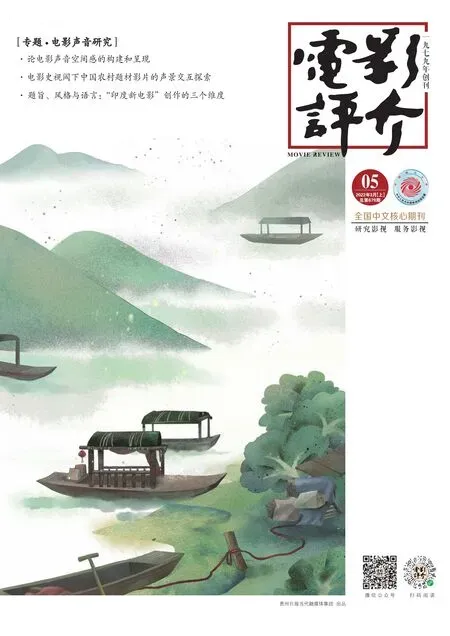电影史视阈下中国农村题材影片的声景交互探索
赵娴 申林
一、概述
“声音景观”(Soundscape,以下简称声景),是由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R.Murray Schafer)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声景:我们的声音环境和世界的调谐》()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声音景观是任何可研究的声音领域(acoustic field)。我们可以说一部乐曲是一个声景,一档广播节目是一个声景,一个声音环境(acoustic environment)是一个声景。我们能够将一声音环境独立出来作为一探究的领域,正如我们能够探究特定地景(landscape)的特质一样。”这一概念的诞生为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生态学等在内的各交叉学科提供了全新的“声音领域”。同时声景的理论意义和内涵也随之受到广泛关注,并由后来的学者不断加以丰富与补充。
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将外部的声音环境与其内在经验、内在感受同时纳入声景概念中,给出较为综合的界定:“正如视觉景观,声音景观应该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同时又是感知该环境的方式,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建构。在声音景观的物理层面,不仅包括声音本身和穿透空气的声波能量,还有那些使得声音得以产生或被消除的物质。在声音景观的文化层面,包括科学的和审美的听觉方式、聆听者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以及支配了什么样的人所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的社会环境。”
为此,声景不仅仅意指外在于人的声音环境,更加强调经由“听觉方式”或“感官文化”的作用,在主体界限之内所形成的对这一声音环境的印象,甚至是内心中“听到”或“构想”的各种声音。因此,声音环境、声音景观与听觉方式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动、互生和同构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声景理论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同时关于“电影声景”的研究也初露端倪。但是中国电影学界对于“电影声景”的系统性研究起步较晚。一方面,由于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学的梳理与建构尚未完善;另一方面,随着虚拟现实技术与电影环绕声的不断进步,声景研究大部分尚处于技术探索、案例分析和理论建构层面。而中国农村电影在电影类型中独树一帜,既有中国乡村生活的人文关照,又有中国农民的本色写实,更有中国人对本土情怀的多维表达。此时,声景便成为中国农村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演变“见证者”,其不仅勾勒出农村电影本身特有的人文底色与乡土底蕴,同时又以一种发人深省的听觉方式默默展现着中国农村大地上所映射的时代烙印与文化嬗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创作并不一味地满足于再现,而是尝试运用声景交互性表达直接呈现时代变革与人文环境变迁。因此,梳理总结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表达方式,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农村电影提供新思路,也能为完善中国电影声景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音环境、声音景观、本土音乐、听觉方式等角度入手,探讨其不断被建构并时刻经历着的变革,试图分析与研究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声景交互性表达。
二、中国农村电影史简述
农村电影是相对于都市电影类型而言较为广泛的电影范畴,其以现代农村为叙事背景,以农村民众为表现对象;有反映农村生存现状的现实题材,也有展现乡土人情与文化的情感故事。中国农村电影在电影中占据着独特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电影虽然只占中国电影的10%左右,但纵观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不难发现,早期电影创作多与农村背景、农村题材有关。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以农村为题材进行电影创作一直都是中国电影的传统。
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电影年”。中国农村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编剧:夏衍,导演:程步高)是第一部深刻反映农村现实生活、探讨农村贫富差距的电影。这时的作品,如《春蚕》《盐潮》《黄金谷》《到西北去》《路柳墙花》《小玩意》等都成为管窥中国30年代农村样貌的珍贵影像资料。
“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中国农村电影,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如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代表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情感为叙事中心,刻画出朝气蓬勃的农村面貌与真诚上进的农村青年形象;6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的代表作《李双双》,以农村家庭喜剧式的表现方式,探讨夫妻人伦、社会道德关系,并展现出乡野情趣与农村生活。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使农村的生活方式、文化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中国农村电影围绕着积极性、时代性、变革性、复杂性等多个议题层面进行探讨。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农村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也几乎是中国电影创作成熟期的缩影,该时期电影的题材广度、表现深度和艺术高度都呈现出一派兴旺,如《喜盈门》《牧马人》《红高粱》《黄土地》《乡音》《野山》《人生》《边城》《老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所体现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与乡村世界、乡土情感、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乡土文化的厚重与底蕴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电影艺术表达的核心。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农村电影创作在激情与理想、反思与怀恋的交错中进行。农村既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又是新生与希望的前沿;既是愚昧保守的闭锁之地,又是温情脉脉的伦理乐园。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1989至1991年连续3年的农村电影创作只有7、8部;而到了1997年,中国农村电影的产出甚至下滑到只有4、5部。自1999年以后,在电视这一新媒体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电影在院线的排片量与上座率都陷入每况愈下的困境。可见,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发展,农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源点逐渐失去被表述的中心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中国电影人将挖掘乡村振兴题材视为己任,积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新农村的变迁。多部电影作品试图通过平民化的视角和喜剧风格,构建新的表达模式。如2020年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引发观影热潮,使“新农村”电影受到空前关注。
此外,中国乡村的独特生态与壮阔美景也逐渐成为农村电影赞颂感怀的主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借助中国农村电影向世界传达。而乡村环境的改善工作、“新农村风貌”的现代化发展都将成为新一代村民共同的课题。为此,中国农村电影所聚焦的新时代乡村建设、新农民形象重塑、新农村生态文明等角度正在指向更加宏大、广阔的创作空间。
不可否认,中国农村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影片中的声景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不同的声音意识和思维变化,从声景忽略、到声景再现、再到声景交互,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三、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再现
声景赋予电影声音以空间的维度和听觉的广度。声音的空间维度将听觉活动作为一种涉身经验、感官与声音环境的互动过程纳入观众的思考中。导演和作曲家不再只是考虑在某个具体情境或电影场景中,声音所携载的内容或意义如何被观众接受的问题,而是将声音作为人文学科领域所关切的一种经验的研究对象,为观众在银屏上构建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
“声音地景(auditory landscape)”在中国农村电影声景中显得尤为独特,这里的声景与人的关系既是身体的,也是文化的。中国农村“地方声景”的特质,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写照;另一方面对村民(特定群体)而言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听觉文化。“地方声景”既是村民身份认同的建构方式,也是村民身处其间并与情感相联结的居所。因此,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性,包含着文化主题和人文意境。
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音景观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农村“地方声景”的再现和艺术化的处理。从潺潺溪水到回荡在山谷间的鸟鸣,从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活动到田园般的农家生活,从村民多样的乡音到形象生动的方言故事,从本土的传统民俗音乐到地方戏曲小调,从民族歌舞到婚丧嫁娶的仪式音乐……这些贯穿在电影中的声景,使观众沉浸于声境、流连于乡野、遐想于山间。这是中国农村的基准声(keynote sounds),即人们平日听惯的日常声音,如气候、植物的声音,市井街道的声音,自养的猪、羊、马、牛、猫、狗、鱼、虫的声音与标志声(sound marks)。标志声是指一个共同体特有的甚至是独有的声音,如特定的动物和植物群落都有独特的标志声,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电影中环境声与音乐创作的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村中的礼俗仪式音乐是在中国农村电影中反复被提及和再现的“标志声”。在当今众多礼俗仪式音乐的研究中发现,其声景样本的独特性,以及其表达的民俗/社会历史意义的时空二维属性(时域性和空间性),都具有可辨识性。这种可辨识性,也可称为是“标志声”的可辨识性。声景样本可辨识性的准确性取决于“时域性”(Time Identifiability)和“空间性”(Spatial Identifiability)中所包含的声音原始发生的历史年代、时间特点、场所、特定情景、仪式特征与地理环境等信息是否足够表达“标志声”的“原生性”(Nativity)。
乡村丧葬、婚嫁仪式声景的形成与葬仪婚仪发生的时间、场地、演奏行为、人们在仪式空间中的身体动作与心理情绪息息相关。而中国特有的乡村葬仪婚仪,都是通过仪式音乐营造共同体验的瞬间,以激发或重塑个体的集体感,从而促成信仰的增强、情感的升华以及集体意愿的一致,将个体融入社会中并借此方法强化社会秩序。因此,在电影中所呈现的是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传统礼仪,也是中国农村祖祖辈辈信奉的生存法则和社会秩序。
《黄土地》《边城》《红高粱》《老井》《那人、那山、那狗》《百鸟朝凤》等多部中国农村电影的代表作,观众都能从中窥见在农村共生环境中所产生的“强调个体或社会感知和理解的声音环境”。中国农村电影这一特殊类型,正是靠着声景这一人文地理景观的重要构成,以塑造电影中的地域文化个性,培育观众对地方身份的认知、确立对村民的地方感知,而这恰恰也是电影视觉景观所不具备的优势。
然而,声景再现已经无法全面展现正处于变革期的中国农村面貌,更无法客观描绘中国村民的众生相。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人民美学观念内涵的丰富化、角度的多维化,新中国时期的农村电影很多都重在表现“人性压抑后的情感释放”或“个人声音的自由表达”,以体现人权觉醒和凸显个人价值的多维叙事主题。因此,立足于文化交互层面的中国农村电影声景,需要尝试破坏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与人文景观,使观众直面矛盾与冲突,感受来自文化侵入的焦虑甚至无力。
四、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交互
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劳动人民仍保留着本土地域特有的生活传统,很多地区依旧会将音乐视为人际交往的手段之一,其中少数民族音乐更是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层次和表演形式。然而,随着时代变革与文化交往,外来文化的融入也不可避免地稀释着民族文化特性。因此,中国农村中的声景并非固定不变的静态声景样式,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和衍生的动态声景。我们需要根据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流动性,分析声景表现的具体样态与具体意义。声景在承载民族记忆、声音遗产的同时,也会反映出一个地域人民的个体感受与性格特征。尤其当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时,潜在的文化主体便会争夺、改造甚至是生产新的声景。
中国农村电影的声景交互性表达,正是聚焦在交互文化中的多元之争,运用多种声音处理手段与叙事方法,将影片中的人与人、人与时代、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敞开的解构过程中,带给观众启迪,引发观众思考。本文将从互动、碰撞、争议和对话四个角度,以四部新中国农村电影代表作《老井》《那山、那人、那狗》《百鸟朝凤》和《三峡好人》为例,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电影的声景交互性表达。
(一)互动
1987年的电影《老井》(导演:吴天明,作曲:许友夫),讲述了一个关于老井村世世代代为水而生、为井而死的沉重故事。影片中人与人的纠葛、人与时代的矛盾,通过传统地方声景、人为制造声景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间的互动,揭示了残酷且严峻的事实。
影片声景中多次出现当地戏班上演的戏曲小调、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信天游以及葬仪婚仪音乐,展现了荒芜的黄土高原与上千年来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尤为特别的是,影片片头持续且富有节奏的打井金属声,仿佛在暗示着旧时代农民祖祖辈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面对的难题与沉重使命,这是历史的延续、是落后的显现、是对愚昧的无奈。伴随着悲凉的独奏旋律,画面逐渐将井口强化为影片的视觉焦点,并随着镜头缓缓从井底上升,从黑暗引向光明,隐喻着世代拼搏的精神信念与终将迎来的希望。
电影中有一处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声景互动”。在盲女所唱的民间小曲《摘豆荚》与青年们起哄的笑声中,毫无征兆地播放了一首动感的迪斯科音乐;在青年们的嬉笑打闹与狂欢般的舞蹈中,时代变革下农村青年的欲望与挣扎呼之欲出,他们已然不再如父辈那般封闭与盲目,他们渴望爱情与自由,但身处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落后的“十字路口”,只有流行音乐才能帮助他们暂时麻痹神经、忘却苦难。
可见,此时的“声景交互”带着隐晦的现实主义试探,以期观众能体味到在社会历史行程中人物命运的沉浮和现实生活的变迁。
(二)碰撞
1999年的《那人、那山、那狗》(导演:霍建起,作曲:王晓峰),电影看似阐述一对父子翻山越岭、饱受劳苦的送信之旅,实则是关于两代人之间传承的故事。影片的声景以悠扬的竹笛声为主线,辅以山林间灵动的鸟鸣、虫鸣声,伴随着男主人公时有时无的独白、湖南侗族的山歌小调,以清新朴实、散文化的声音艺术风格,勾勒出一幅湘西农村青山绵延的田园画。
整部影片聚焦于父子的送信之旅,然而镜头中父子间的对话寥寥数语,尽显生分。影片中,代表父子赶山路时的声景颇有不同,观众可从中窥见父子间无形的隔阂与隐隐的矛盾。父亲出门时特意绑在自制登山杖上的牛铃,持续发出清脆但又有些沉闷的声响,随着父亲已不太轻盈的脚步声,形成独特的节奏,这一贯穿于全片中的特殊声音设计,代表着父亲执着、深沉且隐忍无私的个性。相反,儿子赶山路时为了缓解沉闷,喜欢随身带着收音机,和着流行歌曲《驿动的心》边走边唱,为声景、为山野带来一股城市的现代气息。歌曲似乎无法与周遭的山水、相伴的人所同构,但足以证明,儿子所代表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文化所覆盖。而当儿子看到山下有公车经过时,就“搭车与纯脚力邮路”的问题与父亲发生争执。此时的声景,由汽车引擎声与流行歌曲《恰似你的温柔》代替了乡野的自然声景,将父子间的矛盾无限放大,并以父亲强制性地关掉收音机而结束。尽管父子之间的文化碰撞并未成为“子承父业”的障碍,但父子间的文化裂痕与鸿沟已显而易见。
该片的声景中还多次出现侗族传统的仪式音乐,如村寨男女轮唱的单声部婚仪歌曲、热闹盛大的篝火晚会以及传统的民间“芦笙舞”等。影片中的男主人公与侗族姑娘,和着“芒筒”的低音伴奏,围着篝火翩翩起舞而互生好感,这种属于侗寨独有的青年传统情感互动颇为动人。然而次日在侗寨厨房里,男女青年边做饭边欣赏着西方流行组合“麦克学摇滚”的代表作“That’s why”,两人从歌舞互动到可以毫无芥蒂地互开玩笑,仿佛这段音乐才是属于两个现代年轻人更为自然的共鸣。出人意料的是,女青年将碗倒扣在收音机上,使其产生不同的声音空间而模拟出立体声的效果,从一位山里侗族姑娘对现代音响的渴求中,可见外来文化已悄然影响着大山民族的青年一代。
显然,本片的“声景交互”带着刻意的现代与传统碰撞,将两代人的意识冲突毫不避讳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期观众能察觉到在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变革。
(三)争议
2016年的《百鸟朝凤》(导演:吴天明,作曲:张大龙),电影讲述了陕西关中农村一位德高望重的唢呐传统匠人毕生维护唢呐民间艺术、传承唢呐精神的故事。电影声景中,多次出现时而悠扬、时而灵巧的唢呐旋律,与虫鸣声、割麦声、湖水声、打雷声、落雨声、鸡鸣声以及品种繁多的鸟鸣声等自然声景相融合,铺展出一片淡雅清新的“八百里秦川”样貌。
整部影片以陕西农村婚葬仪式音乐中的核心乐器“唢呐”为主线,借助艺术化的镜头语言对关中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婚丧嫁娶习俗、陕西农村文化与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关照。影片中反复强调的“唢呐”是中国乡土礼乐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尤其在陕西合阳农村更是属于大众流行艺术。无论是婚仪葬仪还是民间娱乐,唢呐音乐都是勤劳淳朴的合阳人表达深厚情感的最佳媒介。电影中陕西本土的丧葬仪式声景,以唢呐、笙、笛子、二胡、钹、鼓的合奏形式,交织着亲属家眷的哭丧声,为观众呈现出为故人盛殓厚葬的场面与气势,同时也展示了唢呐班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随着现代思潮与外来文化的侵入,唢呐音乐及传统的婚丧习俗渐渐受到冲击,农村青年不再如父辈那般崇尚唢呐,开始向往城市、追求时尚。影片中原本以唢呐班主导的农村传统寿宴,突然被一支铜管加电声乐队打断,从爵士鼓的疯狂敲击声到爆竹的一声巨响,再到模拟耳鸣的刺耳鸣叫声,这一系列声景将从没见过“洋乐队”而丢了魂的班主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通过一段“声景交互”的混乱模式,将这种矛盾和争议放大到极致。《哎哟妈妈》《南山松》《拉德斯基进行曲》等中西名曲“竞争上演”,对骂声、嘶喊声、暴打声、唢呐折断声、酒瓶打碎声此起彼伏;画面镜头也从女歌手媚俗的舞蹈,切换成惨烈的群体斗殴和一地断裂散落的唢呐。随着一声唢呐悲凉的旋律与师父落寞的背影,这场“对阵”才草草收场。
不可否认,此时的“声景交互”带着尖锐的人为色彩和浓浓的“火药”味道,同时又怀着对传统文化“被侵入”的控诉和“被遗忘”的无奈,以期观众在思考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能保持一份“文化觉醒”与“文化认同”的客观态度。

电影《一点就到家》海报
(四)对话
2006年的《三峡好人》(导演:贾樟柯,作曲:林强),分别以两个寻妻寻夫故事为主线,将中国基层生态、情感与价值观念进行群像式写照。电影用朴素无华的纪实镜头,结合三峡大坝建设中的自然声景与现代工业化的动态声景,穿插川剧、黄梅戏选段及多首流行歌曲,以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描绘了充满诗情画意却又满目疮痍、悲剧式的现实社会图景。
影片中的“声景交互”呈现出颇为玩味的对话状态。一方面,首尾呼应的川剧高腔《林冲夜奔》唱段,缺乏了传统唱段中的司鼓和笛子配合,却浸润在迷雾般的电子合成器音色中,少了一份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多了一层孤身无靠的悲叹。可见,传统高腔与现代音色的交融交互,从影片开篇就定下了和谐的声景对话基调。另一方面,参与叙事的多首非原创流行歌曲,分别通过少年的歌声、男主人公与社会混子的手机铃声、街边小店的喇叭声、走穴艺人的歌声、舞厅音乐等独特形式,与船鸣声、轮渡广播声、轮船马达声、电视新闻声、汽车引擎声、抡锤声、碎石声,碎玻璃声等“标志声”构成在三峡移民工程背景下,库区人民生活的缩影。可见,带有明显平民文化印记的流行歌曲与粗糙质感的声景穿插交互,将新旧城区两个空间的繁华与颓败、基层与中产两个群体的盲目与现实形成强烈对比。
《三峡好人》中的“声景交互”,体现出多层次的对话意义。在影片散漫宽松的叙事节奏中,用平和的语气和镜头,解构基层人民轮回的宿命、命悬一线的无力、逃离式的解脱等命题,并提示观众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思想状态,在未被禁锢、被钳制的心态里,审视影片所带给人们的启示。
结语
声景囊括声音(sound)与地方(place)两个元素。因此,声景模式成立的基本前提,便是“音地关联”的内涵与再生。然而,理解声景仅从地缘地域与物理表层是远远不够的,声景基于多角度、多维度,展现了其文化感知、情感反馈以及时代反思的能力。“电影声景”研究,是将声音与空间的关联推向新的研究维度。声音凭借其更强的写实性,与画面相比具有更强的召唤性。观众在观影时或许已然感觉到同时来自电影与现实的空间形象在声音的诱导中呼之欲出,每一个有故事的声音在画面间自由回响时,更多层的声景想象也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其超凡的沟通力与延伸感恰恰说明电影声景并非全权以画框为界。
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声景独特且丰富,既有寓意着电影特定地域与人文的声音母题,又有代表其叙事主题的声音群落,他们之间任何一种声音组合、变奏和发展,都将是整部电影声音的根基与力量。因此,“声景交互”就是将这些声音元素视为声景建构的参与者并重新组合,使其映射出一种跨文化或更具颠覆性的声景空间。
总之,以电影声景的方式去观察、聆听和理解中国农村,不仅拓宽了中国农村电影研究的疆域,也为探索新农村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反思与听觉延伸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