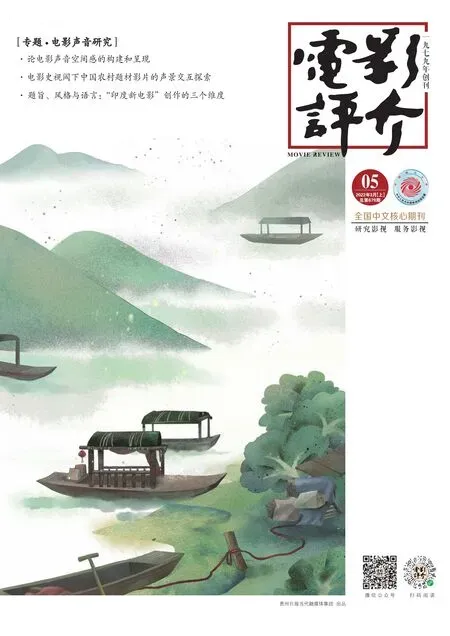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我和我的”系列:微时代主旋律电影“拼盘式”叙事审美之思
李璐璐
“我和我的”系列包括《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以及《我和我的父辈》三部,它们分别上映于2019、2020、2021的国庆节,该系列电影票房总和超过70亿元。可以说,“我和我的”系列是连续三年国庆档的主旋律热门影片。三部集中于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显然具备了献礼片的性质。那么,作为连续三年国庆档的献礼影片,体现出何种特征?呈现了怎样的时代审美特性呢?对此,又该如何进行反思呢?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入乎其内”,立足“拼盘式”电影的特征,厘清“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具体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出乎其外”,通过对该系列电影的时代审美特性进行思考,进一步反思其得以构型的文化背景和意义。
一、“拼盘式”电影的特征
“‘拼盘式’电影一语在西方学界有多种对应的名称,主要有选集电影(Anthology Film)、综合电影(Omnibus Film)、复合式电影(Portmanteau Film)、打包式电影(Package Film)、多片段电影(Episode Film)、短句电影(Sketch Film)等”。拼盘式电影的特征就是综合、复合、合集等。那么,“我和我的”系列在“拼盘式”电影综合、复合等特征基础上又有何其他特征呢?目前,业界对“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旋律叙事及其隐喻等内容,对其如何呈现主旋律与有何时代审美特性缺少解读。“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各个单元故事的拼盘;另一方面是各单元故事的主题拼盘为更高层级的主题。对此,我们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方法来审视“拼盘式”电影的内涵,不难发现,作为主旋律的“我和我的”系列以时空拼贴为内容,以主题为统率,体现人民史观三重特征。
(一)时空拼贴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有着强烈的时空拼贴特征。例如《我和我的祖国》的7个故事都是以重大事件的时间为单元故事线,《前夜》以1949年开国大典前14个小时对升旗旗杆的装配为故事线;《相遇》以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前三天为内容;《夺冠》时间定在1984年,女排首次夺冠的那一年,不同的是,影片的时间却是小美出国前几个小时;《回归》则是1997年香港回归升旗仪式,中国必须0时0分0秒升起国旗为主要内容;《北京你好》则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后为线索;《白昼流星》是以2016年神舟十一号返回和脱贫为故事线;《护航》的时间点定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就《我和我的祖国》而言,一方面,对电影来说时间起到了综合性作用;另一方面,重大事件的时间也是叙述者,推动着故事往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电影中将历史视频与电影文本进行交叉剪辑,使得电影叙事以真实性增强代入感从而获得真切的感动。
另外,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也存在时间拼贴的特征,但与《我和我的祖国》不同,其时间有一定的模糊性。例如《乘风》定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具体年月被隐去,以放大情感的感染力;又如《诗》一节是关于火箭零件的设计,也模糊了时间,以突出主题;《少年行》以穿越为内容,是一种类似于《终结者》的未来拯救现在、现在创造未来的时间游戏。2021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不像《我和我的祖国》那样以具体历史史实为主要呈现内容,而是以情感真实取代历史真实从而,实现放大情绪感染力的效果。相较之下,《我和我的父辈》更多呈现艺术真实性,而《我和我的祖国》则更多呈现历史真实性。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中间,起到过渡作用的是《我和我的家乡》,它以空间拼贴为主要形式。全片包括五个故事,分别发生在贵州、北京、杭州、陕西、东北,这五个空间主要承载的主题是脱贫;它削弱了具体时间,各个故事的时间都可以是2020年。《天上掉下个UFO》主要讲述的是贵州旅游脱贫,其主要展现的是贵州的原生态旅游和风土人情,以及UFO是否存在的瞒与骗建构了本片的奇观化与戏剧冲突;《北京好人》以农村医保普及问题为主题,电影以医保将农村与城市双重空间联系起来;而《最后一课》则是国内外空间对比,老教师旧时记忆中的贫穷空间与现实已脱贫空间形成对比,多重空间以老教师最后一课作为连结;而《神笔马亮》的喜剧效果则是以现实已脱贫的东北农村揭穿马亮营造的俄罗斯留学空间来实现。
由此可见,“我和我的系列”三部影片普遍表现出时空拼贴的特征,时空既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又是叙述对象。通过对重大事件的细节进行影像书写,实质上是在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中突出个体的情感体验,以实现普遍共鸣的效果。
(二)主题统率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我和我的”系列三部影片,从各故事单元“拼盘”来看,是在各自主题统率之下,以各故事单元的小主题复合、综合而成的电影。
从一级主题看,《我和我的祖国》的主题是爱国。二级主题来看,《前夜》是建国时,人民当家作主的澎湃;《相遇》则是原子弹爆炸时,人民站起来的自豪;《回归》则是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兴奋;《北京你好》则是举办奥运国力强盛的欣慰以及汶川地震的伤痛;《白昼流星》是航天大国与脱贫富强的主题;《护航》则是综合国力和世界和平的主题。综合来看,从建国到国家繁荣富强以及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苦难,各二级主题实际上是大主题“爱国”的具体内涵。
《我和我的家乡》的一级主题是脱贫致富。那么各个故事单元的二级主题,则是创业脱贫、教育脱贫和健康脱贫、文化脱贫,以多样的脱贫形式表现出国家全力脱贫的决心也表现脱贫的具体效果。
《我和我的父辈》的一级主题是“传承”。《乘风》电影描绘了一组骑兵团与冀中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军民群像,以新生儿与牺牲儿子同名这一方式实现精神的传承;《诗》则以一个航空家庭的视角,展现了父母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并揭秘父亲抚养牺牲同事的儿子这一真相而女儿长大后继承了父母的遗志,成为一名航天工作者,实现传承;《鸭先知》是通过中国大陆第一支广告的拍摄表现改革开放最早一批感知时代的人以及其传承者;《少年行》则是通过时空穿越主题鼓励热爱科学的少年追求梦想,同样让今天的儿子成为未来父亲,以实现传承。
(三)人民史观
“我和我的”系列还表现出人民史观。《我和我的祖国》的人民史观主要表现为大事件背后人民对历史创造。例如在《前夜》中,关键的国旗红布、阻断球材料都在主角的号召中,人民连夜送来。这本就隐喻着开国大典升旗的圆满完成都得益于人民的支持,故事内容具备延展性,隐喻了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相遇》里故事是原子弹科研人员的爱情,电影中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既表现他们对国家无言的支持与贡献,同时电影更是科研人员背后的家庭无私的奉献与支持。《夺冠》虽然表现女排夺得奥运冠军,但在视觉呈现上,这一故事单元主要以上海市民对女排的支持以及冬冬主动承担信号连结的工作,表现了女排精神对于国人的影响。《回归》以香港回归升旗为故事内容,故事中以平民修表匠和香港警察等一线人员表征香港人民对回归的迫切渴望。而《北京好人》的主角则设定为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工的孩子,进一步突出人民的重要性。
《我和我的家乡》则表现了人民正在创造的历史。该片将视觉焦点集中于正在发生的脱贫攻坚上,具体来说是聚焦于全国各地不同的脱贫实践,实践主体是具体工作岗位的人民大众。而《我和我的父辈》则将焦点聚焦于模糊的时空,对人民史观以抽象形式加以呈现,表现了人民推进时代进步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和我的”系列“入乎其内”的考察,可以看到该系列拼盘双重结构。总的来说,该系列以时空拼贴为内容,以主题为核心体现了人民史观。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主题的拼盘,电影以爱国、脱贫致富和传承为一级主题,统率各单元故事的二级主题的拼盘;另一方面,从传播与接受角度看,各故事单元具备独立传播与接受的延展性,本身碎片化的单元故事存在拼盘的可能。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剧照
二、微时代“拼盘式”主旋律电影的审美特性
经过对“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入乎其内”的概括分析,可以看出,拼贴的时空既是故事内容本身,也是叙事手段;而主题的双重性则表现出次级主题的碎片化特征;人民史观的展现则是通过细节的方式揭示大事件背后的人民。因此,从“我和我的”系列各单元故事的时间长度与紧凑的节奏感来看,其与传统电影的追求故事完整性与“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碎片化的故事单元与人民性的表达方式,符合“微时代”的审美特征和叙事方式。
在新时代微媒介方面,“我和我的”系列符合微时代独有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景观。它们“以简短细小、破碎分裂构成生活行动的空间占有形态,以迅捷发散、社区化或部落化复制传播作为个体情绪的时间存在方式”。微时代文化景观表现在电影上,一方面,传统“起承转合”的整体性电影空间被分割成各个相关的故事单元;另一方面,以个体情绪时间为核心的部落化复制传播,单元故事的情绪渲染大于剧情的深度体验。基于此,“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压缩了电影故事时长,由碎片化的次级主题单元故事组成,压缩的时间删除了故事应有的情绪铺垫,直接通过多个次级主题的堆积实现整部电影的情绪渲染。另外,“我和我的”系列整部电影各自独立的单元故事与其他的电影相比有一定的差异,在传播上,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在传统两小时的电影时间嵌入7个故事,必然每个故事的时长被大大压缩;在呈现上,必然以历史真实的矛盾来减少铺垫时间而直接呈现冲突最尖锐的时刻。因此,此种呈现方式也存在微传播的可能,在“我和我的”系列上映期间,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大量出现电影的“高燃”片段即是说明。碎片化的故事单元未表现的部分表现出强大的延展性,因为“爱国”“脱贫”“传承”等主题的统率,该系列故事单元的延展性在微媒介的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感染力,从某程度上说,对于主旋律起到正向宣传作用。
与传统蒙太奇比较而言,微时代“拼盘式”电影的碎片化与平民性消解了传统电影观影的沉浸式与深度体验模式,转而以情绪取代理性,以浅层感官刺激大于深层反思。根据苏联蒙太奇学派观点,“任意两个片段并列在一起必然结合为一个新的概念,由这一对列中作为一种新的质而产生出来”。从蒙太奇品质可以看出蒙太奇具备一种概括镜头画面的本能,这种概括是片段组合之后的质变。“我和我的”系列在单元故事中片段与片段组成了该单元故事的单元主题,而单元故事之间的再次组合则成为更高一级的电影的主题。例如《我和我的祖国》中《回归》这一章节就通过中英两国对升旗时间的谈判与旗手的时刻练习,将中国对时间的底线表现出来,同时通过修手表与换警徽实现对0时0分0秒的坚守;如《相遇》中科研人员始终戴口罩保持沉默,但镜头在男主眼神与女主角之间脸部特写之间进行正反打调度,表现了女主的等待与男主对国家秘密的绝对缄默,通过小爱与大爱的碰撞,最终展现出了爱国的宏大主题;又如《我和我的父辈》中《少年行》通过机器人的牺牲激发少年的奋发图强之心,最终制造出机器人并完成时空旅行,两个画面实现超越时空的“传承”主题的呈现。
总之,“我和我的”系列整体上既符合微时代碎片化与平民化的时代特性,又具备传统电影的蒙太奇概括的品质。但是,我们也应该也要看到“我和我的”系列碎片化审美对电影整体性构架的消解以及主题先行对主旋律电影的重要价值。对此,我们应该跳出微媒介传播机制,从主旋律电影的文化、社会角度进行反思。
三、微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反思
(一)以“真实感”抵抗碎片化浅表接受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拼盘形式最为突出的便是碎片化特征,这消解了传统电影沉浸式体验与深度模式。具体而言,客观时间的缩减与故事的转场消解观众对故事的沉浸感,不同时空的故事必然导致观众频频出戏;另外,故事矛盾经过短暂的铺垫就直达高潮部分,不同的故事矛盾会打断观众的深入思考。例如《我和我的祖国》的转场是通过写信,而《我和我的家乡》与《我和我的父辈》则通过最直接的黑屏淡出实现转场。碎片化既是观众的观影习惯,也是“我和我的”系列影片的特点,二者的相互建构彻底将故事表达与观众思维拉入碎片化的境界,使得观众失去了深度思考与认同。从“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来看,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那种厚重的时空感,是通过历史影像资料与影片结合实现的,具有历史真实的可靠性,所以口碑票房双丰收。但是到了《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天上掉下UFO》,尽管主题是旅游脱贫,UFO的设定和故事矛盾显然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与沉浸感。再如《我和我的父辈》中《诗》采取荒漠、大雨和孩童的不理解制造矛盾,最后通过毫无预兆的剪辑实现反转,导致原本强烈情绪被消解掉。因此,“我和我的系列”应该继续保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即便是微时代的碎片化传播也能最大限度保持电影本身的真实感。
(二)以“主题”统率碎片化传播
“我和我的”系列另一重要特征是主题统率,而主旋律电影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观众接受主旋律主题。因此,如果主旋律电影选定拼盘组合的外在形式,那么主题对故事单元的统摄力就是核心问题,电影核心主题如果无法涵盖次一级主题,那么单元故事本身的延展性在接受上就容易出现被观众消解和异化的可能。例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白昼流星》章节,故事本身以脱贫和神舟十一号返航为主要内容,但二者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在构成单元主题时就存在多义性与误读的可能,进一步说则破坏了更高层级的主题呈现。
总之,“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以其拼盘式主旋律电影而独树一帜,通过对其时空拼贴、主题统率与人民史观的特征的分析,揭示出该系列深层的微时代特性是其能够成功的原因;同时也显示出其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误读的风险。因此,我们在面对拼盘式主旋律电影时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及加重主题的统率功能,以此抵抗碎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