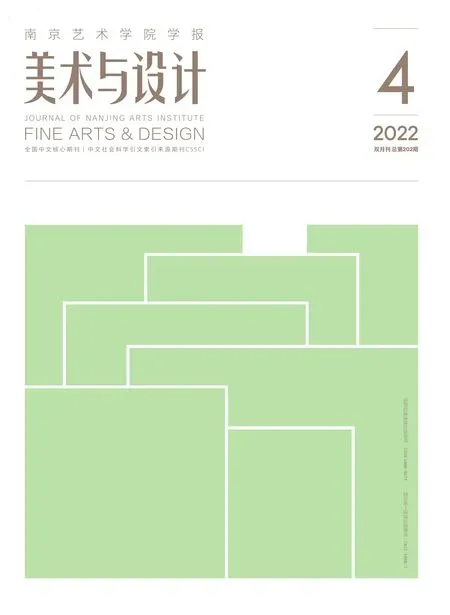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白莲社图》研究
——以“光熟纸”的艺术表达为例
何士扬 饶蔚姝(中国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光熟纸”一词非古之既有,它出自《“羊毫”“生宣”论》,是吴湖帆先生对明代之前主流书画用纸的概括性命名:
羊毫盛行而书学亡,画则随之;生宣盛行则画亡,书亦随之。试观乾隆以前书家如宋之苏、黄、米、蔡,元之赵、鲜,明之祝、王、董,皆用极硬笔,画则唐宋尚绢,元之六大家(高、赵、董、吴、倪、王),明四家(沈、唐、文、仇)董二王(烟客、湘碧),皆用光熟纸,决无一用羊毫生宣者。笔用羊毫,倡于梁山舟;画用生宣,盛于石涛、八大;自后学者风靡从之,坠入恶道,不可问矣,然石涛、八大,有时也用极佳侧理,非尽取生涩纸也。
《白莲社图》(图1)(下称辽博本莲社图),笔墨语言丰富、纸张质地优佳、保藏状况良好,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宋代“光熟纸”绘画作品。目前,与该画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作者考据、艺术风格分析等方面,尚未见结合书画材料与笔墨语言进行研究的案例。

图1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
古代文献虽然没有“光熟纸”一词,但同时以“光”“熟”二字形容纸张性质的记载,曾见于宋代邵博所著的《闻见后录》:“唐人有生纸,有熟纸。熟纸所谓研妙辉光者,其法不一。”根据潘吉星先生对故宫若干唐、宋书画用纸的检测可知,“唐、宋法书多用熟纸……多借拖浆、砑光、填粉、加蜡而成”,宋代延续了唐代的造纸工艺,制造出许多传世名纸,诸如仿澄心堂纸、谢公笺、金粟山藏经纸、瓷青纸等。它们作为宋代书画的载体,乍看似乎只存在颜色、帘纹、花纹等容状上的差异,实则都是由不同工艺、材料精工细作而成的“光熟纸”,其纸性关乎不同的书画用笔。关于宋人用纸,杨仁恺先生曾经一言以蔽之:“皆为细磨琢磨,使纸张表面平滑。”
事实上,两宋书画的笔墨风尚是与“光熟纸”的性能密不可分的。如同北宋黄庭坚喜爱冷金笺、米芾无一笔胶矾绢纸,艺术家选用不同性质的纸张进行创作,书画作品随其所好而风格别样出奇。所以,若要讨论两宋书画的品鉴、创作、递藏等议题,则不可不谈“光熟纸”。
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价值,“光熟纸”作为明代以前主流的书画用纸,亦是如此:它由精工细作而成,为适应书画的创作与保存,从材料的选择到工艺的取用,均蕴涵着丰富的传统工艺(科技)价值;随着书画作品的创作与递藏,蔓生其上的,还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唐代张彦远在谈论书画鉴藏时,就曾提出“收藏—鉴识—阅玩—装褫—诠次”多位一体的鉴藏观,其视角涵盖了上述文物三方面的价值。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鉴藏系的教学与研究中,此一观念被归纳为对书画“艺术经验”“传藏信息”“保藏技术”三大模块的研究,即“全流程研究”。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若要从“光熟纸”的角度品鉴辽博本莲社图,除了要讨论心子用纸的材料与工艺,以及材料与笔墨的关系外,还应兼论与之伴生的书画装潢。
宋代文人是书画艺事风潮的引领者,以宋四家为代表的文人墨客均以精择纸笔为乐,其中尤以米芾为最。他常亲自加工书画用纸,曾用“滑、净、软、熟”概括好纸的特性。由此,本文将借米芾之说,以“光熟纸”为中心,就其材料与工艺、纸性与笔墨、保护与收藏等议题,讨论辽博本莲社图的纸张特性及其艺术表达。
一、辽博本莲社图用纸之“柔韧”
在现存的宋代“莲社”主题绘画中,要数辽博本莲社图的保存现状最为完好。将其对比南京博物院藏南宋佚名《莲社图》(绢本设色)、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宋佚名《莲社图》(纸本水墨)后发现:从画芯状况看,南博绢本莲社图遍布补洞(图2),芯子中间有一道由上至下贯穿的修补痕迹;大都会纸本莲社图比南博绢本莲社图略为完好,纸面泛黄,仅在空白处有几块缺失。但可能由于收卷不得当,全卷留有多条平行于天杆的折痕(图3)。有学者认为,大都会纸本莲社图为明代人所作,若如此,则更显辽博本莲社图心子纸质地之优良,纸面之平整、光洁,通览之下,仅有一些手卷常见的细纹,虽为宋纸,年份较长,但其现状堪称完整(图4)。

图2 (南宋) 佚名,莲社图(局部)

图3 (北宋)佚名,莲社图(局部)

图4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人们往往将书画保藏的好坏归结于装潢工艺,实际上,作为画芯的用纸,其本身质地的好坏,亦是决定保藏现状的重要因素。细观辽博本莲社图,纸张颜色发冷、偏白,帘纹隐约可见,卷尾有几处洇散,推测其用纸可能与《公议帖》相同,都经过白色矿物粉浆的填涂。同为粉笺类的“光熟纸”,宋徽宗赵佶的《池塘晚秋图》涂层较为厚重,属砑花罗纹笺一类。其工艺流程为:先以矿物粉涂布,再借硬挺的织物印出斜罗纹,复于表面施砑,制作蔓藤花纹。由于此卷粉层厚重,在反复舒卷之下,纸面涂层出现了裂纹、剥落,画意涣漫(图5)。此外,近观辽博本莲社图的落墨处,依稀可见纤维状的白筋(图6)。为此,笔者按照硬黄纸的制作工艺,取皮纸就黄蜡施以砑、烫,尝试制成蜡笺纸,试笔后观察到,落墨处有与辽博本莲社图相似的纤维状白筋显现(图7),因此推测辽博本莲社图芯纸张的表面,可能有蜡膜存在。

图5 (北宋)赵佶,池塘晚秋图(局部)

图6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图7 笔者制作的蜡笺,落墨后的白筋 来源:笔者拍摄
综上所述,辽博本莲社图芯的用纸工艺较为复杂,可能是一张质地柔软、纸性坚韧的粉蜡笺,其纸张表面先施涂以轻薄的矿物粉层,再砑、烫以薄蜡层,确为精工细作的“光熟纸”。
1.画芯“柔韧”与修复的关系
书画芯子之“柔韧”,是书画装潢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辽博本莲社图几经揭裱、修复,至今仍然可以保持手卷的样式递藏,可见其芯子用纸之“柔韧”。
早在唐代,张彦远就对卷轴的修复提出了基本要求:“就其形制,拾其遗脱,厚薄匀调,润洁平整。”辽博本莲社图既为卷轴,为保证其厚度均匀,修复时的补缀必须根据芯子的情况进行。后代延续张彦远的主张,针对补缀提出:“补缀须得书画本身纸绢质料一同者……绢需丝缕相对,纸必补处莫分。”在实践中,补的方法通常有三种工艺:斩补法、整绢或纸托裱法、细补法。其中前二者存在“慢性杀画”的隐患,故以细补法最为合理。它是以锋利的马蹄刀在缺口四周刮出平缓的斜坡,用毛笔蘸涂浆糊后,再将质、纹、光、色相同的补料覆上,刮除缺口以外多余的部分,刮至纸张平复。细补最有“补处莫分”的效果,无论从外观和内在性质上,都如同一张从未破损过的新纸。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苏轼《洞庭中山二赋》,该卷卷首破损处的补纸,是从经卷中剥下的经纸。选择同样经过自然老化的经纸补缀,削弱了补纸与芯子之间的应力差,令卷轴平整舒展,只是经纸还存有残墨,从视觉上未达到“补处莫分”的标准。未有记载说明辽博本莲社图的补纸情况,不过从现状来看,它的补缀遵照了传统的修复理念,采用了细补法,选用质、纹、光、色相同的补料,进行“补处莫分”的修复(图8),不细看很难分辨曾经的破损处,排除了芯子与补料之间的应力差,保持了芯子柔韧度的整体性。

图8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书画芯子“柔韧”的特性,可降低因装潢反复干预带来的损伤。米芾曾说:“盖人物精神发彩……旨在约略浓淡之间。”他强调古画若无空壳、起翘、脱落等恶疾就无须重装,以免损伤画意,后人亦以此为警示。辽博本莲社图芯子尾部有“子省”“钱后人用拙翁”两方宋代残印,卷中清代梁清标的“苍岩子”朱文圆印在骑缝处也有缺失,表明此卷至少经过三次装潢,即一次装裱和至少两次的修复。修复时反复的淋洗、揭纸会对书画产生一定程度的损害,然此卷经受多次装潢,芯子仍平整、光洁,且依旧保有传神阿堵的神采,很好地诠释了后人对宋代绘画“薄如蝉翼、浓如点漆”的墨色层次认知。书画性命,全关于揭。作品保存状况良好,除了有良工的补天之手外,还和芯子柔韧、紧密的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经前文的综合判断,辽博本莲社图芯子用纸工艺较为复杂,以矿物轻薄施涂后烫以薄蜡层,是一张品质上好的粉蜡笺,心子密度高、韧性强,在水洗、揭背时,不容易被揭穿、揭薄,无形中保持了绘画“浓淡之间”的神采。
2.芯子“柔韧”与装裱的关系
辽博本莲社图虽然不是宋代原裱,但它的装潢样式仍可见宋代装潢之美的缩影。它的折边与引首用纸说明此卷既有对宋代装潢的传承,也有根植于古朴、雅致宋韵的新阐发。辽博本莲社图在宋代手卷“五段式”的基础上,增加了黄笺引首,折边并未采用明代以来常用的宽绢,而是沿用宋代“宣和装”的古铜色小边。它的折边、引首,均是质地上乘的“光熟纸”,也是体现此卷装潢之美导源的关键之处。明代周嘉胄的书中有以经纸作装潢材料的明确记载:“余装潢以金粟笺用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金粟笺”即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它出自海盐地区,是唐代硬黄纸的历史延续,属于“光熟纸”中的蜡笺范畴。其品质之高,潘吉星先生认为:“宋代名纸应首推金粟山藏经纸。”历代写经纸都由施蜡、砑、烫等复杂的工艺制成,具有柔软、细密、耐折的优点。吉林省博物馆藏《洞庭中山二赋》(图9)的纸边清晰可见经文墨迹,就是“经纸折边说”的一个实例。

图9 (北宋)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局部)
可作辽博本莲社图折边与引首是宋代经纸进一步推论依据的,是此卷的传藏路径。辽博本莲社图有鉴藏章36枚,已考证的印文说明,它曾为清初收藏大家梁清标所有,又进入清宫内府,经乾隆、嘉庆、宣统皇帝品鉴。这两个阶段,是厘清辽博本莲社图装潢样式缘由的关键。梁清标是清初书画鉴藏的核心人物,同时他还是“南画北渡”的关键人物,他的庋藏有一部分来源于南来北往的商贾与装潢师。这些装潢师不仅带来了南方的藏品,还有吴中地区的装潢理念与工艺。清代儒商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扬州有张黄美者,善于裱褙,后为梁清标家装。”再则,后来梁清标的收藏,多归入清宫内府。清代钱泳《履圆丛话·艺能·装潢》又记载:“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无论最后一次重装辽博本莲社图的是梁清标还是清宫内府,都将它的装潢指向吴中地区。
吴中地区的装潢,有着使用宋代经纸的条件与氛围。私人收藏与内府收藏有着此消彼长的规律,但无论书画作品藏于谁手,其递藏都离不开对装潢的倚重。两宋御府的庋藏之丰,造就了为世所重的宣和装、绍兴装,发后来收藏、装潢格式之先声。明朝内府不重书画收藏,致使私人藏家活跃,且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位于鉴藏中心的吴中地区,自然应需求派生装潢之能事。此外,宋代经笺的集中出产地海盐县,亦在鉴藏中心内。周嘉胄的《装潢志》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周嘉胄本是一位鉴藏家,他基于吴中地区装潢技艺写成的《装潢志》,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经纸折边说”代表了明代南方鉴藏圈对装潢用料的态度。在明末清初的藏书圈中,脱胎于毛晋、钱谦益一流的虞山藏书大家,也常取经纸作善本的书面、题签,以此追摹宋人雅致的装潢之美。作为虞山派藏书的集大成者,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记载:“见宋刻本,衬书纸古人有用澄心堂纸,书面用宋笺者,亦有用墨笺撒金书面者,书笺用宋笺藏经纸、古色纸为上。……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更佳。至于松江黄绿笺书面,再加锦套,金笺贴签,最俗。”虞山派的主张为时人所效法,《金粟笺说》中有“宣绫包角藏经笺,抵得当时装订线”的感慨,可见宋式装潢审美理念在吴中地区颇为受用。这样的装潢取法同样在卷轴中有所表现,南画北渡之后,清宫的藏品,其引首多为经纸。辽博本莲社图卷首为几张黄色小纸拼接而成,纸上有一长方小印,前三字可辨为“倪仁禀”(图10),最后一字模糊不清,我们将其与《金粟山笺说》中记载的藏经印(图11)进行图文对比后发现,这枚印章归属于金粟山藏经纸印记体系,是当时造纸坊的征信凭据。

图10 辽博本莲社图引首印记

图11 “倪仁禀”印记 来源:《金粟寺史料》
几番对照下发现,辽博本莲社图得益于芯子“柔韧”的特性,在经过几次重装后,仍以卷轴的样式保存良好。卷轴上折边、引首的材料说明,它的装潢理念导源于明清江南吴中地区,其根本建立在宋式装潢审美之上,体现了明清之人对宋代装潢理念的传承与阐发。
二、辽博本莲社图用纸之“滑”“熟”
“画事精能,全重勾勒,勾勒既成,复加渲染。”在黄宾虹先生的语境之中,画之笔法重在勾勤,集用笔与用墨为一体,可看作是一实一虚的合力。辽博本莲社图就是这样一卷重勾勒、淡墨渲染的绘画作品。黄宾虹先生又说,“古之师徒授受,学者未曾习画之先,必令研究设色之颜料……继教之以胶矾素绢之法。”是以,笔法是万象之始,因墨法更发神采,此二者的发挥则又依附于材料的性能。
1.心子“滑”“熟”与用笔的关系
“光熟纸”的“滑”“熟”特性是辽博本莲社图用笔运转自如的一个重要前提。六朝到唐之间的毛笔以缠纸法一类的工艺为主,这样的毛笔笔头短小而尖锐,蓄墨少,有顿挫、提按不灵便的局限,用笔多短、硬,游丝纤毫毕露,书写时多折笔,少圆转。为追求刚柔相济的笔性,宋元以后多用短毛支撑笔形,代替缠纸笔的笔柱,又增加了笔毫长度,保证了笔肚的腰力和蓄墨力,形成散卓法毛笔。加上对羊毫的适当取用,令狼毫、兔毫等硬毫兼杂柔软之性,此类毛笔用笔时游转幅度大,在纸绢上可见粗、细、圆、折、方等变化多端的用笔。张宗祥先生曾在《书学源流论》中谈论毛笔与纸张的关系,他说:“世之爱书拒笔劣纸者,必为爱用柔毫之人。何以明之?柔毫锋长力弱,一撇一钩,势放而难制,施之拒笔之纸,则执笔者不能制笔而纸能制之;然虽能制之,不能使之恰到好处,此所以不足尚也。”顺着张宗祥先生的话说,宋人多用短锋硬毫,自然对应不拒笔的“顺笔优纸”。辽博本莲社图的人物勾勒(图12),用笔奇巧,以兰叶入,又急转以铁线出,忽提忽按,长短相接,方圆相济,衣摆散处绵软飘举,形体贴合处刚劲有力,比之《朝元仙仗图》(图13)《送子天王图》,可以看出作者运笔如隶、篆、草书随意变换,无有障碍。与辽博本莲社图用笔可相媲美的,是传为李公麟的《西岳降灵图》(绢本),二者都较好地诠释了画者们富有心理节律的情感表达,于人物须发、衣带之间,以精微的用笔直指“应物象形”之理。宋代双缕方眼的织绢工艺,使得绘画用绢更为平滑。《长物志》载宋代院绢细密如纸,以南宋院画《采薇图》为例,无论是近景的斧劈皴或是远景的烘染,都表现出了丰富的焦、浓、重、淡、清的墨色层次。《西岳降灵图》(图14),在勾勒上稍稍削弱了用笔的变化,由于绢本经纬的起伏,行笔多断点,比之辽博本莲社图,运笔生涩,墨色莹润不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曾言:“夫物象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中国画讲气韵,绢本白描人物虽笔断意连,但细细纠来,在笔意上不免略失一筹。可见,尽管宋绢工艺细密如纸,相比纸张仍略显粗糙,在勾勒上稍显逊色。

图12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图13 (北宋) 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局部)

图14 (北宋)李公麟(传),西岳降灵图(局部)
2.心子“滑”“熟”与用墨的关系
“光熟纸”之“滑”“熟”,可令笔墨毫芒毕现、层层分明。历代以矿物粉涂布纸创作的名作,还有米芾《苕溪诗》《公议帖》、苏轼《新岁未获帖》等。其中,米芾的《公议帖》与他的《新恩帖》《韩马帖》一同合裱成为《行书三札卷》,卷尾有一篇明末王铎与友人的书信,作为此卷的观跋。有趣的是,王铎采用的是一张性质偏生的纸张,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图15)。这封书信行笔间墨色浓淡、干湿变化明显,富有跳跃的节奏感。由于纸张偏生,每一次蘸墨后重新起笔都渗漫发糊,多处用笔难分锋毫。相较之下,米芾采用“光熟纸”,通篇以浓墨书就(图16),墨色滢润,笔锋出入转侧棱角分明,飞白爽利,丝丝勾连。辽博本莲社图的纸张“滑”“熟”程度与《公议帖》相接近,用笔勾皴点染,变化十分丰富。它的人物造型清朗,在用笔上气脉贯通,可随意运转,顾盼之间,毫芒毕现,兼备侧、勒、弩、趯、策、掠、啄、磔的“永”字八法(图17)。其勾勒之法一如唐人褚遂良《阴符经》,其运笔灵活,行笔、转折、点画兼有行书笔意,出入锋芒还带有隶书意味,轻重、虚实相互掩映,笔势纵横流丽,天趣自然。不仅如此,辽博本莲社图渲染层次之精微,画中人物仅一人之身既显多种墨色变化,墨彩流动,丝毫不逊色于绢本赋彩。

图15 (北宋) 米芾,行书三札卷(局部)

图16 (北宋)米芾,公议帖(局部)

图17 辽博本莲社图人物用笔与“永”字八法用笔对照
“光熟纸”的“滑”“熟”,令辽博本莲社图烟云、山石、树木于层层分明的墨法中虚实相映。黄宾虹先曾说:“凡画须远近都好看。宜近看不宜远看者,有笔墨无局势者也。有宜远看不宜近看者,有局势而无笔墨也。”远观莲社图,卷首混沌胶着,卷末清旷疏朗,虚实悬异的画面布局,引人一探究竟。展开莲社图,过虎溪、探幽径,作者先掷重笔刻画东林寺的山麓,形成位置经营之“实”;云烟四起,雾破山明,又转以淡墨勾勒在莲社内共修的僧俗,营造位置经营之“虚”。如董其昌所说,“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一实一虚,令人在朝堂与丛林、现实与虚幻、内与外、物与心的畅想中流溺忘返。
侧重以笔墨出入于虚实之间的绘画风格,诸如米氏云山、禅林戏墨,有不少以纸张为载体。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为文人戏墨,李氏延续唐代王洽一脉“烟云惨淡,脱去笔墨町畦”的墨法,将用笔与用墨结合有致。沈周评论此类空蒙的墨法:“烟邪雨耶树色溟,洲兮渚兮水光泫。”董其昌认为此类气韵的用笔“不可用粉染,当以墨渍出”。米氏的墨渍,被董其昌称为“落茄皴”,实际上不拘常规,有违勾、皴、点、染的传统山水画法,仅以深圆凝重的点错落排布成皴法,积点成线,积点成面。《潇湘奇观图》(图18)以卧笔为中锋圆点,干、湿、积、渍并用,表现出迷离的笔墨气势,为文人戏墨“虚中含实”的典范。据米友仁卷末的自跋:“此纸渗墨,本不可运笔。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说明生纸,在画家眼中不是最理想的书画纸,但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文人重体验、不拘泥条分缕析的戏墨。禅画也有戏墨的意味,以偏生的纸张便能完成。关于梁楷的用纸,杨仁恺先生曾谈及:“宋代水墨文人画(如米芾、梁楷、法常的作品)使用未加工的生纸亦是有的,但仅是个例。”目前学界尚未对梁楷的书画纸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检测,但我们仍能从用笔、用墨中看出其用纸的基本情况。《李白行吟图》(图19)以粗放的用笔勾勒诗人的身躯,表现李白豁达的胸襟,梁楷在诗人的面部略收其势,以轻盈流畅的笔墨重点刻画,彰显李白内敛的精神。画中诗人的身躯,在一笔之中,浓淡、虚实、干枯、笔路无不详尽,可见纸张紧实又有一些生涩,卷中人物发髻处墨色浓郁,边缘似有破框而出之意,说明纸张吸墨力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疏水性。与此二卷不同,辽博本莲社图虽也重勾勒用笔,轻水墨渲染,但由于纸张的熟、滑程度较高,表现出“实中含虚”而非“虚中含实”的墨法。以辽博本莲社图山石为例(图20),作者先以长短不一的干墨交搭、皴擦,勾勒出山石形体,再以淡墨润染层次,表现石质的嶙峋层叠,坡脚、石缝中施加浓点,近似郭熙卷云皴,又更加柔和、浑融,因纸张紧密、熟滑,一山一石之间,含有墨色的多种层次。山石风貌的表现风格既写实,又兼有古拙之感。

图18 (南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局部)

图19 (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局部)

图20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与戏墨法常用的半生熟纸张不同,辽博本莲社图心子用纸大约有八、九分熟。此卷墨色莹润,纸张的疏水性较大,落笔不能瞬间吃墨,在笔头湿度较大的情况下,墨在纸面随笔尖的提按有轻微的流动,致使勾勒收笔处有积墨现象(图21)。山石的浓重苔点,其边缘线也多有积墨。若将之与明代文征明金粟山本《听竹图》(图22)再一对照,则更加了然。宋徽宗赵佶《柳鸦芦雁图》第一段《柳鸦图》(图23)的部分,墨色沉着黑亮,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先生认为,此作或有可能以李廷珪墨所绘,它的纸张虽不如辽博本莲社图洁白,但是质地紧密,也是一张高品质的“光熟纸”。与辽博本莲社图相似,《柳鸦图》的墨色层次丰富,在坡脚的勾皴中能看到明朗的墨色层叠关系。相比《柳鸦图》,辽博本莲社图的墨色过渡则更为含蓄(图24),层层叠叠的墨色,融于运转自如的笔法中,所造之象游离在工与意之间,气象极为明净,其中,又以淡墨的敷染最为清透。

图21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图22 (明)文征明,听竹图(局部)

图23 (北宋)赵佶,柳鸦芦雁图(局部)

图24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墨色的层次分明与否,最能体现出纸张是否具有“熟”“滑”得当的性质。在宋代以中锋用笔勾勒为主、水墨渲染为辅的人物画中,属辽博本莲社图芯子质地最优。“九歌”与“莲社”一样,是李公麟擅长的绘画主题,后世画家多以李氏的创作为范本,现有多本纸本《九歌图》存世。其中,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九歌图》(图25)以游丝描勾勒人物,不用墨染,山石无重墨描摹,而用大量的云气烘染氛围。此卷无浓墨勾染,可理解为作者应《九歌图》主题需要,以淡墨入画,营造神灵出行的飘乎仙境。然而从材料上来说,故宫博物院藏《九歌图》以勾勒为主,皴染少,是因为纸张本身的质地相对较生,不适合表现由浓至淡跨度大而层次分明的墨色变化。相比之下,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九歌图》(图26)的芯子与辽博本莲社图的更为接近,即便如此,该卷在光滑程度上仍不及于后者。《临泉高致》指出:“笔迹不浑成谓之疏,疏则无真意;墨色不滋润,谓之枯,枯则无生意。”《洞天清录》又言:“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分晓也。”辽博本莲社图中,树木的勾、皴、点、染,用笔繁复、精到,大抵是以淡墨勾勒,趁笔未干的时候顺势接笔(图27)。浓墨最醒精神,画家们多将它用于结构转折处、枝桠凌空伸展处,或画面前端的树叶。以卷中松针为例,先以浓墨用中锋,由外向内收,团簇成形后再以淡墨勾其隐约处作出层次;而夹叶多以浓淡区别前后关系,笔意交融处,浓淡过渡自然,或勾或点或染,如风动之影绰。反观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九歌图》,树干勾勒简率,树叶的用笔单一且着墨较为枯涩,前后关系大致用三个层级作区分,墨色层次较为刻板,在虚空处的云气渲染亦是如此。说明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九歌图》纸张生熟得当,但在光滑程度上稍逊色于莲社图。纸张的差异决定了画意,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九歌图》有古朴之意,而辽博本莲社图则多一分明朗。

图25 (宋)佚名,九歌图

图26 (宋)佚名,九歌图(局部)

图27 (北宋)张激,白莲社图(局部)
三、辽博本莲社图用纸之“净”
纸张的发明掀起了一场文字的“革命”,为后世、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在文人士夫眼中,它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物件,亦蕴含方正、廉洁、行藏有度的君子德行。历史上,文人常将纸张拟人化,冠以“楮先生”“楮知白”等美名,并为其立传。至南宋,郑清之等文人游戏文章,借鉴这种高度拟人的手法,为文房四宝“封侯晋爵”,并以四六体撰文汇集成《文房四友除授集》,文中将纸张的容状、性态悉数拟人化,给予极高的评价。
概而言之,文人对纸张“光洁”之赞美,是视觉上对物之“实”的喜爱,例如,米芾曾夸赞纸张细润如膏脂:“象管钿轴映瑞锦,玉麟棐几铺云肪。”而对纸张功能之赞美,在精神上则视纸张之白为“虚”,叹其能纳难以斗量的百家翰墨,如同曾丰所说:“同为时用楮先生,万事须臾点化成。”辽博本莲社图的用纸色泽滢白,称得上米芾口中的“云肪”,属同期纸张中的极品,在纸中最“虚”,最能贴切莲社主题的意境。
慧远莲社所修净土,注重观想念佛。“观想”又是以“三昧”的境界为前提。何谓三昧?慧远说“专思寂想之谓也”,即心志专一,破除杂念,令虚空自入于心,观照空明,则心境生光。莲社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以“定”纳万物。定则静,静则空,空才能容得下所思、所悟。观想的境界,亦如同庄子所说:“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文人士夫爱养精神,洒扫庭除、焚香静坐,无杂念、不昏沉,就不怕出口无文字、下笔无神气。
现实世界中,纤尘不染之物,常常能引人入境,令心有所寄寓,或有所参悟。唐代白居易,效仿慧远,在香山种白莲、修净土,自号香山居士,他欣赏素屏的不文不饰、不丹不青:“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好与素屏为伴,并且将它比作皎白的明月、素洁的白云,用它自况高尚的品格。有心之人爱纸,如白居易爱素屏。宋代李德茂在其《书城四友序》中形容纸张“悃愊无华,见地明白”,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了道的哲人,褪去世俗习气,对事理、物理融会贯通,辩才无碍。
形而下的纸张之白,可对应形而上的境界之空。画家以洁白紧密的“光熟纸”创作莲社主题绘画,将“白”活用,化为东林结社之圣境,“随类赋彩”亦不过如此。言至于此,我们不免问绢本莲社图主题绘画又如何?历来绢本绘画多设色,它们在发挥绘画“成教化”的本来功用时,对布衣白丁而言,更具说明性。而文人士夫遣怀舒心,复写经典,不仅在精神上意追古人,更要在笔意上多用苦心。据此,我们不免猜测,辽博本莲社图的作者,是否出于莲社的意境而精心挑选质地上乘的纸张作画。即便作者仅是因为传习李公麟真迹而沿用上好的“光熟纸”,但素净的纸张恰如其分地突出了莲社题材的意境,情景相会,对后世观者而言,确实更引人入胜。
结语
本文围绕“光熟纸”“滑、净、软、熟”的特性,从笔墨语言、保存现状、装潢样式等方面,研究辽宁省博物馆藏《白莲社图》的芯子用纸及其艺术表达,获得了几点认知。
一、作为装潢的对象,质地尤佳的“光熟纸”为书画保藏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得益于“光熟纸”柔韧的特性,辽博本莲社图在历经多次装裱、修复之后,如今仍能以手卷的样式递藏;二、卷中经笺引首、折边,具有上乘“光熟纸”坚韧的特性,也蕴含着辽博本莲社图独特的装潢之美;三、“光熟纸”的“滑”“熟”特性,可令笔锋肆意运转,发墨色之穷尽,辽博本莲社图芯子质地光滑、紧密,比绢本可表现更细腻、丰富的勾勒用笔,比生纸可表现层次明朗的墨色变化;四、“光熟纸”的素净,在意象上如一虚空,能容笔毫万象,与莲社主题绘画中的净土思想相照应,引观者流连于莲社圣境。
“光熟纸”一词不是古之既有,而是吴湖帆先生对明代之前书画主流用纸的概括性命名,它的提出,启发了我们关注书画与材料之间的必有关系。本文希望,通过这一例研究,引发更多的学者参与思考,令“光熟纸”这一蒙尘之珠函幽育明,亦使得我们从完整中国画学的视角获得品鉴书画材料及其艺术表达的视野。
图1(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来源:《宋画全集》。
图2(南宋)佚名,莲社图,绢本,设色,纵92厘米,横53.8厘米,南京市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展览现场拍摄。
图3(北宋)佚名,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9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局部)。来源:中华珍宝馆。
图4(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5(北宋)赵佶,池塘晚秋图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237.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6(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7 笔者制作的蜡笺,落墨后的白筋。来源:笔者拍摄。
图8(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9(北宋)苏轼,洞庭中山二赋,纸本,纵28.3厘米,横306厘米,吉林省博物院藏。来源:中华珍宝馆。
图10 辽博本莲社图引首印记。来源:《宋画全集》。
图11 “倪仁禀”印记。来源:《金粟寺史料》。
图12(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13(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绢本,水墨,纵57.7厘米,横1175厘米,王季迁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14(北宋)李公麟(传),西岳降灵图,绢本,水墨,纵26.5,横513.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15(北宋)米芾,行书三札卷,纸本,行书,纵33.3厘米,横123.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卷末王铎题跋。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16(北宋)米芾,公议帖,纸本,行书,纵30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17 辽博本莲社图人物用笔与“永”字八法用笔对照。来源:笔者自制。
图18(南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纸本,水墨,纵19.8厘米,横28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19(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纸本,水墨,纵81.2厘米,横30.4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0(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1(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2(明)文征明,听竹图,纸本,水墨,纵94.5厘米,横30.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明四大家特展:文征明》。
图23(北宋)赵佶,柳鸦芦雁图,纸本,水墨,纵34厘米,横223.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4(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5(宋)佚名,九歌图,纸本,水墨,纵40厘米,横889.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
图26(宋)佚名,九歌图,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734厘米,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中《宋画全集》。
图27(北宋)张激,白莲社图,纸本,水墨,纵35厘米,横84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局部)。来源:《宋画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