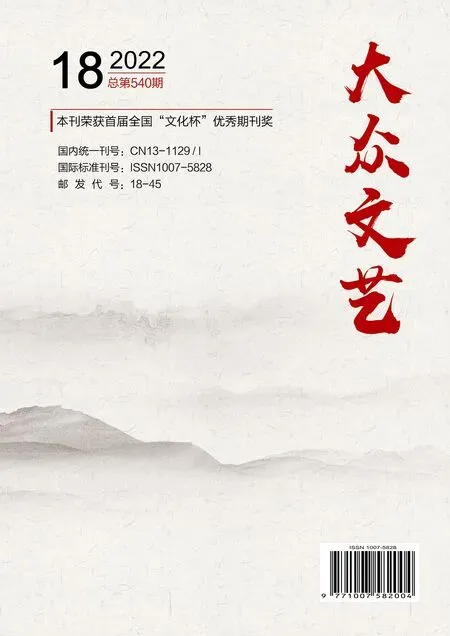静止的困境:探析《电车狂》中的人物与主题书写
杨一欣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91)
一、英雄与英雄的补集
《电车狂》作为黑泽明创作生涯中第一部彩色电影,似乎从某种角度看来,又是黑泽明最为灰暗的影片之一。追溯黑泽明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存有的是一种对英雄人物,抑或是武士道精神的奇特情结——《七武士》是对英雄化身的认可与褒扬,而《乱》却是对武士这一传统英雄形象分裂异化的设问,甚至到《生之欲》或是晚年最后一部作品《袅袅夕阳情》,黑泽明虽然善于书写悲剧性的英雄史诗,但他仍旧期望在寻常个体身上,找到对英雄形象的此心相似的注解。
在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理论中,经典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属于“英雄”一类,而此类角色在整个故事中都要与一个来自外界的冲突做对抗,并在一个封闭时间与空间内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欲求。但善读好莱坞典籍,并对好莱坞创作者影响颇深的黑泽明一反他对经典理论的熟稔,在《电车狂》这部影片中,他并没有刻画一个传统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让从未踏上“英雄之旅”的银幕群像,共同成为一部完整电影长片的集体主人公。
在黑泽明的镜头中,小人物可能会有迷惘和软肋,但黑泽明仍旧相信个体的力量可以改变和造就群体的福泽,即便英雄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孤独,却决不会孤单。甚至如同《袅袅夕阳情》中,始终对人生问题追问“得未”“未得”的内田教授,也有一帮无比忠心爱戴的学生来为他做出热切的回答。换言之,黑泽明始终相信的,是一个人或许可以感召另外的人,一个追寻目标的个体可以唤起另一股集体的决心。就像《生之欲》的结尾葬礼上,渡边勘治的同事仍会表现自己的悔悟,以此反证黑泽明自己对“道不孤”的信心。
但《电车狂》不仅脱离了对单一主角的描摹,成了对在宛若垃圾场的乡村生活群像的刻画,而且事实上观众不难发现,《电车狂》中的每一个家庭,似乎并不交集它们的关系,互通它们的悲欢:从一开始的“电车白痴”小六,再到打散工的增田河口夫妇,以及患有痉挛和短腿的岛悠吉、被姨夫性侵泄欲的胜子……《电车狂》在长达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长中,毫不疲倦地描画了数对各不相同却又各有“病症”的家庭。与其说这是向心的叙事策略,倒不如说这更像借某一个共同的地点,将各具不同的家庭苦难史分别叙述而出。百年前托尔斯泰曾提笔感喟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点上,同样具有人文气质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者黑泽明,秉持了同托尔斯泰一样的想法。
如果说,以往的黑泽明是经典式的,莎翁式的,那么此次的银幕刻画,则不再让他一贯具有史诗气质的角色,走上那条惯常通往悲剧又带有乐观情结的英雄之旅。在罗伯特·麦基看来,故事中的人物总要以行动追寻自己的欲求,而在《电车狂》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像是中国画作散点透视中的一角,他们各自为营,也不期望并无法期望自己能够踏上一条预设终点的旅途。
穷街陋巷,三教九流,比邻而居……这些烟火味十足的底层群众,在黑泽明的幕布中,不仅替代了那些舞刀弄剑的武士贵族,并且独守自己的陋室一角,共同组成了一首有关底层家庭的咏叹调。换言之,在这出两个多小时时长的电影中,观众很难判断谁才是真正的主角,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泽明的呈现重心,已经从单一的英雄人物,转移到了日本底层民众——这些传统英雄人物的补集之上。
二、现实困境的符号意指
在克里斯蒂安·麦茨看来:“电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现想象界,而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为一个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从某个角度来说,电影的本质叙事,就是依靠符号的构建来展示作者的表达。但颇为微妙的是,黑泽明不仅在《电车狂》中设计了许多特别的符号,并且在此基础上,他更依靠人物群像来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从而完成对主题的指涉。
《电车狂》的开头展示的是一个长相颇为古怪的男孩小六——他剃着近乎青皮的平头,穿着一身服务员式的旧西装,整个脑袋也大得出奇。而他的母亲正近乎疯狂地朝神龛大声祈祷,在观众看来,似乎在这个家庭中,“有问题”的人是他的母亲。但实际上,这是黑泽明在叙事上做的一个小技巧:紧接着小六不仅安慰母亲,并称自己“再不走就来不及上班了”。于是观众看着他戴上脏兮兮的手套,系好自己的皮带,在好似虚幻又仿佛真实的电车声中,拿起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具,开始他对想象中“电车”的驾驶。直到此时,墙上贴满的蜡笔画才以近景显出它的内容:上面全都是对电车近乎疯狂般的涂抹描绘。
以小六这对“电车”的癫狂患者作为开头,事实上颇具意味:从符号角度来说,电车不仅是现代化的象征,也是日本“劳碌”大众的符号意指。其“dodesukaden”的声响,不仅是小六古怪的呢喃,也是这一工具宣告发动的声响;而让正处青少年的小六作为这一“电车狂”的具体对象,也使得这种穷苦不幸有了更为深刻悲哀的底色。当小六穿戴整齐,走到屋外用规规矩矩的动作完成他以为的电车运行操作(如打开车门,擦拭车窗,嘀咕保养人员不卖力),然后驾驶着并不存在的电车,横冲直撞地“行驶”在垃圾堆似的乡村中时,他不仅具有遭受遗弃,承受贫苦的不幸少年的缩影,而且更具备“电车”这一他想到痴狂的对象所散发的涵指意味。在对小六的刻画中,黑泽明的镜头不仅钟于停留,剪辑不多,而且在给予其全景从下摇上的客观镜头后,黑泽明对应地给了一个小六视点的摇晃主观镜头。可以说,黑泽明并不带有消费的心态,而更近于以一种体恤的方式,去直面这种不幸的荒诞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用小六作为《电车狂》这些不幸缩影的提领开头,在本质上具有一种更为纯粹的意蕴:他对电车的想象驾驶,实际上成了一种特殊的仪式——对现代工具的渴望和追求,却成为如同癫狂的病症,而这些不幸的结果,最终投射在下一代即青年儿童身上。
另外一处颇值一提的,是接在小六出场后患有面部痉挛和短腿的岛悠吉。他穿戴齐整,衣着考究,正颇为礼貌地冲聚在一块儿洗衣的妇女们打招呼,结果过不多时便突然面部痉挛起来。洗衣服的妇女们在本片中极为巧妙地充当了许多“旁观者”的角色:在一方面,她们起到了介绍的作用,譬如看似在谈论有关如岛悠吉、增田河口夫妇等人的具体信息,实际上在为观众介绍人物;另一方面,她们也通过各具性格的对话,坦陈出这些女性对某一个家庭的议论,而她们的态度就显露于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之中。颇为有趣的是,这些洗衣服的妇女们所聚集的地方,正是这堆破旧屋子前空地的中心处,她们围绕所接水的源头,也恰好形成了一个向心的中心点,而她们聚集的谈论,事实上也成为四散辐射的舆论,成了电影借她们之口所塑造的“旁观者见”。
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角色,或诉说或展现着自己的故事,而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自身的生活困境,共同构成了《电车狂》的言说本身。甚至,为了让他们在镜头前呈现得更为自然,黑泽明放弃一贯的精密排练,而选择更多地让演员在开拍时即兴表演。而正是这种与黑泽明以往动态风格不太一致的“静态”呈现,使那形态各异但又各有苦衷的人物生活,成了整部电影最重要的影像能指。
实际上,黑泽明一直是一个惯用电影符号来叙事的大师。譬如在他的早期作品《野良犬》中,他让一个年轻的警察在一个热天午后,不小心丢失了随身的手枪,而全片几乎就是在讲述一个急躁的青年警察寻找配枪的故事。从符号的文本去分析,寻枪不仅是寻找一个丢失的物件,同样也是以象形的相似性去指代一个男性的尊严,并用文化意涵,去用丢枪来指代日本战后政府对威权与社会公信力的遗失。而在《电车狂》中,黑泽明自然对这种创作的手法举重若轻,但他更删繁就简,令一个角色为另一个角色铺垫,并用这些角色所组成的组群,共同去构建出了一幅有关日本当代底层社会的画卷。
那一扇扇时时紧闭又不知何时开启的家门,那一张张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所往的麻木面孔,组成了一个既指代日本,也指代全人类的符号——黑泽明用它来反诘世界,并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一样,去对遭逢苦难的人类,投去关切的目光。从这点来说,《电车狂》不仅由一个个符号构成,它自身或许也成了某个深刻的符号。
三、悲剧中人物的自洽
善于描绘悲剧的黑泽明,无论是在《乱》还是在《七武士》中,都喜好将爱恨情仇讲述得跌宕和深邃,而他也善于将有价值之物高高捧起,再毫不留情地打得稀碎。但在《电车狂》中,黑泽明似乎对悲剧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悲剧必备的调和统一,也不再抱有热情——他将镜头对准穷街陋巷的每一处,而这些角落的角落,不仅不具有生机上扬的可能,连消亡和牺牲都是默不作声的。
从另外一个颇具悲哀底色的人物——被姨父性侵的胜子身上,我们似乎更进一步,能看到黑泽明对“悲剧”演绎的反思:
在影片大致第20分钟处,我们看到黑泽明给了胜子的家庭一个固定的长镜头:胜子坐在画面前景的右下角,一声不吭地干着女红方面的活儿,而她的姨父坐在画面后景的右上角,背对着观众,正一边大口喝着酒一边大肆谈论着不着边际的话。从他的话中,观众可以了解到,胜子不仅寄人篱下,而且亲生的阿姨住院了,现在需要干大量的活计来补贴家用。紧接着是送酒人来了,观众很快发现,送酒的男青年同胜子之间似乎有暧昧的情愫。但即使送酒青年忧心地说“你又瘦了”,胜子仍旧是一幅迷离无力的神情,而这种神情一直贯穿着影片中胜子出场的每一个镜头。这也暗示着胜子早已被劳力的工作、不幸的家庭关系压抑得几近麻木。甚至换言之,这一个家庭的主角自然是胜子,而她所展现的一个特殊主题,或许便是这种异化家庭关系中的“麻木”状态——面对生活的难题,只能逆来顺受,用沉默捱下所有的苦难。于是,在影片的后半段,姨父真的如禽兽一般侵犯了胜子,后者对此也几乎不做任何神色上的改写,而对于送酒青年的关切,她也显得无动于衷。
对于《电车狂》的相应困境,黑泽明并没有像以往他对“英雄”或是“解救者”的特殊情结一样,设计一个救人于苦海的角色,甚至就连遭遇困境的角色自己,陷于矛盾中也便溺于矛盾的僵局中,他们对生活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盼愿,也对自救提不起兴趣,而所谓的希望和生机,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从未想到的东西。或者,在某一个方面来说,此时作为导演的黑泽明考察的并不是宏观的“史诗命题”,而是聚于微观的“家庭议题”,而对于后者,他显然并不抱有那种洋溢于《生之欲》或《袅袅夕阳情》中“道不孤”的信心和希望。如果说《电车狂》中如胜子这样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潭死水的话,那么这些人物及其故事的各自终点,似乎也只是如水消失在水中。
对于这一点,在《电车狂》中对岛悠吉的描绘颇可佐证:在影片后半段,几个同事一起来到岛悠吉的家中,但岛悠吉的妻子却颇不耐烦,将面前的几人视为空气,不做招待便自顾自地出门洗澡。同事们看不下去,在岛悠吉面前直接吐出了对其妻子的不满,并一边为岛悠吉说话,一边为其感到不值。没想到,岛悠吉大为光火,直接摁倒了同事,称对方并不懂妻子在从前如何和他一起忍耐贫穷,一边为他付出一边为他牺牲。从这个颇为微妙的段落看来,黑泽明设置这些并不太多“纠缠”的家庭苦难,事实上或许也已经展现了他的态度——就如同上文提道的托尔斯泰的那句话:“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这些不幸事实上是由不同的家庭条件,生活环境,个体情感交织而成,而这种不幸也是被当事人消化和自洽的。或许,在黑泽明看来,在具体的家庭困境中,旁人很难去充当一个粗泛的解救者,而也很难真正介入到另一个个体具体而微的生活之中。而这些从未踏上过英雄之旅,也不曾有过具体欲求与终点的故事人物,会如同现实中的每一个底层居民一样,不仅同上路追寻无缘,而是渐渐在生活中溺水消失,并始终与故事宏观叙事中的一波三折,三幕推演没有任何的关联。
也就如在影片之中作为穿插段落,也意在表现黑泽明自身态度的段落戏里,始终有一个陪着小乞丐侃侃而谈日本建筑的老乞丐。他们两人虽然总在梦中建造属于他们的精舍,但实际上却只能卧睡在废弃的汽车之中。老乞丐对于“理想房子”的向往,也同《电车狂》中无处不在的破旧、荒芜、废弃和失落成为反差极强的对比。而到了结尾,当小乞丐中毒近死,老乞丐悲哀到近乎疯狂,却始终无法时,我们才发现精神的“富裕”,事实上仍旧解决不了现实的悲哀。或许,在这一点上,才是有关“悲哀”最为悲哀的答案。
黑泽明对此最消沉的态度或许颇能展现于老乞丐的境遇上:旁人很难介入你的生活,他最多陪你一起挖坟。但事实上,每一个人自己的坟墓,早就被自己挖好了。
结语
作为黑泽明晚年无论在票房与口碑上,都不算太成功的作品,《电车狂》实际上带有黑泽明自身的反思和感喟。无论是从传统的人物构建方面,还是从符号呈现,及主题表达上来说,《电车狂》都算是黑泽明对悲剧故事的某种颇为悲观的自反。
作为一个伟大的导演,黑泽明似乎颇为敏锐地察觉到:悲剧并非一定在英雄人物身上上演,它也出没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面对悲剧,真正现实的做法或许只能是让个体去消化和自洽。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对现当代导演与剧作创作跳脱传统模式,更紧贴现实基底,在人物塑造与主题呈现上,提供了他自己独特的方法论。
①刘迎新,曲涌旭.日本民族性对日本电影的影响[J].文艺争鸣,2020.(02):190-193.
②[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③唐纳德·里奇[M].黑泽明的电影:海南出版社,2010:259-273.
④吴文忠,凃力.浅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J].人民论坛,2011.02.001:21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