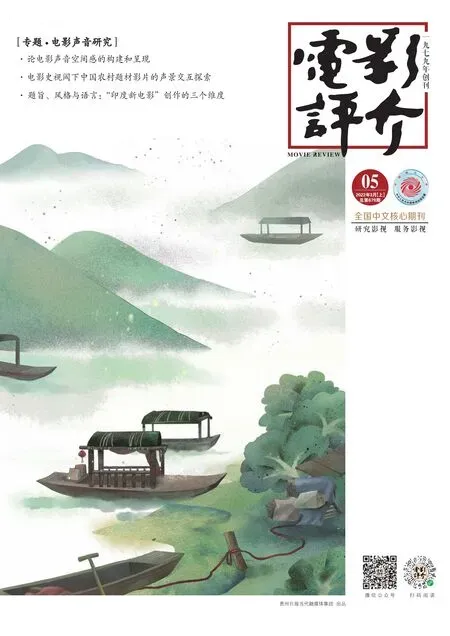题旨、风格与语言:“印度新电影”创作的三个维度
范小玲
印度电影在观众印象中普遍都是“穿插歌舞”“载歌载舞”,而这似乎也成为印度电影叙事的固定模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印度新电影”,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及富含思考的表达,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
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主导下,印度仿照法国的“电影高等研究院”建立“印度影视学院”,成立收藏世界各国大量经典影片的国家电影资料馆,创办电影资金公司,使资助拍摄的“非商业性”影片制度化。伴随制片与发行方式的改变,电影创作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催生出与主流电影直接对峙的“印度新电影”。
印度新电影整体在银幕上呈现出大众的生存困境与人生的惶恐。创作者“认为有责任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奋斗,不仅抨击贫富悬殊,还要用传统的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对社会弊病的抨击”。印度新电影从叙事模式到主题表达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电影植根于印度社会文化,表达深刻的哲理,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与现实主义传统。2019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回顾/致敬”单元展映了10余部印度新电影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一、关注社会现实,题材呈现大众化
从某种角度来讲,题材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印度新电影创作者普遍关注现实,选取现实题材,并将自身价值观融入电影。可以说,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包括文化的分离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印度新电影聚焦社会发展变革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关注底层人物命运,题材呈现大众化。
电影《我们每日的面包》(玛尼·考尔,1969),讲述客车司机辛格与妻子贝罗、贝罗妹妹与詹吉之间的关系。辛格每天开车在乡村穿行,他的妻子贝罗拿着食物在路边等待。有一天,妻子由于妹妹贝罗遭到骚扰来晚了,丈夫因妻子迟到生气而拒绝接受妻子送的食物,开车走了,妻子贝罗则站在路边一直到天黑。整部电影基于相对客观的视角,探讨印度社会的家庭关系以及面临的困惑,聚焦日常单一的“粗颗粒”生活现状,影像表达冷静隐忍,同时该片具有实验性、探索性特征,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艺术创作关注现实,个性化明显,被大家公认为开创了印度新电影的先河。
电影《自己的选择》(阿多尔·戈帕莱克里什汗,1972),用平实冷静的态度表达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观察。电影讲述一对接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抱负,工作努力的青年夫妻维斯瓦纳坦和西塔,为了爱脱离父母的束缚,但由于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窘迫的境遇。维斯瓦纳坦和西塔从城里搬到乡下生活,与赌徒、盗窃犯为邻。青年夫妻起早贪黑劳作,依旧入不敷出且负债累累。从城镇到乡村,电影展现出众生百态,不同人物几乎同一命运的潦倒境遇,是印度特定时期民众生活的缩影,社会问题凸显。电影黑白影像充满极具质感与现实主义的表达手法,不炫技、不张扬、不做作,将故事娓娓道来。主人公维斯瓦纳坦和西塔的命运是当时印度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折射出一批“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反映出社会现实问题。创作者的真诚使其双眼未被尘世的浑浊所蒙蔽,镜头里既有真善,也有伪丑,但是创作者对电影中各人物的同情,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社会,表达了大众个体是无辜的创作立场。
电影《出租车男》(李维克·加塔克,1957),揭露民众的现实生活。电影讲述出租车司机毕马尔与破旧汽车“相处”的故事,采用线性叙事的手法,将滑稽戏剧与悲剧情节相融合,亦喜亦悲,从人物夸张化的表演中能看到舞台剧表演的影子,质朴的镜头语言展现出印度当地的风土人情及群众日常生活场面,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将破旧的汽车搬上银幕并作为与主角“形影不离”的表现对象,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中并不多见,这部电影的出现为印度新电影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电影《马戏帐篷》(葛文丹·阿拉文旦,1978),纪录片式的拍摄将镜头聚焦社会另一类人群——马戏团。马戏团来到村子里,使百姓平静的生活变得热闹起来,奇奇怪怪的马戏人物与朴实的村民融合在一起交叉呈现,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电影自由表达,闹与静交替,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无夸张的渲染,看似平淡、简洁、客观,实则其中隐含种种忧虑与惆怅。马戏团在孩童的簇拥欢叫声中出现,又在孩童奔走欢叫声中离开,热闹过后的村庄重归往日的平静。疲惫的马戏人下一站又会去哪里?一定是重复着往日的轨迹、叙述着昨日的故事,电影展现了一幅印度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人文风情画。片尾马戏小丑吐露心声,使观众与马戏表演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精彩刺激的场面过后引发人们的深思。
电影《摩羯座王宫》(格维单·阿拉维丹,1974),讲述青年学生政治领袖拉维,辗转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寻找就业机会,在此过程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使他对现实产生幻灭。电影以印度抗英争取独立为背景,以理想主义青年拉维参与政治运动后的后续生活状态为重点表现内容,描绘了种种事件,刻画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电影关注社会现实与人物命运,反映出创作者的价值观。
电影《角色》(夏姆·班尼戈尔,1976),以电影明星瓦德卡尔的自传为基础,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命运,讲述乌莎自小跟随奶奶学唱歌,在克沙夫的哄骗下成为一名演员,事业颇有成就但感情生活处处碰壁,展现了乌莎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状态、婚姻状况,起起落落,爱恨交织;刻画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注重挖掘人物内在矛盾,风格呈现多元化
风格即为人格,是借助艺术语言表达创作者的思想、个性、才华等。正如歌德所言:“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标志。所以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印度新电影透过镜头表层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状态,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有机融合,风格呈现多元化。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编剧导演夏姆·班尼戈尔创作的电影《种子》(1973),“1973年当年班尼戈尔38岁,经过12年的长期努力,最终成功上映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乡村地区的压迫以及人间的悲剧故事,聚焦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关系,挖掘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关注人物命运,以少爷苏亚与仆人拉什米为主角,以两家人的生活境遇与命运为展衍,辐射至不同阶层。权贵阶层的少爷苏亚高高在上,属于思想高超、地位超然的人,而电影却将其刻画成胆小、懦弱、粗暴、自私、没有担当的“伪男子”。他诱惑聋哑农民基什提亚年轻漂亮的妻子拉什米,并使其怀孕。拉什米的丈夫以为是自己的孩子,高兴至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少爷,少爷害怕事情暴露,把可怜的聋哑农民打得半死,于是拉什米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向少爷发出控诉。整部电影剧情起伏、戏剧冲突、角色之间关系的变化处理有理有据;叙事张弛有度,人物形象刻画细致、人物塑造饱满且笔墨浓淡相宜。电影叙事与环境氛围紧密相连,影像表达注重景深镜头的运用,电影中多处前后景关系的调度与设置蕴意深刻,精巧的场面调度把人物关系的变化、人物命运的发展体现得微妙准确、恰到好处。电影结尾处小孩子往少爷家窗户扔石头后跑掉的镜头,既有趣味,又意味深长,体现出新一代被压迫者反抗意识的萌芽,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夏姆·班尼戈尔曾说“我崇拜许多印度电影导演,但是其中最有能力的是萨蒂吉亚特·雷伊。在电影世界,雷伊的出现无疑是一场革命”“什么是好的电影以及好电影的标准,都来自萨蒂吉亚特·雷伊”“萨蒂吉亚特·雷伊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似乎就是那种人,他拍的电影就是我想做的。他是一个领路人的角色,他很喜欢《种子》,并对此大加赞赏。”“夏姆·班尼戈尔的电影成为印度宝莱坞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这是第一部打破宝莱坞电影框架的作品。”电影《种子》极具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可谓雅俗共赏,是电影史中难得的佳作典范。
马克思曾指出:“部落之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到《梨俱吠陀》时代末期,随着雅利安人在西北印度定居和向恒河上游的扩张,其内部阶级风化逐渐清晰,相应的社会劳动分工也已形成,于是在古代奴隶社会称为‘瓦尔那’制度有了新的划分,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可以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1947年印度脱离殖民体系独立后,各种种姓分类与歧视被视为“非法行为”,然而在实际社会运作与生活中,其仍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电影《婆罗门村的驴》(约翰·亚伯拉罕,1977),从叙事层面来看,电影讲述了人与驴子的故事,实质是在讽刺种姓制度下婆罗门阶层的偏执、自私和愚蠢。电影看似客观的叙事却蕴含着作者的观点立场与判断,反讽隐喻似乎在阐释关于“智”与“愚”的古老哲学命题。电影采用打破常规的叙事手法,由村民、哑女乌玛等人讲述电影情节,借助动作关系直观体现人物关系的渐变,如:男青年与哑女的三次相遇,第一次哑女果断甩开手,第二次轻轻拿开手,第三次抓着手。电影语言表达独具匠心,风格独特。以驴子作为叙事中心,表面来看是揭露人和驴子的矛盾冲突,实质是在揭示婆罗门与村民不可调和的阶层矛盾。
电影《云遮星》(李维克·加塔克,1960),描绘了难民妮塔一家人的生活情况,镜头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了一段苦难的人生,似一曲不堪吟唱的时代悲歌。电影注重表达与揭示人物内心,多次运用长镜头将整场戏的情绪与不同人物之间微妙的内心捕捉揭示得淋漓尽致。电影中类似虫鸣、鸟叫的声音有序组织,呈现出音响音乐化处理的效果,这种声音看似每次在人物情感出现动荡时不经意出现,实则是创作者用以营造紧张、焦躁、不安的电影情绪的表现手法。在特定时期,无论是从观念还是手法来说,能够在电影中如此巧妙灵活地运用声音,值得称道,成为后人研究电影声音运用的典范。
电影《幻境》(库马尔·沙哈尼,1972),以印度独立为背景,讲述富裕家庭的女儿塔兰每天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出现,改变了塔兰的生活轨迹。然而父亲的独断专行使塔兰陷入困境。电影体现出父权秩序对女性的压制,使用大量的内心独白深入剖析塔兰的内心世界。
电影《自己的选择》(阿多尔·柯普莱克里什汗,1972),场景选择紧贴电影情绪与人物命运的表达,自然光效的运用与环境声紧密结合,刻画出人物形象与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电影节奏控制张弛有度,情绪推进细致入微。电影空间对比、声音音响对比构思巧妙,环境音响如海浪声、锯木厂的环境声、旅馆外环境声、农村出租屋外环境声等的对比变化,体现出电影人物情绪、性格的变化,对挖掘人物内在矛盾起到积极作用。主人公维斯瓦纳坦的孩子出生了,自己却因没钱治病而离世,独自抚养孩子的妻子西塔该何去何从?电影始终关注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充分调动观众的观影心理。电影揭露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引人深思。片尾女主角斜侧着脸、瞪着镜头看着画外,将整部电影的情绪延展推进并实现升华。
三、注重探索视听语言,叙事手法呈现多样化
印度新电影的创作者以艺术家身份展现对国家、政治的思考,体现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电影未使用印度歌舞片这一久负盛名的电影类型叙事,而是充分拓展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手法。这一时期的印度电影朴实无华,创作者认真思考、真诚表达,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技巧的玩味,叙事手法呈现多样化。
电影《婆罗门村的驴》的影像与声音表达较为特别,注重后期声音的挖掘利用,电影叙事简洁,主观化表达意识明显,具有较强的戏剧性,渗透着较为深刻而尖锐的文化隐喻。摄影机推、拉、摇的运用较为频繁。声音运用较为独到,比如,那拉斯瓦维教授卧床读书端详驴子时,声音运用男声无伴奏“哼鸣”独特的表现手法;巫师宣布厄运要降临村庄时,声音运用驴子有节奏的惨叫与音乐进行有机融合,音响音乐化的运用极具特色。
电影《自己的选择》《出租车男》是线性叙事,而电影《角色》即是现实时空与过去时空结合、多时空交叉叙事。电影以乌莎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经历为主轴,将碎片化、片段化的表达揉进叙事主轴,现实时空的音乐与非现实时空的音乐交替,使电影情绪表达更加丰富,时空转换自如巧妙,特别是唱片传出奶奶唱的“弹着竖琴,唱起歌”作为重要的情感寄托,拓展延伸了乌莎的情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电影中插入新闻播报作为背景,借助典型且重要的政治历史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明显、时间跨度大。大时代、小人物,这或许是创作者表达的重点,人物命运与时代发展亦离亦趋。乌莎的人生表面看似热闹,实则内心孤独无助,无论人物身居逼仄亦或宽敞的空间,对乌莎而言自由成为奢望,奶奶、母亲、乌莎、女儿命运依旧亦或会有转折?开放式的结尾充分延展了电影情绪,引人思考。
电影《双重意识》(玛尼·考尔,1973),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讲述住在菩提树上的灵魂对美貌的新娘一见钟情,灵魂变换成新郎的模样,与新娘共同生活。新娘怀孕了,在外地工作的新郎十分诧异,急忙赶回家,却被家人认为是“冒牌货”。电影刻画了极具趣味性的传奇故事,以全知、全能视角进行讲述,包含诱惑与坚守、情感与金钱、真与假、善与恶、智慧与单纯,揭露出当地女性的生存状态。电影大量运用推镜头的视角,深入人物内心深处;借助大量特写镜头,强调人物的存在状态,手法简单、质朴,传奇故事的现实主义表达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性与真诚感。遗憾的是,整部电影制作相对简陋,影像声音剪辑较为生硬,但其价值在于体现在电影语言表现方面的较强探索性。
电影《种子》的整体色调较为浓郁,印度热带季风气候特有的燥热,成为电影人物躁动不安的有机映射。电影外景呈现广袤的热带植物园环境,人物在特有环境下的行为动作、日常起居,极具合理性。从电影的整体色彩到局部色块,都准确表达了人物的情绪,起到衬托角色内心的作用。
电影《肖姆先生》(莫利奈·森,1969),以全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向观众传授换个心情生活、换个角度看问题、换个身份评价、换个方式相处的人生哲学。电影以现实主义手法表达,呈现出轻喜剧风格,表现铁路官员布万·肖姆的人生片段,讲述肖姆工作、爱情等方面的简单故事,其中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电影开放与封闭的空间形成对比,动画元素的加入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形式。电影人物调度巧妙,镜头运用简洁却恰到好处,体现出创作者扎实的电影语言运用功底。
印度新电影在语言探索过程中与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整合,形成自身独特的影像系统与叙事语言体系。
结语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把资金投入转到电视行业,加之电影发行网络未及时跟进,使曾经风光一时的印度新电影计划被搁置。电影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名片或窗口,要有自身的精神内蕴与文化价值的思考,应该表达时代的文化价值追求或反映社会状况与文化的症候。从该角度来讲,印度新电影给各国电影人带来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