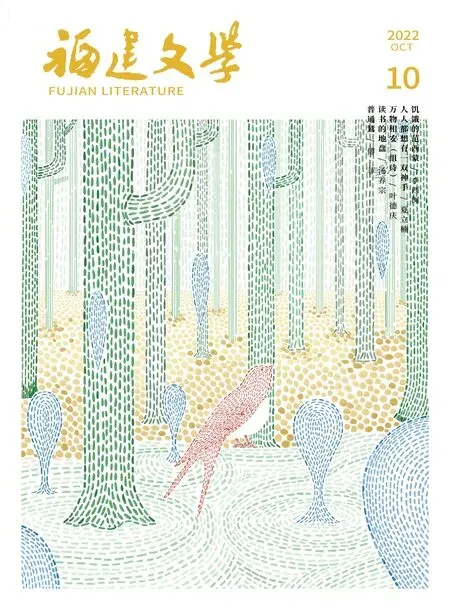人人都想有一双神手
夏立楠
1
刘杨俊垫了三块砖,才够到窗台上。食堂师傅正在炒菜,没发现我们俩。味儿特浓,没到饭点,我们俩的肚子就都咕噜噜地叫了。菜是莲花白,切得大块大块的。炒菜的铲子跟我爸铲灰浆的一样大。我说,刘杨俊,你看到没?那铲子可真够大的。刘杨俊说,这还用你说,我早就知道了。我不高兴地乜了他一眼。刘杨俊说,你猜我昨天看见啥了。我说,啥?刘杨俊说,我看见张三头家院子里有个盆,里面能摸出东西来。我说,你讲的啥,我没明白。刘杨俊说,就是他家鸡圈上有个胶盆,盆上盖着个黑色塑料袋,我看见他手伸进盆里摸出一瓶酒来,是白烧。我说,他藏盆里的?刘杨俊故作认真,说不晓得呢,他拿了一瓶白烧后还拿了一瓶醋。
我说,人家藏盆里的吧。刘杨俊说,这用得着藏嘛,咋不直接放屋里,非要搁院子里?我琢磨着也是。我说,那你给我说这个干啥?刘杨俊说,你没发现那老头很怪吗?
张三头的怪,不用刘杨俊说我也知道。平时上下工,他都是一个人,不咋跟工友们说话。下了工,别家欢声笑语,要么是看电视,要么是打牌,要么是下棋,就他院门锁得紧紧的,没人晓得他在里头干啥。
见我没说话,刘杨俊又说,我感觉那盆不简单。我说,你啥时候看到的?他说,昨天晌午,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从门缝里瞧见他在院子里生火煮面。我哦了一声,没再说话。他说,你不相信?我说,我没不信。他说,那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我有些迟疑,说,看看那只盆吗?刘杨俊说,是啊。
我们俩从砖头上下来,离饭点还有一会儿,大人们还没收工,我们直接去的张三头家。他家院墙修得高,还插了玻璃碴子。我说,刘杨俊,我们俩怕是爬不进去哦。刘杨俊说,爬不进去没关系,我撑着你呗,你试试能不能瞧见那只盆。说着,刘杨俊弓着腰,趴在张三头家围墙上,示意我站到他肩上。我站在他肩上,果然瞧见院子里有个鸡圈,木头搭的,不过没鸡。鸡圈上有只盆,具体样子跟刘杨俊说的一样。刘杨俊说,你看到没?我说,看到了。他说,能看到里面吗?我说,你再等下。我试着换换角度,但盆让黑色塑料袋盖着,看不出里面是啥。刘杨俊说,我快撑不住了,你快下来吧。我就慢慢下来了。刘杨俊的脸憋得通红。他说,我没骗你吧?我说,没骗我。他说,这老头肯定不简单。我没说话。
那是1996 年春天,工三团在火电厂旁边又修了好几幢宿舍楼。不上课的时候,大人们干活,我跟刘杨俊没人管,就成天瞎转悠。到了饭点,就跟在大人身后去食堂打饭,有时候是白菜炒肉,有时候是青椒炒莲花白,还有些时候是土豆丝。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肚子饿,除了饿还是饿。不知道啥原因,那会儿工人们活没少干,账却不好结。好些时候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张三头家里的盆能藏酒,还能摸出醋瓶子,那不是一件小事,至少在我们看来,跟变戏法似的。
晚上,我爸坐在屋里跟王伯伯下象棋。我妈吃完饭,碗筷也不洗,撂下一句话,老夏,记得洗碗,别等下忘记了,《香帅传奇》马上要播了,我先看电视去。说着,我妈兴高采烈地溜了。王伯伯瞅我爸一眼,像是有啥话要说却又没说。我爸说,下棋下棋,我要飞象了啊,你看好。王伯伯说,飞啊,只要你不怕我的马踏你,你就飞吧。
我对象棋没兴趣,也没到我有兴趣的年纪。我喜欢的,是有事没事挂着个弹弓在小河边走,见鸟射鸟,见瓶子射瓶子。我靶子不准,没射中过鸟。刘杨俊射中过一次,不过他力气也不大,那鸟掉了几撮毛后,腾地一下子飞出树冠,活得好好的。
我躺在床上,寻思着张三头家那只盆的事。没敢跟我爸妈说,觉得这是我跟刘杨俊之间的秘密。我跟刘杨俊商量好了,他家离张三头家近,改天中午,他再悄悄去一趟,要是还能瞅见张三头从里面摸出东西,这事就可以断定真不简单了。刘杨俊说,他要真能再摸出东西,我就想办法偷走那只盆。我没说话,心想这事要是被人家发现就惨了。刘杨俊笑呵呵地说,我眼尖,个头小,就算被他发现了,跑起来贼快,他也抓不到我,周边小孩多了,他也不知道我是哪家的。
通过几天的观察,刘杨俊有了结论,他在我面前嘀咕,说不简单啊不简单。我说,那盆真有问题?他郑重其事,嗯,我看到他从里面摸出一把挂面来,崭新的。我说,那你接下来真要去偷盆?刘杨俊点点头,说你不想吗?我说,我怕。刘杨俊说,瞧你那怂样,用我妈的话说,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你怕个锤子。他这话不受听,我有些不爽。他又自言自语,真是个神奇的盆啊,要是是我的多好,就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他这么说,我眼前已经浮现起泡泡糖、干脆面、唐僧肉等吃食。我说,他家墙上有玻璃碴子。他说,怕啥?我家有梯子,我们抬梯子过去,再找根竹竿,竹竿上装个钩子,不就勾过来了?我真为他的聪明感到惊讶,看来他早有预谋,同样大的刘杨俊智商显然高出我大半截。我说,不过我还是担心。你担心个啥?你别再说这句话了,听着就烦。我说,那天我看到他家围墙是一面砖砌的,梯子那么沉,搭上面会不会垮?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年前刮过几次大风,我家院墙被吹倒了,就是一面砖砌的,我爸气得火冒三丈,骂骂咧咧地又砌了一遍。刘杨俊说,别想那么多了,想太多啥都干不成,这是我爸的原话,你怕的话,我去爬,我轻。我想了想说,好吧。
从刘杨俊家抬着梯子到张三头家门口,我们俩不停地环视周围,生怕有人发现。梯子搭在墙上,我在下面撑着刘杨俊,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墙。他说,递竿子给我。我把竹竿递给他。他双手撑着竿子,不停朝地鸡圈方向够。我说,你够着没?他说,差一点,还差一点点。我说,要不要我来?他说,得了吧,还是我来,我再爬一梯试试。他就再爬上一梯。我说,够着没?他说,不行,我手有点短。我说,要不我来吧。他正准备下梯子,我看着头顶上的砖墙慢慢裂开一道缝隙。然后轰的一声,整堵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倒下。
2
我妈问我身上的伤咋回事,我说不小心摔的。我妈就抱怨,一边给我敷药,一边斜视我爸,那意思像是说,都怪你这个没出息的,找不到好的活干,两个大人忙碌,钱没赚着,连带娃也跟着受罪。我爸不知道,背着身子在生炉膛里的火。
好些天,我都没敢再去找刘杨俊,我怕他妈,怕他一五一十说出来。他妈是我们工三团出了名的泼妇,我见过他妈跟人骂街,那架势能顶好几管机关枪,只见嘴皮不停翻动,唾沫星子夹带着各种脏词污字漫天飞舞。她要是晓得,非得把我家门踏破不可。刘杨俊头上的包比我的还大,鼻子还流了不少血。墙倒下的那一刻我们俩都吓坏了,看着灰头土脸的彼此,他灵光一闪,说去溪边洗吧。
好在刘杨俊没计较,他伤还没好完,就又跟我玩了。我拿着弹弓,在巷子里转悠。他坐在地上,手里握着只滚珠。他说,你的弹弓借我玩玩呗。我说,这是我爸给我新做的,你别弄丢了。说着,我取下脖子上的弹弓。他在地上找了颗石子,包在包皮里,向着远处瞄。我说,你别射到我了。他说,不会,我靶子准得很。他一弹弓朝对面墙上射去,石子飞在墙上,溅起小泥块。我说,你没生我气了?他说,我才没生气呢,我爸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要有肚量,再说了,又不是你故意弄的,而且你也受伤了。他能这么说,我还真有点讶异。我说,那你没给你妈说我们俩爬墙的事吧?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反问道,你觉得我有那么傻吗?我说,不傻,不傻。
刘杨俊说,张三头把墙修好了。我说,那么快。他说,是啊,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迟疑着,说他发现就完蛋了,这会儿肯定琢磨着怎么逮弄倒墙的人。刘杨俊说,不晓得了,不过我感觉他没生气,他那个人看不出生气和高兴。说着,刘杨俊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递弹弓给我。他朝着张三头家走去,我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张三头家的院门没上锁,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在家的。我猫着腰蹲在墙根不敢凑近。墙是新砌的,砖缝里的泥也是新的。刘杨俊胆子大,他凑到院门边,眯着眼朝门缝里看。我在后头啥也瞧不见。我说,他那盆还在吗?他说,在的。我说,他咋还没端进屋?刘杨俊说,我咋知道?刘杨俊看得出奇,我再问他话时他就不回我了。我说,你看到啥了啊?他什么也不说。我来了兴致,往前凑,压力太大,刘杨俊反手给我一肘,拐得我胸口痛。我抱怨着,你咋回事?他还是不说话。这会儿,他一下子往后退,我才意识到我们被发现了,连忙起身要跑,刘杨俊却绊到了我,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门开了,是张三头。我们仨彼此对视着。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张三头说,你俩进来。我跟刘杨俊面面相觑,要跑,他一把逮住我俩。
墙咋回事?张三头坐在椅子上问。我说,就是刚才刘杨俊说的那样,不小心给您弄倒的。他沉默地抽着烟。我心里忐忑,不晓得他接下来要干啥。他说,你们好奇那只盆?我跟刘杨俊都点点头。他说,为什么?刘杨俊说,我们觉得你会变戏法。他指着我说,你也这么觉得?我说,嗯,我也觉得你会变戏法。他说,谁告诉你们的?刘杨俊说,我看见的。我说,你能变给我们看看吗?他说,你们想看我变戏法?我们又都点点头。张三头说,那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听他这么说,像是不怪罪我们俩了,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刘杨俊说,什么故事?张三头说,什么故事,你们把我墙弄倒了还好意思问我什么故事。刘杨俊说,你不是说要讲故事的嘛。张三头沉吟片刻,嗯了一声,说一个叫《张三丰盗宝》的故事。我心想,张三丰是谁啊,是张三头他哥吗?张三头像是看出我们的疑惑,解释说张三丰是个传说人物,不过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个人,他的故事很多。刘杨俊说,那你讲讲。张三头深吸一口烟,说好。
古时候,有个地方叫平越,也就是现在贵州的福泉市,那地方住着个民间奇人,叫张三丰,这人高大魁梧,一年四季都喜欢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对自己的形象全然不顾,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邋遢。就是这个张邋遢,别看他样子不咋的,本事却高得很。刘杨俊说,他本事咋高了?张三头说,你别插嘴,听我说。这人有天路过平越街,见到一个小孩披麻戴孝,脖子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卖身葬父”四个字。小孩七八岁,瘦得皮包骨头,很是凄惨。张三丰见后很是同情,就想帮他葬父,于是问他具体情况。小孩说他们家乡遭遇瘟疫了,死的死,逃的逃,全家就剩他父子俩相依为命,跟着流民讨饭到的平越,没想到父亲却又染病死了,丢下他一个人身无分文,只能卖掉自己来安葬父亲。听完小孩的讲述,张三丰感慨道,我有个法子帮你。小孩连忙跪谢,说谢谢恩公,愿来世给您当牛做马。张三丰急忙扶他起来。深夜,张三丰烧香点烛,设了个祭坛,嘴里念着:“奇门老祖,遁甲骨文,日行千里,片刻回程。”念完,他让小孩爬进他的袖口,说里面全是金银珠宝,不过只能拿一样,不能贪心,不能睁眼,哪怕睁一下都不行,爬进去碰到什么就拿什么,得手后赶快退回。说着,小孩就爬进他的袖口里,还没爬几步,手就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你们说他碰到了啥?张三头看着我们俩。刘杨俊说,是拂尘?张三头说,不是。我说,是刀?张三头说,咋可能嘛。刘杨俊说,难不成是银子?张三头说,对。刘杨俊说,我瞎猜的,可我觉得不可能,你不是说他是张邋遢嘛,他哪来的银子?张三头不想解释,说你们不懂,故事里就是这么讲的,说小孩摸到了元宝,他兴奋地伸出两只手到处摸,全是金银珠宝。小孩忍不住了,很想看看这些元宝是不是真的,于是他睁开眼睛,眼前金光闪闪,这哪是什么衣袖,明明是在一间很大的金库里。还有这事?哄小孩的吧?刘杨俊不屑道。张三头说,跟你们说了等于白说。刘杨俊灵机一动,他说,我妈说的,眼见为实,天下哪有这种事?要是钻进一个袖口就能摸到金银,那你们还上什么班?刘杨俊说得理直气壮,张三头无可奈何,说你小子嘴还挺贫的,我就让你俩见识见识啥叫真的隔空取物。张三头这么一说,我俩既诧异又兴奋,心想,这老家伙难不成真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绝技?张三头说,你们俩想要什么?每个人只能说一样。刘杨俊说,我要泡泡糖。我激动着,说我要干脆面。张三头说,好,那你们等着哈。张三头起身,朝鸡圈走去,他的右手伸进盆里,看样子像是在里面抓什么东西,折腾了小会儿,竟然从里面摸出一颗泡泡糖。哇,刘杨俊惊呼。张三头把糖递给他,对我说道,你看清楚了啊。我立在那里,定睛注视他,没一会儿,他从盆里摸出一包干脆面。我没敢接。他说,你拿去啊,怕个啥,是真的。刘杨俊一把帮我接了过去。这个时候,刘杨俊就问道,那个小孩呢,他钻进宝库后怎么回来呢?张三头说,你猜猜,我看你不是挺机敏的嘛。
突然,刘杨俊他妈喊他,再熟悉不过的四川口音,刘杨俊,刘杨俊,你个烂娃仔又跑哪去了?叫你莫乱跑,你硬是一天跑骚气很,又跑哪去了嘛。刘杨俊和我听到他妈的声音,吓得连忙跑出张三头家院子。
3
刘杨俊他妈下的早班,灰浆桶里除了砖刀、勾缝刀,还有只黑色塑料袋,像是装的啥吃食。我跟在她身后,偷偷瞧了瞧,是两包方便面。他妈打开院门,放下桶,让刘杨俊打洗手水。刘杨俊很听话地找来洗手盆,在铁桶里舀了瓢水。
他妈边洗手边说他,哪个娃儿像你浪个野?叫你莫乱跑莫乱跑,就在这个巷子头好好箍(待)起,你硬是不听话,叫坏人抱起走了你才心落,你再乱跑我就把你锁在家里头。说着,一把扭在刘杨俊的耳朵根上,那样子像是有多少气出不完似的。我吓得在后面一动不动。说到锁在家,我妈就锁过我,在家太无聊了,我拧开所有磁带,放在盆里用水洗,洗后发现装不回去了。我爸妈回来,看到盆里一盘乱麻,磁带千缠万搅。我妈气得拎起扫把往我身上抽,我爸只敢看,啥也不敢说。
他妈拧他耳朵时,刘杨俊站着一动不动。不过,我发现他的小拳头握得老紧了。他妈说,小楠,你妈也回来了,估计这会儿正找你呢。我听她这话,晓得是在赶我走。我说,好的,阿姨,那我先回了。走出刘杨俊家,我知道这家伙今晚上完蛋了,少不了挨揍。上次他落下的伤,他妈肯定没少担心。
我还想再回张三头那看看,就又来到他家。透过他家院子的门缝,我看到张三头正蹲在里面削土豆,他身边的铁炉子生着火,有火焰往上蹿。我心想,他这么快就要做饭了啊,他那盆要是什么东西都能捞出来,那么吃的菜肯定也不需要上街买。张三头削好土豆,从屋里拎出一小桶清油,跟我妈平常炒菜一样,洗菜、倒油、炒菜,我没觉得有啥异样。不想再看了,我觉得我该回家了。
我妈正在院子里做饭。我肚子有些饿,又咕噜噜地叫着。食堂包饭,却只包中餐,晚餐工人们要回家自己吃。干一天,还得做饭,真是辛苦得很。我把干脆面往怀里塞,和往常一样推开院门进去。我说,妈,我爸呢?我妈说,你爸有点事,晚点回来,你别乱跑。我快步走进屋,摸出怀里的干脆面,想吃,又觉得可惜,这么好的干脆面,竟然是张三头变出来的,真是神奇。我朝门外看了一眼,我妈背过身的。趁她没注意,我悄悄把干脆面藏床底下了。
吃过晚饭,我爸还没回来,菜搁在桌子上一直没收。我说,妈,你今天不去看《香帅传奇》了?你不是最爱看《香帅传奇》嘛。我妈说,没心情,再说了,你沈姨家没回来,放不了电视。我说,他家人去哪了?我妈说,你一个小孩子,像查户口一样,问那么多干吗?我就没说话了,我妈好像一直在等我爸。我心里纠结,要不要把张三头的事说出来。说吧,怕她知道我弄倒人家院墙会揍我,不说吧,我对张三头盆里能捞出东西这件事迷惑不解。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说吧。我爬到床底下,拿出藏的干脆面。我说,妈,你看这个。我妈说,你从哪来的?我说,你猜。我妈说,买的?我没给你零花钱啊。我摇摇头,说你再猜。我妈说,我猜不到,是不是你拿别人的?你从哪拿的?我说,我没,是别人给我的。我妈说,你撒谎,谁无缘无故会给你这个?我说,真的。我妈说,那你说谁,是不是我们工三团的?你别乱吃乱拿别人东西,妈妈给你说过。我说,我知道,这是张三头给我的。我妈疑惑,他为啥给你这个?我说,他变戏法变出来的。你又在扯谎,我妈一本正经。我说,我没扯谎,你听我慢慢说。
我妈听完我的讲述,面无表情。我说,妈,你说张三头是不是真会变戏法?我妈沉默了片刻,说他会不会变戏法我不知道,这东西你不能要,以后别人拿东西给你你也别要,特别是陌生人,你懂不?我说,我懂。我妈说,等你爸回来了,让他带着你还给人家。我没说话,不想还,凭啥要还?我又问我妈,他是不是真的会变戏法?我妈说,不清楚,也许会吧,也许他早就藏好的。我觉得跟我妈再说多少也没用,所以懒得跟她讲了。张三头是不可能事先藏好东西的,那么个小盆,能藏个啥玩意?他变东西前,也是先问我跟刘杨俊的心愿了的。
外面有虫鸣,风沙沙地吹着,倒是不热,有些凉爽。我听到门口有说话声,知道是我爸回来了,他跟人作别。我爸推开院门,我一下子扑了过去。我说,爸,你吃饭了没?我爸说,还没呢。我妈说再给他热热。我爸说不了,凑合着吃吧,天热,再说了,吃冷菜也挺好的。
我爸像是饿坏了,不停地往嘴里扒饭。我妈说,他们咋说?我爸咽了几口饭,说还是老话。我妈说,你吃慢点,又没谁跟你抢。我妈的脸色有些沉,她瞥向我,我站在旁边观察着他俩。我妈说,小楠,你到旁边玩去。我站到了一边,慢慢移动到床跟前,找了个旧玩具车玩。玩归玩,我还是很安静的,就是想知道我爸干啥去了。我妈说,都四个月了,再这么下去,买菜钱都没有。我爸说,回头我单独再去问问,今天人多,就算有,估计也管不了那么多人。他们怎么这样,百来号人干的活不是活了,想赖就赖?我妈有些懊恼。你小声点吧,实在不行,我给哥打个电话,看看他电厂里有熟人没,能不能说上话。我妈说,也行,不过你别跟别人说哈。我爸说,我知道。
吃完饭,我爸准备收碗,我妈抢先收了。我爸说,今天我不洗碗了?我妈瞥了他一眼,我洗,你带小楠去还人家东西。我爸诧异,说,他拿别人东西?我妈说,没,张三头给的,他说人家会变戏法,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妈这么说,我就大声接了话,说是真的,我没骗人。行,你没骗人,我妈说,那让爸快带你去。我拿着干脆面,跑到我爸跟前说,走啊爸。
我哪会变什么戏法?就是见他俩孩子可爱,喜欢,刚好家里有,给他们吃还不行啊?再说了,又不是啥珍贵物品。张三头坐在板凳上,认真地说。我爸说,知道您是好意,也晓得不是啥贵重物品,但是孩子还小,不能养成这习惯,您说以后要是大了,心也大了,那还得了。张三头说,算了吧,你别磨叽了,多大点事,扯得远了。说着,张三头把我爸递过去的干脆面塞我怀里,我明天还得上工,就不送你们父子俩了。他一边拿瓢舀水,一边提水壶到灶台上烧,看样子是准备洗脸洗脚睡觉。我爸也不好再纠结,就说那先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张三头说,快回吧,快回吧,多大点事。
出了张三头家,我们俩沿着小巷子走,空气像是凝滞了一样,谁也不说话。良久,我爸才问我,你真看到他是从盆里捞出来的?我点点头,嗯,还有刘杨俊,他可以作证。我爸没说话,像在思考什么。我说,爸,他是不是真会变戏法?对了,他说的不是变戏法,说是隔什么干什么来着。我爸说,隔空取物?我说,对,就是隔空取物。我爸摸摸我的头,说走吧。
晚上,不大的房间里睡着三个人,还是挺闷的。我爸呼噜声蛮大,好在他俩白天干活累了,睡得沉,彼此听不到。我没瞌睡,一直在琢磨着张三头的事。在我和刘杨俊面前,他为啥会表演隔空取物呢?等我爸退他东西时,他咋否认自己会变戏法呢?
4
大人们吃完早餐就上工了,食堂里剩我们几个小孩。扫地的叔叔说,你几个臭小子还不走。刘杨俊说,外面风大,怕下雨,我们想在这里躲躲。躲啥躲呢,那叔叔一脸不耐烦,他扫把扫到我们脚跟上来,说哪凉快哪待着去,实在不行,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又不是没家。
我们被他轰了出来。风确实有些大,不知道咋的,大夏天的刮什么风。有个小朋友说去他家玩,他带了钥匙,我们好几个小孩都没带,认为这样挺好。跑到他家,玩的玩玩具车,打的打铁片。玩了一会儿,刘杨俊看看天,不见下雨。他冲我说,你要不要走?我说,去哪?他声音挺小,说还能去哪。我说,好吧。我和刘杨俊就悄悄溜了出来。我说,你的泡泡糖吃了没?他说,吃了啊,不吃就过期了。我说,咋会那么快过期?他说,你的干脆面没吃?我说,嗯,没吃。他说,你傻啊,你真怀疑它是假的?我说,没,就是不想吃。他说,算了吧,走,我带你看看他家的盆去。
到张三头家,门锁着的。我说,进不去,墙也不能再爬了。刘杨俊说,我有办法。我说,啥办法?他鬼鬼祟祟,说开锁。我吓到了,这家伙啥时候学的这种手段?我说,我不敢,要是被他抓住就是小偷了,我妈非打死我不可。刘杨俊说,怕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我说,你进去干啥,把盆拿走?他说,嗯,那盆太神奇了,你们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没?我说,什么故事?他说,阿拉斯神灯的故事,就是有一盏灯,向它许下心愿,它就会满足你,给你想要的。我说,那是童话,不是真的。刘杨俊说,咋不会是真的?不是真的老师讲它干啥?再说了,那天张三头从盆里拿东西你也看见的。我结结巴巴,说,是,是看见,可是……可是什么,你怕的话就算了,我自己来。刘杨俊把锁的屁股朝上,然后摸出兜里的一盒火柴,又摸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还摸出一根细铁丝。我说,你咋开锁?他说,你个胆小鬼,你又不敢,问那么多干吗?我心想,你横什么横。他把细铁丝插进锁屁股里,再把火柴盒放在地上,火柴杆一根根地拿了出来,小刀刮掉火柴头上的火药,一点点落在一张纸片上。我纳闷,开锁不都是用榔头或者扳手嘛,我见我爸就是用扳手撬锁。看了小会儿,他又把刮下来的火药一点点塞进锁屁股里。然后,用火柴杆摁实火药,擦燃一根火柴,朝着锁屁股点去。我害怕会引爆,一下子跑开了。没想到,锁“砰”的一声竟然开了。真是大开眼界,我还不知道能这样开锁,他是跟谁学的?我正纳闷,他已经冲进院子,爬上鸡圈,径自拿走那只黄色的塑料盆。离开前,刘杨俊异常冷静,他锁上院门,捡起门口落下的火柴杆啥的,反正“犯罪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就这样,他头也没回,直接朝着自个家走去。
我独自站在巷子里,不晓得是回家还是该去哪,心里空落落的。明明不该做的事,刘杨俊做了,我没做,反倒觉得自己像是哪错了。我走到家门口,找块石头坐下,估摸着到中午的时候再去食堂吃饭。
到了饭点,我爸妈回来了。人多,我爸给我们打好饭,全家三口就端着饭回家吃。我妈说,你请假没?我爸说,请了。我妈说,那下午小楠你带。我爸说,行。扒完饭,我妈收拾碗筷,拿去食堂,说接着上工,这几天活压头,勾缝的女工都干不过来。
我妈走后,我说,爸,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爸说,你说。我说,要是你的好朋友请你帮他做事,你不做,会不会心里面欠得慌?我爸说,那要看是什么事了,是自己想做的还是不想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要是是自己不想做的,又是一件坏事呢?我爸说,这样的话,那不会。我爸这么说,我就没吭声了。他倒是在那自言自语,说,不过话虽如此,你爸我有时候也挺没出息的,经不住忽悠,有些事晓得不能做,别人多劝几次,就无法拒绝了,你可别学我。我说,哦。我爸说,是不是你那个朋友刘杨俊又让你做什么事了?我说,没,他没让我做啥事,我就是随便问问。我晓得,我要是说刘杨俊开锁的事,传出去的话,刘杨俊不仅会被打,还会扯出一犊子事。
我爸说,午休,靠一会儿吧,等会儿爸爸带你上街。我说,好啊。我们在床上靠了下来。我爸身子在床上,腿搭在地上,我就躺在他旁边。没一会儿,他的鼾声又呼噜呼噜地响了起来,我也不晓得啥时候睡着的。
醒来,我爸带我上街。他是去打电话。进了电话亭,他问打长途多少钱。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面带凶相,说一块二。我爸说,那么贵。那人没说话。我爸说,好吧。老板说,里面有间隔,你挑一个,打完再计费。我爸怕我丢了,就把我带进间隔里。
电话拨通了,是我大伯接的。听筒没开扩音,不过声音挺大,我趴在他腿前,听得真切。我爸说,哥,你最近身体咋样?那头说,还行,咋的,想起给你哥打电话了?我爸言归正传,说手头上遇到点难处。我大伯说,要借钱啊,你要多少,我明天让你嫂子汇过来。我爸说,不是,我干的活要不到账,这都跑了好几回了,找谁都耍赖,不担责。我大伯说,这样吧,你说说具体在哪些人手下干的活,啥时候干的,工种是啥,我请火电厂燃运科的主任问问,看他有没有认识工三团的,要是有,看能不能说上话。我爸说,那行,就麻烦哥了。我大伯说,自家兄弟,咋那么见外?然后说,你老婆儿子他们都挺好的吧?我爸说,都还挺好,小楠就在旁边,来,你跟大伯说几句。我嘴拙,内敛,不晓得咋说,就光喊了几声伯伯。那边问话,我敷敷衍衍地回了下。我爸说,没法了,这娃随我,胆子怯。我大伯说,行,就这样吧,电话费贵,你这事我记着,尽快帮你解决。
挂了电话,我爸结了电话费,问我想吃啥。我晓得他没钱,不过是上趟街,怕我失落,随口问问的。刚才他结账,几块钱都摸了两个兜。我说,爸,我啥都不想要,又不饿,也没有我想玩的玩具。我爸说,那行,我们先回去吧。我爸带着我往回走,路上他没咋说话。我看得出,他有些心焦。
5
后来呢,后来那小孩怎么了?我问张三头。张三头靠在椅子上,说你给我点支烟,我就告诉你。他从兜里摸出烟来,还摸出火柴。算起来,他也是爷爷辈的了,我给他点支烟亏不到哪去。我就说,那行。我点上烟。他说,跟你玩的那个小孩咋没来?我没告诉他刘杨俊偷他盆的事,也没说我跟刘杨俊不玩了的事。我说,他妈管得紧,最近不让他出来玩。张三头哦哦哦的,怪不得,我还说我的盆不见了,怕是那小子给拿走的。我心里一愣,他怎么会想到刘杨俊呢?张三头接着说,你们俩啊,还是你看着实诚,那小子鬼脑筋多得很,长大后不得了,怕是要上天。
我想绕开这个话题。我说,张爷爷,你还没告诉我,那小孩后来怎么样了呢。张三头深吸一口烟,说你要听,那我就继续讲吧。他说,小孩之所以会爬进宝库,是张三丰施的法。现在,小孩睁开眼睛,算是破了张三丰使的法术,回不去了,哪怕玉皇大帝来了也没辙。我说,要是这样,他岂不是要饿死在金库里?
张三头说,那倒不会,这小孩发现不对劲后,急得直跺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咋办呢?只能坐着哭呗。这个时候,巡逻的官兵听到他的哭声,就跑去禀报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晓得后,郁闷得很,这皇宫守卫森严,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咋会有小孩的哭声?于是,他就命人去开金库大门,一看里面果真有个七八岁的小孩,怀里还兜着几个元宝,正坐在地上哭。士兵们一拥而上绑住小孩,像拎鸡仔似的拎到金銮殿。朱元璋亲自审讯,说大胆毛孩,你是何方人氏,怎么进我大明国库来行盗的,快快从实招来。小孩听他这么一训,吓得浑身发抖,连声说,不是我要来偷的,是那个张三丰让我从他衣袖里爬过来的。旁边的人听了觉得不可思议,有人插嘴,你这个毛孩真是胆大包天,死到临头还在扯谎。小孩听他这话,吓得趴在地上求饶,说没有,我没有说谎,真是那个叫张三丰的让我从他衣袖里爬过来的。皇帝说,好了,那你讲讲,那个张三丰现在在哪?小孩说,在平越,在平越的钟鼓楼,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就这样,朱元璋命人先收监这个小孩,等查明后再说。然后,他下了道圣旨,命令御林军快速查找平越是不是真有个叫张三丰的人。经查证,在贵州平越县钟鼓楼真有个叫张三丰的民间奇人。朱元璋晓得后惊叹不已,平越离京城几千里,一个小孩咋可能从他衣袖里几下子就爬到京城的,还钻进国库,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他命令御林军急速奔赴平越,务必捉拿张三丰归案。
那抓到他了吗?我说。张三头说,算抓到了,也算没抓到。为什么?我饶有兴致地问。张三头说,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太累了。我说,你说话怎么只说一半?到底是抓到还是没抓到啊?张三头说,我真累了,想去睡会儿。他起身,我一下子抱住他的腿,让他别走。他说,行,那你告诉我件事,我就讲。我说,啥事?他说,我那只盆是不是跟你玩的那个小孩偷走的?我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张三头说,既然这样,那我先去睡觉了。我又抱住他的腿,我说,我要是说了,你能不能别去找他?不然他会怪我的。张三头说,我不会。我说,嗯,是他偷走的。张三头没问咋偷走的,他应该在想刘杨俊怎么进的门,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经过。张三头说,行,我不会说的,我知道就行了。我说,那您敢保证吗?张三头说,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说,那我们拉个钩。我勾出小拇指,你得跟着我念,念了拉的钩才算数。张三头说,好吧。我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骗了是小狗。张三头就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骗了是小狗。然后,我说,那你接着讲吧。张三头说,既然你那么想听,那我就勉强接着讲吧。
张三头说,一群御林军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来到平越,他们走进钟鼓楼,果然找到一个叫张三丰的人。这人正躺在阁楼上午休。那群御林军二话没说,冲上去就五花大绑把他捆了起来,一路押向京城。朱元璋晓得后,高兴得很,他给大臣们说,朕要亲自审审这个张三丰,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可是呢,就在御林军押送张三丰到京城的头天晚上,他给跑了,只看到押解他的刑具散落在地。要知道,押解他的是很坚实的脚链和手链,他没有钥匙,竟然轻松逃脱。
我说,他是怎么跑掉的?张三头说,他会法术啊,自然就跑掉了。法术,又是法术,那后面呢,抓回来没?我说。张三头说,抓回来了。怎么抓回来的?张三头说,还不是御林军给抓回来的。
御林军气得暴跳如雷,他们不敢怠慢,再次追回平越钟鼓楼,发现张三丰正坐在楼上悠然地喝着茶。而且,他不但自己逃了回来,还在当天晚上把关押在京城的那个小孩也救了出来。御林军一拥而上,又把张三丰绑了起来,这一回,他们轮流值守,不放过任何一个眨眼的工夫,硬是再次押他进入京城。好不容易进了城,大伙刚松一口气,张三丰竟然在眼皮底下没了影,留下一副被他撑破的镣铐。朱元璋晓得后,怒火中烧,说你们这群饭桶,无能之辈,连个臭道士都抓不住,还如何守疆卫土,如何保护朕?要是再抓不住张三丰,我就诛你们的九族。
啥叫诛九族?我说。张三头说,就是满门抄斩,反正就是把连带点亲戚关系的人都给杀掉。我说,哦,好吧,那他挺狠的。
张三头说,我接着讲哈。都说君无戏言,他这么一说,士兵们吓得一个个魂飞魄散,胆战心惊。他们又快马加鞭赶到平越钟鼓楼,这回他们怕了,知道硬的不行得换软的。一个个张爷爷地喊着,说求求您了,您行行好,就到京城见见皇帝陛下吧,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也要交差,这要是再请不到您进京,我们一个个掉脑袋不说,家人还会被诛杀。张三丰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心想,你们这群狗奴才,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嘛,怎么现在一个个认怂了?张三丰说,好啊,我可以和你们去,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这群人听这话知道是有希望了,连忙问什么条件,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尽力满足他老人家。张三丰说,上刀山下火海倒不至于,只是这千里迢迢我年纪大了走起路来太累,要去也是你们抬着我去。大伙心想,路确实远,抬着去不仅慢而且累,不过只要他不逃跑,也能应承下来。于是,大伙就说,抬就抬吧,只要您答应去。张三丰说,那行。接着,班头立即找来一乘轿子,张三丰见了,立马说不行不行,这太奢侈了,贫道不坐这个。军人们一听慌了,忙问那要坐什么。张三丰说,你们找一口大瓦缸来,只需要把我装进缸里,把缸口封住,抬着我去就行,但是这一路上不能有个闪失,要是还没到京城,缸就摔坏了,你们可别怪我不守承诺。众人说,行,行行。
我说,这缸是圆的,抬起来岂不是比抬轿子还费劲?张三头笑道,可不是嘛。我说,那后面缸摔坏没?张三头说,摔坏了。我说,摔坏了?那张三丰到底见没见到皇帝啊?张三头说,张三丰倒是见到了皇帝,可是皇帝没见到张三丰。我说,你说的这是个啥?我咋没听懂?莫名其妙,自相矛盾。张三头说,哈哈,你小子还会用成语啊。我说,老师教的。张三头说,改天再讲,我真累了,我要午休。说着,张三头站了起来。我说,你就不能再讲讲?张三头说,你真是得一碗米等不到天亮,今天就到这吧,改天再讲。
6
我妈啃着馒头,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爸,说,那个周保国咋说?我爸说,他说他跟工三团也不是太熟,倒是认识里面一个管材料的,让我明天去他办公室一趟,他约上那个人,看看能不能说上话。我妈说,只要人家愿意帮我们,就很不错了,我身上还有点钱,你先拿去买包好烟,对了,别忘了给人家说要是能成,后面会感谢他们的。我爸说,我知道的。我妈从兜里摸出两张十块钱递给我爸。
我爸下午没上班,我妈给他请了假,说是头疼,中暑了。整个下午,我爸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我说,爸,我们是不是快吃不上饭了?我爸说,谁说的?我说,没谁说,我看你和我妈这几天愁眉苦脸的,可不是快吃不上饭了。我爸说,瞎说,是工资老不发,我这焦着呢。我没再说话了。我爸不停地看手表,过了一会儿,他说,爸爸去趟火电厂,你在家好好待着。我说,我也要去。我爸想了想,说行吧,不过你哪也别跑,我让你在哪待着你就在哪待着。我说,嗯。
我爸领着我走进火电厂,这还是我头次进电厂。厂子很大,走进大门,跃入眼帘的是一栋很高的办公楼,看外形就晓得高级。道路宽敞,两边种满花卉,有满天星,还有地雷花、野菊花,等等,这些上课时老师教我们认过。办公楼门口是个喷水池,水池里水不停地喷着,太阳特毒,火辣辣的。我爸说,你在这等着我,哪也别去,不能进水池,有电,水深,知道没?我说,知道了。说完,我爸朝着办公楼走去,上了台阶,跟门口的保安解释着,隔得远,我听不清,无非是些他找人办事的话。他解释了一通,保安才信,这才放他进去。我站在水池边张望,周围不是办公楼就是厂房,轰隆隆的作业声不绝于耳,不时有人骑车经过看向我这边,我怕他们不认识我,撵我出去,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悄悄坐了下来。
一直等到七点半,都下班了,一拨拨人骑着自行车出厂,我爸才从楼上下来。我朝我爸冲过去。我说,爸,咋样?我爸说,我们回家再说吧。出了火电厂大门,对面就是工三团,工人们陆续回来了。有人说,张三头,你倒是给我们表演表演啊。张三头走在前面,戴着安全帽,扛着灰浆桶,灰扑扑的,啥也不说。有人在后面起哄,说我还不知道,我们工三团真是个出人才的地啊,竟然有这么一尊大佛在,你倒是让大伙开开眼界啊。说着,张三头的步伐越发加快,跟的人也越来越紧。我爸说,这群人凑什么热闹?我说,他们是想看张三头表演隔空取物的绝技。我爸说,上次我们去他家还干脆面,他不是说他不会嘛。我说,他会的,只是他不愿承认。我爸嘀咕着,这事谁传开的?我没答话,心想,除了刘杨俊还能有谁?还有就是刘杨俊他妈那张大嘴巴。
凑上去的人越来越多,我有些担心张三头,害怕这群人整出什么幺蛾子,又想看看张三头会不会再次表演他的绝技。我说,爸,我们跟上去看看吧。我爸说,走嘛,我也想见识见识。我爸牵着我,跟着人群来到张三头家的巷子里,此时巷子人满为患。有人跟他进了院子。我爸怕我走丢,把我举在他肩上。我说,爸,你跟上啊。我爸举着我在人群里挤,好不容易挤到他家门口,实在挤不进了。我看到有个高头大汉站在他家院子里,说张三爷,我们叫您三爷呢,您就给我们展示展示吧,我们活那么大,还只是听说,真没见过。张三头坐在椅子上,一脸不悦,见识了又能怎样?再说了,一个小孩说的玩笑话,你们也当真。他话音刚落,刘杨俊就站了出来,说我没瞎说,张爷爷确实会变戏法,不信,这就是他变戏法的盆。说着,他妈从他手中夺过那只塑料盆亮给人们看。人们都惊奇地看着这只盆。刘杨俊他妈说,是啊,张三爷,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嘛,我们也好开开眼界。看这些人估计不见黄河是不会死心了,张三头心一横,说见识可以,不过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人们问,啥条件。张三头说,见了以后大家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我这也不是什么法术,你们别想得那么玄乎,不过是个魔术罢了,逗逗乐而已。大伙齐刷刷地说,好。
张三头预知不了未来,要是能预知的话,他当时就不该表演的。就这样,张三头捡起地上的一只塑料盆,找来一只板凳,盆是空的,他拎起来示意给大伙看。看完,他放盆在凳子上,从身边找来几张报纸盖住。然后,他说,你们想要啥?那些人乐开了花,说想要钱了,越大越好。张三头说,好。说着,他挽起袖子,手伸进盆里。没人晓得他的手在盆里干啥,只知道他看上去很累。人们的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似的,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的瞬间。好一会儿,张三头的额头上渗出汗来,像是又累又热。他的手摸出一张100 元现钞,人们看得目瞪口呆。钱放在凳子上,没人敢拿。接着,他的手又伸回盆里,再次摸出一张100 元现钞。又接着,他的手再次伸进盆里,有时候摸出一张,有时候摸出好多张,全是100 元的现钞。
表演完,张三头累得满头大汗。旁边的人连忙给他舀水喝,一瓢冷水下肚,张三头说,我就是会个魔术而已,大伙别当真哈,现在你们见识到了,都回去做饭吃吧。说完,他把凳子上的钱往盆里一扔,报纸一盖,独自进了屋,门插上插销。人们冲上去,要开门,门关得紧紧的,再揭开盆上的报纸,里面空空如也,哪还有什么钱?人们兴致盎然,觉得还不够,在外面嚷着,张三爷,您表演得太短了,我们没看过瘾,再让我们见识见识啊。这个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你们别吵了,我说两句,张三爷要是会什么隔空取物,他还跟着我们出那么大力气干什么活?要我说,会魔术是真,但魔术大伙都晓得,那就是个戏法,戏法是哄小孩的,开心开心就行了,当不得饭吃,要是真能想变啥就变啥,那岂不成神仙了?再说了,要真会隔空取物,他还不比楚留香牛啊,大伙都赶紧回去吧,再过一会儿,《香帅传奇》就要开始了。他说完,人们作鸟兽散,忙着赶紧回家做饭吃,不然,今晚上就得错过楚留香了。
7
我妈一高兴,多吃了一碗饭,说有点撑。我爸说,希望能成。我妈说,这事你不要传出去,我估摸着,有些工友应该拿到钱了的,只是人家口风紧,没说。我爸说,我又不是傻的,知道咋做。
我还没吃完,我妈就开催了,说快点,好去看楚留香,晚了就没地儿了。我爸说,催工不催吃,你慌个啥?我妈说,不懂就别插话。我心想,楚留香有啥好看的?每天那么多人去沈姨家。
工三团有电视机的人家不多,沈姨家是其中之一,她家屋子宽,主要是院儿大,能容纳不少人。带着两张小板凳,我妈领着我,推开沈姨家院门,院子里已经坐上人了。电视机摆在屋子正门口,像是才抬出来的,放在一张桌子上。人们围着电视坐成扇状。我妈环视院子,指着右边一个角落说,那有位置,我们去那。她跨过一个个小板凳,找到个没落凳的地方坐下。我说,妈,楚留香啥时候出来?我妈说,快了,别说话。来看电视的人很多,没一会儿,院子里就坐满了人,大门口还站着几个大叔,只要是能站个人的地方,就没空着。
《香帅传奇》开播了,电视里放着主题曲,歌里唱着:“……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天大地大留下什么话/好名照青史人走天涯……”
人们异常激动,大人们抽烟、嗑瓜子、闲聊,眼睛时刻不离电视,小孩子们蹲在各自的位置上,精神高度集中。男人们会讨论谁长得漂亮,女人们更多关注楚香帅,小孩子们好奇和讨论的是他们在使用什么武功,打斗时会不会死,如何飞起来的,能飞多久。
刘杨俊跟着他妈也来了,我看到他坐在我前面点,他也看到我了,只是他没跟我说话。我觉得他可能还在生我的气。有什么好气的,怨不得我啊,偷别人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俩的目光碰到了几次,不知道啥原因,刘杨俊竟然跟我说话了。他猫着腰,从前面凑了过来。他说,以前没见你来看啊?我说,就今天来呢。他说,走,出去,我跟你说件事。我说,啥事?他瞥了眼我妈,我妈正聚精会神看电视,压根没注意我们。他低着声,说,还能有啥事?他跟我妈说,阿姨,我们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这里人多,怪热的。我妈见过他,知道他是我平日里的玩伴,说去吧去吧,你们别走远啊。
刘杨俊在前,我在后,好不容易挤出沈姨家。巷子里空荡荡的,回荡着《香帅传奇》里人物的对白和打斗声。刘杨俊说,前面你也在张三头家吧?我说,嗯,怎么了?他说,你相不相信他那是魔术?我说,不晓得,他说是就是吧。刘杨俊说,我反正不相信,你还记得他讲过的《张三丰盗宝》的故事不?我说,记得啊,没讲完,咋了?他说,张三丰是个道士,张三头可能也是个道士,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说,你的意思是他是隐居的大侠?刘杨俊说,大侠谈不上,再说了,你见过哪个大侠是他那样的糟老头?怎么说也得是楚留香这样帅的人。我心想,也是,他要是大侠,岂不是能帮工人们讨回工钱了?别说讨回来,他自个也用不着窝在这里干苦力了啊。我说,那你咋会觉得他是道士的?刘杨俊说,他十分熟悉张三丰的故事,不知道从哪听来的,另外我爸跟我讲过茅山道士的传说,说会茅山道术的人,不仅会隔空取物,还会其他法术。我说,都有哪些法术?他说,比如让一匹马喝水,命令它只喝半盆水,水就会只让左边或者右边一半给马喝,还有,会让皮带变成蛇上树偷梨子,反正很多。我听他这么一说,浑身起鸡皮疙瘩,心生胆怯。我说,你讲的像是僵尸片里的。他说,对对,差不多是这样。我说,那张三头会抓僵尸吗?你可别吓我。刘杨俊说,瞧你那点出息,我只是纳闷,他一个老头子,不跟大伙一样看电视,整天关在屋里干啥,再说了,他好像也没有儿女。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说,我爸说的,一般会这些法术的人都不会有后代,有可以,但是自己得残疾或者孤独终老。我说,算了,你别说了,我要去看电视了。说完,我撂他一个人在巷子里,径自朝着沈姨家院子里跑去。
刘杨俊的话,一直让我感到害怕。晚上爸妈睡着了,我仍无困意,透过窗户望着天上的星星。要是张三头真会法术,他岂不是想害谁就能害谁,那咋还能受大家逼迫表演绝技呢?这样推断,刘杨俊的话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张三头这人着实奇怪,独来独往,寡言少语,逢年过节也没个啥亲戚。总之,我对张三头的态度慢慢转变了,对他有些敬而远之。后面的日子里,好多次他看到我都主动给我打招呼,说,你干啥去啊?我说,我爸让我买酱油呢。他说,你上哪玩啊?我说,没上哪玩,去河边呢。他说,张三丰的故事还没讲完呢,要听不?我呆呆地看着他,说家里还有事,改天再去你家,你再讲给我听吧。
张三丰后面去没去京城面见圣上?按照张三头的讲法是去了的。那是张三头最后一次给我讲故事,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说完这个故事,他就从我们工三团消失了。咋消失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认为,跟中秋节前的一场文娱活动有关。
中秋节快到的那段时间,人们穷得叮当响,闹得有些厉害,有人要不到工钱,索性窝在家里不出工,到了饭点就去食堂打饭吃。食堂要看饭票,没饭票的不让吃,工人们窝火,就跟炒菜师傅干上了。炒菜师傅当了冤大头,给揍得皮泡脸肿,叫苦不迭,说我招谁惹谁了,上面说凭票打饭,我也是按规定办事。按规定?还憋屈的工人端着饭,脚使劲往他身上踹。
眼见工程滞后,我妈他们没事干,就搬来小板凳,挨个坐在砖墙根下打毛衣、纳鞋底。大姑大婶们七嘴八舌,说包工头们去找电厂管事的了,看看能不能先结点账出来,要是结了,他们就有钱发工资了。我妈没吭声,我隐约晓得,我爸的工资像是要到了的。有天晚上,我爸很晚才回来,买了袋米,还有面粉,还有些零食,面包、方便面、泡泡糖、火腿肠啥的。我妈说,情况咋样?我爸说,还差点零头,我想着拿不到算了,我请他们吃完饭,每人塞了条烟。我妈说,也成,只要大头的拿到就好。听他们的对话,感觉那钱像是捡来似的,不像自个劳动挣来的一样。我妈揭开炉盘,放上锅,说给我煮方便面吃,说煮的面好吃些。还没吃,我这口水馋得直往外冒。吃面的时候,我妈说,你别出去说你吃方便面哈,也别说你爸买新米了。我点点头,说嗯。
8
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有飞机划过,留下一道白色的划痕。我仰着头,端详着蓝天下蠕动的白云。我妈牵着我,跟着一群人站在学校操场上。主席台上有人在讲话,喇叭声音特大。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你们好!你们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十分同情,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都不容易。工程干了,结不了账,这是谁都不想遇到的事。咋办呢?要呗,我们不是没有要过,要过了多次,电厂方面的领导也表态了,说眼下的局势大家都知道,各方艰难啊,能有口饭就挺不容易了。电厂是大厂,是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办的,亏谁也不能亏咱们老百姓。有钱,谁愿意挨骂,谁愿意背欠债的名?欠你们的钱是钱,欠我们的钱也是钱,我们为了接这些工程,都是砸锅卖铁垫资干的。就在前几天,我们又去了,这回只要到一部分工资,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就是想把话说清楚,钱有限,一次性还不清大伙的工资,我们会按照各家各户的出工情况和条件分发,条件差点的和出工少的,我们先发完。条件好点的,出工多的,我们先发一部分,剩下的我们后面再想办法,还望大伙理解。另外,我们准备了些粮油,怕剩下的工资要不到的同志,可以领粮油回去抵债。在此呢,我也代表工三团的领导们,祝大伙节日快乐。
话音才落,人群就躁动起来,嘀嘀咕咕地抱怨着,说咋回事啊,又来这招,这钱得要到猴年马月啊。见大家议论,有人拿起话筒,接着刚才说的话胡扯一番,无非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大家别慌,稳定情绪。然后,说打算举办一期文娱活动,有愿意报名参加的赶紧报名,排演一天按出工一天算,有工钱。有人听了,就举手报名。不晓得是谁把张三头推了出来,说他会演魔术,能隔空取物。台上领导听了,马上来了兴致,说,行行行,那就让大伙见识见识吧。我妈没报,她对表演不感兴趣。她带着我排队,领了四桶菜油一袋米。油太多,她拎不动,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干坐着等我爸。
中午,人们还没散去,我爸从电厂出来吃午饭。我妈说,你提油,我扛米。我爸说,要那么多粮油干吗?我妈说,你傻啊,我把你没讨到的工钱全算成粮油了,要到多少是多少吧。我爸说,你真行,我还想着要不着就算了呢。我妈说,这够我们吃一阵子的了。此时,我爸已经辞去工三团的活了,他跟周保国认识后,周保国觉得他这人实诚,说在哪干都是干,电厂工资不高,但是工资好拿,就先干一下临时工。我爸盘算过,觉得拿得到手的钱才是真的,就答应了。
文娱活动是在一个艳阳天举行的,太阳火辣辣的,有丝丝微风拂动。尽管如此,大伙看节目的热情丝毫未减,学前班门口的操场上站满了人。我爸怕我看不到,给脚下垫了好几块砖,让我坐在他的肩上,我看得真真切切。表演的人激情满满,轮番上阵,一会儿有人跳迪斯科,一会儿有人情歌合唱,一会儿有人单独唱,还有人表演小品,表演快板。平时大伙干同样的活,没发现谁有啥特长,这会儿才发现,隐藏在民工队伍里的文艺人才蛮多的。张三头是下半场上台的,算是压轴戏,节目名就叫“神手”,表演的还是隔空取物的绝技。道具依旧是一只盆,不过不是刘杨俊偷的那只,是台下观众随便扔上来的,报纸倒是有几张。表演开始了,张三头坐在板凳上,盆就放在跟前的桌子上,他的手伸进盆里,用报纸挡着。旁边有个人递话筒给张三头。张三头说,我今天给大家变钱。大伙乐开了花,说好啊,我们做梦都想着钱。张三头说,大伙先别吵。说着,他从盆里摸出一张100 元现钞。显然,不过瘾,有人就喊了,再变,变更多的钱。张三头就摸出更多的钱,好多张100 元现钞。在大伙的起哄声中,张三头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劲,脸憋得通红,摸出一沓一沓的百元现钞。
桌子上摆满了钱。张三头的手从盆中伸了出来。他接过话筒,说你们都摸摸你们的衣兜或者钱包,看看钱还在不在。大伙听他这话,全都急了,一个个摸屁股揣衣兜,说我的钱没了,我的也没了。张三头说,大伙别急,都站好了,原地不动。人们就都很听话地站着。张三头说,我现在要把你们的钱还回去,你们不能乱动,动了的话,钱就回不去了。说完,张三头把桌上的钱全扔进盆里,又用报纸盖住,他的手伸在报纸底下,不知道鼓捣个啥。好半天工夫,只见他满头大汗,这才收手,揭开报纸,留下一只空盆。他拎起盆说,大家看看,盆现在是空的,你们的衣兜和钱包是不是又鼓回来了?人们又摸屁股插衣兜一番,说,哎呀,真是奇了怪了,钱咋又回来了?这钱可真是长了腿了。
活动结束,张三头风头大出,名声赫赫。一群人围着他不让走,说要拜他为师。张三头说,我这是雕虫小技,自个玩玩可以,教不了别人。人们不信,簇拥着,递烟的递烟,点烟的点烟,说就要跟他学法术。张三头说,这充其量就个魔术,哪是什么法术?这个时候,不晓得从哪窜出个人,四十上下,脸上有疤,瘦筋瘦筋的,看着不咋个面善。那人说,我知道你名字。张三头说,敢问兄弟贵姓?那人说,姓柴,单名一个川字。张三头会心地笑笑,说幸会幸会。那人说,我想跟你比试比试。张三头说,这有啥好比试的。那人说,我想看看自己练到了几重。张三头说,我这是小魔术,不是什么法术,没那么玄乎。那人说,就这样,恕我冒昧,我很想试试,你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三天后,我在这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否则,你会后悔的。说完,那人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张三头身边的人都看呆了,一个个问他,说张三爷,你是不是在哪结下过什么梁子?这显然是来挑衅你的。张三头一声没吭,径自朝家的方向走。那天下午,有人要找张三头单挑的事一下子在工三团传开了,人们都在等着看一出大戏。
9
张三丰就钻进大缸里,好在一路上风平浪静,没出个什么闪失,他们顺利抵达京城。张三头坐在靠椅上,扇着扇子慢悠悠地说。我说,那瓦缸不透气,他没憋死?张三头说,没有,他要是憋死,他就不是张三丰了。我说,那后来呢?后来,后来御林军就高兴地抬着大缸直奔金銮殿呗,谁知刚走到金銮殿门口,一个士兵不小心绊了一跤,大瓦缸哐的一声摔成几大块。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愣了,诧异道,张三丰呢?张三丰不是在缸里吗?他这回又骗我们了啊。有人气得瘫坐在地上,哭着喊,张爷爷啊,你这是故意捣整我们啊,你说如果在抵达京城前摔坏缸子你就可以不守承诺,可我们已经把你扛到大殿门口了啊,你咋就不见了呢?你这不是要害我们灭九族嘛……就在这时,地上的瓦片说话了。瓦片竟然会说话?我出奇地望着张三头,瓦片咋会说话的?张三头说,瓦片确实是说话了,这也是上辈人讲给我们听的,不可思议吧?就像张三丰让小孩钻进衣袖里通往金库一样。我说,是的。张三头说,瓦片中传来了张三丰的声音,说你们哭什么哭啊,我这不是在这儿的嘛,你们只管捡起瓦片去面见圣上就行了,他不会怪罪的。士兵们听他这么一说,想想也没辙,虽然看不见他人,但能听到他的声音,于是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瓦片,走进了金銮殿。朱元璋见了,困惑不已,质问说,你们抓的张三丰呢?还没等士兵们回话,地上的瓦片上就传来张三丰的声音了,他说,贫道张三丰参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说,张爱卿,你在哪里啊?瓦片说,我就在您跟前呢。朱元璋看着地上的瓦片愣神。张三丰说,启禀万岁,贫道并非贪财之人,偷国库金银实在是无奈之举,只是想借此提醒万岁您多了解民间疾苦,做一个为苍生谋福祉的好皇帝。朱元璋听完,喃喃说道,张三丰,真是神人啊,真是神人。张三丰一听,哈哈大笑,那么贫道就先告辞了。说完,他的声音隐遁而去,唯独剩下几块破碎的瓦片,这些瓦片再也不会说话了。我说,完了?张三头说,完了,对了,后来传说张三丰归隐到了武当山,朱元璋命人探寻过他,却怎么也找不到。
听完张三头的讲述,我不晓得该说什么,总感觉那个张三丰不像个人。我这么寻思着,门外突然有人来找,说张三爷,那人来了。张三头站起身,说来就来呗,先喝杯茶。说着,他走进屋子,拿了只大茶缸出来,放在炉灶上煨着。他的茶不怎么好喝,苦得要命,我也跟着喝了一小杯。喝茶的间隙,又有人喊,说您赶紧出去应战吧。张三头端起大碗里的茶一饮而尽,很镇定地站起身,朝着院子外面走去。
他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皆有。不晓得的,还以为工三团的民工又要集结到哪去打群架。我跟着来到操场上。此时,那个瘦筋男人已经摆好一只盆,他的盆比张三头的大,是那种很大很大的胶盆。盆上盖着的不是报纸,是一张黄色帆布。他说,大伙都到齐了吧?不瞒各位,本人是贵州来的,闯荡江湖多年,前几天见识到张师傅的绝技,斗胆造次,没别的意思,就是单纯地想比划比划,让各位见笑了。说着,他开始发功,扎稳马步,双手伸进盆中,一把一把地捞着钱,那些钱有小票,也有大票。捞完,整个人很轻松地站在那里,点起一支烟,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轮到张三头了,人们窃窃私语。有人说这个比赛不公平,有人就问为啥。那人就说,上回张三头变的钱,是从观众身上变走的,后面还给了大家,这回姓柴的变的钱很可能也是大伙身上的,钱都让姓柴的变走了,张三头还能变出什么?他这么说,人们一下子醒悟过来,纷纷摸自己的衣兜裤兜,发现钱还在身上,深深舒一口气。这下子,人们像是吃了定心丸,可以心无旁骛地看表演了。
张三头的手伸进盆里,跟上次一样,脸憋得通红。他从盆里一沓沓地摸出钱来。钱堆在桌子上,像座小山。柴川面色凝重。摸到一定时候,张三头收了手,说我们这么比划没啥意思,谁都能从无变到有。柴川说,那你说说看,怎么比有意思。张三头说,真正难的是从有变到无,无中生有容易,有中化无才难。柴川说,你的意思,是不是好比一个人误食了毒药,要想救他,就得有解药,制毒容易解毒难?
张三头笑笑,算是吧,你怎么理解都行。说着,他把桌子上的钱塞回盆里。柴川跟他一样,也将钱塞回盆里。塞完钱,张三头揭开报纸,盆里空空如也。柴川照做,盆中同样空空如也。张三头用手在桌子上一拍,砰的一声,盆不见了。柴川瞪目,他像是有些不服,显然,他的盆要比张三头的大很多。张三头嘴角微微上扬,什么话也没说。柴川似乎有些急了,他双手合十,紧闭双目,嘀嘀咕咕地不知道念些什么,等他睁开圆目大喝一声,双掌拍在盆边上,整个盆翻了个身,竟一下子也消失不见了。张三头在旁鼓掌,说不错,真不错。说着,张三头说,我现在要遁身了。眨眼的工夫,他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消失不见了。柴川诧异,问道,你走了?张三头说,没走,我就在你身边。声音像是从舞台后面的幕布传来的,柴川没有傻到去翻幕布,不过显然,他对张三头的遁术已经感到惊奇,胜败已分。人群中有人说,他躲在幕布后面了。有人跳上台去揭幕布,发现后面啥也没有。幕布是挂在墙上的,一下子滑落下来。哈哈哈哈,张三头笑道,他的笑声回旋在人们上空。看不到他的人,光听这笑声,还挺邪乎的。
柴川站在原地,顿时手足无措。他朝着空气拱手道,恕小弟冒犯,还望兄长海涵,今日我败于你,口服心服,从此我不再踏足此地,我先告辞!说罢,柴川灰溜溜走下台。观众们起哄,喊道,滚,滚。柴川没说话,闷声朝远处走去。
张三头声名远播,一时间被奉为奇人,来找他学艺的人不计其数。连着好几天,他都闭门不见。有人说,经此一战,他大伤元气,要好好休养,不能打搅。还有人说,他可能短时间内要闭关,等出关后,功力将会大增。四面八方前来观摩的人围得巷道里水泄不通,工三团有些工人索性也不出工了,跟着坐在他家门口,人们在巷子里搭起帐篷、升起炉灶,就等着见他一面。
等的时间长了,人们也会不耐烦,某个早晨,有人说砸门吧,人们情绪高涨,几下就把门踢开了,破门而入后,发现屋子里的摆设都未变,唯独不见他人。
他应该早就离开了的,就像那天他在舞台上一样,从人们眼皮底下蒸发掉了。
后来,我爸回忆,说有个早晨,他刚好下班,出电厂大门时,瞧见一个人朝着南边独自走去,光线有些暗,他不敢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张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