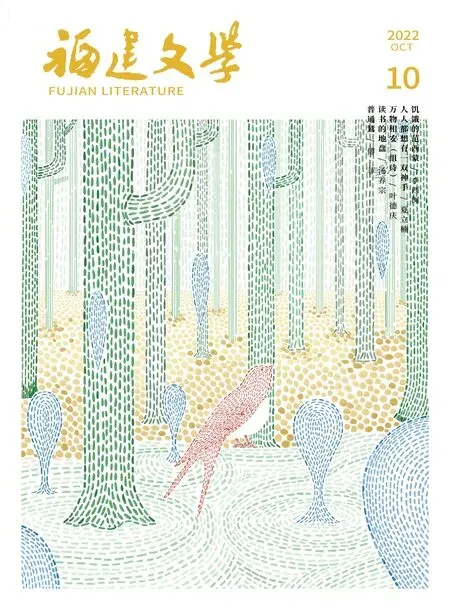苜蓿的诗学
王苑木
1
造一个草原
需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
一株苜蓿,一只蜜蜂
再加一个梦
要是蜜蜂少
光靠梦也行
艾米莉·狄金森没有给这首诗起个名字,她一生写过一千七百多首诗,大多没有名字,都是信手写在纸片上,然后用丝带捆扎起来,束之高阁。如同漫山遍野的杂花小草,在大自然中随机播种,随意生长。
写诗还是随性些好,这样的诗句能散发出天然奇异的光彩,非要刻意起来,字斟句酌,瞻前顾后,便会显得拘束和呆板。对于一首诗,或者读诗的人来说,标题也许并不是那么必要。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有关圣洁、有关死亡,更多的是有关自然,比如天空、山峦、村庄,还比如嶡草、雏菊、水仙、玫瑰、蒲公英、鸢尾花、野蔷薇、蔓虎刺。她写到苜蓿,她的苜蓿在牧场,在村中的庭院,与蜜蜂、与蝴蝶在一起。
用苜蓿去造一个草原。从一株开始,碧绿的苜蓿伸出纤细的茎,茎上再生出三片心形叶子。然后,伸出第二枝、第三枝茎……就这样逐渐铺展开来,从一小丛到一大片,从眼前到远方。再然后呢?开花。花是金色的,小朵小朵,不似油菜花这般的铺天盖地,应是夜空中繁星的样子。这个时候,苜蓿的绿变得浅了,似乎将绿匀了一些给金黄。
这过程中,少不得蜜蜂。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对于一株苜蓿来说,一只蜜蜂是够用了。可一大片的话,恐怕忙不过来。于是全部的蜜蜂都来帮忙,白天忙碌,晚上就住在这苜蓿花丛中。这几天,蜜蜂们真是太忙了,顾不上去看水仙如何摘下它的黄软帽,也顾不上去听大黄蜂有节奏地敲击玻璃窗。在这4 月里,当苜蓿花开遍整个草原,它便成了一个梦。苜蓿们在梦中繁衍,也在梦中逐渐老去。
艾米莉·狄金森的花园,在安默斯特小镇上。4 月的花园,被她比喻成小床,床上有雏菊、鸢尾花,金钟花和圆胖的黄水仙在摇篮里,杜鹃沉醉于梦中,醒得最早的是小小的蒲公英,藏红花眨动着眼睑,当蔓虎刺醒来时,整个山林已经红遍了。在江南绍兴有一座同样意味的花园,那座花园(其实是菜园)名叫百草园。那一年4 月,我漫步于百草园。见到那棵高大的皂荚树,也见到了热烈的菜花、肥胖的黄蜂和“噗——”的一声冲天而去的云雀。最欣喜的是,在一圈半身高的竹栅栏脚边,见到一丛苜蓿。那一丛苜蓿肥嫩油绿,还没来得及开花。
2
在江南,苜蓿有个通俗的名称,叫金花菜。它是一种家常菜,生长于每年的初冬至来年的初夏。可以煸炒,可以烧汤。鲁迅在对百草园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它,但作为一个菜园,而且是位于江南的菜园,苜蓿的存在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它或许就像我遇见的那样,只是一小丛,偏安于竹栅栏的一角。也或许是一大片,如绿色的云朵覆盖着潮湿的泥土。它的根部也会有昆虫出没,至于油蛉、蟋蟀、斑蝥,那是属于夏秋时节的,苜蓿的季节应是另外一些,有蚯蚓、土蚕。撩开匍匐的根茎,就会见到松软的泥土表层上某条蚯蚓露出的一小截尾巴。5 月中下旬时,苜蓿已经结好了籽。它的籽盘子状,带着钩,如微型的风火轮,轻巧地挂在有些老的茎上。它们在等着一只猫、一条狗、一只野兔窜过。要是没有猫、狗、野兔,有一双脚走过也行,攀上布鞋、裤角,也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一株苜蓿都是一颗少年的心,它们的叶脉里印刻着对远方的向往。远方有不同质地的土壤和环境,有异于寻常的阳光和风雨,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总之,远方有着无数的新奇和诱惑,这一切怎能不令人心花怒放,甚而孜孜以求呢?
如何去往远方?植物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一棵树的方式是努力向上,长得高,便望得远。一叶浮萍的方式是顺着溪水随流而去,水静之处随遇而安。一朵蒲公英的方式是跟着风,东南西北,翻滚飘摇。不须担心颠沛流离,也不必怜悯跋山涉水的艰辛,万物自有一套生存延续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又无不蕴含着几千年来颠扑不破的哲理。或许一只鹰会在树上小憩,它会告诉树更远更远的地方正有事发生。一条鱼经过浮萍时,会带给它大海的信息。而东西南北的风总会将蒲公英邮递至宁静而又温润的山坳或者原野。
苜蓿也一样,它会抓住任何机会,跟着猫、狗、野兔……一切能带上它的生物,去寻找远方。两千年前,它们的祖先就是被一匹骏马带来了中原。有一首诗,这样讲述它们迁徙的方式:
苜蓿来西域,葡萄亦既随。
胡人初未惜,汉使始能持。
宛马当求日,离宫旧种时。
黄花今自发,撩乱牧牛坡。
——宋·梅尧臣《咏苜蓿》
如今,它们早已扎根于此。成片成片的绿,细细碎碎的黄,如印在大地上的彩霞,将牧场装点得缤纷缭乱。而它们的祖先已化作天上的云朵,以更为轻盈、更为自由的姿态流动着、变幻着。大多时候,祖先们只是静静地浮在空中,东一朵西一朵,看似随意却错落有致。它们与马的祖先、人的祖先,其他一切生物的祖先都生活在天上,与地上的苜蓿、马、人类从无往来,却又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在它们飘过某一片苜蓿的头顶,遮蔽了些许阳光时,苜蓿们会抬头望向它们的祖先,会想起这些深沉的、厚实的,那些稀薄的、散逸的,都是飘浮在蓝色之中的前世。这一刻,现世与前世遥遥相对,竟惹出无限思愁。
有时,会飞过一只鸟。它披着黑白相间的袍子,从云端落下。袍子的黑色是在穿过乌云时被染上的,而那喙、翅膀尖和尾巴中段的白色,却是它于白云之中潦草洗漱的结果。它从云层间飞来,停在苜蓿地里,跳跃着找寻苜蓿的耳朵。它要告诉苜蓿们有关祖先的预言和忠告,要它们懂得,在舒展肥嫩的叶子时,会遭遇凛冽的寒风,在盛开金黄的花朵时,会有大雨迎头泼来。一切的不确定,一切的曲折磨难,都是上天的安排。对于生活,修饰它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纷繁复杂。
而那些磨难与曲折,那些纷繁和复杂,又造就了苜蓿们的倔强,一种深入骨髓的倔强。我见过傍着君子兰的苜蓿,只有一支细若发丝的枝条,蜿蜒向上,柔弱的样子令人心疼,可就在肥厚硕大的君子兰旁边,在这支柔弱蜿蜒的枝条顶端,居然开出一朵纤细的金色花朵。我还见过它们在萆草丛中肆意伸展,其叶蓁蓁,将所有被萆草不屑的黄泥地表满满盖住。它们的梦想,无论是卑微的,还是伟大的,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它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我们善意的回应。当它们将细弱的茎伸进白菜地里,我们不应粗暴地割去,让它们与白菜共存吧,它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为我们提供食物。当它们结出的籽刺到你的皮肤,我们不应咒骂,它只是想让我们捎它一程,寻找远方的新家。当它们的叶子枯萎,嫩绿的枝茎变成棕黄色的老藤,我们不应遗弃,将它们翻个身埋入土中,会还我们一堆很好的肥料。
3
苜蓿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怀风。取这个名字的人肯定是位诗人,他是婉约派的,也是豪放派的。微风入怀,是清扬婉兮,是脉脉柔情,是恋人的发丝撩拨心弦。而怀间有风,却有威仪暨暨,豪气凌云。仔细琢磨“怀风”二字,真是美好而有无以言尽的意味。“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一片苜蓿草原,在阳光下,时而轻风拂过婀娜摇曳,时而骤风刮起波浪汹涌,好不壮观。
草木的名字好听者众多,甘蓝、茭白、芫荽、芹菜、香椿、莼菜……它们在愉悦味蕾的同时,还在食客的心底留下一首诗。
翻阅前人的诗集,苜蓿往往与骏马如影随形,它们一起出现在关于战争的史诗里。《伊利亚特》中有这么一段:
最英勇的战士是特拉蒙王之子埃阿斯,
阿喀琉斯却还在生气,他本是最强大,
为佩琉斯的无瑕儿子拉战车的两匹马也最强。
可是他待在海船旁边,
对阿特柔斯的儿子、士兵的牧者生气,
他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
标枪,拉弓射箭,他们的马在车旁
吃沼泽里的苜蓿和芫荽,战车存在
他们的主上的营帐里,用布覆盖严密。
无论是阿喀琉斯的神驹,还是那些普通的战马,都喜欢苜蓿,仿佛苜蓿就是因马而生的。苜蓿与马如一对搭档不可分割,在特洛伊城外,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马儿生活的地方,都存在着云朵般的苜蓿草场。
崚嶒高耸骨如山,远放春郊苜蓿间。
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
——唐·唐彦谦《咏马》
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
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
——宋·陆游《秋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料想,这粮草之中便有一捆又一捆的苜蓿。匍匐于地的苜蓿借助于一匹匹骏马实现了它高贵的梦想,这是苜蓿的智慧,更是马的幸运。
然而,苜蓿并不只是马的食料。薛令之的一句“苜蓿长阑干”,又将苜蓿摆上了贫苦人家的饭桌:
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
——唐·薛令之《自悼》
从此,“苜蓿盘”也成了清汤寡水的代名词。《儒林外史》中余大先生一句话:“我们老弟兄要时常屈你来谈谈,料不嫌我苜蓿风味怠慢你。”那苜蓿便有了粗茶淡饭的意思了。
风物、战争、贫寒,苜蓿代表着什么?从不是固定的。时代的变迁,诗人们心境的不同,便赋予它各自的意象。而今说起它,除了春日尝鲜、绿色生态,还会令人想起什么呢?
4
汪曾祺先生是文人中的美食家,菜蔬肉食、米面葱饼,四方食事、咸淡江湖,在他笔下有腔有调,有趣有味。想起故乡的野菜,他着重介绍荠菜,可凉拌,可用来包馄饨。还有蒌蒿炒瘦肉,马齿苋用作包子馅,莼菜烧汤。却没有说到苜蓿。我寻思这苜蓿在高邮可能不常见,也或许对不上老先生的胃口。不过,精于美食的他怎能放过这一味家常菜呢?在他的一篇美国见闻中,终于提到了苜蓿。那些苜蓿长在“五月花”公寓对面的草地上,在羊胡子草之间,他说:“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上海人叫作‘草头’或‘金花菜’,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到此,还不忘调侃一句:“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知道了,也没用,美国人不会炒菜。”读到这里,不禁莞尔,仿佛看到老先生狡黠一笑。
汪老提到的这道菜叫作“酒香草头”。听上去带着点粗犷,似乎与绿林好汉有关,吃起来倒是柔嫩润滑的,因为用的是苜蓿草的嫩头。农家采摘草头都是徒手,一小把一小把地抓取,手法轻盈,三五分钟便有蓬蓬松松一篮子。大多用来烧汤,最为寻常的是草头蛋汤。先将鸡蛋炒熟,再倒入水,待水开了,将草头直接下锅。碧绿的草头浮在汤中,嫩得几乎入口即化。
苜蓿晒成干,可以保存较长时间。苜蓿干烧土豆条,是长江之尾启海沙地的特色菜,一年四季都能做。本地人做菜与别处不同,最大的特点在于汤水。每道菜,汤水的量总是介于热炒与菜汤之间,比热炒多一点,比菜汤少一些。因此,便不分炒还是汤,都用白瓷大碗盛着。这碗苜蓿干烧土豆条亦是如此,一碗菜加半碗汤水,正好。做这道菜,我表哥最拿手。早年,他在部队里当炊事员,负责干休所几位老将军的伙食。老将军们不喜鱼肉,专挑地里长的粗粮野菜吃。有一年,表哥探亲结束,带了半袋子苜蓿干回部队,在食堂做了一碗苜蓿干烧土豆条,把人们乐得不行,多吃了好几碗饭。
这碗苜蓿干烧土豆条鲜香微咸,有草原的味道。苜蓿干中留有少许青春的倔强,土豆条却松软醇厚,再有一些辽阔融入了汤水间,便成了人们纾解怀旧之疾的一味药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