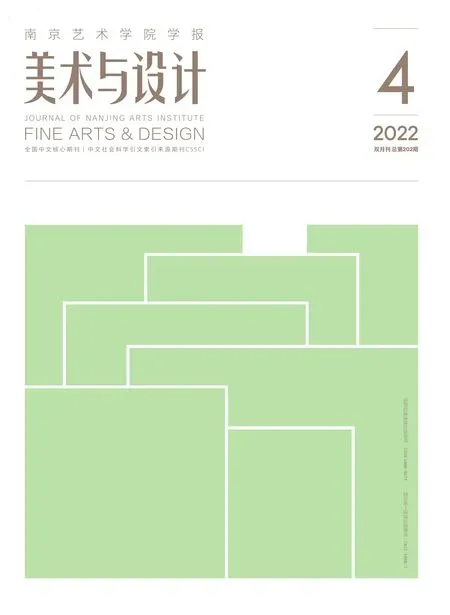文化铸魂 医艺交融
——诸乐三及其绘画艺术刍议
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2)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的美术家个案,迄今为止,诸乐三先生还没有得到他理应得到的充分重视和全面深入的研究。
全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氛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诸乐三及其艺术的人格魅力、历史价值和艺术美学价值。
纵观其一生,毫无疑问诸乐三(1902-1984)乃是中国现代中国画坛的艺术大家和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家。他的名字往往与潘天寿、吴茀之列在一起,而他自己有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和研究价值。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指导诸乐三绘画创作的艺术思维和绘画观念有其特色,它不但来自其学画教画研究创作的漫长历程和锲而不舍的美学求索,而且又与他的学习中医悬壶济世的经历相联系。这在已知的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当中是相当罕见,也是让人深思的。他的医学成就显豁卓著,他的艺术成就出类拔萃,两者在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土壤上得以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本文试图结合诸乐三的生平经历、艺术理念和绘画创作,探讨其如何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魂聚气,育德传道,基于此如何将医艺相融,外化为水墨丹青的形神意境。笔者祖籍孝丰,37年前进入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时,诸乐三先生刚于一年多之前逝世,笔者无缘相识和求教于这位乡贤、前辈,深感遗憾。然而心中对这位画界大家倍感亲切,崇敬仰慕。惟愿此拙文能够多少有助于人们了解诸乐三先生,有助于其人格艺术的传播和弘扬。
在诸乐三身上,可以看到一位中国优秀文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坚守。终其一生,他研习、持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毫不动摇。从根本上说,中国书画具有文性,中国书画家应有文心,首先应当做一个文人。“文人,文德之人也。”文心是诸乐三这位真正的书画大家的初心,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定力。《周易·贲卦·彖传》有言:“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正义》疏云:“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说的是用传统经典教育、涵养人,使之成为“文德之人”。诸乐三正是在文德之教熏染之下成长起来,终身而为“文德之人”。
早在1948年,诸乐三就明确表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他说:“我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各有其特具的文化,尤其是在艺术作品上,表现得更深切,它不但代表了作者的个性,还反映了整个民族的特点,换句话说:没有了这个特点,就不能代表某一个民族的文化。”“无论音乐、绘画、诗歌、戏剧……没有一件不是在一个系统——东方哲学之下发展的,而且某一个时代有某一个时代的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反应。”“在我们悠久的中国文化历史上有丰富的绘画遗产,我们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应当尽所有的可能来建立中国民族的新美术。”时年46岁的诸乐三已越过人生的中途,更加坚定自己的正路。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令今天的我们由衷赞佩和敬仰。1962年9月8日在“黄宾虹画展座谈会”上他表示:“(黄宾虹)这种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心声。
诸乐三的文人秉性可以说是自幼开始养成的。诸乐三的父亲诸献庄好诗文,擅金石书画。诸献庄有六子二女,个个亲近、研修传统文化,后来皆精通诗文书画。而诸乐三的舅父吴昌硕的文化造诣和诗书画印成就更是堪称高峰,毋庸置疑。诸乐三入私塾,从塾师梁漱石习唐诗、“四书”,撰写对联,十三四岁能赋诗、笔下一手好书法,又喜摹画花鸟和戏曲人物。其父乃清末光绪年间秀才,塾师曾为拔贡,皆为彼时乡间为人尊重的文化人。在清末的社会环境当中,加之让人艳羡的家族传统文化氛围,诸乐三的启蒙教育便顺理成章地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被文化传承人领上传统正路。这之后他研修中医,精习画艺,探究创作书法篆刻诗词,亦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
在其成长的过程当中,诸乐三屡屡遇见文化高人,其受益之丰、领悟之深,进而创造之精,都是常人所不及的。这种文化交往圈对一个人艺术观念和创作思维形成的影响同样相当重要。仅以诗词为例,诸乐三就曾受教于诸宗元等人。他回忆道:“有时我和三哥(诸文艺)作了诗还常拿给诸宗元先生看,宗文先生在诗文书法上的功力很深,常常对我们谈作诗的格局、流派和某某朝代的特点。”绍兴人诸宗元乃光绪举人,任知府等,乃清末民初颇有声望的藏书家和书画家,曾参与创办《国粹学报》,著有《大至阁诗》《病起楼诗》《箧书别录》《中国书学浅说》《书法徵》等,也曾与诸乐三谈论书法。早在1923年,诸乐三就有诗作《白荷篇》发表于诗刊《沧海》第3期。他的诗歌创作贯穿其一生,佼佼者如《雪中孤山探梅》(载杭州《东海》1961年第11期),《集龟甲文短歌》(诗书双绝,文后题有“集甲骨字作短歌一首辛丑残腊灯下篆诸乐三”,载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1981年第7辑)。
文化进入一个人的内心血脉,结合其本有的气质,便会处处显现出来。诸乐三温厚待人,有儒者风范,这种秉性气质自然地体现在他的绘画当中。曾经亲聆教诲的朱颖人分析道:“诸乐三先生的笔墨线条,属温柔敦厚的趣味,柔中见刚,浑厚古朴,行笔不迟(疾)不缓”“(用笔用墨)诸乐三先生力求稳重而得其厚实。”
无论在艺术史发展历程上,还是在当下美术现场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绘画领域的集中显现是在所谓文人画方面。有研究者讲得明白:“所谓‘文人画’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一向被视为极具特色的现象。它的若干内容甚至被引来作为整个中国悠久绘画传统的特质,有的时候,它也几乎成为传统的别称,被论者在评述中国文化时作为中国艺术的代表。”自觉地以中国传统文化熔铸灵台心魄的诸乐三便是坚定不移地在文人画的法则规范和审美标准的范畴之内展开其艺术创造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法则标准具体化为画外功夫的重要性和诗书画印和谐一体之美。对此,诸乐三晚年在77岁时在评论、赞赏恩师吴昌硕的艺术时回顾了自己所一路走来的大道正路,他说:“(经由向吴昌硕学习)我体会到,一个画家要懂得诗词题跋,这样绘画的意境就高。所谓诗情画意,就是要求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会诗,‘情’就出不来,诗格不高,画意也不会高。”“吴昌硕先生的画,就是诗文、书法、篆刻融为一炉的集中体现……使人百看不厌,寻味万千。”同时他感慨时下中国画教育、创作的弊端:“当前美术界、教育界较多注重单一的画画方面,而不同程度的忽视了画以外的素养……要造就新一代中国画家,应当具备全面的修养,才能使我们的绘画雄立在世界艺术之林,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诸乐三在教学中也一再强调要追求诗书画印的协调结合,对学生说“没有书法的修养,在金石篆刻中就不会有墨气;反之在书画上,若没有金石篆刻的实践经验,书画上也就不会产生古拙的金石味。”“作画前最好先有诗意……然后生发画意,这样才能有意境”,诗画能否达到相得益彰要凭“根底”。诸乐三这里所说的的“根底”显然不仅是指写诗挥毫技艺技能,而且更是指文化修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把握体悟,亦即画外功夫。诸乐三倡导画家的文化“根底”和诗书画印相融合的意思,也多次通过他纪念和赞美潘天寿、郑午昌等艺术大家的文字,加以表述和强调。今天我们读到诸乐三为黄宾虹的《画学篇》(初名《画学歌》)撰写的《画学篇解释》(又有黄宾虹的批注),可以窥见诸乐三的中国画史画学理论和中国历史文学方面的“根底”。诸乐三自己也是创造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和谐之美的佳作的大家。诚如王个簃所言:“乐三的各项艺术熔冶一炉,对题跋款识和运笔运气等各个方面也别有心得,因此作品中韵味精邃别饶佳趣,曾得昌硕老人评语云:‘乐三能得我之神韵’可以概见乐三成就之深异乎寻常。”
诸乐三守正创新,卓然大家,其魂便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一位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却曾是杏林高手、医道专家,貌似完全不同的两者在诸乐三身上究竟是如何统一在一起的,这种异于常人的情况究竟能够给人以哪些启示呢?
众所周知,如果说诸乐三的传统书画教育始于蒙童时期,从父,继而从塾师学习古书文辞金石书画,萌生对书画艺术的爱好并且持续其一生,那么他的现代教育则可以说是从1916年15岁入孝丰县城的县立高等小学堂正式开始,继而1919年18岁考入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接受现代专门教育的。1920年,诸乐三转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他学习中医的时期,他有幸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颇大的中医专家和医学教育家,两者同时也都是杰出的文化名士,就是何公旦和曹拙巢。前者当时任教中医内科,系杭州名医,从儒通文,好诗词,兼善书画。后者亦名冠杏林,时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主讲《伤寒》《金匮》,为经方派代表人物,后人尊为近代纯粹“经方大师”,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等中医著作传世。曹拙巢光绪二十六年中举,绝意仕进,深研医道,一生悬壶,治病救人无数。他高节清风,富有民族气节,八一三事变后自沪返乡,拒绝任伪维持会长,1937年12月7日痛斥日寇暴行,当场惨遭杀害。诸乐三终身难忘的这位恩师文化修养很深,行医之余攻诗文擅书画明艺理,与任伯年、吴昌硕人称“岁寒三友”,有《梅花诗集》《气听斋骈文拾零》留存。曹拙巢好画红梅,风骨寄寓笔墨之中。
曾经作为一位中医师的诸乐三年轻有为,拔丛出类。1921年时年20岁的诸乐三就经审查合格加入了“上海市国医学会”亦即今称“中医学会”。1922年时年21岁的诸乐三在沪上《中医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有四字骈文祝词,同时在该期发表中医论文《噎膈反胃症候各殊而治法均忌纯用香燥论》《少阴负趺阳为顺释义》,医学验方《神效生肌膏》以及诗作三首。越明年,他又发表了医学笔记《养和斋随笔记》。1923年他还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民国名医丁甘仁之命编录其撰著《思补山房分类医案》八卷。是书至1967年暮秋,经诸乐三两次增补完善,诸乐三并撰写了《思补山房医略》,在“前言”中写道:“余执卷丁师门下,已逾两载,虽能得其治病之大诣,而方药之增减,犹未能尽谙其意,因录此编,匡我不逮。及后四十五年丁未暮秋,余将此编稍加整理,并在编中增入脘腹痛、关格、膈气、噎膈、反胃、消渴、肠痔。”时隔45年,早已以中国画教学、创作为主业的诸乐三依然能够在中医学领域展现自己的学术素养和专业水平,令人感佩万分。更晚的一则文献记载出现在1980年初夏,亦即诸乐三谢世4年之前。省报上一篇诸乐三专访文章《彩笔浓墨画深情》当中,采访者写道:“进入诸乐三家里,只见画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墙边书架画柜上满是书籍画稿,‘突然我发现诸老案头还放着几本中医书’‘非是爱好,而是我的老本行了。’诸老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指着这几本药书给我介绍起来。”诸乐三深情回忆了恩师曹拙巢先生,讲到曹先生的气节和被害,擦了擦泪花继续说:“从这时我才明白,画家的画笔也是一把匕首,一支投枪,不仅能为人民增添美的享受,而且还能画出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心愿。从此,我也更爱自己手中的画笔。” 事实上诸乐三的中医情结贯穿其一生,而且不时地表现在行为实践之中。就中可见诸乐三对中医的热爱和明理得道,更是深明中医并不与艺术相隔绝的道理。
虽说诸乐三一生主要以绘画成就名世,他的绘画生涯和他的中医生涯其实是交织在一起,常常很难剥离的。前已涉及,他的艺术学习起步既早,又是在多位画坛大家艺林高手教导、指引之下行稳致远的。在沪学医时,1920年九十月间,诸乐三拜时年77岁的吴昌硕为师学习艺术,亲聆缶师教诲。这件事对于诸乐三非常重要,自此缶师成为对诸乐三的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的确,“乐三早岁出其门下,于诗书画篆刻皆能深入堂奥,缶老存日,每予称道其好学,良非虚语” 。1922年经曹拙巢推荐,诸乐三加入诗社“沧社”,参与诗歌雅集,他多次受赠曹拙巢所精心绘制的梅花图。在沪5年,诸乐三还与诗书画名家任堇叔、朱孝臧、诸宗元、王一亭、王个簃、俞雨霜、潘天寿、朱屺瞻等交往,得益良多。中国艺术的学习,除却良师教诲领上正路,益友交往,和学子本人孜孜不倦、业精于勤,学子的天赋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诸乐三聪慧颖异,悟性超常,对画学领悟既深,运用又巧。他在绘画方面“出道”也是很早的。他在沪上学医、行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画了。先是替去日本考察的仲兄诸闻韵到上海美专上课教画,因教学效果好而受校长刘海粟等赞赏,故而“中医学校毕业后不久,就为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聘请为教授”。1930年,他与诸闻韵协同吴东迈创办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任文书课主任兼校医,同时教中国画。1932年至1937年,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医师、中医内科主任的诸乐三同时在新华艺专、上海美专等校教授中国画、篆刻和画学,常常是上午门诊,下午教画,角色转换自如。后来又替诸闻韵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篆刻教学。抗战胜利,1946年11月起,诸乐三应聘任教于国立艺专,先是在沪杭两地艺术院校隔周上课,1947年辞去上海美专教职,定居杭州,自此专心在国立艺专任教。之后三十余年,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诸乐三也接受时代洗礼,经历波折坎坷,有过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对诗书画印艺术的挚爱和精研,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懈怠,终臻艺术高峰,成为中国画大家。
纵观诸乐三中医和艺术交织的一生,细读他撰写的文字、他人的记忆评介和他的绘画等创作,可以发现,在这位异乎寻常的绘画大家身上医艺两者是交融的,使得他生命力集中投入的绘画,包括绘画理念、见解、教学和创作,有其个性特色。这种交融的基础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医学与绘画的共通性,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医学和艺术的共通性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医和艺,从根源上说都有关技艺。实际上,中文当中的“艺术”和“美术”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词都是外来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经由日语引进的,日语则是意译自英语的art。根据这同一个英语词,日语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分别译作“芸術”(geijutsu)和“美術”(bijutsu)。而art又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英语art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所说的τεχνη(音近tekhne),其含义不是近代意义上所谓“美的艺术”,而是指技术、技能、技巧或技艺,涵盖相当广,与“自然造化”相对。在当时,古希腊人“专门职业、行业、手艺和美的艺术全都是用一个名称称呼,并且都被认为是合理的系统性活动的例证”。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留下一篇《箴言》,其中有人所共知的名言“人生短促,艺术长存”,这里的“艺术”就也可译为“医艺”。古罗马人的古拉丁语中的ars是art的直接源头,与古希腊语中的τεχνη相类似,“意指完全不同的某些其他东西,它指的是诸如木工、铁工、外科手术之类的技艺或专门形式的技能。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没有和技艺不同而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种概念”。到了20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还曾针对医学明言:“医学恰恰是一种‘艺术’,一种工艺……它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一门应用科学。”从技艺技能手法和锲而不舍工匠精神的层面来说,医学和今天所说的艺术,譬如说绘画,的确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通相合。
医和艺都需要主体对客体心灵的感悟。医生应当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原则,诚心治病,仁心救人,用生命以济危急,就要了解患者的个体特征,关怀、恻隐患者,与对方心灵沟通,方能对症下药,取得理想效果。是为仁医。而绘画,诚如黑格尔所言,“绘画以心灵为它所表现的内容”。他又说:“理想的艺术作品不仅要求内在心灵显现于外在形象的现实界,而且还要求达到外在显现的是现实事物的自在自为的真实性和理性。艺术家所选择的某对象的这种理性必须不仅是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到感动的,他对其中本质的真实的东西还必须按照其全部广度和深度加以彻底体会。”据此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就像诸乐三的不少作品,既是画家内心情愫借助笔墨投射出来,渗透和展现在画上形象当中,也表现出画家所描绘东西的被认识到的某种本质规定性,亦即“理性”,一个重要前提是画家真正为描绘对象所感动,并且的确有高度和深度上的彻底体会。中国画家眼中,一木一草,一山一水,莫不有生气贯乎其间。画家可以吸纳此生气,亦感悟对象,乃至全身心的投入和忘我。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是中国画学所强调的。这些对象可以是中国画传统母题梅兰竹菊“四君子”之类,也可以是画家独特发现和体会到的新母题。1973年时年72岁的诸乐三创作有一幅《棉花图》,今藏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水墨设色,墨色颇丰,行笔劲健,如写如篆,棉朵淡墨略染,棉株干枝施以淡赭。构图取势略呈U字形。画面左侧竖题诗款。诗云:“花开吉贝白茸茸,闪烁银光耀碧空。老笔纷披无俗虑,牡丹不画画棉丛。”“吉贝”,又名“美洲木棉”或“爪哇木棉”,梵语或马来语音译,中国古时兼指棉花(草棉)和木棉。画作选材体现了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影响,“老笔纷披无俗虑”则反映出画家的心态。
具体到中医与中国画,在对象的处理方法上也有着某种共通性。有一段回忆诸乐三两位恩师吴昌硕、曹拙巢之间交往的史传文字涉及这一点:“曹家达(拙巢)家住山阴路,常来吴府小坐与缶翁敲诗,也谈医道。他谈及病中阴阳、五行、经络等辩证关系,后来吴昌硕曾对诸乐三说:‘我看治病方法与画面处理的道理是相通的。’”中国画经营位置需整体考虑,讲究开合起结,虚实疏密,“知白守黑”,诸如此类和中医诊病“望闻问切”考虑患者身体种种辩证关系,诚有诸多暗合的地方。
中医和中国画的产生、发展,无不基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笔者曾写道:“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一种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整体与其中有机构成元的关系。”而中医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结构整体当中的构成元,自成子系统。它与中国画,还有其他构成元书法篆刻、诗词文学,乃至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等,有着有机的联系。也可以这样比喻,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干,而中国画、中医中药等皆为生发出来的枝叶。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文化,在中医和中国画领域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宗白华说得精辟:“中国画……以‘气韵生动’即‘生命的律动’为终始的对象”“中国画既超脱了刻板的立体空间、凹凸实体及光线阴影;于是它的画法乃能笔笔灵虚,不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为物传神。”中国画学所讲的“气”“气韵”,本质上就是生命的律动,生命的气息。生命之力,通过心理活动,指引生理的力,使得毫飞墨舞,创造动态之美,在纸素上留下生命律动的痕迹,进而感染懂画的观众,相应地产生审美经验中的律动感并丰富之。诸乐三的画作几乎处处可见那种“笔笔灵虚”和“为物传神”。也有西方研究者说得有理:“有史以来,中国艺术便是凭借一种内在的力量来表现有生命的自然,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同这种力量融会贯通,然后再将其特征传达给观众。”“内在的力量”不只是生理的力量,更是心理的,精神的力量,生命的力量。中国画的生命本质和生命力交流,与中医的情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中医学原理首先讲“生气”,亦即人的生命运动。诚如研究者指出的“中医发现和证明,人的本质不在人体,而在生命运动,建立了‘生气’概念。‘生气’指‘有生之气’‘生命之气’,是中医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和概括”。“气——构成事物的本原”“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气是宇宙万物之间联系的中介”。
筑基于具有创造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画和中医在哲学原理和思维原则方面有着太多的一致和交融。中国古代哲学浓缩和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和内涵特质,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及其理论之间,也在与中医实践理论之间充当中介和纽带。北宋晚期成熟的文人画可以说是“一种微妙的、哲思性的、内省的艺术”。诸乐三主要画写意花鸟画。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审美价值、情感魅力和花鸟画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体现出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反映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亲和性历史特性,是以 “比德为美”和“自然为美”两大哲学原理为指导的。
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以直观的形象为基础,直接接触外物(譬如药材)、人(病人)而获得感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类比推理,获取新形象(譬如许多中药的命名,像“人参”“锦纹”“牛膝”),从具体事物进行抽象来诊断病情等。这颇类似艺术家的形象思维。中医讲系统思维(元整体、有机性、有序性等原理),讲天人同构同律,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而“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等也被归纳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诸如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之类,实则也是中国画学当中一再表述,中国画家屡屡思考、运用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法则。
医艺交融具有的内在可能性,在诸乐三身上变成现实。的确,至今为止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来分析,在诸乐三对自然事物的观照格致体悟、落笔之前的构思和挥毫泼墨在纸上耕耘之时,头脑中是如何将中医的思维原理和行医经验感受,融合在艺术思维之中的。中医学的“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中医文化主张的致中和这种本质上的和谐之美,却是我们每每可以从诸乐三的画作当中解读、体悟出来的。医艺交融在诸乐三那里是自觉践行的,是深入骨髓的,因而在他的诗书画印四美相得益彰的画作当中的流露和表现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显然我们可以从艺术大家诸乐三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就本文不揣冒昧简略梳理和粗浅剖析的内容而言,诸乐三有以下相互关联的两点是首先值得今天的中国画家充分尊重、认真吸取和努力学习的。
一是毕生修炼画外功夫。1959年诸乐三在《介绍吴昌硕先生艺术及生平》一文当中分析道:“先生之所以在近代美术史上能放出这样的异彩,与他的书法、篆刻、诗文等方面的学术修养不可分割,而且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吴昌硕的高足,诸乐三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国学苦修,终身笃行不倦。对他来说,其实中医学也属于画外功夫。诸乐三“善于在平凡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诗情画意,并以他造诣深厚的传统笔墨技法表达出来”。譬如1960年写生的一个留种玉米穗,题句“留待明年种,收获万斛金珠米”。他以棉丛、玉米、西红柿、水稻、芋艿等为主要题材作画,几乎无不精美,这样的眼光和能力也得力于他广泛而深厚的画外功力。
二是画中追求诗书画印和谐之美。这是中国绘画传统的精粹之一,艺术文化的精神财富,继承发扬它我们责无旁贷。但事实上诸乐三四十年前所感慨的中国画教育、创作的弊端,亦即“较多注重单一的画画方面,而不同程度的忽视了画以外的素养”,不说更见严重,至少是不见有显然的改变。画上要见出“四美”和谐,没有相当多的画外功夫是做不到的,这就需要在画外有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
举例来说,诸乐三的画上题款就普遍出彩,值得学习,值得专文研究。其实一幅中国画的自题款识必须讲究,大有学问。其文辞内容,是画题还是诗文或只是“穷款”,是长题还是短款,字数多少,怎么排列,书法如何写,位置在哪里,都不可随便,须结合绘画还有钤印,有一个通盘考虑,谨慎处理。画前有大致计划,画好要再次推敲,方才落笔题款。现在经常看到画好画了题款马虎的情况,甚至是一些专业人士也如此。尤其不可理解的是,诸如画了幅荷花,赫然题个“荷花图”。其实在这里这三个字不但毫无意趣而且是“多余的话”,这本来就是一幅图画,观者又难道不认得画的是荷花?如此画题类似“麻雀解剖图”“水稻生长过程图”生物挂图的标题,直白、重复而缺少文化内涵。实则用“荷花图”指称一幅中国画作品,多是为了确指一件作品以便评说而为,借用结构语言学的一对范畴,就是用一个明白简捷的语言符号“能指”(“荷花图”)来表示相应的那幅具体荷花画作“所指”。类似地,用“李四”指称具体的李四这个人。难道李四自己会把“李四”两个字写在自己脑门上?道理本来明明白白,偏有画家要辩驳:“题个‘荷花图’难道一定有错吗?类似题款名家也有过。”自然不能说“有错”,但高下、雅俗的区别还是有的。诸乐三画作所题款识常见的一是自撰诗文或录他人佳句,如1962年初,作《狸猫图》(139cm×39.5cm),款识:“狸奴神俊姿,雄踞拟狮虎。宵深护仓廪,人静卫书府。食受鱼饭腥,眠就氍毹煦。得惠岂无由,其能在搏鼠。吁嗟呼,眼前鼠子犹窥壁,狸兮狸兮须乾惕。坡公赋已揭其黠。辛丑腊月,灯下诸乐三泼墨并句。”1971年画墨荷题清人王士祯《再过露筋祠》诗句“门外野风开白莲”;一是署题“晓露”“露气”等在荷花图上,要论诗情画趣,“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跟“荷花图”之类画上题名的差别何其鲜明。73年前诸乐三就说过:“当我们创造的时候,如果学力不深,心为槁木,怎么能够心领神会呢?怎么能达到超现实的意境呢?此怀只堪为识者道耳。”中国画学子和画家要努力成为诸乐三所说的“识者”,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缺少画外功夫便难以懂诗书画印之美,更难以创造这样和谐之美;而画外功夫的坚持修炼,又必须自觉地以文化铸魂。这是我们,包括笔者自己,要真诚地向艺术大家诸乐三先生学习的。“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