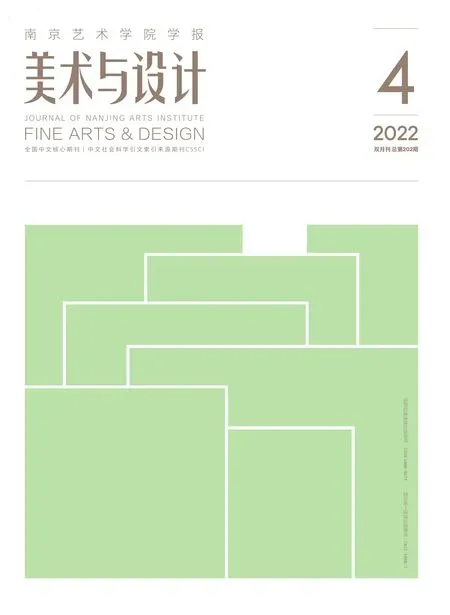诗画之分与文类政治
——菲诺洛萨、冈仓天心与气韵美学的现代发生①
吴 键(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在西方文化与艺术浪潮天风海雨般的冲击之下,其时文脉相通、音信不绝的中日学人与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气韵生动”为抓手进行“艺术”的现代理论话语建构。其时中国学者与艺术家力图围绕着传统“气韵”论言说、构筑并确证着自身的艺术传统与文化认同;日本也希望建构艺术的“东洋”传统来和以普世面目出现的西方艺术与美学相抗衡;而彼时西方正值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之际,同样希望从东方艺术中汲取相关转型资源。在诸方历史合力之下,传统的“气韵生动”论在中国、日本与西方之间展开路径多样的理论旅行。这一理论旅行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前沿热点问题,包华石(Martin J. Powers)、柯律格(Craig Clunas)、稻贺繁美等国外学者以及邵宏、汤拥华、彭锋、张雁、李雷等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为这一宏大论题的全幅画卷添上了不同的亮色笔触。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及了古典“气韵”的现代理论旅行,正肇端于日本学者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1903),其率先以欧美书面语向西方学界译介并阐释了“气韵生动”,更是开启了其后影响深远的“气韵-节奏”阐释路向。但对于这一关键性的起源事件,其内在逻辑与转型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审视与辨明。本文正以此为切入点,聚焦于事件主角冈仓天心与其美国老师菲诺洛萨(E. F. Fenollosa)的相关论说,指出这一现代转型就其外部语境而言,所因应的是近代东西方交融碰撞的全球化语境,与中日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场域。其外部历史语境与内部理论构造发生着密切的耦合与联动,并以W.J.T.米歇尔所言的“文类政治”(the politics of genre)的样态呈现出来,也即通过现代艺术体系中诗与画、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分,在对“气韵生动”进行现代美学阐释的同时,也调适着其间不同的文化祈向与政治诉求。
二、菲诺洛萨:《美术真说》与艺术西潮的变容
经过明治维新的激进西化,其时日本传统美术界一片哀鸿遍野。当此之时,任教于东京大学的美国学者恩斯特·菲诺洛萨,于1882年5月14日的龙池会上发表演讲,凭借着系统的现代美学知识与宏阔的世界美术眼光,为日本古典美术予以强力背书,推动着日本美术由“全盘西化”向国粹主义的历史转进。其演讲稿后经龙池会员大森惟中日译行世,即著名的《美术真说》。菲诺洛萨在这一历史性演讲中,受所习尚的黑格尔哲学影响,贯穿着一种世界史视野与进化论底色,开门见山地指出:艺术史发展本质上依循着一种生物学模型,如草木兴发荣枯,自生发稚弱、伸畅成熟之后便会渐趋衰落。而当下世界美术正处于普遍衰颓之中,不仅西方美术处于文艺复兴高峰之后的波谷之中,中国绘画在唐宋之后也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而日本绘画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同样亟待振兴。
那么究竟该如何振兴日本美术,在菲诺洛萨看来,首先需要从“美学”路径上寻求答案,对各门类艺术普遍共通的性质加以探究。其时西方诸国将形态各异的门类艺术音乐、诗歌、书画、雕刻与舞蹈等都归入“美术”的名号之下,那么循名责实,这些门类艺术必然有一种“共同连带之性质资格”。那么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为何?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共性究竟为何?在此,菲诺洛萨首先批驳了三种流俗的观点:以技术精巧为艺术,以引人愉悦为艺术,以模仿实物为艺术。并且提出他的艺术观。每个事物的整体都由部分构成,恰如众星罗列而成星空浩瀚,部分构成整体的方式无疑是千变万化的,其中大多是单纯地机械性地累加,而当各部分以完全唯一的方式构成一个圆满无缺的整体时,便形成了艺术的“妙想”(idea)。世间纵有万千音声,但只有这些声音以这样唯一的方式构成完满无缺的整体时,才配称得上是音乐,因此声音的妙想即音乐。
菲诺洛萨进一步将以“妙想”为中心的观念论美学,推进到音乐、绘画与诗文三个主要艺术门类的比较之中。每件艺术品都由“旨趣”(即内容,subject)与“形状”(即形式,form)两部分构成,因此艺术的“妙想”又可分为“旨趣”的“妙想”和“形状”的“妙想”。而诗文以“旨趣”的“妙想”为主,以形式为辅,音乐以“形状”的“妙想”为主,以内容为辅,而绘画则居于二者之间。绘画的“妙想”不仅体现在艺术品整体的“凑合”(即统一,unity),也体现在部分的“佳丽”(beauty)。就绘画而言,其形式可以进一步分为图线(线条,lines)、浓淡(明暗,shades)、色彩(color),加上“旨趣”,一共4项,每一项都包括整体的“凑合”和部分的“佳丽”两端,那么一共可以分出8个要素:图线的凑合(unity of lines)、图线的佳丽(beauty of lines)、浓淡的凑合(unity of shades)、浓淡的佳丽(beauty of shades)、色彩的凑合(unity of color)、色彩的佳丽(beauty of color)、旨趣的凑合(unity of subject)、旨趣的佳丽( beauty of subject)。再加上能够自如安排与构思如上各要素的意匠之力(force of subject),以及将之一挥而就、变为现实的技术之力(force of execution),组成了绘画艺术原理的“十格”(ten elements)。可以看到《美术真说》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基本依托于黑格尔的观念论美学。无论是其界定艺术本质的“妙想”(idea,即黑格尔的“理念”Idee),还是将之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以及从“寓多样于统一”来论证艺术美等,都可以看到黑格尔美学的理路脉络运行其间。
虽然在《美术真说》中并未提及,但参考菲诺洛萨自1881年的系列演讲草稿,这一条理分明、逻辑严整,甚至不无叠床架屋意味的原理体系,其潜在的论争对象正是对日本美术也影响颇深的“六法”,在其看来谢赫所提出的“六法”“并非从科学的原则加以演绎,既不严整亦非完善,只是经验的杂凑而已”。因此菲诺洛萨所铺陈的“十格”体系,绝非仅出于纯理论的兴趣,而是要为重新评价中国美术、日本美术与西方美术三者奠定系统性的理论话语基础。在其看来西方舶来的油画恰如磨盘顶石,而中国传来的文人画恰如磨盘底石,而“真正的绘画”也即菲诺洛萨心中理想的日本画介于其间、饱受二者的压迫。菲诺洛萨以系统性的美学知识,论证其时中西美术夹缝之中的日本美术的独特价值。首先针对“西方美术-日本美术”这一向度,从菲诺洛萨的观念论美学出发,艺术的核心在于表现“妙想”,而非模拟现实,因此其时以写实风格见长的西方油画相较日本美术其实也并无优势。而且恰恰因为晚近欧洲画家受科学思潮影响,流于表面的逼真而遗漏内里的“妙想”,才引起西方美术的普遍衰退。日本美术有着自由而简易的表现形式,更易于展现“妙想”,因此西方美术反而应该学习日本绘画简洁纯雅的风格。
而菲诺洛萨在“中国美术-日本美术”之间为后者张目,其间却遍布着理论话语的矛盾与罅隙。因为在《美术真说》所依托的黑格尔美学体系中,艺术史演进产生了三种艺术类型(Kunstform),分别是感性形象压倒精神内容的象征型艺术,物质形式与精神内容完美契合的古典艺术,以及精神内容超越物质形式的浪漫型艺术。菲诺洛萨将黑格尔体系中历时的艺术发展类型史,对应到其时西方美术、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的共时格局之中。其中西方美术执着于表面的逼真写实,而非探索作为艺术本质的普遍理念,舍本逐末地醉心于画面的明暗呈现、色彩的丰富浓厚与物象的错综繁复之中,其中物质形式大于精神内容,隐然对应着象征型艺术。而日本美术有着简易自由的表现形式,正好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妙想—理念”,正对应着古典艺术,作为理想艺术典范代表着世界艺术的发展趋向。正如日本美术研究者高阶秀尔所概括的,菲诺洛萨的艺术立场秉承着“相较写实更注重思想,相较色彩更注重线描,相较多样更注重统一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观”,而菲诺洛萨眼中的日本美术正是这一新古典主义的理想艺术。虽然在黑格尔的艺术发展史论述中,作为理念觉醒更高阶段的古典艺术无疑是高于象征型艺术的,但古典艺术与浪漫型艺术二者究竟孰高孰低,黑格尔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一方面作为古典主义者的黑格尔,无疑对于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二者完美契合、彬彬称盛的古典艺术寄予心香;而另一方面,就其艺术发展史的主线而言,精神内容溢出物质形式的浪漫型艺术,又占据着理念觉醒的更高阶段。因此对应着浪漫型艺术的中国文人画,也比对应着古典艺术的日本画更具有“妙想”,既然如此,菲诺洛萨又如何能凭借这一理论模型为后者张目呢?
菲诺洛萨对于中国源流的文人画的看法,要而言之:“如若把文人画看作是真正的绘画,那么音乐与绘画又有何差别。”在其看来,“夫文人画,缺少作为画之要诀的线色浓淡之统一。所以其中主要部分与次要部分相分离,如以眼目对之,从画之一端摇摇转向另一端,恰如诗由一句转向下一句”。文人画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更近于“音乐”与“诗歌”。有趣的是,在前述菲诺洛萨的美学模型中,音乐长于“形状”的“妙想”,位于形式的一端,而诗歌长于“旨趣”的“妙想”,位于内容的一端,在此却合而论之。实际上,菲诺洛萨此处的理论脉络已悄然由黑格尔变为莱辛,在后者的诗画界限论中,诗歌与音乐同属于时间艺术,而与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相对。日本学者北泽宪昭敏锐地发现了此处莱辛理论的痕迹,并指出在菲诺洛萨这一系列演讲的草稿中确实提及莱辛,并引为同道,称其为“德国最大的批评家”。同时北泽宪昭指出此处“一句转向下一句”的“诗”,实际上指的是诗歌书写,也即“书法”,菲氏在此指出文人画与书法同源,却与绘画异质,因此不得称之为“真正的绘画”。但这“一句转向下一句”的“诗”,并非即指书法,更多是为了强调文人画与音乐诗歌共同具有的时间艺术属性。北泽宪昭虽然点出莱辛理论的影响,但却过快地将这一“诗画界限论”归为“书画同源论”的注脚,遮蔽了这一“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区分所打开的理论空间,实际上其中正蕴含着近代“气韵”跨语际阐释的重要脉络——“气韵—节奏”论的发生线索,需要我们详加审视。
菲诺洛萨从其古典主义艺术观出发,认为绘画需要“各部分布置得宜,将人之心目聚合引向一处,那么余下部分也能同时得以通观。聚合的那一处即为主,其他部分则为次,一瞥之下主次部分尽收眼底”。在其看来,线色明暗的统一是画之为画的本质所在,如果画面无法呈现统一,“美术的妙想”也就无从表现了。而画面之所以需要呈现统一,正是因为只有在画幅上呈现出的是在空间中共同存在、在深度上排列有序、在距离中连续存在的并列事物,才能在眼睛张开或瞥视的一瞬间,将这一作为整体的艺术世界共时地摄入眼帘,在菲诺洛萨看来,这是绘画作为空间艺术的本质要求。但文人画却打破绘画作为空间艺术的本质规定,在其中主要部分与次要部分相分离,无法被共时地摄入眼目,反而使得眼目“从画之一端摇摇转向另一端,恰如诗由一句转向下一句”。诗歌是时间艺术,语言作为诗歌的媒介,需要在时间的先后相继之中才能得以理解。如莱辛所言,诗歌对于各部分的描绘难以显出其整体,“本来是一眼就可以看完的东西,诗人却须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一胪列出来,往往还没有等到他数到最后的一项,我们就已把头几项忘记掉了。但是我们还必须根据这些胪列的项目,来形成一个整体”。在此,菲诺洛萨征用莱辛的“诗画界限论”,通过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对立,将文人画归入后者的范畴,从而将之排除在“真正的绘画”之外。虽然这一看法不无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如其所言“如若把文人画看作是真正的绘画,那么音乐与绘画又有何差别”,这本是对文人画(乃至中国美术)的美术资格的质疑,但却颇具开创性地在现代艺术门类体系中,将中国绘画与音乐诗歌的时间艺术属性相联系,从反面启发了后继者对中国美术乃至东亚美术的阐释。
徐复观在对“气韵生动”的古典阐释史加以梳理后更指出:“在六法成立以后一千多年的绘画范围中,气韵的观念,一直是流注不绝,但中国从来没有画家或画论家,从音响的律动上去体认气韵生动,或由此直接说明气韵生动。”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对于诗与画的紧密关系自有其阐释脉络,但其核心在于强调两者在意境上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形似”与“写意”的问题,并非从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区分的角度加以探究,后者必然在现代艺术体系之下才能得以成立。而菲诺洛萨的日本弟子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1903)中,率先以诗歌与音乐中的节奏(rhythm),来对译作为绘画六法首义的“气韵”,随后英美汉学诸家对此多有呼应。时至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中国艺术史家滕固,在这一阐释脉络中构建体系性的“气韵节奏论”,并在30年代宗白华的对于中国画法空间意识的阐释中呈现出完成形态。宗白华指出“中国画境之通于音乐,正如西洋画境之通于雕刻建筑一样”,“其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宗白华指出对中国绘画山水妙境需“游目周览”:“抬头先看见高远的山峰,然后层层向下、窥见深远的山谷。转向近景林下水边,最后横向平远的沙滩小岛。远山与近景构成幅平面空间节奏,因为我们的视线是从上至下的流转曲折,是节奏的动。”而这不正是让菲诺洛萨对文人画大摇其头的时间艺术属性——“从画之一端摇摇转向另一端,恰如诗由一句转向下一句”吗?
菲诺洛萨认为诗歌音乐等时间艺术如同幽灵与梦魇一般,萦绕在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美术之上。将文人画视为“真正的绘画”,“就如在缣帛上描画笛子,挂而观之,其后吹着真笛,其音声琅琅而从画缣之中漏出,如果有人由此断言这幅画细致优美,那么无论是谁都会耻笑这一妄言”。菲诺洛萨这一譬喻原本要说明文人画之所以得到欣赏,完全是由于其中文学的旨趣,而与绘画的表面无关。但这一比喻滑稽生动,其形象甚至溢出了菲诺洛萨原本的解释,请试想:竹笛清音抑扬婉转,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悠然穿透了绘画的表面,氤氲于画幅内外,弥漫在展示绘画的整体空间之中。原本在时间中定格的画面与在时间中流淌的音乐,在其中纠缠难分,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在其纹理之间却贮满了乐音,萦绕着时间艺术的韵致,这一鲜明的形象自身构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美术的寓言。同时,在菲诺洛萨看来,文人画的绘画表面与诗意旨趣,正如画面上的笛子与画后演奏的笛子之间,是互不关联、断为两截的,因此文人画的画面呈现及其画术技巧,只是构成了一个欺骗性的表面,这无疑透露出菲诺洛萨自身对于中国文化与艺术传统的深刻隔阂。
要而论之,菲诺洛萨的《美术真说》作为明治日本复兴美术的纲领性文献,不仅在当时为日本美术界注入一针强心剂,揭开了日本国粹美术运动的序幕,同时对于本文论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为日本美术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中国美术建立了一套现代阐释范式。虽然在《美术真说》中并未提及“气韵生动”及“六法”,但这一阐释范式却决定了源远流长的“气韵生动”论在近代将如何被言说。具体而言,这一范式从如下三个方面深刻塑造近代“气韵”理论话语。
首先,《美术真说》以系统性的西方美学话语,构筑了分析与评价美术的理论框架——“十格”,如前所述其潜在的论争对象正是作为中国传统绘画准则的“六法”。并在《美术真说》前后的系列演讲中,指出“六法”只是“经验的杂凑”,而非“科学原则的演绎”。自此,对于以“气韵生动”为首的“六法”的阐释就无法只在传统话语中打转,而必须从“科学的原则”出发,也即以系统性的现代理论话语来重新阐述,这正揭开了“气韵生动”论以及所对应的东亚艺术传统的现代阐释序幕。
其次,《美术真说》在整体性的世界艺术视野之中重新对西方、日本与中国美术加以定位,在新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政治框架中论证日本美术的优越性。自此,中日学人对于“气韵生动”及“六法”的阐释,都在全球化语境中生成其独特的文化政治意涵。其中遵循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借以论证自身艺术传统的普世价值,如论证中日艺术具有同西方艺术一样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则以之辨析自身艺术传统与其他艺术传统之间的差异,如正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明治日本,鉴于古典中国在“汉字文化圈”的笼罩性影响,如何与这一血脉相连、影响至深的文化传统辨苗头,更是成为了亟须解决的棘手难题。
最后,《美术真说》在莱辛“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的框架中,指出文人画(及中国美术)的时间艺术属性,从反面启发了近代“气韵”阐释的主流——“节奏论”的脉络。菲诺洛萨《美术真说》在做出如上开创性贡献的同时,也显露出其思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及对东亚文化艺术传统的隔膜,近代东亚美术与“气韵生动”的故事还需要淫浸濡染于这一传统的学者——冈仓天心继续书写。
三、冈仓天心:气韵生动与“东洋理想”的建构
冈仓觉三(OkakuraKakuzo,1863—1913),号天心,是典型的日本明治一代学人:一方面秉承着传统日本学者深厚的汉学素养,另一方面则从明治维新后西学西潮中的天风海雨中汲取滋养。在东京大学求学时期(1877—1880),冈仓遇到了对其一生至关重要的老师菲诺洛萨。虽然冈仓天心与菲诺洛萨之间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但二者投向东亚艺术的探索目光却并非均质而同一,其间存在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视差”。
1886年,冈仓天心与菲诺洛萨受明治政府委派赴欧美考察各国美术制度,归国后发表相关演说。在菲诺洛萨看来,这趟欧美艺术之行正好印证了先前《美术真说》中的判断,西方美术已经“机能枯竭濒于死地”,与此对照的日本美术则是“活跃生动而神采奕奕的美术”,因此需要日本美术坚守“固有的妙处”、而不丧失“固有的性质”,这样就能“执世界美术之牛耳”。菲诺洛萨所热情拥抱的这一完美无瑕的日本美术,与其说是一种实态,毋宁说已经成为其艺术理想的投射,日本美术在西方学者这种理想化因而也是本质化的目光之中,成为了一种“物恋”(fetishism)的对象。与此恰成对照,冈仓天心则在归国演说中,反而质问美术上的“纯粹的日本论者”:“日本固有之物究竟在何处?”如果历叙日本美术发展的各个时期,无不在东亚语境中与朝鲜以及中国的唐、宋、明、清各朝代艺术血脉流贯,要从中剥离出日本美术的“固有之物”无疑是不可能的。这一日本美术对于冈仓天心而言,绝非某种僵化的“物恋”对象,而是亲身所处的、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活的传统”。要为这一“活的传统”建立一套现代历史叙事,冈仓天心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如何界定日本美术的特质与边界,并以此论证其与西方美术一样具有普遍价值,同时又能避免对日本美术的本质化理解,一方面使之涵纳东亚艺术演进的既往历史,一方面使之能够吸纳与包容其时的世界艺术新潮。
由此,在东亚美术史的建构之中,冈仓天心逐渐拈出了“气韵”作为叙事的核心范畴。时至1890年,菲诺洛萨踏上了回国的路程,留下“日本美术的恩人”的余影。同年,年仅27岁的冈仓天心出任东京美术学校的校长,并开讲美术史课程,其讲义以《日本美术史》(1890)为名行世,是日本美术史的开山之作。因为在该书中,冈仓天心采取中国美术史与日本美术史并进的叙述法,在勾勒日本美术史的完整轮廓的同时,也为中国美术构建了一套现代历史叙事。因此,如林少阳先生所言“《日本美术史》不仅是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日本美术史,也可以说是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论”。其中冈仓天心突出中国六朝时期融合南北文化与艺术,开启唐宋文化源流,在整个东亚艺术发展史中的价值与意义,并指出六朝美术能上承秦汉而臻至美术高峰的一大原因,正在于以谢赫“论画六法”为代表的艺术鉴赏论的发展突破:
六法第一即气韵生动,以表露高尚的思想为旨归。以此置于首位,是为了强调画之本意以气韵为主。六朝作为孕育了后世唐宋文化的源头,气韵生动正道破了东洋美术的第一义。如果那时画论之中,不重气韵而以写生为主义,现在的东洋美术必然另是一类体系。
冈仓天心紧接着在这一课程讲义中,颇为平实晓畅地历叙“六法”的意涵,思路脉络并未多有突破传统解释之处,但依然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气韵生动”不仅是中国美术的特质与法则,而且“道破了东洋美术的第一义”,是作为“东洋美术”整体的普遍价值追求而得以强调;其二,“气韵生动”具体体现在“骨法用笔”中,即以“有肥瘦之幅”的“线条”与“孕灵妙之情”的“笔墨”,来呈现一种超越于“形似”的“妙味”。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美术史》中,冈仓天心以“六法”为理论框架与评价标准,来对其时的各派美术加以品评。其中“文人画”偏执于六法中“气韵生动”一端,而失落了余下数端,从而导致画面物象杂芜、笔力非健,相比绘画更近于文学。而日本古典画派狩野派专注于骨法用笔,而缺乏象形之妙,也就难以成就气韵生动。同时西洋绘画以及日本四条派绘画,也仅长于应物象形,而当时在西方艺术界风行一时的日本浮世绘则仅长于随类赋彩。因此在冈仓天心看来,其时的各类美术往往只是长于“六法”中一端,自古及今,能够六法兼备的真正美术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冈仓天心对于其时各家美术的如上评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菲诺洛萨《美术真说》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文人画的评价),但与之却有着根本性差异,即菲诺洛萨认为必须从系统性的西方美学知识出发,所以构建“十格”系统来分析其时的世界美术态势,而“六法”等东方艺术观念作为“经验性的杂凑”不能作为普遍性的法则。但冈仓天心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六法”是“古今论画的真正法则”,其普遍性并不仅仅局限于评价中国美术,甚至可以作为衡量包括日本美术的在内的“东洋美术”,乃至包括“西洋画”在内的世界美术的普遍标准。其后居于“六法”之首的“气韵”观念成为冈仓天心统合东亚美术脉络,抗衡西方美术传统的重要抓手,甚至在189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明确指出与作为西方绘画长处的“写实”相对,日本绘画(而非“东洋绘画”或“中国绘画”)的真髓就在于以“气韵”为重。
冈仓天心1902年于印度旅次以英文写作的《东洋的理想》一书,次年在伦敦出版。在其中,冈仓天心再次强调了谢赫《古画品录》及“六法”的重要作用:“在老庄精神的培育之下,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系统绘画论以及第一部画家传记。与此同时,它为中国以及之后的日本美术绘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其中首次以英文翻译了“六法”之中的前两法“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
第一法则“贯穿于万物律动中的精神之生命跃动”( “The Life-movement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Rhythm of Things”),艺术就其自身而言,是宇宙天地之精气,因循着事物的调和之法即节奏,而无往不复地运动着;第二法则“骨与用笔的法则”( “The Law of Bones and Brush-work”),关涉于绘画的构图与线条,根据这一法则,创造的精神下沉为绘画的构思之时,就不能不生成了作品的有机结构。这一具有宏大想象力的结构,形成了作品的骨架。其后以线条刻画作为作品的血管与神经,以色彩来为作品蒙上皮肤。
细察冈仓天心的英译,实际上将“气韵生动”中的“气”与“生”、“韵”与“动”互相为训,阐释为“精神—生命”(spirit-life)的“节奏—运动”(rhythm-movement)。在冈仓天心的这一跨语际阐释中,有两点影响深远的翻译思路,一是将“韵”翻译为“rhythm”,二是将“气”翻译为“spirit”,有学者认为这样“过于简单的译语”难以呈现“如此重要的文论与画论术语”。但其实在冈仓天心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rhythm”还是“spirit”都不是简单的一般译语,虽然这段文字篇幅并不长,但在其中凝缩着不同的思想脉络,对此需要结合《东洋的理想》的整体脉络与思想语境加以分析。
首先,冈仓天心以“rhythm”(节奏/律动)来对译“气韵”之“韵”,正式开启了“气韵生动”的现代阐释中最为主流而影响深远的“节奏论”建构脉络。虽然汉字“韵”有“韵律”之义,但正如徐复观所言,以音响之“韵律”来直解“气韵”之“韵”,在中国古典文脉之中却是前所未有的。“韵”字起于汉魏之间,至北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在其新附字中著录“韵”字条。一般认为,“韵”字产生并流行于汉魏六朝间,与其时的人伦鉴识有着密切关系,在其时《世说新语》等典籍中,涉及人物评藻时多称“神韵”“性韵”“骨韵”“风韵”“雅韵”“远韵”等,已经脱离了音乐音律以及诗歌韵律的本义,而引申为人物整体的风神气度及审美人格。同时,由于其时的绘画主要以人物神佛的画像为主,所以人伦鉴识中术语之“韵”自然而然地转为作为术绘画术语之“韵”,经由顾恺之的“传神”论,而流转为作为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观念。
而冈仓天心实际上是在现代美学的知识系统之中,颇具创造性地以“rhythm”将其时的三条脉络——形式论美学(与“笔墨”相关的绘画线条的律动之美)、生命论美学(与“生动”对应的生命有机体的跃动之美)与表现论美学(与“写意”对应的人格表现与情感共鸣)——牵合为一,为古典“气韵生动”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
其一就形式论美学而言。冈仓天心只翻译了“六法”中前两法,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写作面向西方读者,他指出“六法”将“应物象形”(与西方“写实”观念相对应)列入第三位,因此只需要强调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最为重要的不同,也即前两法;另一方面,则是出自其一贯而来的思路,认为前两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笔墨在东方美术中居于核心地位,甚至“骨法用笔”正是“气韵生动”的具体呈现,如其所言“老庄时代人们对纯粹朴素的线条给予无限崇拜”,“中国与日本绘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不仅强调构图轮廓,而且单纯的线条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抽象美”。
其二就生命论美学脉络而言。对于“气韵生动”之“生动”,虽然古典阐释理路繁多,但倾向于将之理解为偏正结构的短语,也即“生”作为副词或形容词性(栩栩如生)修饰作为动词或名词性的“动”(运动/活动),但冈仓天心直接将之译为主谓短语“生命的活动”(life-movement),“生”被落实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生命”(spirit-life),而这一生命本体的“节奏—运动”构成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内核。
其三就表现论美学而言。这一笔墨线条中所蕴含的“气韵—节奏”,并非仅是冰冷抽象的线条表现,其魅力正在于主体情感与想象力的呈现与共鸣。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创造的精神”(the creative spirit),沉降为艺术家具体而清晰的想象构思,并进一步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层面——构图、线条与色彩呈现出来,这一阐释也呼应与丰富了《日本美术史》中对“气韵”作为“表露高尚思想”的简要解释。
在此将“气韵生动”的古典阐释与冈仓天心的现代阐释并置,并无意以古典阐释的“正统”来质疑现代阐释的“异端”。而是恰恰相反,如本雅明(WalterBenjamin)所言译文延续了原文的“来世生命”(afterlife),冈仓天心的跨语际阐释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观念交叠碰撞,让古典“气韵”观念“不断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冈仓天心的“节奏论”诠释,在20世纪上半叶蔚为潮流,为其时东西方艺术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此后相关学者无法绕开的阐释脉络。
其次,冈仓天心用以对译“气韵”之“气”的“spirit”,其理论逻辑实际上正运行于黑格尔哲学框架之中。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名词“spirit”的含义大致有着三个向度:第一,“生命的气息”或“生命力”;第二,与物质相对的“非物质”,如精神、灵魂、本质等;第三,主观的情绪、心境、态度、决心等。其中确有和中国古典的“气”论观念相近之处,这也使得“spirit”成为西方汉学家对于“气”的通行译法之一。但冈仓天心的“spirit”却并非仅是在通常意义上而言,而是在黑格尔哲学的阐释框架下有其特定的理路与意蕴。在冈仓天心看来,东方思想文化的特质正在于其“一元论”,“气”或者说“运动着的精神”(the working Spirit)构成了宇宙的本质内核与发展动力:“精神性是一个事物的本质与生命,是万物灵魂的汇聚升华,是燃烧着的内在火焰。”而“美”正是“气/精神”之运行的显现:“美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根本原理,闪烁于群星光焰之中,绽放于鲜花娇艳之中,涌起于行云浮动之中,飘逸于流水杳然之中。伟大的宇宙之灵(World-soul)遍在于自然之中,亦流贯于人身之中,在冥思观想中宇宙生命(world-life)向我们展开;在叹为观止的万物(exisitence)现象中,艺术心灵(the artisitic mind)探寻到映照自身的明镜。”在这一诗意盎然的文字中,我们既能看到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思想基调,也能辨认出黑格尔哲学中的有机论世界观、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以及自然美来自艺术心灵之投射等命题。
虽然冈仓天心将中国古典“气论”观念与黑格尔式的“精神”(spirit/Geist)加以对译,以之阐释世界艺术潮流中的东方文化艺术特质。但两者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与“起源—终点”这一目的论时间观紧密联系,精神之发展构成了历史,精神之觉醒则标志着历史的终点,而中国古典“气论”则毫无这一意味。正如郭象在注解《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时所言:“大块者,无物也。夫噫气者,岂有物哉,气块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则块然之体大矣, 故遂以大块为名。”在这一“气论”世界观中,万物秉气赋形、块然而生,其间并无可供追溯的本源时刻,亦无必须奔赴的终点目的,有的只是无往不复的“自生”与“独化”之境。
但在《东洋的理想》中,“精神”是在一个明确的目的论框架中展开自身,如冈仓天心所确信的“精神征服物质乃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以此区分文化发展的阶段”。“精神”对于“物质”的征服历程,成为以日本美术为焦点的东方艺术史的叙事主线:以日本原始时期到奈良时代初期艺术对应受物质形式支配的象征型艺术,以唐代与奈良时代艺术对应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古典艺术,以足利时代以来的日本艺术对应精神战胜物质的浪漫型艺术。同时和古典主义立场的菲诺洛萨不同,冈仓天心是浪漫主义者,坚定地相信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正寓于浪漫主义艺术特别是“东洋浪漫主义艺术”之中:“虽然东洋与西洋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但精神必将战胜物质,全世界的近代思想必然要向浪漫主义发展。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由于种族本能与政治立场,他们以客观性的与物质主义的方式追求浪漫主义理想。……我们依然以印度思想的灵性内核以及儒家思想的和谐社会为根基,以主观性的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直面这一问题。”虽然“精神战胜物质”是西方与东方的浪漫主义的共通点,但前者依然无法摆脱客观与物质的立场,而后者更具有精神灵性,因此在“精神/物质”二元对立的差序之中,东方相比西方拥有了更高的文化站位。
正如我们所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自由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为线索,娴熟地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与印度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冈仓天心则依照相同的话语逻辑与框架,将东方文明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黑格尔主要在政治意义上的“法”(Recht)与自由的领域中论证,而冈仓天心则在审美意义上的文化与艺术领域加以翻转,呈现了冈仓天心“六法”与“气韵生动”阐释的鲜明的文化政治立场与基调。
四、余论
在20世纪上半叶“气韵”的跨语际阐释潮流之中,“气韵—节奏”论阐释可以说占据着主流位置,这一脉络自冈仓天心(1903)发其端,宾雍(Laurence Binyon,1904)与翟里斯(Herbert A. Giles,1905)扬其波,其后诸多中国艺术的研究者承其流。虽有学者如泷精一、韦利(Arthur Waley,1920)、福开森(John C. Feuguson,1927)等提出商榷意见,但如波西尔(Stephen W. Bushell,1906)、闵斯特伯格(O. Münsterberg,1910)、滕固(1934)、蒋彝(1935)、叶理绥(V.Elisseeff,1946)、科恩 (William Cohn,1948)等纷纷都以“rhythm/Rythmus/rythme”来对译“气韵”,一时蔚为潮流。特别是在这一潮流影响下,经由罗杰·弗莱(Roger Fry)的艺术批评与美学建构,“节奏”成为其时现代艺术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有力推动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兴起,更是构成这场中国“气韵生动”的现代理论旅行中的华彩乐章。
W.J.T.米歇尔在对莱辛《拉奥孔》的批判性阅读中指出,“空间艺术/时间艺术”这一文类之分,有其意识形态色彩,诗与画的界限(Grenzen/borders),与其时欧洲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有着直接的类比关系,并由此提出“文类政治”概念,考察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相互对立的术语在一场辩证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角色,表示不同历史时刻的不同关系”。而在本文所考察的“气韵—节奏”论的现代发生当中,无论是菲诺洛萨运用这一区分在中国美术与日本美术之间强加轩轾,在日本古典绘画中投射其西方艺术理想;还是冈仓天心在这一区分基础上加以跨界,在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中引入时间艺术的“节奏”,以此与强势的西方美术争胜,都呈现了“文类政治”的典型样态。由此理路构造而出“气韵—节奏”论,强调绘画与诗歌音乐相通的时间属性,在彼时近代东亚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语境之中,实现了现代艺术系统内部的文类互动与艺术系统外部的政治光谱的巧妙耦合,同时叩响了东西方学人与艺术家心弦,引起广泛而深切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