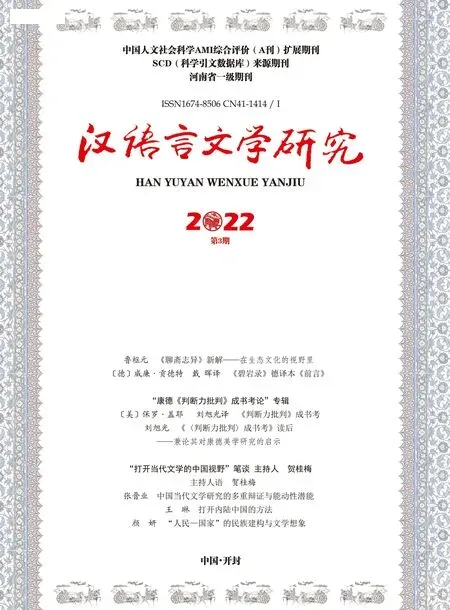语体文的越轨
——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文体试验
陈汝嫣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对刘易斯·卡罗 尔 (Lewis Carroll,1832-1898)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翻译,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在《译者序》中将这次翻译定位为语体文试验:“现在当中国的言语这样经过试验的时代,不妨乘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几方面的试验”,因为“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很难翻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这“试验”的心态,既是赵元任物理学专业思维在翻译文学时的迁移,更反映了当时中国语言文学变革者的共同心态:早在《阿丽思》出版一年多前,胡适《尝试集》问世。相对于胡适“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是在提倡一种“实验的精神”,赵元任则更自信,他认为,语体文之成败可从《阿丽思》来评判。而这“试验”的说法并非宣传之语,仅从《凡例》中的《注音字母》《读音》《读诗的节律》《语体》《翻译》的完整架构,及《特别词汇》的列举说明,就可管窥作者的全盘规划,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用心。
有不少关于赵译《阿丽思》的评价:在它出版前,胡适就读过赵元任的手稿,并称赞:“这部书译的真好!”周作人则推举本书在儿童文学,乃至普遍文学上的价值,同时认为本书译法是“纯白话的翻译”。丁西林认为本书最大的贡献为引入了“国粹里整理不出的”Humor(幽默),并盛赞本书的翻译是超越了“直译”与“意译”的“神译”。不过,时人赞许它的高妙译法,推举其文学意义,却不甚留意其语体文试验的得失。仅从市场反应来看,数十年来,《阿丽思》被数次续写,多次再版,赵元任的成功似乎不言自明。然而,译作的广泛影响力就等于语体文试验的圆满完成吗?
直到如今,学术界对该作的大多数研究依然或延续周作人“儿童文学”的论述角度,或类似丁西林关于翻译策略的分析,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该作语体文试验的面向。胡荣分析了赵元任在《译者序》中谈到的各项试验成果,并认为“无论在白话口语体的运用、新式童谣韵律的讲究还是新词汇的辨析上,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都大获成功”。文贵良从语法、语体、语音和趣味方面,结合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对《阿丽思》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样认为“他尝试通过翻译文学作品以试验现代书面白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试验”。但笔者在阅读中感到《阿丽思》的翻译过程并非“丝滑”,翻译结果也不能说“圆满”:赵元任实际采用的语体,与宣称采用的语体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些裂缝与弥合,或许是把握译者目标与翻译结果之联系的关键。所以,本文关注《阿丽思》翻译作为语体文试验的操作与得失:赵元任为什么要进行语体文试验?他的语体目标是什么?在实际的翻译中使用了怎样的语体?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本文将围绕《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文,结合赵元任的语言观念及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合流的背景来讨论上述问题。
赵元任在《阿丽思》中寄托的语体文试验动机,源于其语言改革观念,并受到国语运动的驱动。他很早就关注中国语言改革问题,胡适曾将文学革命的起点追溯到与赵元任在美国共论“中国文字的问题”。1916年,当胡适尚在关心“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时,赵元任已开始撰写“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他认为“我们语言实际的发展趋向是朝着口头和书面词语的统一”,最终用拼音书写是必然结果。如果说,胡适逐渐形成的白话文观念在同学中尚显偏激,此时赵元任的拼音化构想在留美学生中可谓左之又左,因而显得希望渺茫,他毕业后几经犹豫选择了物理系教职,直到1920年回国,赵元任结识“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对国语运动大感希望,决心未来专门研究语言学。过去的种种方案皆为构想,《阿丽思》的翻译正值赵元任语言改革希望重燃时期,而该作也被寄予了语体文试验的目的。
赵译《阿丽思》中多次使用“语体文”来自我定位,似乎有意避免使用流行的“白话文”一词,尽管后者更富有革命色彩——在胡适的塑造下,白话文成为对抗死文言的活文字。但是,胡适当时所说的“白话”约等于“俗语”,甚至可取文言来补助。这一说法颇为折中,赵元任就曾批评过胡适的白话不够“白”,原因是不够口语,一听录音回放便可知。相较于胡适从传统杂剧、小说中寻找白话文模范,赵元任更激进地主张用“言”规范“文”,他曾区分“国语”与“白话”,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中,“之所以没有用‘白话’一词,乃是因为1919年的时候,人们已经基本认识到了‘白话’一词的局限性。这个口号所倡导的目标,乃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植根于‘白话’,但又在此基础上高度发展,形态完备,以孚国语之名”。在赵元任看来,这一标志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合流的口号,指向的是一种语言。而关于语言特点,无论是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自序中所说的“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或是1948年《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里呈现的“口语的”和“有声的”汉语,以及在1968年《中国话的读物》(Reading in Sayable Chinese)中杜撰的“sayable”概念,他一直在强调语言的口头性。
回到《阿丽思》中对语体的自述,结合教育部条例,“普通语体文”应该是官方“国语”的配套概念。在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八条》中有:“国语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读本宜取用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序。”除了阐明国语与普通语体文的关系外,这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官方“避用土语”的建议,而赵元任自称为了会话生动,采取了活方言的材料。虽然教育部的文件不是赵元任的翻译指南,但以此为参照,或可以理解赵元任颇为纠结的态度,即对于“不得不”加入方言的无奈:“但是会话里要说得活现,不得不取用一个活方言的材料。”并继续澄清:“北京话的用词比较地容易懂些,但是恐怕仍旧有太土气难懂的地方,所以底下又做一个特别词汇备查。”另一个是官方对于教授注音字母及“正其发音”的要求,赵元任在使用方言词语后,又澄清用词归用词,读音依旧可以依照国音:“这个用词的问题与读音的问题绝不相干,例如书中用‘多么’是北京俗词。但是咱们可以照国音念它‘ㄉˊㄛㄧㄜ’,不必照京音念它‘ㄉㄨㄜㄧㄜ’。”以上两点提示了赵元任《阿丽思》语体文试验的一个困境:“普通语体文”是一种想象的规范语,它理应是国语的书面形式,而国家的立场包含着对于方言的摒弃。但赵元任认为,词汇和读音是两个问题,使用土语并不影响国语统一。这也并非辩解,其实,如今的普通话也是二者分离的,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因此,《阿丽思》的语体文试验,并不是在验证教育部标准的成败,恰恰相反,试验是从对条例的越轨开始的。在尝试透视《阿丽思》作为语体文试验的动机和语言改革背景后,需要细察《阿丽思》中语体文生成的实际情况。即在实际的翻译中,赵元任使用了怎样的语体,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赵元任承认在翻译《阿丽思》时使用了两套笔墨:叙事全用普通语体文,而会话加入方言材料。一个典型例子是“老鼠”与“耗子”的使用——在英文版中,对应的单词都是“mouse”,但赵元任却根据对话和叙事的不同,分别对应方言和语体文的翻译,如:“她就开口道:‘哦,耗子!你认得这个池子的出路吗?’(中略)那老鼠听了对她瞅了一眼。”可见,“耗子”是口头称呼,而“老鼠”是书面指称。有趣的是,两类词汇辅助区分了主观和客观的心理描写,如:“阿丽思想道:‘我要对这耗子说话不晓得有点儿用处没有?这儿样样事情都这么出奇,我想这耗子多分也会说话:无论怎么试试总归不碍事。’”“想道”后的内容是人物的内心独白,用的方言“耗子”。而当转述人物想法时,赵元任似乎将其理解为客观的叙事者视角,使用的是普通语体文“老鼠”。如下例中,“mouse”先后被译为“老鼠”和“耗子”:
Alice thought this must be the right way of speaking to a mouse:she had never done such a thing before,but she remembered having seen in her brother’s Latin Grammar, “A mouse—of a mouse—to a mouse—a mouse—O mouse!”
阿丽思想对老鼠说话,一定要这样称呼才对:她从来没对老鼠说过话,不过她记得在她哥哥的拉丁文法书里头有“主格,一个耗子——领格,一个耗子的——司格,在一个耗子——受格,一个耗子——称呼格,哦,耗子!”
在英文版中,这段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在括号中,其中对于“mouse”的各种语法变化在直接引语中用回忆说明。赵元任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引号内外分别译作“耗子”和“老鼠”,以突出叙述视点的变化。由上可知,《阿丽思》中普通语体文和方言词汇的两套笔墨,并不限于叙事和对话的框架,它们与引号相配合,提示了心理描写的客观剖析与内心独白。
然而,两套笔墨在功能上的分野并不严格,方言词汇常常羼入叙事。这里从《特别词汇》中的方言略举一二:关于“扒着”,有“她身子扒着低着头,勉强才能拿一只眼睛看那小门里的花园”,这里并非会话;关于“瞅”,有“阿丽思就很恭恭敬敬地瞅着它听”,这里也只是叙事。在使用方言词汇上,似乎赵元任越是随心所欲,越是反衬了普通语体文表达的限度。问题是,普通语体文就难以“得神”吗?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翻译《阿丽思》同时,赵元任在为教科书拟写“普通语体文”范例。1921年,他受商务印书馆委托,编写国语留声片的课本,其中“会话”篇之《甄国宇和贾观化》,内容本是说北京方言是假官话,而国语才是真标准语。但从实际效果看,“甄国宇”不仅性格上比“贾官话”拘谨,而且他口里所谓的普通语体文,还容易沾染文言色彩。大概是赵元任对普通语体文写作容易滑向文言有所觉察,他在为《阿丽思》选择语体时,虽然需要做一番解释,但最终还是坚持使用了土语。
除了方言词汇,赵元任在翻译《阿丽思》时还十分注意虚词的用法。《阿丽思》的《凡例》共十二条,除却《语体》《翻译》等总述译法的条目,竟有至少四条在辨析虚词,如“的、底、地、得、到”与“了、勒、拉”等。据郁达夫说,文章要做得古,秘诀是“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赵元任对不同虚词的区别体察入微,得心应手地在各处使用它们,有意无意间背反了古文秘诀。而虚词带来的语气变化,增强了儿童读物丰富的朗读腔调。
不过,《阿丽思》中并非没有文言,只是它成了一种讽刺笔法。如在《合家欢赛跑和委屈的历史》一章中,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老鼠“做着个高贵的样子”,说:“威廉大将,其义军本为罗马教王所嘉许,故未久即将英格伦完全臣服,英格伦彼时本缺乏领袖,近年来频遭国内僭篡与夫外邻侵略之乱,亦已成习惯。哀德温与摩耳卡耳,即迈耳西亚与娜司生勃利亚之伯爵——”阿丽思与诸听众的反应是:“我听你讲得一点儿趣儿都没有,简直像嚼着蜡也似的。”原著中对应的老鼠话不是古英语,而是长难句和生僻词。赵元任用文言来转述,以显示角色的装腔作势与话语的枯燥无味。
与上述文言造句类似,书中也有少许故意欧化的地方——尽管赵元任自述翻译时“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在第七章《疯茶会》中,疯帽匠说:“你是不是想要说你想你能找出对它的回答吗?”这是对原文“Do you mean that you think you can find out the answer to it?(笔者自译:你是说,你觉得你自个儿能找到这个谜语的答案?)”这里赵元任颇似逐字对应的“硬译”,其危险不止欧化,更有断句带来的歧义——它可能是“你是不是想要说,你想,你能找出对它的回答吗”,或者“你是不是想要,说你想,你能找出对它的回答吗”等。这里原本较易懂的英文成了费解的中文,或是赵元任有意为之——以强化人物语无伦次的特点,来完成对原作“不通”笑话的翻译。
另外,《阿丽思》中还有对文言俗语的化用,来进行“顽字的游戏”。故事中有个喜欢讲教训“and the moral of that is——”的公爵夫人,赵元任把这个口头禅翻作“于此可见”。夫人的俗话,如“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字面意思是“羽毛相同的鸟儿总在一起”,通常译为“物以类聚”,而赵元任译为“近猪者黑,近麦者白”。将谚语改换字词,不仅传达了原作含义,甚至“添油加醋”,更有趣味。“顽字”的前提是保留原文的口气,在赵元任看来,这甚至比语义更重要。如《凡例》中列举的“The more there is of mine,the less there is of yours”一句,他认为:“这是没法子直译的,所以只得译它成一句口气相仿佛的话,‘所旷愈多,所学愈少’。但是这话的内容,离原文的差得很远了。”所谓“口气”,并非仅着意于还原句式,如“Be what you would seem to be”,赵元任竟译作:“画兔画须难画耳,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里语义与句式都相差万里了。但赵元任没有翻译为字面意思的“你像啥,就做啥”(笔者自译),而是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俗语上略作改动。为什么赵元任选择改动俗语,而非直译原文?或许是在笑话翻译时,语境的迁移比个别句子的译入更能令人会心一笑,而改动俗语则更有游戏的乐趣。
上述举例尚属于汉语,但赵元任有时竟直接用一串字或者注音字母来表音,它们连词都不算,更够不上普通语体文的标准。这点在诗歌翻译中尤其明显,如下表所示:
“Beautiful Soup,
so rich and green,
Waiting in a hot tureen!
Who for such dainties would not stoop?
Soup of the evening,
beautiful Soup! Soup of the evening,
beautiful Soup! Beau—ootiful Soo—oop!
Beau—ootiful Soo—oop!
Soo—oop of the e—e—evening,Beautiful,
beautiful Soup!
体面汤,浓又黄,
盛在锅里不会凉!
说什么山珍海味,哪儿有这么样儿香。
半夜起来喝面汤,体面汤!
半夜起来喝面汤,体面汤!
涕洟糜餍汤!
涕洟糜餍汤!
半夜起来喝面汤,体面汤!
涕漓涂卤汤!
如何理解诗歌中“涕洟糜餍”类“重音轻义”的现象?赵元任晚年在谈论诗歌翻译时说:“翻译诗歌的时候如果还得按原来的调子来唱,那当然节律跟用韵得完全求信,一切别的幅度就管不到了。”这里的原来的调子,是因为原文中“beautiful Soup”拆分为了“Beau—ootiful Soo—oop”,相应的,译文中的“体面”则从音节上被分拆为“涕洟糜餍”。不过,选用“涕洟糜餍”这些较为生僻的字,也是在表音之外,突出了汤或食物的含义。如果说诗歌中如此尚有道理,但叙事或对话中就有些牵强了。比如,在阿丽思掉进兔子洞,正无限下坠时的一段话:“泼里寺,麻达姆,这是纽西兰啊,还是澳大利亚啊?”所谓的“泼里寺、麻达姆”其实是“Please,Ma’am(求您了,夫人)”。但赵元任只是译出了音节,并没有额外加注。这可能是他认为局部的不通并不影响故事全貌,或者预设了读者们至少具有简单的英语知识,或者是重视对语气的还原。另外,《阿丽思》中还有一些注音字母,用来翻译拟声词与叹词,如骨勑凤“Hjckrrk”的鸣叫,译作“ㄜ巜巜厂”,语气词“WOW”译作“メ幺”。这些符号较为不起眼,似乎功能也并不重要,无非是拟音更准确,但这其实暗合了国语运动的主张:虽然国语统一工作尚在推广注音字母阶段,但据黎锦煕的说法,这是“荆轲刺秦”,即“注音字母原来是刺汉字的四十把利匕首”,提倡背后乃是“汉字改换”政策,实施方法:“乃是部分的换,逐渐的换,暂不从中间换而先从旁边换。”
由上可知,《阿丽思》的翻译是在对“普通语体文”的不断越轨中实现的。在官方“普通语体文”之避免土语的要求下使用北京方言,这是《阿丽思》对于官方倡议的越轨;赵元任自述北京方言只用于对话,实际却从对话而溢出到叙事,这是《阿丽思》对于计划的越轨;遇到许多“顽字的笑话”时,故意使用文言或欧化句式,尤其是改编成语,以表现“似通的不通”或者“似不通的通”,这是《阿丽思》翻译之传神需求对于语体文试验的越轨;保留音节不惜舍去含义,这是《阿丽思》对于汉字之表意功能的越轨。但这并非笔者试图颠覆赵元任对于《阿丽思》要用语体文才能得神的判断,而是试图在这种总体性观念中撕出小口——他至少在实践中表明:有部分“顽字的游戏”不化用文言俗语也无法得神。《阿丽思》原作语言中丰富的Tricks(诡计),或者决定了翻译语体的多样性。从而《阿丽思》的翻译,是在口语化语体文的大框架下,异质性语体的不断入侵中实现的。换言之,实践过程对普通语体文要求的偏离,却是《阿丽思》成功的原因。
赵元任实践中对于语体文试验目标的偏离,有部分是贴近原作翻译导致的。如将长难句翻译为文言,用欧化句式强调不通。甚至,普通语体文与文言、欧化语体间的反差,造成的喜剧效果超过了原文。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语体文试验和翻译准确两个目标之间难以避免出现分歧。赵元任在《凡例》中自述翻译方法:“本书翻译的法子是先看一句,想想这句的大意在中国话要怎么说,才说得自然;把这个写了下来,再对对原文;再尽力照‘字字准译’的标准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然而,字字准译的期待和自然的中国话的要求间有着不可逾越的沟壑,终于《阿丽思》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中不西”的表达。如原文:“(1)As soon as the jury had a little recovered from the shock of being upset,(2)and their slates and pencils had been found and handed back to them,(3)they set to work very diligently to write out a history of the accident.”赵元任译文是:“等到那些陪审员因为被倒了出来受惊过后精神复了原,等到他们的石笔和石板都找着了交还给他们,他们就很起劲地记这回出事的本末。”这句整体结构上还原了英文,但在小句(1)的翻译上,赵元任的翻译是“等到那些陪审员因为被倒了出来受惊过后精神复了原”,中间以“过后”一词杂糅了“因为被倒出来而受惊”,“受惊过后精神复了原”两个时间上递进的意思,使得句子很拗口。如今看来,索性依原文译作“等到那些陪审员从被倒出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会更通顺。之所以不将“recovered from”翻译成“从……中恢复”,这或是传统中国小说中表示心理状态的恢复时习惯在时间流动中体现情绪变化,而不是“从……中”状态的直接更新。如果仔细检阅,还能拎出类似例子,但《阿丽思》用大量的方言、虚词以及状态词、拟声词等拉长了句子,偶尔出现的语病也容易被整体朗朗上口的译文所遮掩。总之,翻译和语体文试验的两个目标,在不同的方向牵引《阿丽思》文体的生成,并与所谓的普通语体文拉开了距离。
如何理解翻译作为语体文试验的价值呢?从晚清以来,翻译一直在拓展文言的词汇与语法,例如,不规则长句逐渐变多,甚至标点的需求也应运而生。其中自觉的变革者,以周氏兄弟为例,他们对异质性语言的接纳,或可最大限度地抻开汉语表达的可能性。但赵元任《阿丽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力图在“说得自然”的语体文限度内传达原作神韵,“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国话的时候算危险极度”。排斥欧化的主张看似保守,但实际上,却或在挑战不可能——异质性语言的侵入,这不仅是诉求,或许更是近代以来汉语的宿命。在《阿丽思》出版三年前,周作人曾断定:翻译“总有两件缺点”,同时也是“要素”,即“不及原本”与“不像汉文”。而《阿丽思》中充满了文字游戏的“Tricks(诡计)”——“似通的不通”“双关的笑话”,又兼有童谣与成语等元素,对于翻译技术是个更大的挑战。
那么,《阿丽思》的翻译试验却反证了语体文的局限吗?如果将普通语体文的标准视为官方文件中的声明,那么赵元任翻译时候的种种越轨确实反映了它的局限。但实际上,语体文的规范尚在生成、变化、探索中,而《阿丽思》所代表的口语化语体文试验,丰富和扩展了它的内涵。这或许也是对语体文中许多表达已习焉不察的今天,再回溯《阿丽思》语体文试验的意义。到1922年,《阿丽思》出版后,“国语”成为它的一个卖点,如“今译成国语颇足供儿童之观览”。1924年,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法书,它引用了两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句子。日本学者平田昌司认为,文学革命有视觉与听觉的两次高峰,赵元任是后者代表人物,贡献主要在于话剧与广播实践。事实上,至少在1937年夏天,《阿丽思》是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夜间节目中儿童教育专栏的播音材料。与新技术的结合,使口语化的语体文成为真正的国语之声。尽管普通语体文是个想象的概念,书面语也无法完全还原口语,但赵元任作为后来的语言学之父,通过翻译《阿丽思》进行的语体文试验,尤其具有典范价值。
但是,《阿丽思》语体文试验的影响也有其限度。一个颇为讽刺的例子是:1931年《北洋画报》上刊登旧体诗《章行严先生属为其所著论衡读后记写竟忽得一梦如阿丽思之漫游奇境矣因成三绝句》。尊孔读经,质疑白话的章士钊之梦竟被拟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可见影响的涟漪扩散到读者的最外层,触碰到最顽固的文言势力,就只剩下个符号般的“阿丽思”与“梦”,又与黄粱一梦、南柯一梦一般都化为幻梦了。实际上,在一个战乱动荡的国家,国语统一如同搭建空中楼阁。虽然赵元任之后的主要精力在语言学,但还一直关注着书面语的变革。他欣赏沈从文与老舍遵循口语的语言,暗示他们的语言道路代表了国语的发展方向。有意思的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沈从文、老舍之间的一个奇妙交点,沈从文写过拟作,老舍曾提及加乐尔的原书对自己语言转向的影响。从这个交点回过头看,赵元任在序言中所说,《阿丽思》的价值比得上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作品,在后来这些作家的试验中,使用最简单的语言,也能生长出有声有色的中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