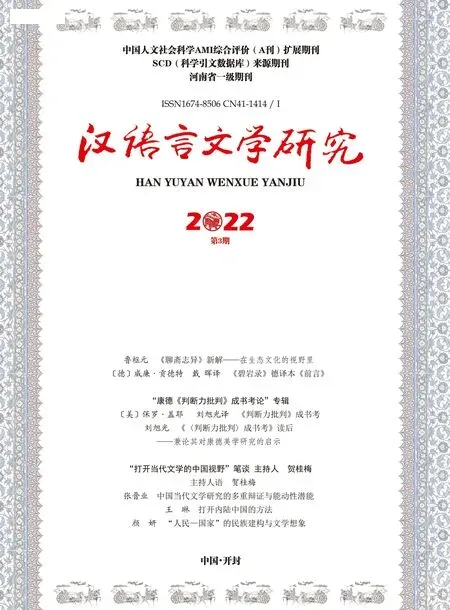“洋泾浜”与主体性:林语堂的双语“小评论”
李成城
1933年,林语堂发表了《论翻译》。这篇文章作为序言收录在吴曙天编的《翻译论》里,随后又收录在林语堂同年自编的《语言学论丛》中,经由后续的翻译研究选集多次收录,逐渐经典化。
吴曙天自述编《翻译论》得到了赵景深的帮助,同时又吹捧林语堂此篇“代序”“已将翻译当注意的事项全说尽”。与之相对,作为翻译论选集,吴编未收鲁迅一篇文章。联想到赵景深和鲁迅此时在翻译上的口角,林语堂这篇“代序”也就染上了文人意气或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色彩。
从这个角度进入《论翻译》,可以发现许多对于“字译”者的讽刺。与鲁迅译得不好总比没有强的立场不同,林语堂认为译得不好不如不译。展开说去,这背后牵涉到鲁迅与林语堂从翻译观、文化观到政治立场,再到写作身份等各方面的不同,比如是否熟练掌握外语写作。翻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关注点之一,其翻译论在各个关键命题上的判断,可以为翻译论者画出各自的光谱。
具体到这篇《论翻译》,林语堂也为各个命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此处不备述。我关注的是林语堂的论述中存在的一处矛盾。林语堂试图抛弃“直译”和“意译”的概念,转而用“字译”和“句译”这对概念来给翻译分类,进而倡导“句译”而贬斥“字译”。回溯此文所引用的《译书感言》,在傅斯年那里,“字译”和“句译”其实都在“直译”的范畴之内,林语堂继承了傅斯年对“意译”的排斥,并更进一步直接将“意译”排除在讨论之外。这种分类方法的变化显示出相关讨论随时代演变的细化、深化。但是,林语堂在论述“句译”时,又以为“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这与“字译”“句译”的上位概念“直译”以及他所强调的“忠实”标准之间都多少有点矛盾。这种矛盾似乎还是纠缠于“异化”和“归化”这对自德国浪漫主义以来就被广泛讨论的概念,同时又因为意识形态的沾染而变得复杂起来。然而无论从直译—意译、异化—归化还是从意识形态争论的角度,似乎都很难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林语堂自1928年便开始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英文文章,一直持续到1936年赴美。《中国评论周报》在1930年为他专门开设了一个名为“The Little Critic”的专栏,即《小评论》。所谓“小评论”,就是反对大文章、大话题,强调轻松、真实,这种论调与林语堂此后提倡的“小品文”以至“西洋杂志文”一脉相承。这些英文“小评论”有一部分被林语堂自译成中文,发表在《论语》和《人间世》等中文报刊上。大致而言,这些中文版的“小评论”与林语堂此一时期的其他中文文章有功能上的不同,后者更接近“论文”,常常提出主张,发表严肃的理论思考;前者则更接近“小品文”,多调侃游戏,往往被视作幽默小品文作家林语堂的代表作。
这批被翻译成中文的“小评论”同时也是研究双语写作这一特殊的实验性写作的样品,涵盖了诸多“翻译”层次。首先林语堂是一个中国人,他写英文文章这个行为本身便是一个广义的翻译;其次林语堂又将写好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英、中文写作的间隔时间也有长短之分,长的过了几年,以至于英文版里被赋予诸多意义的一张桌子,在几年后写的中文版里已经被卖掉了;间隔短的则足以突破狭义的“翻译”的界限:如果一篇文章几乎同时由两种语言写成,那我们便可以怀疑这并非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或许是两种语言同时翻译了作者头脑中所存在的更本原性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存在的话。
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在这里不无解释效用。德国浪漫派如洪堡认为翻译可以激活译入语,本雅明则认为翻译可以同时激活译入语和译出语,以至于凸显“纯粹语言”。相对于普通的翻译,这种视角对双语写作更有启发,因为两种语言的文本自始至终都产自同一个人的头脑。
双语写作与普通翻译的最大差异也就在这里。意译与直译、异化与归化的争论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者和译者的矛盾。直译者的一个理论依据是,即使最优秀的译者也无法保证传达出原作者的所有意思,这是原作注定高于译作之所在。但是双语写作却突破了直译论的边界:如果翻译者同时也是作者本人,那他便拥有对原作无限的解释权,即使原文与译文有千差万别,也无人能质疑译作对原作精义的保留。也就是说,双语写作超越于作者—译者的矛盾之上,中英两篇作品的差异恰恰展现出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由此,我们便可以从双语写作的角度来观照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以至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而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跨语际、跨文化写作者的主体性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对读“小评论”的中英文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一些语言文字上的差异,比如英文版用较为规整的从句集合成篇,而中文版则将从句拆为单句。这种拆分让英文版中一些本来明晰的逻辑关系在中文版里被削弱了,其结果便是相较于英文版,中文版更符合所谓谈话风格,东一句西一句地谈开去,闲适自在。这样的处理自然与林语堂对欧化汉语的反感有关。林语堂按照他心目中英文和中文的应然状态来写作,使两种语言仿佛各列于镜面两端,互相映照的同时又保持距离,为翻译时“完全根据中/英文心理”提供了可能性和样本。同时,小品文本身的格调也随两种语言的特性而各具特色,英文世界的“essay”和中文世界的“小品文”亦如两种语言一样相映成趣,平行发展。
另一个直观可见的差异,是林语堂在汉语写作时将不少英文版中的例子换成了中文世界的例子,比如:
1.英文版:It is a trite saying that every society lady who goes the mad round of parties and pleasures soon is overcome by a feeling of utter boredom.
中文版:富家妇女一天打几圈麻将,也自觉厌烦。
2.英文版:I would read Rabelais along with“Mutt and Jeff”and Don Quixote with“bringing up father”.One or two Booth Tarkington,some cheap third-rate penny novels,some detective stories.
中文版:西洋新书可与《野叟曝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
林语堂试图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对等性,从而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中为某概念/某物找到在各自文化中类似的位置,如西洋的“派队”对应中国的麻将,《野叟曝言》则可与西洋时兴的漫画类比。双语写作中的换例,如他在“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中所说,是为了跨越不同种族的“精神和情感构成”,以求传达特定的理念思想: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多或少是种族气质的结果。特定的文化理念改变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说,精神和情感构成保持不变。这些外国的文化理念可以叠加在一个民族之上,但是除非它们能和这个民族的内在直觉同调,否则便不能称为这个民族的生活中的真正的部分……更经常发生的是,种族的气质改变了那个文化理念。
林语堂采用了一种精神情感—理念思想的二元论来分析文化传递的过程。文化传递其实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两者具有同构性。翻译的换例背后,往往是两种语言、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化元素更广泛的比附,即陈寅恪所谓“格义”。林语堂拿晚明小品文和英国小品文比附,或声称庄子和陶渊明分别代表中国古代两种幽默,正如同严复将牛顿三定律与周易类比。从“融通儒释”的“晋世清谈之士”,到晚清时的严复,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他们的“格义”或各有其理由,但单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林语堂的“换例”却并未如严复那样遭到严苛的否定,这正是双语写作的独特之处。
本雅明曾举例说明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词的关系。德语的“brot”和法语的“pain”均意指面包,本雅明认为前者对于德国人的意味和后者对于法国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两个词不能互换,并且二者都在“努力排斥对方”。但同时,他又认为,二者在另一维度上而言是互补的。这对解释换例很有启发。在严复的翻译中,换例被认为是不好的,其原因是“例”在两种语言中不能互换,且互相“排斥”;但在林语堂的双语书写中,这“互补”性却占了主导,两种语言的不同“例”证结合在一起,恰恰呈现出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林语堂。在双语写作者的实践中,不能合并的两种语言被糅合、重叠在了一起,特定的重叠形式既反映出林语堂的思维结构,也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
林语堂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在圣约翰大学时还上过神学院,在其成长过程中,“传教士”这一形象对他的影响甚大。在中国当一个西洋传教士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向中国人传递从西方来的教义,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向西方解释中国。在林语堂看来,西洋传教士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好。除了传教士,还有很多沟通中西的位置和视角,为林语堂一一论及。在“Do Bed-Bugs Exist in China?”(《中国究有臭虫否》)中,林语堂列举了对于“中国究有臭虫否”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回答,回答者包括了辜鸿铭、爱国者、哥伦比亚博士、帝国主义者、西方教士、中国外交官如朱兆莘之流、党部、道士和尚、胡适之及自由主义者,而自己是最后一类,在英文版中是“Little Critic”,而在中文版中则是“《论语》派中人”。如果我们对比鲁迅的一篇更早而又相似的文章《杂感录三十八》(1918)——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将爱国的自大家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我们便会发现,虽然这十种类型或多或少与鲁迅的五种类型有交集,但林语堂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中西文化沟通的角色上。鲁迅通过排除自大的、虚假的爱国者而确认了真正的爱国者形象,林语堂则采用这个更为细密的分类,通过排除剩下的九类而确认了自己在中西之间独特的位置。两者着眼点的不同也可反映出他们的关切点的区别。
写于赴美前的《吾国与吾民》,甫一开始便讨论了传译者的位置:
然则谁将为此传译者呢?这一个问题,殆将成为不可解决之悬案。那些身居海外而精通中国学术之学者,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仅从孔氏经籍所得的感想中观察中国,自然绝非肩荷此等工作之适当人物。一个十足的欧洲人在中国不说中国语言,而道地的中国人不说英语。一个欧洲人说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将养成同化于华人的心理习惯,此等人将被其国人目为古怪人物;中国人说英语说得太流利而养成了西洋人的心理习惯,将被削除国籍。又有一种说英语的特种华人,或则系根本不会讲本国语言的,或甚至用英语发音来说中国话的。这些人当然也不可靠。
事实上,不管是在《中国究有臭虫否》中自我指认的“小评论家”“《论语》派中人”身份,还是《吾国与吾民》中赛珍珠指认的“客观的”“足以领悟全部人民的旨趣”的中国英文作家的身份,都并不稳定。随着时代风向的转变,这些细微的分类学所呈现出的身份的正当性也随时跟着晃动。一方面林语堂在不断调整对自己身份的自我阐释,另一方面也不断面临针对自己尴尬位置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贬义符号是“西崽”,在英文里林语堂将之对应为“boy”。
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性的符号。林语堂曾盛赞的一本英文书Audacious Angles on China(《大胆角度看中国》),其封面上便印着一幅题名为“The Call of The East”的漫画:一个中国伙计端着一盘酒水,另一边传来一声洋人的传唤:“Boy”!这样的“boy”或“西崽”是旅华外国人接触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他们借以了解中国人的窗口。一方面谄媚外国人,一方面瞧不起中国人,通过两种文化的信息差以获利,“西崽”在民族危机下自然为时人所不齿。而身处两种文化之间、肩荷传递西方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自然对这个角色避之唯恐不及。在躲避背后,是两方面压力的夹击之中“沟通者”角色建构失败而退化为“西崽”的焦虑。戏剧性的一幕是,林语堂先用这个词来批评左翼文化人,他在《今文八弊》中批评他们“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只知跟随“洋大人”而不能“自作主人翁”。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的鲁迅将这个词回掷给林语堂,在《“题未定”草》中,鲁迅讽刺林语堂“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为“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抛开褒贬来看,鲁迅的话倒是道出了实情。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与“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褒贬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在“西崽”称号的互相抛掷的喜剧之中,正可见出“西化”的几代人心思的细密与身份的微妙。不过,对于“西崽”这个符号,林语堂在中文世界里虽尽力回避,在英文世界里却并非一概否认与推远,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为习惯的视角所遮蔽。
在“Confucius as I Know Him”(《思孔子》)中,林语堂称赞Audacious Angles of China(《大胆角度看中国》)的作者Elsie McCormick做出了他阅读范围内唯一一个对孔子公正的批评。埃尔西是《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记者,此书即由她在该报上的文章合集而成,为西方人讲解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从林语堂建构的类型学上说,这是由西方的“中国通”所写的书,这种书多半只能造成误解,而埃尔西的这本书似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第22篇为“Pidgin English as a Liberal Education”(《作为通识教育的洋泾浜英语》),展现出外国人对洋泾浜英语的态度,如林语堂所说,这是西崽(boy)所用的语言。
这篇文章向西洋读者介绍了洋泾浜英语的概念、词汇的来历,以及它的发展历史。很多旅华外国人不愿意对中国人说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因为他们觉得如同妈妈不应该对小孩说儿语(baby-talk),向中国人说洋泾浜英语会妨碍中国人学会真正的英语。但埃尔西认为,西方人应该利用洋泾浜英语来教育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埃尔西所用的英语(english)是小写的,这是英语母语者对于殖民地英语或地方英语的一种区别性的指称。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著作《逆写帝国》分析了English(欧洲中心英语)和english(地方英语)这对概念,并将english解读为殖民地写作者对于欧洲中心英语,乃至欧洲中心话语的一种解构工具,他们用这种地方英语书写“发展了另外的颠覆策略,推翻约束他们的形式和主题,将他们的后殖民性的‘局限’转变成他们的形式和题材原创和力量的来源”。
林语堂对这种西崽的语言很感兴趣。在“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今译美国独立宣言》)中,林语堂谈到美国批评家孟肯(H.L.Menck en)写的The American Language(《美国语》),后者提醒了林语堂,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语文学家(a philologist by profession)。作为一部语言学著作,孟肯的这本书让美国读者知道美国式的英语不是一种方言,而是一种民族语言 (national language),应当被看作一种标准的美国语(American vulgate)。孟肯在书中用美国语重写了《独立宣言》,林语堂则模仿孟肯,将中译版美国《独立宣言》再翻译回英文版,所用的语言则是洋泾浜英语。
用洋泾浜英语来写作首先是一种幽默的游戏,林语堂在“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为洋泾浜英语辩》)以及“A Reply to Hirota in Pidgin”(《用洋泾浜英语答复广田》)中也做了类似的游戏。这种游戏文字是林语堂最为出色的一种写作,用幽默的语调,在正反说夹杂的含混之中,让读者会心一笑或是反躬自省。林语堂“推崇”洋泾浜英语,所对话的正是如埃尔西的文章中所呈现出来的西方人对于这种劣等的地方英语的鄙视。如同孟肯为美国英语写的研究专著确认了美国英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合法性,林语堂肆无忌惮的调侃未尝不是对洋泾浜英语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之上的:通过对洋泾浜英语的“自嘲”,林语堂也同时攻击了西方人的傲慢及其对中国人的轻蔑。洋泾浜英语或许不足以成为一种如美国英语一样的正式语言,但它反映了被迫所使用他者语言的生命力。
在“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为洋泾浜英语辩》)中,林语堂仿照“西崽”,用洋泾浜英语拟了一份可笑的菜单,四不像的菜肴名称都是用洋泾浜英语拼成的,或许真正的西方人却看不懂。这种戏拟本身是一种自我隐喻,作为一个或主动或被动受西方影响甚大的知识分子,他如同“西崽”说洋泾浜英语一样,利用了西方的语言、概念、知识结构,创造出了一种西方所无的东西。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中提到,翻译给语言带来了一种激活或更新,林语堂的经验可以部分地证实这一点。但在林语堂这里,翻译或双语写作所激活的,不是如本雅明所说的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纯粹语言,而是一种游戏性的甚至诬蔑性的“洋泾浜”语言。
如前所述,林语堂的双语书写具有丰富的层次,先从中文(脑中所想)译为英语(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然后再从英语译回中文(发表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他在 “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今 译 美 国 独 立 宣言》)的戏拟中,刻意强调这种来回翻译的无意义,这凸显了双语书写行为本身。他就像弗洛伊德分析的那个将线轴来回抛掷而同时口中喊着“Fort-Da”的小孩,这种看似无意义的来回翻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衍生出了大量的文本,同时也在一种“浪费”和“无意义”中确认了自我。由此,“洋泾浜”的态度也就超越于语言之上,成为林语堂跨语际写作实践的意旨。
在这种似游戏似练习的来回翻译之中,我们既能看到一种更新的英语,也能看到一种更新的中文。中文版《今译美国独立宣言》有趣地呼应了英文版,林语堂尝试用“京话”来翻译美国《独立宣言》,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只能随时参考希利亚氏(Hillier)的《英汉京话字典》,“然吾必须要试一试,自己练习,以待老舍老向等之修饰改正”。他知道自己的“京话”写得不好,但这种尝试是为了“能激发北方文士,立志做一部好好的京话辞典及京话文法,如孟肯之治美国俚语一样”。这是林语堂提倡口语及“语录体”的另一面。
在《小评论》中,林语堂有两篇介绍中国古代思想的文章“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半部〈韩非〉治天下》)和“Confucius as I Know Him”(《思孔子》)。两篇文章的中英版本写作时间间隔较久,内容差别较大。中文版多针对国内现实,通过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或是为人处世来批判时人;英文版则照顾到西方人的视角,倾向于展示中国古人思想的新奇之处,以别于西方人对中国人旧有的负面看法。
文章写如何疗救中国,它的理想读者却是英文读者;在英文版诞生几年之后,相应的中文版才面世。如何看待这种错位之处?进一步看,发表“小评论”的《中国评论周报》有着发表时事评论,“使外人明了中国政情,于国际甚有关系”的远大抱负,但同时也有一种中国同人性。《中国评论周报》的作者多与清华大学有关,往前回溯,又该如何理解其与留美学生的中文报纸,如《留美学生季报》的镜像对称般的关系?
回到这两篇文章,林语堂通过中西比附来建构起韩非与孔子的形象。经过林语堂丝滑的翻译与介绍,韩非与孔子看起来像是两位来自西方的另类智者:韩非有着德国式的对于政府功能的机械、抽象的理解,他关于“国王”(king)“无为主义”(Do-nothing-ism)的设想,如今在君主立宪的英国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位古代思想家孔子,经由圣伯夫(Sainte-Beuve)式的叙述,即“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家庭关系和敌人来重建一个人的画像”,而展现出一个或许因为在饮食问题上过于挑剔而与妻子离婚的形象。两位中国古人的人格融解在了西方的文化氛围之中,他们的概念则被西方的概念所肢解。
如果我们对比《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中国概念时“放慢速度”的风格,便会发现林语堂写作的另一副面孔。如第二章名为“The Chinese Character”,首先便介绍中国人的“德性”观念(Chinese character),并与英语世界的character做区分:英语的character多指力量、勇气、癖性等等,而Chinese character则多指性情温和、圆熟、镇定和清醒。宋桥(Joe Sample)解读道,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向西方展示中国概念时,“先试图在英文译文中找到同义词,继而又转向寻找类似的概念”,继而“将同义词在不同语言中的用法拿来比较,正是试图避免把一种诠释强加于另一种诠释的过程”。同是将中国的概念翻译给西方读者,《半部〈韩非〉治天下》《思孔子》和《吾国与吾民》的两种写法似乎摇摆在“通顺”与“忠实”的两极之间。
《论翻译》纠缠于直译、意译、字译、句译诸种概念,讨论忠实、通顺、美诸种标准,要为翻译定立某种原则。既强调忠实,又强调“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这个原则在“忠实”与“通顺”之间保留下模棱两可的空间,原则因缺乏有效性而不成其为原则。但在实践中,这个空间又给他的翻译策略提供了足够的施展可能性。所做的“策略”远比所说的“原则”更为鲜活有生命力。当他需要目标读者看到中国的特殊性以保持民族尊严,或借异域风格吸引西方读者的时候,便会选择以更加忠实、更加谨慎的方式介绍中国的理念;而当他想将中国的理念刻画得酷似一个现代西方理念——无论是想借此激活中国旧理还是想证明中国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种子——的时候,他便会选择用西方概念来肢解中国概念。他有抵抗西方话语的一面,同时也有顺从西方话语的一面。这种顺从不应当简单地被看作一种无意识,或许恰恰相反,正是“弱者的武器”。抵抗与顺从之间,策略上的灵活性才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地位的写作者的主体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