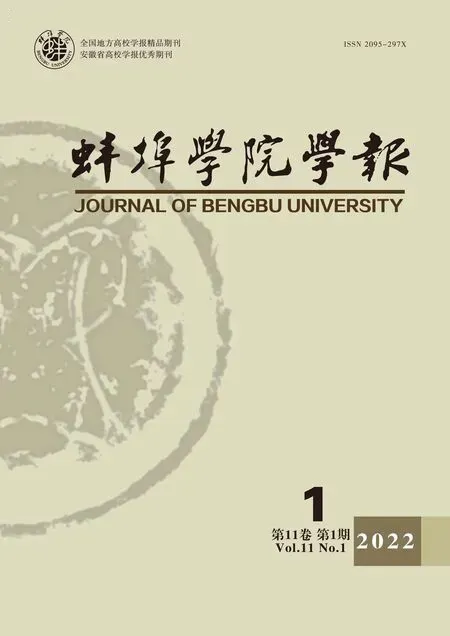洪泽湖渔鼓的发展及其功能研究
程启芳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洪泽湖渔鼓是洪泽湖区富有特色的艺术,融合了说唱、曲艺、音乐、舞蹈、杂技于一体,并配合着表演现场的纸扎、绘画、刻纸、面捏等的艺术布置,而具有综合性艺术特征。其含有多种文化价值,表演中展现了洪泽湖的渔家生活面貌,承载了洪泽湖区域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随着渔民生活的变化与湖区的发展而以不同的形式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
洪泽湖渔鼓又称为“端鼓舞”“打端鼓”“端鼓腔”“跳大神”,其中,“端鼓腔”是湖区渔民惯常使用的称呼。早期的洪泽湖渔鼓是将日常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渔民祈福信禳灾仰所结合,如渔家生产大会、渔民烧大纸、造船会、庙会或者是续家谱、祭洪泽湖大王等活动。现今洪泽湖西岸偏南的穆墩岛,在每年的三月初六进行“敬大王”仪式中,仍然能够稳定而完整地展现洪泽湖渔鼓的表演仪程。在穆墩岛村西的大王庙,每年参加人数达200余人,人员主要来自临淮、成河乡等洪泽湖附近的渔民。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情况下,敬大王仪式是渔民生活的印记,传承延续着渔民质朴的惯习,同时也加以转变以满足当下渔民的需求,使得洪泽湖渔鼓仍然鲜活存在于渔民日常生活中。
1 洪泽湖渔鼓的发展演变
洪泽湖渔鼓有文字记载其来源的便是在《中华舞蹈志·江苏卷》中,它是洪泽湖上的“童子”为渔民们祈福消灾、保佑丰收而表演的歌舞,起源于萨满文化中的“跳神”习俗,传至鲁南地区后,多称“跳大神”,随着山东逃荒避难的民众而到洪泽湖地区谋生,进而传入了洪泽湖地区[1]434。
萨满“跳神”的功用性表现在其一是祭祀,其二是医病治疗。“跳神有跳家神、跳大神之别,祭祀用者曰跳家神。……其专以治病惑人者曰跳大神。”[2]这种祭祀性的萨满汉译为“司祝”,巫医性的萨满汉译为“大神”。通过家传而有萨玛作为与神沟通的中间者,在布置的仪式场景中,着五彩衣,执铁丝贯钱的太平鼓,通过唱祝词与跳舞、击鼓的形式[3],有祛除病祟、祈福、崇敬祖先、敬畏神话、自然、动物之意,根据不同的仪式目的需要而变化唱跳的形式[4]。此种活动后传鲁西南一带,弱化了功能性的名称划分,以“跳大神”为人们熟知。随着地域文化影响,这种习俗进入鲁西南的南四湖,即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徽山湖,以及东平湖的渔民生活中,在清代中叶兴起,盛行于明末清初。因为湖上渔民在捕鱼作业之前,俗称“打生产”,将其用于“敬大王”祭神仪中,古称主祭人为“端公”,故称“端公腔”。因其在徽山湖地区多种活动场景中,如“敬大王”(即指蛇神)、水神、逢年过节、续家谱或者袪病、病愈还愿,由表演艺人演唱《百神赴号》时,需要准备用以请神而来的供品以娱神敬神,所以也称“端供腔”[5]。现在为表演艺人称呼的“打端鼓”,是由其仪式表演道具而得名。仪式表演过程中的乐器只有渔民艺人的芭蕉扇形状的单面羊皮鼓,随着表演曲种的不同,左手把鼓端在手中,或摇动鼓把,或配合右手用竹制的细鼓来敲打不同的鼓点, 故得名“端鼓腔”。端鼓腔在徽山湖的发展渊流考证结果,不同于《中华舞蹈志·江苏卷》中提出的是由山东地域传入洪泽湖区域的说法,它是受到江苏淮河流域洪泽湖的香火戏演变而来的。从流域形成及演唱曲调情况看,清初顺治年间,南四湖形成,洪泽湖的形成时间早于南四湖,且渔民“哪里鱼汛好哪里跑”,洪泽湖与微山湖的渔民多有迁徙往来[6]。由此带来香火戏中的锣鼓伴奏,与当地艺人跳神所用羊皮鼓结合,不断吸收运河号子、民间俗曲小唱一类,在原来跳神的基础上融入地方民间故事,演变成为具有特色的徽山湖端鼓腔[7]。
上述端鼓腔和洪泽湖渔鼓发生地所指虽有差异,但也正是反映了两地是存在往来交流的。胥国红分析香火戏与端鼓腔的渊流体现在香火戏发展的地理位置、表演内容和形式以及流传的剧目上。运河和淮河的交汇,使得两地渔民交往密切,渔民湖上捕捞多处行船,带来了多种文化,在文化上的交融性加强,使得香火戏与端鼓腔有相互融汇的可能。整个香火戏的表演程序有开坛、请神、跳神、发表、净坛、送神等程序,端鼓腔的表演程序有开坛、展鼓、拜坛、请神、演唱、送神,两者的表演程序基本相同。表演中都是男扮女装并且表演目的都是为了祈福禳灾,以敬神袪病,实现娱人娱神的目的。端鼓腔中的部分剧目在江苏扬州一代的香火戏和南通一带的僮子戏中都有相同或者是相近的名目[8]。
端鼓腔在洪泽湖区广为流行,集中于清末至民国前期。这时期的表演主要体现了渔民祈福禳灾的心理,祭祀表演具有封闭性。这时候舞蹈的“童子”换由成年人扮演,左手持端鼓,右手执鼓槌,边鼓边唱边舞。唱词和曲调祖传口承而来,非日常性交流言语。渔民随着生计需要不断调整着表演形式,当湖区渔民以渔业劳动为主要收入源时,童子由职业变为半职业,端鼓腔表演程序的日常娱乐性开始发展,渔民会在劳作闲暇之时以鼓起舞,由此渔民又称之为“渔鼓舞”。
抗日战争时期,渔鼓舞的整个表演程序剥离,曲调、舞蹈部分得到发展,开始面向大众,赋有多种功用性,不断改编创新走向开放性的舞台活动。渔民会改编唱词填于渔鼓舞的曲调中,也会以鼓点为战鼓,号召团结护家园,从而发挥鼓舞作用。1957年半城镇文化站站长张坤同当地的文化艺人开始整理渔鼓舞,组织艺人排练、加工成舞台表演艺术,命名《渔鼓舞》。1983年张仁高站长对渔鼓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断地深入洪泽湖区域,走访表演的渔民老艺人,对渔鼓舞有了更加系统性的梳理,对舞蹈的各方面加以调整,作为地方文化而发展多样化的舞台表演活动[1]437。张仁高站长同时注重渔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组织申报的《洪泽湖渔鼓》在2014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洪泽湖渔鼓的舞台化随着表演需要而具有多种舞蹈形式,内涵更为丰富。
2 洪泽湖渔鼓中祭祀的功利性
在穆墩岛的“敬大王”仪式中,洪泽湖渔鼓保留着不同于舞台化的形式内容,展现着渔民对日常生活的思想逻辑解释,且贯穿在整个仪式中。从神灵信仰的主体上以及在仪式过程中所呈现的表演都与渔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2.1 神灵信仰的转换
洪泽湖渔鼓中显著的特征是祭祀。祭祀一词其意指以酒肉等供品祭神和先祖,有世代的延续,对神和先祖表示敬意或求福[9]等内容。穆墩岛“敬大王”仪式中的“大王”即指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深受洪泽湖区渔民的敬重,其在渔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流变与洪泽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敬大王”于漕运和治河患活动中发展旺盛。金龙四大王原型为谢绪,南宋诸生,杭州钱塘人,隐居在安溪下西湾,因其兄弟四人,排行在第四,就读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由书生成为神灵,是以其显神性的事迹而得以凸显。谢绪领兵对抗元军失败投苕水而亡,在人们的梦中成为水神而后于苕水河畔立祠,至元末,元军和明军在徐州吕梁洪交战时,改变了明军的不利局面而获得胜利,其神灵性获得承认[10]。之后官方追其封号、敕建庙宇,进行祭祀,明清时期成为运河保护神和漕运保护神,深受黄河、运河沿线人们的信奉。胡梦飞指出在明代前期,徐州黄河、运河交汇,借淮行运的原因,黄河冲堤泛滥威胁到了漕运通畅,及其漕运险段徐州洪、吕梁洪治理难度大,官方便求助于有神性的金龙四大王,明代中后期,在治黄保漕运平安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进入官方祭祀中,信仰与祭祀深入民间。到了清朝时则更加推崇金龙四大王,封号和敕庙行为愈盛,成为黄河神兼运河神[11]。在治黄通漕的背景下,金龙四大王信仰的深入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洪泽湖位于淮河的下游,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因黄河泛滥导致淮河下游堆积,河床抬高,江淮地势变为北高南低,加重了淮水南下夺运的危险性,也使得洪泽浦因此变为了洪泽湖[12]。于是在固堤、疏通淤泥的过程中,官方以祈求治理顺利,在洪泽湖区域官民共同虔诚奉祀金龙四大王,其信仰繁盛。明万历年间,老子山大王庙建立,祀金龙四大王。大王庙中书“人寿年丰惟愿大王常保佑,风调雨顺当教洪泽永安宁”。老子山在洪泽湖南岸,是淮河进入洪泽湖的入口,在当时受到南北商船及湖上渔民的祭拜[13]。
洪泽湖的水域位置有启承之用,上承河道包括湖西的淮河、怀洪新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民便河等河道,下泄河道主要在河东,受到湖区人民围湖造田以及历史遗留的淮河自身的泥沙淤积,洪泽湖的水文变化比较敏感。清至民国时期,较多受到严重的水涝干旱灾害。汛期由下接的水道坝口放掉,以致于遇到少雨季节时,整个湖区会出现干涸的情况。而雨季或者是洪峰时期,湖泊涨水,泄洪不及而产生水灾,不仅对渔民的水上生活,而且对湖区渔民的捕捞工作都会产生影响。民国时期,洪泽湖渔民的捕捞渔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了洪泽湖的水文情况受气候影响之外,捕捞工具发展技术水平以及渔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也对渔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金龙四大信仰成为现实的洪泽湖保护神,主保护渔民造船、出湖捕捞方面收获丰厚、人口平安。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大了对整个湖区的蓄水、泄洪治理,洪泽湖大堤的维修、加固工程投入建设,防止其汛期决堤,同时加大抗震加固工程,全力保障洪泽湖,建设治理入海河道,开拓了洪泽湖的蓄水调度路线,纾解了洪泽湖蓄水压力,直至洪泽湖挡洪堤工程在2003年淮河大水期间受到威胁,汛后开始了挡洪堤的建设投资工程[14]。后期湖区蓄水泄洪的能力大大提升,湖区渔民生活渐趋稳定,对湖区的开发建设稳步进行中,渔业捕捞在政府帮扶下,渔民生活渐趋稳定,生活水平提升,转而对与自身生活切实相关的利益更加关注,需求更加多样化之后,对神灵的职司需求就相应不断增加,在神灵祭祀中采用各种方式予以酬谢[15]6。此时金龙四大王信仰仍然在渔民的信仰中居于首位,受到供拜。以老子山大王庙为中心,洪泽湖地区的渔民也会在家中进行供拜,挂金龙四大王神像,摆瓜果、面点,而后烧香。金龙四大王信仰深入渔民的生活中,节日、续家谱、造船等活动时进行祭拜。同时因信仰的功利性指向,渔民也会对专职的神灵加以供奉,以神灵的专司职能链接民众的利与害[15]4。穆墩岛渔民最为看重的供奉的神灵便是财神爷、观音、八仙及土地爷。湖区渔民船上生活方式转向定居,水产养殖成为主产业后,金龙四大王仍居首位,同诸神佑湖区养殖、人口、生活各方面。近年来穆墩岛大王庙应渔民生活需要,以养殖为主办动力,增加岛上渔民的生活性,改变了岛上渔民各家祭祀的状况,使得金龙四大王祭祀具有仪式性。以金龙四大王为首,同时兼有诸神供奉区域及财神殿,在大王庙外还建有土地庙,渔民因穆墩岛在2003年特大水涝中没有被淹没而祀土地爷,祈佑穆墩岛平安。金龙四大王信仰同时链接了湖区的其他渔民,以临淮一带的渔民参与居多,他们距离老子山偏远,穆墩岛的敬大王仪式满足了渔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内容指向当下生活的同时,也对过去金龙四大王信仰而有所呼应。
2.2 献祭中的洪泽湖渔鼓
对神灵的功利性崇拜,还表现在民众对神灵的献祭上,换取鬼神满足是崇拜者的实际要求[15]5。穆墩岛的“敬大王”仪式便是渔民对金龙四大王及其他诸神的信仰上所举行的“馈神灵”的献祭活动,其中洪泽湖渔鼓则是仪式性的突出特征。洪泽湖渔鼓在整个仪式中服务两个部分,即剧目表演与神灵表演,它们在活动中交替进行,贯穿在四大程序中,即开坛、请神、唱神、送神中。洪泽湖渔鼓随着敬大王活动而进行,由渔鼓艺人组织参与,在不同的阶段表演具有对应性,在音乐和舞蹈的环境中将人和神的本质转换,是人和神沟通的媒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16]。首先渔鼓艺人参与的是祭坛的布置。在大王庙内正中屋是主神金龙四大王神像屋,左为诸神屋,右为财神殿。祭坛则设置在神像屋和财神殿连接的区域,面向庙门的方向,表演则在祭坛正前方,祭坛上悬挂神像和刻纸装饰,刻纸则是由洪泽湖渔鼓艺人来制作。刻纸呈窄宽长方形,和神像同长,刻有花草、鱼类,相连排列呈现,多层错位覆盖叠加悬挂。下方摆了矮脚长条桌,摆放的物品包括西瓜、菠萝和橘子等瓜果类,塔状的面捏造型,又称面塑,以及各式糕点。供有烧香坛,香火不断。矮脚长桌两边各摆有五谷钱箩,将三角彩旗和纸钱元宝,也称神挂,插入装有谷物的稻箩中。在矮脚长桌前,于上方悬挂彩色刻纸,长度相较于神像两侧的刻纸,略短,整体形成门楣状。此刻纸前则是表演区域,由此祭坛完成。
然后由渔鼓艺人组织开始表演,表演的内容与渔民生活、生产相关,有教育规训的曲目,也有与生产相关的物产祈愿平安、丰产之意。渔鼓艺人通过服装、道具的装扮,以说唱和舞蹈的形式,配合剧情表演,同时还有艺人在表演区域两旁,间或以羊皮鼓的节奏鼓点完成一场剧目表演。表演的曲目通常是《魏征斩小龙》《刘文亮赶考》《张郎休妻》《孝顺女吊孝》。请神环节,一人颂吟诸神的介绍,部分艺人则在此过程中敲击羊皮鼓配合,一人成为神与人的媒介,以“拉刀子”表演,即在胸前、肩膀上划伤制造伤口,作为神来之显示。同时有两名艺人画符于神像前,从保管神像的渔民家中接神于此。之后便进入唱神环节,继续之前未表演完的曲目,同时进行“午坛绞生”的活动。一名渔鼓艺人仍为媒介,“汇报”穆墩岛渔民过去一年的收获,以神挂前悬挂鲜鱼、螃蟹各一只表示。然后绞杀新鲜的牲口,包括八只鸡、一只鸭、两头猪、四头羊,为上献的供品,同时祈祷新的一年生产生活的丰产、顺遂平安等美好的祝愿。一人表演“划刀子”,以此显灵。仍然有部分艺人敲打羊皮鼓构成表演一环。唱神结束,继续恢复剧目的表演,送神环节开始时,剧目暂停,艺人开始同请神一般,负责吟诵、表演羊皮鼓,成为由人转换为神的媒介,向洪泽湖渔民表达对此次活动的满意,表示将降福佑于穆墩岛,佑洪泽湖渔民之丰。神灵送归回其保管渔民的本位中,艺人完成剩余剧目的表演,所要表演的剧目结束,则敬大王活动结束。
3 洪泽湖渔鼓的日常转向
当前的洪泽湖渔鼓表演,在祭祀内容的关注上,娱乐性的成分有所增加,洪泽湖渔鼓艺人、渔民的交互性增加。
3.1 交互中的渔鼓艺人表演
洪泽湖渔鼓艺人主要以家族传承为主要的传承方式。洪泽湖区的渔民在自身有需要时便请渔鼓艺人进行表演,职业型的渔鼓艺人便转向半职业的形式,后继传承动力仍存在。目前洪泽湖区域渔民中老年人数居多,青年群体的活动地点以湖区外为主,生计选择更加多样化,生活水平提高,地域性质突出,学习洪泽湖渔鼓的兴趣和需求降低,洪泽湖渔鼓的家族传承动力减弱,表演艺人老龄化,无传承人,现存的湖区渔鼓表演艺人也仅五人参与到穆墩岛“敬大王”活动中。岛上渔民中有一支“敬大王”活动组织队伍,为了保证渔鼓曲目的顺利完成,除了联系湖区的表演艺人,也会联系山东的渔鼓艺人来共同表演。山东渔鼓艺人在穆墩岛“敬大王”活动中表演人数达八人,职业从事渔鼓表演。山东渔鼓艺人以表演团为活动中心,根据需要,出发前往各地进行渔鼓表演。参与穆墩岛的渔鼓表演团的成员皆为山东微山湖一带的艺人,通过家族传承和收徒制双重并行的传承方式使得山东渔鼓艺人的中青年人成为表演团强有力的群体。
洪泽湖渔鼓艺人和山东渔鼓艺人在曲目安排上,以洪泽湖地区为主,根据岛上渔民需要而安排剧本,表演的道具、出场顺序安排则是双方艺人交流决定。整个表演过程中双方艺人既独立又统一。山东艺人在剧目表演中,负责说唱和舞蹈表演部分多于洪泽湖区域渔鼓艺人的表演部分,洪泽湖区域的渔鼓艺人主要负责敲击渔鼓配合表演,于是在面向穆墩岛渔民时,转换身份,代为洪泽湖区域的渔民,加强和台下观看的渔民之间的互动性,夸大表演的动作幅度。在神灵表演环节中,山东艺人成为人神媒介者,以中间者的身份吟诵唱词,转述表达洪泽湖区域的状况和渔民的祈愿。多神秘性的中国民间信仰,以超常的表演方式及多样的表演法具表现出人们对神灵的崇敬[15]8。不论是“拉刀子”表演还是艺人在成为人神的媒介时,山东渔鼓艺人及洪泽湖区域艺人都在表演中显示出弱神秘性的特征。在表演区域,敲打渔鼓的艺人则会着日常服饰,而艺人也会在唱、跳的剧目表演时进行装扮,个别曲目中这种行动没有严格的服装要求。如《魏征斩小龙》剧目中,会有艺人在表演审判情节时直接穿日常服饰,戴上黑色礼帽即表示神官。艺人表演的服装、道具很轻便,易穿着,同时也便于舞蹈。
3.2 洪泽湖湖区渔民交往密切
在“敬大王”活动中,洪泽湖渔鼓面向渔民娱乐性增强。这种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行的群体性敬拜活动本质上就是日常的信仰行为的延伸与集中展演,是日常实践的整体呈现[17]。社会记忆的方式之一即包括周期性的仪式,是集体记忆得以形成的手段与策略,同时也固化了群体认同[18]。每年三月初六洪泽湖渔鼓表演曲目反映了渔民生活状态,同时又蕴含渔民处世精神,对岛上养殖为生的渔民来说,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娱乐节目,同时联结的还有已经搬离岛内、但仍来参加活动的渔民,引起生产、生活的共鸣,走亲访友的时刻,使得地域认同感增加。如表演曲目中关于婚嫁的片段,加入渔家传统的婚俗,和渔民观众撒喜糖互动,气氛活跃。开始吟诵环节时,渔鼓艺人领头,渔民集体跪拜叩首,配合渔鼓敲击的鼓点,谈及祝愿时,渔民齐声附和“好”并伴有欢呼手势和嬉笑。
在神灵祭仪中,通过信仰链接的渔民生活具有同质性。由渔民对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和洪泽湖渔鼓的不可或缺性构成的“敬大王”活动对整个湖区具有影响。活动的第四天,渔鼓节目全部表演结束,开始金龙四大王烧香活动,除了本岛的渔民,还包括靠近穆墩岛的洪泽湖其他区域的渔民参与到活动中。所有上香的渔民在集体烧香祈愿金龙四大王活动结束后,可以得到“大王旗”,将它插于田地间可以佑财进、养殖顺利、人口平安、心愿事成。领旗间隙人们互相交流养殖、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会准备共同进祝早餐,将渔民的日常生活性放大,这些活动密切了洪泽湖区域的渔民生活往来。对穆墩岛渔民来说,娱乐性的指向也增加了其经济收入,以上香和大王旗为主的收入来源,也是将这一活动持续开展下去的动力之一。
4 结论
洪泽湖渔鼓随着历史的变迁,进入洪泽湖区域,与洪泽湖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融合,随着时间而具有地域特色。当下洪泽湖渔鼓舞台化发展繁盛,而对于岛上的洪泽湖渔鼓来说,地域性的渔鼓传承人保护与传承工作仍然具有现实困境。在仪式性的地域需求下,人们对生活向上的祈盼,质朴而又浓烈,拉动了穆墩岛、洪泽湖区域的人员来往与交流,对地方文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