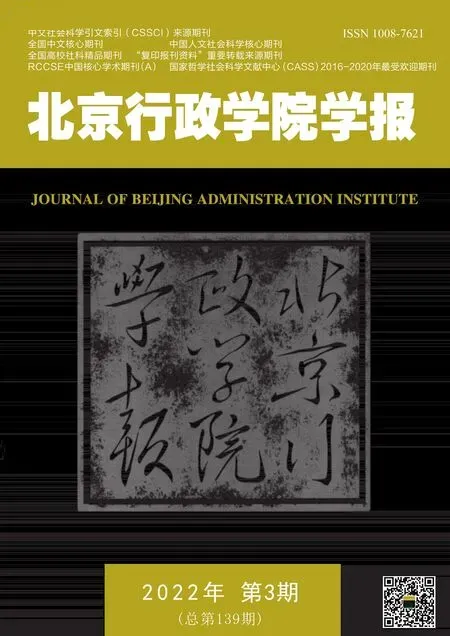逻辑行为主义的心灵解释及其困难
□欧阳文川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引言
作为一种心灵哲学思潮,从形式上来看,逻辑行为主义的外延似乎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逻辑行为主义者的论者既有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也包括个别日常语言分析论者以及一些持物理主义的心灵哲学家。由于和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思潮处于同一时代,并且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导致二者之间常常容易被混淆。这些方面都为厘清逻辑行为主义主要观点带来了困难。实际情况是,现有文献往往都是基于上述某一特定立场来进行分析,这样对逻辑行为主义的解释便成了对诸如逻辑经验主义的行为主义心灵哲学的解释,或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行为主义心灵哲学的解释。然而,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横向梳理是有必要的。一方面,这主要体现在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逻辑行为主义的理论贡献和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其本身的重要理论影响也需要人们去重新审视它,这尤其体现在逻辑行为主义对笛卡尔主义所引发的心身关系问题提出了崭新且极具启示性的解决方案,为此后的各类身心同一论、功能主义等物理主义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逻辑线索。因此,重新理解逻辑行为主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20世纪心灵哲学和科学哲学的逻辑发展脉络。正是在此意义上,“任何具有真理性的关于心灵的理论,都对逻辑行为主义有所汲取并与之具有一致性”[1]68。
一、逻辑行为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一般来说,逻辑行为主义主张心灵并不是一种内在的与外部行为偶然相关的隐秘机制,而是诸如行为(倾向)及相关外部结果的构成之物。据此,具有心灵仅仅意味着展现某种可被观察的行为,或者某种可被观察行为的倾向。然而除去这一共同点,逻辑行为主义者之间在基本立场与方法上又存在明显差别,很难说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且通常他们也拒绝将自己称为是行为主义者。如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和亨普尔(Carl G. Hempel)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有时逻辑行为主义专门指代他们的哲学观点;后期维特根斯坦与赖尔(Gilbert Ryle)专注于对日常语言的哲学分析,所以有时也会称他们是“日常语言行为主义”者[2]。除此以外,应当特别注意将“逻辑行为主义”与“取消的行为主义”“心理的行为主义”“方法的行为主义”或“经验的行为主义”做出区分。后者主要是20 世纪初由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和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在心理学领域主导的一场旨在变革研究方法,并借此使心理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心理学或心理哲学思潮。“取消的行为主义”主张以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人在“刺激—反应”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行为进行描述的科学理论,来取代传统的内省式研究方法与以心灵实体的存在为预设的“民间心理学”理论[3]。
可见,虽然都主张研究心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行为和行为倾向,但是逻辑行为主义将心灵描述为行为(倾向)并非意味直接否认本体论层面的心灵实体以及相应心理法则的存在,并不声称心灵只是行为(倾向),而只是将之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来看待,通过研究心灵及其同源性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意义,以此为基础获得像自身心灵认知一般确切的关于他人心灵的知识。例如亨普尔将心灵是否存在的问题视为伪问题,“心理结构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伪问题……不能认为我们只知道心理过程的‘物理方面’,而关于物理过程背后的心理现象是否存在的问题超越了科学范围,因此只能作为个人的信念而存在。……信念的对象原则上也应当是知识的对象。”[4]赖尔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亨普尔的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对于去除像心身关系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有着类似的观点和方法。他认为心身关系的困难起源于二元论哲学对心灵概念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运用,即将心灵作为服从机械因果律的概念来使用,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一旦将其消除,“心与物之间的神圣对抗将不复存在,但既不是心灵被消融在物质之中,也不是物质被消融于心灵之中”[5]12。
由此可见,逻辑行为主义者为避免他人无法像思维主体那样达到对自身心灵的直接准确把握而只能做间接推测的认识论困难,从而基于对笛卡尔主义传统的批判在根本上否认思想、意识或感觉的本质特性是私密的主观性。因此,为了使“他心”成为可靠的认知对象,就应当使心理内容具有可公共观察性与可理解性。然而,逻辑行为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既非直接取消心灵,也非寄希望于对心理现象的经验性研究来赋予心理学本身以科学地位,而是通过对包含心理概念的日常和科学语句的逻辑功能分析,来揭示隐藏在其表层语法和逻辑形式之中的更为基础和真实的逻辑功能,进而将之转化为具有相同内容或意义的关于行为(倾向)的物理性陈述。例如,赖尔将包含“信念”的心理陈述句的一般逻辑形式概括为“我相信X是Y”,它可以翻译为“我相信如果X被证明是Y,那么陈述句‘X是Y’表达了一个事实”[6]。亨普尔以陈述句“保罗牙疼”为例,也曾对此做过清晰的说明[4]。含有“疼痛”概念的心理性陈述“保罗牙疼”,可以被分析为若干具有可证实条件的行为—物理性陈述,例如:
a.保罗哭泣着并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姿势。
b.对于“你怎么了?”的问题,保罗回答“我牙疼。”
c.通过近距离的检查可以发现暴露着牙髓的腐坏的牙齿。
d.保罗的血压、消化过程和反应速度显示出一些改变。
e.保罗的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内部处理进程。
亨普尔认为“保罗牙疼”可以被重述为包括上述但不限于上述的行为—物理性陈述,类似的心理性陈述及其真值,实际上就是这些相对复杂的行为—物理性陈述所表述的可被证实或证伪的事实。显然,这些重述后的行为—物理性陈述不再包含“疼痛”这样的心理概念,但却表达了与之相同的内容和意义。简而言之,“疼痛”在这里的逻辑功能就是扮演这些较为复杂的行为—物理性陈述的缩略形式。
然而进一步分析亨普尔所列举的行为—物理性陈述,其性质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包含了面部肢体行为(a)、言语行为(b)、外部生理变化(c)和内部生理变化(d、e)。那么这里就存在不同类型的表述各自在何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行为—物理性陈述的问题,即行为—物理性陈述的标准问题。逻辑行为主义对此实际上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陈述应有公共性与可观察性。但即使如此,这个标准似乎仍然过于宽泛,因为在具体解释层面,哲学家们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何为逻辑行为主义的“行为”以及“行为倾向”做进一步澄清。
二、行为的可公共观察性
关于这一点,金在权(Jaegwon Kim)认为对于“行为”的判定还应区分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的不同,即行为是出自自身还是他人(物)。自己抬起手臂和被他人抬起自己的手臂,显然前者是主动行为。此外,主动与被动不能与有意和无意混淆,因为即使自己只是不自觉或无目的地抬起手臂,这也是一种行为。按照这一标准,金在权进一步区分了四种“行为”:一是生理反应,如分泌唾液、血压升高;二是身体运动,如投掷棒球、抬起手臂;三是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如向朋友致意、打电话;四是不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如推理、计算[7]66-67。金在权认为行为主义者最有可能接受第二种行为类型,这里结合亨普尔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行为d 可与金在权的第一种分类对应。按照亨普尔的证实性原则,这些变化显然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揭示并进而具有可观察性,但是由于d属于内部生理性变化,即使可被观察也需借助专门仪器,因而缺乏公共性,正常条件下人们会因无法观察他人的内部生理变化而导致不能辨识保罗牙疼;此外,单纯的生理现象描述虽可被证实但无法转译与“保罗牙疼”相同的意义与内容[7]70。由此可见,只以证实性原则解决心灵的内在性问题并不能达到对心理概念的交互理解,亨普尔后期也相应修正了这种观点。对于e,与d 的不同之处在于物理主义者有时将它作为心理现象的原因而非结果,但即使如此,因为它也是一种内在的生理现象,因此其面对的主要问题与d 并无不同。与d、e相比,c 虽然属于外部症状,但其是否具有公共可观察性是存疑的,并且人们可以合理设想一种逻辑可能性,即c虽然发生,但保罗并未感到牙疼,或者感受到的是其他部位的疼痛,这样c与“牙疼”之间只是偶然关系。由此可知,如果不将c、d、e和其他条件联系起来进一步考察,很难认为它们表达了同“保罗牙疼”一致的内容。
言语行为b可以与金在权的“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作比较。它们都具有可公共观察的特性,而且也是较为一般和可靠的获得关于他人心理感受和意图的行为类型。当保罗表情痛苦地说“我牙疼”,对方会自然获知“保罗牙疼”这一信息;当保罗向某人做出挥手的行为,对方很容易知道这是在向他致意。正因如此,这种行为类型被大部分逻辑行为主义者接受并据以认为是表达心理现象的较为合适的行为—物理性表述。然而问题在于它们存在一些隐蔽的心理预设[7]72,例如b实际上预设保罗是一个英语的熟练运用者,这意味着他对于对方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回答所蕴含的意义具有明确把握;另外当保罗确实感到牙疼,并进而做出b 中的回应,也说明他有向他人表达真实感受的意愿。向朋友致意同样如此,如果伴有言语行为,就涉及与b 同样的心理预设;如果没有言语行为,只有某种手势或其他示意行为,至少也预设行为主体一方面知晓其动作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默认他人有理解此动作意义的能力。固然,为了摆脱心理预设,b 行为以及与之类似的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可以被翻译为纯粹的物理语言,但显然这样完全脱离“民间心理学”语汇的表达方式将会丧失语言的日常交流功能,从而失去原有意义。由此,有关“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的表述至多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物理性陈述。
行为a 是保罗牙疼时所表现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可以与金在权的“身体运动”相对应。这类行为同样具有明显的可公共观察特性,能够很好地传达心理性陈述的内容,而且不存在明显的心理预设。因此,可以认为关于“身体运动”的陈述对于逻辑行为主义而言是最为适合的。金在权“不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在亨普尔的例子中没有对应陈述,可能的原因是这类行为只是停留在意识中的单纯心理活动,既缺乏可公共观察的特性又难以被证实(除非将之进一步还原为相关生理反应的物理性陈述)。因此,这类“行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具有相对于外部行为的独立性,例如保罗可以在不表现任何行为的前提下进行数学思考。这是否意味着实际存在着类似于“思考”的独立心灵活动?赖尔通过对“倾向”(disposition)概念的分析对此类问题进行说明。
赖尔并未将“不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视为一种私密的心灵活动,而只是将它作为主体在某种条件下会以某种公开方式展现的某种行为,即主体具有一种行为倾向,当条件满足时,他会将这种“不存在身体运动的行为”以公开的方式展现出来[5]108。赖尔将之表述为条件句“如果条件C 出现,那么X 会做出或者表现Y”。具体而言分为两种类型:“确定”(determinate)的倾向与“可确定”(determinable)的倾向[5]102。前者表示某种明确的行为倾向,后者表示不明确的一系列可能的行为倾向。例如“保罗有烟瘾”表达了保罗有吸烟的明确倾向,而“保罗很贪婪”则表达了保罗在某些情况下有做出某些行为的倾向,但未指定具体条件以前,无法明确保罗倾向于做什么,只有指定具体条件,如分配食物时,才能推断保罗倾向于获得超过他本应获得的份额。无论是有烟瘾还是贪婪,关于这些倾向的判断都是基于此前已经发生过的情况,如保罗频繁吸烟和索取过多的食物份额。因此对于“保罗在思考数学题”,不应当理解为存在一种内在独立的关于心灵实体的隐秘活动,而应将其理解为具有现实性的确定倾向,它意味着保罗具有将解答过程和结论以书写或语言等行为方式展现出来的倾向,在一定条件下,他会这么做而且能反复如此。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人们具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对“可确定的行为倾向”的解释是赖尔去除笛卡尔“机器中的幽灵”的重要部分。赖尔认为支撑笛卡尔心灵实体存在的关键是人的认知能力和意志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分析相关范畴的逻辑功能。这里与行为倾向密切相关的是认知能力。他认为认知能力源于人的理性,是搜集、处理各类事态和事物的信息以使其成为具有连贯性的能力。具体来说,人的认知能力集中体现为明智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特性,如精明与不精明、谨慎与不谨慎、愚蠢与不愚蠢等[5]14-28。判定一个人是否明智不是依据他掌握或者缺乏某些内在的知识,而是根据可供人们观察的历史经验,即他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是否具有在相应条件下做好某些事情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低又体现为他倾向于如何做事,换言之,判定的关键在于他如何去做而非在于他知道什么。显然,诸如一个明智或谨慎的人在何种条件下做什么、怎么做,这是一种“可确定的行为倾向”。
三、心灵现象的非本质性
针对一些可能的困难,逻辑行为主义者(如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①虽然学界一般将阿姆斯特朗称为“功能主义”或“物理主义”者,但很少有人怀疑他的哲学理论与赖尔之间具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有时他也被称为“当代行为主义者”。针对行为和心灵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1]58-64,从而进一步澄清人们将心理现象作为内在本质性状态的认识误区。
首先,与某一心理概念对应的行为陈述之间不存在共同特征。晚期维特根斯坦在对日常语言的功能分析中得出结论:基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定义概念的方法不符合概念的实际功能,概念的外延没有固定边界,其包含的特殊个体之间只具有“家族相似”性。他以“游戏”举例,“请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被叫做游戏’……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8]。与之类似,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心理概念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也是因为受到了传统定义方法的错误影响,因此由心理概念分析得来的行为—物理性陈述之间不存在某种共同的连续性特征,它们只在某些方面具有非连续的相似性。例如“高兴”,人们可以将之表述为“大笑”“手舞足蹈”“拍手祝贺”“拥抱他人”,甚至“哭泣”等,这些行为的特征之间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联系,但是并不存在共有的属性,“高兴”与这些行为陈述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具备排他性的对应关系。
其次,与某一心理概念对应的行为陈述之间有“中心”和“外围”之分。所谓“中心”,指一些典型的易于被他人理解的行为表现;“外围”则指一些非典型的不易于被他人理解的行为表现。例如当看到某人手舞足蹈,与此同时说着“我很高兴”,人们很容易将之理解为是“高兴”的表现;但如果某人面无表情地说着“我很高兴”,人们很有可能会产生疑惑。逻辑行为主义者认为,不能因为有时心理现象表现为不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行为而否认它们实际上就是这种心理现象的一种表达方式,从而得出心灵具有相对于行为的独立性的错误结论。因为这些不易被理解的行为只是相应心理现象的一种非典型的“外围”表现方式,它们好比是“家族相似”中相对于“近亲”而言的“远亲”。
最后,“中心”的行为陈述可能并不具备中心地位。根据“家族相似”理论,扮演“中心”角色的行为陈述并不是相应心理概念的唯一或者本质性陈述,“中心”不能理解为本质,既然如此,人们对于中心行为的设定完全有可能存在错误。例如,看见某人在笑,人们会自然将之理解为“高兴”,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或许他只是出于无奈地发笑。这再次说明心理现象与行为之间不存在非常确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逻辑行为主义者不认为造成这种理解偏差的原因是心灵具有相对于外在行为的内在独立性,而只是说明应当继续观察主体进一步的行为表现,或者将行为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来理解,以此来纠正对行为的错误解读。
归纳以上内容,心理概念与行为陈述之间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这是因为行为陈述本身所传递的内容缺乏相互区别的明确界限。一方面,某种心理概念可与包含“外围”性陈述在内的多个行为陈述对应;另一方面,某种行为陈述也可与多个心理概念相对应。从正面来看,逻辑行为主义者经此证明不存在独立的心灵实体及其内在活动,心理概念的真实意义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人的行为方式和功能的多样性中去寻找;然而从反面来看,为了解决身心关系问题,描画关于行为及其倾向的脉络图不仅是一项较为复杂的任务,而且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四、行为分析的问题
第一,对行为(倾向)的分析始终面临“社会文化”和“生物类型”背景两方面的限制。上文提到行为(倾向)的心理预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文化背景与主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的隐蔽关系;另外,它也说明如果将这种关系置于更广阔的跨文化社会背景之中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即由差异性社会文化而衍生的对主体行为理解的不对称问题。设想保罗向某人挥手致意,而对方与其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可能保罗的行为对他来说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涵义,这就导致了对方对此行为意义的理解偏差。言语行为存在类似情况,不同语言系统的人面临蒯因的“译不准”问题[9]。蒯因设想一个语言学家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依靠与直接经验相联系的“场合句”(occasion sentences)作为与当地人交流的基础,通过反复观察与检验,他将“兔子”与当地人发出的gavagai 声音相对应。蒯因认为语言学家的翻译预设了两种语言的概念指称系统相一致,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不同的概念指称系统所对应的是不同的概念和语言系统,以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之间不可能做到彻底翻译。
相较于b 而言,行为a 作为“身体运动”具有较大普遍性,没有明显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限制,也就是说,无论何种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当出现疼痛时,他们会表现出大致相似的面部表情和行为动作并发出类似的声音,但这是否意味着关于它们的陈述是被绝对蕴含于“疼痛”概念中?如果肯定,则任何有机体疼痛时都会出现基本一致的行为表现,包括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但显然并非如此,因为人类与其他生物类型的生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受生物类型背景的限制,任何有机体必然只会表现出与其生物类型相对应的那种特殊的行为类型。
第二,对行为(倾向)的分析具有“末端开放”的特征[10]。严格来说,行为分析的“末端开放”也源自“环境限制”,但这里主要指主体所处外部环境中的一种具体情势,而非社会文化环境。它指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心理概念确实可以作出一系列关于物理—行为陈述的分析,但必须将这种分析置于主体所处的具体外部环境之中,并与主体因为环境而产生的其他新的信念、欲望等心理现象结合起来考察。然而环境变量是极其多样的,因此一旦将这些影响结合起来考虑,那么在理论上主体的行为(倾向)可能性就是无限多的。例如一个感受到剧烈疼痛的人,他可能在敌人的酷刑下(a 场景)为了展现视死如归的决心而放声大笑,也可能在被敌人搜寻的危险境况下(b 场景)因试图隐蔽自己而悄无声息。逻辑行为主义所提出的关于“中心”和“外围”、“典型”和“非典型”陈述之间的区分,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行为(倾向)分析的这种“末端开放”特征的描述。诚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结合主体所处的具体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具不确定性和极其复杂的任务。
第三,对心理概念的分析面临“恶循环”的逻辑困难。逻辑行为主义者揭示了同一行为(倾向)可能对应于多个心灵状态,然而仅仅将之归因于二者之间的模糊性,他们并未认识到心灵状态具有整体性,特定行为(倾向)通常都出自多个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心灵状态[11]。如上文所述,当保罗告诉他人“我牙疼”时,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心理预设,即保罗具有告诉他人自身真实感受的愿望,如果没有这个愿望,保罗不会将“我相信我牙疼”的信念传递给他人。同理,如果保罗仅有愿望,而没有“我相信我牙疼”的信念,或者对此存疑,即怀疑疼痛很有可能源自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么保罗也不会回答“我牙疼”。换言之,“是否相信自己牙疼”的信念与“是否愿意告诉他人自己牙疼”的愿望是言语行为“我牙疼”的共同构成条件。
为了消除问题,逻辑行为主义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物理—行为陈述来分析存在逻辑关联的其他心理概念,这虽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但尚且可行。然而由此引发的真正困难在于由心灵状态分析得来的行为(倾向)在逻辑上总是可能因为与之伴随的其他心灵状态而被改变或者取消,并因而导致心灵状态之间形成无限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从而永远无法将心灵状态分析为某种明确的行为(倾向)。例如,当保罗告诉他人“我牙疼”,对方可由此分析他具有“我相信我牙疼”的信念与“我愿意告诉别人自己真实感受”的愿望。但如果保罗也认为如果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会因此失去重要活动的邀请,那么他会隐瞒自己的情况,但如果与此同时保罗又认为及时就医比参加活动更重要,他就会告诉对方“我牙疼”,以此类推没有终点。这导致无法将言语行为“我牙疼”对应于任何心灵状态。金在权将这个问题描述为身心之间的“可废除性蕴含”(defeasibility entailments)关系,并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种形式[7]74:
1.如果行为B 可被合理蕴含于心灵状态M1,…,Mn,那么总是存在进一步的心灵状态Mn+1,从而使得M1,…,Mn,Mn+1一起合理地蕴含-B;
2.如果行为-B 可被合理蕴含于心灵状态M1,…,Mn,Mn+1,那么总是存在进一步的心灵状态Mn+2,从而使得M1,…,Mn,Mn+1,Mn+2一起合理地蕴含B。
显然,不能简单将身心间的“可废除性蕴含”关系理解为其相互对应的模糊性。后者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将行为(倾向)置于更广阔背景中理解或者对更进一步的心灵状态展开进一步行为(倾向)分析来解决;而前者的问题在于对行为(倾向)的分析始终面临无限的更进一步的其他心灵状态,这导致解释的恶循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对于心灵状态的行为(倾向)分析变得完全不可能。
第四,行为(倾向)与心灵状态之间存在“解释鸿沟”[12]。莱文首次以“解释鸿沟”一词来说明以纯粹的物理性质或功能难以解释人的“感受性质”(qualia)。虽然不能直接将逻辑行为主义等同于物理主义,但二者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简单来说,“感受性质”是意识经验的质的特性,是一种本质的非关联、非意向的内在体验。实际上,行为主义的哲学方法正是在忽略或者否认心灵这一独特性质的前提上构建起来的,然而这也恰恰说明逻辑行为主义无法解决它。
主体的行为(倾向)不应被仅仅还原为内在的物理机制或单纯的外在现象,C-纤维肿胀和特定的肢体言语行为使得“疼痛”被认识和理解,但除此以外还有主体对它的真实体验。因此,行为(倾向)不是心灵状态的充分条件。对此可以借用“僵尸”这种可设想的逻辑可能性加以反驳[13]。可以设想一个在所有物理方面(包括外部行为动作和内部生化状态)和有意识的人一样的“僵尸”,但它缺乏人的主观意识。例如,当僵尸被针刺伤时,它会表现出和正常人完全一样的行为动作、发出一样的声音,其体内也会出现和正常人相同的生理变化,如C-纤维肿胀,不同的是它没有真实的疼痛感受。在此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区分僵尸和一般人,甚至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僵尸。
某种行为(倾向)可能永远不被表现出来,但不能因此否认主体没有表现它的那种实际特性。因此,行为(倾向)不是心灵状态的必要条件。非生命物体既没有行为也没有心灵,但对于生命有机体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丧失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和掩饰情感的伪装者。关于伪装者,亨普尔认为可观察的外部行为仅仅是一些局部证实性条件而已,如果进一步深入主体内部的生理变化过程,人们就能够辨识出这种伪装。然而上文已经论证生理现象并不是对于行为的合理解释。普特南在批判逻辑行为主义时提出过一种“超级斯巴达人”的思想实验[14]。他设想经过对于意志力的常年严苛训练后,“超级斯巴达人”在感受到疼痛时,除了会告诉他人自己感觉疼痛以外不会表现出任何行为动作。人们还可以设想经历更久的时间后,“超级斯巴达人”甚至不会告诉他人自己疼痛,或者佯装不知道“疼痛”一词的所指。应当说,这不仅是一种可设想的逻辑可能性,还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结语
逻辑行为主义的特殊贡献在于指明对行为(倾向)进行细致分析是理解心灵的颇具启示性的方法,然而完全依赖这种方法却注定是要失败的。上述四个方面问题实际上都朝向一个点,即要使得心灵状态成为可理解的对象,不能将它单纯还原为对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倾向)的分析,相反还应再设立一种扮演心灵角色的内在机制,使它成为联系特定条件和行为(倾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又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这种内在机制到底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它与“心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它是心灵本身还是仅仅发挥着与心灵相同的功能:如果是前者,是否有先天必然性?如果是后者,它的自身特性与功能特性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逻辑行为主义虽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却引发了这些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后来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前进的所有心灵哲学思潮都无法避开逻辑行为主义①本文也为新疆师范大学哲学重点学科一般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