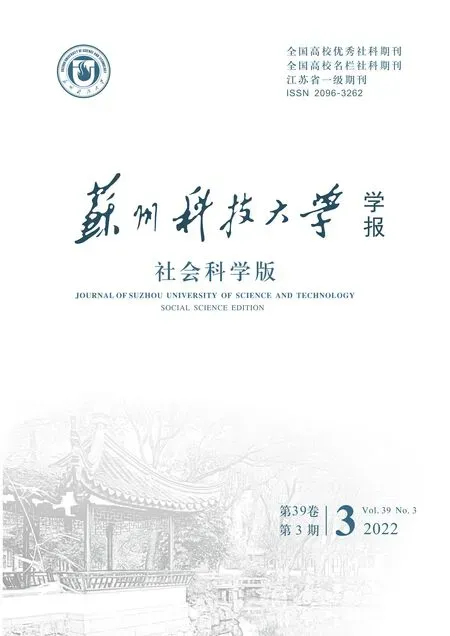嘉庆四年“苏州诸生案”诗歌本事考*
赵杏根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引 言
范来宗(1737—1817),字翰尊,号芝岩,一号支山,吴县人,范仲淹二十三世孙,擅诗词,王昶《湖海诗传》卷三十三、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卷十四分别选其诗词。今考其《喧喧》诗之本事。该诗为二首,其一云:
喧喧走集尽如迷,患起纤微转怆凄。
狱吏权尊威似虎,儒生力弱命如鸡。
笔书牍背刑章定,帜偃文坛党祸齐。
惆怅一亭芳草绿,春风虚掩夕阳西。
其二云:
九重明诏忽遄临,宝鉴高悬翳不侵。
除酷更穷贪墨弊,裭官先慰士民心。
今看对簿仓皇出,昨见排衙气象森。
雅化至今思单父,风清堂上昼鸣琴。[1]
该诗见范来宗《洽园诗稿》卷十,编年在嘉庆四年己未。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三云:“范来宗,……举乾隆庚寅乡试,壬辰,以中正榜,授内阁中书。乙未,成进士,官编修十余年,乞养归。为文正义庄主奉二十余年,百废具举,增置义田一千八百亩。嘉庆十九年重游泮宫。卒年八十一。”[2]此“乙未”即乾隆四十年(1775),据此推算,范来宗写此诗的时候,就在家乡苏州居住。
《喧喧》诗的本事,当是发生在嘉庆四年的“苏州诸生案”,有些载籍或作“吴县诸生案”。该案起因固然是吴县诸生,但实际上被卷入的还有元和、长洲两县的许多秀才,故以“苏州诸生案”名之比较合适。从《喧喧》诗的内容看,当是地方官员打压儒生,将他们关进监狱,严加刑讯,后皇帝下诏,追究这些地方官员的罪行。
二、“苏州诸生案”的大致经过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记载“苏州诸生案”之过程,甚为详细。略云:嘉庆四年四月十七日,吴县生员吴三新,以负杨敦厚钱,为知县甄辅廷杖责二十。按照规定,诸生是不能受刑的,除非其已被革除诸生资格。二十七日适院课,诸生李福、顾莼等二三十人知道后,诉于知府任兆炯,任不理。五月十一日,学政平恕考松江回到苏州,苏州诸生按例到码头迎接并面诉此事,而地方官已贿请平恕严办诸生。次日,学政平恕在书院考诸生,诸生抗议当局对吴三新“未革先杖”,不愿应考,以致到者寥寥,监院吕星垣马上以“罢考”公示并且上报。于是巡抚宜兴、臬司署藩司通恩命总捕同知李焜、长洲县令梁兰生、元和县令舒怀及吴县县令甄辅廷查办。李焜等传集各学门斗,命开报闹事诸生姓名。元和训导杨廷棐将三县和苏州府学中家里富有的以及他平日心怀恨意的诸生全部开列,呈送李焜。李焜等遂一面拘传诸生;一面对各学校门斗施加刑罚,让他们交代闹事诸生。许多诸生被捕后被革除诸生资格,如不按照官员们的要求供述,则加酷刑。自十二至十六日,计拘诸生二百余人。巡抚宜兴会同学政平恕以“纠众扛帮滋事劣生照例严办”具折入奏,折内所叙,半属虚词。嘉庆帝朱批:“江苏文风最胜,士习安分,朕所深知。尔听一面之词,办成大案。甄辅廷着革职,交费纯秉公质讯覆奏。”在嘉庆帝的干预下,宜兴、平恕、甄辅廷俱被劾去,绝大多数诸生被取消的诸生资格得到恢复。[3]776-777这就是《喧喧》诗第二首所云:“九重明诏忽遄临,宝鉴高悬翳不侵。除酷更穷贪墨弊,裭官先慰士民心。今看对簿仓皇出,昨见排衙气象森。”[1]但是,诸生马照、袁仁虎、王元辰被充军或流放。赵怀玉《书吴县诸生狱》所载稍略,而主要情节大体相同。[4]
王先谦《东华续录》之《嘉庆八》载,嘉庆四年(1799)七月“丁卯,宜兴以偏听属员滥刑解任。以岳起为江苏巡抚”[5]447,此“丁卯”为十一日。学政平恕于八月初一日召回京城,降为少詹事,但此年就晋升为内阁学士,次年晋升兵部右侍郎,并有再任江苏学政之议,遭到御史王苏的竭力反对。王先谦《东华续录》之《嘉庆十二》载御史王苏的奏章,称“平恕前在江苏斥革生员多名,人人切齿,即商贾小民无不痛恨”[5]525,王苏因此被嘉庆帝处分,但嘉庆帝也因此取消了平恕江苏学政的任命,将他调任户部右侍郎。
前期直接负责此案刑讯且对诸生下手最为毒辣的是李焜。此案结束后,他自然被追究,甚至还被下狱,后为人所救。秦瀛《小岘山人续文集》卷二《山东泰安府知府沈君舫西墓表》云:“君遇事直陈,刺举无所避。其最著者,苏州总捕同知李焜,以嫌捕系诸生,牵连下狱,君奏白其冤。”[6]686其实,李焜在此案中岂是“以嫌捕系诸生”而已?岂止受“牵连”而已?后来,李焜又在湖南当上了知县,以非法为其子谋取诸生资格事,被湖南学政吴省兰参劾,流放新疆。嘉庆帝朱批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语,即指李焜酷虐苏州诸生之事。事见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三、俞正燮《癸巳剩稿》、《清史列传·吴省兰传》和《同治苏州府志》等。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三《闻吴侍讲泉之时有参劾作为湖南学政》即写吴省兰参劾李焜事,也涉及当年“苏州诸生案”。诗云:“觍颜尚冀履花封,快听风雷下九重。豺虎有知原不食,鹰鹯必逐自难容。旁观尚欲舒公愤,当事能无愧曲从?谓平宽夫学使天道恢恢原不漏,昌言真足警群凶。”[7]此“平宽夫”即平恕;此“天道恢恢”,即本于嘉庆帝的朱批。
三、当局兴此大狱的目的
一个秀才拖欠富户钱财这样的小事,竟然发展成轰动苏州的一个严重悲剧,真如范来宗《喧喧》诗第一首开头所云:“喧喧走集尽如迷,患起纤微转怆凄。”[1]这颇有值得我们探讨之处。甄辅廷身为知县,岂有不知诸生不能用刑之理?因拖欠财主债务这样的小事,何至于把生员吴三新杖责二十?诸生为同学遭到知县违例用刑而告官乃至罢考,当局有多种选择轻松化解此事,何至于拘捕两百余诸生?当局对诸生的手段,远出于情理之外。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云:“(李)焜等遂一面拘传,一面刑门斗,遍令妄供。诸生或拘于土地庙戏台下,或拘于府署马厩中。是夜,通臬司饮平学政酒,其署与总捕署相距数十家。李焜传一人,即书姓名,送臬署,学政即批‘斥革’二字。未及一更,已革二十余生。自十二至十六日,计拘诸生二百余人。每集讯,诸生受刑惨酷。窃听者填街塞巷,有持梃以俟者,有登高以呼者,忿激之气,不可遏抑。所具供,李焜必加朱改削,勒令重写。有不遵者刑之。”[3]776-777可见范来宗《喧喧》第一首颔联“狱吏权尊威似虎,儒生力弱命如鸡”[1]完全是写实。苏州知府任兆炯的表现尤其令人费解:“十六日,兆炯自江宁回。戌刻,悬示于门。将所拘诸生及已传而未到者,单开晓谕。人心稍定。盖兆炯欲严办此案,恐制府掣肘,故赴江宁探意,而使李焜受首祸名。其诡诈如此。”[3]777些微小事,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借此兴此大狱? 答案很明显,他们为了谋财。当然,他们之谋财有层次之分,也和当时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
地方官敛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对富户或者下级官吏、绅士下手,如在河中汲水,即使河不多,但获得的数量可观;二是利用赋税之类的工具对治下百姓下手,如汇集大小沟渠之水,即使一沟一渠之水量不大,但沟渠众多,总数也会可观。官员们对秀才们下手,是用从河中汲水的方法谋取钱财。甄辅廷违制对吴三新用刑,是为了给债主逼债。一个堂堂知县为何冒险为债主逼债?王昶《与平恕书》云:“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其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扑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此非该令平日与富户交结往来,受其馈赂,即系意存庇奸为事后得钱之计,情事显然,不待推求而可见。”[8]343他们对众诸生下手最为表层的目的也是为了钱财。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云:“江苏生员之狱,巡抚宜兴庇护属员,又信任管门家人,致使苞苴日进;特造严刑以讯告者,有小夹棍、头脑箍诸名目。”[8]351-352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载,“有元和训导杨廷棐者,将四学富生及平日所心忮者开具小折”,实施抓捕,元和县令舒怀“则诱诸生妄供富衿,及到案,则又竭力周旋,为求钱计。(长洲县令)梁兰生亦然”。[3]776-777这些官员显然把诸生当成他们的鱼肉了。诸生未必都是富户,但属于贫困户的诸生显然不多。可是即便如此,也不值得众官员如此大动干戈,其实,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的地方社会生态中,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和绅士、百姓是重要的三种力量。百姓如果无人带领就无法形成力量。绅士可以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即乡居官宦、本地官宦近亲和举人属于上层绅士,诸生和没有科名的读书人属于下层绅士。上层绅士往往和高层有联系,社会地位高,社会影响大。一般来说,以诸生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年纪较轻,富有正义感,和百姓最为接近,最有可能为百姓的利益说话,站出来反对官员的不公不义。我们不难发现此类例证,如清代的“抗粮哭庙案”,此类事件也是民间故事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众官员如此大肆迫害苏州诸生的深层原因,也正在这里。
王昶《与平恕书》就揭示了这样的原因:“至近来州县所以鱼肉诸生,其意盖在立威。威立而诸生箝口结舌,则庶民何敢出而争控?是以狱讼之颠倒,征收之加耗,无所不至。比者言路大开,江南漕政,横征重敛,已一一仰叨圣鉴,故制府亦力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县或有阳奉阴违,倍收多取,恐生监连名讦告,而州县指为哄堂闹事者甚多,未知执事可能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后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县之失,而即科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焰而长其气,则吏治之坏,不知伊于何底也。”[8]345王昶致仕前官居刑部右侍郎,又曾“陈臬三司,且于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为堂上官,所见生监控告之案,不胜枚举”[8]345,故对此类案件,可谓洞若观火。
在封建社会,政治的力量总是最为强大的。即使是秀才这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甚至是读书人群体,遇到知县或者同知之类的下级官员,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即使他们在道义或者法律上处于优势,如果没有更加强大的体制内的政治力量援助,仍然改变不了这种劣势。就在与此案相隔两个甲子多一点的顺治末年,苏州爆发“抗粮哭庙案”,金圣叹等十八位秀才掉了脑袋。和金圣叹等人几乎同时,浙江台州的诸生为了抗议知县对某秀才逼交拖欠的钱粮用刑致死,集体签署声明,放弃诸生身份,结果两人被杀,六十多人被流放。如果百姓介入,那么事件的性质就改变了,成了体制内外的冲突,结局很可能更加糟糕,这样的事情后来在浙江发生过。以上发生在浙江的事件,笔者另撰文予以研究。
“苏州诸生案”中,涉案的诸生没有人被杀,实在是侥幸。案件之所以有绝大多数诸生资格被恢复、相关官员被处分的结局,关键在于嘉庆帝的干预。范来宗《喧喧》第二首“九重明诏忽遄临,宝鉴高悬翳不侵。除酷更穷贪墨弊,裭官先慰士民心。今看对簿仓皇出,昨见排衙气象森”[1]云云,既是纪实,也揭示了封建社会解决自身负面势力最为常见的模式,即比这种负面势力更为强大的力量出手战胜之,而体制内最为强大的力量,就是王权。古代忠奸小说、戏剧中,正义和邪恶较量,正义的一方经过诸多曲折,付出巨大代价,乃至惨烈的牺牲后,皇帝出手,顿时势如破竹,正义才能战胜邪恶,这已经成为模式。范来宗《喧喧》诗,竟然也符合这个模式,可见这样的模式是有一定的事实为基础的,并不纯粹是作家的虚构。
那么,上层绅士又如何呢?和以诸生为主体的下层绅士相比,上层绅士离百姓的距离较远,年岁较大,社会政治经验较丰富,正义感和锋芒显然远远不及诸生,对当局的威胁也就小得多。就当局而言,府县官员一般都注意维护和上层绅士的关系。例如,苏州知府任兆炯和当时苏州及其周围地区的上层绅士有互动。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三有《题任太守晓林兆炯虎丘白公祠长卷》、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之《济上停云集》卷一有《白公祠为任太守兆炯作》、洪亮吉《卷施阁集》之《诗》卷十九《全家南下集》有《虎丘谒白公祠即呈同年任太守兆炯祠即太守所建》、王芑孙《渊雅堂全集》之《惕甫未定藁》卷七有《灵鹫寺增置田屋记》,都是明显的证据。可见,任兆炯是很注意维护和上层绅士之间的关系的。官员也会避免和上层绅士的冲突,主要因为上层绅士很可能引来更为强大的体制内政治力量,他们不得不忌惮。“不得罪巨室”的古训和《红楼梦》中的“护官符”,都是这样的道理。这在政治力量最起作用的社会,州县府级别的官员不大敢向上层绅士下手,上层绅士也不大会主动挑战当局官员。当时苏州那么多家居的上层绅士,为此事件发声者只有范来宗,且《喧喧》还是写在大局既定之后。在诸生遭受重刑乃至“笔书牍背刑章定,帜偃文坛党祸齐”的时候,他所做的也不过是“惆怅一亭芳草绿,春风虚掩夕阳西”[1]而已。
四、失职的官场和沉默的舆论场
当时的官场,正义的力量不免薄弱。这和当时普遍存在的官场黑暗有关,也和当时江苏某些职位不稳定有关。王昶《与平恕书》云:“惟是时承审之员,非该令平日结纳之上司,即系狼狈为奸之寅好。通臬将赴湖南,不顾其后,而抚军初莅新任,以至四出查拿,牵连数十,掌嘴镇项,凌辱不堪,成何政体?”[8]344查《清代职官年表》可知,嘉庆四年(1799)二月十三,宜兴才由仓场侍郎署理山东巡抚改为江苏巡抚。布政使荆道乾当年二月初二才上任。于苏州,他们确实是初来乍到,平恕担任江苏学政也不足一年。按察使述德三月十三才到任,大概没有履行职责,故由通恩代理,而通恩已有赴湖南任职的任命,述德在七月因年老被召回京师。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年二月十三日由江苏巡抚晋升两江总督的费纯,就容易一手遮天了。当时江苏巡抚的衙门在苏州,苏州知府任兆炯以及吴县、常州和元和三个县的知县,都是费纯的老部下。正如王昶所说,对吴县知县甄辅廷来说,“惟是时承审之员,非该令平日结纳之上司,即系狼狈为奸之寅好”[8]344,当时官场的这张关系网就明明白白了。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云:“审案各官如费总督纯、孙布政日秉、钱学政樾、江宁知府许兆椿,皆心知其冤,欲解救而无及者。其次常州府吕燕昭、太仓州汪廷昉,虽与兆炯等同时承审,而颇费调护。”[2]778费纯的官位和权力比巡抚大得多,钱樾更是后期介入的,有嘉庆帝的支持,案件的是非更是不难明了,可是,他们竟然如此软弱,原因何在?关键在于费纯本人。由《同治苏州府志》中“盖兆炯欲严办此案,恐制府掣肘,故赴江宁探意”[3]778等句可知,苏州知府任兆炯从南京回到苏州后就放手迫害诸生了,“严办此案”是任兆炯和老长官费纯商量好的。既然如此,作为这个大狱的幕后主谋,费纯还会秉公办理吗?其他参与审理的官员都是费纯的部下,他们有那么大的胆量违背费纯的旨意秉公办理此案吗?结果是,此大狱的实际责任者费纯、任兆炯都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处分。
此案中的一些小官吏却表现出可贵的品质和鲜明的正义感。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云:“若书院值路门斗以受刑毙命,东城地保某以奉牌拘人自缢。……长洲教谕汪广堂、吴县教谕洪守义、训导程廉,未曾开报一生。府教授汪佑煌、训导秦智钅共,于李总捕饬传开报滋事姓名时,言府学实无一人,如必欲妄开,情愿听参。李焜亦无如何。”[3]778又云:“初,狱未具,兆炯召书院门斗俞闻,令具姓名。鞭挞横施,臀肉尽脱,俞坚不承。”[3]778朱绶《知止堂诗录》有《俞文传》记其事。[9]188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十二《书吴县诸生狱》云:“教谕洪守义持正弗阿,奔驰援救,力不胜,愤懑死。学吏方泰不肯罗织,撄严刑,雉经死。其子某痛父亦死。乌呼!教谕之伤其类,死固宜;泰以学吏,乃甘受挫辱,罔惜身殉,至于父子并命,视读书自许,俨然而为民上者何如哉!”[4]可是,他们位卑职低,根本无法改变官场的黑暗。
令人浩叹的,还有当时江苏特别是苏州及附近地区的知识界的失语。江苏特别是江南,文风极盛,当时在朝当官,在野治学、写作诗文的知名人物很多,其中不少是上层绅士。但是,除范来宗写《喧喧》诗、赵怀玉写《书吴县诸生狱》、王昶给平恕写批评信外,其他人都是沉默的。江南士气从清初被毁灭性打击以来,至此还没有恢复。诸生如初生牛犊,为同学的不平罢考抗议,虎虎有生气,但经此一案,这些生气恐怕也所剩无几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昶和张焘。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云:“及事急,青浦王司寇昶致书学政,浙西张侍郎焘致书巡抚,切责之。”[3]778张焘的信已难以找到,王昶的信是其退休家居时所写。嘉庆四年(1799),王昶到京师参加乾隆帝的葬礼后回乡,七月间路过苏州,拜会江苏巡抚宜兴等人,回乡后给江苏学政平恕写了一封长信,严肃批评和深刻揭露平恕等的行为,敦促平恕改正错误。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三《春融堂集诗纪李焜事》记载:“司寇先有与平学使一书,责其徇州县而虐诸生,语甚侃直,为时传诵。而《文集》未编入,后见钱思元《吴门补乘》中已刻之,故不复缀。闻狱方急时,乡先达皆以慎默远嫌,虽为之师长负重望者,亦嗫嚅不敢发一语与有司抗。得司寇此书,士气赖以稍振焉。”[10]此信未编入王昶《春融堂集》,除叶廷琯所说的《吴门补乘》收录之外,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和顾沅《吴郡文编》亦收录之。
五、结 语
“苏州诸生案”在嘉庆帝的干预下,绝大部分诸生的资格得到恢复,但有三位秀才被流放。江苏巡抚宜兴、学政平恕、知县甄辅廷被撤职,但主谋并负有主要责任的两江总督费纯、苏州知府任兆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局兴此大狱的目的,不仅是谋取诸生家的钱财,更是以此打击士风,方便他们鱼肉百姓。因此,此大狱实际上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地方官员和当地下层绅士矛盾的体现,官场的黑暗是导致此大狱的主要原因,舆论场对与政治相关的公共事件的沉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