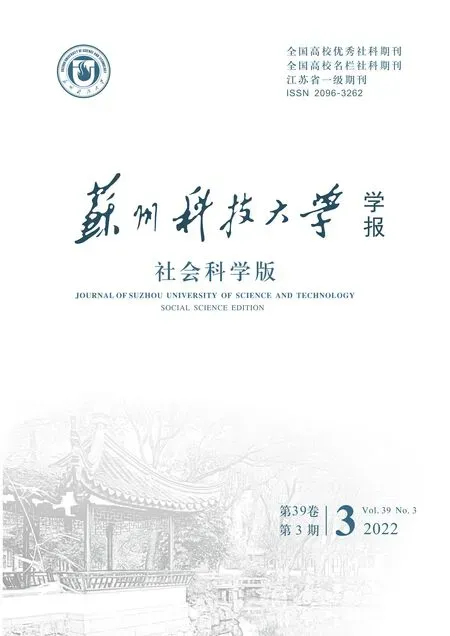“我”的还乡之旅*
——《小妖集市》的拉康式解读
慈丽妍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一、引 言
《小妖集市》(“Goblin Market”)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的名篇。近二三十年来,这部作品引起了中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界对该诗扑朔迷离的主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首诗所表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堕落与救赎主题[1];有人认为它表达了强调姐妹力量的女性主义主题[2];还有人认为它所表达的是十九世纪工商业发展所导致的食物掺假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损害[3];等等。笔者认为,对于这首诗主题的探索应该结合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和诗人的个性及背景。拉斐尔前派以忠实于自然为宗旨,但“它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所宣称的那样,在于它表现的高度精确性,也不在于其科学的完整性,而是在于它对想象力的运用”[4],因为他们所忠实的并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一种心理的自然。可见,拉斐尔前派艺术旨在摆脱理性束缚,真诚自然地表达内心情感。克里斯蒂娜性格内向,“害羞,难以捉摸,但却像他的大哥一样情感深刻,富有诗人天赋”[5]21。从年轻时候起,她就基本上过着一种宁静的半隐居生活。她从18岁开始就不再去剧院,“从1854年到1866年(《小妖集市》就是在此期间创作的),她的生活基本上只围绕着三件事儿,那就是艺术、宗教以及照顾瘫痪的父亲”[6]。而她的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使她对自我的心理真实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因此她的诗歌表面看来简单平静,可是这平静之下却汹涌着诗人对人生的无比困惑、矛盾和挣扎。莱昂内尔·史蒂文森(Lionel Stevenson)认为:“她的这种自我克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谦逊的习俗,而是与流淌在罗塞蒂家族血液中骚动不安的那不勒斯人的激情进行殊死搏斗。”[5]80克里斯蒂娜的诗歌主题之一就是分裂的自我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与和谐,如《三位修女》(“Three Nuns”)、《阻挡》(“Shut Out”)、《高贵的公主》(“A Royal Princess”)、《小妖集市》等。对此,研究者们也早已给出了评价:“克里斯蒂娜建立起一种内部神话,来讨论她强烈意识到的那些心理现实”[7]81,“我们更应该将她视为一位严肃的、技艺精湛的末世论和心理学诗人,她已经稳稳地跃出维多利亚和拉斐尔前派的语境而进入时空更为广阔的人类经验的语境之中”[7]89。鉴于此,笔者以法国心理学家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 1901-1981)关于主体的理论来解析《小妖集市》,探讨诗中由“小妖”“水果”和“姐妹的家”构成的心理世界,并以此反观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现实和个体存在的思考。
二、“三界说”与《小妖集市》——“故乡”的由来
根据拉康的观点,主体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现实界与母亲的身体合一,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在这里,物我未分,没有自我也没有他者,完全处于一种无知无序的自然状态。现实界是一个无法象征化的领域,因此是主体无法接近的领域。人要进入文明世界成为主体,就必须打破这种自然的圆满具足的状态,与母亲分离。而人一旦离开现实界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总是渴望回去,追求缺失的母亲。这就产生了丧失或者缺乏的概念。缺乏必然产生欲望,因此现实界是欲望之源。人一旦离开现实界就进入镜像阶段,想象界或想象秩序就产生于镜像阶段。此时,儿童通过与镜中的他者的错认而形成自我。在拉康看来,自我总是在某个水平上的一个幻想,一个对于外部图像的认同。“想象界是一个欲望、想象与幻想的世界。它是在主体的个体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个体无意识往往在其间显露。”[8]想象界不受现实原则支配,而是遵循着视觉和虚幻的逻辑,具有个体无意识的色彩。想象界诞生于镜像阶段,但并不随镜像阶段的消失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至象征界并与之并存。婴儿随着语言的掌握而进入象征界或象征秩序。“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它是支配着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个体在其间通过语言同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人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客体化’,即作为‘主体’出现。”[8]象征界与语言、父法、文明、理性相连。无论是语言的领域还是律法的领域,都是静止、固定、明晰、有序的。因此,象征界的特点是明晰单调、整齐有序的。由此可见,主体性的确立是以本初的混沌未分的本我的一部分受到压抑为代价的,即主体的确立是以对现实界和想象界的压抑为代价的。因此,处于象征界的“我”已不再是“我”,而是一个被语言分离出来的漂浮的能指。受到语言系统压抑而形成的自我,虽然得到文明社会的认同,具有了社会性与文明性,约束了性与侵犯的本能却永远会有一种丧失、缺乏感;因为他在进入语言系统的同时丧失了被父法所压抑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永远留在了无法言说的前象征之域,即自我产生于其间的现实界和想象界的某些区域。前象征之域是主体永远向往却无法企及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每一个主体都是远离故乡的游子,而且每一个主体对于自己的故乡——前象征之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怀有一份莫名的乡愁;所以海德格尔才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
克里斯蒂娜的《小妖集市》所写的内容是一个童话故事。一对可爱的小姐妹每天黄昏都会听到来自峡谷的小妖的叫卖声。小妖所卖的水果品种多样,味道鲜美。姐姐莉姬抵制了诱惑,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家里,而妹妹萝拉却以自己的一绺秀发换取了水果,并饱餐了一顿才回到家里。妹妹从此陷入对小妖的水果的渴望之中不能自拔,但是她却再也听不到小妖的叫卖声。妹妹因强烈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而日渐憔悴,生命垂危。为了救妹妹,一直躲避小妖的姐姐勇敢地面对诱惑,经受了小妖的逗弄、取笑、撕打、揉捏,最终将解药——小妖的水果带给了妹妹,挽救了妹妹的生命。作为拉斐尔前派的诗人,克里斯蒂娜成功地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诱惑的主题,展现了主体确立之前的前象征之域的丰富魅惑,探索了理性规约下主体的心理状态。诗歌中的小妖似人非人,形态各异,举止离奇,神秘魅惑,他们的水果品种多样,味道鲜美,是欲望之源。小妖及其水果的这些特点与拉康所说的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前的现实界和想象界相似,是前象征之域的象征。在诗中,姐妹的家中生活平静、安详、有序,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她们像“茎上的花朵”“飘落的雪花”“象牙”一样纯洁、干净。“星星月亮看护着她们”,象征着神的佑护和理性的坚守;“猫头鹰忍住不飞”,就连蝙蝠也不再“扇动翅膀”,则暗示了秩序对于欲望、复杂多变等原始状态的压抑与规约,即象征界对于想象界与现实界的压抑与规约。姐妹家中的生活特点与拉康所描写的象征界雷同,是象征界的象征。妹妹禁不住小妖的诱惑而堕落就是诗人向前象征之域回归的一次“还乡”之旅。“当克里斯蒂娜在描写萝拉对‘那些快乐的昔日时光,永远无法重来的过去’,那些有‘小妖出没的峡谷’和‘邪恶古怪的水果商人’的日子的回忆时,一缕乡愁悄然飘入她的诗行。”[9]126通过这首《小妖集市》,诗人努力要拂去缠绕着自我的语言文化之网,竭力想要看清“我”来到象征界之前的模样。这一点,从《小妖集市》的最初名字《窥视小妖》(“A Peep at the Goblins”)也可见一斑。据说“克里斯蒂娜原本将这首诗定名为《窥视小妖》,在发表的时候接受其兄长加里布埃尔的建议而改成《小妖集市》”[10]。
三、小妖与水果——“故乡”的魅惑
前象征之域是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前的心理状态,是自我产生期间的现实界和想象界的某些区域。如前所述,现实界是欲望之源,而“想象界是形象和想象、欺骗和诱惑的世界”[11]。“拉康最初把想象这个词当作名词来使用可以追溯到1936年,从一开始这个术语就具有幻想、迷恋和诱惑的意思,尤其与自我和镜像之间的二元关系密切相关。”[11]因此,前象征之域充满欲望,无知无序,丰富奇异,神秘魅惑,险恶而富有颠覆性。《小妖集市》所描绘的小妖市场与前象征之域的上述特点基本吻合。因此可以说,小妖市场正是象征了自我心理的这个神秘的区域,是被象征界所压抑的“我”的故乡。
首先,“小妖”(goblin)一词本身就具有某种异端的、离奇的、邪恶的、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色彩。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goblin是一种传说中的类人邪恶生物,由精灵异变而成。Goblin的皮肤是暗绿色的,一般都长着长长的尖耳,红红的眼睛,矮小且难看,主要生活在黑暗深处的地下世界,有着独特的行动秩序与体系,个性贪婪、狡猾、卑劣、邪恶而且善于欺诈。Goblin是西方神话故事里的一种生物,东方语言并没有等同的概念,不同的作品对其翻译也各不相同,有“鬼怪”“地精”“妖”“妖魔”等。可见,goblin这个词本身就具有神秘、邪恶、黑暗的特点,与原始、自然、无意识相连,而与文明、理性相对。
其次,妖魔的来处、去处、形象、语言、举止等也都符合前象征之域的特点。在《小妖集市》中,他们来自神秘的峡谷,形象各异,举止离奇和语言怪异:“小妖们沿着峡谷走来。/一个拖着篮子,/一个端着盘子,/还有一个拽着金碟子,/……/有的长着一张猫脸,/有的摇着一条尾巴,/有的走起路来如老鼠一般,/有的像蜗牛一样慢爬,/有的像袋熊一样蹑足潜行,徘徊躲藏,/有的像蜜獾一样仓皇奔走,跌跌撞撞。”[12]6在这里,小妖都是以克里斯蒂娜喜欢的小动物形象出现的,如袋熊、老鼠、蜗牛等。这些动物形象在她的其他诗作里也经常出现,如《从屋到家》(“From House to Home”)、《夏娃》(“Eve”)、《少女之歌》(“Maiden Song”)、《如果老鼠会飞》(“If a Mouse Could Fly”)等。克里斯蒂娜和哥哥但丁·罗塞蒂(Dante Rossetti)都十分喜爱动物,家里饲养了袋鼠、浣熊等奇异的动物。童年的克里斯蒂娜将她外祖父位于白金汉郡的农舍视为地上乐园,在那里她有机会直接接触青蛙、老鼠、松鼠、蜗牛等小动物。[13]这种对动物的喜爱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动物身上看到了人类所丧失的天真。莱昂奈尔·史蒂文森认为,对于克里斯蒂娜而言,“这些小生灵代表着世俗之爱”[5]105。而且,小妖们形象各异,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既有人的特点又有兽的特点,这似乎暗合了人在进入文明秩序之前的原始的、自然的、人性与兽性混沌不分的特点。诗人在诗中不断地重复使用“一个”“有的”等词语,形象地描绘了小妖们各不相同的形象和怪诞离奇的举止行为。这些描写强调他们的个性与多样性;同时暗示了前象征之域的那种无序的、不整齐划一的,没有受到象征秩序或者说是文明规约的那种自然的、原始的状态。
最值得注意的是小妖们的语言。按照拉康的观点,人学会了说话就进入了象征界,成为一个受到父权压抑规约的主体,而永远告别了那个本来的圆满具足的“我”。因此,前象征之域是没有语言的。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那是一个记号(the semeotic)的世界,它是语言的物质层面,是被象征语言所压抑的身体欲动之流;它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或者在语言的矛盾、无意义、混乱和空缺之处,具有游戏与非逻辑的特性。[14]小妖们所说的似乎正接近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语言”:“摇尾巴的商人请她品尝,/那语调甜如蜜糖;/长着猫脸的那位呼噜呼噜地讨好;/走着鼠步的说了声欢迎;/甚至如蜗牛般爬行的也开了腔;/声如鹦鹉的更是叫得欢畅,/却把‘漂亮波莉’叫成了‘漂亮妖精’;/还有一个如鸟儿般啼鸣。”[12]8诗人并没有直接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只是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说了什么,仿佛是替我们翻译了他们的语言;而且似乎他们只能简单少量地运用语言,或者根本不能称其为语言,只能是一种表达,或者说他们是介于能用语言表达和不能用语言表达之间。他们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是甜蜜的语调、呼噜声、兴奋的叫声等语言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即朱丽叶·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符号界”的东西。而“符号界”和“象征界”是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对拉康“三界说”的改写,“符号界”大致相当于前象征之域,也就是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前的领域,所以小妖们使用的语言是前象征之域的语言。
小妖们来自峡谷,诗人并没有描述峡谷是怎样的,但是峡谷本身就暗示了小妖们来处的幽深、昏暗和神秘。在诗歌的最后,当莉姬坚持着并未屈服于小妖的诱惑时,他们的消失也是异常离奇的,离去的方式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去向哪里,似乎去了人所未知的神秘领域:“向四面八方、一哄而散,/没有留下一根一芽、甚至一枚果核;/有的翻滚着消失在土里,/有的潜入小溪,不见了踪迹/只留下一圈圈涟漪,/有的悄无声息地飘散在风里,/有的则隐没在远处。”[12]16可见,小妖来处和去处就是永远逃逸于语言之外的,无法言说、无法象征化的现实界。
小妖们所卖的水果极其丰富、甜美、神奇,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诗人在《小妖集市》开篇的前十四行里就一口气列举了不下十六种水果,跳过五行之后,诗人接着又列举了十三种水果。这不仅显示小妖的水果的丰富性,而且表现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和势不可挡的征服感。小妖的水果种类丰富,味道甜蜜,模样可爱,真是“既愉目又可口”。更神奇的是,这些水果无论产自何方,是什么种类,都在同一时间成熟,而且无论你吃多少这样的美味水果都不会感到满足。“它们比岩上的蜜还要甘甜,/比醉人的酒还要浓烈,/……/她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吃得再多又何曾厌腻?”[12]8诗人通过水果的丰富神奇暗示了前象征之域的魅惑与险恶。这里让人产生欲望,且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又使人产生疑虑和恐惧:“我们千万不要看那些小妖,/一定不要买他们的水果:/谁知道它们那饥渴的根/是长在怎样的土里?/……/我们不该让他们的东西迷住,/他们会伤害我们,/用他们恶意的礼物。”[12]6
总之,离奇怪异的小妖及其水果对于萝拉和莉姬,就如同神秘而魅惑的前象征之域之于自我。小妖及其水果丰富多彩,神秘离奇,充满魅惑与险恶,既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又具有难以抵挡的破坏力。
这种对前象征之域的向往与描写在英国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作家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如艾米丽·勃朗特(Emily Jane Bronte)的《呼啸山庄》、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无情的贝拉夫人》等。《呼啸山庄》中来历不明、野性暴力的希斯克利夫和粗劣阴暗、恐怖神秘的“呼啸山庄”都具有前象征之域的特点;而《无情的贝拉夫人》中的贝拉夫人则与《小妖集市》中的小妖相似,她居住在“妖精洞穴”里,给脆弱的骑士喂食神秘、美味、极具诱惑力的食物——甜蜜的根、野生的蜜以及天赐的露珠等。作家迷恋前象征之域,极力想要言说难以言说、不可言说的前象征之域,正是文学作品的不朽魅力所在。文学作品试图拂去语言之网,让我们看到自我的本真状态。
四、堕落与救赎——“还乡”与回归
既然自我是由镜中的他者的错误认同所形成的,那么自我就必然是一个分裂的自我,分裂成本我与超我,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神性,或者潜意识与意识。《小妖集市》中的萝拉和莉姬的家中就只有这亲密无间的姐妹两个,她们长相相似,但性情各异。她们并非现实中的真实的姐妹,而是主体性格的两个方面的象征。对自我的不同侧面的探索在克里斯蒂娜的许多诗中都有所表现,如《怨》(“Repining”)、《最低微的房间》(“The lowest Room”)、《三个修女》等。克里斯蒂娜虽然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是她的诗歌却一贯地呈现出一种在俗世与天堂间摇摆不定的态度。萝拉和莉姬也体现了她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她们可能是克里斯蒂娜本人性格的两个方面,即感性的和禁欲的”[5]105。诗中这样描写二者的亲密无间、和平共处:“她们头挨着头,像同一个窝巢里的两只鸽子”,“仿佛是同一根茎上的两朵花”,“她们脸对着脸,心贴着心,锁闭在同一个窝巢里”。[12]10姐妹俩看上去是如此和谐宁静,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但是,一方面,象征着前象征之域的充满着魅惑与颠覆性的“小妖”不断地向象征界侵入。无论晨昏,她们都能听到小妖精的叫卖声“来买吧,来买吧”。这充满诱惑的叫卖声不断侵入并干扰着秩序,破坏着和谐。另一方面,来自前象征之域的“我”又不断地想要回归自己的“故乡”,追求缺失的“母亲”,从而寻求一种自身的完整。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很可能导致自我的平衡状态的打破。面对小妖的诱惑,萝拉和莉姬的反应截然不同。萝拉侧耳细听、张望、流连直至最后的一丝约束也荡然无存,不惜用自己的贞洁——一绺秀发和一颗眼泪来换取欲望的满足,或者说是换取了与本我的一次亲近;而莉姬却捂着耳朵、闭着眼睛跑开了。饱餐了小妖的各种水果之后的萝拉依然沉浸在那美妙的幻想中,并决心第二天再去买些回来与姐姐共享;而莉姬却明智地告诫她小妖的危险,并提醒她曾经吃了小妖水果的珍宁的死亡。可是萝拉无法抗拒小妖及其水果的吸引力,无可挽回地向前象征之域沉沦下去。前象征之域的这种欲望的无法满足性和颠覆性,打破了姐妹和平宁静的生活,也就是自我的心理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一个心满意足,一个却心事重重;/一个为白昼的欢欣而低唱,/一个却渴盼着黑夜快些来临。/……/莉姬神情安详,/萝拉的心中却跳动着火焰。”[12]10
萝拉沉溺于前象征之域,日夜追寻。她诸事无心,无精打采,无法自拔,几近死亡,自我处于崩溃的边缘。处于崩溃边缘的失衡的自我,必然要重新寻求自我的平衡,那就是让萝拉脱离前象征之域而向象征界回归,而这个过程就是语言文化对前象征之域的压抑,在《小妖集市》中,就体现在莉姬的信念和理智对小妖诱惑的抵制和抗拒。挽救妹妹的坚定信念、对小妖邪恶低劣的动物性的理智判断以及对于珍宁结局的时刻警惕,让莉姬在小妖面前保持着镇静、贞洁、智慧;“莉姬站在那里,/如洪水中一朵白花金蕊的百合,——/如一块长着蓝色纹理的岩石。”[12]16诗人把莉姬比作“百合”与“岩石”,用白色、金色和蓝色代表她“神圣、纯洁”的品质,用百合代表着“纯洁与牺牲”[15],用岩石代表着坚定。正是内化在莉姬心里的这些品质让小妖的诱惑在她面前失去了效力。回到家里,莉姬坚持要萝拉“拥抱她,吞食她,啜饮她”,这样萝拉就“吸取了她苦涩的压抑的智慧”[9]131。在经历了类似中毒者的可怕的扭曲和象征性的死亡之后,萝拉得到了救赎,获得了重生,“快乐与痛苦都已成往事,/这究竟是死还是生?/是死中得生”[12]19。事实上,萝拉已经死去,重生的萝拉已经成为莉姬,也就是自我构成中的本我、自然、感性的一面已经死去。小妖所象征的前象征之域受到语言文化的压抑而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于是“我”就结束了自己的前象征之旅又回到象征界,回到姐妹宁静和谐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自我平衡和谐的心理状态。
“我”回到了象征界,言说主体的身份又牢固地确立起来,但是,“我”的确立是以对本我的压抑为代价的。此时的主体已经成为语言文化体系所认同的一个理想的“我”,一个漂浮的能指,维多利亚时代“房间里的天使”。她们再也听不到小妖的叫卖声,从此平静而有序地生活,生儿育女,代代相传。在全诗的结尾,诗人还特别强调了姐姐的不可或缺:“因为没有一位朋友能像姐姐/无论晴雨都如影陪伴;/在苦闷的时候替你解忧,/在迷途的时候带你回家,/在摔倒的时候将你扶起,/支持你,让你变得坚强。”[12]20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诗人的态度,即强调了人性的理性与信仰的重要性。人只有具有了信仰和理性,才能抵抗人生的各种诱惑与挫折,才不会迷失摔倒,才能获得永久的平静与幸福。这个结尾也体现了克里斯蒂娜诗歌一贯拥有的那种矛盾性。诗人在此虽然点明了象征界,即语言文化的规约的“我”才是主体发展的必然和人世幸福的归宿,但诗中浓墨重彩描绘的自然、感性的前象征之域却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强烈印象。正如沃德曼所说:“尽管在《小妖集市》中,幻想以受到压抑而告终,这首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集市景象的奢华。”[16]
五、结 语
从拉康的关于主体心理构成的理论的视角来看,《小妖集市》事实上是自我的一次还乡之旅,其中所描绘、探寻、呈现的就是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之前的杂乱无序、丰富多样、充满欲望的心理状态,以及主体是如何进入象征秩序成为一个文明理性的人。结合诗人其他关于描绘心理的诗歌,可以看出诗人逃脱现实的欲望,反映了诗人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诚然,正是因为人类有了语言、文化才使人类有别于自然万物,成为万物之灵,才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同时正是语言、文化使人类不可避免地远离了其自身的自然性,而异化成一个文明所要求的应该是的样子。我们离不开文明,可是我们又与生俱来地要亲近“本我”。如何平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以达到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正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不断探索的一个主题,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