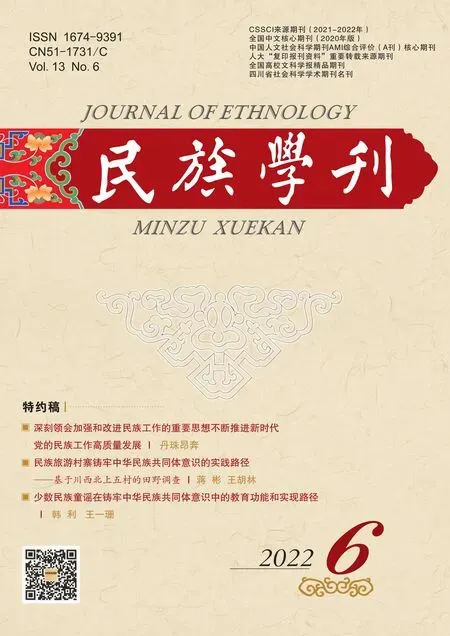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刘嘉颖 摩瑟磁火

一、史诗演述的社会效力:列维-斯特劳斯和雅柯布森的理论视角移用
对于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探索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及其《神话学》另外三卷中对口头艺术和仪式音乐化言语类型的互文理解。他在《生食与熟食》的绪言中指出了神话、语言和音乐的密切关系,认为神话连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符号系统——一面是音乐语言(musical language),另一面是清晰言语(articulate speech)”[12]。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神话在仪式中的结构再现是一种重要的沟通过程,它以集体可理解的精神意象确立了某种文化的象征力量或者意义来源。
基于巴西南比宽拉人(Nambikwara)的“灵异事件”、北美祖尼普韦布洛(Zuni Pueblo)男孩“被控巫术事件”和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萨满的“游巫”经历三个案例,列维—斯特劳斯建立了“巫师—病患—公众”三位一体的分析模型来阐释这种集体表征的效用。他谈到:
我们看到在巫术的效应中也显示出对巫术的相信。这种相信包含着三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首先是巫师对于自己法术效果的笃信,其次是病人或受害者对于巫师法力的信任,最后还有公众对巫术的相信与需要——这种相信和需要随时形成一种引力场,而巫师与中邪者(患者)之间的关系便在其间并从中得以确立[13]。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巫术的可信度和实践效力在于萨满对患者疾病的亲密体验与群体共识之间的双向互动[14]。如在对巴拿马库纳(Cuna)巫师为难产妇女举行分娩仪式的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将仪式专家唱诵的“巫歌”理解为神话叙事的再现和意义确立过程,并借用了精神分析学的“发泄”(abreaction)概念来解释库纳巫师擅于诱使和化解病人疼痛体验的“病理性思维”(pathological thought),从而表明萨满巫师的表演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行为”,而是对患者疾病的精神、社会和其他原因的重新体验。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有力说明了疗愈仪式是将个人的疾病、疼痛和痛苦经历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精神联系中,通过调适不同主体间的适当关系而得以确立仪式效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于巫术的信任是巫术效力达成的社会基础,也是象征体系构建的根本所在。
列维—斯特劳斯围绕神话叙事来理解萨满疗愈仪式的方法为我们理解广泛存在于我国民间的祖灵信仰、祭祖类巫祭仪式中的复杂语用关系,以及具体仪式实践所呈现的社会互动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具体来讲,萨满巫师的出神表演与彝族祭祖送灵仪式中的史诗演述有着相似特征,但史诗演述人并不会进入“萨满意识状态”(shamanic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来表现与超自然力量沟通和协商的行为。然而,在进入神话创造和毁灭的象征领域时,史诗演述人如萨满一样会强化自己的叙事和听众聆听叙事的体验。换言之,所有聆听史诗演述的公众都必须相信演述的内容和演述人的力量,从而参与至一种社会宇宙时空的建构过程。
如果我们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模型并作一定调整,那么可以看到史诗演述在遵循祭祖送灵仪式的仪轨和口头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其沟通力量的达成需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1.史诗演述人对于自己演述效果的笃信;
2.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对演述效果的相信与需要;
3.社会公众对史诗演述的期待与需要
这种三位一体的笃信、期待与需要也表现出史诗演述人所主导的文化翻译过程。在史诗演述中,关于勒俄本源、人类起源等叙事可以理解为对祭祖送灵仪式符号交流体系的“元语言”评论[15]或者语言内解释过程。赛维里(Severi,2014)[16]和希尔(Hill,2019)[17]分别在他们的研究中重新审视了雅柯布森[18]的翻译理论方法,指出文化翻译的三种过程:一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翻译本身,即通过其他语言对语言符号的解释;二是语言内解释(intra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即通过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对语言符号的解释;三是嬗变(transmutation),即通过非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的中间翻译。他们对南美洲印第安社会的研究探讨了叙事话语、音乐声音和视觉代码间的跨符号转换机制,说明了嬗变这一文化翻译过程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而本文将重点围绕语言内解释这一文化翻译现象,考察史诗演述人如何表现出对生者与逝者、个体与公众、人类与他者关系进行协商的能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勒俄的神话和起源叙事能够以其“听闻性”“可理解性”和“赛说娱乐性”在仪式中得到观众的即刻回应,其在毕摩专业的宗教言语类型和日常社会生活语用之间充当着文化内部的语言翻译,也因此建构了一个知识共享的文化渠道。
最后,由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开创的“讲述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研究方法也为我们洞察勒俄表演的社会文化形态带来了启发。讲述的民族志强调对“讲述事件”的分析,关注口头艺术形式在社会互动中的交流性质[19]。当前,民俗学学者们纷纷关注到表演者调度口头传统的知识库(repertoires)并根据仪式语境即兴创造听觉等感官交流体验的灵活性特点。而本项研究也旨在探讨史诗演述人在演述的实践场域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中是如何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确立其演述效力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勒俄演述的情境,还需要把一个社区的交际习惯作为整体语境来考察其中的语言互动及阐释规则。基于以上理论视野的启发,我们将在下文中解读到史诗演述如何伴随多向度的沟通达意过程来创造、指导和解释具体的仪式实践。
二、彝族史诗“勒俄”演述传统及其仪式表演语境




勒俄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与毕摩的言语艺术相得益彰,不仅体现了这种口头文类的传播价值,也充分展示出其文化翻译的重要性。可以说,勒俄演述是毕摩们的宗教知识与民众的世俗知识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结点。
三、彝族祭祖送灵仪式的文化背景

彝人认为若不为逝者举行超度活动,其灵魂就会无家可归,游荡无着,受苦受难,当然也就免不了有时会变作鬼怪来祸祟子孙。举行送灵大典可以为逝者之灵解除各种劳累病苦和从世间带去的各种业缘,使其轻松、愉快、健康地加入祖先的行列,得到安宁的生活,且能福佑子孙。所以,举行超度送灵活动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方面可藉此表达子孙们的孝心,寄托对逝者的思念,缅怀祖先;另一方面可以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向祖妣祈愿,祈求子孙人丁繁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在本次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们特别关注史诗演述如何以巧妙的指意过程揭开了一个灵魂得以升华而持续影响世间的宇宙世界。史诗演述的比赛互动在毕摩仪式中嵌入了关于物种间的转换过程(神话祖先和人类后裔、人类与动植物、男性与女性、血亲与姻亲、我族与他族),以及人类生命周期转换的叙事,从而在仪式中生动展现了人与万物的交流协商、空间想象和文化记忆的思维过程,并折射出彝族谱系观的道德意涵。这也提醒我们密切关注神话与巫祭行为在共同促成祭奠与安抚逝者灵魂这一项仪式工作时的关键作用。
四、祭祖送灵仪式中勒俄演述的个案分析
我们的田野点⑧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一个高寒村寨,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J乡S村。该寨共居住有寨民13户,分属4个家支。举行祭祖送灵大典的仪式男主人名叫阿伙某某,时年45岁,是家中独子,有4个姐姐嫁去了邻县雷波境内,将在仪式第二日代表姻亲方来参加仪式。阿伙家举行祭祖送灵仪式的目的是为阿伙某某已故父母、前妻和夭折女儿的灵魂进行超度。由于主人家经济条件困难,无力在祭祖仪式中自主举行勒俄演述比赛,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课题组决定予以资助,于是邀请了居住在美姑县佐戈依达乡温子觉村的曲比拉合(男,时年38岁)和美姑县拖木乡拖木村的吉则洛哈(男,时年45岁)两位勒俄演述艺人前来进行勒俄演述和赛说表演,并通知阿伙某某以其主人的名义向两位演述人进行了电话邀请。
(一)勒俄演述事件与仪式性互动
在为期三天两夜的祭祖送灵仪式中共进行了两场演述比赛,涉及口头论辩克智和广义的勒俄内容。第一场安排在仪式第一天的晚上主人家屋内举行“咒鬼”仪式环节中,待毕摩们诵完《驱鬼经》之后(当晚21点左右),按照惯例和主祭毕摩的时间安排,两位勒俄演述人便在赶来参加仪式的亲友及邻里的簇拥下开始进行勒俄演述比赛。曲比拉合代表主人家(坐在主人家火塘里侧的主人位),吉则洛哈代表姻亲家族(坐在火塘外侧的客人位),演述持续约2小时。
按照通行的程式,两位演述人开场时从本次演述发生的缘由说起,先介绍本次祭祖送灵仪式的主人及仪式的主祭毕摩,然后用克智互相酬问应答,其间多有自我标榜、互相讽喻之词,多个回合之后才进入正式的勒俄演述比赛,以双方轮流演述的方式进行。在从克智的知识论辩过渡到勒俄的时候,通晓这一程式的听众积极回应并影响、参与了演述文本创造的过程,如例1⑨所示:
例1:

(听众:干,上升到勒俄,进入勒俄。干得好,哎呀干快点,到路上方,克智多了点。势均力敌,许多都从来没有听到过呢。)

(曲比拉合:好的。你再来一段,路上方还是我先来,因为我是主人家。)

(听众:原来你两是互相谦让着来的。)
在例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听众能够领会表演的文本内容和话轮转换语境并予以回应,且在演述人的克智论辩文类趋于尾声并准备过渡至勒俄时,能够理解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以期望并助推演述人加快节奏进入“路上方”(即勒俄)环节。另外,由于听众插入的话语是轮至代表主人方的曲比拉合演述的小节尾声,曲比拉合随即采取了应对策略,根据语境进行了“协商”,转而告知客方代表吉则洛哈继续演述一节克智,从而表明按照仪轨应由他本人在下一轮来“主导”进入勒俄演述。紧接着,听众对讲述结构的调整也作出了“原来……”的评论回应。
在接下来两人进入勒俄演述前的尾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演述人也在话轮转换的过程中进行了文本内容的协商。主导方曲比拉合并没有急于进入勒俄,而是对勒俄进行了铺垫和补充说明:
例2:

(吉则洛哈:那就往前走嘛现在就?)

(曲比拉合:等会儿,我先来。)

承咦!
…………

结婚时是重谱系的嘛

送灵时是重勒俄的嘛
…………

超度送灵是由阿署阿俄兴

承咦!

为何由阿署阿俄兴起呢

远古时候尼扎山下孜阿迪勒一代生子不见父而亡

(听众:今夜干对了)

迪勒苏涅两代生子不见父而亡
(曲比拉合:哎—就是这样的呢)
…………

你家现在.祖灵竹篓呢送到木屋石屋中去

之后就会子孙繁衍子孙千百数云云

(听众:哦—哦—哦啊!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哎呀。虽然是个年轻人怎么,聪明得很的呢。好好好啊。)

(听众:哦,曲比家的小伙子呀主人家的你也说了,客人的你也说了,我会听。)

(曲比拉合:现在呢你就进入勒俄吧,你还是来一段史尔俄特。)

在进入勒俄环节后,曲比拉合共演述了“勒俄十九枝”中的八枝,内容包含“勒俄本源”“开天辟地”“天地演化”“修整天地”“创造生灵”“上界落种子”“武哲十二子”“人类起源”等,接着演述了“洪水泛滥”“天地婚姻”“族群繁衍”“糯恒赛变”“君长迁徙”等内容。而吉则洛哈也相应地演述了 “勒俄十九枝”中的八枝,内容包含“勒俄本源”“开天辟地”“天地演化”“上界落种子”“狐狸勒俄”“修整天地”“生灵演化”“作祭促进繁衍”等,还演述了被他们看作为“波帕”的“阿留举日”“支格阿龙”等内容。演述过程中,听众们与演述者密切互动,每表演完一段,听众们都不由赞叹,且有听众不时给两位演述者一些奖励。


例3:

褆比乍穆因此来发话

下界之中呢

长出什么草牛羊就吃什么草

上侧有牛羊

牛羊做牺牲

下侧有猪鸡

猪鸡做拴牲

杨树削白做神枝

如此作祭后

灵牌挂到屋上侧

杵臼安在屋下侧

如此做之后

上方喊父得父了

下方唤母得母了

如此之后呢

如今此时呢

顺便由此说到谱系去
例3源自吉则洛哈演述“寻父买父”尾声阶段的转录文本,穿插着传说中天界毕摩师祖昊毕史楚和下界毕摩始祖禔毕乍木的人物形象。演述以诗行为结构,长度从四到九个彝语音节不等。这段演述内容强调了为祖妣作祭的起源——包括具体的贡牲、植物用品和空间实践。鉴于彝族宇宙观建构了一个受昊天神灵启发的时空流转过程,这些对祖灵信仰实践的神话叙事也暗示了元始神话时代中,人类从“动物性”中分化开来而逐渐获得“文化”“语言”和“谱系”的思维过程。“喊父得父”“唤母得母”即是在这种调解人与非人之间的转换和分化状态中付诸实践的。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冗长的神话和起源叙事也是对“有声言语”的元语言阐释。
在双方进行多个回合的演述比赛之后,最后都谦虚地表示自己为输的一方,互相敬酒之后收场。尽管室外的天气非常寒冷,但一点也不影响勒俄演述者和听众们的热情,大家都凝神静听,有的听众还不时激动地发出赞叹之声,有的大呼精彩。如上述语境介绍,讲述“寻父买父”的神话起源是在祭祖仪式中演述勒俄时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与青棚下毕摩和主人“朵体”叙话内容互文,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呼应、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毕摩们的宗教知识与世俗的勒俄知识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结点,通过在同一场所进行的“朵体”和勒俄演述,毕摩、勒俄演述艺人与民众之间实现了真正的知识交流和分享。
勒俄演述完毕后,毕摩们继续在青棚下举行仪式,主要是诵读《献水分魂经》,将祖灵与其在世的子孙灵魂区分开。最后献酒给祖灵让其睡觉,当晚的仪式才算完成。仪式第三日将持续完成送灵仪式的后续环节,并最终将亡魂超度至前文所述的祖先世界。
(二)基于听觉的交流体验和知识共享
史诗演述的仪式化表演是传递和传播彝族人的传统知识、世界观、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祭祖仪式中的勒俄演述表明了彝族的谱系制度和文化记忆源于这些知识共享群体正在经历的当下、最近的过去和神话般的过去。在许多语境中,诸如“支格阿尔”“史尔俄特”这样的神话英雄人物在故事中的重要性不在于这些名字本身,而在于名字和故事被不断铭记,以及史诗演述比赛的声音被发出、听见和笃信的过程。
在这种由口头表演形成的赛说传统中,所有已“出师”的克智和勒俄演述艺人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口传心授训练和现场赛说演练。在每一次现场的口头表演中,他们需严格遵照一定的程式,先互相问候平安吉祥并就红白喜事的仪式语境来进行起源叙事、猜谜,从而在你追我赶、你来我往的赛说中比赛口才,进而才能进入勒俄演述,以及顺理成章地说到属于“布茨”的谱系范畴。经过比赛经验的积累和荣誉获得,某些演述艺人的名字会传到百里开外,从而也会收到更多的邀请,并逐渐建立自己和其家族的口碑。

前面的都没有说,后面的怎么能成立呢,最初没有地,也没有天,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之后由一些神人圣人来创造出来,没有树木没有水,原野没有云雀叫,森林没有獐鹿跳,什么也没有之后,全部都由神人圣人阿普阿萨,天神地祇一起创造出来安在天上,上界和下界一起管理才把这些创造出来,那么,现在你却私自要把它搅乱从中间隔开,只说谱系知识的话,不应该这样的嘛。
可见,吉则洛哈严守勒俄演述的程式,并暗示出演述仪轨的道德内涵。勒俄鲜活地描摹了一个宇宙从最初的混沌时代向天地分离时代的元始转换,叙述了世间生灵在昊天神明启示下的创造与改造过程,以及人性的不断建构、毁灭和重塑过程,另外还囊括了远古部落迁徙历史和强调亲属及性别关系的叙事。因此,诸如在丧礼和祭祖送灵仪式中的勒俄演述也说明了它为人类的起源、分化和社会建构(谱系)的稳定转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基于演说和诗唱的文化解释。
那么,史诗演述是如何呈现出仪式主人家及其家族亡灵对演述效果的相信与需要的呢?主祭毕摩阿尔可地这样说道:
老人去世时间太久以后就无人关注了是吧,一般做毕(家中举行各类仪式)时他们也不知道,终有一天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已经被超度了……在家进行热闹的赛说他们就可以听见。有人会说“啊呀你们家里不知怎么回事,赛说的人也在座。很热闹的样子,你去家里看看后代吧,不知在做什么。”……(赛说中)谈论勇士的故事,谈论高低贵贱的时候,他们(祖妣)就高兴了,毕摩也为他们指路,子孙们也为他们送行。
如阿尔毕摩所言,赛说暗示出一种声音的效力,它以热闹和论辩的社区氛围烘托出对家中逝者和地位跃升的祖妣的祭奠与记忆。在这些文化记忆中,我们会发现史诗演述人追忆他者生活的痕迹,对于吉则洛哈来说,每一次演述发出的声音也是自己已故父亲为其口传心授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仪式场域被记住并被唤起,也能够让参与仪式的公众触及到与先贤的情感和道德联系。基于这种听觉交流的文化效力,有关创世神话、祖先和谱系的故事都能够被广泛聆听、理解、传播,并且得到整个社区的共鸣:






五、结语
彝族诺苏支系史诗演述传统与其社会历史不可分割。史诗演述的仪式化表演是传递和传播诺苏人的传统知识、世界观、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史诗演述人的口头表演在毕摩主持的仪式中嵌入了关于物种间的转换过程(神话祖先和人类后裔、人类与动植物、男性与女性、血亲与姻亲、我族与他族),以及人类生命周期转换的叙事,从而在仪式中生动展示了人与万物的交流协商、空间想象的思维和文化记忆的过程。基于对祭祖送灵仪式中举行的勒俄演述内容和互动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史诗演述为人类的起源、分化和社会建构(谱系)的稳定转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基于演说和诗唱的文化解释,并嵌入了彝族谱系观的道德意涵。勒俄史诗包含了彝族的当下、历史和神话经验所集成的知识、智慧、记忆和情感,这种具有神秘力量的演述话语被视为具有调节我者与他者关系的互为主体性力量,也因此需要在一定的口头程式和仪式互动中来呈现与重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南美仪式的研究首先转向了以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29],开始出现一种更为平衡的方法来研究仪式专家的口头表演[30][31]。本文研究表明,基于对“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沟通过程分析,能够洞察出仪式诗唱和演述专家如何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动态转变与更新过程。如果我们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模型并作一定调整,可以发现史诗演述为祖灵信仰和巫祭行为提供了可理解和交流的感官维度,其在专业的宗教言语类型和日常生活语用之间搭建了一条重要的文化翻译渠道。这种三元一体的分析模式以及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的关联性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的社会价值。
注释:
①毕摩是彝族民间的宗教执业者,掌握彝文典籍,熟谙彝族宗教仪礼。“毕”为“诵读”之意,“摩”指长老、耆老,合之指诵读经典的长老。毕摩在创造、规范和整理彝族文字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史上的土司辖区,世俗层面的彝文教育也曾得到发展,特别是从民众经籍的抄后记中记载的传抄谱系来看,大部分都会将其源头追溯到某一家著名土司。参见摩瑟磁火《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经籍写本特征概述》(2016)。
②仪式话语是具有语言-音乐连续体特征的话语,指仪式专家在仪式场域中强有力的诵唱、吟诵、言说等复合性沟通话语。如杜梦甦(2012)从音乐性探究了这一话语特征,将凉山毕摩仪式表演中的经文唱诵风格分为“咏唱式”“吟唱式”“诵唱式”和“综合式”四类。

⑤彝族诺苏支系使用彝语北部方言,具体又分为两种次方言和五种土语。从语言、地域和服饰综合来讲,通常分为圣乍、以诺、所地三个区域。如果将勒俄传承情况作一个比较,所地地区的濒危状况更为明显,圣乍地区次之,以诺地区因为处于彝族诺苏支系分布的腹心地带,彝族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彝族文化氛围浓郁,所以其传承情况相对良好。
⑥有的则认为在祭祖送灵仪式上演述的为“花勒俄”,如下文提及的演述人吉则洛哈。
⑦“克斯”为彝语音译,“克”为“口”之义,“斯”为“谈话”、“聊天”之义,合之指相互酬问应答,引申指在婚礼等场合进行的赛说。
⑧本次田野调查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子课题“彝族史诗《勒俄》(四川省美姑县)”资助(主持人:摩瑟磁火);第一作者刘嘉颖时为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在四川凉山州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并协助课题组完成了勒俄演述的摄录工作。文章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2020SQN25),在后期田野回访和材料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
⑨有“括号”和斜体字标记的部分为转录文本中的交际话语,其余为勒俄演述内容。